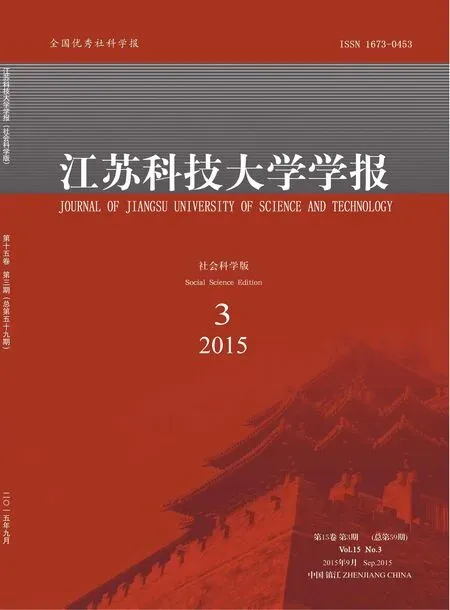“魏晋风度”表现形式刍议
方坚伟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40)
“魏晋风度”表现形式刍议
方坚伟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40)
“魏晋风度”是中古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褒扬。“魏晋风度”是名士服药集体迷失的生活表达方式,“超脱玄虚”是“魏晋风度”的人格表现特征,“通侻清远”则是“魏晋风度”的文风特点。这种文风至晋宋彻底完成过渡,同时也意味着“魏晋风度”的终结。
“魏晋风度”;名士服药;“超脱玄虚”;“通侻清远”
“魏晋风度”是中古文学史上一个人格美学范畴,是当时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并不能直接表明魏晋文学的风格特征。“魏晋风度”的形成有其时代特殊性,名士服药后随之而来的荒诞率性,是构成“魏晋风度”特有的背景,这是区别古代任何时期的文人集体行为。这种行为被鲁迅先生概括为“魏晋风度”之后,就为现当代学者文人所褒扬。实际上,“魏晋风度”是一个被人为无限拔高的集体美誉标签,其形成背景与对后人的迷惑之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魏晋风度”与“通侻清远”的文风是相一致的,这种文风随着“魏晋风度”的结束而终结。
一、名士服药:“魏晋风度”的生活表达
《世说新语·夙惠》曰:“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魏武知之,即遣还。”[1]322这条材料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一个问题,作为被后人视为服药祖师的何晏七岁即已表现出惊人智慧,若将其服药简单归结为企求长生恐怕说不过去。陆机《长歌行》曰:“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2]阮籍《咏怀》曰:“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3]王瑶先生便认为:“魏晋人士,尽管有相信神仙不死的,也有不相信的,如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4]108与何晏同样少年早慧的王弼、夏侯玄等魏晋名士,都知道服散稍有不慎便会痈疽发背或脊肉烂溃。这些平时行步顾影的魏晋美男,未必肯为长生不老而自残。
魏晋士人服药与美姿容之间有密切关系。王瑶先生认为:“服药后是有现实效力的,那就是他的面色比较红润了,精神刺激得比较健旺了,这都可以视为‘长寿’的一种象征。”[4]114这种爱美的风气,且是倾向于女性美而非阳刚美的氛围,在魏晋时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就连曹操都是舍英雄之美誉而取仪容之美称。《世说新语·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1]333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建安二十一年时曹操被封为魏王,七月匈奴来朝后,同年崔琰便被杀。崔琰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如《世说新语》所言不得而知,至少说明当时上层社会关注仪容可谓到了自恋程度。《晋书·王衍传》称赞王衍曰:“神情明秀,风姿祥雅。”[5]1235《南史·谢晦传》称誉谢晦曰:“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6]《世说新语·容止》载时人形容王恭的身姿容貌是“濯濯如春月柳”。从这些文献资料的遣词用语来看,根本就是在欣赏女性之美,哪里看得出阳刚之气。既然社会崇尚花样男人,那么以何晏为首的名门望族施粉、着妇人之服在当时便是很正常的了。《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对何晏的评价:“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7]《宋书·五行志》曰:“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8]886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就连服药都会引发时人仿效而成为一种潮流。这些或许就是魏晋之所以引人入胜之处。《世说新语·言语》十四刘孝标注曰:“秦丞相《寒食散论》曰:‘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1]40这也成了何晏是魏晋士人服药始作俑者的明证。可以肯定的是,服药本来是一件危险事,但确实有一定美容和养生功效,这就像现代整容一般,风险与美貌并存,所以魏晋服药之风只能是贵族阶层所能享受的,且迅速风靡上流社会。
美姿容是养生的外在表现,服药的最大好处是使人神清气爽,旁人视之则风姿特秀,所以后世对魏晋人的印象是褒衣博带、飘逸如云,正如鲁迅所说:“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9]508《与皇甫隆令》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10]28曹操欣赏皇甫隆体力不衰及颜色和悦,正是魏晋人所企羡的,这也是道教的一种人生理想。《抱朴子·对俗》曰:“人道当食甘旨,服轻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11]若以此标准来衡量魏晋士人,下面两点就不难理解了:一是服药(寒食散)之后,在隆冬腊月时节散发过程裸袒食冰块。《晋书·皇甫谧传》就记载皇甫谧服药后自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5]1415皇甫谧服药的苦状与何晏喜称“神明开朗”可谓天渊之别。从散发后果来看,这实际就是葛洪所说“寒温风湿不能伤”要达到的效果。但并不是每个服药的人都能掌握寒食散的药性,寒食散本来与道教的炼丹就有密切关系,目的是能让人内治百病,外安万神,延年益寿。二是服药时辅以“施行导引”,此为道教至高无上的养生之术,也可以看出魏晋人服药与道教的要求一样,需配以“导引”之法。《史记·留侯世家》就有张良“学辟谷,导引轻身”的记载。葛兆光先生就认为:“‘导’与‘引’,实际上是一种深呼吸健身法与体操健身法。”[12]药物是用来辅助保持运行元气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服药后要行走,魏晋士人服药后便有“行散”一说。《世说新语·文学》曰:“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1]149服药实为道教养生之术,至于长生甚至仙化的问题,魏晋人更多是借诗歌来逃避现实问题。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4]104所以,魏晋人服药更多的是追求生命的维度,并非追求生命的长度。
清谈与服药,都是魏晋士族的生活方式,服药是自道教而来的,清谈的理论本源于老庄之学,而道教又借用了许多道家思想。魏晋清谈名士有服药的,也有不服药的,但清谈名士中,能称得上论坛领袖的却多有服药的。《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1]106与之同样貌美令时人倾倒的夏侯玄、王弼,都为当时清谈高手,也是服药之人。正始间,何晏与王弼曾就圣人有情无情展开了争论。竹林七贤中嵇康服药,嵇康也是清谈名家之一,只不过不如何晏、王衍、王导等人出身显赫。《晋书·嵇康传》曰:“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5]1369《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偏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5]2101魏晋清谈主要涉及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圣人有情无情论及才性四本等内容,品评人物是魏晋清谈一个常见论题,由才性四本衍生而来。品评人物包含了人的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品鉴内容,但魏晋人物品评已由汉末的政治品评转向了审美与鉴赏,故有时仪容比起风度更引人注目。《世说新语·容止》曰:“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1]337王济已经是才华出众一表人才了,但一见卫玠,不是佩服其玄谈的理论水平,而是为其容颜所折服。魏晋士人追求貌美,服药有助于美姿容,貌丑形秽的人谈玄水平即使再高也始终进不了主流圈子,像左思只是仿效潘岳的样子到外面逛逛而已,便引来“群妪共乱唾之”,更别说一群人会耐心坐下来听他旁征博引、高谈阔论了。服药有助于清谈,固精凝神,使人思理缜密,言说流利,何晏便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1]40神明开朗,当指精神的舒畅,魏晋清谈是一项思辨性强、耗体力的思维活动。卫玠问乐广何为梦,因苦思该问题而“经日不得,遂成病”。另《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尊崇老庄仰慕道家学说的人请教王衍,王衍婉拒的原因是“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只能以身体不适回避。何晏自觉神明开朗,五石散对其谈玄实是大有裨益的。这种效果也恰恰是“魏晋风度”所必需。
二、超脱玄虚:“魏晋风度”的人格表现
汉魏之际可算得是中国文化史上世风为之一变的时代,由经明行修变为通侻清远则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具有美学意象的“魏晋风度”是一个为广大文人学者所膜拜的标签。汤用彤先生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超脱者重玄虚。”[13]35这是一个由重视外在世界向追问内在境界的转变,也是一次从遵循道德人生向诗意人生嬗变的进程,其丝缕相牵,并非偶然。汉初至武帝时的士风昂扬,有囊括宇宙、笔挫万端、直露胸臆的气势,这可从汉赋创作的铺排纵横感受到汉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司马相如《上林赋》曰:“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勃)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14]104同样,班固于《两都赋》对明帝的德治武功进行颂扬:“内抚诸夏,外接百蛮。”[14]20汉赋固然有沟通天人之壮丽,才气横溢,但从汉人极具描摹之能来看,也让人看到了汉代学风的日渐繁杂,其崩离繁琐也已显山露水。每个时代的文风与其学风基本是相适应的,汉学的渊综广博与文风的铺彩摛文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汉书·艺文志》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5]《晋纪总论》批评汉学曰:“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14]1499要求汉学“通变”,实际上也是当时学风凝滞、呆板的反映。至汉末,这种呼声也就自然为以简驭繁、举一统万的学风所取代,中经汉末魏初之苍健悲凉,终归于魏晋之通侻清远。
大凡一代世风之崩溃常伴随着新的世风的兴起。当东汉后期的天人感应神学被赶下神坛之时,所谓的“魏晋风度”也就顺理成章的为人们所慢慢熟悉。当人们长期受压于仁义道德之后,发现原来在老庄的守静坐忘、无为自然的境界里有一个自我的形象在那里时,表现出来的是集体反思进而群体迷醉,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清谈与服药便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魏晋风度”的内涵是通侻清远,但其表现行为却是多样的,魏晋名士服药纵酒、散发裸袒,却也风神超逸、不滞于物;他们狂傲不羁、荒诞忿狷,而又长啸山林、雅量十方。“魏晋风度”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魏晋名士的放达、真性情。
嵇康《释私论》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16]任自然的魏晋名士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遵名教而任自然派,何晏、卫玠、谢安、山涛等人可归此派;一派以竹林七贤的嵇康为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派,阮籍、刘伶、张季鹰等人都可归入此派。前一派的“魏晋风度”主要是服药美姿容以养生,清谈老庄以怡性。《世说新语·文学》曰:“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1]107这一派由于家底殷实,属于既得利益集团,遵名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魏晋风度”在他们身上更近神仙道教,在未涉及政治斗争的前提下,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逍遥派。《晋书·谢安传》曰:“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濬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5]2072对谢氏大族的人来说,无处世意或许有些矜持的成分,他们寄情山水多出于修身养性的需要,该当官的还是当官,不当官的也不愁生活会否困顿。《高僧传·支遁传》言支遁由京师还东山时就曰:“昔四翁赴汉,干木蕃魏,皆出处有由,默语适会。今德非昔人,动静乖理。游魂禁省,鼓言帝侧,将困非据,何能有为。”[10]1716四翁中就包括谢安。“魏晋风度”于这一派而言,高逸之中多少带有些虚像,像石崇一方面骄奢汰侈,另一方面又说“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更直言“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世说新语·汰侈》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1]467石崇当时宴请的是王导和王敦,石崇因为王敦不肯喝酒已连续斩了三人,面对石崇的残酷冷血行径,王敦依然不为所动,王导劝之,王敦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实令人发指。王敦、石崇虽然不能算“魏晋风度”的典型,但至少说明魏晋士人有潇洒风雅的一面,也有冷酷阴鸷的一面。这正是“服食后药性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变得暴躁、狂傲,所以有许多忿悁得不大近情理的事情”[4]122。
后一派也可称荒诞派,虽然后人多认为他们长啸山林、纵酒狂歌更代表“魏晋风度”之美学内涵,但他们的内心是痛苦、压抑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以反常的风度来对抗现实,渲泄内心的抑郁与愤懑。《世说新语·任诞》曰:“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1]390阮籍的这种表现已非常人所能。又《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邓粲《晋纪》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1]393如果说前面我们可以理解阮籍反应的话,那么《晋纪》所记阮籍之风度只能说是有违常理了。这些竹林名士的言语细嚼起来似乎有时表里不一。嵇康于《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14]118《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曰:“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10另据该条注引《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1]10观此语当不假,然嵇康实有臧否人物、简傲难驯之性。这就是名士矛盾之处,处于政权过渡时期的文人,其处境进退两难,往往坚守风度与生存是难以两全的。《康别传》认为嵇康的性格是“美范”“胜业”,说明当时的社会是赞赏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爱憎不显于颜的。后世文人多视魏晋士人简傲、任诞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特点,其实这正是所有文人的通病,是内心与现实之间产生的不平则鸣。盖古今文人均有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偏爱风流及指点是非的习气。
现在看来,“魏晋风度”这一概念毋庸置疑应该是褒义的。在文人学者眼里,“魏晋风度”代表着率真脱俗、潇洒自然、不拘礼法、超脱任性的人生态度,这也象征着魏晋士人的精神境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魏晋始,“文人无行”的批评也成为一种普遍声音,而且这远远早于对“魏晋风度”的褒扬。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讲稿中提出了“魏晋风度”,但并未作具体界定,之后这一概念便被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广泛接受并使用。同时,他也在《辩“文人无行”》中说:“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9]393若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魏晋名士们风度翩翩的同时又是“无行”之士了?对于“文人无行”,曹丕《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14]925杨遵彦《文德论》曰:“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17]《颜氏家训·文章》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至于帝王,亦或未免。”[18]除曹丕之论外,《文德论》与《颜氏家训》主要是就文人与文学创作要合乎德行、道统而言。魏晋士人文章传世不算多,但他们的行为却是批评文人无行者所涵盖的范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文章名世的文人郁结于胸,针砭时弊,是继承了发愤著书的传统。至于魏晋文人也多为士人,鲁迅先生所言之“轻薄、浮躁、酗酒”,正是魏晋士人的鲜明特点。“文人无行”之说兴于魏晋六朝实在是有其现实文化土壤的。《世说新语·言语》曰:“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1]43同样,《言语》曰:“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1]56又《晋书》赞美潘岳华丽文辞曰:“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俦于贾谊,先达方之士衡。”[5]1525同时又指出其低劣的人格:“然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乾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5]1525像此类风采超逸却审时附趋的名士,在魏晋时期不在少数。对于“魏晋风度”与“文人无行”,笔者将撰文另作研究,在这里举若干材料主要是说明一个问题:在文人学者眼里,“魏晋风度”是迷人的,但实际上也不乏迷惑人之处。这是一个被世人无限拔高的集体美誉标签。从这个角度说,“魏晋风度”实为特殊时代矛盾人格的表现。
在这种世风底下,此时的文风也相应的由魏晋通侻清远向晋宋浮华繁缛转变,为晋宋后追求形式美做了历史的铺垫。这是“魏晋风度”在文学创作上的同步消涨。
三、通侻清远:“魏晋风度”的文风特点
关于“魏晋风度”的定义,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未定义该概念,其内涵也众说纷纭。“魏晋风度”虽然适用于形容魏晋名士,但并不能直接概括魏晋文学。“通侻清远”不仅是魏晋士族之人格特征,同时也是魏晋文风之特点。
前面我们已论及服药、清谈作为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主要活动,是体现“魏晋风度”的重要活动内容。清谈过程相互辩难要求言简意赅,品鉴讲究瞻形得神。魏晋名士虽清谈以阐发老庄之学为主,注经却仍有儒学经典,如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也兼治《论语》。人们一谈到“魏晋风度”时,总感觉这些清谈名士与儒学是绝缘的,殊不知何、王两人却是以注儒家经典传世。王弼虽为玄学之宗,然其儒学根底深厚,汤用彤先生便认为:“多知王弼好老,发挥道家之学,而少悉其固未尝非圣离经。其生平为学,可谓纯宗老氏,实则亦极重儒教。其解《老》虽精,然苦心创见,实不如注《易》之绝伦也。”[13]76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魏晋玄学与儒学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一种关系,而只是一种间歇性的此消彼涨的过程,只是汉末魏初注解儒家经典进入阶段性式微而已。这从《魏书·王肃传》引《魏略》一书中可看出当时儒生的锐减。其曰:“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麄疏,无以教弟子……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7]420儒学在玄学冲击下,魏晋名士注经已非汉人之穷经皓首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的繁琐刻板了,取而代之的是何晏、王弼等清谈名士注经讲究思辨、推演义理,虽然“治学的精神与汉人不同,但其学正是由汉代经术变迁而来,则有迹可寻,并非偶然”[4]23。何、王等人是循着古文经学的路子,这种学风对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曹道衡先生便认为:“古文经学却使文学得到发展,古文经学的兴起,使人们的思想变得活跃,扬雄、张衡、马融都是文学上卓有贡献的人,也正是古文家如桓谭等不守礼法,喜爱俗乐,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19]相比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不拘泥于章句,尚通大义,这在治学的取法上已经与魏晋玄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了。故陈柱说:“西汉儒者求通大义,故多工文;东汉儒者局促于训诂,故尠能文者。”[20]玄学家阐发儒学经典,必然与经学家治学讲究穷经、训诂的方法有所区别。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之学术虽然表面上看是取径不同,但内在学理其实是经脉相接,两汉经学蜕变而为玄学,玄学亦讲通大义,这种学风映照到文学上,便讲求言不尽意,通侻清远。
通侻清远本是形容“魏晋风度”,是概括士人的个性气质。在中国人眼里,人的精神主要在于气,文章也在于气,通侻清远的本质实际上仍然在于气,这在魏晋大量谈论气与文之关系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21]60。赵壹《非草书》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10]828《颜氏家训·文章篇》亦云:“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18]268建安文学重风骨,同样强调气的重要性。曹丕《与吴质书》云:“仲宣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18]1088曹丕评王粲体弱并非指其身体,而是论其文章。钟嵘《诗品》亦言其“文秀而质羸”,仍然是指文章之气力不足的问题。对于风骨,刘勰也是以气论之,《文心雕龙·风骨》曰:“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17]513建安文学高扬风骨,其内涵是追求通侻清远,这从本质上是排斥繁辞丽藻的。辞繁则力求物具,藻丽则言外无物,但这恰恰在曹丕、曹植的诗文里已渐呈丽藻之势,只是二人才气高逸,以气统文,不致于风骨尽散。这就是所谓得失一寸间,二曹很好的控制了文气与辞藻之间的关系。
我们讲“魏晋风度”,多以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王羲之等魏末晋初的名士为代表,很少将三曹作为“魏晋风度”的典型拿出来说。《世说新语》载魏武事迹的有20条,魏文事迹的有10条,但事不关高雅脱俗,关于曹植的事迹则未见片言只语。但是三曹在魏晋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却是引领风骚的。这与他们在政治上的领袖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文心雕龙·时序》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7]673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8]1778沈约认为曹氏文学是文质彬彬的典型,但是作为建安文学的特点来说,“咸蓄盛藻”却意味着在曹操慷慨悲凉的调子之外正酝酿着新变。这种变化在魏晋玄风日炽的大环境下,只是一股潜流尚未形成主流。钟嵘《诗品序》评价曹植诗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22]实际上就非常中肯地揭示了这种流变的线索,晋宋文风的浮华繁缛正是脱离了风骨,沿着曹植的辞采华茂路子,在魏晋士人注重“交会”的浮华学风下最后进入了晋宋文学的浮华繁缛,吹响了南朝文学追求美文创作的号角。这实与曹植有密切关系。
[1]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金涛声.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71.
[3]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9.
[4]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
[7]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292.
[8] 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12]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7.
[1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 萧统.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1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23.
[16]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4.
[1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
[1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237.
[19]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4.
[20] 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5.
[2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2] 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
(责任编辑:喻世华)
Discussion on Form of Wei-Jin Demeanor
FANGJian wei
(Departm net of Chinese and Culture,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China)
Wei-jin demeanor,an im portant concept of medieval literature,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praise of many scholars as an ethos of the times.Wei-jin dynasty demeanor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lost life of the drug-addicted celebrities.Its character performance is unconventional and m ysterious.Its style of writing is fresh and elegant.This style ended in the Jin-Song dynasty and that im plies the end of the Wei-jin demeanor.
Wei-j in demeanor;drug-addicted celebrities;unconventional and mystery;fresh and elegant
I206.2文献标示码:A
1673-0453(2015)03-0016-06
2015-06-10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2013年度院级科研项目成果(2013 K01)
方坚伟(1980—),男,广东惠来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