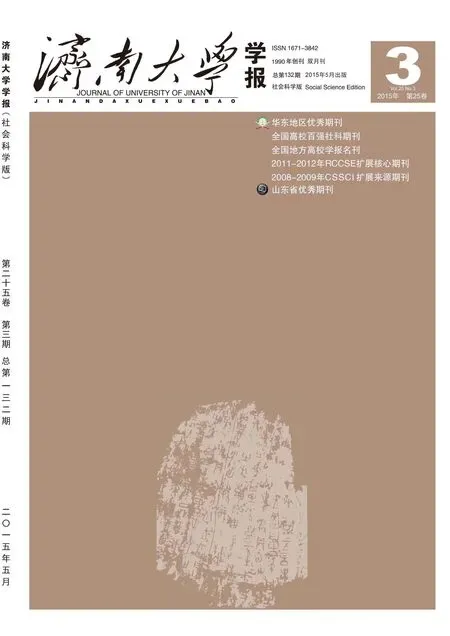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丑意识及其对“自然派”崇高风格的消解
张中锋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丑意识及其对“自然派”崇高风格的消解
张中锋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如果说审美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那么审丑的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主义。因此,与审美更多关注人的外在征服自然的理性能力相比,审丑则更多关注人自身的非理性能力,即人的本能欲望、病态人格,以及生命被异化等现象。总的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审丑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生命欲望的接受与认可;二是对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等生命非正常现象的揭示;三是对虚无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生命被异化现象加以批判。作者的审丑意识不但使其创作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对当时占主流的“自然派”所体现出来的崇高风格,亦起到消解作用。
审丑意识;本能欲望;人格扭曲与心理变态;虚无主义;崇高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论者认为这和俄罗斯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关。因此,强调人的价值,关注弱势群体,针砭社会弊病,抨击官方教会所存在的蒙昧现象,建立现代性社会,成为这时期文学的主题,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够融入欧洲并具有世界性的标志。这一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以“自然派”为主的文学创作上,并由此形成了弘扬理性精神的崇高风格。“自然派”是19世纪40年代初在俄国形成的以别林斯基美学思想为指导、以果戈理创作为方向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通常被视作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但是,“自然派”在借助理性张扬人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对人性做更深的探索,即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和超理性,因此,该文学流派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后期,许多作家在创作美学上试图有所改变,而在这一点上成效比较突出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他在创作中引进了新的美学风格,这便是审丑。
“审丑”这一近年来才流行的美学概念,逐渐得到美学界的认可,并被视作与“优美”“崇高”“荒诞”等相并列的美学范畴。现代社会伴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个体价值、肯定自我需要,开始看到个人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近代启蒙理性的局限性,逐渐接受人的心理世界的复杂性,像病态心理、变态心理,以及人格扭曲等,都被视作主体性的客观存在。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作家们审丑意识的觉醒,这在陀氏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美不再是崇高的、优美的东西,“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的美不只是可怕的东西,而且也是神秘的东西”[1](P114)。既然美是“可怕的”“神秘的”,是魔鬼与上帝的斗争,那么这种美就不再是赏心悦目的“美”,而只能是“丑”。陀氏在创作中就表现出浓重的审丑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生命欲望的接受与认可;二是对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等生命非正常现象的揭示;三是对虚无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生命被异化现象加以批判。审丑意识不但给作者带来创作上的巨大成功,而且对当时占主流的“自然派”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崇高风格,亦起到消解作用,从而深化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自然生命欲望的接受与认可
认为自然为善还是为恶,是东西方自然观的本质差别,也是传统伦理观和现代伦理观的分野。由于东方或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差,人和自然还处在一种主客不辨、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状态,其自然观当然是善的。这种自然为善的观念既表现了人对自然认识的浅显,也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妥协;而西方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达,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较强,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把自然当成对象来看待,就像培根所说的要把自然放在实验台上,强迫它回答出人类所提出的问题。这样人们就把自然本身的意志,转变为属人的意志,这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所指出的:“科学褫夺了大自然的种种人的形态,将一个中性的、异己的、茫茫无垠而又力量无限的宇宙呈现在他面前,以适合他那人所具有的目的。”[2](P34-35)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除魅的自然当然就变成恶的了。面对自然的恶,狄德罗曾对作家发出质问:“诗人需要的是什么?是未经雕琢的自然,还是加工过的自然?是平静的自然,还是动荡的自然?……诗人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3](P371)也许只有异己的、恐怖的自然才是自然本身的真正面目。如果说审美是借助人的理性力量以征服外在的自然,那么审丑则开始关注人的自身力量,特别是人身上属于非理性的自然力量,因此,当说自然为恶时,是对人自身的正视,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关注与肯定,是人性在更深的层面上获得解放。这正如康德所说:“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则是从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作品。”[4](P68)康德的这句话也点明了审丑的本质,这便是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和对人性的更深刻解放,因为不可否认,欲望满足也是人性解放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传统理性和启蒙理性对人的感性抑制已经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人性的认识和对个性的创造发展。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欲望”已经不是一般伦理意义的“丑”,而是审丑。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俄罗斯,随着19世纪西方文化影响的加强,俄罗斯人的自然观开始由善趋向恶。如果说在那些“自然派”为主的小说家那里,他们虽已意识到了自然的恶,但他们还留恋于东方人关于自然为善的观念,还停留在优美或崇高阶段,而到了陀氏这里则把自然完全看成是恶的,并且把恶放到了本体地位。如果说陀氏在他的成名作《穷人》中还在宣扬男女之间的高尚爱情,带有崇高色彩的话,那么在紧接而来的《双重人格》中则开始揭示人性的卑琐和丑恶,开始展露出人性的另一面,对此别林斯基开始对陀氏感到失望,可以说此时的别林斯基那崇尚审美的文艺观,已经不再能适应陀氏的审丑美学观,并导致后来俩人的彻底决裂。黑格尔的理性至上的崇高美,一方面成就了别林斯基对同样处在崇高美风格的俄国的“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出适时的评价,并形成审美批评文风,领时代风骚,但理性的美丽光环却遮住了别林斯基对非理性世界的窥探,把陀氏更为深刻的心理描写看成是对精神病现象的关注,这一误判使他只承认美而不承认丑,或者仅仅把丑视为衬托美,是荣耀理性的消极材料,因此最终导致他和陀氏友谊的破裂。陀氏剥去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罩在人身上的美丽光环,还原了人的本来面目,这虽然让人难堪,但却是真实的,是人对理性枷锁的重新摆脱。历史证明,对人性的摧残有时并不是以丑化人的方式出现的,而恰恰是以赞美人的方式出现的,通过把人抬高到君子、圣贤、英雄的地步,来异化人、贬低人,因此,当作家们开始“贬低”人时,反倒是对人再次重视与尊重的开始,特别是在消解神圣亵渎崇高的时代,这真是历史的吊诡。
陀氏对人性丑的描写,是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启发”,在陀氏看来,把建立在精确计算基础上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当作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改良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样的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不是人的社会,
而只能是“蚁穴”,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陀氏为反击《怎么办》而作的《地下室手记》,在作品的一开始,作为主人公的“地下室人”就说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5](P171)“要知道人是愚蠢的,少有的愚蠢。也就是说,他虽然根本不愚蠢,但是却非常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到了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忘恩负义的人了。”[5](P198-199)“由于文明的发展,如果说人不是因此而变得更加嗜血成性的话,起码较之过去在嗜血成性上变得更恶劣,更可憎了。”[5](P197)甚至地下室人把自己不当成人,而是当成“耗子”,对人如此“贬低”,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可是这种“贬低”却是对以往把人理性化崇高化的消解,是向人本原的复归。人性不但如此“败坏”,而且对弱者还充满了虐待和折磨,在《罪与罚》中,作品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梦到人们折磨一匹小马,来反映人的恃强凌弱的虐待本性。一匹小马,拉动满载一大车的人已非常不易,但乘车的人们非要让它跑起来,跑不动就用鞭子打,鞭子不行就用铁棍子,直至把马打死。对动物如此,对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讲述的一个将军只因为一个七岁的孩子不小心用石头把他的一只狗打瘸,便下令他的群狗把小男孩撕碎。还有一位做父母的,生了女儿不疼爱抚养,把她关进厕所,在冰天雪地里挨冻挨饿,还往她身上泼屎尿。特别有意思的是作品中的老卡拉马佐夫有四个儿子,其中竟有三个儿子想把父亲杀掉。人不但残忍,而且还自私和贪婪,在《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中,主人公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一个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毫不掩饰:“我没有理想,也不想有理想,我从来也没有感到需要理想。没有理想照样能在世上逍遥自在地生活……”[6](P346-347)荒淫好色的老卡拉马佐夫对其幼子说:“现在我总还算是个汉子,只有五十五岁,但是我愿意再做二十年的汉子,等到老了,我会显得丑陋可厌,她们不会甘愿到我这里来的,到那时候我就需要钱了。……过龌龊生活比较甜蜜;大家咒骂它,可是谁都在过这种生活,只不过人家是偷偷地,而我是公开的。”[1](P191)《少年》中的主人公多尔戈鲁基说:“最困难的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7](P69)虽然在陀氏的创作里对人性恶的表现还有很多,但仅仅这几例就对人性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更为可气的是,陀氏对人性恶的表现是冷静的、客观的,并没有表现出传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惯常表现的义愤态度,那么陀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陀氏对人之欲望的客观呈现有着自己对人性的独到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人性恶的描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把人身上美丽光环剥离得最彻底的一次。人“为什么一定要做个高尚的人”?这是多么大胆的质问,也是多么惊心动魄的质问,是生命重要还是道德重要,更何况我们所遵从的是什么样的道德?传统的封建礼教把人束缚在虚伪的宗教教条里,启蒙的宏大叙事把人捆绑在“自然规律”的战车上,而作为生活主体和历史主体的“人”,以及作为生命欲望的活生生的“人”,却被迫失踪了,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呵!难怪陀氏对人性恶和人性丑等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因为他看到了生命本能需要的强大和合理性,因此,表面上看陀氏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他对人的充分发现,对人的本能的充分肯定,使人获得了自启蒙运动之后的第二次解放,因而可以说陀氏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是最为深刻地领会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就是张扬主体性,进而发扬人的创造性。是呵,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贫富差距和新的不平等,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效率优先观念和拜金主义风气绞杀着人的个性,制造着新的平庸和新的压抑,时代似乎需要新的道德来涤除旧的道德的同时,消灭新的庸俗,需要重新激活个体生命的创造性,何况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人的自然需求得到适时满足,应该说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为人性解放的目的也应当包含有对自然欲望的满足。对自然恶的正视也是对人自身的正视,对丑的承认也是对人的非理性本质的肯定,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上述列举的这些僭越道德的人又都是些强有力的人,拉斯科尼科夫精通法律理论;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异常狡诈,很轻易地就把对手打败,并霸占了其全部财产;老卡拉马佐夫本出身于破落的贵族,但凭借着妻子陪嫁的第一桶金却赚得十万卢布的家资,等等。这些在道德上欠佳的人却要么智慧异常,要么孔武有力,这在过去不可能的现象现在却矛盾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道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脆弱过,显然陀氏也并不想从道德上去贬斥他们,尽管他们身上的的确确存在着违反道德的现象。
当然,对人的生命欲望的宣泄不是无止境的,否则人类会在伦理上走向疯狂而最终导致回到动物状态,在美学上也会超出审丑阈限,这就得在高扬生命欲望的同时以更高的理性来调节,这个“更高的理性”在陀氏看来就是对东正教的信仰,这正如其在对《安娜·卡列尼娜》评价时所说的,“恶隐藏在人性深处,比我们那些社会主义医师们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种社会状态能够消除恶;人的思想永远原封不动,反常和罪恶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末了,人的心灵的规律,人们还远远不知道,科学还远远不能设想,非常捉摸不定,神秘莫测,因而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治疗它的医生或做出最后裁决的法官,只有他,那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上帝”[8](P95)。也许陀氏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才促成了其审丑而非嗜丑的美学风格,才提高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恶之花”来。
二、对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等生命非正常现象的揭示
现代文明的到来给人类造成的第一个巨大影响便是彻底斩断了人和自然的联系,这便是由人与自然的和谐转向对立,由依赖转向分裂,人开始出现忧虑和孤独等现代情绪,这常常表现为人格分裂、矛盾、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变态。在西方文学中哈姆雷特是第一个现代人,也是第一个害现代病的人,他常常因为内心痛苦而导致精神失常,甚至一度想自杀,因为精神的困惑远远超过了复仇本身。父死母嫁的突发事件,弑兄盗嫂的乱伦行为,彻底斩断了他对血缘亲情的信赖,而被推向孤独的深渊。继哈姆雷特之后,卢梭的感伤、拜伦的孤独、司汤达的激情、巴尔扎克的悲愤、托尔斯泰的痛苦,至陀氏这里,才真正把现代人的病症清晰地描画出来,这便是对人物的人格扭曲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并由此对人性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现。分裂的人性是恶的,变态的心理是丑的,但从美学的角度讲这种恶、丑又是审丑的。
在陀氏看来,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但人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人除了自然本能外还有理性,即人的人格、尊严、良知等。于是自然本能等非理性就和理性时常发生剧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人格尊严常常被扭曲。由于恶的力量过分强大,它像一个凶神恶煞、一步步手持鞭子逼近灵魂的行刑者,把灵魂抽打得遍体鳞伤,呻吟啜泣。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会扭曲,人性会异化,心理会变态。这样的描写会揭示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了理性在强大的自然本能面前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的伟大,因为人具有超越自然的本能,尽管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痛苦,但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等却是属人的。
陀氏最早写人格分裂的作品是写于1845年夏的《双重人格》。作品中的主人公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生性怯懦,逆来顺受,在官场中有一种危机感,他恐惧、怀疑,发展到病态。他本想在一次盛大的生日宴会上表现一下,但弄巧成拙,被逐出舞会,造成他内心的极大痛苦,最后戈利亚德金精神分裂了,幻化出了一位与他同貌的怪客,这位怪客卑鄙、狡猾、无耻,处处与他做对,却处处顺利,非常成功,这样,戈利亚德金的妄想症日益加重,他最后进了疯人院。这部小说通过同貌人揭示了人格的双重性。尽管别林斯基对这篇小说不欣赏,但陀氏却颇为得意,并不无骄傲地坚信双重人格是他的创造,“这个典型是我首先发现的,我是这个典型的宣告者……”[9](P95)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为了维持尊严,辞去官职,隐居地下室四十年,受尽了孤独的痛苦,但也渴望过正常人的社交生活,在一次参加同学朋友的聚餐时,因看不惯同学的庸俗而发生了冲突,这就使得他再次被众人(社会)抛弃,当他在宾馆偶遇妓女丽莎时,他为丽莎的不幸和美丽单纯所打动,他慷慨激昂地向丽莎陈述她的生活如何不幸,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等启蒙话语,并使得丽莎爱上了他。但是当丽莎真正出现在他面前时,地下室的肮脏,穿着衣服的破烂,使他非常尴尬,贫穷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为了维护其高傲的尊严、变态的虚荣心,他不但没有欢迎丽莎,却狠狠地把她污辱一通,以表示自己不屑与之为伍,最后丽莎在痛苦绝望中离去。其实地下室人的这种矛盾性格正是由于长期处于贫困境地,变得胆小、虚荣、自私,以及良知未泯造成的。
陀氏关于人格扭曲的描写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更加重了分量,也赋予了人格被扭曲以更多的社会内容。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有着高傲的自尊心,但贫穷却使他丢尽了面子。他本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但现在由于穷困他不得不辍学,整日呆在租住的房子里,受着良心的折磨。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当掉先父留给他作纪念的银怀表。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为了供他上学(家里还不知道他已辍学多日),他的母亲提前支取了养老金,他的妹妹杜尼娅去给一个地主当家庭教师,该地主斯维里加洛夫是个好色之徒,让杜尼娅受尽了屈辱,并且这还不够,杜尼娅为了使哥哥将来便于在彼得堡谋生,她还要违心地嫁给一个市侩卢仁,所有这些情状都折磨着拉斯柯尼科夫那颗高傲的灵魂,在极度的内心痛苦中人格发生分裂,导致癫痫病时常发作,最后想当一个“不平凡的人”,去杀人抢钱,以此来安慰病态的自尊,却没成想由此陷进更大的痛苦之中。陀氏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简直就是弱者群体维护尊严、人格独立而导致痛苦的总集。史密斯、卡捷琳娜、叶莲娜、伊赫缅涅夫、娜塔莎(真名叫涅莉)这些社会的弱者,这些善良的人,由于他们太善良、太重情感、太容易相信别人,结果他们被心狠手辣的瓦尔科夫斯基所欺骗。仅仅欺骗还不够,瓦尔科夫斯基还要凌辱他们,使他们在人格上受尽屈辱。卡捷琳娜受尽了瓦尔科夫斯基的欺骗和凌辱之后,陷入穷困的境地,失去了父爱,一生受尽了苦难,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原谅。在《白痴》中,娜斯塔霞·费莉波芙娜是个性情高傲的贵族女性,但由于家庭穷困,她不得不委身于一个大富豪托茨基,过着半养女半情人的生活。如今她就要出嫁了,并且为了使其便于出嫁,托茨基竟拿出七万卢布作为“陪嫁”,以便有人迎娶她。长期过着屈辱生活的娜斯塔霞在将要出嫁的时刻,她所受到的屈辱达到了顶峰,因为实际上她是被“拍卖”。在娜斯塔霞痛苦的抉择中,她的人格被扭曲到几近发疯的地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贵族小姐卡捷琳娜,性格高傲到变态的程度,她既不爱德米特里,也不爱伊凡,但她却以爱的名义尽情地折磨这哥俩,在对方的痛苦中找寻快乐。因此,陀氏正是通过描写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理性之间的巨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心理变态行为,从而展现出人物深层的内心世界。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越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心情与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探索,才能认识到。”[10](P35)人格扭曲导致心理变态,而心理变态则是最为深刻的心理现象,它所呈现的东西是平时看不到的。对于作者这一心理描写上的巨大成就,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道:“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二元论者,才闯进了这一秘密,只有他对情感作了全面分析。……在陀氏之前,人们对感情的多样性、对心灵的复杂性从来没有知道得这样多。”[11](P132-135)所有这些对人物潜意识和阴暗心理的描写,都揭示了陀氏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力。
也许在传统社会里人们还活在心灵宁静的天人合一境界之中,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与自然的对立造成人内心的失衡,这看上去似乎不是好事,但却使人的心灵变得深刻和复杂,使人们更易于接受复杂多变的对象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不再是完全否定意义上的,而是对人性状态的一种认可,也许是人性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因而应该得到正视。正是如此,这里的丑已经成为审丑,是陀氏对审丑内涵的开拓。
三、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和价值虚无
虚无主义的内核就是极端理性主义,并由此带来对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和对世界的重新解释。极端理性主义的形成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崇尚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对世俗世界的合理化解释(祛魅),来取代基督教的神圣世界,最终在人间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发挥,人类社会不断得到改善并走向完美,而所有这些就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人性的解放,“理性”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崇,因为理性不但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世界获得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且也是人类获得个性解放的依据,理性给人们建立了新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承担着过去只有基督教才有资格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功能。
可是,当我们把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时,谁也没有对理性本身产生过怀疑,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开始崇拜理性,认为理性万能,并发展为极端理性主义。所谓极端理性主义即往往过分夸大人的理性能力,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夸大人的知识理性能力,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规律是可以被发现的;二是夸大人的道德理性能力,认为人的道德完全可以控制人的意志,并和意志相统一,这便导致道德理想主义。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人的理性过分膨胀,人成了“人神”,并将导致两种结果:对内来说,极端理性主义造成对人自身的新压抑,人们凭借理性来摆脱蒙昧,而启蒙的手段如今却成了对人性压抑的方式,因为人的本质不是仅有理性,除了理性之外,人还有诸如情感、欲望、本能、预感、意志、潜意识等非理性,因此,道德理想主义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禁欲主义;对外来说,既然社会“规律”一经发现,统治者会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遵循这个“规律”,因此整个社会也就形成了奔向某个规律目的的“宏大叙事”,一切有悖于这个“宏大叙事”的个别现象都会受到压制,再加上启蒙时期人们对科学的崇拜惯性,人们会自觉地服从社会统筹和安排,因此新的极权专制便建立起来,人们再一次丧失自由。马尔库塞说:“技术合理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在工具理性主义的视野中,展现出的是一个合理的集权社会……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为了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12](P135)上述两种现象虽然分开来说,但二者又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理性的霸道和道德理性的自负再次把人沦为现代奴隶,这是所有启蒙者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因此,理性因过度膨胀而失去了昔日的崇高光环,变成了生命的桎梏,造成人性的异化和人生价值的虚无,尽管极端理性主义以各种看似前卫的虚无主义思潮出现,但审丑美学批评的运用仍然可以对其起到批判和否定作用。
理性这个本来关乎人的认知能力的特性,在后来的发展中早已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价值功能和信仰功能,理性从而取代了基督教而成了新的上帝,并由此衍生出诸如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等虚无主义思潮。早在19世纪,陀氏就已经比西方人更早地认识到了理性膨胀的灾难,并以审丑的美学批判眼光来看待它,因为说到底,理性的过分膨胀导致了感性、偶然、情感、意志、欲望等这些非理性受到压制,张扬生命,强调非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否定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异化,成了审丑的使命。更何况理性发展为理性主义,再发展为极端理性主义,这样就会导致美学上的倒退而成为“伪古典主义”,使文学丧失自身的价值而导向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陀氏对理性膨胀之丑的描写早在《地下室手记》中已经开始,其主人公“地下室人”对理性的作用做了较为清醒的评价:“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搔耳挠腮。”[5](PP201-202)“地下室人”甚至认为人并不总是趋利避害,按照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行事,而是有时“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去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聪明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5](P202)。“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上的琴键,可以任由自由规律随意弹奏……”[5](P204)这里很明显是作者在调侃“合理利己主义”。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按照自己想象出来的理性法则,把人类分成两类,即平凡的人和超凡的人,前者只是平庸的繁殖同类材料的人,后者是少数的改变历史发展的人和具有在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的人。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超凡的人有权利革除凡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是历史理性的障碍,是对理性生活来说全然无所谓的人。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平凡的人是“虱子”,理应服从超凡人,并任其宰割,即使那些超凡的人杀了人,也是为了推动历史,把世界引领到美好的未来。历史理性崛起,上帝消遁,拯救世界需要“新人”,他们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他们之所以杀人也被许可,是因为他们是以拯救世人的名义,以人类的恩人自居的,他们的行为符合历史理性的需要,代表历史按照客观规律前进的方向。这种人不能用血肉之躯构成,只能用石头和青铜铸成。“他在当街筑起一座坚固的炮台,不由分说,把无辜的有罪的人一齐轰死!颤栗的畜生,只许你们服从,不许你们有愿望,因为那不是你们的事!”[13](P364)在《群魔》中,陀氏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借用《圣经》中的典故,把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的俄国虚无主义者比作魔鬼附身。陀氏在1870年5月19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谈到了《群魔》的主题,“群魔附在一个人身上,多的不可胜数,并且央求耶酥:把我们引入群猪中去,他同意了。群魔附在一群猪身上,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入海里淹死了。……我国发生的事情与此完全相同:群魔离开了俄国人,附到了一群猪身上,即附在涅恰耶夫、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之流身上。他们已经淹死或者一定会淹死,群魔离开以后获救的人也坐在耶酥的脚下。理应如此。俄国吐出了人家喂给她的肮脏东西,在这些被唾弃的坏蛋身上当然一点俄国的气味都留不下了。而且您要注意,亲爱的朋友;谁抛弃了自己的人民和民族性,他就会丧失对祖国的信仰和上帝。”[14](P262-263)陀氏对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者韦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等这些“群魔”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作品中这些人都不配有好下场。而在陀氏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作者仍然在对虚无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伊凡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学,善于分析、思考,试图寻找到生活的意义;他不相信灵魂永生,否定上帝,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从同情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走上了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道路,陷于矛盾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陀氏对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不再像《群魔》中那么绝望,伊凡这个杀害父亲的真正凶手,他身上仍然有向往光明的冲动,但他终究没能站起来,而是精神失常了。由此看来,临终前的陀氏对俄国这些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而变得“丑陋”的虚无主义者们,还是抱有些许希望的。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便会发现陀氏的审丑意识来自对自然欲望合理性的认识与接受,对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现象的正确看待,以及对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生命异化和价值虚无的批判等三个方面,并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重新审视,从张扬生命、赞美自由的角度,挖掘出了新的美学趋向——审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然派”的崇高美学风格。作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自然派”,其哲学基础仍然是理性主义,因此塑造典型人物,批判社会现实,弘扬人道主义仍然是其创作的主旨,而陀氏建立在非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审丑创作观却不满于此,双重人格的塑造显示了多重主体的存在(即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并由此引发出来的“主体间性”理论);罪恶之源存在于人性本身的观点是对外在环境决定论的不满;启蒙的人道主义远没有基督之爱的博大,并有走向虚无主义之嫌,于是本身曾是“自然派”一员的陀氏到了19世纪60年代却“反戈一击”,用审丑消解了“自然派”的崇高,拓展了主体性仅仅局限于理性的不足,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并超越了同时代的欧洲文学。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法]狄德罗.论戏剧艺术(上)[M]//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M].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损害的[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M].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安娜·卡列尼娜》[M]//陈燊,编选.欧美文学研究导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9][苏]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M].王健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奥]斯蒂芬·茨威格.六大师[M].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12][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铝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4][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M].冯增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张东丽
I106
A
1671-3842(2015)03-0034-07
10.3969/j.issn.1671-3842.2015.03.06
2014-12-02
张中锋(1964—),男,山东夏津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美学。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审丑的生成与转换机制研究——以外国文学中的审丑现象为例”(12YJA75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