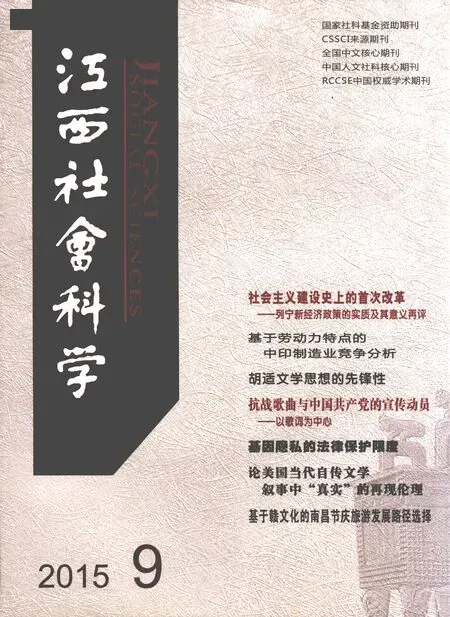基因隐私的法律保护限度
■秦天宝 虞楚箫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得以从分子层面解析自身的生理结构,是人类认知活动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重大发展,带领人们走进了“美丽新世界”。然而,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领域的问题,它在给人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冲击原有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的规则。基因技术的日臻成熟一方面为破解人类遗传和生老病死之谜,解决人类健康问题带来希望,另一方面也将人们置于基因信息被暴露、被滥用的焦虑和不安之中。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规制此类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深刻反思。在上述背景之下,对基因隐私的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基因信息相较于一般个人信息而言是否真的那么特别?它是否不同于普通的个人医疗信息?以至于在面临基因隐私权与其他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它会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其他权益而成为最优位的权利吗?如果它不具有绝对优先性,那么在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权衡?
一、基因隐私的概念
在生物学上,基因是指DNA分子上的具有遗传效应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的总称,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分子片段。[1](P399)基因信息则是指DNA分子上载有的信息。隐私是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2](P7)基因隐私则是与基因信息相关的隐私。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基因信息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激发了民众对基因信息保护的强烈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基因隐私的概念应运而生。
个人对其基因信息同时享有 “信息隐私”(Privacy)和“信息自主”(Autonomy)两种法益。其中基因信息隐私属于隐私权的客体,而基因信息自主则属于个人信息资料权①的客体。个人信息资料权是指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资料的一种控制权,更加强调自主控制信息适当传播的权利。隐私权虽然包括以个人信息形式存在的隐私,但其权利宗旨主要在于排斥他人对自身隐私的窃取、传播。[3](P120)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信息资料与隐私之间在范畴上确存在一定的交叉,如擅自窥探他人病历资料,既侵犯个人隐私权,也侵犯了个人信息资料权。这样的交叉也存在于基因信息之上。也就是说,对于基因信息而言,信息隐私和信息自主这两项法益的意涵是重叠的,只是基因信息隐私偏向于防范信息的披露和被窥探,基因信息自主更强调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和利用。
对“基因隐私”的含义,理论界也存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基因隐私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有选择不知悉自己基因状态的权利;二是知悉自己基因状态的个人有不与他人分享该信息的权利;三是个人有利用该基因信息独立为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4](P39-48)国内学者张小罗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基因隐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1)个人对自己基因隐私的知晓权与拒绝知情权;(2)对个人基因隐私信息的保密权;(3)对他人非法搜集、利用个人基因信息的禁止权;(4)家族权等。[5](P78-81)但是有学者主张,上述所称的“对自己基因隐私的拒绝知情权”和“个人有利用基因信息独立为自己做出选择的权利”属于自主权(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而不是隐私权的范畴。[6](P49-50)美国学者Anita L.Allen则认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现今的隐私权不能再被简单地理解为Brandeis和Warren在1890年所称的“独处的权利”,它已经发展到了以下几种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身体隐私权、信息性隐私权、具财产价值的隐私权和自主决
定隐私权等。[7](P31)[8](P18)
有学者认为,无论隐私的内容多么宽泛,也不管“隐私”一词有多么难界定,基因信息因为能揭示从个人的体格状况、易患病体质,甚至精神特征,并有泄露个人生活中最隐私和最私人信息的潜在可能性,是 “个体的本质信息”,因此,被认为本质上是私人的并有被保护的资格。[9](P23)[10](P105)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但若以此作为提倡绝对基因隐私保护的理据,则进入了一定的误区。因为有许多其他的医疗信息,同大部分基因信息一样,“能揭示从个人的体格状况、易患病体质,甚至精神特征,并有泄露个人生活中最隐私和最私人信息的潜在可能性”,为什么基因信息能够得到特殊的法律保护,而它们不行呢?
二、基因隐私有限度保护的学理分析
基因信息和基因隐私的特殊性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探讨,通过法律保护基因隐私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的共识。社会对基因隐私法律保护的强烈诉求主要来源于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它使得基因隐私在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普遍倾向于采取基因隐私单独立法的方式。这种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一切组织或个人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收集、使用基因信息行为等较为强硬和一刀切的保护基因隐私的方式,可以称之为绝对基因隐私保护主义。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绝对基因隐私保护主义不仅欠缺法理依据,且容易导致相关立法的激进,从而超越民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相关行业的抵触和反抗。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信息流通愈发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基因科技带来巨大的风险负担和巨大经济收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基因隐私凌驾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对基因隐私的保护应当有所选择、有所限制。
(一)基于法理的分析
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保障与维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义务,公民有充分行使其权利的自由。然而隐私权不是绝对的,并非可以漫无限制的行使。[11](P117)权利的确立首先基于对权利的限制,权利的享有同时也意味着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申言之,公民所享受的权利边界,是由公民为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义务所确定的。如果公民不履行义务,社会就不存在这种权利的条件。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对该权利的限制,在与其他权益发生冲突时,没有任何一项权利能够绝对地优于其他而成为 “最高级别的利益”。
随着基因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体基因所蕴含的价值愈发得以彰显。个人的基因隐私与个人信息的知情权②和利用权等之间的冲突也愈发紧张。在现今社会这种多元价值体系中,随着人与人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人们权益意识的不断提升,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碰撞。通过法律的方式保护基因隐私的价值目标,核心是对基因科技所引致的权益纷争加以平衡。在对这些权益冲突进行协调时需要依据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如保险人的知情权与被保险人的基因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孰轻孰重,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后者的价值一定高于保险人的知情权之价值。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利益是绝对优先的。“尽管隐私非常重要,但隐私不是一切”。[12](P1377)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正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在找出各自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析与比较,做出价值判断,而不能以一个正当利益来断然否定与之相冲突的其他正当利益。③
此外,道德、伦理和法律等都属于拘束性社会规范的范畴,虽然它们的效力来源和效力范围有所不同,却拥有普适的、不受时代限制的共同根源和一致内容。[13](P23-27)法律调整的目的、目标与伦理、道德也具有相对一致性。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的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14](P162)对基因隐私法律保护程度的决定,应当加入对伦理、道德问题,甚至是代际关系的考量。当基因隐私权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点相背离时,对基因隐私的绝对保护将会受到社会公众的诟病。由于基因隐私的保护所产生伦理、道德问题多发生在家庭维度,从对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维护以及对妇孺儿童等社会弱者的关怀出发,对家庭范围内基因信息权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应当体现一种人文关照和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点的尊崇,而不应当一味地强调基因隐私保护的重要性。
(二)基于法律的分析
1.绝对保护会给立法带来巨大挑战
绝对的基因隐私保护,其前提是必须在法律上给出一个明确的、具有操作性和科学说服力的“基因隐私”之定义,并回答基因信息与其他的个人信息,或者基因隐私与一般的隐私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等问题。然而截止到目前,对于什么是基因信息尚未发展出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要么过于狭窄以至于保护不足,要么过于宽泛以至于保护过度。[15](P33-34)[16](278)并不是所有的基因信息都需要法律对其加以保护,④如果法律将这类基因信息纳入保护范围,就会出现过度保护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其他医疗信息与基因信息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亟需立法保护,但它们并未被纳入基因信息的保护范畴,因此导致了保护不足的窘境。[17](P672)在法律上定义基因信息的难度将远远超出那些主张基因信息具有独特性的学者之想象。有学者认为,要想完全将基因信息与其他医疗信息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5](P33-35)这种区分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主张的这种区别是不合理的,[18](P40-41)或者说这种区别并非是至关紧要的。
[19](P60)
有人认为将基因信息定义为基因检测分析的结果就能避免上述问题。然而,基因检测的定义和范围也是引起当前国际立法实践和学界广泛争论的问题之一。基因检测是一个新兴的科技领域,具有高度科技性和专业性。基因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包括在读取基因检测结果时的人为错误因素)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基因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尚不确定,是否需要加以保护就显得有些疑问。[20](P418)
2.绝对保护有违法律的整体性
大部分主张基因隐私绝对保护的学者都提倡通过基因立法,对基因信息和基因隐私进行特殊保护。然而在一般医疗信息法律保障尚不完善的中国,一味地强调基因信息的单独立法不利于法律的整体性和一贯性。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的基因隐私保护立法可以充当个人隐私法律保护的“特洛伊木马”,带动其他隐私保护立法。基因隐私立法对基因隐私的保护,也可以随基因信息的广泛运用而逐渐扩张至全部医疗信息的隐私保护。[16](P283)在基因隐私法律保护领域,社会公众、媒体、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立法者之间构成一个循环的圈。公众对基因歧视和基因隐私被侵犯的顾虑和恐慌,是基因立法的最大动因之一。一旦一部基因隐私保护单行法制定完成并公布,立法者就会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社会公众、媒体、甚至科学家也会认为他们担忧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失去了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和呼吁,对其他敏感医疗信息隐私的保护将很难得到立法者的再度关注,从而破坏法律的整体性。这样的做法也会导致挂一漏万,造成其他医疗信息无法可用的窘境。
(三)基于现实的分析
1.绝对保护可能导致基因决定主义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之初,基因决定主义的盛行加之人们对于新鲜事物先入为主的倾向,使得对基因信息神秘化、神圣化的社会认知大行其道。这种认知误差加上基因隐私易受侵害性的特征,使得若不及时通过法律对其加以保护,可能会造成公众的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当我们还原基因决定主义的时代背景,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可以发现,除了公众、媒体和科学家之外,立法者(政策制定者)也是主要的幕后推手之一。一方面,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基因隐私主要是基于各行各业广泛的呼吁和支持,包括公众、媒体、科学研究员、遗传学家、伦理学家等。大部分立法反映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在保险和就业领域,对基因歧视和个人隐私被窥探的担忧。另一方面,基因立法同时也促成了某些观点的形成。[17](P690)基因立法从法律的角度将基因信息和其他医疗信息区分开来,无疑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对此反复宣传和强化,让公众认为法律已经明确认可了基因信息与其他个人信息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恐慌。这时,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就会开始呼吁对基因隐私更高层级、更严格的保护。如此循环往复,会反复加固“基因信息具有决定性和独特性”这一观点,构成一个最终通往基因决定主义的怪圈。这样的立法,将会超出社会民众的承受范围。
2.绝对保护有碍社会的整体进步
一项权利的具体界定,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于法律主体之间利益纷争的解决。在法律层面上对该权利予以多大限度的保护,将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交往和互动,以及这项法律规定的社会实施效力。对基因隐私过分的保护将会导致对个人社会属性的忽视,使之怠于履行其负有的社会责任,不利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21](P512)[22](P54-70)事实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隐私保护的需求以及对隐私法律保护的侧重点也在发生着变化。
法学界对隐私权问题最早的专门研究是Samuel D.Warren和Louis D.Brandeis在1980年发表于《哈佛法学评论》的《隐私权》一文,该文将“不受干扰的权利(right to be let alone)”定义为个人的隐私权。[23](P193-220)这种空间性隐私权是隐私权探讨的原型。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话等通讯设备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等使得隐私权表现为一种伴随着人类空间活动的不断拓展而动态发展的权利。现代隐私权的权利内容开始主要侧重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通讯自由的保护。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隐私权不再被单纯地理解为独处的权利,而是对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人信息和通讯秘密的保护,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理性选择的产物。对隐私法律保护的目的在于满足人际交往的需要,以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因此也应当负有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有学者认为隐私权的功能之一在于对公共生活的解脱,实现个人的自我调适。[24](P1017-1040)笔者对隐私权的这一功能并不否认,但这种 “解脱”的功能,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社会生活的自主参与和对社会责任更好的履行。绝对的基因隐私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阻碍社会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影响社会主体关系网的编织强固。基因信息,无论它的定义为何,其本身都是中性的。现有的争议都是由对基因信息的不当使用而引起的。因此,法律不应当阻碍信息的交流和获取,而是应当规范谁有权获取,以及他们意图如何使用该信息。[25](P121)由隐私权权利内容的演进来看,避免对隐私权的过分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人们在各自的社会责任方面对其做出的回应。绝对的基因隐私保护,无疑会对基因科技,尤其是人类基因库的建立,带来一定的阻碍。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对基因信息太过严格的保护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关注基因隐私或基因歧视的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级,如果立法只注意到基因信息,(对其施加严格的隐私保护),就没有平等地对待大多数下层阶级人民所面临的医疗隐私和医疗信息歧视问题。”[17](P671)
三、合理保护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小综合立法模式”为主,行业自律为辅
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 “小综合立法模式”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保护进路。[8](P16-26)基因隐私综合立法模式,是指将基因信息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以一般性的隐私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基因信息进行不区分于其他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方式。“小综合立法模式”则是指对个人数据加以适当的区分,对敏感信息等进行区分规定,但是并未对基因隐私区分对待的一种立法模式。
如前所述,我国尚缺乏一部隐私保护方面的基本法。由于我国大众对隐私保护的认识有限,法律实践较少,在制定法律时,首当其冲是要制定一个该领域的基本法,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使公众树立隐私保护的法律意识。若单独制定基因隐私保护立法,在基本法缺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缺乏该领域的指导性原则而给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带来难题,实施效果也会不尽人意。现阶段,要提高社会对于个人隐私保护水平,制定明确和系统的基本法律规范,告诉民众正确处理对待个人隐私的行为方式远比单独制定“基因隐私保护法”合理和可行。此外,在基因隐私保护领域,应当鼓励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自治。虽然传统上来说,我国在自律传统和观念方面是相对比较缺乏的,民间组织发展不甚完善,社会自治能力也比较薄弱。但是,在基因隐私保护领域,在消费者的强烈倡导下,企业有可能会出于企业道德或提升商誉等考虑而制定相关的企业自治规范。
在“小综合立法模式”中,在隐私保护基本法中对敏感信息的保护提供法律强制保障,加上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企业自治规范,可以构成对基因隐私较为合理且可行的保护。
(二)实体上容许例外规定
基因隐私不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在具体的法律制定过程中,应当注意加强对例外情况的规定,以及该规定与已有法律法规的协调与衔接。例如,对于雇主知情权与员工基因隐私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分类讨论的方式。对于企业而言 (尤其是上述所提到的特殊行业),其存在的直接目的就是营利,同时也肩负着避免对社会公众的健康权、财产权造成侵害的义务,这导致雇主在各种决策领域都会将公共安全和经济利益纳入考量范围,而且雇主应当也享有一定程度上招聘员工的自主选择权,我们在分析基因信息在职场中流通的过程中也应当采取一种市场化的角度,一概禁止雇主对员工基因信息的获取会导致法律违背经济系统运行规律,也会将社会民众的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我们则应从行政检查权边界控制的角度来分析,对行政权力而言,法无规定即禁止,因此公务员的录用应严格遵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相关规定,超出《通用标准》中规定之体检范围的检查事项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事实上,在实践中不少国外的基因立法都对基因隐私的保护做出了例外规定。例如,美国《禁止基因信息歧视法》(Genetic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GINA)分别在第202(b)条和第206(b)条对就业领域中“基因信息的获取”和“基因信息的保密”做出了例外规定。[26](P53-59)与《禁止基因信息歧视法》相似,美国各州的相关法律也列举了具体的例外情形,最常见的例外情形主要包括:诚信职业资格、员工赔偿金或伤残索赔请求、对工作场所中有毒物质的敏感性或接触、司法或行政程序、死者或其血亲身份的查明以及法律强制执行目的。[26](P202)
(三)程序上引进公众参与机制
现今社会多元价值取向共存,人类科学技术进步也正在加速着社会变迁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当上述提到的设置例外或但书规定无法调整多元价值冲突时,需要引进一种理性对话的框架,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保证决策的公开透明以及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基因隐私予以保护,究其根本是因为存在这种社会需求。为了更好地回应和满足这种需求,并充分尊重私权、尊重个人隐私的道德直觉,基因隐私的法律保护进程中应当将社会公众的观点和顾虑纳入考量,以保持必要的觉醒,实现理性对理性的竞争反省。由于基因隐私保护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且随着基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还会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而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长期的互动博弈能够自发形成一些信息流通与隐私保护的道德规范或伦理制度。这些社会中自发生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可以通过公众参与机制的引进,透过合理对话的方式成为法律的重要补充。对于基因隐私保护而言,基因信息无处不在的特质和信息的家族关联性给通过法律来保护基因隐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因为基因隐私保护过程中出现的多维道德伦理因素,使得基因立法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而通过公众参与机制,引进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强化在此过程中民众自身的作用,能够更有效地禁止非法获取、使用公民个人基因信息的行为。
将公众参与机制纳入基因隐私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其优势不言而喻:首先,公众参与基因隐私保护的决策制定有助于提升公民对基因科技的认识,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瓶颈与落差;其次,公众参与机制的保障可以避免使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专家、利益团体或政府机关,促进对资源分配的理性审议,从而有助于规范与决策程序的透明化;最后,对公众参与的保障能够使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民之所想,对与基因隐私保护有关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收纳与广泛讨论,提高保护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总之,对基因隐私的法律保护志在必行,但也应当注意到保护的限度问题。在“小综合立法模式”中,透过稍广泛的信息保护范围和合理的保护程度,加上例外情况的规定和公众参与程序的引进,摆脱上述提出的缺陷,将会使得这种立法更加平等、和谐和有效。
注释:
①个人信息资料权,德国将其称为“控制自己资讯的权利”或“资讯自决权”。就目前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还缺少相应的权利类型。
②有学者认为,知情权仅指公民个人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悉与自身相关的信息的权利,属于政治上的权利。此处所称之“知情权”应当属于一般意义上“知的权利”。笔者无意对学界中知情权的概念与内涵的争议展开讨论,谨借用“知情权”的语词来表达第三人对公民个人的与其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
③例如,在雇主的知情权和员工的基因隐私权之间,后者并不是绝对优先的。考察相关立法可以发现,为了确保劳动安全,现在的劳动法均要求雇主对求职者或员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而员工也有接受检查的义务,尤其是在食品、医药、军工、交通、原子能等特殊行业。
④如控制人体毛发、身高、性别、眼球颜色等形状的基因,它们并不具有我们所认为的“敏感性”特征。
[1]John K.The Encyclopedia of Nuclear Biology.Blackwell,1994.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3]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J].法学家,2012,(1).
[4]Kardn L.Genetic Privacy:No Deal for the Poor.AJournal of Theology,1994,(1).
[5]张小罗.基因权利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
[6]Juha R.Autonomy and Genetic Privacy.Veikko L,Juha R.Genetic Democracy: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2008.
[7]Anita L A.Genetic Privacy:Emerging Concepts and Values.Mark A R.Genetic Secrets:Protecting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in the Genetic Era,1997.
[8]秦天宝.论我国基因隐私保护的立法模式选择[J].政法论丛,2013,(6).
[9]Jeffery SG.The Bloodingof America:Privacy and the DNADragnet.Cardozo Law Review,2002,(23).
[10]邱格屏.人类基因的权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1]张莉.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2]Anita L A.Privacy Isn’t Everything:Accountability as a Personal and Social Good.Alabama Law Review,2003,(54).
[13](德)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基本问题[M].王亚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M].陈林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5]Mark A R.Why Treating Genetic Information Separately Is a Bad Idea.Texas Review of Law and Politics,1999,(4).
[16]罗胜华.基因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7]Sonia MS.The Allureand Peril of Genetic Exceptio nalism:Do We Need Special Genetics Legislation?.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1,(79).
[18]David K.Genetic Privacy,Medical Information Privacy,and the Use of Human Tissue Specimens in Research.Clarisa L.Genetic Testing 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1999.
[19]Thomas HM.Genetic Exceptionalismand Future Diaries:Is Genetic Information DifferentfromOther Medical Information?.Mark AR.Genetic Secrets:Protecting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20](美)艾米·福斯特.公民基因信息隐私权的扩大保护——从基因测试的角度说起[A].黄淑芳,译.张民安.公开他人私人事务的隐私侵权——公开他人的医疗信息、基因信息、雇员信息、航空乘客信息及网络的隐私侵权[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21]David F.Civil Libertiesand Human Rightsin England and Wales(2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2]Atina K.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in(Post)-genomic Medicine:a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new Frontier.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2011,(1).
[23]Samuel DW,Louis DB.The Right to Privacy.Harvard Law Review,1890,(4).
[24]Alan FW.Science,Privacy,and Freedom:Issuesand Proposalsfor1970’s.ColumbiaLaw Review,1966,(66).
[25]Jonathan W.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Genetic Privacy Act,The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2003,(24).
[26](美)乔伊·沃尔特马斯.美国禁止残疾与基因信息歧视法解读[M].蒋月,郑净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