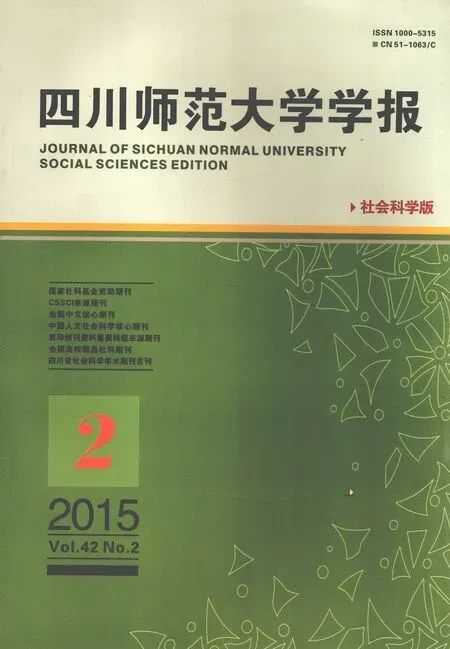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旨再探
宋 威 山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23)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旨再探
宋 威 山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23)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一组无论从创作时间、文体风格还是诗歌主旨上都饱受争议的拟作。该诗并非模拟历史上不曾记载过的《邺中集》,而是谢灵运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以魏太子与建安诸子的宴集及作品为原型所拟构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完美盛宴,是谢灵运元嘉五年政治理想破灭后的寄托之作。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拟构作品;寄托之作;邺中宴集
一
魏晋以降诗歌摹拟之风盛行,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即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叶梦得《石林诗话》云:“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谢灵运《拟邺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1]433这组诗自诞生以来就受到高度的评价,如钟嵘《诗品序》即称其为“五言之警策”[2]211。 但是围绕拟诗风格是否肖似的问题,后世文论家却产生了颇多分歧。
从正面肯定谢灵运拟诗艺术效果的,如刘克庄《后村诗话》云:“谢康乐有《拟邺中诗》八首,江文通有《拟杂体》三十首,名曰‘拟古’,往往夺真。”[3]5与之相反的是,方回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却认为:“此全是晋、宋诗,建安无此”,“皆不似建安”,“全无所谓建安风骨”,“近世有《休斋诗话》者,谓灵运《拟邺中八首》,无一语可称,诚哉是言!”[4]1906非但批评谢灵运在摹拟艺术上的失败,更是彻底否定拟诗的整体艺术成就。类似见解又如毛先舒《诗辩坻》云:“灵运《邺中八子诗》,是拟建安,却得太康之调”,“《拟邺中八首》,行墨排钝,无复宛然,几成寿陵之步”[5]34,41。 由此可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一组颇具争议性的拟作,其摹拟效果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此诗的文学价值。更有甚者,对谢灵运的所有拟作均抱有轻视态度,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云:“康乐《拟邺诗》及《拟古》诸作,不必不佳,然实无谓。阮亭不取,颇见鉴裁之善。”[6]13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对拟诗文学价值的认定。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谢灵运这组拟作呢?
矛盾的焦点既然集中在《拟魏太子邺中集》的摹拟效果上,因而我们有必要针对原作进行一番讨论。由上引诸家观点可知,谢灵运此诗当摹拟自魏太子曹丕的《邺中集》,但是六朝史志目录和其他文献中从未有《邺中集》的明确记载,因而是否真的存在《邺中集》一书则成为问题的关键。现代学者对此多有考辨,如邓仕樑《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一文称:“根据谢拟诗和皎然《诗式》的资料,我们知道魏文当时确曾撰《邺中集》,集中录了曹丕、王粲、陈琳、徐幹、刘祯、应玚、阮瑀、曹植八人之诗各一首。”[7]而孙明君《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研究》一文却认为:“《拟邺中》不应该是对八首具体诗歌的摹拟,而是对邺下时期众多诗歌(主要是游宴诗歌)的总结和模仿。”[8]201刘则鸣《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考论》一文则推测:“《邺中集》在谢灵运所处的晋末宋初就早已散佚,谢灵运亦未见传本。《拟邺中》诗题中之‘拟’乃虚拟、揣拟之意,而非摹拟、仿拟之意。”[9]但颜庆余《〈邺中集〉小考》一文却认为:“所谓曹丕编纂的《邺中集》并不曾存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虚拟邺下诗人的宴集,而非模拟所谓的《邺中集》。”[10]这些结论各不相同,往往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重作审视。
《文选》李善注在该诗序文后引曹丕《与吴质书》“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八字作为“撰文怀人”的注解[11]591。其实,曹丕所言之文集,实为除孔融外六子的遗集,因为此时曹植尚在人世,其诗文自然不当在内。所以,假使《邺中集》就是曹丕所言的文集,谢灵运拟诗中当无曹丕曹植二人之诗。今拟诗中二人之诗皆在,由此可推曹丕所言的文集一定不是《邺中集》。又黄节《谢康乐诗注》据《初学记》引《魏文帝集》“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一句,认为“此即《邺中集》诗也”[12]682,这也只是推测《邺中集》乃数次宴会的总集,并不能直接证明曹丕为此曾纂有《邺中集》。此外,皎然《诗式》中有“邺中集”一条目,其云:“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祯辞气偏,王得其中。”[13]110这是否说明皎然曾经寓目《邺中集》呢?其实仔细分析可知,皎然之说实际上源于谢灵运。谢灵运的拟诗中一共有八个人,其中曹丕作为宴会主人存在,而其余七人分别是王粲、陈琳、徐幹、刘祯、应玚、阮瑀和曹植;而皎然“邺中七子,陈王最高”的说法是将曹植纳入七子之列,这显然是受谢灵运拟诗中出孔融入曹植的影响。而且在前引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谢灵运此诗的题目被写作“《拟邺中七子》”,或许正是因袭皎然“邺中七子”之说而成。由此可知,历史上并没有编纂《邺中集》的明文记载,也没有证据证实皎然曾经寓目过《邺中集》一书。
因此问题的关键便转为谢灵运此诗是否确实摹拟《邺中集》?如果不是,那么诗题中的“邺中集”究竟所指何意?有关该诗的风格特色,前文已经征引各家说法,大约均就文辞方面发论,并未揣测诗人之用心。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称:“康乐深于性情,而不审格调。公宴诸作各体,本人怀来,至于风度,未协建安风旨。”[14]549他认为谢灵运的摹拟并不追求格调上的逼肖,而是从诸子的怀抱性情上着眼。类似说法又如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孙鑛语:“此诸作非若士衡之句字皆拟,只是代为之词,兼效其体耳,细玩亦不甚似。然比之康乐,自较苍劲有骨力,犹有建安黄初遗意。”[15]卷七,眉批由此可见,谢灵运此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摹拟,而是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所评价的“拟古变体”[16]936。 对此,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方伯海语云:
按八首中,首篇是子桓自叙一时诸贤会聚之盛,余七首是代诸人写其遭逢出处及怀抱性情,故为集诗。此体从前所无,乃灵运独创。其与《五君吟》异者,用代与不用代耳。
右八首中,皆以操与子桓为纲。中间有略有详,以避前后复叠。妙在设身处地,于个人神理无不逼肖。可知文家轶切为佳,全在用意落想。后来唯杜工部《饮中八仙歌》,差足步其后尘。[15]卷七
他不再将谢灵运此诗与陆机《拟古诗》十四首、江淹《杂拟诗三十首》等传统拟作相提并论,反而将其与颜延之《五君咏》、杜甫《饮中八仙歌》联系起来,因此我们需对三者的关系加以详细考察。
《宋书·颜延之传》记载了《五君咏》的创作背景:
延之好酒疎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17]1893
由上可知,《五君咏》是颜延之在政治上遭到贬谪后的发愤之作,通过歌咏竹林七贤的人格风范以自比。如“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是指其性格像嵇康一样难被驯服;“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是借阮籍的穷途而泣表达自己的悲哀;“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指代自己被贬而外放永嘉,同时又指此前因“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出为始安太守”[17]1892之事;而“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则指其“独酌郊野,当其为狂,傍若无人”,“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之举[17]1903-1904,借以韬光养晦、明哲保身。这些诗句本是颜延之对竹林七贤人格风范的归纳和评价,可是字字句句皆直指自己的胸怀和遭际。因而与其说是凭事咏史诗,倒不如说是借人咏怀诗,正如刘熙载《艺概·诗概》中区分的那样:“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18]266而谢灵运此诗正是本着自己的怀抱和心志,拟构了一场魏太子邺中宴集,并用八首诗塑造了建安诸子的形象,如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云:“八诗八人小传,确而不泥,疎落多姿,方见心思宛转,手笔灵活。”[19]卷二在这一点上,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塑造的八个饮者的形象正可与谢灵运的建安诸子相媲美。
综上可知,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诗并序》一诗并非意在摹拟《邺中集》,而是拟构了一场魏太子邺中宴集,通过摹拟建安诸子口吻的方式,代为创作了八首诗歌,将诸子的形象栩栩托出,借此寄寓和抒发自己的怀抱和志趣。
二
那么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诗并序》的意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谢灵运假曹丕口吻所作的序中看出端倪: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讌,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时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20]135-136
方回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理解为:“予谓此序使其主宋武帝、文帝见之,皆必切齿。‘其主不文’,明讥刘裕。‘雄猜多忌’,亦能诛徐、傅、谢、檀者之所讳也。”[4]1906可见,他认为谢灵运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怀才不遇,才假借曹丕之口以讥讽宋武帝的不喜文才和宋文帝的雄猜多忌。对此,张溥《谢康乐集题辞》亦有阐发:“宋公受命,客儿称臣。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悄实乖。文帝继绪,轻戮大臣。与谢侯无夙昔之知,绸缪之托。”[21]169由此可知,谢灵运正是拟构了一场邺下诸子的宴集,借此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慨。
但是,针对谢灵运笔下的盛宴,古往今来的诗论家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如顾绍柏在《谢灵运集校注》中称:“灵运是要借《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诗来间接追忆他与庐陵王刘义真、颜延之、慧琳等人在建康相聚的一段美好生活。”[20]156显然,他认为谢灵运笔下的邺中宴集是为了追忆当年与庐陵王等人的欢宴,这样便与宋武帝和宋文帝的宴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明君则在《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认为:“一方面,《拟邺中》以建安时代邺下文坛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回忆中‘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的生活;另一方面,拟诗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拟诗中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诗人也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可以说,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8]210可见他眼中的宴集,是由不同时代文人凭借记忆所建构而成的完美场景,记忆和文学均滤掉了历史事实的残酷部分,而建安诸子也成为一群只图享乐的士人[22,23]。无论如何,以上观点均将谢灵运笔下的邺中宴集理解为一场欢乐美好的盛宴。
与此相反,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却将这场宴集描绘得很不愉快:
盖康乐自伤其才大不偶,故于诸子止写其丧乱流离之苦,或写其人品卓荦与不乐仕宦之意。即间有优渥之言,不过在游戏饮讌之小礼,总非有国士之知也。[24]381
在他看来,谢灵运为了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极力渲染诸子身世流离之苦和仕宦不乐之意,而由于诸子身处魏太子的公宴之上,不得不违心地报以奉承之言。因此,他在解读诸子之诗的时候频繁使用“虚拘”一词,如评王粲“虚拘于邺下”、评刘桢“礼数虚拘”、评应玚“虚拘以饮讌之小礼”、评阮瑀“总归于虚拘耳”[24]384,387,388,借以强调诸子在宴会上的情非得已和在政治抱负上的无可奈何。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持有相近的观点,如评王粲“自伤止以文义见赏,不参权要,如仲宣在建安中”;评刘桢“古今逢乱失所,何事不有,缘此互相解譬,虽乖平生之素,亦安之也”;评应玚“皆飘荡不见礼,不胜后生末契之感”[16]936。这些解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谢灵运自身的遭遇,如《宋书·谢灵运传》云:“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17]1753,1772。
上述理解看似已趋完满,但吴淇又补充道:
前论以伤己才智不用于时而托之此诗,固是康乐之正意而非其隐情,盖有感于庐陵王义真之事也。[24]381
原来吴淇认为,谢灵运借邺中宴集上的诸子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宋武帝、宋文帝的嘲讽都只是其正意,而另有与庐陵王刘义真相关的隐情。《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云:“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慕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17]1636少帝刘义符被废,帝位顺次当属庐陵王刘义真,但是徐羡之等又阴谋将其废杀。相较于宋武帝和宋文帝,庐陵王刘义真对谢灵运可谓有知遇之恩,如《宋书·谢灵运传》云:“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17]1753而且庐陵王似乎也满足了其政治理想,如《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云:
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17]1635-1636
庐陵王刘义真当初信誓旦旦地声称,得志之后必将以谢灵运为宰相,而徐羡之等人废杀庐陵王无疑扼杀了谢灵运的政治前途。因此吴淇认为,谢灵运笔下的邺中宴集隐含着一场政治冲突,谢灵运“托之魏太子邺下集诗者,盖以魏武屡有易储之意,太子、平原各竖羽翼”[24]381。具体说来,谢灵运以曹丕为宋文帝,而曹植“实是庐陵王真替身”;进而“以孔璋比徐羡之”,阮瑀“似指谢晦”,而二人虽与曹丕亲昵,但均未被大用;徐幹因无宦情而置身事外,刘桢则两无所党;而应玚有汝颍节义之遗风,王粲乃“贵公子孙”,二人从属于曹植,其中谢灵运又借王粲以自比。总而言之,“康乐所留心者,止平原一事之本末;而注意者,止仲宣一人之才望”,虽“分写八人之心,只是写平原一人之心事,盖借平原作庐陵影子以写自己心中之事耳”[24]381-382。一场邺中宴集被吴淇描绘得暗流涌动。所以,不论是正意还是隐情,谢灵运笔下的这场邺中宴集都绝非一场欢宴。
吴淇的观点看似言之凿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庐陵王刘义真本人本非帝王之材,如《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17]1636。 这是说庐陵王刘义真轻率浮躁,又不蓄德,实非社稷之主。吴淇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修桓、文之业以继魏武,子建做得;修桓、文之事以继宋武,庐陵做不得。辅子建以修桓、文之业,仲宣或可做得;辅庐陵以桓、文之业,康乐决做不得。”[24]384-385在他眼中,刘义真无法与曹植相比,就连谢灵运也非王粲那样的辅佐之臣。但他又辩解道,“康乐自恃过高”,所以以庐陵王比曹植、以王粲自比也未尝不可。那么庐陵王刘义真是否真正赏识谢灵运的政治才能呢?《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云:
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暱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17]1636
原来庐陵王刘义真只不过是欣赏谢灵运的文学才能。又《宋书·颜延之传》云:“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17]1892同样也是欣赏颜延之的文辞而已。因而当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的承诺,只不过是庐陵王刘义真一时兴起的大言罢了,正可以说明他为人的“轻动”与“轻訬”。尽管谢灵运在《过庐陵王墓下作》一诗中,将庐陵王许为知己并表达对其感怀哀痛之情,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庐陵王刘义真最多只是其政治梦想在现实中的无奈寄托罢了。正因为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真正的“晤言之适”,谢灵运才会为自己拟构了一场完美的邺中宴集。
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们有必要对谢灵运此诗重新加以解读,在正确分析邺中宴集的基础上探求诗旨。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谢灵运的序文基本上是依据曹丕《与吴质书》一文进行摹拟的。例如序文给曹丕设定了两重身份,既是宴集之主,又是能与诸子“获晤言之适”的知音,这与曹丕《与吴质书》中“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的师友二重身份相似。同时,序中“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的表述,即《与吴质书》中“后生可畏,来者难诬”之意;其“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创”之语,亦化自《与吴质书》中“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二句。但颇有意味的是,谢灵运并非一味忠实地摹拟曹丕此文,而是突破历史时空的限制,使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合在,昆弟友朋二三诸彦俱存,更假曹丕之口极力称颂这场邺中宴集为空前绝后。因此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这是谢灵运有意在拟构一场从来都不曾有过的盛宴。
至于邺中宴集上所作之诗,谢灵运也在遣词造句上多化自《与吴质书》和诸子之诗,这在《文选》李善注中已经明确指出,如“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化自《与吴质书》中“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一句,“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化自“高谈娱心,哀筝顺耳”一句,又“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象”化自曹植《送应氏》“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和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二句,“爱客不告疲,饮宴遣景客”则化自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一句等。但是诸子之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宴诗,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方伯海语云:“切各人处俱在上半截,下半截只是叙一时共事游讌歌舞之乐。”[15]卷七也就是说,诸子之诗均是遵循上半部分写身世遭遇、下半部分写宴游之乐的模式创作的。这个主题和宗旨在宴集主人曹丕的诗中已经有所交待,即“莫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相遇”即昆弟友朋二三诸彦俱存,“此欢”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合在。
所以在诸子的诗中,谢灵运为了体现相遇不易,首先花费大量笔墨描写诸子此前遭遇到的丧乱流离:
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象。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20]《王粲》,140
皇汉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沦关西,袁家拥河北。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羁勒。岂意事乖己,永怀恋故国。[20]《陈琳》,144
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违寒长沙渚。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20]《应玚》,151诗中描写王粲、陈琳和应玚等人在汉末乱世中四处寻求栖身之所,即便暂时得到归宿也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或郁郁寡欢欲图他处,或思乡情起欲归故山。其后,谢灵运便叙述诸子终因倾心贤明而陆续投奔曹操,正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兹集于国矣。”[11]593以上便是诸子诗歌前半部类似生平小传似的描述,真可谓命途多舛、相遇不易。在谢灵运的笔下,诸子仿佛正从四面八方历尽艰险地奔赴这场空前绝后的邺中盛宴。
而在诗歌的后半部,邺中宴集才正式展开。谢灵运首先描绘了宴集主人曹丕爱贤若渴、殷切好客的形象,如“公子特先赏”,“不谓息肩愿”[20]140,“爱客不告疲,饮讌遗景刻”[20]144。 紧接着,宴集的盛况便呈现出来:
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20]《魏太子》,136
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绸缪清燕娱,寂寥梁栋响。[20]《王粲》,140
夜听极星烂,朝游穷曛黑。哀哇动梁埃,急觞荡幽默。[20]《陈琳》,144
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20]《徐幹》,146
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终岁非一日,传卮弄清声。[20]《刘桢》,148
列坐阴华榱,金樽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继以夕阑语。[20]《应玚》,151
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躧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倾酤系芳醑,酌言岂终始。[20]《阮瑀》,153
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哀音下回鹄,余哇彻清昊。[20]《平原侯植》,155
以上谢灵运描绘的情景正如曹丕《与吴质书》中归纳的那样:“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11]591因此,谢灵运借诸子之口表达了对邺中盛宴的憧憬和赞美,即“辰事既难谐,欢愿如今并”、“自从食萍来,唯见今日美”[20]148,153。
也正是这样一场轻松愉快的宴集,触动了诸子对盛宴难常、人生短促的感慨与思考,所以谢灵运在诗中不断写到主客流露出的隐情:有人希冀长生,如“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20]155;有人及时为欢,如“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20]140,144;也有人渴望功名,如“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20]148;更有人希慕隐逸,“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20]146。所有这些情感正说明主客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晤言之适”,即诗中所说的“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倾躯无遗虑,在心良已叙”,“欢娱写怀抱”等[20]148,151,155。 这些表现正是建安诗人的慷慨风骨,这场宴集也变成了建安时代诗人精神的缩影。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安诸子在这场盛宴上得到了真正的礼遇,并且邺中宴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欢宴,而这种畅快恰恰是谢灵运在现实的公宴中所无法获得的。
此外,有关谢灵运该诗的创作时间,古今学者亦有不同的见解。何焯《义门读书记》云:“当是与庐陵周旋时所作。”[16]936邓仕樑《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一文称:“也不能排除作于早年摹拟用功于五言诗的可能性。”[7]又孙明君《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作年考》一文认为:“谢灵运《拟邺中》完成于乌衣之游解散数年之后,大约在义熙十一年前后。”[8]211而顾绍柏《谢灵运事迹及作品系年》则将此诗附于“元嘉四年”下,编在《庐陵王墓下作》之后,认为“盖亦于是年或去年”,即元嘉三年或四年所作[25]439。那么谢灵运此诗究竟作于何时?虽然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今已无法确考,但我们却可以从谢灵运的生平经历大致推断其创作年限。《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了一则颇有启发的故事:
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谢灵运)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17]1774-1775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在责备谢方明不能礼重谢惠连和何长瑜时,有意将谢惠连比作曹植、何长瑜比作王粲,这种想法正与《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中的意旨相同,而他本人或许正是以邺中宴集上爱才礼贤的曹丕自居。那么谢灵运为何会有此之叹呢?《宋书·谢灵运传》云:
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17]1772-1774
原来谢灵运常出游不归,又无上表请急,所以宋文帝令其解职。谢灵运虽假疾东归,但还是对宋文帝抱有最后的幻想,因而上书劝其讨伐河北,希望能趁此良机建功立业,但是这个幻想最后也破灭了。谢灵运只能无奈东归,与友人日夜宴游,借以排遣自己的愤懑,却未料又被有司奏免官职,这对于谢灵运来说不可不谓雪上加霜。因此,当谢灵运见到谢惠连和何长瑜不被谢方明重视时,顿时生发出充满同病相怜的愤慨,这才将自己比作曹丕,希望像当年的邺中宴集那样,“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以此弥补自己政治理想的落空。所以,谢灵运此诗当作于该时,即元嘉五年东归之后所作。谢灵运凭借文学的想象力为天下沦落人拟构了一场邺中盛宴,而自己则成为文学世界中的王者,使得这场宴集成为文人理想和抱负得以尊重与实现的象征。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一组在创作原因和风格特色等方面均饱受争议的作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诗是元嘉五年谢灵运政治理想破灭之后的愤慨之作。谢灵运此诗并非意在摹拟所谓的《邺中集》,而是拟构了一场魏太子的邺中宴集,通过摹拟建安诸子口吻的方式,代为创作了八首诗歌,整部作品都试图极力渲染出这场宴集的空前绝后。诗中谢灵运将自己视为宴会的主人曹丕,希望凭借文学的想象力为天下失志之士建构一片乐土,使得盛宴之上的每个人都得到晤言之适,因而这场宴集也成为文人理想和抱负得以尊重与实现的美好象征。
[1]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G]//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M].王秀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G]//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毛先舒.诗辩坻[G]//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邓仕樑.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J].“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994,(1).
[8]孙明君.两晋士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刘则鸣.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考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10]颜庆余.《邺中集》小考[J].古典文学知识,2009,(5).
[11]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黄节.谢康乐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3]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M].乾隆四十三年启秀堂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6]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9]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合刻曹陶谢三家诗·谢集[M].卓尔堪近青堂刻本.
[20]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21]张溥.谢康乐集题辞[G]//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2]朱晓海.读《文选》之《与朝歌令吴质书》等三篇书后[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3]田晓菲.宴饮与回忆:重新思考建安[J].中国文学学报,2010,(创刊号).
[24]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汪俊,黄进德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9.
[25]顾绍柏.谢灵运事迹及作品系年[M]//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78.
A Re-evaluation of Poetic Themes in XIE Ling-yun’s Ni Wei Prince Yezhongji
SONG Wei-s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China)
XIE Ling-yun’s Ni Wei Prince Yezhongji is quite a controversial imitation work in its writing time,literary style and poetic themes.It is not an imitation of the unrecorded Yezhongji,but is a work born out of Xie’s literary imagination,describing a unprecedented grand feast based on the feasts and works of Wei Prince and Jian’an scholars.It is Xie’s sustenance after the disillusion of his political dreams in the fifth year of Yuanjia period.
XIE Ling-yun;Ni Wei Prince Yezhongji;imitation works;sustenance;feasts in Yezhong
I206.2
A
1000-5315(2015)02-0126-07
[责任编辑:唐 普]
2014-09-10
宋威山(1988—),男,辽宁丹东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