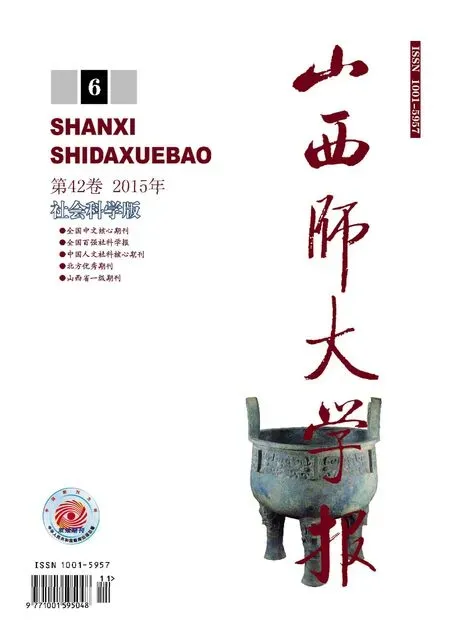现代新诗中蛇意象初探
梁圣涛,蒋登科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意象一直以来都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和范畴,《周易·系辞》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较早论述了象和意的关系并指出了象的用途,而意象第一次正式作为诗歌批评术语出现是在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同时也确立了意象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也可溯源于此。[1]14—20然而现代新诗中的意象及其含义更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白话新诗开拓者胡适的意象观念主要来自国外尤其是英美的意象主义,“诗须要用具体的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其后的郭沫若、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包括艾青和九叶派的意象运用及其观念探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和意象艺术。[2]而蛇这一意象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例,与其说是对传统蛇意象的唤醒与改写,不如说是对西方这一意象的移植和本土化,因此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这一意象在本国传统和西方视野中的基本内涵及其使用变迁,以便于考察其在现代新诗中对于传统诗歌意象的偏离策略以及所产生的美学效果。
首先从字源上来看,《说文解字》云:“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屈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3]678以蛇作为日常问候语,可见早期人类对蛇这一形象存有的畏惧心理。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蛇的形象最为集中和丰富的要数《山海经》,据学者叶德均统计,其中提到的蛇有70处之多,泛述怪蛇、大蛇的地方则有13处。[4]从中可以看出,在早期社会,蛇是以神怪异兽的形象出现的。另外此书中还记载了古代58个有图腾信奉的部落,其中有8个以蛇为图腾。其实对蛇的图腾信仰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十分普遍。据闻一多和李泽厚的观点,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最初也是从蛇的形象演变而来的。[5]21由此来看,典籍和神话中有关盘古、伏羲、女娲、夸父等中国早期神祇人首蛇身或龙首蛇身的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且后世传说和民俗中有关蛇的吉兆、祥和等正面意义也多源于此。然而在传统诗歌中蛇的意象并不是很多,且除了个别刻意吟咏外多是负面含义。如《诗经·小雅·斯干》“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里说的是吉兆;李白《蜀道难》的“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清代吴恭享《得君复上海书却寄》道“凶岁大兵俨相接,长蛇封豕欲安归”,这些诗句蛇的意象多是邪恶凶残。而郑板桥《比蛇》诗“好向人间比长短,截岗要路出林塘;纵然身死犹遗直,不是偷从背后量。”咏蛇明志,确为少见。[6]
西方视野下包括埃及、印度等蛇意象的最初涵义及图腾崇拜、巫术仪式与中国大同小异,其中对西方文学艺术中蛇意象影响最大的要数《圣经》。蛇诱惑人类始祖偷吃禁果有了智慧和性爱从而遭上帝惩罚,成了诱惑者、邪恶、卑鄙、狡猾、欲望的代名词,带有原罪意识;与此相似的还有拉弥亚的传说、拉奥孔父子被毒蛇咬死的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美杜莎和《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等。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蛇的意象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异,尤其是在反抗神学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时代风潮影响下,蛇意象在文学和艺术中经历了空前的改写和释放。蛇作为撒旦的化身成为上帝权威不屈的挑战者和反抗者,把智慧和文明带给人类,其潜在的机智、灵活、叛逆、自由和独立等含义被不断发掘和重视。如济慈长诗对“拉弥亚”意象的重新塑造,雪莱诗歌中多样的蛇意象,波德莱尔诗歌从不同侧面对蛇意象做出开掘以及D.H.劳伦斯《蛇》诗以日常化内心独白表达了对蛇的喜欢和赞美等。而受西方文学艺术影响巨大的中国新诗,其蛇意象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第一个高峰,鲁迅笔下有众多蛇的意象,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美女蛇”,《我的失恋》有“赤练蛇”,《伤逝》中把“新生的路”比作“一条灰白的蛇”,《社戏》《论雷锋塔的倒掉》等文章中也多有涉及。无论有意还是无心,小说集名“彷徨”也是古时对蛇的一种称谓,语出《庄子·达生》:“野有彷徨,泽有委蛇”,成玄英疏“彷徨”为“其状如蛇,两头五彩”[7]。以上蛇的意象多半没有出离其传统意蕴,而《野草·墓碣文》里蛇的意象却颇具现代意味,其精神蕴含明显来自西方。试看“……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8]207这一情节常被研究者视为现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主体处境的经典隐喻。而蛇这一意象在此承载的便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形象,这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自我追问和自我纠缠的一个心灵症结,直到四十年代诗人穆旦仍苦苦探索着“丰富而痛苦的”自我。此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痛定之后,徐徐食之”,顺着以上思路分析,可以发现此诗中蛇的意象极为生动地象征着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自我的矛盾、分裂乃至崩溃式的自戕,体现在鲁迅身上就又多了一层自我怀疑、自我解剖和试验的文化意义。[9]“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0]81;担心自己身上的毒气鬼气贻误青年,虽创痛酷烈,只好抉心自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体现着一个中国脊梁式现代知识分子伟大而痛苦的灵魂。彭小燕认为《墓碣文》把鲁迅对虚无、积极无畏的体认推到了最高地带,而此段文字是它的“更精深之处,这也是整个‘野草世界’的最深处”。[11]如果此论成立,那么此处蛇的意象功不可没。新诗史上这种从鲁迅开始的对自我及灵魂的严酷审视延续不绝,直至当代且俱以蛇意象作为隐喻主体,欧阳江河的《蛇》纠缠了个体精神、生存及文化处境的痛苦蜕变,西渡的《蛇》隐喻着灵魂的困境及其表达。
其实,现代新诗中蛇意象更早的出现是1922年文学研究会新诗合集《雪朝》中徐玉诺的《跟随者》,“烦恼是一条长蛇”、“烦恼又是红线一般无数小蛇”,在新诗史上较早地用蛇这一具体意象来写抽象感觉,且极尽其妙。“我走路时看见他的尾巴,/割草时看见了他红色黑斑的腰部,/当我睡觉时看见他的头了。”用长长的蛇来象形诗人的烦恼,漫长、痛苦而又惊悚。“开眼是他,/闭眼也是他了。”无时无处不在的烦恼,厌恶纠结却又挥之不去。最后诗人不无无奈地说:“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他很尽职,/一刻不离的跟着我。”可见这烦恼已侵入骨髓,形影难分。此诗紧扣蛇的形体特征,虽仍是原初含义,却极为传神地再现了一般人难以言说的心理感受,深刻道出“五四”落潮以后当时知识分子“不明方向、无所出路的孤苦无告的苦闷情态”。[12]95—96而冯至写于1926年的《蛇》似乎承此而来,其中“它是我忠诚的侣伴”一句与徐诗结尾颇为相似。冯诗以蛇喻寂寞,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名句“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当然冯至此诗的重心还不止于“寂寞”上面,据其晚年回忆,当时“看到一幅黑白线条的画”,“画上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立,头部上仰,口中衔着一朵花”,“我看不出什么阴毒险狠,却觉得秀丽无邪。它那沉默的神情像是青年人感到的寂寞,而那一朵花呢,有如一个少女的梦境。”[13]197—198于是创作了这首以“蛇”为题的抒情短诗。
此诗以蛇为中心意象,层层铺展开来,从“寂寞”写到“乡思”再到“梦境”里“绯红的花朵”。很明显抒写的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青年人正常的单相思或青春期渴望,心里炽热而外表却故作冰冷,直到不敢言语,辗转反侧,希冀着万一能梦到情人。第一节用蛇写寂寞,青春的寂寞像蛇一样长长的,却又冰冷得不能说,给人奇美之感。[14]441第二节和第三节蛇的意象就具备了结构性功能,甚至悄悄地把“蛇”和“我”作了一个偷换,其实是“我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我在想着”“你头上浓郁的乌丝”,取蛇栖身草丛的属性。第三节取蛇无声无息特征,代指“我”轻轻潜入姑娘的梦境,惊悚而又幻美。回过头来,如果结合蛇意象原初的性象征,再来看诗中“茂密的草原”、“浓郁的乌丝”和“一只绯红的花朵”也就具有压抑变形的性意味,但这并未降低此诗的格调,反而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上丰富着这首诗的内涵。以蛇写寂寞到1940年郑敏诗《寂寞》中再次出现,“‘寂寞’它啮我的心像一条蛇/忽然,我悟道:/我是和一个/最忠实的伴侣在一起”[15]23—27,显然受了她老师冯至的影响。
如果说冯至诗中的性意味还不够明朗,那么被苏雪林诩为“颓加荡派”邵洵美的《蛇》就是赤裸裸的有关女人和性爱的情色诗。这首诗里蛇的意象被更多地赋予了女人的特征,全诗处处在写蛇却无处不是女人,蛇的属性与女人的特点缠绵交织,难分彼此;蛇垂下的“最柔软的一段”像“女人半松的裤带”,也像女人的腰身;“血红分叉的舌尖”既是蛇的也是女人诱惑而可怕的双唇;蛇身体“捉不住的油滑”更是女人的特征。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较出色的却是他非但把蛇美人变成诗人(我)的对象,而且还要在对象身上做爱,达到一种极致的欢欣(当然也有死亡的意味),最后带入神话的意象——云房、冷宫——恰与诗的开头(宫殿、庙宇)相呼应,产生的却是中国古诗的效果: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性爱和疯狂联在一起”;[16]71“男性的颤动”、“双倍的欢欣”和“磨光的竹节”都是这方面的表征,以蛇写性爱过程确为少见,这首诗奇崛而又诡异。同时此诗还借助蛇的意象传达出一种既舒服又伤痛,既担心又渴望,“冰冷里还有火炽”,欢欣里透出凄凉的感觉,形象准确地描摹了复杂的性爱心理却又不囿于此,又有一种繁华历尽的空虚和忧伤意味。此诗中蛇的意象虽主要是女人和性等传统意蕴,却也在邵氏特有的唯美和颓废气息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穆旦的《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19]63—67写于1940年2月。此诗借圣经中人类受难根源的解释,来写现实中人类尤其是清醒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痛苦。诗歌在开头直接引用了《旧约·创世纪》中“蛇诱惑人类被放逐”的故事,接着写道:“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地上”,“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这条蛇诱惑我们。有些人就要放逐到这贫苦的土地以外去了。”这段引述不仅造成了与《圣经》故事互文性效果拓展着诗歌的外延,而且 “蛇的诱惑”这一意象也成为解读本诗内涵的一把钥匙。众所周知,也如诗中所述,《圣经》中在蛇的诱惑下,人类偷吃禁果获得了智慧和性爱却丧失了天堂的安乐和永生,终生忍受“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那么第二次蛇的诱惑呢?从诗中可以看到“夜晚的狂欢”、“污秽的小巷”、“家家门前的死寂”、无聊重复的德明太太和汽车、无数“是的”和机械而“痛苦的微笑”,贫民窟和玻璃柜, 随处可见的空虚、疲惫和无目的,人像“枯落的空壳”麻木地消耗在日用品上,“微笑着在文明世界里游览”;在蛇的诱惑下人类“二次被逐”,得到惩罚是“诉说不出的疲倦,灵魂的哭泣”,甚至连真实的哭泣都被剥夺,是“永远的隔离”、寂寞和空虚,连贫穷和劳役的权利都要失去。这里通过“蛇”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的表达着人在现代文明和庸常生活中逐渐远离生命真实和丧失自我的惊醒。但到底何去何从?诗人心中也没有确定的答案,“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其实这也是穆旦一贯思考的主题之一,《从虚空到充实》《童年》《线上》《成熟》等诗多有涉及,《玫瑰之歌》中“什么都显然褪色了,一切都是病恹而虚空”和《还原作用》中“污泥里的猪”“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都是明显的表征,怀疑与不安,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惊醒,对历史文明的反思甚至包括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与担忧,[18]这些都共同彰显着一个丰富而痛苦的灵魂,构成了穆旦诗歌巨大的精神能量和丰厚的阐释空间。而蛇意象在此就暂时提供了一个可以捉摸而进入的参照,也无形中被灌注了无比丰盈而复杂的精神内涵。
当然,现代新诗中还有其他关于蛇意象的作品,但其基本内涵和表现方式都不出以上几首诗歌。通过对这些典型文本的细读,可以看出现代新诗中的蛇意象,虽有取自传统的“畏惧”、“厌恶”、“淫邪”等负面含义,但在具体作品的展开中却并不如此单纯,而是更多地利用新诗语言贴近口语的便利,充分借鉴西方文学艺术中蛇意象的蕴含及其表现方法,通过自觉改写和嫁接来更妥帖地表达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真切的生命体验。虽然上世纪末以来弘扬传统的呼声日渐高涨,如郑敏、李怡和邓程等,但不能遮蔽新诗及其意象诞生与成熟的另一重要资源即西方诗歌,继承传统从来不意味着排外,相反中国诗歌要继续前行和取得成就,就必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且古今杰出的诗人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蛇意象在现代新诗中的成功转换和运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进入现代以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维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入现代,只能退居背景或呈点块状地影响新诗的取向与发展;作为历史文化形态的传统只有进入后人的理解范围与精神世界,并随着当代人的认知流动而不断自我激活与重新展开才成其为传统。[19]279蛇意象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借助外来资源不断地自我更新与拓展,在新诗中重新展现出有别于传统且更富现代魅力的独特意象。
[1]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J].天津社会科学,2004,(6).
[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叶德均.《山海经》中蛇底传说及其它[J].文艺先锋,1933,(6—8).
[5] 蔡春华.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6] 宋向红.诗歌蛇意象的文化意蕴解读——以部分中西诗歌为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7] 王诗客.论隐喻的辐射空间及其现代变迁——从鲁迅《野草·墓碣文》中的“蛇”谈起[J].浙江社会科学,2011,(2).
[8] 鲁迅全集:第2卷·野草·墓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富强.提灯寻影 灯到影灭——从《墓碣文》看《野草》[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10] 鲁迅全集:第11卷·两地书·二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野草》: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正面决战”(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
[12] 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13] 冯至全集[M].韩耀成,等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4] 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一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15] 郑敏文集·诗歌卷(上)[M].章燕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6]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A].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7] 穆旦诗全集[M].李方编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18] 段从学.穆旦对抗日战争的认同及其诗风的转变[J].社会科学研究,2005,(4).
[19]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