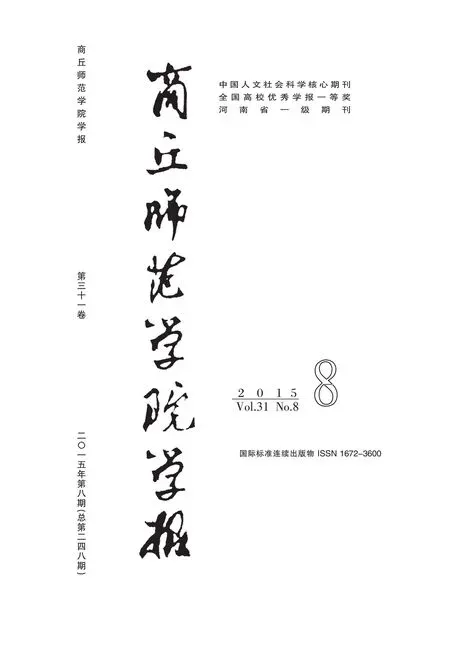从实践到后实践:论人与自然关系之哲学向度
宋 丽 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从实践到后实践:论人与自然关系之哲学向度
宋 丽 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生态文明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和目标。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当下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的热点。以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以实践的现实和经验维度为视域,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后实践的思维方式则从实践的超验维度出发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借鉴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注重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联,注重对群体和个体思维方式的超越,强调自然的普遍秩序同个体行为自由之间关系的内在统一。从实践到后实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反映了从经验理性到超验理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从物质文明到生态文明时代主题的转换。
实践;后实践;人;自然;生态
实践概念是哲学史上较为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什么是实践?一般认为,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实践密不可分,社会生活的本质性问题都能在实践中找到根源。不仅如此,实践还是人的存在的最本质的特征,换言之,人以实践为其存在方式。以实践为视域,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同时,它也是哲学上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维度。借助于科技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各种本质上的自由,但自然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影响也日益加深。随着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出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定位并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成为时下的热议和焦点。
一、实践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样态
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反思离不开对现实对象性活动的观照。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的角度看,自然是人类生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重要的审美资源。人类常常以主体的身份作用于自然,并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了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在实践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界限和主从性质,从下文几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认识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关系是指自然是作为主体人认识的客体而存在的,二者之间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深化和扩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经历了畏惧自然、崇拜自然、认识自然的系列过程。在此阶段,人类一方面摆脱了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学会了从社会生活和实践中解释未知的自然现象和存在,把自己从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6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发源地和最终根源;另一方面,人类不但能认识自然的表象,更会利用分析和综合的理性能力认识和探求自然的本质。这使得人类理所当然地从自己的视角思考自然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二)实践关系
实践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不仅增强了人类本身的自然力,同时,人类通过创造性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品,并使自己明显区别于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47。改造自然的活动一方面使得人类获得了相对于自然的某种优越性,人类的主体性日渐澄明;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活动使自然日益走向人化,日益进入社会生活的领域,成为人化自然。人类不但能自觉地引发、调整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使其向有利于人的方面发展,而且能使自然物渗透进主体的因素即客体主体化,产生自然所不能自生的新性质。对人而言,自然具有工具的性质,成为人类谋生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价值关系
一般而言,所谓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即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和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属性和特征之间的关系。自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人类的需要成为衡量自然价值的重要因素。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的驾驭和控制带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当然之义,自然因此便沦为人类的工具。人类以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对自然施加影响,使其同自然相关的实践活动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其实质是以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最终导致了人本身的异化。因此,对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扬弃,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将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其直面自然的价值,从而对自然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
(四)审美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指自然作为人在审美活动中的特定对象,从视觉或者心理上与审美主体的情感、经验和价值取向产生某种共鸣,进而使审美主体产生愉悦、轻松并回归内心本真的状态。在对自然的审美活动中,人以审美主体的身份与自然对话,自然作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审美客体而存在。这种审美活动发生的领域非常广泛,不论是在生产实践还是日常生活实践中,当人的实践活动和活动的成果感性直接地显示出人的智慧、力量和才能,确证人的自由的时候,在满足人的功利需要之外,引起一种与功利无关的精神上的愉悦,这就是本质意义上的美感,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劳动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7。人类对自然的静观,乃至人与自然合一所达到的无我之境中,自然成为主体人的内在世界的一部分,两者并无二至。人对自然的无功利性的审美情感和体验,形成了其与自然之间的生生而和谐。人向自然回归,并内在于自然。
综上所述,在实践的视阈下,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考察着重关注以下内容:其一,人类作为自然的主宰而存在,是一切行为目的和价值判断的中心,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中。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控制和征服,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主客二分的倾向。其认为在自然界中人类是中心,其他生命的存在具有附属作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旨在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优越性和主体地位。然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在这种观点中,作为中心的不可能是人类的整体,而只能是人类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与其说它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如说它是形形色色的“群体中心主义”。由此,人类主体便成为一个虚幻的概念。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和危机,部分是由于这种所谓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心主义所导致。因此,传统的实践视域下,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真实的主体;若要真正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澄清“人”的内涵和外延。其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考察,始终立足于实践的现实维度。人在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再将经验中得到的认识应用于自然,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中, 实践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自然和人之间冲突的产生和解决,也往往求助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实践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依托和出发点。但是,实践是否是自本自根的?它不受任何因素制约而具有恒常的性质吗?实践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扬弃的人的对象化的活动。实践活动必须具备主体、客体和劳动手段(包括生产工具)等要素。实践主体有独立的意识,同时又受着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实践的客体和劳动手段,则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实践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意味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问题上的多维性。由于对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的高度关注,使得实践的视域往往成为经验的视域,从而对实践的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和超越现实的维度关注不够。以经验为核心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然会使得人类的认识以及活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问题引发了有些学者的思考,他们将实践的视角放得更远,并试图解决以上困境。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理论探讨
以科学和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将人对自然的驾驭和利用发展到了极至。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上预设了自然的无限可承受性和人干预自然的合法性。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承受性的短见,使得社会经济因忽视生态完整性而走向了片面发展的路径,并导致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为挽救和解决此危机,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和主张。
(一)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
后现代学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皆源于现代性的本质,源于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自大和对自然的强权使人类忽略了自然的自主性,将其变为人的附属品。人和自然都具有生态学的意义,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因此,人类的出路在于扬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重建一种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世界万物和谐同在的后现代逻辑上的理想国。
(二)自然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阐释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持有自然主义观点的理论认为:生物圈中的动物、植物等同人类一样,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它们也是伦理和道德主体。生物、物种同人一样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些理论观点主张以环境整体主义作为其最高目的。面对自然,人类的行为无论是初衷还是最高目的,都不能忽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无疑,这些理论的基础是自然主义。其从纯生物学角度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其所倡导的行为模式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三)生态人类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
美国哲学家诺顿提出生态人类主义。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中,它偏重于人类的安康。此观点坚持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上的误区。它是文化知识渐变积累中出现的文化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把自然纳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框架。它反对人类和自然平等,提出人际平等和代际平等。这种生态伦理学理论把人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关怀推广到生态上。不难看出,生态人类主义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又区别于自然主义的主张,是在对自然价值的重估和关注上对人类主体的价值印证。
(四)人与自然统一的共生理念
这种观点指出,协调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必须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重新定位,从制度上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互益的机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生产力中客体系统中重要的内容,它构成了生产力的源泉。因此,自然和人的经济主义行为之间相互依存。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在的。所谓共生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指向之间的相容、互惠和互利关系。曾有一个时期,人与自然是在不对等的条件下发展的,但自然本身对人实践的限制作用并未突出表现出来。基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类对作为其生存环境条件的自然的某种关注,短时期内漠视了自然界的不平衡发展。随着生态问题的出现,人类逐渐发现,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的成功是短暂的。因此,要在共生的理念下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三、后实践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之哲学向度
人毕竟是思想的存在。人类的理性中除了经验理性外,理性还具有超验的特点。只重视实践的经验维度,忽视对实践的超验维度的考察,往往会导致认识和实践中的偏差。本文所谓的“后实践”,与对“后实践哲学”的认识密不可分。那么,什么是后实践哲学?它和实践哲学相比有何特征?所谓后实践哲学“只是‘实践哲学’之‘后’的一种哲学探索的精神姿态”[2]。这里所说的“后”不仅仅具有时间的向度和意蕴,它旨在对实践的反思和超越。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研究上,从实践的现实性维度直接转向实践的超验维度,这是“后实践”哲学视域最明显的特征。“后实践”视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不简单强调“人”或“自然”的主从问题,而是注重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联;其超越群体和个体的思维方式,彰显了独特的生态智慧;自然的普遍秩序同个体行为自由之间关系的有机结合,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因此,后实践视域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已经从经验维度转向了超验理性。随着环境等全球问题的出现,从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一种理论资源。从此视域出发,并且结合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向度。
(一)辅万物之自然:调和自然的无限性与人自身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生态理念
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理论观点中,往往关注于自然的某一个属性和特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么将人的主体特质无限张扬,突出人的宇宙之尊的地位;要么提升生物、物种的地位,与人齐而论之。事实上,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思维出现了“前识”和某种“定势”,似乎离开了“人”和“自然”的话语范式再无更好的见解能正确界说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共生理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一面,避开了对其关系孰主孰从的争论,指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路径。综观以上种种理论,其话语权掌握在人类手中,这样一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则始终无法离开对人、对自然本身的考察。
就自然而言,其存在和发展本质上具有自发性。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211不言的自然呈现出天然的性质。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介入,自然呈现了人化的特点。这并非意味着自然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个性,而屈从于人。即便自然界中个别生物、物种会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而消亡,但自然本身不断自我更新。自然的整体过程具有无限的特点。相比而言,人类本身的自然力具有局限性,无论是从感官能力还是体力上,很多地方远不如某些生物。仅从寿命而言,即使注重养生并借助于现代医学技术,人类也活不过某些动物和植物。人是有限的存在,人力图通过科学技术实现对自然的统治。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深化和扩展。但现实中,对自然施加影响的并不是整个人类本身,而是单个的个体或者群体。这样以来,人对自然的理解就是以有限理解无限。这势必会造成很多问题。那么,人与自然如何对话才能既突显人的独特性,又不挑战自然的无限性呢?我们不妨放下今胜于古的成见,反观一下古老的中国智慧。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69这里的“自然”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说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道纯任自然;就道和万物的关系而言,万物自己如此。由此可见,老子认为人和万物包括和自然界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与客体、主干与附属的关系。人同天、地和道一起作为宇宙中的“四大”,人的地位并不优越于天地万物和自然。具体而言,人对待包括自然在内的万物的态度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4]301。“辅”恰当地表达出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在“辅”自然的过程中,有限的人类同无限的自然才能合二为一。陈霞强调指出,人没有办法不把自己当中心,但这个“中心”是责任性中心,即是说人类对自然负有顺应、保护的责任,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安然和自然同在。可见,人类的活动始终无法离开“以人为本”的路向。那种认为可以完全摈弃人类中心、敬顺自然的主张,是纯粹自然史的问题,并不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以道观之:超越群体思维方式和个体思维方式的生态智慧
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群体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常常存在着群体和个体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生态危机来看,人类唯有与自然和谐共处,方能解决生态问题。这必然要求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与自然的关联中以超越高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始终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然而,人类往往以群体或者个体的形式作用于自然。由于群体或者个体行为的目标限制抑或出于经济增长等考虑,往往会忽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上,国家和地方可以通过立法的手段和建立生态制度来限制群体和个体对自然的误用。目前,国家对自然环境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日益增多,执行得好,可缓解群体及个体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解决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个体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问题,需要将自然变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素,而不是将自然始终看成是人的外部要素。人与自然本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在中国道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庄子从“道通为一”的哲学本体思想出发,得出“以道观之”的认识路径。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5]193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划界,将二者的地位进行高低区分,这种观点显然是“以物观之”。与此不同,“以道观之”更多体现地是超越个体和群体乃至类的界限,以形上的智慧从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万物,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万物,都内在地统一于“道”。人与自然“各得其性”,“自足其性”,互不相害,这是庄子所讲的“两行”。因此,超越群体和个体的思维方式对于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法天贵“无”:自然秩序下的普遍法则与个体行为自由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发性的特点。然而,这种自发性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自然的发展和变化表现为一种秩序。在自然秩序的背后,是自然发展的普遍法则。人类个体在参与自然的行动中,无疑会受到自然的普遍法则的制约,个体行为的自由取决于其对普遍法则的遵循。荀子在天人之辨的问题上反映出较高的哲学智慧,他一方面对人的存在本质进行澄明,指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明于天人之分”。对自然普遍法则的认识和遵循,是人顺应自然为我所用的基础。唯有如此,人类个体行为才能摆脱盲目必然性的制约,达到行动的自由。如此以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个体的行为必然要合乎自然的普遍法则。这同古代道家哲学“法天”的思想不谋而合。以天(自然)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化解现实的人的不自在和不自由。贵“无”则是对自然无为的道的顺应。杨国荣也指出:“行动和实践的理性品格,主要便表现为行动和实践过程本身合乎社会规范、体现合理需要、依乎存在法则。”[6]195可见,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对自然法则的遵循是个体行动自由的基础。与此同时,个人的实践过程同时也体现出智慧来。“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了相应于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着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6]271个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行动自由体现为对自然法则的遵循,这是人对自然的德性,也为个体的行动自由获得了普遍性的保障。
当今时代,发展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绿色革命”的号角早已吹响且环保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当代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意识尚在生成之中。自然是人类的生存家园,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下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从不同的视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樊志辉.实践哲学的域限及对实践的自明性的质疑——后实践哲学论纲[J].求是学刊,2000(2).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M].北京:三联书店,2013.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3-26
宋丽艳(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哲学研究。
B0
A
1672-3600(2015)08-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