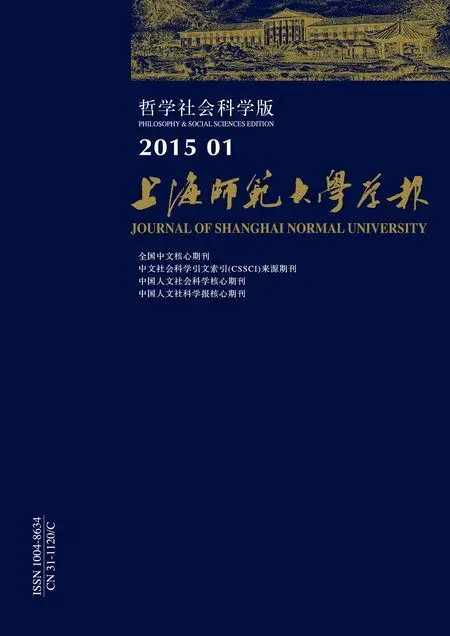论德国劳工培养中的合作主义
陈 莹
(上海师范大学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上海 200234)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劳工市场的均衡和有序至为重要。劳工是和雇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属于雇佣关系的一对范畴;一般来说,劳工指的是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工作的劳动力,从数量上看,占据了劳动力的大部分;劳工培养主要依托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进行;劳工培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行会和工会,它们同时也可以是劳工培养主体;对劳工培养权利归属的不同解答,构成了形态各异的劳工培养制度。分析劳工培养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认识不同劳工培养制度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德国的劳工培养富有成效,因此成为各国借鉴的典范。就德国劳工培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行会、工会和国家共同发挥作用培养劳工,具有明显的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特征。①合作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合作主义确保了劳工培养的职业导向;确保了劳工培养的高效运转。然而近年来,合作主义遭受来自各界的诸多诟病。从外部视角看,合作主义无法应对服务型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从内部视角看,合作主义是产生劳工培养体系结构性问题的根源。
本文从概念阐述、历史背景、传统优势和当前困境这几方面入手,对合作主义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结论。这对于透彻理解德国劳工培养制度的特点,理顺我国劳工培养主体权利归属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合作主义的概念阐述
合作主义首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对于合作主义的内涵,有着诸多的解释,概括起来,它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指的是通过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化合作,来确保各团体的利益均衡。“从政治角度讲,合作主义指的是国家的权利下放给公共的私立机构,尤其是给利益性集团。”[1](P2)其次,它试图将劳资双方整合在一起,并且在它们当中产生一个稳定的关系。它最基本的观点是,劳工和资本合作共生。因此,在现代民主国家,人们形象地将合作主义称为三元主义(Tripartismus),即国家、工会和行会共同发挥作用。
对于劳工培养而言,合作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中世纪,它指的是传统的手工业者通过行会联合培养新生劳动力的组织形式。“行会组织意味着学徒与手工业者之间是一种紧密合作的关系。行会不仅关注其成员的私利,而且关注普遍的利益,行会作为基本的政治实体,构成了连接国家和人民的桥梁,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等级化的秩序。”[2](P58~59)也就是说,一方面,行会把学徒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利益进行捆绑。另一方面,行会将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共同培养新生劳动力。可以说,行会作为一种政治实体,代为行使了相关国家职能。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民主国家的诞生,这种传统的培养劳动力的方式在变革中获得重生,形成了新合作主义(Neokorporatismus),通过国家、工会和行会共同发挥作用,来合作培养新生劳动力。
关于新合作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在新合作主义中,延续了个体和企业之间利益捆绑的传统。企业将劳工培养视为一种权利,将它看成获取人力资源的绝佳途径。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新生劳动力,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而从个体角度来说,获得优质的职业教育当然是符合切身利益的。因此,尽管历经时代变迁,个体和企业之间利益捆绑的传统始终得以延续。
其次,在新合作主义中,个体自由(IndividuelleFreiheit)和国家利益(Gemeinwohl)能够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得益于古典职业教育理论对“职业”概念的解读。古典职业教育理论认为,“职业”概念包含了双重维度。“职业”的主观维度可以顺应个体的内心旨趣,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职业”的客观维度则体现了国家利益,是效率、公正和团结的保障。正是“职业”概念的双重维度,使得个体自由和国家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因此,个体和国家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合作关系。
再次,在新合作主义中,行会和国家之间实现了紧密的合作。具体而言,行会和国家之间的合作表现在职业教育双元制中。双元制的一元是以行会为代表的企业,另一元是职业学校。行会体现了雇主的利益,职业学校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两者的合作,兼顾了雇主和国家的利益。
另外,我们可以从相关权力部门的人员构成上来进一步解读新合作主义的内涵。对此,德国学者贝特格(Baethge M.)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宏观层面,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联邦教育部,其人员均来源于三方代表,且有着均衡的比例(雇主、工会、联邦各州和联邦政府代表,各方都拥有16张选票);在地方层面,两大职能部门,联邦州和行会劳工教育部门的人员构成显示出同样的特征(比如在行会劳工教育部门,雇主、工会和职业学校的代表各占6名);在企业层面,作为基层劳工教育部门,企业委员会由雇主和工会共同组成。按照1972年的《企业法》和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律》,企业委员会对企业教育事务拥有共同决定的权利(Mitbestimmungsrecht)。[3](P439~440)因此可以说,从人员构成上讲,德国劳工培养体系中富有明显的新合作主义特征。
那么,合作主义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要深入解读合作主义,必须勾勒出它的历史轨迹。可以说,德国劳工培养中的合作主义由来已久,并且历经时代变幻留存至今,是一种内生性的制度文化。
二、合作主义的历史背景
1.合作主义的兴衰和复兴
中世纪,行会组织极其发达。“到1300年之后,德国行会开始蓬勃发展。14世纪行会组织已经相当强大,14世纪因而被称为行会的世纪。从15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职业都属于某一个行会或者类似行会的组织。”[4](P28)“行会的功能是极其强大的。尽管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行会的功能还是几乎覆盖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按照‘市民生活水准’,决定着个人的收入水准,并且也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形象;行会的功能也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会调节着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乃至文化艺术生活;行会对于学徒的培养有着严格的规定。”[4](P29)然而到了18世纪,德国行会呈衰退之势。“严格地讲,18世纪后半期开始直至19世纪末,中世纪的学徒培训模式几乎不再存在。”[4](P33)“尤其是1810年施行的从业自由政策”,[4](P34)使得行会影响力达到最低点。“就手工业培训形式而言,自1869年颁布《北德联盟手工业规定》以来,传统手工业培训模式就解体了。”[4](P39)
在欧洲范围内,这一手工业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其历史命运也基本相同。因此,英法德三国的劳动力培养基本遵循同样的发展轨迹。然而,和英法两国不同的是,在德国,到了19世纪后期,手工业又迎来了复兴的好时机,行会也重新得势。
“德国统一(1871—1873年)后,为了应对经济的大萧条,同时也为了稳定政治,政府开始实施中产阶级政策。”[4](P41)“中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民”,[4](P41)尤其是手工业者占据了主力。“从1873年开始,中产阶级运动得以开展起来。”[4](P42)手工业的复兴,正是属于中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从1878年到1897年间,以及在1908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手工业补充条例,极其明显地提高了手工业者的权利。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1897年通过的《手工业保护法》。”[4](P42~43)自此以后,德国行会重新掌握了劳工培养的主导权力。德国行会的职能表现在:学徒教育;学徒教育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咨询;出具职业教育的报告和年度报告;对于非行会学徒的考试组建考试委员会;对于行会学徒的考试组建聘任委员会。[4](P49)
2.新合作主义的诞生
在手工业复兴的过程中,合作主义经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形成了新合作主义。国家权力的介入是促成新合作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将进修学校改造成职业学校的过程中,逐渐勾勒出了新合作主义的景象。
“进修学校成立于18世纪,当时的进修学校多为私人举办,教育状况堪忧,面临倒闭的危险。而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青年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这样的局势倒是为进修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5](P119~120)在这样的背景下,凯兴斯坦纳提出了对进修学校的改革方案:将进修学校改造成职业学校。凯氏的主张被当局所采纳,“在1895年至1914年间,政府对进修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扩建和标准化”。[5](P120)由此,进修学校得以成为手工业学徒培训的有益补充。
一战后,职业学校由行会监控和管理的局面被打破。地方政府和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职业学校事务。职业学校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并构成新合作主义中的一大势力。
总之,如果与英法两国作一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经历现代化历程之后,英法两国劳动力培养中的合作主义已经荡然无存。而德国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主要得益于富有德国特色的中产阶级政策。德国行会虽然经历衰败时期,仍旧以强劲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这为合作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合作主义的保留,培养了大量优质的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合作主义的传统优势有哪些呢?
三、合作主义的传统优势
1.劳工培养的“职业导向”
德国劳工培养体系具有明显的“职业导向”特征。在宏观层面上,德国的劳工市场以统一、完整、同质的职业资格为标准。在中观层面上,劳工的资质化目标具体化为教育职业。在微观层面上,劳工的培养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的。[6](P248~254)
“职业导向”是合作主义的产物。在合作主义中,行会作为企业的代表,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参与劳动力培养,为“职业导向”的生成提供了一种最为合适的土壤。
“职业导向”的优势是明显的。在合作主义框架下,企业既是劳工的招聘者,也是劳工的培养者。因此,企业参与劳工培养的好处就在于能及时更新和调整资质标准。企业是进行职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场所。工作方式的变更,工作内容的变更,最为直接地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职业导向”实现了劳工培养和岗位要求的零距离对接。这使得培养的人才不需要额外的入职培训就可以胜任工作。同时,以企业为劳工培养的主要场所,保证了在教学过程中,所习得的不仅仅是专业资质,还有方法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以企业为主要教育场所,也有利于学习者养成职业归属感。
同时,“职业导向”也是合作主义运转的依据。“职业导向”的原则一旦动摇,合作主义就失去了运转的基础。
2.劳工市场相关者的“双重身份”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联邦教育部,地方层面的劳工培训部门,还是企业层面的企业委员会,人员的构成都来自于三方代表:雇主、工会以及国家。而同时,这三方也是劳工培养的直接参与者,即企业、学徒、学校。
也就是说,劳工市场相关者同时具有劳工教育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这样的制度特点,使得劳工教育的实践问题能够直接反映到决策层面。这就避免了层级管理的弊端:信息在从实践层向决策层传递的过程中容易丢失或者失真。相比之下,在合作主义中,三方代表的双重身份直接促成了管理体制的高效运行。
同时,在合作主义框架下,雇主、工会以及国家这三方组织必须具有相当的行动能力,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才能确保劳工培养体系的正常运作。
总之,合作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优势的发挥依赖于“职业导向”的原则,依赖于劳工市场相关者的行动能力。那么,如今合作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是否依然存在?
四、合作主义的当前困境
1.外部环境的变化
(1)服务型社会的到来
如上所述,合作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必须依据“职业导向”的原则。教育职业的统一、完整和同质化,是行会主导的合作主义得以发挥职能的基础。而服务行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模式。
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转变。服务产业突出的特点是多样性(Heterogenitaet)。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服务产业从一开始就在工作内容、工作组织和发展速度上呈现异质性”。[7](P463~474)由于工作条件、活动范围的林林总总,使得制定一个统一的职业标准在德国日益成为不可能。加上新的交际手段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职业在时间上、空间上和专业上的限制被打破。因此,常规工作模式将被部分时间制的、短时合同制的和新型的就业关系所取代。
服务行业的兴起,意味着传统职业模式的终结。这对合作主义劳工培养制度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以盖斯勒(Geißler K.A.)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随着职业的消亡,传统的德国劳工培养体系也应当进行彻底的改革。[8](P651)他认为,传统的合作主义培养模式是以培养工业的专业工人(Facharbeiter)为主的。在服务行业面前,它显得僵硬、落后,无法发挥应有的职能,因此这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那些局部适应式的改革,比如对教育职业进行现代化革新,已经无法赶上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变化。正是因为不少学者赞同盖斯勒的观点,从1993年开始,对于劳工培养体系的批判,已经深入到制度存废的问题。
(2)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对每一个社会来说,全球化是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因。”[9](P94)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德国劳工培养中的合作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合作主义各方职能被大大削弱,合作主义制度面临着失效的危险。
首先,全球化销蚀了国家权力。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高额利润,许多德国跨国公司纷纷转移资本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国家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在合作主义制度中,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维护社会公正,原本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然而,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国家用于扶持弱势群体的经费也相应减少,从而导致国家职能的发挥受阻。
其次,全球化分解了行会职能。全球化背景下,强市场、弱行会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全球化的中心逻辑就是市场逻辑。因此,成本核算成为企业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企业成本预算中,劳动力培训费用被尽可能地压缩和削减。面对这一情况,行会显得无能为力。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1975年到1985年,劳动力培训位置严重不足。在行会的组织下,尽管企业没有劳动力需求,还是提供了更多的培训位置。而在解决始于1993年的危机的时候,行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据统计,71%的企业对于培训一揽子计划(Ausbildungspakt)无动于衷。②
再次,全球化弱化了工会职能。外国移民以及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进入,使得劳工阶层出现了分化。这大大增加了工会组织活动的难度。与此相对应,工会组织变得日益松散。在工会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之时,工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这使得工会与国家和行会对话的能力日益下降。
总之,服务型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动摇了合作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阻碍了合作主义传统优势的发挥。由此,德国劳工培养体系出现了内部结构的失衡。
2.内部结构的失衡
(1)过渡系统日益臃肿
在合作主义框架下,劳动力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数量。而企业培训位置的不足,成为一种常态。由此,过渡机制应运而生。过渡机制的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政府期待借助过渡系统来缓和年轻人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的困境。当时,政府认为危机是暂时的,因此完全没有考虑结构性改革。然而,一直到1990年代末,这一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从1990年代末开始,政府加大了改革的力度。通过引入两年制的教育职业、降低获得培训师资格的难度、发放培训红利等措施,来促进企业增加培训位置。然而,这一系列的改革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过渡系统日益臃肿。即使在经济形势不错的2008年和2010年,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年人无法获得企业培训位置。参与各种过渡系统的促进项目后,仍然有不少年轻人无法获得企业培训位置。以实科中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有30%仍旧滞留于过渡系统中。[10](P6)
人们不得不承认,劳工培养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在合作主义框架下,过度依靠企业提供培训位置,无法确保劳动力培养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之外,必须发展其他类型的职业教育,才能确保整个劳工培养体系的良好运转。在目前看来,发展全日制职业学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理想的选择。然而,在合作主义框架下,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2)全日制职业学校发展面临困境
比较研究成果表明,丹麦、奥地利、荷兰三个国家,除了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外,全日制职业学校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消除年轻人失业方面,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甚至更有成效。而且事实表明,在上述这些国家,年轻人专业理论知识更为扎实、综合素质也更胜一筹。在服务性社会和知识性社会中,这无疑有助于年轻人提高竞争力。[10](P9)
然而,在德国,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发展受到合作主义体制的诸多制约,始终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首先,在合作主义体制中,合作主义的各方对全日制职业学校的认可度都较低。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更愿意招收接受过企业教育的劳动力;工会则看重企业教育所带来的良好的就业前景;即使是作为全日制职业学校举办者的国家,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也更愿意支持企业教育。
全日制职业学校的认可度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双元制体系中职业学校地位低下的传统的延续。回顾历史,职业学校的成立,是传统手工业学徒培养模式对工业化做出的最主要的反应。工业生产对专业工人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传统的手工业学徒培养模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由此诞生了职业学校。职业学校的成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手工业自主培养新生劳动力的传统。然而,从本质上讲,培养新生劳动力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行会手中,国家权力仅仅是有限的干涉而已。因此,职业学校一直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变迁,职业学校的功能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然而,职业学校的次要地位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就劳工培养而言,相对于企业教育,学校教育俨然是次等教育的代名词。
其次,在合作主义框架下,全日制职业学校无法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原本在2005年修订《职业教育法》之时,有望出台规定,允许全日制职业学校学生参加行会考试。然而,因为行会的极力反对,这一方案破产了。原因在于,行会担心全日制学校和企业形成竞争的教育格局,从而损害企业的利益。因此,全日制职业学校未能争取到法律层面的有效保障。
五、德国合作主义的出路及对我国职业培训的借鉴意义
1.德国合作主义的出路
合作主义将何去何从,将如何继续改革历程,是德国劳工培养面临的重大问题。
(1)尊重自身传统
制度改革必须尊重自身传统。制度不容易改变,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现代化改革历程中,如果全盘否定传统制度,只会离改革目标渐行渐远。
就德国劳工培养主体关系而言,合作主义是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制度形式。这使得德国劳工培养制度在传统和现代化改革的取舍之间,凸显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无论是19世纪末的现代化改革,还是1969年《职业教育法》的出台,无不打上了合作主义传统的烙印。实践证明,只有尊重社会历史文化,改革才能获得最大化支持并最终走向成功。另外,合作主义制度本身蕴含的优势,也为传统的延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顺从传统的惯性,抛开合作主义制度的存废问题,聚焦于解决具体问题,也许是一种可能性。解决过渡系统日益臃肿的问题,可以依赖发展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因为和市场化相比,全日制职业学校保留了合作主义体制下劳工培养的基本特征:它是职业导向的;它是高度结合实践和理论的;它是输入导向的,具有完整性,和相关考试挂钩。因此,以奥地利为榜样,扫除改革的障碍,大力发展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也是对合作主义传统的一种尊重。
(2)借鉴他国经验
全球化时代,制度的互补成为常态。借鉴他国的经验,能对本国提供有益的参考。对德国来说,解决合作主义制度困境的出路在于适度加强国家权力。
首先,通过修改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掌管各类劳工培训的权力。在德国,国家参与劳工培养的形式比较复杂,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两种制度形式都有体现。概括来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中央集权制,而对职业学校的管理体现了地方集权制的特点。企业的主管机构为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而职业学校的管理权限归属各联邦州。原因在于,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地方分权制的特征。“地方分权制是指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体制,即在机构设置上,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之间表现为一种平行的、或合作的、或讨价还价的对等关系,上层对下层权力范围内的事务不加干涉,由下层自主决定。”[11](P182)也就是说,各个联邦州对职业学校事务具有自主权。造成的结果是职业学校各自为政,联邦政府行动能力薄弱。事实上,劳工培训作为一项共同任务,联邦政府完全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无论是学校、企业还是跨企业机构,无论是公共培训还是私立培训,在非学术领域,包括职业教育、残疾人培训、职业咨询、继续教育,联邦政府都有掌管的权力。因此,合理借鉴政府集权制度,通过修改法律加强联邦政府接管各类劳工培训的权力,具有必要性。
其次,在现有劳工培养制度部分失灵时,国家权力加强介入。随着服务型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展开,现有劳工培养制度部分失灵。国家权力加强介入,成为有效发挥政府职能的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各种促进措施以及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建设,成为国家对劳工培养加强支持力度的表现。
2.对我国职业培训的借鉴意义
(1)尊重我国“政府导向”的传统
和合作主义相对,我国劳工培养的主体较为单一,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特征。这和劳工培养的性质以及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关。劳工培养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具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功能。因此,劳工培养有益于整个社会,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点。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对于劳工培养显然责无旁贷。在我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下,我国劳工培养体系采取政府集权的制度形式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的改革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一传统制度的特征。忽视这一传统制度进行改革,必定得不偿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德国劳工培养模式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劳工培养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善,一向奉德国劳工培养模式为圭臬。因此我国曾经引进过不少试点项目,试图通过企业和学校的密切配合来培养高质量的劳动力。然而,这些试点项目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些试点项目,尽管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开拓了一定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然而,这与人们所期待的能够通过试点项目,由点及面,深层次、大范围地提高我国劳工培养的质量,尚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德国合作主义面临的当前困境表明,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因此,社会语境的不同和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引进他国劳工培养模式,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只有适合国情和时代的制度才是最好的。我国劳工培养制度改革必须尊重“政府导向”的传统,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2)我国劳工培养体系应当实现分权化管理
对我国来说,借鉴合作主义制度,适度下放劳工培养各项权力,实现分权化管理,应当是改革的方向。我国劳工培养主要采取政府集权的制度形式。政府集权体制带来诸多问题。
政府集权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中间环节繁多。从国务院、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到省级政府、教育厅及相关部门,再经由市级政府、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到职业院校,然后从所属院系传递至教职员工。在冗长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极易出现信息失真。政府集权体制下,行政未能得到有效监督。行政官员垄断政策制定、经费划拨等权力,为权力寻租、谋取私利等提供了温床。集权体制下,公众利益一旦被侵蚀,政府就丧失了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合法性地位。
政府集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行业、工会等重要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缺失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劳工培养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脚步,导致结构性失业严重,就业层次低下。另一方面,劳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个体难以真正得到全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工培训的牺牲品。另外,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分离,使得相关决策无法获得应有的支持。重要利益相关者在决策层面的缺失,导致相关政策在实践层面难以得到有效贯彻。
针对这些问题,合理借鉴合作主义制度,是一种可行的做法。对于政府而言,需要转变政府垄断决策权力的局面,强调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一方面,适度下放劳工培养权力,进行分权化管理。对传统的政府集权的层级管理进行改革,缩短从决策层到实践层的中间环节,从而减少信息失真,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应当落实问责制度,加强有效监督,确保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合法地位。
在各级政府层面、学校层面和企业层面上,建立健全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机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效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政治精英的头脑中,而是各利益团体相互妥协的产物。换句话说,政策的制定应当是各个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政策制定的过程,并非仅仅在于寻找最理想的问题解决方案。政策制定的过程,关键在于各利益团体充分的协商与沟通,相关政策才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化支持。同时,剖析利益相关者与劳工培养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挖掘和利用各大利益相关者所具有的宝贵资源,最大限度地促进行会和工会等团体在培养劳工方面的协同合作。
总之,合作主义作为和政府集权截然不同的体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参考合作主义制度的做法,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现有体制中的很多问题。
注释:
①合作主义包括传统合作主义和新合作主义。新合作主义和传统合作主义原本一脉相承。在相关德语文献中,对两者并不作区分,而是统一使用合作主义一词。在本文中,除了专门区分传统合作主义和新合作主义的章节以外,为了行文方便,也统一使用合作主义一词。
②BIBB.Berufsbildungsbericht. 2006:31.
[1] Streek W. Steuerung und Regulierung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Die Rolle der Sozialpartner in der Ausbildung und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M]. Berlin,1987.
[2] Howard J. Wiarda.Corporatism and Development: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M]. Massachusett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7.
[3] Baethge,M. Staatliche Berufsbildungspolitik in einem korporatistischem System[A].In: Weingart,P./N.C.Taubert(Hrsg.). Das wissensministerium. Ein halbes Jahrhundert Forschungs-und Bild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C]. Weilerswist, 2006.
[4] Wolf-Dietrich Greinert. Erwerbsqualifizierung jenseits des Industrialismus, Zu Geschichte und Reform des deutschen Systems der Berufsbildung[M]. G.A.F.B Frankfurt am Main, 2008.
[5] Wolf-Dietrich Greinert. Der Beruf als ein Anker deutscher Arbeitskultur-oder wie erklaere ich einem Englaender unsere besondere Berufsausbildungsphilosophie?[A]. Ulrike Buchmann,Richard Huisinga,Martin Kipp(Hrsg.).Lesebuch fuer Querdenker[C]. G.A.F.B. Frankfurt am Main, 2006.
[6] Thomas Deiβinger. Beruflichkeitals, Organisierendes Prinzip“ derdeutschenBerufsausbildung. Schwaben: Eusl-Verlagsgesellschaft MBH Markt,1998.
[7] Werner Dostal. Der Berufsbegriff in der Berufsforschung des IAB[A]. Gerhard Kleinhenz (Hrsg).IAB-Kompendium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Beitraege zu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C]. Beitr A B, 2002,250.
[8] Geiβler K A. Vom Lebensberuf zur Erwerbskarriere. Erosionen im Bereich der beruflichen Bildung[J]. Zeitschrift fuer Berufs-und Wirtschaftspaedagogik, 1994,Jg,90.
[9] 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 Marius R Busemeyer. Reformperspektiven derberuflichen Bildung Erkenntnisseausdem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Bonner Universitäts-Buchdruckerei,2012.
[11] 成有信,等. 教育政治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