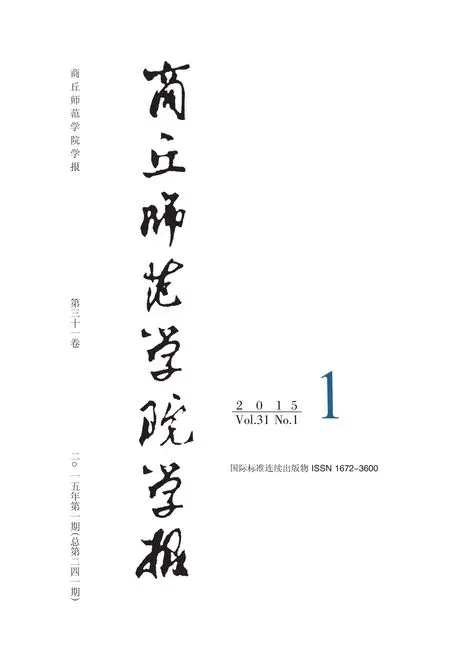论乌热尔图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类型
罗宗宇
(湖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外来者形象是一种他者形象。外来者从某一民族、地域或国家进入到另一民族、地域或国家,常常出现在文艺叙述中。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沈从文的《凤子》和《阿丽思中国游记》、老舍的《二马》和《猫城记》、茅盾的《子夜》、艾芜的《南行记》、玛拉沁夫的《爱,在夏夜里燃烧》、贾平凹的《九叶树》和《西北口》、张承志的《黑骏马》、叶蔚林的《茹母山风情》、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众多知青小说和涉及异国形象塑造的小说都有外来者,它成了一个现当代小说叙事现象。当代作家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讲述者和代言人,同时也是鄂温克族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小说在创造一系列作为鄂温克民族自我形象的萨满、猎人、老人、儿童等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不少外来者形象。根据外来者进入鄂温克民族地域的目的态度及小说的叙事处理,乌热尔图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可分为帮助者、过路者、旅游者、冒犯者和入侵者五类。
相对于森林里游猎的鄂温克人,山外人是他者。山外人进入森林里就是外来者。在乌热尔图小说中,一些被鄂温克人指称为山外人的外来者进入大森林中,和当地鄂温克族人民一同生活,建立友谊,帮助鄂温克族人民提高社会生活和生产力水平,引导鄂温克族人民走向解放和现代,这些外来者就是一种帮助者形象。如《森林里的梦》中的工作队王队长,小说采用侧面描写,借走出山林受教育又回来当旗长的鄂温克族人奔布之口说:“那年工作队顶着风雪进山,找到了我们鄂温克人,给了粮食、布匹,还为我们治病。”[1]209又如《熊洞里的孩子》,小说以小孩子酿满那和爷爷的经历写1949年冬天来的山外人即共产党对他们的拯救。“在这冻死松鸡的冬天进山,就是来找我们——受苦的鄂温克人。孩子,他们要让咱们也过上你常想的小鸟在天上唱歌,小鱼在河里游,那样没人欺负的好日子。孩子,是他们从熊洞里救了咱们,是共——产——党!”[2]238在此,外来帮助者成为了共产党的政治化身,对其肯定和歌颂具有政治认同的功能。类似的形象还有《瞧啊,那片绿叶》中的老吴,他过去是山外人,现在是民族乡政府的乡长,他执行民族政策,帮助猎民建起了猎民新村,村子里的房子都像画一样漂亮。
外来者形象中的过路者是由于偶然或不清楚的因素临时路过鄂温克族生活地的人,在小说中,他们自身的个性特点模糊不清,基本上起一种构架叙事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展现鄂温克族文化图景、实施文化评价的功能者。如《琥珀色的篝火》中的三个无名无姓的外来者和《绿茵茵的河岸》中的“我”。《琥珀色的篝火》中出现了老汉、中年人和年轻人三个外来者,他们无名无姓,来自城市,在山林里迷了路,又冷又饿,鄂温克猎手尼库在护送重病的妻子去医院的途中,发现了这三个外来者的足迹和危险,尼库钻进森林里搜索并成功救助了三个冻得半死的外来者,然而他的妻子却生命垂危。小说中三个无名无姓的外来者,是作为鄂温克人的他者符号来处理的。他们与尼库的有限对话,并不呈现自身的个性特征,而在于延续叙事,显示鄂温克猎人尼库高尚而朴素的道德与精神品格,如下段文字:
“您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戴眼镜的老汉嘴唇在抖,眼眶湿了。
他坐起来,瞅瞅他们,没说什么。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不论哪一个鄂温克人在林子里遇见这种事儿,都会象他这样干的。只不过有的干得顺当,有的干得不顺当。……他的眼神在这些陌生人脸上慢慢地滑过。那种不痛快的感觉消失了,他心里又觉得很顺畅。这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呀!他们见过多少世面!现在,他们用这么恭敬的眼光望着他——一个鄂温克猎人。他发现自己被人推到一个尊贵的位置,这是难得的心灵里的位置。这是第一次!多漂亮的第一次呵![3]17-18
在此,外来者的遇险经历及获救后的感激和崇拜,从他者的角度肯定了鄂温克人的德性之美。同样的叙事处理还见于小说写尼库烤狍子肉。三个外来者吃光了尼库带的饼和熟肉,满脸忧愁,尼库只好出去打猎,在连个锅桶都没有的情况下,用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将肉炖熟了,“把祖辈传授的古老的生活经验表演出来了,就凭一把猎刀,一双手”[3]22,其中“表演”一词显示了外来者的过客身份,他们对尼库的佩服,正是对一个民族生活文化的肯定。
如果说《琥珀色的篝火》中的外来过路者因其是一个集体而不好作个性化呈现的话,那么《绿茵茵的河岸》中的城里人“我”应当是可以进行个性化刻画的,但小说并没有如此处理。“我”的车出了毛病,在等车修好的时候遇到了“他”,“我”于是充当了“他”讲述自己那段浪漫而忧伤的异国爱情故事的听众。车修好时,“他”讲完故事,骑马离去,“我站在那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望着那片绿茵茵的河岸,想把这最完美的印象记在心里”[4]41。在此,“我”由于汽车故障与鄂温克男子“他”相遇是偶然的,“我”与“他”的对话,并无显现“我”个性的语言,“我”的性格特征也因此模糊不清,而“他”与“我”的对话却呈现出“他”的人性美。“我”作为过路者的看、听和感慨,肯定的既是“他”这一个,也是“他”这一族,“我”成为表现和肯定鄂温克民族的他者镜子。
第三类外来者形象是旅游者。旅游者与过路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有意识有目的地,成了文化穿梭者和进入者,他们自身的个性特征也不鲜明,小说叙事同样让他们充当叙事聚焦者和文化评价者。如小说《萨满啊,我们的萨满》和《缀着露珠的清晨》中的外来者。在前一篇小说中,公路伸进森林里后,旅游者一批批从远方涌来,络绎不绝地出现在鄂温克人的林子里,“好似从另一个世界闯入的”,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一切,“神情好似他们在某一处辉煌的圣地和苍老的古墓之间漫游”[5]164,发现了老萨满达老非和鄂温克文化的神性之美。一批批的旅游者面影模糊,只是作为与老萨满互相“看”与“被看”的对应物而存在。当老萨满发现自己被旅游者当做“活化石”而猎奇、民族庄严神圣的含魅文化滑向世俗的商业文化后,他主动失踪躲在熊洞里。在最后一次出于无奈披上神袍被游客观看时,他发出了“我——是——头——熊”的呐喊,旅游者的猎奇观赏终于让老萨满以愤怒的方式表达出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
《缀着露珠的清晨》也写到了外来旅游者,他们是应邀来参加鄂温克族猎人定居欢庆大会的舞蹈家、歌唱家等人:
这是从远方飞来的鸟儿,头一次飞到这样一片陌生的林子,树枝上的每片叶子大概都使他们感到新奇。说实在的,能陪着这样的名人在村子里转游,我心里也真够畅快。这可是城里来的名人,要不是村里举办鄂温克猎人定居欢庆大会,有野餐,有篝火,人家才不来钻你的山沟沟。[6]165
这些外来者由“我”陪游,他们对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桦树皮文化、驯鹿文化、民歌以及服饰文化都很感兴趣,并对其赞美。“‘昨天,一下汽车,我真呆住了。在车上,我打了个盹儿,睁眼一看,你们猜是什么感觉,觉得自己走进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歌唱家扬着一双细长的眉毛,说得那么动情,两只眼睛闪着迷人的光亮。‘我真想坐在钢琴旁,弹上一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6]166对鄂温克文化的传播者别吉大叔,歌唱家还以称赞佩服的语气说:“你是真正的猎人!”[6]168
外来者形象中的第四类是冒犯者,他们无意或无奈地进行文化犯规。冒犯者的个性特征相对过路者和旅游者更为鲜明,如《森林里的梦》中外来的套鹿人。鄂温克老猎人沙日迪在林子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的足迹,他积极追踪,发现了外来的套鹿人,老猎人于是坚决制止他的套鹿行为。当老人听说套鹿人是因为家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生活惨状被迫来套鹿时,又主动送给套鹿人两张熊皮和五张狼皮。套鹿者以“不能白要你的东西”予以拒绝,谁知沙日迪“脸上露出悲愤、坚毅以及被人蔑视而盛怒的神色,‘你看不起我,看不起鄂温克’”[1]217。外来套鹿人于是收下礼物,向沙日迪猛一个鞠躬,带着对老人也是对一个民族的感动走了。小说叙事通过外来套鹿人的纠错,既展现了外来套鹿人和鄂温克老人沙日迪的“义”,更唱出了鄂温克民族心性美的颂歌。又如小说《熊洞》,其中的林场主任也是外来者。“他”在林场发现有熊后,请“我”当枪手去猎熊,“我”按鄂温克族的习惯保持着沉默和悲哀,“他”却不明白要闭紧自己的嘴,张嘴说了犯忌的话,无意中冲突了文化的规定。
外来者形象中的最后一类是入侵者。与冒犯者的无意或无奈的文化犯规不同,入侵者是故意的文化侵犯者,他们凭借权力或暴力进入鄂温克族地域进行侵略。乌热尔图小说中的入侵者形象有两种,其一是日本侵略者。小说《雪天里的桦树林》写鄂温克人雅日楞和兴泰被日本鬼子抓到山下关押做劳工,日本人川岛将雅日楞摔在地上,用脚踩踏着侮辱他。后来两人逃回森林里。一天,他们在雪天的桦树林里发现了三个日本军人,“小路上急匆匆地奔过来的是三个日本军人。他们耷拉着脑袋,脸色灰暗,溅满泥水的皮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7]47。面对侵略者,他们举起了枪,但当雅日楞发现川岛在其中后,立即制止兴泰开枪,而是选择用川岛曾经羞辱自己的方式解决川岛:
川岛很快从地上爬起来,直奔雅日楞冲去。雅日楞退了一步,双手抓住川岛的右手,用力一扯,川岛趔趄着朝雅日楞怀里扑去。雅日楞闪身动作干净利索,他拽住川岛的右臂,用肩、腰、手的全部力气猛地朝前一甩,川岛顿时双腿腾空,整个身子从雅日楞的肩上甩过去,咚地一声,狠狠地摔在地上。
……
川岛脸色青紫,从地上爬起来。雅日楞重又拉开摔跤的架式,等待着他。[7]50
雅日楞最终赢得摔跤胜利,羞辱了川岛并使其自杀。雅日楞的举动显现出鄂温克人独特的血性和勇敢,小说因表现抗日而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其中也蕴含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
另一种入侵者则是极“左”时期的某种山外人。乌热尔图的这种小说因其对极“左”政策的反思与批判而带有反思小说的味道,其中也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认同内蕴。如《一个猎人的恳求》,古杰耶等鄂温克猎手在极“左”政策下被收缴了猎枪,他本人被山下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了三个月,他弄坏木窗逃回山里。外来者张喜胜和王斌为了追捕古杰耶而进山,在他们抓捕古杰耶的过程中,没有了猎枪的猎人古杰耶力除熊害,只身用猎刀杀死了一头熊,让追捕者惊得目瞪口呆,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鄂温克猎人和文化。小说借波热木老人的口表达对外来者收缴鄂温克猎手的枪实际上也是对侵犯民族文化习惯的行为的愤怒:“可现在,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为啥没收我们鄂温克猎人的枪?唉!是条鱼就把它放回水里,是只鹿就让它跑回山上”,“为啥不让我们靠山吃山?收枪,还随便套死我们的鹿,呸!”[8]149类似的小说还有《森林里的梦》,小说以鄂温克老猎人沙日迪的回忆展开叙事,其中第三件事与外来入侵者相关,“文革”时期的一天,沙日迪在森林里巡视,发现一伙带着红袖标的外来人进山打天鹅,老猎人坚决阻止,被外来者“前进帽”痛骂:“混蛋,你这个老不死的!”“你他妈的好大胆,敢挡我们的驾!”[1]219老猎人愤而开枪警告,却招至毒打,“从西边的树丛中突然冲出一伙人,还没等沙日迪清醒过来,他就被打倒在地。在飞舞的拳脚中,他看见了那顶前进帽”,“带红袖标的这伙人,撇下了他,发疯似地在河岸上挥舞着猎枪,追赶着越飞越高的天鹅”[1]220。他苏醒过来后,对保护动物无怨无悔,并祈祷恶梦快点过去。在此,入侵者因其文化入侵行为而遭到了鄂温克人的坚决反抗,同时更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文化坚守和认同。
比较文学形象学学者亨利·巴柔曾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9]4乌热尔图笔下的外来者形象正是在一种自我与他者的自觉意识中塑造的,是对“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表述,融入了个体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其中有一种“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立场,显现的是鄂温克人对新政权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姿态。由于外来者形象中并没有鄂温克文化的反思者一类,乌热尔图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大体上成为了美己之美的借镜。
[1]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森林里的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2]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熊洞里的孩子[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3]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4]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绿茵茵的河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5]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啊,我们的萨满[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6]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缀着露珠的清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7]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雪天里的桦树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8]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一个猎人的恳求[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9]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