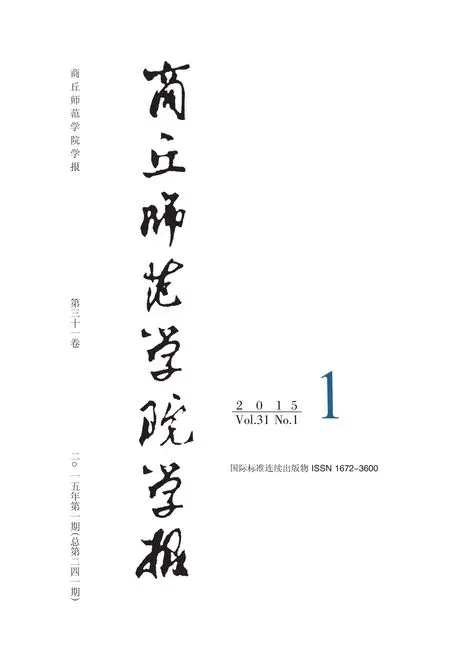儒道家/乡信念的社会学基础
——丧服单元理想模型的“三位一体”分析
安 继 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儒道家/乡信念的社会学基础
——丧服单元理想模型的“三位一体”分析
安 继 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通过对丧服单元理想模型的分析,可以揭示其生活-生产-祭祀的三位一体性,并可以此支撑国人的家/乡信念。宗亲血缘/姻亲地缘作为儒道互补的社会结构基础,全幅面满足国人的传统物质-精神生活。在当代经济学、法学和宗教性问题上,她依凭以人为本的坚实生活基础、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大一统价值共识,将可以支撑现代化的成功转型。
儒道互补; 丧服单元; 家/乡信念; 宗亲血缘/姻亲地缘; 大一统价值共识
一、为什么是孔/老?
孔子和老子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观念让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世代前辈长期服膺呢?它的秘密发祥地究竟在哪里?儒道奥秘的社会学基础实乃宗亲血缘/姻亲地缘的儒道互补,使社会生活得以可能正常进行。它因其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质而成为儒道互补的原型,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深层结构和社会基础。儒家从孔夫子开始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他的两位精神传人孟子和荀子,从理想(仁与人性善)和现实(礼与人性恶)两个向度展开深入思考,对整个中华思想传统和社会历史演变构成了巨大的影响;老子的精神传人庄子和黄老学派,同样以理想个体道德和群体的现实调控成为与儒家既互斥又互补的对立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农耕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形成的东方一重化生活世界,也迥异于西方的一神教商业文明。从中国历史的演变看,秦汉至隋唐的800多年间,儒法两家经互补性博弈,终于通过“以礼入法”,在法理上渗透了法家;接着从韩愈开始,通过程朱陆王对孟子式理/气-性/心并同构于道家的道/德等观念,这就在形而上学层面实现了对道家的裹挟,儒家道家化的同时,道家也儒家化了。
在中国历史上,法/儒/道三家,不仅构成中国思想传统自由问题的资源,更在秩序问题上表现出独立超迈于世界各大文明的宏大品格。如果对仁与礼、道与德进行观念的寻根,它是“孝”:礼以义为质,仁以孝为本。尽管“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韩愈)现实地掩盖了道家的存在,道教与禅宗的互补存在却仍深深地浸润在社会底层的民俗生活中。在仅以“孝道”再也不能全面维持政统/道统历史连续性的全球化时代,面对一神教商业文明的强大压力,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角度,怎样认识“孝”这个根本性观念并赋予其时代精神的新内涵?这是当下学术界仍然要严肃面对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正象科学是技术的前提。人文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人的生活世界内部进行综合的考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的概念清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特点的思想传统和唯名论色彩的观念形态来讲,它们本身即是整全性的,是“理在事中”(晚年冯友兰)或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性质的,学科的人为分割使得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得到关注。所以,与其说这里的思考是哲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人类学或者说是民族学的。
《论语》讲“孝”,而《老子》讲“慈”,这构成儒道互补的基础观念。牟钟鉴认为,老子的“慈”与“母”相关,故道家智慧往往表现为某种意义上的“女性哲学”。就此意义而论,儒道互补也可以说是关于男女-夫妇究竟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的元伦理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指出:与皇权相对的绅权,往往表现为儒道互补的智慧。“孔孟老庄合作努力达到的理想政治”正是要把“天高皇帝远”落实为一种乡土自治性的政治上的“无为而治”[1]6。“小家庭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相同的是数量、在大小上。……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2]39“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2]46,“国是皇帝之家”[2]28,“乡土社会是‘礼治’[2]49……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2]50。不过,“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2]52。“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2]55但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负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2]58。我们不惮其烦地引述费老这许多话,是因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究新知。费老的说法实质性地蕴涵了一个儒道互补的内在结构,在《皇权与绅权》中,他确实一再指出儒道两家联盟的实际有效性①。
传统中国人既信天神,又信祖神,到处可见的“天地君亲师”崇拜是国人信仰的基本形式。不管采取何种信仰形式,作为人最为内在的情感,在人类理性面前,信仰在逻辑上总是自相矛盾的。人类永远不得不面对这一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展开其内在的情/理冲突。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强调反求诸己,要解决的最深层问题,仍然是逻辑冲突的信仰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以儒家的“丧服单元”作为“理想模型”的基本单位进行分析,以证明道家姻亲因素在生活-生产-祭祀三位一体的整全性社会功能上,如何满足了我们先辈们的基本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
什么是丧服单元呢?瞿同祖论宗族说:“一个父系家族——‘宗族’或‘族’——包括所有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的男系后裔,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被同宗的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但是因为人们在人际关系上存在着等级的差别,所以整个宗族就被划分成为若干次级群体。每个次级群体就是一个丧服单元(横线为引者所加,下同),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彼此迥异的服丧等级。每个宗族都包括从高祖到玄孙的直系成员,还包括也是这同一个高祖之后裔的旁系亲属。”[3]15-16此即经魏晋积累、终被隋唐列入法典的“准五服以制罪”中的“五服”,也是《尚书·禹贡》中的“地缘五服观”和与之伴生的“血缘五服观”。
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地缘关系是空间展开的生活关系。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殷周鼎革,宗法血缘关系被提升为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被汉儒抽象为一套五服观念,并非没有客观的历史根据。从地缘关系讲,五服制度是以京畿为中心的五服天下观。以京畿为中心,把世界划为五百里半径递次向外展延的同心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隐含着四方辐辏、八荒来朝的聚合性文化观。服是服事天子,五服地理同心圆使天子得以和神意沟通。董仲舒的宇宙图式将这种五服观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天象神意保障。这种规划得过分规整的理想,作为一种空间秩序的规划虽不切实际,却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理想模型。
二、丧服单元的理想模型分析
关于丧服单元,历来有上五服/下五服之说,“从高祖到玄孙”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我”→子女→孙子→曾孙→玄孙。所谓上五服,理论上讲就是一个人一旦出生,即不得不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上四代男系祖先及其配偶这样的宗亲属和姻亲属,加上自己就构成“上五服”。因为此时,如果他的父、祖、曾祖、高祖辈中,无论有谁逝世,他或她都必得穿戴特制的丧服;所谓下五服,理论上讲就是,一个人假如活到了百岁高龄而逝世,他可能有四代的宗亲属和姻亲属为他或她服丧,这些人都要根据相关规定为他穿戴特制的丧服。这样,任何人就都一定被实际地关联在九代之中,即九族:
“我”为上四代祖宗穿戴丧服,这是“我”的义务;作为下四代的祖宗,下四代为“我”穿戴丧服,这是我的权利。此即所谓“九族”之根本一说,理论的表述即:任何一代人中的“我”都要被关联在如此上、下的两个五服之中,从而构成一上、下五服的加和:5+5=9。
这里说5+5=9,没有对不起弗雷格等算术哲学家们的意思,因为,如果从儒家子孙后继的宗教性意义而言,“我”在理论上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丁克”,所以,为维续这种世代继替的关系,男必为夫而女必为妇。民间称夫妇俱在为“全活人”,只有“全活人”,才能参与操办某种喜庆的仪式。故5+5=9实际上隐含了一个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儒家奥秘,即儒家观念要求一种必然确定性的数学二进制换算关系:夫妇。正是这种二进制规范性要求,使得中国的“家”——不管是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还是理论上可以无限大的大家族——具有了自然数十进制3(核心家庭最小数)→∞的特异性。“天下一家”或与之相关的道德上的“天下为公”,从而能够成为支撑天下大一统价值共识的自然科学基础。故这种丧服单元决非仅仅是儒家的观念,而是一个文明形态的内在奥秘。
据此,我们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理想实验”的逻辑思想方法,借助于二进制,设定出一个“五服单元理想模型”,以便进行分析。这一科学设定可以这样表述:
设任一对夫妇中之男姓之夫为A,妇小4岁为B,以每对夫妇生一双儿女为准,据古代男20岁行冠礼并同时结婚生子为a1,4年后生女为b1,顺延20年后逐次男婚女嫁,顺序如上设定,谱系性地顺次生育子女,而对于此一男系主干家庭来说,即为a2,b2;a3,b3;a4,b4。此十口之“家”即构成一父系理想五服单元的理想模型。
(一)丧服单元理想模型之分析一:结构
如果这对夫妇正好都能活到100岁且子女相序,各代俱全,则80年后A死时,由于他代代单传,子、孙各代均无叔伯、叔伯兄弟、堂兄弟之类的复杂计算,这样的丧服单元也就是一个最简丧服单元。不必引述资料根据,我们可以直接作出以下设定性推算:
他(A)的妇96岁(B),子(a1)及儿媳各80、76岁,孙(a2)及孙媳各60、56岁,曾孙(a3)及曾孙媳各40、36岁,玄孙(a4)及玄孙媳各20、16岁;女(b1)及女婿各76、80岁,孙女(b2)及孙女婿各56、60岁,曾孙女(b3)及曾孙女婿各36、40岁,玄孙女(b4)及玄孙女婿各16、20岁。外孙及媳各60、56岁,外孙女已嫁无服;孙女及孙女婿各56、60岁,余皆无服。五代十口之家,A死为其服丧之宗亲属九人,姻亲属单代八人(四代女即b1、b2、b3、b4及女婿),双代3人[外孙及媳、孙女(b2已计算)及婿]。这些人各依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制,从3年(25个月)至3个月各有等期。抛开时代和地域各有不同的具体规定,理论上可以清晰无误地计算出此丧服单元的人数:A=9+(8+3)=20人。五年后B死,丧服略有降等亦可清晰计算略同于A,即20-1=19人。
(二)丧服单元理想模型之分析二:功能
根据理想模型对丧服单元的人为设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基本结论。
1.只有宗亲亲属才是其五世主干家庭或家族生活单位,也只有此10人才是同一生活单位中人,且依同姓不婚之古制,必有半数为外姓[4+1(B)=5人];且由于A的逝世,此一生活单位的人数降为9,此9人为宗亲属服丧人数。
2.父系宗亲属加姻亲属构成一地缘性生产互助单位。意思是:(1)姻亲属为A服丧,固然可能有血缘的天然关系为纽带,却并不必以此纽带为前提。因为在未曾生育儿女之前,女婿与A并无血缘性自然关系,只是社会性婚姻关系。(2)婚姻关系虽然是将男/女转换为夫/妇的最重要人际关系,却仍然是社会关系;但一旦此对夫妇生育儿女,儿女即成为他和她之间的血缘纽带,他们因此有了血缘关系。(3)由此可以推算,一丧服单元的人数,即按最简关系计算,亦远远大于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主干家庭的人数:[9+12(包括孙女即b2已计入,故)-1=20人],显然,9 < 20。(4)根据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提供的基本观念,这20-9=11的人,家里有了事——不管是生活性还是生产性的——他们自然有前来帮忙的义务,从而即构成一基本的生产互助单位。服丧时的相聚,是形成这一互助关系的默契性生产配合的协调组织方式。
3.丧服单元并非生活单位,而是一个生活、生产二重性复合单位。(1)依传统农耕生产性质以及大量历史资料、现实经验可知:人们以“家”这一生活单位为基础,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因为土地和房屋是不动产,难以做到清晰的产权界定,礼法亦都不准主干家庭父子间别籍异财②;饭菜一“吃”即不再是“财”,故此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事实上也无法清晰异财。(2)由此可知,上述的9+11人就一定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性互助单位。即“丧服单元”是一物质生活-生产的复合性社会单位,一个结构/功能性的二重性单位。
4.丧服单元既为祭祀而设,则任一丧服单元都是一生活-生产-祭祀性(精神信仰,心灵生活)三位一体的基本社会单位。即(1)在祭祀单位意义上,它作为物质生活-生产性单位,既可以满足“养老送终”等一系列具体的人生需要,又可以满足人类心灵的终极关怀,是一物质-精神一体化性质的弹性化社会团体。(2)作为祭祀单位的丧服单元,其社会组织形式融生活-生产-祭祀三种功能于一体,并以类宗教形式将如此自然的“一群人”(相对于基督教堂中,无任何身份之别,一切都原子化地称“兄弟姊妹”,故有数理逻辑的可“集合”性而言,此即荀子意义上的“群”),以血缘/地缘两种自然方式聚合在一起,可以展开全幅的生活世界画面。(3)作为满足终极关怀的中国社会传统组织形式,这三位一体单位的聚合,以行“孝道”为其终极理由。故作为基础的“孝”观念,即通过反覆盖方式,将生活-生产问题一并加以综合性解决。(4)“孝”观念因此不仅是一空洞的伦理-政治观念,借助于“孝”,人生在世的所有问题都得以全面彻底、完善完美地根本性解决。(5)就生产互助意义言,这是宗亲属血缘和姻亲属地缘的地缘性社会团体或单位,这一团体或单位由儒道互补的家/乡信念来支撑;但就遗传学意义讲,孙子和外孙与A实际上都有同样的血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向血缘关系的自然转化,可以解释儒家思想越到后来支配地位越强,从而出现了儒家成为正统、孔夫子成为人格性文化象征符号这一重大现象。(6)就个体人的意义上,我们说“人生在世”即与此上五服、下五服有关:你一生下来,无论有无服丧事情的实际发生,你在理论上都已经承担着服丧义务;一旦有事(“当大事”),你便必须实际地履行一切相关的义务;你履行一生的义务,都是为“向死而生”的你获得相应的对等性权利作预付性的准备,谓之“哀荣”。哀荣是一个人得以“不朽”的权利。此即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之一。
若将此理想模型以图解的方式直观表示,有似于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中的图式③。但由于制作不便,我们这里不再画出。
(三)丧服单元理想模型之分析三:定义
根据上述对丧服单元理想模型的结构/功能分析,我们可以对丧服单元进行如下定义:
丧服单元是借服饰等次的仪式,满足人类生活-生产-祭祀三位一体综合需要的中国伦理-政治秩序传统的逻辑架构。从个体人/关系人的修身到天下一家,借不能承受之轻的生离死别之机,人生在世所有的身/心问题,都能以此逻辑架构进行框套,并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心”得以安顿。
这一结构/功能分析基础上的定义可以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是自足的、人本的,至少在农耕生产条件下,她具备了满足一重化生活世界中人类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
根据理论的理想性要求,在丧服单元理想模型设定中,我们不仅有意舍弃了兄弟姊妹多子女情况下所涉旁系亲属的复杂性,而且只讲到A即“夫”而不述及B即“妇”。仅以此最简最小丧服单元理想模型而论,如果依极端个人主义的男女平等原则,即姻亲属等原则为老人服丧进行计算,结果就正好是自然十进数制的N代人数向二进数制的扩张问题。A即“夫”之服丧人数为20+21+22+23+24+1(妇)=0+2+4+8+16+1=31人,而非前述的20人,实际意义为“儿女辈亲属+孙及孙女辈亲属+曾孙及曾孙女辈亲属+玄孙及玄孙女辈亲属+妇”。
若使A=我(任一男姓),“他”并非仅是被“孝”的对象,而在后代理论性越来越强的儒家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必为“孝者”。依同一原则上推即父辈+祖辈+曾祖+高祖四代亲属,即可形成新的“丧服单元”。以“我”为二进制性质的0∨1(殁或活着),上4下4分别构成上五服、下五服即9代已如上述。在婚姻半径小的情况下,姻亲属的生产互助是一现实。故牟钟鉴先生指出:“道家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女性哲学,它把女性的许多智慧和美德从理论上加以升华了。”④
三、丧服单元之相关经济学、法学及宗教性问题
(一)经济学问题
无论事实上兄弟姊妹的人数如何变化不定,作为自然的血缘关系,它与农耕生活-生产的要求是一致的。由于农耕社会婚姻半径小,生产互助并非虚言,守望相助可为事实。土地是特殊的生产资料,土地与房屋是不动产,只有通过登记来实现所有权的确权。这一登记制度在秦汉已经由法家所确认,即所谓“齐民”;明代发展为“黄册”和“鱼鳞册”,它们是人口、土地管理的文档根据。唐代杨炎的“两税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等,无论具体的治理方式发生何等的变化,围绕人口与土地进行治理,都永远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
(二)法学问题
先秦诸子百家到后来之所以只剩下儒家,正因为丧服单元的结构功能深深切入了社会生活的礼规范。在隋唐之前渗透了法家之“法”,而在宋明之后又裹挟了道家之“道”,这就是魏晋时代的“名教”和五四时期的所谓“礼教”即天理之教。
中华法系从隋文帝《开皇律》始,以唐代的《唐律疏议》为代表性法典,一直被奉行至清末。“以礼入法”为其根本特征,“准五服以制罪”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其中的“五服”即上述的丧服单元。礼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性法典的中华法系的宪政精神,它以等差性的法律成就了现实的时间自然性,而非西方神本性地对自由至上进行空间性逻辑的理论抽象。
从秦汉至隋唐的儒法两家博弈中,法家的小家庭和儒家的大家族原则,正是历史展开的核心内容即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历史展开。儒家大家族血缘联系认同渠道如何形成展开?瞿同祖之论即涉及儒家“大家族”和法家“小家庭”的社会-政治学如何转换的问题。法家体制表面推崇儒家“孝道”,但皇权与官吏永远存在政治学性质的利益博弈。所以,在中国传统中,永远是政法一体、先政后法的。唐代完成以礼入法后,“法”即成了“礼法”,儒家之“礼”也就从伦理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三)宗教性问题
丧服单元是生活-生产-祭祀三位一体的,是宗教性祭祀单位,“孝”道信念由此而获得它坚实的生活-生产性支撑,并非坐而所论之“道”。丧服单元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也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张世英的“横向超越”之所以比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更加具有说服力,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际横向依存关系,更能说明儒家的“仁爱”以及作为其精神支撑的祖先崇拜信仰方式。就结构-功能意义而论,它生活-生产-祭祀三位一体圆满自足;就精神超越上讲,它与农耕生产方式制约的婚姻半径小直接相关⑤。宗亲/姻亲的儒道关系,通过“服丧”表现为与生死相关的天人合一,使文明得以长期延续。
卡尔·J·弗里德里希说:“对于任何建立在人权信念基础上的社会来说,生存和安全的任务成了保护最深处的自我这样一件与保护最外层的边界同等重要的事情。”⑥这里,美国人的“人权信念”基础亦是“生存和安全”之类的基本个人需求。一种文化形态若要存续下去,生存和安全一定是个必要的条件。所以他又说:“宪政论的宗教基础几乎业已消失”,“所有现存国家都不能完全践行其对人权的承诺”,“这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国际社会。”[4]111,111,112显然,他的“超验正义”是一神教义支撑并经由悠久的传统积淀下来的宗教文化心理,非一神教传统的东方对此不必太当真。
就中国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而言,如果依照易学最简关系的阴/阳(— —/——)思想方法,在承认“身心一体”的基础上,将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一起考量,我们凭什么要和西方等发达国家一道并按照他们的“人权”定义“为人权而奋斗”呢?我们从来没有《福音书》,也没有使徒保罗、约翰。即使在美国,表面上宪法与教会无关,事实上,美国宪政却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都与公民普遍的一神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于是我们理解了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中划分“文明”的标准为什么正好是宗教而不是别的什么⑦。
“信”在儒道观念中的地位都不甚高,因为儒道两家都是人本主义者,他们的哲思都立足于社会人生。就中国思想传统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讲的是熟人际的“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81章)也是就熟人际社会讨论“信”。人际间的问题不是信仰关系,而是信任关系。农人生活在熟人社会,相互信任不是问题。此即相对于一神教商业文明的儒道两家均不重“信”的社会学基础。反过来讲,强调信仰的一神教文化传统是生人际社会,是人际信任关系不容易建立的商业传统。所以,一神信仰是与商业伴生的生活方式。中国思想传统“以哲学代宗教”(冯友兰),这里的哲学即道德形而上学。恃才力者功小,恃智能者功大,恃德性者功久。我们在社会道德而非宗教道德中满足了自己的终极性精神生活(李泽厚)。“由特殊的家庭关系,或社会政治秩序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特定的环境构成了区域,区域聚集于个人,个人反过来又是由他的影响所及的区域塑造的。”[5]44
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并在《五帝本纪》劈头一句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他已将中华民族的根深深扎在了宗亲血缘的关系上,姻亲血缘关系则被悄悄地掩盖起来。但“炎黄子孙”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散布开来,依靠的却是姻亲关系的自然扩张。于是,所有的历史便都成了“家族/乡村”史。这种世代继替的历史观将世界事件的空间性按历史年表的方式排列在时间长河中,在复杂的法、儒、道阴/阳互补中互为动力、互为因果,从而成就一元、自因、时间性哲学。这样,李泽厚“心理成本体”、“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的思考⑧便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说明。人生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永恒,并从而满足中国人的希望性信仰。
儒家的伦理-政治学原则建立在“家”上,如果儒家确如杜维明等认为的是宗教,它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家教”。只要有人类,就一定会有“家”,如此近切实在的“家”,人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家”。但在实际的家庭-家族事务中,母亲从来都是最为重要的角色。所以,“性质上严父和专制君王究竟是不同的”[2]66,母亲是一定会呵护儿女的。“丧服单元”至今犹存于族谱制度中,一个老人过世了,他(她)的直系亲属自然要服丧。但其旁系的亲属该怎么服丧,要不要服丧,即怎么样参与葬礼?此即五服制要解决的社会学问题。
“五服”观念系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态,地缘姻亲的利益冲突被整合在血缘的时间-历史性世代继替之中,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最大的价值共识:大一统。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
注 释:
①费孝通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一、论绅士;二、论“知识阶级”;三、论师儒。见《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9年版,第1-38页。在费老看来,以上凡被归入该“类”的人,都是儒道互补性质的。
②从商鞅到魏晋之间的五六个世纪推行的是法家的法律,故有所例外。魏晋至隋唐“以礼入法”后,儒家思想成为立法的主导精神,故不再允许“别籍异财”。关于此点请参瞿同祖著、邱立波译的《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的相关论证。
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5-171页《商王庙号新考》对“乙丁制”作有一图,见156、158页。拙著《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版),将殷商时代的这种“乙丁制”看做与西周儒家“昭穆制”相对应的道家历史渊源。可参看该书第135-146页。
④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商原李刚在《道治与自由》一书中也认为道家强调“地缘文化”,恕不赘述。
⑤据笔者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社会学教授宝森桂(Laurel Bossn)25年前在豫北的合作研究,当时的乡村婚姻半径尚在五公里之内。
⑥[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0-111页。该书作者为美国前政治学学会会长,这尤其能说明问题。
⑦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争论。他不久即发表后续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996年他著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对其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阐述。他在划分文明的标准时,基本采用“宗教”这一标准,并将中国定义为儒教国家。
⑧请参考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84等页的论述。
[1]费孝通 ,吴晗.皇权与绅权[M].观察社,1949.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3]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美]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高建立】
The Sociological Basis of Family or Hometown Faith of Confucianists and Taoists:The Aanlysis of the Trinity of the Ideal Model of Mourning Apparel Unit
AN Jimin
(Researching Center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Hen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Zhengzhou Henan 450002)
The analysis of the ideal model of mourning apparel unit can reveal its trinity of life,producing and socrifice,and sustain people’s faith in family and hometown.Ancestral consanguinity or affinity,the social basis of the mutual complement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fully meets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 of the people.As for th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law and religion,it can support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human-oriented life,and the deep cultural evolution and by following unified value consensus.
the complement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mourning apparel unit;the faith in family and hometown;consanguinity or affinity;unified value consensus
2014-10-22
安继民(1955-),男,河南焦作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B222;B223
A
1672-3600(2015)01-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