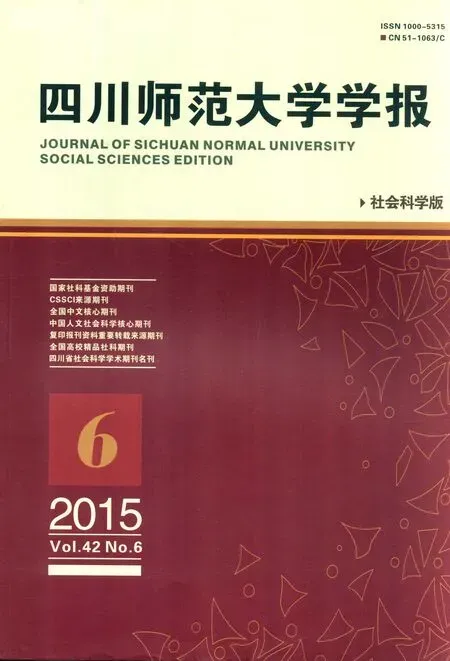求真务实:戴震《诗经》研究特色
徐 玲 英
(安徽大学 学报编辑部,合肥230039)
戴震于《与姚孝廉姬传书》中说:“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1]372戴震所谓的“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是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的。无论是对于人类社会还是个人而言,人的认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遗经的研究只有达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才能叫做“十分之见”。“十分之见”的获得必须本末兼察、空所依傍、言而有据、多闻阙疑。梁启超以为戴震求“十分之见”之法实乃科学之方法,他说:“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借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道德矣。”[2]36-37戴震的《诗经》研究是对其寻求“十分之见”之法最好的诠释。
一 三易其稿,不以己自蔽
戴震以《诗经》“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贤妇、良友之言”[3]126而精心研究《诗经》。他最早的《诗经》研究著作是《诗补传》。据段玉裁《戴东原年谱》记载,是书完成于乾隆十八年,戴震时值三十一岁[1]663。戴震于《诗补传》序言中交代了该书治诗的原则,即“今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3]125。于《诗经》传注中,戴震最为推崇《毛诗故训传》、《毛诗郑笺传》和朱熹《诗集传》,故《诗补传》于每章之下,首列以上三书释义精准者,至于未释语词,戴震则为之作释,以“震按”标识,附于其后。例如:于《鄘风·君子偕老》“蒙彼绉絺,是绁袢也”章,戴震按曰:“绁袢,袢延。盖古有是语,今并未闻。绉絺精而细靡,当暑用为服。疑诗意言其无流汗沾濡之苦,服之在体,热气散解,袢延而宽也。绁之言洩,袢之言泮。延,宽舒也。”[3]208于《卫风·芄兰》“虽则佩觿,能不我知”章,戴震按曰:“《方言》‘知,愈也。’病愈亦谓之知。史传有‘几日知’之语。盖古语之别,而今人失其解也。”[3]225-226时之相隔千百年,犹如地之相隔千百里,不借助于训诂便难以通古人之语言。然而亦有虽有训诂,读者仍不能理解者,戴震便为之沟通训词与被训词的关系。例如《周南·汝坟》“惄如调饥”之“调”,《毛传》释曰:“调,朝也。”[4]593如此训释,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故戴震以按语解释道:“调、朝语之转。”[3]160又如《召南·雀巢》“百辆御之”之“御”,《郑笺》释 曰:“御,迎 也。”[4]596戴 震 按 曰:“御、迎 语 之转。”[3]165除训释实词外,戴震还注意虚词的注释。例如《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章,戴震按曰:“卬、吾、言、我,一声之转,或五方异语有之。《诗》中但为辞助。《易》‘说言乎兑’‘成言乎艮”,言亦辞助也。”[3]153又如《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章,戴震按曰:“斯,辞也。或曰螽斯,或曰斯螽,便文协句尔。”[3]156
戴震尝云:“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1]371所以戴震释读《诗经》,除词义训诂外,他还广泛考证名物、典制等知识,希冀通过对名物典制的考证,一步步接近《诗经》时代,以古人的眼光观照《诗经》。例如《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章,戴震按曰:“黄鸟,经或谓之仓庚,《夏小正传》谓之商庚,亦谓之长股。《尔雅》谓之黧黄,亦谓之楚雀。”[3]152-153又如《卫风·硕人》“葭菼揭揭”章,戴震按曰:“萑未秀为菼,《尔雅》亦谓之骓,骓其色也。萑之小者谓之蒹,《尔雅》谓之薕,今人通谓之荻。凡曰葭菼、曰蒹葭、曰萑苇、曰芦荻,皆二物并举。葭、芦、苇一物也。菼、蒹、薕、萑、荻一物也。说者多混。”[3]221-222由于方言的存在,一物多名现象较为普遍。戴震罗列名物的异名,达到由已知知未知的目的。此外,戴震还详考古代典制。例如戴震于《鄘风·君子偕老》考证了王后礼服之制,曰:“《周礼》‘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褕翟、阙翟、鞠衣、展衣、褖衣。’郑《注》:‘王后之服,刻缯为之形而采画之,缀于衣。袆衣,画翚者,褕翟,画鹞者。阙翟,刻而不画。从王祭先王,则服袆衣。祭先公,则服褕翟。祭群小祀,则服阙翟。鞠衣,黄,桑服也。展衣,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3]207于《大雅·绵》,戴震考证了门的建制,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诸侯三门:库、雉、路。皋、郭语之转。郭门,外门也。诸侯之外门谓之库门。中门谓之雉门,亦谓之阙门,有两阙,《周礼》所谓‘象魏’,《春秋》所谓‘两观’是也。路寝之门谓之路门,亦谓之虎门,亦谓之毕门。”[3]451正如戴震所言:“盖名物字义,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俱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3]125-126戴震本着求真务实的治诗态度,故而详于名物字义考订,而不推衍作诗之意。梁启超盛赞戴震这一治诗原则,曰“洵治诗良法”[5]87。通过对字义、名物的推求,为回归《诗经》时代创造可能;而以夫子“思无邪”拟定篇旨,则还原了《诗经》作为礼乐制度一部分的本性。
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诗补传》虽是戴震治诗的唯一完书,但是戴震认为此书为识见未定之作,尚需修正。“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辩证成一帙”[1]664。所谓的“未成”就是未成定论,所谓的“辩证”就是指《毛郑诗考证》。在《诗补传》基础上,戴震专摘《毛传》《郑笺》或经文中有异议之处,详加考证,所依材料大都本之古训古义,言而有据。例如《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毛传》释“厉”为“以衣涉水为厉”[4]637。戴震于《诗补传》中已意识到《毛传》训释之讹,指出:“厉,不成梁之名。”[3]190在其后的研究中,戴震发现释“厉”为“不成梁之名”仍未至十分之见。他于《毛郑诗考证》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厉”由“履石渡水”而引申出桥梁之义,并广征博引,使释义确凿可信。戴震首先指出《毛传》训释之非:“既已以衣涉水矣,则何不可涉乎?似与诗人托言‘不度深浅,将至于溺不可救’之义未协。”然后戴震依据《说文解字》释“砅”为“履石渡水也”,并引《诗》“深则砅”,指出“濿”本字为“砅”,省而为“厉”。“厉”的本意为“履石渡水”,引申而有桥梁之义。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云:“段国《沙州记》:吐鲁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这是桥有“厉”之名之明证。戴震又根据《卫诗·有狐》“淇梁”“淇厉”并称,推定“厉固梁之属”。释“厉”为桥梁,则诗句“深则厉,浅则揭”的意思是“水浅可褰衣而过,水深则必须依桥梁而过”,这便与诗人“不度深浅,将至于溺不可救”之义相协了[3]598-599。戴震一字之训,做到了本之六书,贯通群经,而又实行本经前后互证,所以所作结论多为不刊之论。又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曰:“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4]654《郑笺》曰:“自防如城隅。”[4]654戴震不同意《传》《笺》之解说,于《诗补传》中指出:“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也。”[3]199但《诗补传》对于为何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解说不详。戴震则于《毛郑诗考证》中依据古代婚礼,指出“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姪姊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媵则至乎城下而俟迎者,然后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指的就是“媵俟迎之礼也”[3]600。
此外,对于《诗补传》中对《毛传》《郑笺》解说语焉不详之处,《毛郑诗考证》也摘出补充说明。例如《邶风·新台》“籧篨不殄”,《毛传》曰:“籧篨,不能俯者。”[4]656《郑笺》曰:“籧篨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者也。”[4]656于《毛郑诗考证》中,戴震通过对“籧篨”词义引申系列的梳理,进一步解释《毛传》《郑笺》以籧篨指口柔的原因。他首先据《方言》“簟或谓之籧䒼,其粗者谓之籧篨”,指出籧篨是竹子编的粗席之名,不能卷折;后来引申为病名,《晋语》曰:“籧篨不可使俯。”以此疾似籧篨,不能俯仰;后又引申为口柔,因为“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观颜色,病若籧篨之不能俯,故又为口柔之名”[3]601。他通过对“籧篨”词义引申系列的呈现,使人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于《毛郑诗考证》中,戴震考据务求言而有据。相较于《诗补传》,戴震作《毛郑诗考证》时视域更加开阔,引用书目不再局限于《尔雅》《说文》《周礼》《经典释文》等几本字书、训诂专著,而是扩大至经史子集。具体而言,《毛郑诗考证》中所引书目包括:《仪礼》、《礼记》、《春秋传》、《离骚》、《汉书》、《韩诗外传》、《五经异议》、《晋语》、《方言》、《史记》、《论语》、《释名》、《国语》、《杂问志》、《文选》、《魏都赋》、《思玄赋》、《谷梁春秋》、《曲礼》、《孟子》、《淮南鸿烈》、《后汉书》、《考工记》、《读韩诗》、《尚书古文疏证》等。
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考证积累,戴震对《诗经》已经有了全面认识。时隔十三年,戴震在《诗补传》的基础上,融入了《毛郑诗考证》内容,作《杲溪诗经补注》,希冀为后世《诗经》研读提供一个定本。《杲溪诗经补注》仍沿袭了《诗补传》体例,“就全诗考其名物字义于各章之下”。戴震仍于每章之下首列《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有资参证的材料则用小字注于相关条目之下;然后以按语形式阐说己见。“《补注》以《补传》为基础,在文字考订、典制辩证、词语释义、篇旨探索乃至行文修辞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补加工,其质量无疑高出《补传》”[6]3。以《关雎》首章为例,戴震于《诗补传》中只是引用《毛传》释义,而于《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辨析了《郑笺》“挚之言至,谓王雎之鸟雌雄情义至然而有别”[4]570之非。戴震以《夏小正》“鹰始挚”、《曲礼》“前有挚兽”为依据,指出“挚”为“鸷”的假借字,义为“猛”。又《春秋传》杜预注曰:“鸷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是杜预注本引《毛诗》而取猛鸷之义。《诗经》以猛鸷之鸟兴淑女,戴震认为是“关雎之有别,本于其性,诗经单取其有别之性耳”,“凡诗辞于物,单取已端,不必泥其类”[6]5。此外,《杲溪诗经补传》还对《毛传》“窈窕,幽闲也”[4]570作了补充说明。戴震指出:“窈窕,谓容也,其容幽闲、窈窕然。礼四教: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容者,德之表。”[6]5-6将窈窕解释为四教之妇容,指女子出入端庄持礼,便恢复了诗经的教化功能。《杲溪诗经补注》虽然仅完成《周南》《召南》二卷,但它是戴震识见稍定之作。段玉裁于《戴东原年谱》中说:“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先生所谓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者,于此可见。”[1]678作为完书的《诗补传》一直没有刊行,而只刊行了二《南》,这正是戴震传信不传疑精神的体现。戴震《诗经》研究历时十几年,其间三易其稿,力求做到不以己自蔽。戴震对十分之见的苦苦追求,于此可见一斑。
二 空所依傍,不以人蔽己
对于《诗经》学史上的争议问题,戴震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盲从、不偏信,唯求其是;对于证据不足者,则兼收并蓄、多闻阙疑。
不同于清代学者“主汉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汉”[3]125,戴震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1]495,所以戴震治诗跳出汉宋门户之争,志存闻道,空所依傍,做到不以人蔽己。戴震认为知人论世是推演作诗之意的前提,然而由于关于作诗之人的文献缺如,后人无法确定作诗之意。即使明了《诗经》如汉之毛亨、郑玄,宋之朱熹,也仍会一诗或以为是君臣朋友之辞,或以为是夫妇男女之辞;或以为刺讥之辞,或以为称美之辞;或以为自己所为指辞,或以为他人代为之辞。戴震冷静地对待诗序,加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唯是而从。例如他认为“南、豳、雅、颂,固有专为乐章,非咏时事者”,“《关雎》之言夫妇,《鹿鸣》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燕飨,俾闻其乐章,知君臣、夫妇之正焉。礼乐之教远矣,非指一人一事为之者也”[5]7。戴震一改说诗附会历史的做法,淡化史实,作泛泛而论,并不将具体诗篇傅会到文王、后妃或夫人之上。更何况戴震认为诗篇不一定为特定目的而作,“南、豳、雅、颂,或特作诗以为乐章,或采所有之诗定为乐章。……《仪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又射节用騶虞、狸首、采蘋、采蘩。其采蘋则本为女子教成之祭而作。古人乐章,一诗而数用有如此”[3]131。戴震主张,对于诗旨的不同阐释,在文献缺如的情况下,只要言之成理则不妨兼收并蓄。例如《陈风·衡门》,《毛序》曰:“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4]801-802《诗集传》则以为“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辞”[7]517。戴震则曰:“是诗也,以一国言之,国虽小可以兴治,不必待大国然后可为,义如是也,以一人言之,虽穷饿可以乐道,而不必求奉身之厚以自快,义又如是也。三百篇,失其传矣,苟无害乎义、不失乎辞,可以之此、可以之彼者,则未知其孰是也,兼收而并存之可也。”[3]307-308戴震虽然主张兼收并蓄,但是他对朱熹等将一些诗篇定为淫诗仍不赞同。他相信无论正诗变诗,三百篇皆“思无邪”。戴震说:“风虽有贞淫,诗所以美贞刺淫,则上之教化有时寝微,而作诗者犹欲挽救于万一,故诗足贵也,三百篇皆思无邪也。”[3]125他认为,之所以一部分变诗被定性为淫诗,一是因为对孔子“郑声淫”的误读,二是因为说诗者比拟《春秋》书乱臣贼子之法,认为《诗经》存淫诗以识其国乱无政,使后人知有所惩,所以将“本非男女之诗,而说者亦以淫奔之情类之,于是目其诗则为亵狎戏谑之秽言”。戴震一方面指出:“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诗”,并在详细阐释了音、乐和诗的区别的基础上总结道:“是知夫子之言‘郑声淫’,《乐记》之言‘桑间濮上之音’,不可据以论《诗》辞也。”[1]136-137另一方面,戴震以春秋诸国燕享所赋之诗,多为后人所谓的淫诗为例,驳斥存淫诗以识其国乱无政之观点,说:“郑六卿践行宣子于郊,赋其本国之淫诗,岂亦播其国乱无政乎?”戴震认为:“五伦之理,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妇之诗,用之于君臣;或男女之诗,用之于好贤。然不可以小人之言加之君子,鄙亵之事诵之朝廷、接之宾客。”[6]489戴震以孔子“思无邪”为指导思想,认为即使是变风也当止乎礼义。例如《邶风·静女》,朱熹定性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也”[7]483,戴震认为此为“思贤媵”。戴震说:“《静女》其诗,所谓贤贤易色矣。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女史之法废也。故其诗非荡佚之言也,所以讥荡佚者之言也。荡佚者,无贞静之操。曰静女,明不淫也。荡佚者,无取乎彤管。女史曰彤管,主乎宫中之宜有法度也。《春秋传》曰:‘《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是也。归荑,亦以为洁白之喻。若荡佚者,曷取是?其辞微,其志壮,其称物也可以训,其思美也,不动于淫。使徒以色而矣,岂足美哉!”[3]200戴震所释诗旨与《毛诗序》“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4]654相为表里。
《郑氏诗谱》为三百篇拟定世次,戴震作《毛郑诗考证》录为卷首,以存梗概。但是戴震并不盲从郑玄的谱系,认为不可以今之诗篇次第定作诗世次。例如他于《小雅·鹿鸣之什》曰:“《采薇》《出车》《杕杜》汉世有谓为懿王时诗者,据诗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郑解为‘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尔。苟有诗得乎义之正者而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文王未尝自称王,成康以后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八王,而宣王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炽’。则前此二百余年间,固亦有玁狁崛强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谓南仲为太祖,岂必远求南仲为文王时乎?文王之臣,亦未闻有南仲者矣。《南陔》已后,则又周初雅乐,未可以今之诗篇次第定作诗世次也。”[3]143。戴震又于《小雅·节南山之什》再次强调曰:“《节南山之什》以下,旧说以为幽王时诗,朱子尝疑《楚茨》至《车舝》十篇为正雅,错脱在此。《鱼藻》《采菽》《黍苗》《隰桑》《瓠叶》同。《黍苗》言召伯营谢,与《大雅·菘高》皆宣王封申伯事。然则诗篇次第,不可以定作诗之世次明也。”[3]144戴震“未可以今之诗篇次第定作诗世次”的观点得到后人证实。例如魏源作《诗古微》,依据《尚书大传》、《汉书》、《风俗通义》、《潜夫论》、《盐铁论》等典籍关于《出车》与《常武》之南仲的记载,实行典籍互证,详细辩证《采薇》、《出车》、《杕杜》三诗非文王时诗,“皆宣王诗也”[8]254-259。
《周礼·大师》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4]1719程颢言:“诗有六体,需篇篇求之,或有兼备者,或有偏得一二者。”[9]之后朱熹作《诗集传》便于每篇之下标注赋、比、兴。戴震对朱熹此种做法提出异议。他于《经考》中指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诗义。“赋比兴三种特作诗者之立言置辞,不出此三者。若强析之,反自乱其例。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何尝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观之,非指明敷陈,则托事比拟;非托事比拟,则假物引端。引端之辞,亦可寄意比拟,比拟之辞,亦可因以引端。敷陈之辞,又有虚实、浅深、反侧、彼此之不同,而似于比拟、引端,往往有之。”[6]241接着,戴震以《周南·樛木》为例,指出该诗先儒以为兴,以葛藟兴福履,但是此诗为“后妃待下,众妾称愿之”,诗中无从知其为众妾所作,只是因为樛木下垂,葛藟上蔓,比喻后妃待下,众妾下附,可见又是比也。又如《曹风·下泉》“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先儒以为比王室陵夷、小国困弊,但是该句又兴以下忾然念周京。所以戴震说,“此三者(赋比兴)在经中,不解自明;解之,反滞于一偏矣”[6]241-243。
对《诗经》文字的训释,戴震也不盲从一家之言,而是本之六书、征之群经,综合条贯、以理论定。例如《周南·关雎》“左右芼之”之“芼”,《毛传》曰“择也”[4]572,《郭注》曰“谓拔取菜”[4]572,朱熹曰“熟而荐之”[7]403。戴震指出,“说经者就经傅会而不可通于字,说字者就字傅会而不可通于经”,都在缘辞生训,而不明于字的偏旁[6]7。戴震考证曰:“芼,从草,毛声,菜之烹于肉湆者也。考之《礼》羹、芼、菹、醢,凡四物。肉谓之羹,菜谓之芼,肉谓之醢,菜谓之菹。菹、醢生为之,是为豆实,芼则湆烹之。芼之言用为鉶芼。”[3]595-596择于众说以裁其优不是求十分之见的做法,所以戴震另辟蹊径,从文字形体分析出发,证之以相近时代的典籍,论证了“芼”乃菜之烹于肉湆者。又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曰“不显,显也……不时,时也”[4]1083,以“不”为发声词,《郑笺》曰“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4]1083,增加“乎”字以为反言。戴震指出“《传》《笺》各缘词生训,失其本始”,比之古人金石铭刻,“丕显多作不显,二字通用甚多”,“不显”当为“丕显”。《诗经·桑扈》中“不取”、“不难”、“不那”,《生民》中“不宁”、“不康”,《清庙》中“不显不承”,“不”字皆为“丕”[3]633。后来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便继承了戴震的观点,以为“不、丕古通用”,“不显犹丕显也”[10]262。戴震词义考释的方法得到时人赞同。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11]23。
戴震早年就志存闻道,并选择了由词通道之路,所以他刻苦研读《说文解字》、《尔雅》及《方言》等字书,并由此广及汉儒传注,“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1]651。戴震也自称:“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诵也。”[1]651正如戴震所言:“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1]156,“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1]213正是凭借其深厚的学术根柢,戴震对于《诗经》中的争讼问题,皆能空所依傍,提出独到的见解。
三 是正文字,还原经典原貌
典籍传抄翻刻,鱼鲁虚虎之讹在所难免。校订典籍文字,是正确释读文本的前提条件。戴震曾以《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为例说明校正文字的重要性,说“《水经注》‘水流松果之山’,钟伯敬本‘山’讹作‘上’,遂连圈之,以为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见《山海经》”[1]716,并指出“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1]378。文字讹误则所释之义已非经之本义了。
为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求真务实,戴震在训诂的同时不废校勘。例如《陈风·墓门》“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戴震指出“讯”乃“谇”字转写之讹。他所列理由如下:第一,《毛诗》曰“告也”,《韩诗》曰“谏也”,于义皆为“谇”;第二,“讯”音“信”,与韵不协,“谇”音“碎”,与“谇”上句“有鸮萃止”之“萃”协韵;第三,王逸注《离骚》引诗作“谇予不顾”,是东汉时字仍不误;第四,《尔雅》曰:“谇,告也。”《释文》云“沈音粹,郭音碎”,是郭本“谇”不作“讯”,且张衡《思玄赋》注引《尔雅》仍作“谇”[3]609。戴震著述,孤证不为立说,言必有据。为证明“讯”乃“谇”字之讹,戴震以字书韵书参伍考证,并征之汉唐典籍,言必有信。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时便继承了戴震的观点,指出今毛本“讯”为“谇”字之误,形近而讹[12]100。戴震的论断还得到出土文献的验证。出土于西汉初年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妻合葬墓的阜阳汉简,便有《诗经》残卷,其《陈风·墓门》正作“歌以谇之”[13]。又如《周南·卷耳》“云何吁矣”,戴震指出“吁”为“盱”字转写之讹。他首先用本校法实现前后互证,《何人斯》“云何其盱”、《都人士》“云何盱矣”皆为不得见而远望之意,字皆作“盱”;然后他引用《说文》“盱,张目也”,《尔雅》“盱,忧也”;最后用《毛诗》为生字释义的体例,说明此处不释义是蒙《卷耳》篇而省略[6]12。戴震还利用《诗经》用韵规律,订正经文讹误。例如他于《毛郑诗考正·汉广》中总结道:“凡诗中用韵之句,韵下有一字或二字为辞助者,必连用之,数句并同,不得有异。”据此,戴震指出《诗经·汉广》“不可休息”之“息”为“思”字之讹;《陈风·墓门》“歌以谇之”之“之”为“止”字之讹[3]596。戴震总结一书义例的校勘方法为后世树立楷模,王国维曰:“‘审其义例’属于本校……皆是戴震的创造,为后代校勘家所遵循并加以发展,可见其价值和影响。”[14]342
正如戴南海所说:“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俞樾等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根基和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善于发现古书文字上致误的原因,据理加以改正。同时,他们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读得精通。他们以理校为主,又善于从本书和他书取得证据校正文字,且把严密的考证用于校勘,因此时出奇迹,多有创获。”[15]110戴震利用音韵校勘之例,如:他据“軓”字不与“牡”字押韵,知《匏有苦叶》中“軓”为“轨”字之讹[3]599;据“疧”字不与“尘”字押韵,知《无将大车》中“疧”为“痻”字之讹[3]626。戴震据群籍传注校勘之例,如:他据《夏小正传》,知《木瓜》中“芦”为“雚”字之讹[3]603;据《尔雅》释义,知《陟岵》中“岵”与“屺”字释义互讹[3]605;据《释文》知《小戎》中“靳”为“靷”字之讹[3]607,《节南山》中“方有穀”衍“有”字[3]621。戴震以理校订之例,如:他据音义考证,指出《女曰鸡鸣》中“赠”为“贻”字之讹[3]604,《月出》中“惨”为“懆”字之讹[3]609,《六月》中“急”为“戎”字之讹[3]618,《雨无正》中“讯”为“谇”字之讹[3]623,《小旻》中“膴”为“腜”字之讹[3]624。另外,戴震还依据语法考证,指出“惨”字不可用为叠字形容之辞,知《北山》中“惨”为“懆”字之讹[3]626。各种校勘方法的综合运用,戴震往往能于不经意处发现讹误,并以理校订,从而尽可能地还原《诗经》原貌。
戴震坚信人虽愚必明。他由天道推演人性,认为人禀天地清明之气而具有血气心知,“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175;人具有了血气心知,便有了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1]155-156。心知之能通乎理义,就如同口、耳、目之能辨别味道、声音和颜色。然而,由于人所禀之气的清浊不同,人心之精爽也有等差之别,不可能世人皆为尧舜;但是“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1]183,只要通过学习就能进于神明。圣人得天下之理义,以六经垂教天下,常人学然后便能明乎礼义。戴震以《诗经》乃“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贤妇、良友之言”,而精心研究《诗经》。不同于宋儒的以意逆志,戴震通过对字义、名物典制的考证,试图还原《诗经》时代的语境,揭示出蕴含于其中的微言大义,为世人提供一个好的读本。戴震研究《诗经》三易其稿,力求不以己自蔽;对于《诗经》学史上的争议内容,戴震空所依傍,力求不以人蔽己,并是正文字,力求还原经典原貌。戴震的《诗经》研究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哲学精神。
[1]戴震全书:第六册[M].张岱年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7.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戴震全书:第一册[M].张岱年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7.
[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M]//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戴震全书:第二册[M].张岱年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7.
[7]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魏源.魏源全集: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9]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戴震全书:第七册[M].张岱年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7.
[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李晓春.阜阳汉简,国之瑰宝[J].文史知识,2000,(6).
[14]王国维.五声说[M]//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99.
[15]戴南海.校勘学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