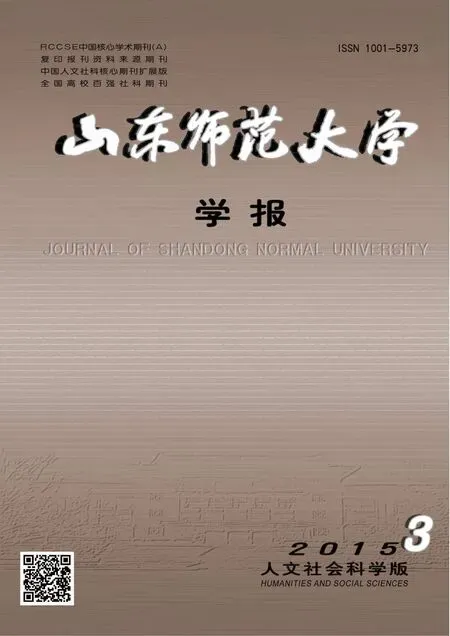西方艺术中的感性迷狂*①
陈 炎
(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中心, 山东 济南,250014 )
西方艺术中的感性迷狂*①
陈炎
(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中心, 山东 济南,250014 )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从“迷狂说”入手,将艺术创作看成是宣泄内心情感的手段和渠道,于是便有了死尸满台的悲剧、狂放不羁的舞蹈、声嘶力竭的摇滚、人欲横流的电影等。这种感性欲望的宣泄,不仅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激情与活力,而且可以纠正理性思辨行为所导致的精神异化,因而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义;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感官刺激的极端性发展,进而陷入肉体欲望的误区。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正面作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艺术的美学特色;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负面影响,就不可能彻底反思西方艺术所存在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感性与理性相分裂的民族心理结构说起。
西方;美学;艺术;感性;迷狂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3.002
同理性与感性分裂的民族心理结构相对应,西方的艺术精神也呈现为理性思辨与感性迷狂彼此分裂的两种倾向。从宗教的角度上讲,前者起源于阿波罗精神,后者起源于狄俄尼索斯精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前者起源于“摹仿说”,后者起源于“迷狂说”;从艺术的角度上讲,前者体现为从代数的角度研究音乐、从几何的角度研究建筑、从解剖的角度研究雕塑、从透视的角度研究绘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等一系列理性思辨行为,后者体现为死尸满台的悲剧、挑动欲望的舞蹈、狂放不羁的摇滚、人欲横流的电影等一系列感性迷狂现象。关于前者,笔者已在《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②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这里仅就后者进行必要的分析。
著有《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十分重视酒神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在某种状态中,我们置光彩和丰盈于事物,赋予诗意,直到它们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丰富和生命的快乐;这些状态是:性冲动;醉;宴饮;春天;克敌制胜,嘲弄,绝技;残酷;宗教感和狂喜。三种因素是主要的,即性冲动、醉和残酷,它们都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庆之快乐,也都在原初的‘艺术家’身上占据优势。”③[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54页。尽管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中未必包含着哲学本体论的自觉意识,然而与尼采的理解相类似,笔者也认为以感性迷狂为特征的狄俄尼索斯崇拜确实有助于西方人在艺术行为中释放自己的生命快感和肉体冲动。因此,就像受日神影响的西方艺术有着“泛科学”的理性冲动一样,受酒神影响的西方艺术则有着“泛体育”的感性迷狂。这种与理性思辨刚好对立的感性迷狂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
柏拉图不仅是“摹仿说”的奠基人,而且是“迷狂说”的始作俑者。他认为,摹仿的诗人对所摹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艺术才能,只有依靠神灵的启示和灵感的获得,才有可能创作出美好的诗篇。在《伊安篇》中,他曾借用磁石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认为诗神就像一块磁石一样,给人以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古希腊]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总之,在柏拉图看来,虽然人们通过理性的认识途径无法摹仿出“理念世界”的原貌,但却可以在一种非理性的迷狂状态中把握其本质。换言之,只有陷入迷狂的人才能产生艺术的灵感,从而创作出美的佳作。在这里,柏拉图首次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他曾借一位雅典陌生人的口说:“当诗人们一旦坐在缪斯的三脚凳上就不再有他自己的头脑了。他自觉自愿地让他进入他心中的东西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转引自《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这种说醉话一样的创作状态,很可能来自狄俄尼索斯的宗教灵感。
与“摹仿说”不同,这种“迷狂说”不是寻求艺术与客观生活之间的联系,而是在寻求艺术与主观情感之间的联系。或许是受柏拉图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有关Katharsis的著名观点——悲剧效用说:“借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Katharsis。”*[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罗念生将Katharsis译为“陶冶”,现据其注释及《卡塔西斯笺释》一文,将引文改为原文。根据罗念生、朱光潜等人的研究,“Katharsis”一词含义复杂,在医学的意义上可译为“宣泄”,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可译为“陶冶”,在宗教学的意义上可译为“净化”。然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它都是一种强烈情感或狂热情绪的释放。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像哀怜和恐惧或是狂热之类情绪虽然只在一部分人心里是很强烈的,一般人也多少有一些。有些人在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卷入狂迷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它类似情绪影响的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5页。于是,艺术也便像狄俄尼索斯仪式那样,成为情绪释放的手段和途径。
一 、死尸满台的悲剧
最为直接地体现“酒神精神”和“Katharsis”的,当然要属希腊悲剧了。这种起源于狄俄尼索斯祭祀仪式的艺术行为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希腊悲剧大都取材于神话、史诗和英雄传说,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出于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命运无常的恐惧,希腊悲剧常常笼罩着一种宿命论色彩。然而,在那死尸满台的悲剧故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悲剧人物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了从天堂“盗窃”火种给人类,甘愿忍受众神的惩罚。宙斯命令威力神和火神将他钉在高加索的悬崖上,暴露在雨雪风霜和烈日炙烤之中,以警告他以后不要再对人类滥施同情。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一心为城邦免去瘟疫的俄狄浦斯王决心去追查那位“杀父娶母”的罪魁祸首,当他最终发现自己竟然正是那个无意中犯下这一罪行的元凶时,并没有借助国王的权力来宽恕自己,而是刺瞎双眼,自我流放。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先是被忘恩负义的丈夫抛弃,后又被冷酷无情的国王驱赶的美狄亚,决心实施残酷的报复。她一方面设计毒死了丈夫要娶的新娘,一方面亲手杀死了自己与丈夫的子嗣,变生离为死别,再玉石俱焚地完成了自己的悲剧人生。所有这些悲剧的结局大都充满了暴虐和血腥,但与此同时却又酝酿着一种快感和激情。
这样的悲剧不惟古希腊所独有,在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乃至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中,它始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种。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一再“延宕”的复仇故事中充满了鬼魂和乱伦,奥赛罗鲁莽的报复情节里埋藏着嫉妒和悔恨,李尔王悲惨的遭遇中包含着痛苦和绝望,麦克白无谓的挣扎中充满了残暴和血腥;在拉辛的笔下,安得罗玛克痛苦的抉择中交织着责任与情感;在席勒的笔下,斐迪南的追求中潜伏着阴谋与爱情;在斯特林堡的笔下,老人亨梅尔和木乃伊之间甚至演绎了一场鬼魂奏鸣曲。
人类欣赏艺术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所以,从娱乐的角度上讲,人们喜欢喜剧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但是,何以西方人却始终对这种惊心动魄、死尸满台的悲剧情有独钟呢?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引起了哲学家们持续不断的思考。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人公不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好人,也不应该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常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些错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正是由于常人犯了错误,遭受了不幸,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并借此获得教益。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冲突双方是“绝对精神”外化、分裂后的产物。由于他们所体现的“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4页。,如人伦之爱、国家观念、宗教信仰等等,因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他们又都以否定对方为条件来肯定自己的合理性,因而又都是片面的。“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6页。而悲剧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弘扬了冲突双方的正义感,一方面又扬弃了冲突双方的片面性。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入手,将这类戏剧的产生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6页。。叔本华既不愿意站在“绝对精神”的立场上来俯瞰人类的不幸,也不愿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分析悲剧的原因,而宁愿站在个体人的立场上来发现原本无辜的冲突双方却要玉石俱焚地相互摧残。因此,他认为:“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2页。这种不幸既不是来自异乎寻常的恶人,也不是来自闻所未闻的意外,而只是由于悲剧的双方所处的相互纠葛的现实关系。所以,他主张悲剧的意义不是宣布什么“绝对精神”的合理性,而恰恰是要宣布人类命运的荒谬性。尼采则认为,尽管宇宙是荒谬的,人类是痛苦的,但我们仍然勇敢地面对痛苦而又荒谬的人生。“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心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45页。这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或许正是西方悲剧艺术的动力所在。在这样的悲剧舞台上,冲突、苦难、挣扎、毁灭顷刻间打破了往日生活的宁静,原始的欲望、人类的本能、伦理的意志、宇宙的力量,以一种比喻的形式粉墨登场了。于是,在那瞬息万变、一触即发、惊心动魄、死尸满台的悲剧艺术里,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矜持优雅的阿波罗,而是疯狂放纵的狄俄尼索斯了。
二、狂放不羁的舞蹈
尼采曾经指出:“在狄俄尼索斯的醉之中有性欲和情欲。”*[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49页。谈到艺术行为对性欲和情欲的表达,不能不涉及舞蹈问题。因为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舞蹈所使用的媒体是人类自身的肉体。这种被科林伍德称之为“一切语言之母”的肉体,是最基本、最天然、最原始的生命载体,因而也最具有表达性欲和情欲的吸引力。从艺术符号学的角度上讲,如果说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最接近于理性、接近于“灵”,那么以肢体为载体的舞蹈则最接近于感性、接近于“肉”。而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这种被苏珊·朗格称之为“人类第一艺术”的舞蹈,在现存的许多原始民族中也确实有着两性之间求偶的功能。难怪古希腊哲学家琉善说“舞蹈像爱情一样古老”呢。当然,除了求偶之外,早期的人类舞蹈还常常具有巫术的功能,即通过疯狂的肉体动作而达到祛妖降魔、与神沟通的目的。或许,在原始人的行为中,“性”与“神”的关系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人们可能会通过“性”的比喻来祈求“神”的佑助,从而获得丰收,求得吉祥。研究表明,早期的酒神祭祀中就有此类舞蹈。
妇女通过一些类似性交的巫术仪式,在纵酒狂欢中,裸体奔行舞蹈,祈祷大地丰收。酒神之所以在这种仪式中被崇拜,主要因为酒能把妇女带入迷狂沉醉状态。*李咏吟:《原初智慧形态——希腊神学两大话语系统及其历史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我们从雅典卫城里的那幅红色素描的花瓶图案上,看到一个全身裸露的狂舞女正在心醉神迷地舞动着一根男性生殖器模型。在出土文物的挖掘过程中,人们不仅挖掘出大小不同的人体塑像,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用石头和其他材料做成的阴茎模型。*[德]利奇德著,杜之、常鸣译:《古希腊风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有人把古希腊本土的舞蹈分成三种类型: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荷马式舞蹈”,发扬尚武精神的“斯巴达式舞蹈”,以及赞颂太阳神阿波罗的理性精神、讴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精神和崇拜三女神的阴柔之美的“雅典式舞蹈”,后者最能充分地体现感性迷狂的美学特征。
与古希腊的文化气质不同,古罗马有着尚武轻文的特征。据普卢塔克记载,古罗马早期有着跳战舞的习俗,即把舞蹈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准备。但汉尼拔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的安定,享乐主义的提升,娱乐性的舞蹈渐渐风行。这一时期,古罗马开始有了专门的舞蹈学校,“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女与那些堕落的人混杂在一起,在舞蹈学校学跳舞。”*[德]奥托·基弗著,姜瑞璋译:《古罗马风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不仅如此,职业舞女表演时往往进行性挑逗。大量资料表明,她们这方面技艺高超,无与伦比。奥维德在《爱情诗》第2卷第4章第29节中说:
她双臂优美,动作细腻,
她摆动柳腰,有所暗示。
任何新奇的美都能打动我,
可是她却能使纯洁的希波吕托斯
难以自制。*[德]奥托·基弗著,姜瑞璋译:《古罗马风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罗马人一方面认为体面的女性热衷于跳舞有伤大雅,另一方面又喜欢观看职业舞女的色情表演,而且喜欢将美丽的舞女纳入他们的诗歌、雕塑和绘画。”*[德]奥托·基弗著,姜瑞璋译:《古罗马风化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8-189页。
进入中世纪以后,这种对待舞蹈的矛盾态度转化为“灵”与“肉”的对立。受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挑动肉体欲望的舞蹈会玷污灵魂的纯洁,于是舞蹈也就难登大雅之堂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感性生活开始有了萌生的机会,于是就有了芭蕾。作为一种欧洲的经典舞蹈,“芭蕾”一词来自法语ballet的音译,特指有一定动作规范、技巧要求、审美理想的欧洲古典舞蹈;或泛指以这种舞蹈形式表达思想情感、推动故事情节的舞剧。芭蕾作为舞台艺术形式,始见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宫廷盛大的宴饮娱乐活动之中,后来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公主凯瑟琳将这种舞蹈形式带入了法国宫廷。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其说芭蕾源自狄俄尼索斯,不如说芭蕾源自阿波罗。1581年,法国宫廷所表演的第一部芭蕾舞剧《皇后的喜剧芭蕾》,其内容就是表现女妖西尔瑟如何征服阿波罗的故事。该剧的编导博若耶认为,芭蕾是“几个人在一起跳舞的几何图案组合”。17世纪的路易十四十分喜爱这种具有理性精神的舞蹈形式,他本人也受过良好的训练,15岁时曾参加宫廷芭蕾《卡珊德拉》的演出,扮演过阿波罗神。在路易十四的倡导下,芭蕾开始在法国发展起来,并在不断革新中风靡了整个欧洲。由于受日神精神的影响,芭蕾的舞蹈形式极具理性化、程式化、标准化、规范化、精致化的特征。
如果说芭蕾舞体现了日神精神,那么交谊舞则体现了酒神精神。交谊舞原名“社交舞”,英文为Ballroom Dancing,它最初也起源于文艺复兴的宫廷。“当时各国宫廷流行的正式舞蹈,很像今日的波罗乃兹舞,一对对男女在音乐伴奏下在舞厅里移动;跳舞的人肯定比较文静比较古板。……即使在这种古板的礼仪性舞蹈中,姿势、节奏、动作和舞者的鞠躬行礼,也都是由性感决定的。这些也无非是男女之间爱情的象征性表现,无非是互相求爱的模拟形式。”*[德]爱德华·傅克斯著,侯焕闳译:《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3-494页。法国大革命以后,这种社交性舞蹈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将这种舞蹈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标准交谊舞。
现代交谊舞吸收了南欧、南美一些民间舞蹈的成分,一般分为摩登舞和拉丁舞。摩登舞是在传统宫廷舞蹈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包括华尔兹、探戈、狐步、快步四种舞蹈类型,其动作轻盈、舒展。拉丁舞是拉丁和美洲的缩写,而不是指地理上的拉丁美洲。现在的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均起源于古老的拉丁语,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人向美洲的移民,将这三种语言带到美洲,并与当地的土著结合形成一种文化。标准的拉丁舞包括桑巴、伦巴、斗牛、恰恰、牛仔五种舞蹈类型。与优美、典雅的摩登舞不同,拉丁舞更为狂放和性感。
尽管拉丁舞融汇了美洲黑人舞蹈和本土文化的元素,但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欧洲,在那个不死的狄俄尼索斯身上。“在某一具体时刻,您应该不知为什么变得阴郁、忧愁、怀旧,而在一分钟之后又像酒神女祭司一样发起疯来。在需要时必须同时感受这一切。必须既快乐又忧郁,既冷漠又热情——总之,必须跳舞、寻欢作乐。”*[德]爱德华·傅克斯著,赵永穆、许宏治译:《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3-414页。毫无疑问,交谊舞中包含着两性之间挑逗的内容,这种内容可以是桑巴式的狂热,也可以是探戈式的冷漠。就像库尔特·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所说的那样:“西班牙舞蹈所表现的经常是冷漠多于热情,这种舞蹈和谈恋爱一样,拒绝与冷漠是诱惑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可以逼得男人们发疯。”*[德]库尔特·萨克斯著,郭明达译:《世界舞蹈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第328页。无论是服装还是表情,无论是音乐还是动作,这种直接利用人的肢体、充分表达人的欲望的舞蹈已成为最原始、最现代,最个人、最集体,最淋漓尽致、最扣人心弦的酒神精神的艺术载体。
三、声嘶力竭的摇滚
传统的西方音乐长期以来致力于借助数学手段来追求一种声音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古典音乐、尤其是交响音乐中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从音乐内容上看,交响音乐对和声、配器极为讲究,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多样性统一的完美和谐;从欣赏方式来看,欣赏者必须衣冠楚楚、盛装出席,以一种高雅的姿态来享受文明的盛宴。然而,与这种日神式的古典音乐刚好相反,19世纪以后,来自民间的蓝调、爵士乐、福音音乐、节奏蓝调、乡村音乐异军突起,以一种酒神式的野性汇聚成20世纪中叶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摇滚音乐,并成为当今世界流行音乐的主干。
“蓝调”(Blues)音译为“布鲁斯”,是一种基于五声音阶的声乐和乐器混合体,它起源于过去美国黑人奴隶的灵魂乐、赞美歌、劳动曲。这种音乐有一种很鲜明的特点,便是采取“一唱一和”(Call and Response)的对应方式。早期的“蓝调”音乐往往具有松散的叙事内容,以讲述一个人的不幸遭遇、苦难生活、情感经历。一般来说,蓝调音乐作品的起始常常会营造一种忧伤、哭诉、无助的感觉,接着便像是在安慰、舒解受苦的人们,宛如受苦受难的人们在哭诉后得到上帝的安慰与响应。所以“蓝调”一词又有着与“蓝色魔鬼”(Blue devils)一致的意思,以显示情绪的低调、哀伤、忧郁。蓝调音乐的形式并不复杂,起初甚至没有和声的明确定义,后来以12节蓝调为基础,形成了标准的12巴和声,节奏为4/4或2/4拍。在这种简单音乐套路的基础上,“蓝调”很重视即兴式的表演和原创式的发挥,以实现自我情感的自由宣泄。
“爵士乐”(Jazz)是在“蓝调”和拉格泰姆(Ragtime)基础上的综合,后者起源于蓄奴制解体后的美国。当时获得自由的南方黑人纷纷涌入新奥尔良、孟斐斯、芝加哥等大城市中寻找工作。他们除了出卖体力之外,也常以音乐为生,在咖啡店和酒馆里演奏那些蓄奴时期曾被禁止的黑人音乐,并在精疲力竭的演奏中催生出一种高音和低音相互侵略、混杂后再次分开的音乐形式。由于这些乐手没有受到专业训练,因而只以节奏为主,不太顾及旋律方面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解构。在此基础上,讲究即兴和摇摆的爵士乐出现了。作为黑人文化和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爵士乐以英美传统音乐为基础,混合了“蓝调”即兴创作的特点和拉格泰姆节奏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表达形式。一般地说,爵士乐都是二拍子的,每小节两拍或四拍。这种二拍子的节奏背景在低音部始终存在,使得爵士乐有一个稳定的、规则的节奏基础,以便配合身体的摇摆。在节奏性低音的上方,则是重音位置不规则的旋律、和声和对位声部,它们惯常使用的切分音效果与规律的低音声部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世纪初期,爵士乐主要集中在新奥尔良发展,后来转向芝加哥、纽约,直至风靡全世界。
福音音乐(Gospel Music)起源于黑奴的祈祷,后来演变为即兴的音乐表演,演唱风格以运用单音节装饰音与歌词高声喊唱为特点,常常用击鼓和电吉他伴奏来形成亢奋的节拍。20世纪20年代,福音音乐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音乐类型出现。20世纪中期,著名的歌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猫王)把福音音乐引进到自己的风格中,并使之商业化。
“节奏蓝调”(Rhythm and Blues)也可以译作“节奏布鲁斯”,或者简化为R&B,它是一种融合了蓝调、爵士乐、福音音乐的音乐形式。大部分“节奏蓝调”作品以4拍为一小节,12节为一段落,并强调每节中的第2拍和第4拍,以制造出一种新鲜、强烈的节奏感,所以又有人将其称之为“跳跃的布鲁斯”。“节奏蓝调”还常常在作品中多次反复一些乐句、句子,以产生痛快淋漓的效果。除了强化节奏感之外,“节奏蓝调”的歌词内容也更加坦率直白,绝无温柔敦厚、忸怩作态之感,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符合节奏的顺口溜、大白话。
“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部,其根源来自英国民谣,是当时美国白人的流行音乐。“乡村音乐”的曲调流畅而简单,节奏自由而平缓,多为歌谣体,伴之以吉他或口琴。歌曲的内容,除了反映劳动生活之外,也常常表现厌恶孤寂的流浪生活、向往家园的乡村记忆、失去爱情的痛苦情感等,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亲切热情而不失流行元素。由于这种音乐代表了下层民众的趣味,因而表演者常常不穿演出服,而代之以牛仔裤、休闲装、皮草帽、旅游鞋。
正是在上述乐音的基础上,摇滚乐(Rock and Roll)出现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音乐形式,摇滚乐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态驳杂,有民谣摇滚、艺术摇滚、迷幻摇滚、乡村摇滚、山地摇滚、重金属、后车库、朋克等等,其共同的特点与其说是一种音乐形式,不如说是一种人文情怀:民间的、下层的、在野的、边缘的、自由的、反叛的、抗争的、异端的、野性的、反商业的、反文明的……不再是和谐优美的动听,不再是多愁善感的抒情,不再是浅吟低唱的含蓄,不再是端庄优雅的姿态,而是简单的、直白的、强烈的、有力的、激越的、震撼的、颤栗的、无拘无束的、奋不顾身的、撕心裂肺的、几近癫狂的。在乐器上,摇滚乐偏爱电吉他、打击乐、重金属;在服装上,摇滚乐手喜欢无拘无束、奇装异服;在生活上,为了保持其疯狂的状态,摇滚乐手常常酗酒,甚至吸毒。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演出环境上,摇滚乐并不常在标准的音乐厅中表演,而是喜欢体育场、露天舞台。在这里,摇滚乐所追求的,与其说是一种音乐的效果,毋宁说是要给观众提供一种全民狂欢式的场所。在这里,演员要做的,不是给观众提供一种美妙的音乐,而是要点燃观众心中的火种,煽动观众潜藏的激情,从而在一种感性迷狂的状态中宣泄内心的情绪。如果仅从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来看,充斥噪音的摇滚乐和动作古怪的太空步都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任何亲临现场的观众都会发现,那人声鼎沸的环境与其说是一个艺术的圣殿,毋宁说是一个狄俄尼索斯的集会。观众们来这里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欣赏,毋宁说是为了发泄,就像那些亲临比赛现场的足球球迷们一样,是要借助这样一种群体狂欢的场所而进入一种酒神式的迷狂。而舞台上的歌者和舞者,则不啻于当代的狄俄尼索斯。
四、人欲横流的电影
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走进剧院去欣赏那些动人心魄的悲剧了。然而在西方,作为取代戏剧艺术的影视艺术,却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负载着狄俄尼索斯的灵魂。走进电影院、打开电视,今天的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莱坞式的“巨片”。那些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作品,始终占据着当代西方影视的主要屏幕。这些作品的意义何在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拿那部英国制作的经久不衰的系列影片《007》作为个案分析。这是一部花样翻新而又一成不变的电影:说它花样翻新,是指其不断放映,不断拍摄,不断制造着新的感官刺激;说它一成不变,是指其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是那种单一的创作模式:
人物:潇洒、冷峻而又智勇双全的詹姆斯·邦德和美丽、性感而又神秘莫测的邦德女郎(前者的演员是相对固定的中年男子,以满足女性崇拜者从一而终的追星欲望;后者的演员是不断变换的妙龄女郎,以满足男性猎艳者见异思迁的求新口味)。
环境:或冰川,或荒漠,或海岛,或森林,或其他什么足以同城市生活造成巨大反差的地方(因为越是陌生的环境就越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心)。
对手:或专制帝国,或邪教组织,或秘密团伙,或阴谋集团,这些恐怖的活动最好发生在异国他乡,再加上一点儿风化场面和浪漫情调。
工具:具有科幻色彩的交通、通讯设施,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装备,令人眼花缭乱的间谍的手段,再加上迷宫一样的地下防空设施或海底秘密世界(以此来满足青少年观众的好奇感)。
情节:主人公出生入死,经受了反间计、苦肉计、美人计,或其他种种三十六计、七十二计的考验,最终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而旋转乾坤,挽救了国家或人类。
细节:追车,或比追车更加刺激的游艇、飞机甚至宇宙飞船之类的追杀场面,还有那永远也演不够的床上戏,等等。
总之,要最大限度地调动高科技手段(理性之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的感官愉悦(感性之欲望)。需知,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007》系列产品,而且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好莱坞大片。难怪马尔库塞在去世前的一次谈话中会愤然指出,现代西方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自淫。
尼采在谈到狄俄尼索斯崇拜对艺术的影响时曾经指出:“醉感——它实际上同力的过剩相应——在两性动情期最为强烈。”“对艺术和美的渴望是对性欲癫狂的间接渴望。”*[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349页。按照弗洛伊德后期的思想,人类被压抑的潜意识“本我”,可以分为“爱欲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两部分,而上述艺术作品,无非是通过爱与死这两大“永恒的主题”来释放人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利必多”(libido)本能。当然,除了永恒不变的追车场面和翻来覆去的床上镜头之外,这种“智力上的自淫”还会不断地进行花样翻新,为了给人们已经疲惫的感官带来更加强烈的刺激,当今好莱坞的导演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替身演员的危险动作,而是通过高科技手段使死去了上万年的恐龙重新复活,使失事了上百年的轮船重新触礁,甚至使无法被证实的外星人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银幕上。于是,除了色情和暴力之外,恐怖、神秘、荒诞和变形也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常态,就在美术馆里的作品越来越丑陋、越来越荒唐、越来越刺激,音乐会上的演出越来越嘈杂、越来越凌乱、越来越刺耳的同时,电影院里的场面越来越宏大、越来越奢华、越来越恐怖。
该怎样评论当代艺术呢?一提到这个问题,数量惊人、支离破碎、商品化、怪诞、活力四射等字眼就闪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肯·贝恩斯在20世纪60年代评论当代先锋派时宣称:“艺术家争取自由的勇敢呼号已变成为小丑式的呐喊了。”对于艺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它已经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噱头。尼采曾经预言,一旦脱离古典规则和界线的束缚,就会出现“艺术解体”。第一代试验艺术家体验过一种令人振奋的自由;但是,用斯蒂芬·斯彭德的话说,“接下来就会导致一种更新的和更彻底的支离破碎局面,晦涩难懂,没有任何目的地讲求形式(或者说无形式可言)”。永无休止地寻求新奇会导致益发怪诞的浅薄空洞,这是严肃艺术死亡的先兆。*[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20页。
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简单地指责当代西方艺术是有欠公允的。或许这种感性自由的泛滥来自西方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感性一极,一种至深至远的狄俄尼索斯精神。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简单地指责当代西方艺术也是有欠公允的。或许这种感性自由的泛滥恰恰出自抵御理性生活的需要,“为了抗击理性化的科层社会——工作的单调、闲暇时间的无聊、科学以及商业扼杀灵魂的实用倾向——人们需要艺术,就像需要宗教一样。艺术挺身而出,对抗骨子里与审美背道而驰的社会主流。艺术批评社会主流而且提供取代它的办法,或者说解脱方法——为群众提供娱乐,即无神论社会里麻醉人民的鸦片”*[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22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为西方所独有,在分工日益细化、异化不断加深的现代社会中,包括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观众在欣赏口味上也越来越西方化了。在抽象的符号世界里思考了一天或在机械的流水线上忙碌了一日之后的人们,宁愿让自己已经麻木的神经和已然疲惫的身体去接受《007》式的刺激,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吟咏那余音绕梁的唐诗、宋词了。
“今天,个体可能更加孤独,或许因为密切的人类接触几乎不存在;孩子越来越少,家庭生活远不如从前丰富,而家人住处更加分散,相隔甚远。人们更有可能在图书、电影、电视节目中寻找发泄情感的途经。”*[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27页。换言之,当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被西化之后,我们又有什么可能拒绝或避免西方式的情感方式和艺术方式呢?因此,不独今日的西方人,在全球化浪潮日甚一日的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陷入了感性与理性分裂对立的心理——文化格局。理性的极端发展需要感性的极端发展加以补救,以相反相成的方式重新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Sensuous Craziness in Western Arts
Chen Yan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100)
Ever since ancient Greece, the Western people began to regard artistic creation as means or channels to let off their hidden feelings, thus appeared their tragedies full of corpses on the stage , their profligate and unrestrained dances, their hoarse and exhausted rock and roll, and their films with unbridled indulgence of human desires and passio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 catharsis of sensuous feelings not only intensifies the passion and vitality in art creation, but also corrects spiritual alienation caused by rational speculation, thus bearing certain meaning of humanism. But, meanwhile, it brings about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sensuous incitement, and lead to impasse of corporeal senses. One cannot understan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ar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ir sensuous craziness whereas one cannot rethink its problems thoroughly without know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ensuous craziness. And all of this should begin with ethical mental structure with the fission of sensuousness and rationality.
Western; aesthetics; art; sensuousness; craziness
2015-03-06
陈炎(1957—),男,北京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文明的结构与艺术的功能”(07JJD751079)的阶段性成果。
I206.7
A
1001-5973(2015)03-0012-09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