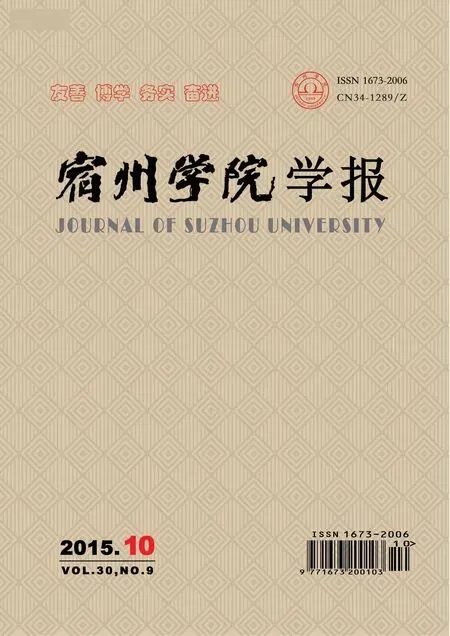互文性视角下《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对比
汪蓝玉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互文性视角下《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对比
汪蓝玉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选用《红楼梦》两种英译版本,就“云雨”一词的翻译作对比分析,在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作为互文指涉的避讳语的翻译策略。“云雨”一词在原文中共出现8次,两种版本的译文对该词的处理共有5处不同,3处相似,不同之处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云雨”一词的翻译对比研究为避讳语的翻译提供了启示:直译,保留原互文指涉的符号地位,并根据被动互文性构成的语篇内的语义连贯“释一而足”;意译,以译入语读者为导向转变原互文指涉,并适当增添新互文性作“补偿式译写”;略译,在特定情景下,基于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可在译文中略译互文指涉,以产生“留白”效果。
关键词:《红楼梦》;避讳语;互文性;互文指涉;语料库
1 问题的提出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艺术瑰宝,自1830年以来,共出现了9种英译本[1]。国内学术界对《红楼梦》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9年以后,研究呈现多样性、深入性与跨学科性。《红楼梦》英译研究主要分为总体研究与局部研究[2]85两大类,总体研究包括文化翻译研究、单个译本或多个译本对比研究、翻译策略研究以及翻译史研究等;局部研究主要是微观研究,包括对某个或某类词语的翻译、修辞(如隐喻、委婉语等)翻译、小说中的诗词翻译、人名翻译、服饰或饮食名词翻译等。据统计,后者在全部《红楼梦》英译研究中所占比例超过65%。此外,《红楼梦》译本研究的跨学科特色日益显著,已将翻译学、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理论应用于《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之中,开拓了研究视野,推动了《红楼梦》英译研究的学科建设[2]90。这些成果,都为日后《红楼梦》英译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本文着眼于局部研究,结合互文性翻译理论,探讨《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
《红楼梦》中多次用委婉而极富诗意的“云雨”一词暗指男欢女爱之事。“云雨”是汉语言文学中一个经典的性爱隐语,其意象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学界普遍认为,“云雨”的性爱涵义来源于古人的原始生殖观——云为天地阴阳结合之状态,雨为结合之产物,云雨是“天地交媾的产物”[3]。殷墟卜辞就有“性交求雨”的祭祀形式[4]。另外,“云雨”的性爱意象也可以在《周易》《诗经》《高唐赋》等作品中找到用例。《红楼梦》中,“云雨”一词与“风月”“眠花卧柳”等相似,暗指男欢女爱之事,都属于避讳语的范畴。“云雨”不仅是一个避讳语,从其意义起源与演变来看,其本质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与中国历史上诸多文学作品以及古人的思想观念有着种种联系。因此,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一内涵丰富的避讳语,需要深入研究。对于诸如“云雨”这类避讳语的翻译,可以尝试从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来进行探究。

[4]顾曰国.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J].外语电化教学,2007(2):3-12
[5]Kress G,T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M].London: Edward Arnold,2001:87-88
[6]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中国外语, 2009(1):24-30
[7]潘艳艳.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及身份构建[J].外语研究,2011(1):11-15
[8]Tsur,Reuven.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M].Amsterdam:NorthHolland.1992:1-2
[9]Tsur,Reuven.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Second,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M].Brighton/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2008:1
[10]Gibbons A.Multimodality,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M].London: Routledge,2012:1,208-211
[11]Stockwell,Peter.Cognitive Po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J].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2007(1):135-152
[12]Lewis,David.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 books: Picturing Text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31-45
[13]赵秀凤.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认知诗学研究的新进展[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3(6):43-51
[14]Ensslin A.Responsibility Narrative and Cybertextual de-intentionalisation:Kate Pullinger's The Breathing Wall[C].//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d Multimodal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9:158
(责任编辑:李力)
2 互文性理论与《红楼梦》中避讳词英译的概说
本文将在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下探讨《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最早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的是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多娃(Kristeva),而首次真正系统地将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 Theory)介绍到翻译研究领域的人是哈提姆(Basil Hatim)和梅森(Ian Mason)。该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5]125。广义上来说,互文关系不止存在于文本间,还可以拓展到文化之间、人类的思想体系之间。哈提姆认为,翻译本身也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在源语与译语、作者与译者、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乃至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都有着广泛意义上的互文性关系”[6]。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是互文性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识别与转换”技巧的使用水平直接关乎译本质量[7]。此外,互文指涉从一个语篇到另外一个语篇之间所跨越的距离便构成了所谓的“互文空间”(intertextual space)。互文空间的跨度小至语篇之间,大至时间或是地域。在这一跨越的互文空间之中,互文指涉会形成一个“互文链”(intertextual chain)。“根据互文链是存在于语篇之内还是指向语篇之外,可以将互文性区分成两类:被动互文性和主动互文性”[5]129。本文讨论的“云雨”一词就是一个互文指涉,分别与诸多文学作品和古人的思想观念构成狭义与广义的互文。故翻译这一互文指涉时,应当注意其信息地位的保留、互文空间的变化、互文链的形成等。
《红楼梦》中避讳语的英译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如张映先等将霍克思的“译者三责”理论与翻译伦理中的再现伦理、规范伦理和交际伦理相结合,探讨霍克思英译《红楼梦》对避讳语的处理方式,最终说明伦理的视角在翻译批评与实践中颇具指导价值[8]。马文书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比杨、戴夫妇和霍克思的两版《红楼梦》译本中性爱避讳语的翻译,发现前者多直译、后者多意译的现象是由中西方性爱观的差异所致[9]。胡君等从译者主体性看《红楼梦》中死亡委婉语的翻译,认为翻译委婉语时, 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证译文语义的准确与文化特色的保留[10]。这些研究对于本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将互文性翻译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和实用文体翻译研究,如吴迪龙从互文性角度讨论了诗歌的可译性、翻译标准、翻译归(异)化策略以及翻译中语音传递的处理等问题,论证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诗歌翻译研究的可行性[11]。李建红从互文性翻译理论的视角探究电影片名的翻译,指出在翻译电影片名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译者要采用虚化和实化的翻译策略,正确处理互文指涉的保留与转换[12]。此外,《红楼梦》中互文性文本的翻译研究已有先例,如祖利军从哲学视角和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出发研究《红楼梦》中“引用”的俗语和谚语的翻译,分析发现,由于受到译者“主体”与“他者”互动关系的制约,“引用互文性”无法在译文中得以再现[13]。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比较与探究《红楼梦》不同译文对性爱避讳语“云雨”一词的处理技巧,进而探讨避讳语的翻译策略。
3 《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比较
3.1语料库检索结果
本研究所用语料来自绍兴文理学院语料库的《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从中选择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简称“杨译”)和霍克思的译本(简称“霍译”)作对比研究。检索发现,“云雨”一词出现在《红楼梦》的前15回,共计8处。就语篇内而言,依次出现的8处“云雨”构成了一条互文链,意义相互连贯;从语篇外看来,“云雨”与古人的原始生殖观以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云雨意象构成互文链。
就“云雨”一词的翻译而言,对比显示,两版译文在第4处(杨译为“love”,霍译为“art of love”)、第6处(杨译为“the instructions”,霍译为“the lesson”)以及第8处(杨译为“carried her to the kang”,霍译“carried Sapientia to the kang”)的译法相似,其余5处各不相同。这5处中,杨、戴夫妇多将“云雨”译作以 “cloud and rain”为中心的短语,即对“云雨”的直译(第1、2、5、7处),而霍克思的译文则多为含有“love”的短语(第2、3、4、5、7处)。两版译文对“云雨”一词的不同译法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杨、戴夫妇与霍克思不同的翻译思想与策略;同时,从互文性翻译理论的视角观之,两版译文间的异同均为翻译避讳语提供了策略性的启示。
3.2不同译文体现的两种翻译观
“云雨”一词的译文在杨、戴夫妇与霍克思的笔下不尽相同,可体现出双方不同的翻译观。党争胜曾概括性地指出,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为严谨忠实原文的“临摹”,而霍克思是富有创造性的“译写”[14]99。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为“尽可能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且秉承将中国文化推出去的理念,他曾表示“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15]。由于“云雨”这一避讳语有着深厚的文化蕴含,与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因此,对于肩负着向外国人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的杨宪益来说,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保留“云雨”这一意象,这便取代了译文的易读性,于是他多将其直译为以“cloud and rain”为主体的短语。霍克思的翻译思想则为强调忠实于原作艺术性,以让读者能完全理解作品为目的,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从而进行创作性的翻译。他在《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言中曾表示“我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把一切都传译出来……”[14]99“云雨”这一互文指涉的意象对外国读者而言是陌生的,因此,不难理解,霍克思更倾向于传达出其本质意思,为读者理解排除困难,所以便有了“made love”“art of love”“act of love”等意义清晰直白的翻译。
在不同翻译思想指导下,“云雨”这一互文指涉的识别与转换的过程在两个版本的译文间有着极大的差异,这将为翻译避讳语带来策略性的启示。此外,两种翻译观都存在局限性:杨宪益注重文化外宣的“临摹”译法很可能造成译文与译入语读者的跨文化鸿沟——“cloud and rain”的翻译会让外国读者费解;霍克思以译入语读者为出发点的“译写”则会牺牲原文的文化特质——“云雨”的意象与文化蕴含被摒弃。由于“云雨”这一避讳语的特殊互文性特征,这些局限性实际上并不明显,后文将对此作详细分析讨论。
4 互文性理论下两种译文对翻译避讳语的启示
4.1“释一而足”的直译
对“云雨”一词的翻译,杨、戴多作直译处理,从而在译文中保留了“云雨”的意象与符号地位,虽然这会造成外国读者的理解困难,但因被动互文性的存在,问题便迎刃而解。互文性翻译理论认为,语篇之内的互文链能构成被动互文性。被动互文性可以构成语篇内部的连贯和衔接,从而互文指涉在语篇内的意义得以连续。鉴于此,杨译中四处含有“cloud and rain”的短语已构成互文链而具有被动互文性,第一处的译文“sexual transport of cloud and rain”中的“sexual transport”解释并赋予“cloud and rain”以性爱指示意,于是后文第2(rain-and-cloud games)、第5(sport of cloud and rain)、第7(the sport of cloud and rain)处则基于被动互文性秉承了第一处的意义,“cloud and rain”的性爱蕴含得以延续,为读者所接受。因此,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杨译对“云雨”的处理策略不单单是直译,译者同时利用了被动互文性,仅在第一处作详细解释,便将“cloud and rain”的含义统一起来。这不仅在译文中省去了不少笔墨——无须对每个“cloud and rain”加注,而且巧妙地填补了外国读者对“cloud and rain”这一直译词理解上的鸿沟,成功地保留了“云雨”这一标志性避讳语的文化特质与符号地位。这种处理方法对翻译在文中依次出现的避讳语提供了启示:直译,保留原文的符号地位,再利用被动互文性的意义连贯特征“释一而足”。
4.2“补偿式译写”的意译
与杨、戴夫妇的直译不同,霍克思以读者为中心,舍弃了“云雨”本身的符号地位,转而将其“译写”为“act/art of love”和“made love”。实际上,对比可发现,霍克思对“云雨”的翻译并不像杨译那般符号化,而是只求意义传达——两处译为“make love”,两处为“art of love”,一处为“act of love”,剩下各不相同。虽说译文大多是以“love”为中心的短语,但并未统一使用一个相对固定的短语来翻译“云雨”,显然符号化程度低。从互文性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看,这里霍克思在翻译中采用了转化互文指涉的方式,即舍弃了原文互文指涉的符号与信息地位,将其转化为意义相关的新互文指涉。但在转化过程中,难免会丢失原互文指涉的部分信息与互文性。而“art of love”的译文则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art”即“艺术”,常与“beautiful/wonderful creation”等文本或意识形态形成互文。换言之,“love”前加上“art”,便使译文增添了新互文指涉与互文性,不仅向读者传达了“云雨”的性爱之义,还告诉读者,这是具有艺术性、美妙的性爱。这与“云雨”表达出的含蓄、文艺的性爱之义相似。然而可惜的是,“art of love”仅出现两次,未能形成更大规模的互文链。霍克思将“云雨”译作“art of love”对翻译避讳语的启示可概括为:可意译,为方便读者理解,转化原互文指涉,同时添加新互文指涉来弥补转化过程中信息量的丢失,即“补偿式译写”。
4.3“精简式留白”的略译
语料库检索的对比结果显示,两个版本的译文对“云雨”的翻译有3处相似。首先是第4处,杨译为“love”,霍译为“the art of love”。这里霍克思的译文与别处类似,无须多言。而杨宪益夫妇在此处非常简略地将“云雨”译作一个“love”,与其他几处的译法大相径庭。第4处“云雨”所在的文本是《红楼梦》第六回的标题,而标题理应简单明了,故可以推测,杨、戴夫妇是为了精简篇幅,在译文中省去了原互文指涉的大部分信息,营造出“留白”的效果:“taste of love”虽未明确指出原文的性爱含义,但却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宝玉究竟初试了怎样的爱?如此可以提高读者兴趣,吸引读者接着往下看。
第6处原文为“所训云雨之事”,杨译为“instructions”,霍译为“lesson”,两译文意义相近,均只译出一个“训”字,“云雨”未被译出。究其原因,由于前文已经交代过了警幻仙子曾“秘授云雨之事”(第3处,杨译:initiated him into the secrets of sex,霍译:give him secret instructions in the art of love),因此不将“云雨”译出,而只点到警幻仙子的“训”为止,读者也能明白,这里的“instructions/lessons”即指代前文的“the secrets of sex/ the art of love”。如此略译,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译文出现重复罗嗦
最后,第8处两种译文也都未译出“云雨”,而只译出“抱到炕上”(杨译为“carried her to the kang”,霍译为“carried Sapientia on to the kang”),究其原因,由于前文已经交代秦钟偷偷摸摸来找智能,就是要非礼她,因此,当将“抱到炕上”译出来时,读者就已明白后面要发生什么,因此,这里略去“云雨”,与其说是省去了原文部分信息,不如说是再次制造了“留白”效果,给读者留下自行想象的空间。若是皆遵循原文,在“carried her to the kang”后再加上一些表示男女之欢的描述,反倒会使译文显得冗长而趣味性大减。
两种译文相似的处理方式对翻译避讳语的启示为:根据需要适当略译互文指涉,避免重复赘述,同时营造出“留白”的效果,即“精简式留白”译法。
5 结 语
语料检索结果反映,《红楼梦》杨、戴夫妇与霍克思两个版本的译文间,“云雨”一词的译文共3处相近,其余5处各不相同。分析发现,他们不同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由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所致:杨宪益重视中华文化的外宣而尽可能使译文贴合原文的内容与形式;霍克思则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云雨”这一互文指涉的识别与转换的差异为翻译避讳语带来了如下启示:直译,保留原互文指涉的符号地位,并根据被动互文性构成的语篇内的语义连贯“释一而足”;意译,以译入语读者为导向转变原互文指涉,并适当增添新互文性作“补偿式译写”; 略译,在特定情景下,基于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可在译文中略译互文指涉,以产生“留白”效果。
“云雨”具有深远的中国文化内涵和明显的互文特征,在翻译中值得研究。本文尝试以互文性翻译理论视角分析《红楼梦》中“云雨”一词的翻译,结果证实是可行的。《红楼梦》中类似的避讳语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作系统性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24(5):46-52
[2]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J].中国外语,2012,9(1):84-93
[3]杨琳.“云雨”与原始生殖观[J].社会科学战线,1991(1):80-89
[4]翟明刚.论中国文学的云雨意象[J].浙江社会科学,2009(5):88-93
[5]Hatim B,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90
[6]Neubert A,G M Shreve.Translation as Text[M].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123
[7]马向辉.互文指涉识别方法与探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27(2):94-96
[8]张映先,张人石.《红楼梦》霍克思英译本中避讳语翻译的伦理审视[J].红楼梦学刊,2010(2):306-322
[9]马文书.试论中西方性爱观之差异在《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体现[J].作家杂志,2012(4):167-168
[10]胡君,贾文波.从译者主体性看《红楼梦》中死亡委婉语的翻译[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9(3):100-102
[11]吴迪龙.互文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10:165-172
[12]李建红.电影片名翻译的互文性探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12):42-47
[13]祖利军.《红楼梦》中俗谚互文性翻译的哲学视角[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4):74-77
[14]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J].外语教学,2013,34(6):99-103
[15]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责任编辑:胡永近)
作者简介:汪蓝玉(1992-),女,安徽金寨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互文性理论视角下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避讳语翻译对比研究”(yfc100093)。
收稿日期:2015-07-17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5)10-0080-04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5.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