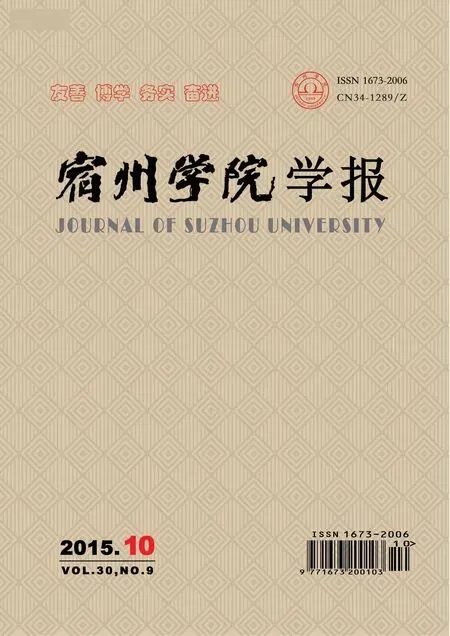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视阈下的《都柏林人》
刘学云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视阈下的《都柏林人》
刘学云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都柏林人》是一部诊断20世纪初都柏林社会文化症候的经典之作,詹姆斯·乔伊斯以其深邃的笔触揭示了当时都柏林的社会现状。在殖民文化的大背景下,都柏林人逐渐变得精神麻木,处于双重压迫之下的男性更是濒临崩溃边缘,男性气质面临危机。立足于社会语境,借助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详细解读《都柏林人》中的男性气质。通过分析发现,不管归类于何种男性气质类型,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最终都陷入迷茫的精神困境,最后指出自我身份的焦虑和男性角色自身的软弱是导致男性气质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精神困境;男性气质
1 问题的提出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20世纪伟大的爱尔兰小说家之一, 其作品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柏林人》(《Dubliners》)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由15个短篇小说构成,以都柏林社会为大背景,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20世纪初都柏林人的精神困境。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乔伊斯主要是以描写男性人物的精神困境来表现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非但没有表现出男性角色赋予他们的力量与坚定,反而一个个呈现出胆小怯懦的精神特质。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家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类型划分来分析《都柏林人》中的男性气质,进而揭示出自我身份的焦虑和自身的软弱是导致男性精神困境的重要因素。
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将女性研究推向顶峰,而与女性研究密切相关的男性气质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发展。社会学家康奈尔是男性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1],她(康奈尔是位跨性别者,其生理性别为男性,生活中用女性身份出现,故文中称为“她”)[2]的著作《男性气质》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在她的著作中,康奈尔首次指出男性气质具有多样性,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占统治地位,而其他三种男性气质则处于被支配、被利用和被边缘化的性别权利关系中。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为解读《都柏林人》中的男性气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虽有维护或建构男性气质的欲望,然而由于社会的瘫痪和自身的软弱,他们构建男性气质的欲望均以破碎告终,继而陷入迷茫的精神困境。
以下将对四种男性气质逐一解读。
2 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危机
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支配性指的是一种“文化动力,凭借着这种动力,一个集团可以声称和拥有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3]105。而支配性男性气质正是与整个社会所颂扬的文化息息相关,因而也被大众广泛接受,它代表着权力和力量。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统治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遇到外界的挑战和威胁。“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力达成一致时,支配性才能建立起来。”[3]106因此,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地位与社会的主导文化以及历史语境戚戚相关。当颂扬它的文化氛围发生变化时,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其统治地位也会随之动摇。20世纪初的都柏林仍然处于父权制社会,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紧密相连的力量、权利、地位等也就成为当时社会所称颂和膜拜的品质。《都柏林人》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渴望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是在建构过程中有的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声称自身支配地位,有的则面临着来自社会和女性的挑战。久而久之,社会赋予他们应有的力量逐渐衰退,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地位也出现危机。他们无法找到正确的出路,最终陷入迷茫的精神困境。
《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就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但同时他也面临着潜在的男性气质危机。他的男性气质具体表现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两方面。首先,加布里埃尔下意识地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满意,并引以为傲,经常表现出一种以我为中心的高姿态。其次,作为男性,他很享受自己的主导地位,乐于出席并把控各种社交活动,并且已经习惯于成为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的焦点人物。此外,他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妻子对他的无条件崇拜和顺从上。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个拥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形象。然而,与三位女性的正面交锋冲击着他男性气质的支配地位,巨大的心理落差将他席卷到迷茫的精神困境中。故事刚开始,带有某种优越感的加布里埃尔试图用教育和婚姻话题调侃姑妈家的女仆莉莉。“现在的男人都是直说废话,直到骗到你身上的所有东西”[4]252。莉莉不经意间的回应似乎使他高高在上的男性地位受到打击,虽然刚开始他像做错事一样感到局促不安,最后他还是高姿态地硬塞给莉莉些许小费,并匆忙逃离现场。如果说与莉莉的交流不畅使加布里埃尔初次体验被挑战的失落,那么与艾弗丝小姐的争辩则使他爆发被质问的愤怒和无奈。艾弗丝小姐是一位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她言语犀利,直言不讳,用略带挑衅的语气质问加布里埃尔为什么选择去欧洲大陆而不是自己的国家爱尔兰旅行。艾弗丝小姐的犀利盘问让加布里埃尔变得不知所错,他极力地想维持自己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清醒与镇定,但面对艾弗丝小姐的逼问,还是控制不住激动地情绪,“跟您直说吧,我的祖国让我感到厌烦!厌烦!”[4]266艾弗丝小姐的质问让加布里埃尔变得被动、焦虑甚至有点惧怕,他的这种情绪直到艾弗丝小姐离开才稍微得以缓解。在内心强大的艾弗丝小姐面前,象征男性权威的理智、自信和尊严破碎了,他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再次出现危机。但是,最后给他支配性男性气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妻子,家庭生活中,加布里埃尔无疑是主角,享受着绝对的权威地位,作为丈夫,他把掌控整个家庭视为理所当然,包括主宰妻子的行为甚至思想。夫妻两人回到旅馆后,加布里埃尔一直在回忆他和妻子在一起的甜蜜场景并试图同妻子亲热,但妻子格莉塔却沉浸在对初恋情人的回忆中不能自拔。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情感世界却似两条平行线一样没有交点,此时的他觉得已经失去掌控妻子的能力,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为何伤心。他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焦急地想要维护自己的支配性地位,就像不慎落水的人一样,拼命地想挽回,却只能做无力的挣扎。面对来自女性出其不意的挑战,加布里埃尔的男性权威地位步步下跌,直至谷底。然而面对女性的直接叫板,加布里埃尔并没有正面反击,反而表现得怅然若失,不知所措,最后陷入迷茫的精神困境。
3 共谋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失落
一般来讲,社会生活中,能够真正实现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很少,但大多数男性可从中获得益处。“男性与父权制存在共谋关系,一方面谋取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又避开父权制推行者所经历的种种风险。”[5]这就是共谋性男性气质。而从属性男性气质则突出了男性的从属地位,特别是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被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驱逐出男性气质领域,从而处于社会的底层,毫无地位可言。《都柏林人》中,很多男性都试图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是在建构过程中却遭到种种困难与无奈,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共谋性或从属性男性气质。《对手》中的法林顿便是共谋性男性气质的代表。由于社会的瘫痪和自身的软弱,法林顿的男性气质也出现相应的危机。他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抄写员,枯燥的工作使他厌烦,老板的责骂使他无力反抗,沉重的家庭负担更使他几乎窒息。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家庭生活的窘迫使法林顿的男性气质屡遭重创,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努力工作或者乐观生活来维护受挫的男性气质。相反,他选择了用暴力来发泄这种不悦。他经常在破旧的酒馆里喝得烂醉如泥,甚至还摆阔,典当手表请别人喝酒,并自欺欺人地向酒友吹嘘自己战胜了老板,以此满足男性破碎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力量的强大,他和别人掰手腕,失败后却质疑比赛的公平性并要求再来一次。他甚至还试图在酒馆里引诱一位女性,以此显示自己作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力。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回到家中他还对自己的孩子施展暴力,全然不顾孩子凄惨的喊叫。所有这些行为在法林顿看来都是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所以他想极力地维护他扭曲的男性气概,只不过是通过一些病态的方式,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他注定还是无法逃脱困境,只能痛苦地挣扎在原地。
在康奈尔看来,从属性男性气质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寄宿公寓》中的多伦先生就是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典型代表。面对强势的莫尼太太,多伦先生的男性气质变得不堪一击,这主要表现在他和莫尼太太较量中的被动和从属地位。当发现女儿波莉和多伦先生的恋爱关系时,精明的莫尼太太不动声色地打着如意算盘,并掌控着事态的发展,有十足的把握能成功将女儿嫁给多伦先生,而多伦先生的胆怯懦弱和莫尼太太的自信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伦先生一直忐忑不安。他两次试着刮脸,但那双手总在发抖,只得罢手……他在下楼时,觉得面前朦朦胧胧的,原来镜片上又积了一层水气。此时,他恨不得冲破房顶,飞入另一个国度,再也听不到这类烦恼之事。”[4]90两人谈判之前,莫尼太太信心满满,而多伦先生则显得异常紧张,双手都在抖动,甚至还想用逃避的方法摆脱麻烦。多伦先生清楚地知道自己陷入了莫尼太太的圈套,也明白他与波莉结婚对他没好处,因为和波莉结婚会使他臭名昭著,甚至丢掉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屈从于强势的莫尼太太。在这场两性地位的无声较量中,多伦先生并没有体现出男性应有的权威和力量,只是唯唯诺诺地屈服于女性的强势,他毫无主动权,甚至想要以逃离的方式结束心中的焦虑。女性的强势淹没了男性的力量,消弭了男性的意志。面对女性的强劲挑战,两性地位被颠覆,男性只得被动地接受他的从属性地位。
4 边缘性男性气质的迷失
当“性别与其他机构相互作用后发展出的男性气质间的进一步关系”[6]时,男性气质的边缘性随之出现。《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是边缘性男性气质的代表。他不像加布里埃尔一样渴望支配性男性气质,也没有像法林顿一样向生活妥协,被迫接受共谋性男性气质,同时又不甘于从属于女性,他只是蜷缩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与世隔绝,不仅在空间上处于社会的边缘,在心理上也将自己封锁在情感的角落里,不与外界发生任何交流。孤独的折磨使他不敢投身生活,他无力地在精神的边缘地带忍受着痛苦,心灵慢慢走向死亡。边缘性男性气质在达菲先生身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他完全排斥充满物欲的现代社会,也不想在社会中争权夺势只为获得权威地位。城市是权威的中心,能够在中心获得一席之地也是显示支配地位的一种方式,但是,达菲先生却排斥城市,他宁愿生活在偏远的郊区。从对住处的选择来看,他排斥构建支配性男性气质。其次,达菲先生的生活圈子完全是由自己组成的,他拒绝他人的介入,也排斥任何物质或精神上的混乱[7]。“他既没有同伴,又没有朋友;没有加入教会,也没有任何信仰。”[4]149作为男性,他不憧憬体现男性力量的体育运动或社交活动,只是喜欢在音乐会上听音乐。他身上似乎看不到男性力量和权威的影子,仅存的只是艺术家的细腻敏感。这种特质也印证了他男性气质的边缘性。再次,达菲先生的情感世界是一片荒原,他已失去了爱的能力。他和辛尼科太太开始了一段感情,但在一次倾心的谈话之后,当辛尼科太太热情地抓住他的手去贴她的脸时,达菲先生竟然恐惧地反抗,并决定离开她。几年之后,辛尼科太太的死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故事的最后,心灰意冷的达菲先生被孤独包裹着,他突然心生顿悟,自己在剥夺自己人生的权利的同时也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此刻的他就像是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宛如一具空壳飘荡在精神的荒原中。精神的幻灭使他本就处于边缘地带的男性气质更加摇摇欲坠,他不得不迷失在孤独的困境中,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5 结 语
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塑造了不同的男性形象,借用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类型划分,本文分析了小说中的男性气质问题。20世纪初的爱尔兰仍然是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但是,由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和自身的软弱等原因,男性气质也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有的试图维护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地位却以失败告终,有的无奈地作出妥协,接受共谋性男性气质,还有的面对强势女性的挑战,不得不被动地使自己处在从属性地位,有的甚至试图远离父权制社会,将自己蜷缩在孤独的边缘地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男性气质类型,这些男性角色最后都挣扎在迷茫的精神困境中,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如果把《都柏林人》中所反映的男性气质危机纳入更为广阔的范畴,就会发现小说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其实喻指了整个爱尔兰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困惑。20世纪初的爱尔兰处于一种麻木瘫痪的状态,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焦急地想要找回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束缚和自己的软弱病态,均以失败告终。他们不能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因而陷入迷茫的精神困境,无力地挣扎着。乔伊斯就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带着矛盾的情感审视着爱尔兰,无情批判同胞的同时,也流露出他对爱尔兰民族的无限同情。通过对男性气质危机的思考,乔伊斯也表现出对整个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担忧。
参考文献:
[1]方刚.康奈尔和她的社会性别理论[J].妇女研究论丛,2008(3):10-14
[2]胡晓军.男性要走向哪里:论《洪堡的礼物》中的男性气质[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90-93
[3]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110
[4]乔伊斯.都柏林人[M].孙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90-266
[5]黄河.男性研究对性别平等教育的意义[J].妇女研究论丛,2008(3):40-47
作者简介:刘学云(1991—),女,河南鹤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小说。
收稿日期:2015-08-01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5)10-0063-04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5.1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