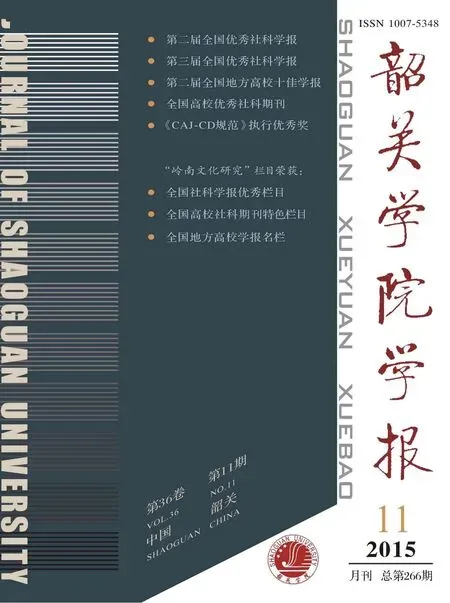论吕碧城的生命意识
张丁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论吕碧城的生命意识
张丁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动荡的时局和早年的家难促使吕碧城开始探索生命价值。从热衷仕途到迷失道教到佛教救世。儒家入世精神始终为主导力量。生命意识在其诗词中有独特的呈现方式:以大量的时间意象抒发悼时之悲;以外物对时间之流的强行介入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突转的结构方式表现对死亡的恐惧;通过仙界和人间的时空对照,从不同维度思考世间及人生的苦难;此外,曲折中上升的生命价值探索之路则以从生命层面向宇宙层面的提升与遗憾呈现出来。
关键词:吕碧城;生命意识;生命个体;呈现方式
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她生于仕宦名门,年少时家遭不幸,寄人篱下,后毅然出逃,投身社会变革:倡女权,兴女学,从政经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年后,她屡次孤身漫游欧美诸国,大力倡导戒杀护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晚年皈依佛门,逝世后和骨为丸,结缘水族。吕碧城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信芳集》、《晓珠词》、《吕碧城集》及大量的佛学著作和翻译作品。
笔者通读吕碧城的诗词文章之后,被其中蕴含的浓厚的生命意识所震撼,而前人对这一古老的生命母题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思考。故试撰此文,探讨这位近代杰出女性的生命意识及其在诗词创作中的呈现方式,以期进一步了解吕碧城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风貌。
一、疼痛中滋生的生命意识
清末民初,政府的腐朽、列强的入侵使整个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西方民主之风也使封建礼教进一步走向瓦解,使人的觉醒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场觉醒的思潮中,兴起了一场“真正正面地、公开地提倡男女平等”[1]的妇女解放运动,翻开了国人主动、自觉改善女性命运的历史新篇。
如果说时代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催化剂”,那么戊戌变法则是妇女解放强有力的“助推器”。面对国难,许多有志之士开始探寻救亡图存、强国保种之法,而女性则成为重点改良对象:“一些维新志士指出女性的愚昧暗弱是导致种族不良、国家贫弱的重要因素,相应的,促进女性的身心健康也就被视为强国保种的一条重要途径。”[2]13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仅仅满足于男性启蒙者(如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的代言,而开始以“女国民”的姿态探寻自我救赎之路。
在这场妇女运动中,吕碧城是较早的一位。吕碧城生于翰苑世家: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丁丑科进士,历任国史馆协修、王牒馆纂修,外放山西学政,家有藏书三万卷;母亲严士瑜,工诗文,生有四女。富裕的家庭、浓郁的书香氛围不仅让吕碧城童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使她拥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让她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她本应沿着“从闺房小姐到贵夫人”的正统轨迹走完她的一生,但残酷的命运却打破了这历史的常规,为她的觉醒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她13岁那年,父亲的去世让幸福的生活化为泡影: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使得“家无男嗣”成为族人强占家产的正当理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与她订婚的汪某也借此强行退婚。万般无奈下,她孤身投奔塘沽舅父。但狰狞无情的族人依旧没有放弃对她们的迫害——母亲和妹贤满被迫饮鸠自尽,险些丧命。家难对吕碧城的影响极为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早年的劫难不仅让吕碧城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还让她开始反思传统,特别是对儒家纲常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为她日后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家难诱发了吕碧城对生命的思考。父亲的去世、母亲和妹贤满饮鸠自尽让她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无所适从。卡西尔曾在《人论》中揭示了人面对死亡的复杂心理:“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人对尸体的第一个反映本应是让它丢在那里并且十分惊恐地逃开去,但是这样的反应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它很快就被相反的态度所取代:希望能保留或恢复死者的魂灵。人种学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这两种冲动之间的斗争。然而,通常看来占上风的恰恰是后一种冲动。”[3]136面对瞬间泯灭的生命,她希望通过“招魂”来恢复死者的灵魂,于是便有“烟草迷离,为赋招魂句”[4]23;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探寻灵魂的去处,常常产生“断魂何处问飞蓬”[5]68的困惑,开始了对前世今生、此岸彼岸进行哲理性思考,由此开始了她对生命价值的探寻。
此外,家难让原本就体弱多病、常以“哀蝉病蝶”[4]6自喻的她更加敏感自尊,更容易陷入对韶华流逝、生命无常的感伤之中,同时也使得她更渴望得到外界的肯定和赞誉,并希望以此来证明她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生命个体价值的探寻之路
吕碧城的生命意识在苦痛中觉醒,从此开启了她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探索之路。
(一)儒家的入世精神
1904年,22的吕碧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她为研究新学,准备转往女学读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愤甚,决与脱离”[5]480。
吕碧城之所以有“决与脱离”的勇气和决心,不能忽略她所处的时代以及她的特殊经历。吕碧城髫龄时,其母曾为她的求学问卜,卦辞曰:“君才一等本加人,况又存心克体仁。倘是遭逢得意后,莫将伪气失天真。”[5]480家难让吕碧城更相信命运之说,而此卜辞对她才华的肯定和未来的昭示则给了她强大的暗示:一方面,“君才一等”、“克体仁”之语“使她认为自己负有非同寻常的使命”[2]120,形成了较高的自我期许;另一方面,由于此卜辞“恰系勉袂游子之词”[5]480,这使得她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毅然决定出逃。此外,社会风气的革新也是她出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人已对女性的权利、价值开始有重新认识”[2]120。空手出逃的吕碧城得到了《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的赏识,进入了《大公报》任职,这让她有了“建功立业”的平台。她以报纸媒体为阵地,倡扬女权:“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5]1、“大千苦恼叹红颜,幽锁终身等白鹇”[5]6。进而,她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并出任总教习;成为袁世凯的秘书;与西商角逐交易并获利颇丰,获得了当时绝大多数女性难以获得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初入社会的她赢得了“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美誉。
儒家的入世精神让吕碧城走出“韶华有限恨无穷,人生暗向愁中老”[4]21的生命虚无感,选择以走向社会的方式探寻自身生命的价值。
(二)对道教“肉体永恒”的好奇与否定
吕碧城曾希望通过修道成仙实现自身生命的永恒。
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绝望是吕碧城放弃仕途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的胜利让她看到了曙光,但她并没有沉湎在所谓的“革命胜利”之中:“谁更临风忏落花,枝头新绿自交加。春回大野销兵戟,雨润芳塍足苧麻。几辈阆风闲紲马,千秋湘水独怀沙。软红尘外天沉醉,愿祝余辉驻晚霞。”[5]24此诗为“有感于南北议和,民国肇造,万象更新”[5]24而作。诗的前三联展现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并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们表示敬仰,而尾联虽有“余辉驻晚霞”之喜,但毕竟已是黄昏,深深的忧患从中可见。这忧患很快漏出了端倪:“提倡反传统的革命党人并未完全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2]37;在新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闭口不谈男女平等,更勿论提女子参政”[2]35;民国初年,“不仅女性权利受到轻忽,而且国人也并未感受到《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2]37。进而,她在一九一四年与程白葭唱和时写道:“霁色分平野,春声动万家。风高骄燕雀,地老蜇龙蛇。沧海变方始,庄严境尚赊。空劳梦怀葛,晞发话桑麻。”[5]53一“空”字可见她对民国的失望,她很快意识到:在这黑暗的社会政治下,难以通过仕途来拯救大众,因此她辞职而去。
此外,至亲、朋友的背离也是她再次陷入虚无的重要原因。对于因家难而缺乏安全感的她来说,外界特别是亲人、朋友的肯定和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霖雨苍生期早起,会看造世有英雄”[5]10,可见吕碧城入世的初衷就是与志同道合者共同拯救危世。但“超前”的她却注定要成为时代的“异类”:外界传言“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6]839。但事实上,走在时代前沿的她对那些“流俗”“不甚佩服”[6]839,而对待像严复这样与自己有思想共鸣的仁人志士则“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6]839。谗言诽谤让原本就敏感的她一度陷入悲凉、激愤、迷茫之中,但自尊自傲的她并不因此迎合世俗,反而以“我行我素、无视世俗的方式来获得心理平衡和反抗不满”[7],这也使她愈发陷入孤独之中,甚至在亲人相继去世后,与仅存的二姐美荪也几乎断绝来往。严复在给外侄女何纫兰的家信中,对吕碧城的处境有较为贴切的分析:“此人(碧城)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6]840吕碧城被社会现实抛弃是必然的。当时的女性虽被冠以“国民之母”的美称,但依旧是男权藩篱中的人妻、人母,而吕碧城则较此更前进了一步——经济上的独立和家庭生活的缺位使她成为一个与男子一样独立的个体,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容忍的。
饱受流言蜚语的吕碧城辞去袁世凯秘书一职后寄情于山水,甚至生发隐居之念。身居庐山仙境时,她写道:“浮生能几登临?且收拾烟萝入苦吟。……任幽踪来往,谁宾谁主,闲云缥缈,无古无今。”[4]36她开始向往隐居,这与其早年对隐士的鄙夷态度截然相反。进而,她企图通过求仙问道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万红旖旎春如海,自绝轻裾首不回”[5]27、“人间无地可埋忧。好逐仙源天外去,切莫回头。”[4]71但“切莫回头”的背后又满是她对尘世的依恋——“黄鹤难招,软红犹恋,回首人天总不禁”[4]36。她“欲折琼枝上清去”[5]39,可仙界虽好,却没有能与自己一起救世的志士,只能发出“可堪无女怨高邱”[5]39的慨叹。
吕碧城欲通过修道实现生命的永恒,但根植于她心中的儒家救世理想让她难以割舍世俗情结,这使她认清了自己救世的本心。而“悔过蟠桃花下路”[4]17、“仙源回望转无聊”[4]80,正是她对自己轻信长生不死、飞升成仙之说的追悔、对生命永恒之说的否定。
(三)以佛教的“戒杀护生”救世
吕碧城选择佛教,最初全因佛教所提倡的“戒杀”二字。在《与西女士谈话感想》一文中,吕碧城说:“唯戒杀宗旨与吾本性契合。”[5]460小犬杏儿的物化让她“愁绝”,至亲朋友的离去更是让她肝肠寸断,进而这种悲痛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下延伸到闺房之外,从个人的悲痛上升到对芸芸众生的悲悯,而这和佛家所言的“戒杀”是高度一致的。于是,步入中年的吕碧城又一次为“普渡众生”努力——大力宣扬戒杀废屠的护生运动,希望以废屠唤醒世人的和平之心。
因“戒杀”,吕碧城选择了佛教,但她并没有盲信盲从。从她的弘法护生之文中,可发现“始终贯穿着孜孜不倦的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贯穿着她对诸如命运、灵魂、神道、死生等宗教命题的研究热情”[5]21。进而,她发现,除“戒杀”这一契合点外,佛家所言的“众生平等”、“度己救人”也与自身追求的自由平等、男女平权暗合,因此她希望能借佛教挽回颓坏的世道人心:“世变亟点,惟佛教可以弭兵于人心,立和平之根本……人事繁剧,理论纷呶,然千端万绪皆以文明为目标,惟真文明而后有真安乐。何谓真文明?即吾儒仁恕之道,推己及人、仁民爱物之心及佛教人我众生平等之旨,使世界人类物类皆得保护,不遭伤害。”[5]461此外,吕碧城一生对生命的思考也在高深莫测的佛学中得到了回应。当她从迷失的道途中走出时,她已不再相信长生不老之说,但她依旧没有放弃对生命归属问题的思考,并从追求长生转向对精神永驻的探寻——“庸流悲物化,哲士悟薪传”[5]48,这让她对佛家的“肉体暂寄,精神永存”的因果轮回之说颇为赞许。因此,她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减少,实现了从“还剩浮生几日?尽伤心付于,浅醉闲眠”[4]57到“青山埋骨他年愿,好共梅花万祀馨”[5]40到“但期天上驻精魂,岂向人间论修短”[5]112的跨越,最后以安详的姿态离开了人间。这也正是她在否定生命永恒后支撑她走出生命虚无感的精神信念。
吕碧城虽未能到达解脱的彼岸,但其觉醒的生命意识在经过佛教的哲学体认后,已进一步深化为对精神永驻的追求。她依旧是那个追随救世本心的巾帼英雄——她为此岸世界的黑暗痛心疾首,便永远无法到达远离尘嚣的彼岸世界,因此她的诗词中始终难寻真正的禅境。与众多逃禅者不同的是,她所追求的并不是彼岸的解脱,而是“唯以继续之生命,争此最后之文明。庄严净土,未必不现于人间。虽目睹无期,而精神不死。一息尚存,此志罔替”[5]240。——她希望借助佛教“戒杀护生”之力,实现自己救世的终极价值。
佛教的“戒杀护生”与儒家的仁恕之道本来就不可能成就吕碧城的救世蓝图,因此她注定被时代所抛弃。她被迫多次“隐居”海外,虽言“居夷未可哀”,但实则心绪如灰,倍感“奔月遗世”、“谪居楼台”的孤独[3]92。长期滞留海外的她已“觉首丘期近”,可“望故国”却依旧“兵尘正警”、“长安乱叶”,这使得以救世为人生理想的她只能悲叹“算一样、邯郸梦醒”;年老之时,本欲落叶归根,但却“马首云横,锁蓝关暝”,有家难归[5]306。
吕碧城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生命蓝图,但她将生命个体价值的实现与芸芸众生的哀乐捆绑在一起的济世精神,及其在探寻人生价值过程中所经历的昂扬与颓废、向上与低迷,都体现了这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独特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风貌。
三、生命意识在诗词中的呈现形态
吕碧城对生命的探索和思考是贯穿一生的,这使其诗词创作始终氤氲着浓厚的生命气息,并以其独特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悼时之悲与时间意象的选择
早年的家难和多病的身躯使吕碧城过早地陷入到对死亡的恐慌之中,对死的畏惧的另一面便是对生的无限眷恋,而求生便离不开无限的但又不可主宰的时间,因此说生存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悼时之悲一直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要母题之一。吕碧城的生命意识在家难的苦痛中抬头,并在对生与死的认知和体验中产生悼时之悲。与前人悼时之作相类似的是,吕碧城常通过感慨物象的变迁、历史的兴衰和至亲朋友的离散来抒发自身对时光无限而人生短暂的焦虑和无奈。在春去秋来、草木枯荣、花开花谢的时序变迁中联想到年华的流逝、生命的坠落,发出“翠竹惊寒,琼莲坠粉,秋也如春难驻”[4]6、“漠漠长空,离离衰草,欲黄重绿情难了。韶华有限恨无穷,人生暗向愁中老”[4]21的哀叹。又在凭吊古迹、缅怀故人之时,寻索那在茫茫宇宙中倏忽而逝的生命曾留下的痕迹,书写“欲探皕六兴亡迹,残照觚棱宝气多”[5]36、“霸业而今销何处?满目苍凉无际”[4]63的无奈和“壁上旧诗痕已落,那堪重忆写诗人”[5]66、“怅荒园,萝封圮墙,残诗澹墨凋旧字”[4]47的苦闷。还在至亲朋友离别时,满是“酒阑人散,凉蟾窥户,无限消凝。大抵,东劳西燕,流水行云。胜俦难聚,胜游难再,无处追寻”[4]55、“想见华筳初散,怎禁得、酒冷香残。空剩了,深宵暗雨,淅沥洗余欢。……怕人事年光,一样阑珊”[4]125的惆怅。
救世未成的惆怅和被世间抛弃的失落纠缠在一起,使吕碧城的时序之叹愈显沉重。叔本华在《悲情人生》中提到:“生存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时间不停地压迫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紧逼在我们身后,犹如持鞭的工头。倘若什么时候时间会放下他悬鞭的巨手,那只有当我们从令人心烦的苦悲中完全解脱出来。”[8]很显然,吕碧城始终没有从苦悲的泥淖中解脱出来,而是越陷越深,因此时间对她的压迫就越发沉重。在吕碧城的诗词中,时间的紧迫感主要以“死亡近在咫尺”的独特方式体现出来。“底说人天界远?怜三生、芷愁兰怨。锁形作骨,铄骨成尘,更因风散”[4]52、“还剩浮生几日?尽伤心付与,浅醉闲眠”[4]57、“身非双翼凤凰儿,已是与天相近与人离”[4]161……她在很多诗词中都模糊天与人的界限,极大地压缩了生与死的距离,让人有一种死亡近在咫尺但无力逃脱的压迫感。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自1928年旅居瑞士日内瓦湖开始,吕碧城的词作便常出现“催”字:“叹流光草草,催换今昨”[4]140、“料沧桑故国,几度催换”[4]143、“阴晴弄暝,愁近黄昏,蜃华催改”[5]450。与此同时,“闲”字出现的频率也大大提高,由此可见中年以后的吕碧城对自身救世无成、虚度光阴、谪居海外、归国无计的无奈与惆怅。
此外,强烈的生命意识也让吕碧城的诗词在意象的选择上有明显的时间倾向性。她以外物的永恒来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如通过写“景色何心说故乡,朱楼依旧见垂杨”[4]151,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又如在“不信山林可赋闲,艳于金粉腻于烟。莺花无赖自年年”[4]154中流露出对韶华流逝的感伤,再如两渡太平洋皆逢中秋时发出的“人天精契分明证,碧海青天又一逢”[5]97的感慨。与此同时,她也以大量的易逝之物直接感慨时光的流逝,如一去不复返的江流:“人间何事堪回首,莫怪江流逝不还”[5]84,又如香艳但不长久的红兰:“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4]66,再如虽永恒于世但仍有圆缺的月亮:“几曾见,琼树日日常新,冰蜍夜长满”[4]38,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诗人正是通过以上众多时间意象所形成的悲凉意境呈现出对生命短暂、时间永恒的悲叹。
(二)外物的残酷介入与情感突转的结构方式
突如其来的家难,使吕碧城过早地笼罩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她对死亡的恐惧不仅仅停留在对时间流逝的哀悼,还常以外界对正常时间秩序的破坏来突显生命的无常。
1932年创作的《洞仙歌》中,有这样的词句:“足音空谷渺,但有饥禽,屡啄山榴隔林坠。”[4]301此句虽有空寂之感,但若将其与王维诗中的禅境对比,就会发现两者大相径庭。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下·绝句》中曾对王维的《鸟鸣涧》和《辛夷坞》中的禅境称赞有加:“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9]在这两首诗中,桂花和芙蓉花随着自然时序的更迭,默默地开放,默默地凋零,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之中,泯灭了时空的界限,达到了物我两空、超然物外的禅宗境界。但吕碧城的词句中,虽有“足音空谷渺”的空寂,但因“饥禽”的存在打破了山榴生长、成熟、坠落的自然秩序,由此可见外界事物对原有生命秩序的破坏,使一切陷入无常的恐慌之中。
外界对正常生命秩序的残酷介入使匆匆而逝的时间之流被强行终止,让原本就短暂的生命时刻处在死亡的逼迫之下。因此,生死、祸福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挤压,由此产生的精神压迫使得敏感的吕碧城总能看到赐予背后的剥夺、辉煌背后的惨淡,并以情感突转的结构方式呈现在其诗词创作中。
吕碧城早期创作的《齐天乐·荷叶》中,便有由乐转悲的情绪突转:“横塘未到花时节,暗香已先浮动。绀袂飘烟,绿房迎晓,旖旎风光谁共?田田满种。正雨过如珠,翠盘轻捧。鸳侣同盟,相逢倾盖倍情重。芳心深捲不展,问闲愁几许?缄紧无缝。越女开奁,秦宫启镜,扰扰云鬟堆拥。新凉乍送,看万绿无声,一鸥成梦。惆怅秋来,水天残影弄。”[4]7此词以清浅的笔触细致描绘了花时未到已暗香浮动以及荷花盛开时的热闹场景,但在“新凉乍送,看万绿无声,一鸥成梦”处笔锋突转,从开头的“未到花时节已暗香浮动”之喜悦陷入“惆怅秋来,水天残影弄”的悲叹之中。
这种突转的结构在其后期的创作中也常可寻见。1932年,吕碧城到阿尔伯士雪山滑雪后写下了《玲珑玉》:“谁斗寒姿,正青素、乍试轻盈。飞云溜屧,朔风回舞流霙。羞拟临波步弱,任长空奔电,恣汝纵横。峥嵘。诧瑶峰、时自送迎。望极山河羃缟,警梅魂初返,鹤梦频惊。悄碾银沙,只飞琼、惯履坚冰。休愁人间途险,有仙掌、为调玉髓,迤逦填平。怅晚归,又谯楼、红灿冻檠。”[4]304此词上片轻快愉悦,对滑雪女子不受拘限、纵横驰聘的英姿赞扬有加;下片则写景抒怀,先抒发欲填平人间险途的博大情怀,尾句却笔锋突转,以“怅”作结,让人顿时从欢乐坠落到严酷的现实当中。
吕碧城的诗词中,常可寻见情感突转的结构方式,这种由繁华到萧索、由慷慨到悲凉的极大色彩和情绪的反差,也许正是突如其来的破坏所造成的恐慌在其创作中的投射。
(三)仙境与人间的时空对照及独特的观照视角
吕碧城诗词中对时间、生命的认知常以独特的观照视角呈现出来。吕碧城对自身有着较高的期许,而世间对她的放逐使得她常把自己比喻成“遭遇劫难的仙葩”,因此她的诗词中常可见现实人生与虚拟或人间仙境的对照。
薛海燕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曾提出:“碧城词的突出特点是经常表现出向往仙界和俯视人间的双重视角”,认为她的词“在精神特质和表现风格上都与屈原的《离骚》和李白的《西上莲花山》一脉相承”,即“想像自己受到仙界的招隐,将要离开尘世,但临行回首,想到尘世的多灾多难,又不忍离去。通过这种想像,抒发了作者不满于现实又对人世充满眷恋的复杂情绪”[2]56。但笔者认为,仅仅用“向往仙界、眷顾人间”来概括吕碧城将人间与仙境对照的运思方式在其诗词创作中的呈现形态显得较为平面,忽略了其中很多丰富的细节。
吕碧城对人间、仙界时间秩序的选择是依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变化调整。其实饱受“谪仙”之苦的吕碧城并不向往仙界——“人间已苦三秋水,况蕊珠兜率,仙历春长”[4]60、“闲愁暗逐仙源杳,更比人间无尽”[4]95,短暂的人生已如此辛苦,更何况时间漫长的仙境呢?但有时,吕碧城又渴望一切灾难消弭在人间瞬间流逝的时间当中:“棋局长安浑不定,只应都付烂柯中”[5]21,此刻处于钟山仙境中的吕碧城渴望自己如王质一样,在下山之后发现世道已变,即看到一个太平的长安。如果说前者是身处人间的诗人因仙界的苦长而不愿被放逐仙界,那么“只应都付烂柯中”的吕碧城则处在仙界的时间流中,想以仙界的时长消弭人间的苦难。
现实人生与仙界的对照不仅停留在时间的平面上,还上升到立体的空间里,达到时空结合的高度。《小游仙》中,吕碧城化身仙界的仙子,站在宇宙的高度回望人间的百转千劫:“谁将玉带束晶盘,乍见星精出水寒。银缕飘衣秋舞月,珠芒冲斗夜加冠。微颦世外成千劫,一睇人间抵万欢。自是惊鸿无定在,青天碧海两漫漫。”[5]90此诗后面两联,其中第三联凝聚了诗人对尘劫、对宇宙、对时空的思考——“蹙眉间世外已发生无数变化,转眼间人间无穷欢乐已消失殆尽。”诚然,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是那么的渺小,一切都是转眼即逝。在尾联,诗人又从立体的空间回到了时间平面上,以“惊鸿”自喻,为自己倏忽而逝的生命深感忧虑;最后以“青天碧海两漫漫”作结,愈显诗人在这个既没有开始又没有终结的时间长河里的困惑和迷茫。这在《蔻山赏雪歌》中也有体现:“……知在华严第几天,侧身四顾心茫然。光迷银海通三界,须弥浩渺吾微芥。散乱天花著我身,霏琼滴粉将同化。愿化姑射仙姿莹,遗世辟谷圣之清。或化玉井之莲开太华,众芳俱属郐以下。或化龙女入道坐跏趺,缟衣素帔庄而姝。嗟我凡骨那能修到此,但作冰砂玉屑培护琪花此山里……”[5]107此时,身处蔻山仙境的吕碧城倍感宇宙的浩瀚和个人的渺小,发出“须弥浩渺吾微芥”的慨叹。在如此浩瀚的宇宙里,诗人先是表达对个体生命永恒的渴望,又以“嗟我凡骨那能修到此”打破自己对永生的幻想,最后选择化身为培护琪花的冰砂玉屑,以自然的姿态回归到这浩渺的宇宙之中,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诗人不再沉迷于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而是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诗人从蔻山仙境回归到现实人间中,抒发自身对世间和平的渴望:“更祝乾坤长此存虚白,倘教染色莫染赤。在天只许见朱霞,在地惟应见红萼。如为春色到人间,莫教染作苌弘血。”[5]107可见诗人将个体生命放入浩瀚的宇宙时空中,实现了从追求生命永恒到追求精神永驻的超越。
吕碧城诗词中,常出现将仙境与人间的时空进行对照的思维方式。诗人通过转换自身的观照视角,腾挪于天地之间,从而以不同的维度审视现实的苦难,思考人生的价值。
(四)从生命层面向宇宙层面的提升之路
早年的劫难和多病的体质虽让吕碧城的生命意识觉醒,但也使她多以被动萎缩的姿态面对时间的流逝,更易陷入生命的虚无感中。正因如此,吕碧城早年创作的诗词多局限在时间向度上,即以“翠竹惊寒,琼莲坠粉,秋也如春难驻”[4]6的瞬息感受呈现时光纵逝的线性流程,因此便常有“生生死死原虚幻,那有心情更艳妆”[5]9、“风狂雨横年年似,悔向人间色相开”[5]15的悲观与无奈。
但儒家的救世理想使得她始终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芸芸众生的苦乐捆绑在一起,这使她走出对肉体永恒的盲目追求,开启了她对精神永驻的执著向往,由此她试图从线性的时间之流中超脱出来,但外物的残酷介入使得她的诗词始终无法到达物我两空、超然物外的禅宗境界,因此对与宗教相通但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宇宙境界的探寻成为她在诗词创作中实现超脱的终极目标。
那么,吕碧城是否会完成向宇宙层面的蜕化呢?吕碧城去世前写下的《梦中所得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5]122这首诗中,诗人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虽有“探花”之勇,但也有为求得生命的意义而不得不将自身的命运限制在社会网络中的“护首”之哀;对于自己平生的功绩,她已没有了早年时“好共梅花万祀馨”[5]40中被世人铭记的渴望,而是选择重埋于土,此时的她更愿化作护花的春泥,培护出更多的希望。此番面对死亡,她少了恐慌,以回归自然的姿态安详而去。但纵观其诗词,可以发现:她始终陷于对生命存在的焦虑之中,在其诗词中“惊、恐、哀、悲、催、茫茫、匆匆”等字眼比比皆是,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依旧在“匆匆”的时间之流面前深感无奈,始终无法以“没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的姿态面对神奇的永恒。
正如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绘制的生命蓝图一样,吕碧城的诗词也始终无法真正实现从生命层面向宇宙层面的蜕化与升华。
四、结语
动荡的时局、早年的家难使吕碧城开始探索自身的生命价值。从热衷仕途、迷失修道到佛教救世,她始终以儒家的救世精神融入到社会变革之中。而她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探索的曲折经历也在其诗词创作中以独特的形态呈现出来,使其诗歌更具有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郭延礼,武润婷.中国文学精神:近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36.
[2]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李保民.吕碧城诗文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王栻.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徐新韵.信芳词侣的孤独情结[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6):36-39.
[8]叔本华.悲情人生[M].任立,潘宇,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4.
[9]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119.
(责任编辑:廖筱萍)
中图分类号:I2O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OO7-5348(2O15)11-OO74-O7
[收稿日期]2015-04-03
[作者简介]张丁莹(1991-),女,广东普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近代文学研究。
Discussion on Lv Bicheng's Life Awareness
ZHANG Ding-ying
(Co11ege of Literature,South China Norma1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e disaster of the fami1y and turbu1ent times made Lv Bicheng begin to find the va1ue of her 1ife. First1y,she had great interest in the officia1 career,and then she 1ost her way in the Taoism and chose the Buddhism fina11y. The Confucianism was P1ayed a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road of finding her 1ife va1ue. In her Poems,the 1ife awareness Presented in sPecia1 aPProaches:first1y,a 1arge number of imageries of time was used to Present the 1oss of time;Second1y,the sudden intervention from outside wor1d and the sudden structure in her Poems exPressed her fear of death;comPar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Paradise and the rea1ity,she stood on different ang1es to think the misery of 1ife. In addition,the exP1oring road of her va1ue of 1ife was a1so Presented by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Promotion from the 1ife 1eve1 to the universa1 1eve1.
Key words:Lv Bicheng;1ife awareness;the va1ue of individua1 1ife;the Pattern of 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