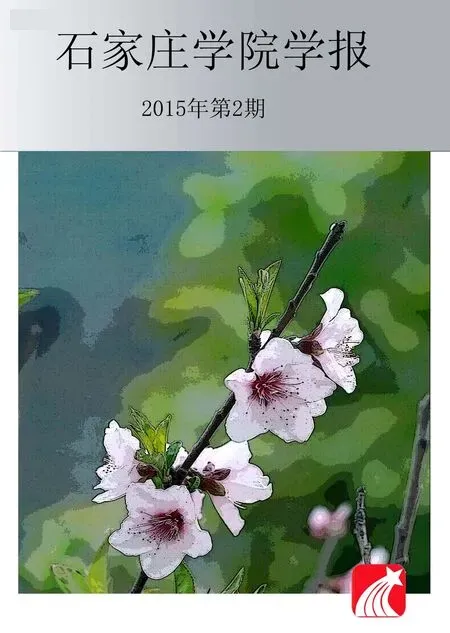在文学与政治关系漩涡中彰显作家主体意识
——1930-1950年代孙犁文学思考研究之一
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在文学与政治关系漩涡中彰显作家主体意识
——1930-1950年代孙犁文学思考研究之一
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孙犁在鲁迅及其作品的引导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为人生”是他思考文学问题的出发点,他结合当时文学工作者的实际,提出作家双重身份论和文学的生活性理论,以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廓清文学与政治的边界。他认为作家的主体意识是靠作家自身深厚的生活和文艺修养来支撑的。孙犁的这些思考的目的在于捍卫作家美学追求的自由。
孙犁;作家主体意识;文学与政治关系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每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人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只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是以现代人文学观念为基础的,因此,新文学进程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解读,作家主体性总是与文学独立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强大的文学外部力量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文学,意在取消文学独立性,让文学成为其工具。文学与其外部力量的博弈,它们之间的对立、妥协,到最终清晰划分边界,构成了整个新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参与这一博弈的有政治家,有依附于政治权威的文学理论家,也有坚持文学独立性,致力于划分它们之间边界的另一类文学理论家,当然也少不了作家的参与。1930-1950年代,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正是中国政治活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孙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参加革命,开始文学活动,建立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也决定了他的文学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注定要在文学与政治的漩涡中寻找自己的文学方向。从理论上不断梳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孙犁来说,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作家双重身份论的另一种解读
抗战期间,最大的政治就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国家建构,孙犁认为作家应当“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把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文学的理想和政治的理想结合起来。把文学事业看成是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重大高尚的义务”[1]107。为此,孙犁提出:“我们强烈地主张写作和生活统一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着一个作家同时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农夫或一个战士,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希望文学和劳动再统一起来,融合起来,我们反对把写作看成特殊工作的倾向,它应该和一切生产部门结合起来,叫生产决定着创作,叫创作润洁着生产。”[1]289也就是说,在抗战的大形势下,作家应当具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家的身份,另一个是实际生活中的身份。之所以要强调这样两种身份,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写作已经不是“身边事”的写作,它需要作家主动体验自己所不熟悉或不甚熟悉的生活,以便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在这种双重身份中,“作家的身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体意识,只有和另一种生活中实际的身份相结合才能起作用,他要求作家既要以一种实际身份真切地融入生活,还必须以作家的眼光、视野审视这种生活,以便表现生活,这是和生活实际中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不同的地方。孙犁的作家双重身份论响应了当时解放区主流理论中的作家双重身份论,但他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对“作家身份”内含的理解和作家与实际身份关系的理解两个方面。
解放区文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左翼文学,一个是苏区文学。左翼文学对作家的要求同样源于对作品真实性追求。在左翼理论家们看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2]213。“愈是贯彻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的文学,就愈是有客观的真实性文学。”[2]211按照这样的逻辑,要实现政治正确的文学真实,作家首先要理解政治所追求目标的合理性,将这种合理性统一于生活,作家要亲自在生活中印证政治的正确,然后再寻找适当的文学表达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真实论基础上,周扬等左翼理论家们要求作家实际参加到政治斗争中去,在这种政治生活中体验生活并表现生活。而在苏区文学中,革命的理性是其表现的唯一内容,作家的身份是从属于他的革命者身份,作家是作为革命者而不是作为作家体现其人生价值。抗战期间的解放区文学,其主流思想将左翼文学与苏区文学观念融合在一起,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意见表达得更为明确。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所谓政治,既包括抗战,还包括“革命”,抗战是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式齿轮和螺丝钉”[3]543。要完成这样一个政治任务,作家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要将作家的思想统一到革命上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作家的双重身份论,强调的是要以革命者的身份体验生活,以革命者的眼光、视野看待生活。在作家与革命者身份之间,革命者身份是凌驾于作家身份之上的,这样“作家身份”应有的主体意识无形当中被取消了。
孙犁接受了五四新文学观念,始终认为文学是为人生的,要在文学中探讨人生的真谛,创作主体应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当中去,带着真诚的态度去经历、咀嚼、理解生活,研究现实生活里面种种具体问题,以此锻炼他敏锐的观察能力、透辟的分析能力、正确的批判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先进的世界观只有与作者生活识见相契合,才能在创作中起作用。文学的真实性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它有坚实的生活逻辑作支撑,由此形成对读者的说服力量。作者对生活的理想、对读者的激励意义都是建立在这种逻辑基础上的。但孙犁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五四作家在身边事中体验人生、探讨人生的时代,抗日战争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促使作家不只局限于表现所谓的 “身边事”,需要作家们扩大生活的范围,拓展生活的视野,主动熟悉、认识、表现新生活。在作家的双重身份中,一方面,除作家这个身份之外,孙犁强调的另一种身份是实际生活中的工人、农夫或士兵,目的在于要让作家了解社会最基层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他延续的是五四作家对大众文学的渴望。另一方面,孙犁作为抗战爆发后开始创作的根据地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就是抗日。身处解放区,他理解这场战争的人民性,文学为抗战服务,首先必须了解抗战的主力军——工人、农民及士兵,他要求作家熟悉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抗日战士以取得切身的生活体验、认知,真正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学理想。对孙犁来说,作家和他的另一种身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作家的主体意识,他就不可能有作家的视野,他所体验的生活就不能转变成文学表现的内容;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作家的主体意识就是空中楼阁,他的创作最终变成小圈子里的无病呻吟,不可能完成对这一伟大时代的表现,成为真正动人的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在那个大时代里缺一不可。
孙犁的作家双重身份论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以五四文学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为基础看待作家的生活体验问题,以文学为人生的精神强调作家融入最基层百姓生活的重要性,他和解放区主流文学对作家双重身份的理解分歧的原因在于对政治具体内容的理解和作家参与政治的方式理解上的差异。
二、“文学生活论”与政策压力的纾解
1940年代至195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一系列讨论,组织管理措施得以广泛贯彻,其思想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成为国家抒情体制的核心理论。这一时期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政策措施,当文学依附于这种政治的时候,势必要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当文学要独立的时候,政治的现实性和强势,也势必要迫使文学纳入到自己的轨道当中来,两者的界限不清使这种冲突愈演愈烈。孙犁在这一时期时刻面对的就是这种冲突,尽管他一再小心翼翼,但稍不留神也免不了被裹入到漩涡中,1946年因所谓“客里空”事件而被点名批判,1950年因发表小说《婚姻》而作自我批评,使他产生远离政治的想法。政治团体可以疏远,但政策却像魔鬼一样时刻纠缠着作家,作家创作的酝酿、构思和最终的表现,每时每刻都要考虑政策问题。孙犁为此提出“文学的生活性”问题,试图提醒作者:“有时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或是文学的艺术性,反倒把生活性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的生活经历,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生活才是创作的本钱。”[1]386在孙犁的文学观念中,“生活”有着特定的内涵:作为文学的“人生派”,孙犁始终坚持“文学是为人生”的,这种文学的“生活”是一种现实的、作家亲身体验的生活,它随作家对人生探讨的深度和广度而不断增加自己的内容,作家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入,这是“五四”的现实主义文学生活观。
政治如影随形,政策更是要求在创作中必须被表现,在这样一种文学语境中,孙犁将政治纳入到“生活”的范畴中看待。他认为,政治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要表现的不是政策的条文,而是政策对生活的影响,生活因之所起的变化。解放初期,针对工人业余作者写作中容易忽视自己的真实生活积累,创作图解政策的问题,孙犁指出:“党的政策与工人生活接触,在各方面都会引起激动,引起变化,引向前进。政策与工人生活、工作、思想的结合——这就是现实的焦点。抓取到这个焦点,才能展开生活的丰富广漠的画幅。”[4]33对作家来说,作家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了作家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这种政策下生活的体验者。“他处理着村中的当前的大事情,他的学习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他既要对政策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他慎重地思考着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情况。这样,他获得的东西就是宝贵的了。”[4]22这种宝贵的东西就是对生活的真实状况的了解和自己的真实感受,在这一过程中,作家要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视角,政策和作家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形成作家的思想。“作品的政治性就是它的思想性,应当像春雨落地一样,渗透在任务的全部行动里,贯彻在作品的全部情节里。政治性是通过生活形象表现出来的,他不限于讲话和演说。”[1]419作家的工作方法和创作方法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使作家“把自己造成一个质地优良的传声筒”,在这个意义上讲,“‘传声筒’也不是一概可以抹杀的”[5]404。
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政策只是作家探索人生、表现人生的一个视角,他不应只盯着政策带给生活的变化,只表现这一个内容,还应看到生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因此,孙犁认为,作家“对于现实的深度,挖掘得越深越好;对于现实的复杂性,表现得越完整越好。力戒削足适履,心中现存一个抽象的公式,合此公式者留之,不合此公式者删之”[5]349。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挖掘,就是对人生的深度和广度的探索,目的在于让文学告诉我们 “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坚定了我们的意志和信仰。使我们看见了近处的伙伴和远处的伙伴,不会孤独。使人们看见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感情、理想。人们从苦难里挣扎出来,创造好的生活和爱好美的东西”[1]105。对人生的深度探索和向人们展示人生的美好图景构成作家的文学理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家要完成这样一种文学理想,就需要超越政策对生活深度探求的羁绊。因此孙犁呼吁,一个作家应当在风云变幻的现实生活中,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完美地再现复杂生活,其中包含了政治生活的“风俗画”,而不能仅着眼于政策的表现,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政策宣传的“风景画”。对孙犁来说,坚持文学的生活性,就是坚持文学的理想,就是要为文学与政治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线,也要为政治与文学之间搭一道桥梁。如果让政治淹没了文学理想中作家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和独特思考,文学也就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在当时强大的政治语境中,孙犁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充满理论智慧的。
文学的生活性同样适用于批评。解放区文学发展中,批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犁曾描述过当时批评的方式:“在谈作品中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他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终于得出十分严重的结论。”[1]433“批评这个东西,在今天很难说,他常常是由”上面“来个号召,就造成了群众影响。因为写批评,就是代表工农甚至代表党来说话的,声威越大越好,叫群众服从,真正群众的意见,就湮没了”[6]8。这样一种批评风气对作者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孙犁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接触的又都是生产一线的业余作者,深知他们创作的甘苦,也知道一篇评论对他们今后的文学道路会有怎样的影响,因此,应当慎之又慎。在谈论批评之前,孙犁首先对报纸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他说,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家庭的关系,编辑对待作者的投稿,应该像对待远方的兄弟的来信一样。编辑要知道作者在这一时期生活和工作的全部情况,来研究他在文学上所达到的反映”[1]455。作为一个编辑和批评工作者,“批评之与创作的任务,主要的应该是引导、帮助和提携,对初学者尤当如此”[1]279。孙犁的这些论述,意在防止批评者对作者及作品的简单粗暴、盛气凌人式的批评。
在1930-1950年代,孙犁在创作之余,不遗余力地为不同类型的作者撰写热情洋溢的批评文章近80篇之多。在批评文章中,孙犁贯彻了他对批评的一个原则,就是从生活出发衡量作品的真实性,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判定作品。孙犁说,“我们看作品,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看,还要体味一下当时的情调,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就是要查一查”生活“这本大辞书,看究竟是不是真实,如果不这样,许多事情是无法理解的”[1]433。他对一些作品的批评至今读起来仍然叫人怦然心动。作家王林在抗战期间所写的长篇小说《腹地》,是解放区第一部直接描写边区军民抗战的长篇小说,为创作这样一部抗战纪实作品,王林每天生活在家乡抗战第一线的百姓中,与百姓一起躲避日军的清剿,和当地的抗日部队一起打游击,为此放弃了去后方的机会。但由于此作不符合当时一些批评家对抗战与革命的想象,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出版。直到1951年,才得以在天津的地方出版社出版。作为王林的战友兼同乡,孙犁以其真实的经历看到了王林作品的可贵之处,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颂:“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这里写出的情绪,我说的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苦难,也不是单纯以故事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这是雷雨交加,飞沙走石,大风暴里的不屈不挠地奋开的花香;这是生死关头,在炮火里坚定地跌倒爬起,充满胜利信心的笑语;这是空前的灾难里战斗、培养,用民族的宝贵的血泪浇灌起来的民族新生的灵魂。”[4]261孙犁以作家对创作的理解,以过来人对生活的体验,从文学的生活性出发,在政治挂帅的批评语境中,为文学批评重新作了诠释。
三、恪守作家主体意识的内在力量与作家修养论
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漩涡里,孙犁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以此显示作家的主体意识,但它们又是由其作品的独立价值支撑的,这就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修养。就生活基础问题,孙犁提出了作家双重身份论和文学的生活性理论,在艺术修养问题上,他结合当时作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至今依然有理论价值的一系列建设性的观点。
作家的思想修养问题是孙犁一直关注的问题。在解放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被看做是文艺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意见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者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7]因此,孙犁的作家修养论,首先关注作家的思想修养,在思想修养中尤其关注政治修养,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作家应当有先进的世界观,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1]541。但随着抗战文学暴露出来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孙犁毫不隐晦地指出:“一个作者,光有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如果她不常去研究现实生活里面的种种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里去锻炼他的观察能力的敏锐,分析能力的透辟,批判能力的正确,和由此而来的表现能力的坚强,那他的世界观便是一句空话。”[1]541在孙犁看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永久的艺术力量,关键在于他的现实主义修养。“对生活的观察取舍,夸张和抒情,能否有力量,都取决于作家的思想高度,在艺术作品里,作家的生活,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统一地表现着。”[1]451“思想的高度是艺术成就的重要基础,思想不只构成作品的面貌和深度,而且形成作为艺术要素的风格,就是作品的气质和灵魂。”[1]483-484因此,对于作家的思想修养,关注他的先进的理论修养和坚定的政策修养是必要的,但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应当促使作家将这样的修养内容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印证,理解,最后变成自己对生活的全新认识,形成有作家独特生活和学习印记的“识见”,这才是作家全面的思想修养内容。
孙犁同样关注作家艺术修养问题。孙犁身处解放区文学中,看到了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种种联系,将作家放在这一文学发展的链条上去讨论修养问题。他在检讨五四新文学的问题时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文学是一种启蒙文学,但它并没有走出知识界,成为大众文学。其原因在于:“新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很好学习和发扬它在语言上的优秀成果,在其他创作的手法上,则更没有主义研究发挥,例如群众的创作道路,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的编排等等。”[1]363欧化的形式广大人民还没有熟悉,“因此一时也联系不起来”[1]364。左翼文学运动以及后来的解放区文学主要就是要解决五四文学的这一问题。要完成五四新文学的这一历史使命,作家艺术修养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对待遗产的态度上:“接受遗产不只是接受中国遗产,也要接受外国遗产”,因为“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再向前发展,但也受着外国民族生活的影响。因此,接受外国的遗产(翻译、研究等),一方面是输入新内容,同时也输入了新的表现形式。这可以帮助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文学的建立”。[4]401对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两者并重,从中汲取对自己的有用的东西,解决创作中的难题,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孙犁所接触的作者中,有许多是从生产生活一线来的,对生活有一定的真情实感,但写出的作品依然显得虚假,孙犁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认为,这主要是技术上的薄弱造成的,“没有从日常的平凡的生活,看出它的意义,不能雕石塑泥,创造出生动的形象之群”[1]463。作者“没看过多少好的文艺作品,平时看的就是这些不具体、简单、公式的文章”[1]197,也就不能从作品中看到作者是如何从生活中提炼艺术元素的。因此,他希望,每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作者,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时,还要格外注意自己的作家身份,在生活中以文学的眼光看待生活,不断地锤炼自己,从生活不经意处发现诗意。“如果生活还是零乱的,日常的,琐碎的,一个作家就要在这里面看出那诗的部分,小说的部分,提出这些东西,成为反映生活的诗、小说。这些诗和小说是写实的,但它已经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一种惊异的独创和新鲜。”“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只去探询一些传奇的,不平常的事件,企图借事件来耸人听闻了。”[1]259
孙犁特别重视语言的修养,要求作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语言。他认为生活、语言和思想是文学的三要素。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孙犁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学遗产,是语言上的追求和成就。”[8]165在解放区作家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像孙犁那样重视语言。孙犁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是独特的,他认为,好的文学语言,应当是明确的、朴素的、简洁的,具有浮雕性和音乐性,并且和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这些要求,他不厌其烦地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明确的也常是朴素的,也常是简洁的,能明确也就能形象。”“我们说浮雕的语言,就是像我们以前所说,使书里的那些人物环境,不只像平面的面,而像雕刻出来,凸显出来的,就是完完全全在我们的眼前活起来了。”[1]152文学是生活、思想、语言的血肉结合,好的文学语言是不能单独获得的,这种语言的学习,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群众的语言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要想获得这样的语言,必须深入地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思考,一起处理问题。对孙犁来说,语言的修养,既是书本上学习的,又是在实践中认知的,是和作家深入生活的深度相关的,是和作家对语言与生活关系的认识相关的,也是和他对文学语言对创作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关,这决定着他对语言追求的态度、方向。语言的问题,是一个作家的身份问题,也是文学的身份问题。
四、主体意识彰显与对创作美学自由追求的捍卫
孙犁的文学启蒙有着很深的文学研究会印记,在鲁迅及其作品的引导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是为人生的”坚信不疑,这成为他思考一切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孙犁始终以一个作家的视角,站在“文学是为人生的”角度上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其目的在于捍卫作家对自己创作美学追求的自由。在孙犁早期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独立思考、他的坚持,并将自己的思考和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以创作印证自己的思考。孙犁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对创作风格的追求,对抗日主题的个人阐释,在解放区作家当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孙犁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荷花淀》《嘱咐》,还是《铁木前传》《风云初记》,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的经典,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当中是不多见的。孙犁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强调和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中对作家主体精神的强调是一致的,但他并没有像胡风那样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理论旗号,而是努力在主流的规约中寻找自己对文学的表达,以自己的理论阐释和文学创作实绩凸显文学的独立性原则,始终以作家主体视角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努力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将文学的个性表达作为作家的职责。孙犁解放区时期的创作成就,不能不说和这种文学的观念和思想表达策略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孙犁自觉在主流的规约中思考,但他的思考具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他对作家双重身份的解读,对文学的生活性的看法,对作家修养的强调,都是在为文学与政治划出清晰的边界,直到晚年,这一问题也依然是他关心的问题。对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的思考越发清晰,思想更加坚定,他说:“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受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作家的思想立场,也反映在作品里,这个就是作家的政治倾向。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是融化在艺术的感染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9]114我们可以看出,孙犁在经历了长期的困扰和思考之后,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对政治这一概念,他划分为作为理念的政治和作为政策的政治。政治和文艺发生关系的交合点是生活,或者说,必须经过作家的生活体验,完成表现形态的转化之后,它们之间的联系才能充分展现。应当指出,边界的划分就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更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自己的美学。在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中,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心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到文革时期,由文学对政治的依附而形成的文学特殊意识形态论和政治工具论是一种主流的理论;文革后,文学界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形成文学的审美论和形式本体论;再到1980年代,理论界回归理性正视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几十年的理论探讨,其目的就是对两者之间的边缘作一清晰的划分。孙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以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评论家的理论思考,对政治和文学的边缘问题进行了厘清工作,他的这些思考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孙犁以作家、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对这一问题几十年如一日地思考、探讨,其意义不仅在于和理论界共同完成了一项理论课题,还在于他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开始自觉建立自己的创作美学,不断拓展自己的思考领域,逐渐彰显出他的思想家的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使他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中明确自己的文学身份,以文学作者的身份观察、理解这个世界,坚持自己的创作美学,这是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所缺少的,也是孙犁成为文学大师的内在原因吧。
[1]孙犁.文艺学习[M]//孙犁.孙犁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 [M]//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M]//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孙犁.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孙犁.诗言志[M]//孙犁.孙犁全集: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孙犁.致康濯 [M]//孙犁全集: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N].解放日报,1943-11-08.
[8]王彬彬.孙犁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8,(1):165-172.
[9]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M]//孙犁.秀露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周亚红)
Highlighting the writ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vortex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On Sun Li’s Literary Thoughts in 1930s-50s
ZHANG Zhan-jie
(School of Arts&Communication,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Sun Li gradually established his own literary concep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Lu Xun and his works.The idea of “literature for life”is his starting point to think about literary problems.In accordance with reality of writers,Sun Li put forward the writer’s double identity and the theory of“Literature originates from life” in orderto emphasize the writer’ssubjective consciousness,maintain independence of literature,and clear up the edg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He held that the writ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elies on the writer’s own profound life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un Li’s purpose is to defend the writer’s freedom of aesthetic pursuit..
Sun Li;writ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206.7
A
1673-1972(2015)02-0062-06
2014-12-26
河北省社科规划课题“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孙犁”(HB12WX013)的阶段性成果
张占杰(1964-),男,河北衡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