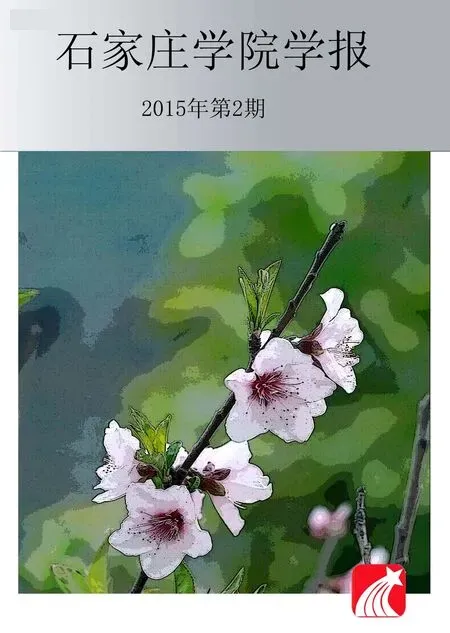国学的实证原则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国学的实证原则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国学之所以传播百世,生生不息,自有“健”的内质和“易”的精神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有些人以为陈旧的消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亦有接近现代科学的学术风格。这就是实证原则。研究和理解国学,应当注意到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实证原则。国学之所以绵延长久,并且显现出适应现代社会条件的新气象,正是因为实证原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也是符合进步趋向的。中国学术的实证传统在20世纪某些时段的“不遇”遭际,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的曲折表现,也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学术;国学;传统;实证;乾嘉学派;二重证据法
《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子夏易传》卷二《周易·上经泰传第二》:“夫易者易也,刚柔相易,运行而不殆也。”①《子夏易传》卷二《周易·上经泰传第二》又说:“阳为之主焉,阴过则阳灭,阳复则阴剥。昼复则夜往,夜至则昼往。无时而不易也。圣人是以观其变化生杀也,往而复之也,而无差焉。”国学之所以传播百世,生生不息,自有“健”的内质和“易”的精神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有些人以为陈旧的消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亦有接近现代科学的学术风格。这就是中国学人坚持不渝且百代相继的实证原则。研究和理解国学,应当注意到中国学术世代相承的实证原则。国学之所以绵延长久,并且现今又显现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气象,正是因为实证原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也是符合进步趋向的。中国学术的实证传统在20世纪某些时段的“不遇”遭际,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的曲折表现,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中国学术的实证传统
文献形式是中国学术得以传播和继承的重要条件。《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在说到前世典籍制度遗存时曾经惋叹“文献”的缺失:“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在总结《春秋》二十三家学术渊源时曾经引用此语:“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3]卷三〇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写道:“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4]卷一重视历史文化的“征”,反对“空言”,讲究“深思”,是成功学人一贯的坚定理念,长期以来成为中国学术的传统。
实证传统体现于国学创制与继承者对于重要学术对象“文献”的表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5]1220据马端临说,“文”则“叙事”,取典故史传,“献”则“论事”,取“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①有学者可能据《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解释马端临文意,以为“‘文’的意思是典籍”,“‘献’的意思是‘贤者’”。今按:以“贤者”释《文献通考》之“献”,此说似未可从。。这种“订”“得失”、“证”“是非”的工作,正是国学的任务。
《左传·文公五年》所谓“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6]卷五,如果扩展以喻学问,转“怨”之意以指示各种消极影响②[宋]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五《文公上》解释“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此句以草木譬之,华不必尽是诈伪。”,可能也是适宜的。“实”,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永久的追求。《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所谓“实事求是”[3]卷五三,明代学者张宁说:“天下之事,是非二者而已。世之为非者,固不足论,其间为是而实非,是乃自以为是而不求者多矣。观‘求是’一语,此三代圣贤之学也。”[7]卷二九清代学者何焯言:“四字是读书穷理之要。”[8]卷七均以为“实事求是”并非仅仅是技术性要求③如宋人刘跋《赵氏金石录序》所谓“别白抵捂,实事求是”,强至《谢除校勘启》所谓“实事求是,聚精□神,芟夷复重,笔削讹缪”,参见《宋文类》卷九二,卷一二二。,分别强调了此“四字”所体现的文化传统的意义和学术原则的价值。
二、清人的“实学”主张与“实学”实践
经历对明代学风的反思④明代学界空疏之风盛起,如杨慎《邵公批语》所说,甚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参见《升庵全集》卷五二。正如丁文江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所指出的“明政不纲,学风荒陋”,“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至于明末则“物极必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明清之际,高攀龙倡议:“今日虚症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参见《知及之章》,《高子遗书》卷四。,中国学术进入乾嘉时代,在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上实现了突出的进步。有学者指出,“考据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古文献学发展的高峰,而乾嘉考据学又是这座高峰的主要标志”[9]1。这是符合中国学术史研究者的共识的。因此,对于乾嘉学风进行必要的总结,有助于我们说明国学研究的学术脉络。胡适曾经说,乾嘉学者是当时“最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的 “可靠的工具只是他们的严格的方法”,“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第一流的有知识的人几乎都受了这种方法的吸引,都一生用力把这个方法应用到经书和文史研究上。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学术复兴的新时代,又叫作考据的时代”,“这种严格而有效的方法的科学性质,是最用力批评这种学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胡适甚至认为,总结他们的方法,则“足够给一个大可注意的事实做一种历史的解释”,这就是,“那些只运用‘书本、文字、文献’的大人物怎么竟能传下来一个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仅能够心安理得”⑤胡适《中国人的心灵——中国哲学与文化要义》,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转自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上册第432-433页,第436页。。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天下之学术”应具二途,即“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10]内篇六“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实“相需”而不宜“两伤”。这一见解,当然是超越了一般考据家的识见的。他又曾经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0]内篇一“六经皆器也”[10]内篇二等命题,有学者评价说,“这些是在当时被认为最放肆的学说,也是他被后人所最注意的学旨”[11]509。他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将以明其义理尔”[10]内篇四,“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10]内篇二,“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10]内篇六,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开明清醒之见。其说对于国学研究的历史总结,也有不宜忽视的意义。《文史通义》一书中,创见不可悉数,正如梁启超所说:“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12]57他强调在“学之贵于考征者”的基础上,亦应注意时代的“势”,这是非常明智的理念。
接近前引胡适 “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之说,傅斯年亦肯定清代学术“比较的近于科学”。他说:“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这种学术史的判断是发人深思的。傅斯年甚至认为:“平情而论,西洋文化进化的步次,虽然和中国的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还有近似的地方。”西洋近世科学家对中世纪的迷信“造反”,“我们中国的朴学家对着宋学开衅”。中西确实相似,“这不是我好为影响傅会的话,实在由于同出进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踪迹了”。这种比较确实可以给我们启示。傅斯年进一步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尤其值得注意:“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的Re aissance时代的学者,求的是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的真话。他未尝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万物。”傅斯年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中写道:“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2)清朝人的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代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13]傅斯年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以及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两相结合,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工作,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结清人学术风格,曹聚仁评价道:“这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又指出:“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依这一治学的方法和精神,中国的学术思想,该比欧西早一个世纪现代化了。”[14]266-269
所谓“清学”的研究方法,既然说是“科学”的,为什么又没有能够对于中国文化产生全面的影响,使其迈进科学时代呢?究其深层原因,除了前引傅斯年“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当做真理了”之说而外,梁启超又曾经有这样的分析:“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疑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12]24梁启超所论“须有相当之历史”以及“又乘特殊之机运”,是否确定符合历史真实,还可以讨论。但是他关于“考证新学派”之兴起,“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的观点,却值得学术史学者和文化史学者充分重视。
考据学起初“不过居一部分势力”,但是到了清代学术的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据学以外,殆不必置论”,于是形成了“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的形势,“故言考据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12]26。关心国学研究的学者,不能不注意这样的事实。然而,学术史发展到近代,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三、近代史学进步的双轨
史学曾经是国学的主干。讨论国学的学术史,不妨以史学作为标本。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论者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此外,“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新史学方法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使近代史学方法论发展到发展历史本质的唯物和辩证的高度”,是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15]225-253
其实,近代史学大体有两种倾向或者两种风格各自集合了数量和素质相当可观的史学人才,他们分别推出了成为史学进步之时代标志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公认为学术经典。这两种倾向或者两种风格,一种偏重于实证研究,追求历史真实的恢复;一种偏重于理论说明,追求历史规律的探求。以“方法”或“方法论体系”来概括这种倾向或风格的区别,似乎并不十分确切。实际上,两者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亦体现出文化立场、学术理念和思想风格的差异。倾重实证的史学和倾重理论的史学,其实共同承载着史学进步的车轮,也许可以看做并行的不可偏缺的双轨。
梁启超所总结清人学术研究的10种特色,大致可以看做倾重实证的学术家坚守的原则:(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则以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12]24
我们在回顾中国近代史学史时确实可以看到,史学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政治因素而明显扭曲,其学术成果往往可以经受较为长久的品质考验。
四、时代冷遇:实证之学20世纪的命运
史学的实证研究,作为继承了考据学传统、又借用近代科学方法,以追求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为主要目的的史学方向,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之中,在特殊社会文化风潮的影响下曾经遭遇鄙弃和批判。《艺文类聚》卷三〇有董仲舒《士不遇赋》及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不遇”的反义词是“见亲”。①《宋史》卷四〇九《张忠恕传》:“迩来取人,以名节为矫激,以忠谠为迂疏,以介洁为不通,以宽厚为无用,以趣办为强敏,以拱黙为靖共,以迎合为适时,以操切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见亲。”实证学风在20世纪即经历了“不遇”的遭际。
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的序中写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6]7在革命精神成为社会意识主流的20世纪,史学的实证研究因研究形式的传统以及与社会潮流的疏远,其“盛衰”与“升降”是有目共睹的。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界先进分子注视的焦点,多集中于社会变革的方向,而西方各种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学界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时对于旧学的态度,有忽视乃至厌弃的倾向。当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的主要趋势,是胡适所批评的“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②《〈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参见《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0页。。被郭沫若称为“新史学阵营”里面的激进的学者们,对于传统的研究方向,大多是持鄙夷甚至批判的态度的。
郭沫若1929年9月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17]10然而持这种轻视实证态度的史学研究,却可能导致误解和误用材料的偏差。郭沫若这部对“谈‘国故’的夫子们”有所嘲讽的著作,果然出现了这种性质的失误。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和评断的:“谁都知道,古史分期研究中的一个突出困难就是材料问题。仅有的一点材料,时代浑沌,真伪难分。郭沫若早期从事古代研究之所以产生某些重大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先秦的某些文献的考订重视不够。”[18]77有的学者又指出:“文献考辨是历史考据的首要工作,也是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研究历史的必要前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出现若干重要的失误,与他对一些历史文献的时代性判断错误有关。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首先检讨了自己这方面的毛病。他深有体会地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9]204这种认识之深沉的涵义,我们应当认真理解。
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实证研究由于与现实政治斗争存在距离,容易为激进的革命力量所轻视。以实证研究为主要学术方向的学者,也长期受到批评。
批判者指责道:“胡适正是引导青年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钻进故纸堆中,埋头于一字一义,相信什么 ‘一个字古义的发明和发现一颗恒星同样重要’。”“胡适承继了满清封建统治者的故技,把青年们引进故纸堆和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上去,使他们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①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参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5年4月版,第113-114页。批判者认为,所谓“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在思想上,它引导人们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抗革命;在实践上,它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钻牛角尖。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古典文艺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用处。至多只能解决些枝枝节节的芝麻般的小问题,而它的危害性却很大”②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参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3辑,三联书店1955年4月版,第257页。。有人如此批评在胡适学术影响下形成的学风,“我们的一些考据学家,他们的眼界实在很狭隘。他们的研究领域也不宽广”,他们“只是以资料证资料,埋头故纸堆中去钞录,于是就闹出种种笑话,牛角尖愈钻愈深了”③陈炜谟《论考据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兼评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考据学及其毒害》,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参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8辑,三联书店1956年4月版,第140页。。于是,“故纸堆”“牛角尖”等成为实证研究之消极意义的代表性符号。
对于时人所谓在“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时“没有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的批评,顾颉刚曾经不得不作出如下的回答:“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20]22-23
实证研究在20世纪的后50年所受到的严重压抑,导致史学界所谓“以论代史”的风气曾经形成很不好的影响。1958年至1959年,甚至北京大学历史系也组织编写过 “东抄西抄,再加上一些空洞的说理”的“跃进本”中国通史教材。“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反科学的狂热有所冷却,但是历史学科的青年学人对于史料的重新重视,又被指责为“对马列主义的兴趣又降了下来,想多捞点资料,认为只有资料才是‘老本钱’”而受到鄙薄和批判。[21]338,435在这样的气氛中,史学实证研究发展的阻障可以想见。而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学者于相应时期在这一方面的艰苦的学术努力更值得敬重,他们在学术史的这一非常阶段所取得的学术创获有更多的学术含金量。
五、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实证之学在20世纪是实现了新的进步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设《古史新证》演讲课。在此之前,他已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毛公鼎考释》等著名论文发表,《古史新证》可以看做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新的学术阶梯。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2]《古史新证》一书,就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实践。如以甲骨文资料证明《史记·殷本记》所载商王世系确为实录,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以探索古代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一种公认科学可靠的学术正流。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否定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王国维的学术榜样,对于此后的国学研究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学界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也与王国维所开创的学风有关。今后任何一种论及20世纪的严肃的学术史、学术思想史、学术方法史,都不会忽略王国维提出的这一学术方向的科学价值。
1934年,陈寅恪曾经这样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学术风格的特征:“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这一学术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23]219。“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以及“外来之观念”得到重视并加以利用,体现出20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性超越。陈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说法,是对于国学研究利用考古学资料所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和影响的客观总结与热情肯定。
在“二重证据法”为学界普遍应用取得颇多收获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对于所谓“三重证据法”,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李学勤在一次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中,谈到“两种考古证据”。他说:“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考古发现的没有字的东西,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24]3-5
有的学者提出过另一种“三重证据法”,即在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同时,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叶舒宪最早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还指出:“超越二重证据的研究实践在建国以前的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大笔丰硕成果。”一些历史文献研究学者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在这一方向已经踏出了新路。叶舒宪说,“假如把王氏的《观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25]稍加对照,从‘二重’到‘三重’的演进轨迹也就一目了然了。”郭沫若在这部书的《序录》中所列出的14种主要参考书中,“除前9种为甲金文专著外,后5种却都是域外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叶列妙士的《古代东方精神文化纲要》、威德讷尔的《巴比伦天文学概览》第1卷等。这些外文文献说明郭沫若已在尝试某种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思路,而他所倚重的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是人类学史的经典文献。可以说从‘二重证据’到‘三重证据’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据学、甲骨学同人类学相沟通、相结合的结果。”其他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成就突出的名家名作,叶舒宪又举出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26]3-34等。“从神话学出发研究古史,有卫聚贤《古史研究》(1936)、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3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等著作问世,从神话学出发研究文学则以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和郑振铎《汤祷篇》最为突出。所有这些尝试,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就在于将民俗和神话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经史文献和地下材料并重的高度,获得三重论证的考据学新格局。”鲁迅1926年在中山大学讲中国文学史的讲义中的一段话:“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浸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淳朴,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矣。”[27]343叶舒宪亦解释为“运用了关于原始社会方面的第三重证据去分析和解决古书上聚讼不清的问题——诗之起源”,“鲁迅的这一辨析虽嫌简略了一些,但他的论证方式却已超出了考据学的封闭视野,多少具有了人类学的性质,其意义和影响均不容低估。”在鲁迅发表这一看法16年之后,朱光潜又提出了融贯中西的诗歌发生论,他批评了“以为在最古的书籍里寻出几首诗歌,就算寻出诗的起源了”的思路,指出,荷马史诗是希腊最早记录下的诗,其原始程度却不如非洲土著的歌谣,“所以我们研究诗的起源,与其拿荷马史诗或《商颂》《周颂》作根据,倒不如拿现代未开化民族……的歌谣作根据”[28]2-4。叶舒宪提出,国学的进步,应当“借鉴我们自己传统中缺如的世界性通观视野和人类学方法”。他确信,“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放置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加以探讨,这将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一种融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①本段中叶舒宪的言论均出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的《自序: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这样的认识,值得学界重视。
六、乐观的前景与学术隐患
在20世纪的最后十数年至21世纪的最初十数年,国学的自立意识逐渐上扬。国学的学术自立表现为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已经为多数学者从内心摒弃,学术实际上成为政治的附庸,已经被看做一种非正常的非科学的现象。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也有助于唤醒国学学者追求真正的学术创造和学术发展的意志。
于是,国学实证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条件。在20世纪实证研究遭遇鄙薄和批判的另一面,我们还看到时代赋予的宠惠,这就是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发表。对于这一情形,在21世纪可以有更乐观的期待。
推想21世纪学术实证研究的发展,学界自然会因更多考古新资料的面世而预见到光明的前景。从现今学术发展的势头看,简帛研究所具有的潜力未可估量,其可能发生的学术影响力也未可估量。
传统学术实证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也将实现新的历史性的进步。20世纪后期的有关研究已经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例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对于秦始皇陵的结构有这样的记述:“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4]卷六对于这样的记载,人们以往只能半信半疑。但是,由于汞及其化合物的扩散、迁移能力极强,它们可以从深部的矿床及邻近围岩中主要以气体状态向地表迁移,并以气体状态保留在土壤间隙中,或者被固着在土壤颗粒上,这样就在深部埋藏矿床的上方地表形成汞的异常。另外,汞在土壤中的迁移有“各向异性”的特点,即在垂直方向上扩散较大而侧向扩散较小。在具备了这样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考古学者和地质学者用新的地球化学探矿方法——汞量测量技术测定地下汞含量,在秦始皇陵墓封土表层发现了很强的汞异常,面积达12 000平方米,据考古钻探的资料,该异常恰好位于秦始皇陵的内城中央。这证明了《史记》中关于秦始皇陵中曾经大量埋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29]这样的工作收获在21世纪初又有新的资料发表。[30]26,58至于古代生态史研究不能不利用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有关成果,更是众所周知的。
21世纪的国学实证研究,很有可能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若干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取得突出的进展。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是可以直接对实证研究有所助益的。
实际上,现在很难预料,在未来的100年中,国学将会出现何等的新新国学家和新新国学流派,他们在理论上的标新立异和方法上的标新立异,将会给国学实证研究带来怎样别开生面的历史性的推进。
在政治生活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限制已经逐渐淡薄的另一面①还应当指出,现在有一种力量似乎要再次掀起政治干预学术、政治折腾学术的恶潮。这不能不让我们心存警惕。,经济生活那看不见的手对国学研究的干扰却愈益显著。在经济力量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以史学为例,近30年面世的史学论著中,可以看到不乏次质、劣质的出版物夹杂其中,形成恶性泡沫。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者,也常常不得不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较低层次的写作。于是从总体上说,造成了社会学术实力的某种浪费。就某一学术层次、某一学术方面来说,因此导致的学术水准的局部退化是有可能的。而通常以为用力甚多而收益甚微的实证研究或可首当其冲。某些传统学科因价值取向的影响导致人才转业使得学术力量削弱甚至学术绪统断绝,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于国学实证研究的影响可能也是灾难性的。在学科专业愈益精细的趋势下,未来学人才识的偏畸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1]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徐光烈.文献通考 [M]//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6]吕祖谦.左氏传续说[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7]张宁.方洲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75年(1986年).
[8]何焯.义门读书记[O].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
[9]孙钦善:《乾嘉考据学研究》序一[M]//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M]//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3]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M]//新潮:1卷4号.上海:上海书店,1986.
[14]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5]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3.
[1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8]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9]林甘泉.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的史学思想[M]//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20]古史辨第四册顾序[M]//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张传玺.翦伯赞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25]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26]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8]朱光潜.诗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9]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 [J].考古,1983,(7):659-663.
[30]刘士毅.秦始皇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 [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程铁标)
The Positive Principle of 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Guo Xue(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has spread and multiplied in an endless succession in that it abounds with“jian”(vigor)and“yi”(change),which exert a major effect.Althoug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utmoded and passive in some aspects,it is close to academic style of modern science,thus it is regarded as positive principle.To comprehend and study Guo Xue,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positive principle,which has been kept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 reason why Guo Xue is so continuous and unbroken and presents a new atmosphere under the modern social conditions is that Guo Xue accords with scientific spirit as well as trend of progress.The positive tradition of Chinese academics confronted difficulties,but those complications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call for deep thoughts.
Chinese academics;Guo Xue;tradition;positivism;Qianlong-Jiaqing school;dual evidence
K061
A
1673-1972(2015)02-0015-08
2014-12-10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