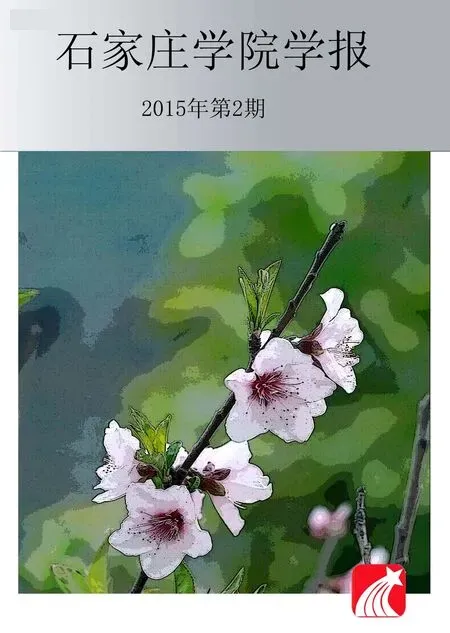从《滦阳录》看柳得恭多重文化心态
刘清涛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从《滦阳录》看柳得恭多重文化心态
刘清涛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滦阳录》是朝鲜实学学者柳得恭所写的一部使清日记,具有很强的史料和思想价值。《滦阳录》不仅客观呈现了中国乾嘉时期的社会图景,同时也深刻表现了柳得恭复杂多重的文化心态。柳得恭文化心态在《滦阳录》中主要表现为:理智的“北学”心态、“小中华”的民族自傲心态和“崇儒抑佛”心态。
《滦阳录》;柳得恭;文化心态
《滦阳录》是朝鲜李朝正祖时期柳得恭所写的一部使清日记。柳得恭(1748-1807年),字惠风,一字惠甫,号冷斋、冷庵、歌商楼、古芸堂。他10岁入朝鲜实学派大师朴趾源门下学习,是著名的“北学派”实学学者。柳得恭曾三次出使中国,《滦阳录》是柳得恭1790年为祝贺乾隆80寿诞第二次出使中国时所写。整部作品以49首纪行诗的方式进行串联,详细记述了赴热河沿途的地理情况、风土人情、人物见闻,以及与清朝士人之间的交游情况。《滦阳录》在很大程度上对清乾隆后期中国社会状况作了一个详细的记录,以一个域外文人的眼光客观地再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图景,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但作为文人著作,《滦阳录》也深刻反映了创作者本人的文化态度及其复杂的文化心理。
一、理智的“北学”心态
首先,作为“北学派”实学思想家,柳得恭对中国是心向往之的。在朝鲜文人看来,能够出使中国是他们的“梦想”。柳得恭《热河纪行诗题跋》中写道:
我东人无从至热河。庚子使臣则至矣。而自燕京出古北口。复从古北口入而止矣。考之前史。高句丽将葛庐孟光。迎燕王冯弘至龙城。命军士脱弊袴。取燕武库精伏给之。大掠城中而归。龙城者今朝阳县也。朝阳以西建昌平泉等地。孟光之所未至也。余是行自辽野之白台。径涉奚地。游避暑山庄。入古北口出山海关而归。闾山在一周之中。长城历万里之半。可谓未曾有也。[1]
从这段话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柳得恭对此次出使清朝的功绩颇为自得。因为对当时的朝鲜人来说,出使中国是切实学习中国先进的精神文化和器物文化的一个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这些朝鲜使者在使燕的过程中,把在中国见到的一切都详细记录下来,他们像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婴儿一样渴求知识、渴求发展。柳得恭作为这些使燕使者中的一员,抱有这种“北学”心态是自然的。
所谓“北学”即北学于中国。早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李朝的社会生产在多次战乱的影响下受到了严重破坏: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党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状况下,“清代的思想与学术,以及传入中国的欧洲文明……尤其是清代的思想与学术对李朝实学的产生与发展”[2]285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朝鲜由此产生了以“利用厚生”为主的“北学派”实学思想。“北学派”思想家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金正喜等人在出使清朝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偏见与不足,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自己对朝鲜发展的学术见解。如北学先驱洪大容就在游记中大量、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的强大、繁荣、文明,以及对清朝统治者的真实看法:“康熙皇帝,我东亦称以英杰之君,此一事亦历朝之所不及。”[3]184而在“北学派”思想产生之前,朝鲜国内一直怀有清朝是夷狄之国的文化偏见。“北学派”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描写无疑是对这一看法的反驳。它打破了长久以来朝鲜国内对清朝的盲视,以及由于闭关排外而产生的对清朝社会的虚假认识,为朝鲜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朝鲜有识之士开始渐渐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以期实现朝鲜王朝的持续发展。“北学派”实学大师朴趾源曾提出过“师夷之计以制夷”的对清观:
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3]228
柳得恭作为朝鲜“北学派”的一员,同样抱有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在《滦阳录》中,他描写了清朝统治下繁华的城市景观。《平泉州》中他作诗写道:“九边风雨百年空,河朔商车处处通。口外繁华君听取,垂杨十里市楼红。”[1]这里记录了连接口外和热河的边塞要道平泉州的热闹景象,同时在诗注中他详细地描写道:
七月十四日到平泉州,热河渐近,人物殷庶,市肆繁华,甲于口外蒙古部落,男女僧尼往热河叩头而归者,繦续不绝于道。[4]202
而热河的繁华景象更是令柳得恭印象深刻:
五十余年民物渐殷,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闾栉比、吹弹之声彻宵不休。康熙时万家,今不啻数倍。不待远方之兵,而六七万甲卒可以立办。富矣,庶矣。[4]203
作者不仅描绘了热河的繁华,而且对热河作为军事要地的重要性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窃观热河形胜,山河周匝,野衍而泉,驶风气高凉,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今皇帝即位以来,继志述事,肯堂肯构即在于此。[4]245
很多来清的朝鲜使臣都对中国的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视,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朝鲜与中国处于一种边境邻国的关系,中国稳定与否对朝鲜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作为藩属国的朝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所以,使臣在出使途中可以通过对中国边境军事策略的了解进行学习和借鉴。热河的地理重要性早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就被提到过:
大抵天子近北居住,数出巡猎,则诸胡虏不敢南下放牧。故天子往还常以草之青枯为期,所以名避暑者此也。诸臣常得驰马奏事,视漠北如门庭,身不离鞍,此圣人安不忘危之意云。[3]214
从中可见,这些朝鲜使臣是“体会到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而对蒙古、西藏等地所费的一片苦心”[3]214。
其次,作为一名有思想的学者,柳得恭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中国,而是以理智的眼光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缺陷和不足。
自乾隆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国家内部官吏贪污腐败之风骤长,上至朝廷公卿贵胄下至地方官吏,严重地侵蚀着清朝朝政。柳得恭以一个外国使臣的眼光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客观的描写和揭露。在《圆明园扮戏》一节中柳得恭描写了乾隆万寿节时铺张的情况:
皇帝万寿节,各省督抚献结彩、银屡锯万两。和中堂珅主管料办,内务府笔帖式言之,如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内务府奏之,皇帝初批不必,再奏以出于诚心,批。[4]205
铺张的程度可见一斑。但这些银两自然不是官吏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靠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底层人民的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同时,柳得恭还以旁观的角度对独揽大权的和珅进行了详细描写:
和珅权倾天下,带衔经筵讲官、御前大臣、太子太保、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提举阁事,管理吏部、户部、理藩院,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教习庶吉士,管理上驷院,武备院、御船处、乡道处事务,正白旗满洲都统,总理建锐营,圆明园八旗,内府三旗官兵大臣,步军统领、三府等忠襄伯悉兼枢要。满洲之俗,贵贱等威不甚分明,而望见和珅坐者皆起立,他大臣则未必然,威已立矣。”[4]229和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朝中大权,朝中大臣几乎人人惧怕。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这种朝臣控制朝政的局面无疑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和珅俨然是一个代天子行令的实际君王,《滦阳录》中这样写道:
和珅之子驸马丰伸殷德,亦美少年,于宴班走来问余曰:“本国有戏无戏?”答以:“有。”后问:“与中国同不同?好不好?”余答以:“有同,有不同;有好,有不好。”则笑而走去,似是皇帝使问于我使也。[4]230
权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极大地扰乱了纲纪,一些看来不合理甚至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朝政的腐败中亦能成为现实。《滦阳录》中记录了安南王阮光平之事:
阮光平,初名惠,安南世族也。乾隆五十四年,举兵叛,攻陷国都。安南王败、死,世子黎维祈与其母逃至广西,请救。皇帝遣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孙士毅、将兵討光平,光平败走。……维祈嗣立,请还师,皇帝从之。光平复攻维祈,缘何事皇帝封光平为安南王,召维祈拜为参领,三品武职也。[4]209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广西保险业创新路径 ………………………………………………………………… 吴望春 李春华(5/44)
本为叛贼的阮光平最后却名正言顺地被封为王,这在朝鲜使者眼中是不可思议的。朝政腐败至此,着实令朝鲜使臣咋舌。
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对汉族知识分子实施文化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这是加强思想和文化控制的一种反动措施。为了防止知识分子的反抗,清统治者从文人书籍中搜罗字句,罗织罪名,造成了大批冤案。这一反动的文化钳制措施自顺治时期就已开始,经过康雍乾共四朝,长达百年。而且在雍正和乾隆年间是“文字狱”最盛的时期,这致使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在言行举止、著书写作的过程中都谨小慎微,生怕一个不慎就招致杀身之祸。柳得恭对汉族知识分子这种被动的文化处境进行了深刻描写。在《滦阳录·李墨庄凫塘二太史》中“墨庄曾寄《洌上诸子诗》云:‘自从别后废吟哦,洌上周旋近若何?几度梦游沧海上,醒来犹自怯风波。’汉学士之忧畏如此”[4]228。柳得恭在此对文人士大夫害怕被迫害的忧惧心理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这些文人士大夫们不仅在诗作、文章的创作上谨小慎微,而且在与外国使节的交往上也是小心谨慎的,生怕被满清统治阶级抓住什么把柄。潘庭筠是陕西道观察御史,他与柳得恭神交已久,互相之间多有书信往来,但从未真正见面。但是在这次参加乾隆万寿节的8月13号这一天,“太和殿宴礼与之相逢于午门前,引席并坐,谈笑叙旧。满洲人来,乩作初逢高丽人,问姓、问名状,其实非冷人也”[4]230。本是神交已久的旧相识,却要在满族统治者面前做戏,装作不认识,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处境可见一斑。
二、“小中华”的民族自傲心态
朝鲜历史悠久,早在70万年前半岛就有人类居住。而且由于朝鲜与中国一衣带水,所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早在箕子朝鲜时期,中国的文化就已经传入朝鲜。据《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带领5 000人到朝鲜,他们中有懂得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和百工技艺的人物,他们的到来把先进的中国农耕文化引入了朝鲜,同时还推广了殷商的“七十而助”的井田制,制订了“犯禁八条”。这标志着朝鲜早在箕子时期就已经进入了有成文法的时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朝两国之间在不断的交融、摩擦和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互通。朝鲜从各个方面接受了中国的封建文明。可以说,朝鲜是接受中国文化最全面也最彻底的一个域外国家,因而长期以来,朝鲜都以“小中华”自居。而中华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先进文化,所以“小中华”的称谓带给朝鲜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认同感。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再加之传统儒家“夷狄观”的影响,使得朝鲜在对待其他番邦少数民族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傲心态。而这种心态在柳得恭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在《滦阳录》中,柳得恭描写了很多来为乾隆贺寿的边疆王爷和番邦使者,在对这些人的描写中,时时能看到柳得恭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轻蔑心态。如在《南掌使者》一节中这样写道:
余见蒙古王一人踞炕上,俯视南掌人而微笑,南掌人以狼眼仰视。一则有铁马踏蹴之状,一则有深箦中放毒箭之状,南蛮北狄相遇可笑也。南掌人甚毒。古北口南天门上,我国马头一人偶唾城下,南掌人适过,中其面,发怒,脱衣仰视喃喃其来热河也。礼部处之文庙之彝……忽見南掌一人裸体、跣足、被发蒙班布被,贸贸然在殿内行可骇也。[4]210
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卷六《王者不臣》一节中说:“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仪所能化,故不臣也。”[5]1表现出对夷狄的鄙视。这种传统的儒家“夷狄”观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一种民族固定心理。柳得恭在讲述南掌使者和蒙古王爷的时候称他们为“南蛮北狄”,足见柳得恭对他们的文化轻视。同时在后文中,柳得恭又对南掌使者“裸体、跣足、被发蒙班布被”的风俗不屑一顾,认为这样在殿内行走有伤风化——“贸贸然在殿内行可骇也”。而且从主观上,柳得恭认为这样的“南蛮”由于文化上的落后,人自然也是不够仁厚的,所以才会发生“我国马头一人偶唾城下,南掌人适过,中其面,发怒,脱衣仰视喃喃其来热河也”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柳得恭的这种民族自傲心态在《台湾生番》这一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里,柳得恭甚至不再称其为“使者”,而是直接称为“生番”:
台湾生番凡十人。乾隆五十二年讨林爽文之乱,爽文兵败入内山,生番等缚而献之,有功。……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幂不献琛,独东番远避,和恶之,家遗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坠数枚曰:“此祖宗所遗俗”,不食鸡雉但取其毛以为饰。今见其人,果悬铜铃插鸡羽。[4]211
对台湾打扮习俗的叙述,虽属客观,但从中却可以感受到柳得恭潜意识中对这种文化习俗的不以为然。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柳得恭所处的文化优越性所决定的。柳得恭在《滦阳录》中还着重写到了蒙古对清朝的威胁:
余尝问于口外居民曰:“而不怕蒙古乎?”曰:“不怕。”余曰:“何故其人作打之、缚之之狀,曰不怕。”不怕盖蒙古之俗犷猂无耻,二十五部今虽归顺,尚有剽窃之患。[4]197
蒙古人在柳得恭的眼中是“老者沉雄如虎,少者俊爽如鹰。当今之世,为满洲深忧远虑非蒙古而谁也。皇帝每年一至热河,抚摸之弹压之乌可已乎?”[4]207
对蒙古的野心,柳得恭深表忧虑,他甚至觉得满清对蒙古过于优渥而不知其野心,在《蒙古诸王》中柳得恭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老王指一少年王曰:“此王能画。”余曰:“明日持东扇來,王其为我画之乎?”少年王曰:“是也。”其翌日,余与次修各持一扇请之,则掉头曰:“不能。颇可讶。”后日达尔汗王来言曰:“君知不画之意乎?其日满洲王在座故然耳。”[4]207这里把蒙古在清朝统治者面前假装 “训顺”,背后却暗藏机心的行为揭露得淋漓尽致。
柳得恭对蒙古的提防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高丽时期朝鲜作为蒙古的藩属国,长期以来被元朝控制,没有政治主权。为了控制高丽,蒙古对高丽进行所谓的“联姻”,高丽国王成为元朝的“驸马国王”,并在成婚之前,往往以“质子”的身份被羁留在元大都。与蒙古公主成婚后,蒙古的公主可以处理各类朝政,高丽国王根本没有政治决定权。所以,元朝时期蒙古对高丽的政治控制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这一历史阴影如影相随地影响了文人士子的文化心理。所以,虽然清朝也是所谓的“夷族”——满族统治,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朝鲜采取了较为柔软的“怀柔”政策,加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繁荣富足,所以朝鲜也渐渐愿意向中国学习,这就使得朝鲜对清朝的态度与对蒙古的态度又有所不同。朝鲜虽然还是清朝的藩属国,但国家政治清朝政府基本不过问,朝鲜在国家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且比之以前历代,清廷非常重视和朝鲜的关系,往往给予朝鲜使臣最高规格的礼遇。从赐宴的次数和规格上来看,凡朝鲜国贡使赐宴四次:
至东京宴一次,至盛京在礼部宴一次,在使馆宴一次,回至东京宴一次。如朝鲜王子来朝,则有特别优待,至凤凰城宴一次,至东京遣侍郎往迎宴一次,进盛京后在礼部宴一次,朝见毕,在内宴一次,以大学士陪宴,诸王府按旗各宴一次,回日筵宴再一次。[6]11947
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其他国家的使臣是难以享受得到的。所以满清和蒙古虽同是“夷狄”,但因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朝鲜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对满清统治者,朝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对于蒙古则始终是厌恶的,甚至是具有一种时时警惕的提防之心。
除了以上的历史原因外,柳得恭对蒙古敌视、提防的态度主要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固有观念,即始终把蒙古看成是与文明相对的“野蛮”民族,是文化上未开化的“夷狄”。而中华文化的先进发达,只能由先进的汉民族来领导才行,处于文化劣势的民族是没有治理资格的。柳得恭大体上是从文化优劣性角度来衡量蒙古的,所以,他始终认为蒙古是北方的“夷狄”,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态度,柳得恭对蒙古才表现出极大的排斥性。
三、“崇儒抑佛”的文化心态
李朝的开国功勋大多是儒士出身,所以在李朝初年,太祖采纳了儒臣们的建议,“一反新罗、高丽尊佛政策,实行尊儒排佛政策”[2]285。在哲学思想上,李朝仍然承袭了高丽末期便已传入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这种哲学思想依然是以最基本的儒家思想为依托的。所以在李氏朝鲜时期儒家思想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佛教思想则遭到了极力的限制与压抑。李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抑制佛教:世宗时期(1419-1450年),将佛教合并为禅、教二宗;成宗时期(1470-1494年),废除度牒法,禁绝人们出家;燕山君时期 (1495-1506年),废除寺院,没收寺田;中宗时期(1506-1544年),取消僧科。由此佛教日趋衰落,儒教日兴。
柳得恭作为正统的儒家士子,处于李朝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然在思想上也是“崇儒抑佛”的。在《滦阳录·夜不收》一节中,柳得恭对当时中国颇为盛行的喇嘛教颇多微词,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的漫画式描写上:
行到蟒牛营又有福宁寺,见一老僧状貌丑怪,披黄衣在甓厅中负壁而坐,左右各六僧列坐念咒,其声极可笑,如众蝦蟆唱诺,鸣吻咆哮流汗淋漓,方其唇焦之時,一僧雏持椀水泼之,而过诸僧以次伸指蘸水涂唇。念讫,击鼓、吹螺、鸣铮,绕殿三匝而止,云:“是西藏僧,为皇上祈福每日如此。 ”[4]201
喇嘛僧的念经行为在柳得恭的眼中是极其可笑的,对喇嘛僧的这种描写表现了柳得恭对佛教的厌恶心理。其实这种心理在朝鲜使臣中是普遍存在的,朴趾源曾斥喇嘛教为“缁黄之流”。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记载了朝鲜使团不愿拜见班禅一事:“使臣虽勉强就见,内怀不平,任译则恐生事,以急急弥缝为幸;下隶则莫不心诛番僧,诽谤皇帝。”[3]217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五常,而其中“信”即指“不妄言”,同时孔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即不讲一些不着边际的神鬼之事。这些儒家学说的主张深刻地渗透在儒家士子柳得恭的身上,使其对喇嘛教的一些言行提出了批判:
余问其老僧曰:“西藏距此几里?”答曰:“六万里。”又问曰:“班禅额尔德尼喇嘛今又投胎夺舍否?”答曰:“是也,如今九岁。”按藏僧自古称有异术。……我国使臣亦见其体相,绝大面黄金色,后闻发痘死,番人最畏痘,已出痘曰:生身,生身不敢入内地。然则班禅者,一凡常之番人有何投胎夺舍之异术哉?西北诸番崇奉黄教,故中国因其俗而抚之,其徒敢为妄言不足信,西藏距此又非六万里之远也。[4]201
柳得恭此处所指乾隆庚子时期朝鲜使臣见班禅一事,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扎什伦布寺》中均有记载:
皇帝放梅花炮于苑中,召使臣入见……时班禅独先至,坐榻上。一品辅国公辈及廷绅显贵者,多趋至榻下,脱帽叩头。班禅则亲手为一摩顶,则起出,向人举有荣色。[3]216
在柳得恭看来,清朝如此重视藏传佛教主要是因此教在蒙藏诸番极为盛行,为了更好地控制关外诸番而利用这种宗教而已。柳得恭对喇嘛教所谓的班禅能转世投胎之说颇不以为然,同时对喇嘛僧夸说西藏距中原六万里也十分反感,称其为“妄言不足信”。柳得恭对喇嘛教的种种看法固然与其对这一宗教文化不甚了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朝 “崇儒抑佛”文化心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看法。
综上可见,《滦阳录》作为柳得恭使清记忆的一部分,不仅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乾嘉社会场景;同时,使清文人复杂文化心态的呈示也为后人对历史上中朝文化关系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因而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1][朝]柳得恭﹒冷斋集[EN/OL]﹒[2015-01-20]﹒http://db.itkc. or.kr/index.jsp?bizName=MM﹒
[2]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3]陈尚胜﹒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4][朝]柳得恭﹒滦阳录[M]﹒沈阳:辽海书社,1934﹒
[5]班固﹒白虎通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O]﹒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责任编辑 周亚红)
On Multiple Cultural Mentality of Liu Degong from The Record of Luanyang
LIU Qing-tao
(School of Arts,Baicheng Normal University,Baicheng,Jilin 137000,China)
The Record of Luanyang is a diary about the mission of the Qing Dynasty written by Liu Degong,a scholar of practical learning in ancient Korea.It has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and ideology.It not only presents the objective pictur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Emperor Jiaqing but also deeply expresses multiple cultural mentality of Liu Degong.Liu Degong’s cultural mental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diary in the mentality of sanely learning from others,mentality of self-respect for national culture,and mentality of esteeming Confucianism and suppressing Buddhism.
The Record of Luanyang;Liu Degong;cultural mentality
I106.6;K312
A
1673-1972(2015)02-0052-05
2015-03-12
刘清涛(1976-),女,吉林梨树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朝鲜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