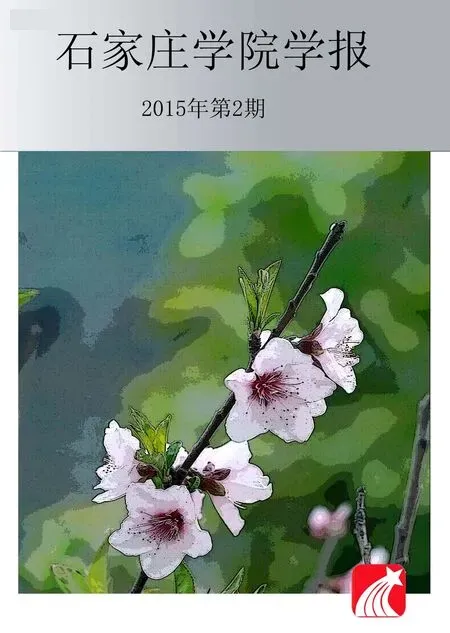沥血的乡村经验与素朴的乡土叙事
——《赤驴》阅读印象
杨红莉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沥血的乡村经验与素朴的乡土叙事
——《赤驴》阅读印象
杨红莉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赤驴》以素朴的表达方式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60-70年代乡村社会的赤贫状态,准确地描摹出特殊时期人性被摧残、被磨蚀及其挣扎的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地表达了极左政治所带来的愚昧与荒诞,是新时期以来书写文革的极有深度与厚度的一部作品集。
老奎;《赤驴》;小说;人性
老奎的中短篇小说集《赤驴》①老奎,本名王嘉波,河北井陉人,1960年出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后离教从政,历任团县委书记、县体改办主任、县建设局党委书记、供热公司总经理等职。2014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赤驴》。文中所引小说中的内容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标注。是一个独特和深刻的文本,它用极其素朴的表达方式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60-70年代乡村社会的赤贫状态,准确地描摹出那个特殊时期人性被摧残、被磨蚀及人性抗争、挣扎的过程,深刻地表达了极左政治所带来的愚昧与荒诞。阅读这部小说,能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曾经熟悉的特殊时代,思考“赤”与“贫”之间密切而缠绕的关系,也让我们再次反思极端政治对人的戕害,感怀人性可能的高度与温度。其中的几篇作品,如《赤驴》《半块字典》《胡全奎当官》等,更是富有强大的文学艺术魅力。
一、“赤”与“贫”的胶着及人的“兽化”
中篇小说《赤驴》写的是光棍儿王吉合从人被催逼到“驴”的过程。王吉合是赤贫阶层的一个光棍儿,也是生产队里的一个红色饲养员,他用全部的赤胆忠心喂养着生产队的驴,也掌握着喂驴的粮食、饲料,做着集体的保管员。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生理的欲望尽管已然在他的内心蓬勃燃烧,但如果没有机缘,王吉合最终会成为最合乎那个时代所召唤的人物:为了大家舍弃小家,只有集体观念没有个人观念,集体的驴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但是,富农王大门的老婆小凤英为了多得一点粮食勾引了王吉合,让这个四十多岁的光棍儿汉知道了男女之乐,从而引发了作为红色饲养员和男人双重身份的纠结。“红色饲养员/光棍儿”,这双重身份在他身上交集并构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他的生命与命运向矛盾悖反的两个方向不断延展伸张。
故事的矛盾开始了:作为有着正常生理欲求的王吉合,觉得理所当然应当对小凤英有所回报,对她的要求应当满足;作为红色饲养员的王吉合,似乎也应该守住所谓集体的财产。小说的魅力也恰恰由矛盾处逐渐生成:王吉合偏偏既需要小凤英的身体,也要尽可能守住集体的财产、驴的口粮。于是,行男女之事时数数儿就成了王吉合调和平衡的方式,“多数了五下,少抓了两把”,既安抚了小凤英,也安抚了驴,王吉合尽管内心纠结,但似乎也只能在这样一种两厢欺骗或者两厢抚慰中暂时求得平衡。
但是,继续发掘王吉合的内心,我们会发现,他这个“红色”饲养员可不只是一个标签,他是从内心里生发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对生产队集体财产的热爱、对他所饲养的驴的超乎常人的感情,以致他给予小凤英回报时要讨价还价,生怕驴受了委屈。用王吉合的话说:“多给你一把牲口就少吃一把”,“我是爹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肉,没有集体我连根草也长不成;长大了党把我交给驴,我就好好喂驴,驴圈就是俺的家,驴就是俺的孩子老婆……”王吉合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怕累着驴,怕饿着驴,有好吃的让驴吃,看驴比任何人都亲。有人打驴,他能骂得人家抬不起头;叫“孝顶”的驴摔死了,他给驴守灵上香。在王吉合的眼里,除了“驴不是牲口,而是有灵性的通人性的生物,这种因农业生产中牲口的巨大作用而产生的普遍情感”以外,他还有另一种“阶级论”的观念:在他眼里,他的驴比人至少比那些富农分子更宝贵。
也就是说,所谓“阶级”的观念早已经深入到王吉合的骨髓中,而使得王吉合眼中和他同一阶级的驴不仅仅是动物牲畜意义上的驴,而是神圣的圣物;非同一个阶级的人不再是人,而是连驴都不如的另类。小凤英是女人,但她更是“富农婆子”。因为是“富农婆子”,王吉合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小凤英,即便在两人相好的时候,王吉合也从来没有给予小凤英足够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动不动就威胁小凤英要“到大队告你勾引贫下中农”。黑/红的身份差异始终是横亘在两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即便小凤英娘家出身贫农,即便小凤英以身体为代价,即便小凤英为王吉合怀上了孩子,这一切都无法撼动政治身份差异带来的巨大悬殊。因此,当他的生理欲望不能再在富农老婆小凤英身上得到发泄和满足,他要寻找替身——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代替物时,那头叫做“红大嫂”的草驴就成了最佳“人选”。这一点,其实是理解王吉合和驴行苟且之事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王吉合看来,他和驴之间反倒没有那么大的悬殊,一方面,他始终将驴看得通人性;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的问题上,他也在之前就完成了归类的问题:为了防止有人虐待驴,他给集体的驴起了“革命化”的名字,诸如红卫兵、红小兵、红大嫂等,从地主富农分子家归公的驴,则被他命名为鸠山、胡传魁、刁德一等“坏名儿”。从而,他和这些红字辈儿的驴有了共同的标记,完成了他和驴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在身份至上的那个时代,王吉合和红字辈的驴远比他和富农婆子小凤英之间更为亲切和亲密,所以,当他最终因为要当典型了决心再也不找小凤英,而又要解决生理欲望最后站在那头叫“红大嫂”的草驴跟前,打算让它替代小凤英的时候,王吉合是这样想的:“要是它能了事儿,以后也就不用求谁欠谁怕谁了,自己的驴方便。”但是,尽管在他的心目中,驴已经被他“人化”“阶级化”了,但是,驴终究是驴,或者说,驴并未把他当驴。当他试图在与驴——这一非政治物的苟合中平衡理性与欲望这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时候,王吉合的人性表征便彻底丧失了,所谓的“阶级”,这个政治身份迫使王吉合一点点放弃了人道,而走向了兽道。而一当王吉合的人性表征丧失,那么,他作为人的生命也必然完结——母驴“红大嫂”踢死了王吉合。《赤驴》写了一个人因“赤”而沦落为“驴”——即兽的过程,“赤”对于人性的挤迫、压制、磨蚀亦显而易见。
如果说《赤驴》写的是“赤”对人性的挤破,那么,《半块字典》则着眼于贫对人性的压挤。贫农出身的灯奎家里极度贫穷,长大成年找不到媳妇。偏偏他还比一般人多认了些字,多知道些事,因而被戏称为“半块字典”。但是,这一点点“多”于他个人构不成任何智慧,于别人眼中反倒让他因为与众不同而更加遭人唾弃,因此,这一点点“多”实质上构成了通往他的悲剧命运的桥梁。这一点点“多”让他算出了自己“觝牝食母,无妇无嗣”的命运,却无力做任何改变。小说合理地自然也是生动地展示了灯奎怎样一步步走向他所预测到的结局。灯奎因为穷,因为那“一点点”而找不到媳妇,自然欲望无法满足而与一只他极其喜爱的名叫白白的母羊苟合,是为“觝牝”。但是,灯奎身上的人性依然丝丝缕缕,这种人性良知所导致的愧疚与他的愚昧、无知混合起来,让他始终担心母羊会生下一个长得像他的羊,这种担心促使他害死了他极度喜爱的白白。害死白白的灯奎依然无法抑制内心极度的不安和自责,导致他一步步走向疯癫:逼父亲自杀,与母亲乱伦,是为“食母”。忍无可忍的母亲最后亲手将儿子灯奎砸死。灯奎终于如其早就预见的,走向了那个唯一的结局。从见识多于一般人的超常人而失去人伦而走向疯癫而终被母亲砸死,灯奎的蜕变与死亡过程同样是人性被扭曲、被摧残、被磨蚀的过程。如果我们追问一下根源,为什么灯奎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当然不是神秘的命运使然,而是极度的贫穷以及与其如影随形的愚昧。这两个亲如兄弟的搭档一起,将灯奎送到了生命的终点,送到了人性泯灭的终极之地。
人降生在这个世上,却始终无法成为一个人——这个“人”尚不是甚至还根本不是富有道德与精神指向的个体的完整的人,而只是一个有着基本欲望的需要满足基本人性欲望的人。一个人因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的人而不得不堕落为兽,这样的状况何以发生?当然,这绝非人自己的选择,而是那个特殊时代社会对人的逼迫。在那个社会里,人的生命价值几何?《八两生命》有揭示;人的尊严何在?《赤驴》有交代;人的廉耻何存?《贼骨头》有展示。《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荀子所阐释的是人与水火、草木和禽兽的区别。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天下之最贵者,根本原因在于“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而所谓“义”者,孟子认为是“羞恶之心”,其实就是作为人才有的尊严感、道德感、价值感。而当人的生命价值如草芥,人的尊严如尘灰,人的廉耻之感、羞恶之心也必不复存在,无有“羞恶之心”的人与草木、禽兽也必无从区别。所以说,小说集《赤驴》与以往任何文革题材的小说比较起来,其价值在于它把那个时代连最基本的人①相比于知识分子,贫农应当算做那个时代最基本的人。的最基本的人性②“最基本的人性”指的是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都无法予以保障的残酷性呈现出来,因此,其对时代的发掘之深也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如果说,以往我们所接触到的诸多“文革”题材的作品,多数探讨的是不同阶级,即知识分子和贫农、富农和贫农等间的平等、尊严问题,那么,这部小说则直面那个时代“最红”的阶级——贫农阶级,以及他们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生存本相。这部小说集所展示给我们的是:当知识分子在要求和呼唤生命的平等和尊严的时候,贫农——乡村社会最为普遍的大众,尚处在与群兽共舞的蒙昧时代。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恩格斯曾经谈到人与动物的密切关联,他说:“谁设想人已经完全克服了自己身上作为生物机体而固有的自然因素,谁就是天真的和错误的。”[2]他又说:“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2]固然,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但是,人与人却有摆脱得多与少的区别。笔者以为,人摆脱兽性的多少取决于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即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与人摆脱兽性的多少成正比,或者说,一个社会里人性的高度就是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从这一基本认识来看,笔者认为,老奎的小说集《赤驴》用生动的艺术形象阐释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是怎样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催逼为兽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在从人性向兽性的被迫堕落中苦苦挣扎的,这种挣扎是怎样得痛彻心扉、不堪回首。而当小说展示这一触目惊心的景象的同时,还呈现了这样一种思想:极端的政治高压与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之间有密切而深远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以本能的需要为基础的食欲、性欲,如果由人自身所建立的社会连这种基本机能都无法满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建立和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人是需要反思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集《赤驴》在揭示特定时代社会的荒诞性和不合理性方面,所达到的深度是令人惊叹的。
二、素朴的叙事及审美空间的生成
作家在《后记》中说,这些作品,都是他“曾经耳濡目染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农民生活的沥血感受和非常印象”。新时期以来,以“文革”作为叙事内容的小说并不少见,且不说“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的直面“文革”,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革”作品也依然持续不断地从知识分子作家笔下汩汩而出,王安忆《叔叔的故事》(1990年)、张承志的《心灵史》(1990年)、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991年)、李锐的《无风之树》(1995年),以至余华的《兄弟》等,都是对于“文革”的不断梳理和打捞。但是,从近年反映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看,似《赤驴》这种源自切身体验和长期回味、思索而生成的作品并不多见,尤其着力于发掘“赤”与“贫”之间的胶着关系且笔力达到如此深度的更不多见。小说集《赤驴》能够抵达如此深度的缘由当然与作家身在其中所获得的切身生命体验密切相关,更与作家所选择的素朴无华的叙事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唯此素朴无华的叙述,方能带来无比真实和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方能获得恒久厚重的艺术效果。
(一)民间化的讲述方式
《赤驴》中的每一篇小说都不曾刻意构造某种讲述方式,而采用了古老素朴的“从前有个山”的叙述方式,在一种回忆的口吻中缓缓带出人物,带出故事,带出命运,同时带出世态人心,带出历史全景,小说于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深刻的力量。
《胡全奎当官》以时间为序顺次铺展胡全奎的历程,但在这一时间线索之下隐含着两条轨迹:其一是其政治的发迹过程,其二是其梦想当一回真男人的破灭过程。胡全奎因为偶然的机缘一夜之间从普通人突然被提拔为村革委会主任,又于突然之间被任命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这个火箭式的穿越过程,对胡全奎而言,是失重的过程,是不知所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心惊肉跳,而且他越是拒绝,来得越快:他的结巴和内急正是这一心理状态的直接反映。而他发自内心当一回真男人的梦想却始终未曾实现:始则无妇,其后无能,再后无力,最后无果。对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男人而言,胡全奎的政治事业可谓发达,但是,对完全没有政治理想的胡全奎而言,当官是被迫的,尤其他的 “官服”都被要求按照规定的样子来——戴破帽子、扎破带子、背粪篓子,甚至他的姓氏也必须改变——因为他的本名胡全奎与反面人物胡传魁①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人物。太接近了,不符合革命干部身份,“一个革命干部哪能叫个坏蛋的名儿”。因此,公社张秘书命令他改姓王:“沾沾沾,我就姓王吧。”愿意还是不愿?没有用。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如胡全奎一样欣欣然接受全新的赐名。于是,胡全奎如演员一样,穿着指定的戏装,扮演着指定的角色,做着指定的却荒唐的种种事体,然而,却要承受他所不得不扮演的角色所带给他的所有后果。小说最后,在确定胡全奎能否做一回真男人的最后一刻,他死于“为官”所带来的报复。总之,胡全奎不想做的事不做不行,想做的事却怎么也做不成,他无法成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个人,这就是时代给予他的无可逃脱的命运。小说在素朴的叙述里将胡全奎的“尴尬”表现得淋漓透彻,将一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对人的虐迫、挤压、扭曲、异化呈现得纤毫毕现,同时,也将人性固有的局限、狭隘彰显得自然而然。
如前所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文革叙事并不罕见,甚至,新时期文学肇始于对“文革”的讲述。但是,以往的文革叙事多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这些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批判意识或反思意识,揭露着现实或反思着自我,完成的是如同五四知识分子一样的启蒙使命,表达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对农民的批判,抑或对自我的反思,而如《赤驴》一样从那个时代从那个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作品并不多见。它就如同那时被埋藏起来的一颗天然珍珠,在今天被我们重新发现,让我们从这颗珍珠中遥想和回味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和那一群曾经存在也许一直存在着的人。
素朴无华的叙述对于作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处理不好,极其容易沦为流水账而让阅读者疲惫生厌。所以,平铺直叙考验着作家捕捉生活、把握人物的功力。老奎虽平铺直叙但跌宕生姿,非但不让人疲惫厌倦,反而让读者一旦进入文本便欲罢不能,连连叫好,这显示出老奎如同武林高手一样的深厚内功。这个内功体现在他捕捉生活的能力之强、思考生活的程度之深、把握人物的分寸之恰当等诸多方面。老奎的小说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素朴的力量。
(二)有距离的介入
阅读作品,我们不时发现叙述人是站在当下的历史姿态:小说里不断出现“在那个年月”“就如同现今”“不像如今”等语句,《胡全奎当官》中更是插入“运动刚开始那几年,村里很乱,你斗我我斗你,你上来我下去,正经人都靠边儿站了,剩下在台上的不是不爱干活儿的意见篓子,就是无恶不作的噶古人,每天琢磨整人,实在找不下茬儿了,就藏在茅房旮旯、躲在墙角、悄悄跟在人后、趴在窗户底下偷听人们说话……”等整段回忆、评述。这种叙述的口吻印证了作者后记中所说意在 “祭奠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们”的话。这种“祭奠”基调和口吻,使得叙述人对人物的同情保持了必要的审美距离,既保证了故事和人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又合理地克制了叙述人与人物的关系,同时,还产生了反讽的效果,进而生成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如同一个历经沧桑的智者,他将丰富的经验用平平淡淡的口吻叙述出来,但是,我们却从这种貌似平淡的口吻中遥想到了不平静的风云,嗅到了来自那个时代的淋淋血腥。“小说是回忆”,老奎用他的作品印证了沥尽火气之后的平淡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与人性深度
老奎刻画人物并未采用什么新方法,甚至连景物描写都几乎没有,完全是以语言、动作、细节、心理刻画人物。这种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却将人物刻画得准确、生动,极具典型性。王吉合(《赤驴》)、灯奎(《半块字典》)、秃嘴(《八两生命》)、胡全奎(《胡全奎当官》)、胖英娥(《贼骨头》)等,我们都可以将他们看做是那个极端特殊的时代所生成的或被挤迫而成的畸形人、变态人、异化人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矛盾、痛苦、希冀等丰富的情感和心理,被作家把握得异常准确,被作家刻画得异常生动。
在老奎这里,塑造人物一靠细节,二靠心理描写。王吉合是个红色饲养员,但也有着人性的基本要求。他禁不住富农老婆小凤英的诱惑,但是,红色饲养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他心中同样不可动摇,他每次都和小凤英讨价还价,还“怕拖长了粮食太多”,甚至小凤英给他送来的好吃的他都要给驴分一些。这些行为、细节、心理对于呈现王吉合的赤色身份简直是神来之笔。这种集体主义观念,责任感的内化、神圣化正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一种赤色标帜。
胡全奎更是如同被时代这个指挥棒引导的一只猴子,被迫爬到不属于他的高高的竹竿顶部,被迫做出原本不是他所愿意的种种动作,只为了取悦所谓的看客。作者将胡全奎的这种尴尬、无奈通过对他说话的结巴、关键时候闹肚子等细节予以反复勾勒、渲染而体现出来,将他的善良、滑稽、可怜、可爱以及荒诞等诸多复杂因素纳于不可言说中,使得胡全奎的形象饱满、生动、丰富、立体。
形象的典型程度是作家发掘人性深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者说,作家对时代对人物发掘越深,捕捉越细,表现越准,其刻画的形象才能越典型。反过来说,作家笔下的人物达到了典型的高度,意味着作家准确而深刻地呈现出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人性特征,代表着作品达到的艺术高度。从这个层面看,我认为,老奎在他的这部小说集中所刻画的几个人物,尤其是胡全奎、王吉合、灯奎等,可以称得上是表现文革时期被异化了的赤贫阶级的典型形象,甚至从某个角度看,这几个形象填补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此类形象的空白。
最后,笔者谈谈老奎的语言。这是一种极富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语言,简约、质朴,还带着来自大山里的一股子野性、泼辣和憨厚,让人过目不忘,流连忘返。
综上所述,笔者愿意将老奎的《赤驴》看做是用中国语言中国方式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和经验的典型文本。
[1]荀子.荀子·王制[M]//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周亚红)
Painful Rural Experiences and Natural Rural narration:A Review of Red Ass
YANG Hong-li
(School of Arts&Communication,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In a natural and unadorned expression,the novel Red Ass presents de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1960s-70s.It accurately depicts the struggle of how human nature was destroyed and worn out in the special period,created a series of lively and typical characters,and artistically describes ignorance and absurdity brought by the ultra-Left politics.Therefore,Red Ass is the collection that gives an in-death and in-breadth description of“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
Lao Kui;Red Ass;novel;human nature
I207.427
A
1673-1972(2015)02-0057-05
2015-01-09
2014年度石家庄市社科专家培养项目成果(2014zjpy05)
杨红莉(1969-),女,河北无极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