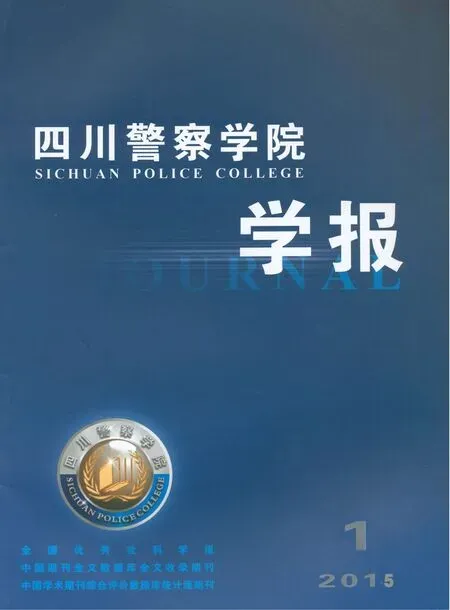自贸区走私犯罪停止形态相关问题探讨
金华捷,李舒俊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自贸区”)的正式成立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措施,继续扩大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贸区在行政监管模式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既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初露端倪,也是很多经济犯罪出现了新的态势[1]。应该看到,自贸区采取的“一线全面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监管措施以及上海海关推出的14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制度,使走私犯罪的停止形态出现了新的疑难问题。
具体而言,在海关监管制度方面,自贸区实行的是“先入区、再报关”的政策。当货物从境外进入自贸区时,监管部门允许自贸区内企业凭进口舱单将货物先行提运入区,再办理进境备案手续,从而实现海关在自贸区内的软化监管。当货物从自贸区进入国内其他区域,或是从国内其他区域进入自贸区时,行为人必须向海关履行相关报关手续,海关则依据海关法的规定,征收相应的税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相关走私犯罪,我们应当如何认定走私犯罪中的停止形态?自贸区走私犯罪的着手应当如何认定?自贸区自私犯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如何确定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且必须给出答案的问题。
一、自贸区走私犯罪着手的认定
根据刑法原理,在故意犯罪中,犯罪着手是犯罪预备行为和犯罪实行行为的界限。即如果行为人尚未着手,则其处于犯罪预备阶段。如果行为人已经着手,则已经进入犯罪实行阶段。在传统的走私犯罪中,司法机关一般是以行为人是否向海关履行报关手续,作为认定走私犯罪着手的标志。但是,在自贸区内走私犯罪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自贸区实行“先入区、再报关”的监管政策,行为人在履行报关手续之前,会先凭进口舱单将货物先行提运入区,再办理进境备案手续。那么,自贸区走私犯罪的着手的认定是应当延用传统走私犯罪的标准还是以自贸区走私犯罪出现的新变化为依据确立新的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所谓着手,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2]。同时,根据理论界的通说和刑法的相关规定,走私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刑法规定的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行为[3]。然而,通过分析上述的刑法原理和刑法规定,我们还是很难为自贸区走私犯罪的着手提供清晰和明确的标准,即在自贸区走私犯罪过程中,哪一个行为环节可以被认定为“逃避海关监管”的开始?应该看到,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主要通过形式判定的路径确定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但是,随着经济犯罪的日益复杂以及经济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仅仅依靠形式判定的方法,未必能够准确地判定犯罪着手的节点。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在传统形式判定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借助实质判定的方式,为犯罪着手的判定提供依据。
有学者立足于客观未遂论,即未遂犯可罚性的基础在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客观上有可能对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即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造成侵害之危险。因而,实行的着手,应当认为是指含有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危险性行为的开始,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发生时,是行为的着手[4]。有学者甚至提出,预备行为也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犯罪未遂只能是具有侵害法益紧迫危险性的行为,当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时,就是着手[5]。
尽管上述学术观点是相关学者对于德日刑法中犯罪着手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但是这些学术观点所体现的理念完全可以为实践中自贸区走私罪的认定有所帮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犯罪是侵害犯罪客体的行为。就此而言,无论是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都会对犯罪客体造成一定的侵害。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应该看到,刑法之所以对犯罪预备、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在处罚上“比照”犯罪既遂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完全是因为这四者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是有所区别的。正如前述,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犯罪未遂是具有侵害法益紧迫危险性的行为。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预备行为具有侵害犯罪客体的危险,而犯罪未遂是具有侵害犯罪客体紧迫危险性的行为。由于犯罪未遂是以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条件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犯罪的实行行为也是具有侵害犯罪客体紧迫危险性的行为。根据刑法原理,犯罪着手是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过度节点。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犯罪着手是实现“侵害犯罪客体的危险”向“侵害犯罪客体紧迫危险性”转化的节点。换言之,认定犯罪着手的实质判定标准就是判断行为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是否已经从“危险”向“紧迫危险性”过度。
但是,无论是“危险”还是“紧迫危险性”都是一种价值判断,似乎难以在司法实务中为司法机关提供判定犯罪着手的标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以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对于犯罪客体侵害程度上的差异性为基础,为判定犯罪着手设立客观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应该看到,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所以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两者距离犯罪危害结果的远近程度不同。预备行为距离犯罪危害结果的距离较远,而实行行为距离犯罪危害结果的距离较近。如果犯罪实行行为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刑法》总则第14条规定的故意犯罪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该犯罪行为理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如果犯罪实行行为最终没有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该犯罪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犯罪实行行为能够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预备行为由于距离危害结果较远而不会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以故意杀人行为为例,举刀劈砍的行为完全可能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先前的买刀、磨刀的行为似乎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行为“是否会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划分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的界限,并以行为“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向“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转化的节点,作为认定犯罪着手的标准。
自贸区走私犯罪的犯罪着手认定完全可以适用这一标准。应该看到,“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是刑法规定的走私犯罪危害结果。在自贸区海关的监管体制中,一线备案既是一道形式审查程序,也是二线报关的前置程序,实际上并不会对事后海关征收关税产生直接影响。行为人只有进入了二线报关程序才会涉及到海关检验、核定应缴税额等核心监管环节。换言之,只有在二线报关环节中,行为人的相关行为才会具体指向海关征收的关税,并对海关征收关税制度产生直接影响。就此而言,一线备案的行为,只能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而不会直接导致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二线报关环节,行为人实施虚假报关行为,才会直接导致“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刑法》规定的走私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正因如此,司法机关应当以是否履行报关义务作为认定自贸区走私犯罪着手的标志。如果行为人在一线备案环节实施虚假备案行为,尚未进入二线报关环节即被相关部门抓获或是自动放弃继续实施犯罪,司法机关理应将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预备或是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一旦在二线报关环节已经开始实施虚假报关行为,那么,司法机关无疑应当排除走私犯罪的犯罪预备的成立。
二、自贸区走私犯罪未遂形态的辨析
上海海关缉私部门有一种观点认为,自贸区走私犯罪并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如果行为人的相关走私行为偷逃应缴税额尚未达到走私犯罪的起刑点,相关监管部门则将这一行认定为行政违法。如果行为人的相关走私行为偷逃应缴税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司法机关则将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既遂。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这是因为:
首先,自贸区走私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并不符合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相关原理。所谓的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停止形态[6]。而犯罪未遂中的“未得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没有齐备。换言之,犯罪未遂的本质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其行为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停止形态。从中我们不难得知,在通常情况下,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存在着手实施犯罪以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导致行为人的行为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亦即,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故意犯罪理应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当然,举动犯和实害犯并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是故意犯罪中的两个例外。在举动犯中,行为人只要一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即达到犯罪既遂形态,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在实害犯中,如果行为人的相关危害行为导致了实害结果的发生,该行为则构成实害犯的既遂;如果行为人的相关危害行为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实害结果,该行为则构成危险犯的既遂,并不存在犯罪未遂。应该看到,走私犯罪既非举动犯,也不是实害犯。因而,认为自贸区走私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的观点,无疑违背了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自贸区走私犯罪理应存在犯罪未遂形态。正如前述,在自贸区走私犯罪中,当行为人在二线报关环节开始实施虚假报关行为时,司法机关应当认定行为人开始着手实施走私犯罪。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走私犯罪,只要该走私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齐备走私犯罪的构成要件,该行为毫无疑问应当构成犯罪未遂。
其次,自贸区走私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势必不利于惩治自贸区的走私犯罪活动,也不利于维护自贸区的海关监管制度。应该看到,自贸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政策的试点区域。随着海关监管制度的创新,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自贸区的走私活动必将日渐频繁。就此而言,我们理应加大对于自贸区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遏制自贸区走私活动的发展趋势。然而,根据《海关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所列行为(走私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根据《刑法》第151条至第157条规定,走私犯罪共十一个罪名,这些罪名的最低法定刑为管制,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在这十一个罪名中,绝大多数罪名的最低法定刑都在六个月有期徒刑以上,有近一半罪名的最高法定刑在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上。通过对比海关法和刑法对于走私活动的处罚,我们不难得知,海关法和刑法对走私行为的处罚力度轻重悬殊。对于那些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齐备走私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果司法机关不将其认定为走私犯罪的未遂,而仅仅作为行政违法处理,无疑会降低走私犯罪的犯罪成本,并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大肆利用自贸区的“便利政策”实施走私犯罪活动。这不仅不利于惩治自贸区的走私犯罪活动,也不利于维护自贸区的海关监管制度。
综上所述,在今后自贸区走私犯罪中,当行为人着手实施走私犯罪后,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行为没有齐备走私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可能时有发生。对于这类行为,司法机关理应以走私犯罪的未遂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认定
在司法实务中,走私犯罪的既遂认定标准极不统一。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公布的《关于对海关监管现场查获的走私犯罪案件认定既遂、未遂问题的函》规定“对于行为人通过国家设置的海关监管场所‘闯关走私’的,只要走私货物、物品到达海关查验关口,或者进入海关专设的监管货场而被查获的,应当认定为走私既遂”。据此,不少实务部门认为,在自贸区走私犯罪中,只要走私犯罪行为人在二线报关环节中以伪报、瞒报方式实施虚假申报行为,并被现场抓获,该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笔者认为,上述实务部门的观点值得商榷,从犯罪既遂的成立条件以及从有利于区分自贸区走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角度分析,司法机关应当以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符合犯罪既遂的成立条件。根据我国刑法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既遂,应以该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要件为准[7]。正如前述,《刑法》分则规定的走私犯罪的构成要件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刑法规定的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从中我们不难得知,“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是走私犯罪的法定危害结果。就此而言,在自贸区走私犯罪中,只有当实施走私犯罪的行为人完成了“偷逃应缴税额”这一行为环节且“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危害结果出现后,司法机关才能认为行为人的走私行为实施完成,从而认定该走私犯罪齐备了全部的构成要件,达到犯罪既遂。反之,按照某些实务部门的意见,只要走私犯罪行为人在二线报关环节中以伪报、瞒报方式实施虚假申报行为,就构成走私犯罪的既遂,这种观点显然缺乏理论依据。在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尚未出现的情形下,我们显然不能认为行为人的走私行为已经实施完成,更不能认为行为人的走私行为已经齐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走私犯罪的全部要件。因而,我们不能将某些实务部门的意见作为认定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准,而应该严格以以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记过的出现作为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
其次,以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有利于区分自贸区走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正如前述,犯罪未遂之所以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主要是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犯罪未遂对于犯罪客体的侵害仅仅具有紧迫的危险,却没有实际侵害到相应的犯罪客体。与之相反,犯罪既遂一旦成立,就标志着犯罪行为已经对相应的犯罪客体产生了实际的侵害。以故意杀人罪为例,如果行为人着手实施杀人行为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以致没有出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那么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仅仅对被害人的生命权造成紧迫的危险,却没有实际侵害到被害人的生命权;反之,如果行为人的杀人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出现,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行为人的杀人行为已然对被害人的生命权造成了实际的侵害。在自贸区走私犯罪中,如果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的行为导致“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那么,自贸区的海关监管制度已然受到实际的侵害;如果行为人在着手实施走私犯罪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并没有导致“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那么,行为人的走私行为对于自贸区海关监管制度仅仅具有紧迫的危险,该行为并没有实际侵害到自贸区的海关监管制度。以此而论,以行为人“偷逃应缴税额数额较大”这一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作为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志能够使自贸区走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泾渭分明。如果我们以某些实务部门的意见作为认定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的标准,那么自贸区走私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将会变得十分模糊,司法机关难以对两者作出清晰的界分。
[1]刘宪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J].法学,2013,(12):130-137.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8.
[3]刘宪权.刑法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4-451.
[4]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529.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
[6]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27.
[7]刘宪权.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