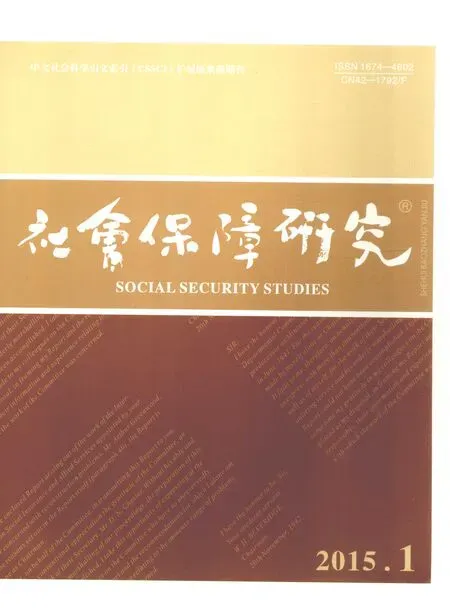职业福利功能之争
丁学娜
(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1815)
职业福利功能之争
丁学娜
(南京审计学院公共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1815)
对职业福利功能的判断或定位,决定了在职业福利发展及其与公共福利的合作机制方面的政府政策引导方向、力度、方式或方法。国内外学者对本国或世界范围内公共福利与职业福利作用关系的实际考察发现:补充理论、替代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职业福利的功能做出了不同的判断。由于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功能等价原则以及国家之外的福利供给主体对国家的替代能力的质疑,替代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缺少广泛支持;对公共福利的补充功能成为世界范围内职业福利的功能定位。然而,职业福利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要使职业福利充分发挥补充功能,仍需对其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职业福利;国家福利;补充;替代;福利多元主义
职业福利的发展历史悠久,但并未得到重视;即使蒂特马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对职业福利的定位也终究被福利国家或国家福利的光芒所覆盖。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改革运动的开展,职业福利开始受到重视;不管是从福利的多主体供给方面,还是从覆盖人群的受益水平方面,职业福利都带来了新的思考。从社会政策角度看,职业福利受到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与国家福利之间的某种关联,即在福利供给过程中,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或公共福利间存在怎样的作用关系,或二者扮演怎样的角色。
而在中国,随着公共保障或国家保障体系构建逐步完善,作为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作组织所提供的职业福利将成为社会保障领域关注的重点。尤其,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的推进更为职业福利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为,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应注重转换保障机制,而非降低待遇;而相应的改革方案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由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构成。如此,在养老金的提供机制上实现了并轨,但要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不降低,就意味着职业年金需要得到充分发展,以弥补在基本养老金部分的缺失。而与之相应的,将带动企业年金的发展;虽然企业年金制度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之初就以做出明确定位,并提供激励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今后随着职业年金制度的推行,必定会带来企业年金的进一步发展。补充养老金这一收入补偿保障是职业福利的重要内容,仍有大量职业福利内容有待发展和完善。
虽然职业福利的内容或提供形式并不陌生,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福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补充社会保险等收入福利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福利项目都是职业福利的内容。但从社会政策角度看,职业福利仍是有待明确的领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应的改革,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职业福利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差异不断明晰,尤其是供给主体、资金来源、覆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在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的背景下,对于职业福利的发展如何把握,对其功能的判断非常重要。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本国或世界范围内各国公共福利与职业福利作用关系的实际考察,发现三个主要理论能够概括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或公共福利之间的关联:补充理论、替代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三种理论对职业福利的功能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也显示了职业福利的不同发展方向。
一、补充理论
补充理论认为每个福利供给组织都有本身的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他们只能执行某些特定与其结构相匹配的任务或目标。不同福利供给主体都有各自专业的领域,提供不同种类的福利服务,也就是,不同主体供给的福利项目基本不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该理论认为一方福利主体供给活动的增加会引发总体福利供给水平的增加,而其他主体的福利供给量或者增加,或者不受影响。这意味着在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即不存在正向也不存在负向相关关系。[1]
蒂特马斯关于福利社会分工理论[2]的演变逻辑即反映了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的补充关系。福利的社会分工缘起于劳动社会分工,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个体化、专门化的时候,各种关系都会更加不稳定,个体也就变得更加具有社会依赖性;通过更多对个人依赖和依赖的社会起源与影响的承认,社会政策就越能反应对依赖的“人为”成因更多的认知,同时对依赖“人为”成因的认识也会影响到其他类型福利的发展。每个人都是福利依赖者,但不同社会群体或多或少依赖福利社会划分中的不同组成部分。[3]所有集体性提供的服务都是精心设计出来满足某些社会认可需要的,整体来看,所有为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和/或服务于社会的更为广泛利益的集体性干预,可以宽泛地分为三种主要的福利类型: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财税福利(fiscal welfare)和职业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从三个体系的最终目标来看,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远比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重要,故而,对“社会服务”的界定应该从目标来看,而不是从完成这些目标的管理方法或制度设计方面看。[2]
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构成“社会服务”的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满足不同人群以及不断变化的需要,两种福利在功能目标上相互补充。社会福利是集体主义对人们无法为其自身和他们的家庭“赚钱谋生”时所产生的“依赖状态”的需要回应;而职业福利的绝大多数津贴明显地给予状况较好的人群,是锦上添花。[4]此处也表明了社会福利相对于职业福利的基础地位。
公共福利传输系统提供基本经济支持,职业福利系统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这种额外的经济支持在很多国家会让员工的福利补偿达到正常的工资收入。有学者已证明这是职业福利发展的部分原因,社会保护的个人与职业福利系统在回应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真空中崛起。自愿的私人社会补贴(voluntary private social benefits)经常出现在公共福利受到限制的国家。[5]当公共部门不提供某项具体的社会福利时,私有部门会供给。“企业或职业养老金系统最基本的目标是适应国家养老金系统的转变,同时考虑到自身产品市场的转变。”[6]例如,荷兰没有公共的收入相关联式养老金(public earnings-related pension),只是依赖贝弗里奇式(Beveridge-style)的定额养老金,而私营公司则通过工会协议或雇主的自主精神弥补这一空隙。[7]
对于福利服务而言,面对国家不能够及时或没有能力依靠公共力量解决的新社会风险问题,企业层面的职业福利能够对其进行补充。应对新风险产生的工作——家庭生活矛盾问题、教育或训练不足产生的失业问题等的公共福利供给在欧洲国家发展并不平衡。例如,在儿童和老年人公共照料服务很发达的北欧国家,其照料服务依旧面临新的挑战:对儿童照料而言,家长工作时间的延长、工作时间的不规律以及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多,使得传统朝九晚五的日间照顾模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对于老年人照料而言,老年人长期照料的支出增长迅速,威胁到国家老年人服务模式的可持续运转,为此,国家收缩了此项公共服务的规模,这意味着更多的老年人照料服务需要由私营部门和家庭来满足。[8]同样以荷兰应对新风险的福利项目——部分时间工作制、儿童照料和家长假为例,政府在创建应对新社会风险上存在多种困难,针对工作——生活风险问题方面的社会保护供给还没有纳入到荷兰国家福利的范畴,因而,政府没有提供与新增社会风险相关的福利项目,但这种福利提供的角色就被工会与雇主的集体协商所替代。[9]企业内设置的与女性就业相关的照顾津贴、假期、相应的照料设施和工作制度等的配套措施、就业培训、教育等就成为对劳动者而言非常重要的福利补充项目。
二、替代理论
替代理论暗含着在国家福利与职业福利之间的反向关系,一个主体供给活动的增加会导致另一个主体的总体福利供给减少,反之亦然。集体社会福利处在私人职业福利的反向主导地位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或零和博弈关系。[1]国家福利的扩展对职业福利具有挤出效应,职业福利的增加也会对国家福利的供给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社会保障发达的地方,企业保障则不发达;相反,企业保障的发达也会妨碍社会保障的发展。这是替代效应的一个论据。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儿童保护在先进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在工资中包含了抚养补助的缘故。另外,日本的社会保障给付额相对较低,这除了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欧洲国家出现较晚的原因外,多半是由于企业在社会保障中发挥的作用大,尤其是企业退休金的存在对社会保障给付影响极大。[10]在美国,这种替代效应表现得也很明显:美国职业养老金发达,而法定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则显得非常萎缩。德国的职业养老金比例较低,原因在于它的公共养老金较高的替代率。但是,随着福利国家收缩改革,德国2001年养老金改革方案将部分法定收入关联养老金体系私有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降低替代率,引入对具有执业资格的私人和职业养老金计划的国家补贴。一个标准养老金领取者的净替代率(net replacement ratio)从2007年的约70%降到2030年的54%。[11]
但是,与以上观点相对,通过对现实中福利供给情况的考察,多数学者认为,私人部门福利不是公共福利的替代而是补充,两者相得益彰,为双方的扩展创造条件。替代理论的现实用途似乎仅仅是批评福利国家的一个语言工具。[1]例如,美国私人雇主对职业福利的回应高涨期是社会保障法案出台后,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职业福利的边际成本存在优势。[12]私有保障与公共保障之间具有连续的、互补的关系。[13]面对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补充关系理论相竞争的替代理论,瑞恩(M. Rein)通过考察各发达国家法定与私有养老金之间的变动关系发现,虽然有部分数据显示替代效果,但是某些国家的数据让这种此消彼长关系的假设变得迷离,因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国家法定的福利项目在增加的同时,企业自主的福利项目成本却没有减少,而是维持不变。[7]再通过职业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各国的比较,也发现,职业养老金对公共、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理论存在破绽。虽然在美国、英国,职业养老金对支出不足的公共、法定养老金存在明显的替代作用,但是在大部分国家,甚至在荷兰,这种替代作用受到质疑:尽管职业养老金的比重是在上升,而且高于公共、法定养老金支出增长的比例,但是这些国家有相对高水平的公共社会保障支出水平。[6]慷慨的福利国家服务供给不会替代其他供给者的服务,而是允许他们以自身的特性提供其他形式的服务。
对于替代理论,学者们还有关于除国家之外其他供给主体的替代能力的质疑,由于该质疑最初由福利多元主义者提出,因而放在下面的部分详细阐释,此处不多解释。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对于福利服务供给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缺乏清晰的论证,没有能力描述市场和志愿部门与国家的相互渗透过程。[14]达尔伯格(L. Dahlberg)尝试将其前提或假设进行澄清,并与替代和补充理论进行对比。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的前提是多个不同部门共同提供相似性质的服务,各项福利主体能为使用者提供相互转换、替代的选择。各主体间并非一定存在竞争关系,福利供给的总量或许因为供给者的增加而增加,国家福利与其他福利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正向关系。[1]这种福利理念的假设是福利供给各部门在功能上是等价的,各部门之间可以进行替代。部分福利多元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主要是国家在总体福利项目中主导地位的一种转变,各种福利提供者之间的功能正在重新分配,而福利总体水平将几乎仍然保持从前的规模。伊瓦斯和奥尔科认为,照料政策精心地将不同的部门混合在一起,以建立一种合作式混合(synergetic mix),一个部门的弱势由另一部门的优势所抵消。以此为基础,他们强调国家责任、家庭照料潜力和正式照料服务供给者多元化之间的联合以保证使用者导向的(user-oriented)、有效率的长期服务供给。[15]社会福利总体规模是各部门提供福利规模的总和。如罗斯认为,市场、国家和家庭在社会中提供的福利总和即社会总福利,用公式表示为:TWS = H + M + S。TWS 是社会总福利,H是家庭提供的福利,M 是市场提供的福利,S 是国家提供的福利。社会总体福利是由家庭、市场和国家共同的、或补充或竞争的提供的福利混合。[16]
福利供给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福利多元主义分析的重点。约翰逊(N. Johnson)就指出,福利混合经济中的关键问题不是考察提供福利的四个主体是否存在,重点在于分析四部门之间的平衡,需要考虑四部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福利服务项目以及相同服务项目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变化。罗斯(R. Rose)也指出,一个既定社会的福利混合特征表现为由三个部门所提供福利产品和服务比例的不同,福利混合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两种极端形式是由其中一个部门垄断,另一种形式是每个部门提供1/3的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福利供给的各部门之间有一条“移动的边界”,在供给福利过程中,每个部门的作用和介入程度因时、因地而异。福利混合经济因此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现象,其走向取决于特定时点上的特定历史情境。[17]鲍威尔和犹伊特(M. Powell & M. Hewitt)通过分析英国的福利供给状况,认为英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福利混合经济,只是混合的要素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应将英国看作一个一直具有福利混合经济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志愿部门、家庭和市场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18]在国家集体主义的潮涨潮落中,家庭、市场和志愿性/慈善性部门并没有消失过。贝弗里奇的保险原则恰到好处地展示了福利多元主义的价值,若将他所支持的普享主义与制度型福利国家义务等同,就产生了对贝弗里奇的误解。因为他将法定干预与直接的个人责任联系起来,低水平的法定最低生活保障,为个人依据自身能力和愿望增加保障留出了空间和激励。在国家法定部门和私人部门外,贝弗里奇也看到了日益兴盛的志愿部门的道德和现实价值,他相信生计方面的国家法定保障将会鼓励私人部门的自助精神以及志愿部门的利他主义。[19]
福利混合经济术语的规范性使用表明,不同的福利意识形态对不同的福利混合会有相应的偏好。大致而言,政治左翼会倾向于国家在福利中占据强大的位置,而市场的空间会很小,或者甚至没有;强大的商业、志愿性和非正式部门则被认为与不平等相联系。另一方面,政治右翼却倾向于以商业性、志愿性和非正式方式取代国家方式,倡导一个福利社会而非福利国家。政治右翼认为国家是一个低效的福利生产者,过度的国家责任会导致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e)。[20][21]
但是对于这种功能等价的前提认定,学者们存在异议。约翰逊(N. Johnson)认为,英国在福利供给上一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来源,但是保守的撒彻尔政府偏向福利的混合系统,这种混合系统意图减少国家的作用,相应的增加非正式部门、商业部门和志愿部门的作用。但对于非正式部门、商业部门和志愿部门接管福利供给的能力状况,他持有深深地怀疑;因为非正式部门、志愿部门和商业部门都存在福利供给能力缺陷。[22]职业福利是企业供给的福利,相对于企业的生产功能而言,它的福利功能相对较弱,没有能力替代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福利。英国在养老金方面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将收入关联的公共养老金设置为可以与职业养老金相互转换的国家。英国战后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发展出一个特殊的混合养老金体系,在国家基本养老金计划之外,雇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协议退出机制”从国家提供的工资比例年金计划替换到由雇主提供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两者之间只能参加其一),同时政府规定,职业养老金计划必须至少与国家工资比例年金计划保持同一水平的资金给付。[23]但在基础养老金方面,职业福利没有涉入的空间和能力。
福利混合经济作为学术术语可能是中立的,因为它包含任何一种特殊的混合,但是对它的应用却远非如此。混合经济运动是世界对国家作用的重新评估,在此过程中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结构都会发生变化。[24]米什拉(R. Mishra)认为,总体福利(total welfare)并不是各个部门所提供福利的简单加总,不同部门的混合还增加了更多的东西。国家可能从直接提供福利的角色上退下来,鼓励雇主、志愿组织、家庭和其他人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政府在劳动力市场福利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而且社会福利的提供从一个部门到另一部门之间的转移,其背后掩藏着深刻的价值含意。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福利的提供形式看做是“功能等同物”(functional equivalents);不同的部门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之上,其作用范围也就不同,也就不能被单纯地看做是彼此的替代品。[25]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研究表明,各个部门在功能上不能被简单的等同。在对福利体制方法修正中,他指出,福利是在国家、市场、家庭以及所谓的第三部门之间相互作用而生产的,但是由于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风险管理原则,他们不能相互替代。
四、小结
总体而言,以上对于公共、法定福利与职业福利提供福利关系的补充与替代理论的争论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模式实际上都是对福利供给中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凯恩斯—贝弗里奇式或凯恩斯—俾斯麦式都将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作用配置压过了市场、社会。随着福利国家改革的开展,这种福利供给力量模式进行了调整,市场的力量开始突出,国家力量开始收缩。针对这种力量调整变化,市场主导提供的职业福利与国家的法定、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讨论就出现替代与补充、抑或福利多元主义之说。
由福利多元主义引发的关于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出,福利多元主义者在大多数时候遵循的是各供给主体的功能等价原则,各主体具有同等供给福利的能力,这与替代论所遵循的前提是一样的。两者不同的是对于福利供给总量的判断,随着福利供给主体供给活动的增加,前者认为可能会增加福利供给总量,而后者认为福利供给总量会保持一个与供给活动变化前大致相当的水平。但是现实中各国的福利实践证明,在福利供给中,国家之外的其他部门对国家福利供给的替代能力有限,不可能实现替代;而补充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验证。职业福利尽管存在负面影响,但其社会功能不可否认;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存在着辩证关系,职业福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社会福利。[26]
本文认为,国家介入福利提供对于纠正市场失灵、保障基本社会公平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一点上,国家提供福利的作用是市场取代不了的。大多数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由政府支付;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公共社会支出占总社会支出的比例为95%,而在荷兰和英国稍微低一些,但也在85%左右。虽然美国私人社会支出非常重要,约占GDP的8%左右,占社会总支出的1/3左右[5],但是公共社会支出依然远远超过私人社会支出。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经验材料显示,政府的社会支出其实并没有减少,虽然职业福利的支出在增多,但国家依旧处在应对社会风险的主导位置。[27]因而,在应对社会风险中国家所起到的作用是最基本的,市场力量起到的是补充作用,“通过建立国家供给的最低标准,国家养老金实际上在鼓励额外的私人养老金储蓄。那么,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补充而非替代关系。”[6]但是,各国保障体系的不同决定了补充程度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五、国内学者对职业福利功能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立足于中国从单位福利向社会福利转型的实际情况,多数认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从替代关系向补充关系的转变,并认为两者之间的补充关系是中国未来福利改革的趋势。
(一) 国内学者对职业福利的国际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杨艳东认为,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的替代关系会发生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特定时期,如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实行的单位福利制度,19-20世纪西方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前的时期。[28]
国内学者通过对国外福利国家福利实践的观察认为,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存在着以国家福利为基础或主导的补充关系。在发达国家,由于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水平降低,需要各机构举办相应的补充保险等作为弥补;职业福利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功能,许多机构提供的福利甚至可以满足其员工的多数社会服务需要。[29]陈银娥认为,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并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职业福利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功能,并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由于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在性质、目标、调节机制、系统性能、内容、经费来源、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区别,两者在福利供给方面,各自依据自身的职能特性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社会成员(或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单位自主兴办的职业福利构成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有益补充;但职业福利关注局部、本部门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缺陷决定了它远远不能取代社会福利,只能是社会福利的补充。[30]
仇雨临认为,在全球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中,政府都在尝试收缩其福利供给的边界;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政府在客观上需要各机构举办相应的补充保险来弥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承担福利责任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法定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并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起到积极有益的支撑作用。[31]
杨艳东认为,从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特色来看,二者之间也应当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职业福利的激励功能使其具有效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是社会福利难以比拟的;社会福利的普惠制度,弥补了职业福利过度重视效率而造成的社会差距,对社会发展起到公平作用,又是职业福利所无法具备的。发展职业福利不是为了替代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即使再发达,也不能完全替代职业福利的作用。[28]
杨燕绥认为,在信息多元社会下,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面对的社会风险也不断增加,而政府功能和国家责任局限性日益凸显,为此,政府需要利用法律约束和政策激励推动企业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建立员工福利计划,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其他需要的服务。[32]
(二)中国职业福利功能研究
计划经济时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形成了以职工福利为主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职工提供了全面的福利性保证,但最终导致企业成为“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型自给自足的社会,造成了政府、社会、企业角色严重错位,企业福利走向异化:性质异化、地位异化、功能异化、影响异化。此时,中国的企业福利实质上并非是企业的福利,而是企业办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将自己的社会职能强制转嫁给企业。[33]
陈银娥认为,在我国传统职业福利背景下,职业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主体,单位代替国家和社会承担社会保障职能。[30]杨艳东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职业福利成为国家-单位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承担了基本的社会保障职责,它实质上成为对社会福利的替代,而非用人单位的内部事务,中国这一时期的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28]
针对中国从旧福利制度向新保障制度的转换,改革过程不能极端,职工集体福利不仅不应被抛弃,而应让其有机会发挥其真正的功能。职工集体福利的存在对于职工和企业都是正当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占据着福利制度中无可替代的位置。[34]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需采用保障供给的混合机制,在有限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障机制,而发挥补充保障功能的典型保障计划即是员工福利计划,它可以使劳动者在基本社会保障之外获得补充保障,以改善劳动者丧失经济收入能力后的生活水平。[35]
中国的职工福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取向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的一种补充。[36]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原有的福利结构不利于员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福利需要的满足,为此,社会福利结构需要重构,社会化福利是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主体,职业福利作为企业自主兴办的福利则构成整个福利制度的有益补充。[33]政府将成为福利体系的第一主体,职业福利在发展定位上应作为福利体系的第二支柱,起到责任分担的作用;后者不应占据主体地位,而应关注其补充作用的发挥,与国家福利、民间福利共同构成福利体系的三大支柱。[28]
综合国内对于职业福利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替代关系的论点有待深入考虑。而对中国转型时期职业福利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则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关于国家福利与职业福利之间替代关系的考虑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实际上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组织手段,企业依附于政府。而职工福利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这种福利形态由国家强制举办,其项目的设置和水平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出发点是保证职工生活,维护社会稳定。[37]在这种国家-单位的福利模式下,国家成为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责任主体,企业仅仅是实施福利管理的具体机构。[38]在供给福利方面,企业鲜有独立性和自主决定权。
而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的替代关系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分别作为独立主体的基础上,一方主体的供给活动影响到另一方主体。但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与企业并没有相互独立,而是企业变成了政府的行政附属。虽然,企业也有对于政府的某些反馈影响,但是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政府决定了职业福利的项目设置和项目水平。“中国传统企业的福利与其说是一种企业福利,不如说是一种国家福利。”[39]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替代关系来概括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福利有失妥当,政府和企业本身就是一体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福利供给方式。如果存在替代关系,也是国家福利对职业福利的全面替代,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互动关系。
2. 国内学者对于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的补充关系形成一致观点
从以上国内学者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而言,两者形成补充关系是一致的观点:在基本社会保障的基础上,由职业福利作为第二支柱进行补充。
综上,对于职业福利的功能,虽然存在着补充理论、替代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之间的不同看法,但总体来看,支持补充理论的学者占据多数,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多事实论据,因而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对职业福利功能的判断或定位,决定了政府在职业福利发展及其与公共福利的合作机制方面的政策引导方向、力度、方式或方法。如,职业福利福利补充功能的确定,需要政府继续明确等等。
本文仅关注了职业福利与公共福利在功能上的补充关系,但是对于补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很少进行考量。其中,主要的原因多半在于职业福利项目的复杂性、广泛性,也在于相应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取。那么,要想进一步考察职业福利与国家福利之间补充关系的发展情况,需要对职业福利本身的性质和程度进行详细的了解,对其内容本身的复杂性进行解剖;这牵扯到对职业福利的界定和类型划分,需要学术界更多的探讨。
[1]Dahlberg, L. (2005).” Interaction between Voluntary and Statutory Social Service Provision in Sweden: A Matter of Welfare Pluralism,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arity? “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39(7), 740-763.
[2]Titmuss, R. M. (1958).”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earch for Equity”. In R. M. Titmuss. “Essayson‘theWelfareStat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p.34-55, 42.
[3]Mann, K. (2008). “Remembering and Rethinking the Social Divisions of Welfare: 50 Years On”.JournalofSocialPolicy, 38(1), 1-18.
[4]保罗·怀尔丁:《福利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福利理论渊源与蒂特马斯典范》,载《社会保障研究》,2009(2)。
[5]Pearson, M., & Martin, J. P. (2005). “Shouldweextendtheroleofprivatesocialexpenditure?”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23. Paris: OECD.
[7]Rein, M. (1996). “Is America Exceptional?The Role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M. Shalev (ed.),”ThePrivatizationofSocialPolicy?OccupationalWelfareandtheWelfareStateinAmerica,ScandinaviaandJapa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p. 27-43.
[8][爱尔兰]威尔皮·铁蒙恩:《新风险——在北欧福利国家还新吗?》,载[英]彼得·泰勒-顾柏:《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77~101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9]Yerkes, M., & Tijdens, K. (2010). Social Risk Protection in Collective Agre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European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 16(4), 369-383.
[10][日]武川正吾、佐藤博树:《绪论》,载[日]武川正吾、佐藤博树:《企业保障与社会保障》,李黎明、张永春译,6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11]Seeleib-Kaiser, M., Saunders, A. M., & Naczyk, M. (2010).ShiftingthePublic-PrivateMix:ANewDualisationofWelfar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The Dualisation of European Societies?” Green Temple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12]Esping-Anderson, G. (1996). “Conclusion: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the Social Policy Nexus”. In M. Shalev (ed.), “ThePrivatizationofSocialPolicy?OccupationalWelfareandtheWelfareStateinAmerica,ScandinaviaandJapa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p. 327-338.
[13][日]铃木宏昌:《欧洲的企业保障》,载[日]武川正吾、佐藤博树:《企业保障与社会保障》,李黎明、张永春译,202~219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14]Kramer, R. M., Kramer, R., & Seippel φ. (1992). “The Roles of Voluntary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Four European States: Policies and Trends in England, the Netherlands, Italy and Norway”. In S. Kuhnle and P. Selle (eds.), “GovernmentandVoluntaryOrganizations:ARelationalPerspective”, Aldershot: Avebury, pp.34-52.
[15]Theobald, H. (2012). “Combining Welfare Mix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Cas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Germany”.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21, S61-S74.
[16]Rose, R. (1986).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In R. Rose and R. Shiratori (eds.),Thewelfarestate:Eastand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39.
[17][英]约翰·斯图尔特:《历史情境中的福利混合经济》,载[英]马丁·鲍威尔:《理解福利混合经济》,钟晓慧译,27~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Powell, M., & Hewitt, M. (1998). “The End of Welfare State? “SocialPolicyandAdministration, 32(1), 1-13.
[19]Pinker, R. (1992). “Making Sense of 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SocialPolicyandAdministration, 26(4), 273-284.
[20][英]马丁·鲍威尔:《福利混合经济和福利社会分工》,载[英]马丁·鲍威尔:《理解福利混合经济》,钟晓慧译,1~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1]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载《社会》,2002(7)。
[22]Johnson, N. (1987). “TheWelfareStateinTransition:TheTheoryandPracticeofWelfarePluralism”. Brighton: Wheatsheaf.
[23][英]爱德华·布伦斯顿、玛格丽特·梅:《职业福利》,载[英]马丁·鲍威尔:《理解福利混合经济》,钟晓慧译,193~1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4]Johnson, N. (1999). “MixedEconomiesofWelfare—AComparativePerspective”, London: Prentice Hall Europe.
[25][加]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113~12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6]朱丽敏:《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述评》,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7]Seeleib-Kaiser, M. (2008).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ocial Policy?” In M. Seeleib-Kaiser (ed.), “WelfareStateTransformations:Comparative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1-14.
[28]杨艳东:《职业福利的社会功效与发展问题研究》,184~18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29]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26~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0]陈银娥:《社会福利》, 216~2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1]仇雨临:《员工福利概论》,15~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2]杨燕绥:《员工福利计划及其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载《中国金融半月刊》,2003(24)。
[33]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 227~231页、360~364页,76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34]闫海:《职工集体福利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载《云南大学学报》,2006(4)。
[35]李永忠:《社会保障结构与企业福利制度》,载《西部财会》,2007(12)。
[36]于景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福利的发展取向》,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3)。
[37]杨生勇:《中美日传统企业福利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日本研究》,2005(3)。
[38]成海军、陈晓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嬗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3)。
[39]刘昕:《福利是否需要全部货币化》,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1)。
(责任编辑:H)
Debates on the Function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DING Xuena
The functional judgment or positioning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strength and ways or methods of public policies in occupational welfare development, and its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public welfar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study their own or world countries within the scope of public welfare and occupational welfare function relationship, find that the complementary theory, substitution theory and the welfare pluralism theory have made a different judgment to the function of the occupational welfare. However, due to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principle of various welfare suppliers and the ability of welfare supplies besides the state to replace the government on the aspect of welfare supply, substitution theory and the welfare pluralism theory lack wide support. Therefore, supplementary function theory become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occupational welfare worldwide. Nevertheless, to give full play to supplementary function, occupational welfare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s itself with high complexity.
occupational welfare,public welfare,supplement,substitute,welfare pl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