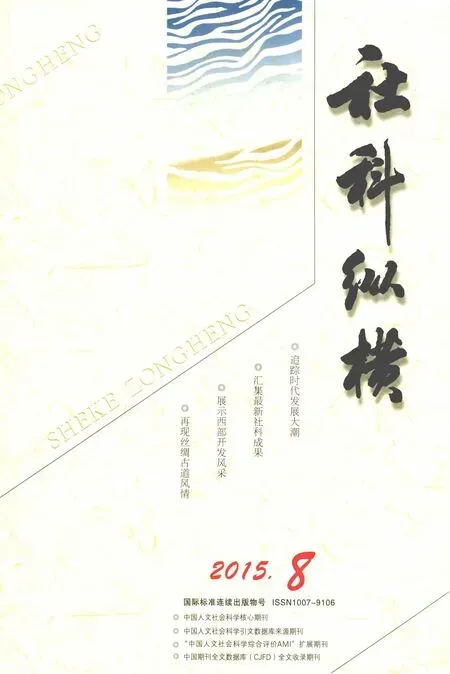宋代赘婿的财产继承权利
石 璠
(东莞理工学院政法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中国古代的继承,长期以来就将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连在一起,称为“承继”,承继人的资格受到严格限制,基于“鬼神不享非类之祀”的观念,只有同族之人才是正当的承继者,与之相连的家产的继承也被严格限制在族内。
赘婿一方面作为妻方之家庭成员,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赘婿作为异姓之人,缺少宗法血缘上的根据,其财产继承权利一直以来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宋代最主要的传世法典《宋刑统》中关于财产继承的法条完全没有提及赘婿,他的财产权依附于妻子。所幸这样一种与实际生活需要相悖的情形,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逐步地得到了改善,法律对赘婿的财产继承权利逐步地作出了规范,其财产继承权的大小与其所赘居的家庭男丁状况密切相关。
一、户绝财产之继承
在户绝的情况下,因为继承家产的男子缺席,赘婿的财产权利最有可能被显现出来,有关赘婿的继产问题也最早在户绝的情况下被提及。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因各地对户绝之家所遗财产的归属不断地发生纠纷,有大臣上书要求朝廷立法解决,其提议被朝廷采纳:
秘书丞知开封府司録参军事张存言:伏睹元年七月敕,户绝庄田检覆估价,晓示见佃户依价纳钱,竭产买充永业,或见佃户无力即问地邻,地邻不要方许无产业中等以下户全户收买勘会。今年春季后,来振东明诸县申:户绝状虽已依敕,内有相承佃,时年深理合厘革者,并是亡人在日已是同居,户绝后来供输不阙,或耕垦增益或邱圆已成,无赖之徒因为告诉,久居之业顿至流离,官司止过莫能,狱讼滋彰逾甚,况孤贫之产所直无多,劝课之方其伤或大。欲乞应义男、接夫、入舍婿并户绝亲属等,自景德元年以前曾与他人同居佃田,后来户绝,至今供输不阙者,许于官司陈首,勘会指实,除见女出嫁依元条外,余并给与见佃人,改立户名为主,其已经检估者,并依元敕施行。从之。[1](P5901-5902)
这时候,户绝之家的赘婿只要是自景德元年(1004年)起到户绝时止一直与妻家人同居佃田,并尽到了对妻之父母的赡养义务,即可以拥有对妻家财产的所有权了。这几乎是宋代法律首次对赘婿财产权作出的规定,由此,赘婿的财产权被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赘婿的无权地位得以改善。
但是,上述的法令对赘婿获得家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但要求赘婿“供输不阙”,而且对赘婿的同居年限做了严格的限制,从景德元年到天圣元年,前后十九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于妻家的赘婿才是合格的权利人。而且,更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法令似乎只有溯及既往的功能,它只给与了景德及以前成为赘婿的男子财产权,而没有承认景德以后成为赘婿的男子有这样的财产权,这使得很大一部分赘婿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到天圣四年(1026年)的时候得到了改善,国家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关于户绝财产的继承法规:
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丧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如无出嫁女即给与出嫁亲姑姊妹侄一分,余二分若亡人在日,亲属及入舍婿、义男、随母男等自来同居营业佃莳至户绝人身亡及三年已上者,二分店宅财物庄田并给为主,如无出嫁姑姊妹侄,并全与同居之人。若同居未及三年及户绝人孑然无同居者,并纳官。庄田依今文均与近亲,如无近亲即均与从来佃莳或分种之人承税为主。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1](P 5902)
在有出嫁女或出嫁亲姑姊妹侄时,在妻家居住三年以上的赘婿即可得到家产的三分之二,若无以上女性,他就可获得全部的家产了,这是赘婿对妻家财产最大份额的权利了。此时,法律所给予的赘婿对户绝之家的财产权更具有合理性,无论是对同居时间的要求上还是继承财产的份额上。这种法律的变化主要考虑的仍然是赘婿对妻家所作的贡献,给予同居三年者一定的财产,而不及三年的什么也得不到,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考虑到赘婿对妻家实际所作贡献的大小,对那些经营妻家财产而使财产增值达到一定数额的赘婿,国家降低了其获得妻家财产的同居三年以上的时间要求:
三省言:看详元符户令,户绝之家,内外亲同居记年不应得财产。如因藉其营运措置及一倍者,方计奏裁,假如有人万贯家产,虽增及八九千贯文,犹不该奏,比之三二百贯财产增及一倍者事体不均。兼昨来元佑敕文但增置及一千贯者奏裁之法,今参酌重修虽不及一倍而及千贯者,并奏裁之。诏依仍先次施行。[1](P5904)
因此,即使赘婿在妻家户绝之前,没有在妻家居住三年以上,但是依靠他的经营使得妻家财产增值一倍或者千贯以上的,他有权通过法定审批程序获得部分的财产。而到南宋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不需要经过特殊的批准手续即可获得一定的财产了:
在法: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2](P215-217)
法律发展到这里,赘婿对妻家财产的继承权已经比较合理和有保障了,法律对权利的直接规定使得他成为了妻家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但是,赘婿获得上述的权利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户绝之人没有留下关于其遗产处分的遗嘱。如果户绝之人留有遗嘱,家产如何继承将完全按照遗嘱的要求进行了,此时,赘婿如果不是遗嘱人选中的继承人的话,他就无权对妻家财产作出要求。但存在希望的是,毕竟赘婿对妻家作出了贡献,对妻之父母尽了赡养的义务,他也可能因被遗嘱人喜爱而被选为继承人,此时,他对妻家的财产继承就要按照另外的方式进行了。
宋代法律自《宋刑统》开始即承认了户绝人的遗嘱权利,之后的法律都坚持了《宋刑统》的精神,户绝条件下遗嘱继承的规则优先于法定继承的规则适用。赘婿作为遗嘱继承人能够继承多少财产,除了取决于遗嘱人所遗嘱的份额外,还要受到宋代遗嘱规则的限制。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遗嘱继承的最高额,继承人不能超出这个限额获得财产,即:其得遗嘱之人,依现行成法,止合三分给一。[1](P5906)也就是说,通过遗嘱的方式赘婿最多只能获得三分之一的家产,这与他在户绝条件下适用法定继承时获得的份额要少得多。但无论如何,这也是赘婿继承妻家财产的一种途径。
二、非户绝财产之继承
在父亲死后有儿子存在,家庭处于非户绝的情况下,赘婿的继承权利以及继承份额将因为与其并存的这个儿子是亲生子还是养子而有所不同。
1.赘婿与亲生子并存
一个家庭在父死有子的场合,儿子成为当然的继承人,这是同居共财的家庭里继承发生时最自然的结果。由于赘婿往往是在一个家庭无子时招入的,因此,子与赘婿并存的情形是不太典型的,法律最初也忽视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一直没有规定赘婿在这种情况下的继承权。虽然北宋的社会中,赘婿与子均分家产已经是川峡之民俗了,但法律对此未作承认,这使得赘婿此时在法律上完全处于无权的状态。为消除这种不合理,遗嘱在此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法律规定遗嘱只在户绝或无承分人的场合才发生,但是习惯上,亡人特别是父祖的遗嘱权受到人们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乃至法官的判案过程中,非户绝情形下父祖所立的遗嘱并没有因为家庭中有法定承分人而失去其效力。这种现实状况的发生也是与中国古代家庭财产的共财性质相连的。在父子共财的家庭中,家长是整个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他拥有对家产的处分权,对家产进行遗嘱处分是他行使其处分权的表现。因此赘婿通过遗嘱方式继承财产成为可能。
这种遗嘱继承的方式也是赘婿在此时获得继承权的唯一途径。因此有赘婿为获得财产伪造岳父遗嘱的案件发生,这时法官需要证明的只是遗嘱的真伪,并不需要说明被讼之人有没有继承权:
县吏死,子幼,赘婿伪为券冒有其赀。及子长,屡诉不得直,乃讼于朝。下简劾治,简示以旧牍曰:“此尔翁书耶?”曰:“然。”又取伪券示之,弗类也,始伏罪。[3](P 9927)
在此案中对遗嘱效力的否定就是对其继承权的否定,郎简只需要证明赘婿所持书契是伪造的就可以证明他没有继承权。
《清明集》中的另一个案件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遗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后财产合作三分,遗腹子得二分细乙娘得一份,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应龙为人子婿,妻家见有孤子,更不顾条法,不恤孤幼,辄将妻父膏腴田产,与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标拨,天下岂有女婿中分妻家财产之理哉?县尉所引张乖崖三分与婿故事,即现行条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东尉,索上周丙户下一宗田园干照并浮财帐目,将硗腴好恶匹配作三分,唤上合分人,当厅拈阄。[2](P 277-278)
赘婿李应龙“妄作妻父、妻母标拨”的行为充分说明了赘婿此时没有对妻家财产的法定继承权,想要有所“占据”只有通过妻之父母的遗嘱,遗嘱是赘婿获得妻家财产并为官方及妻方族人承认的必要条件。
但是,考虑到非户绝情况下遗嘱继承的发生只是一种习惯的约定,虽然人们出于对遗嘱人财产权的尊重往往会按照遗嘱的要求处理遗产,但是,这种遗嘱的效力毕竟没有法律的保障,而且在这种遗嘱的内容过分牺牲了亲子的利益时,将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它的效力也可能受到置疑。所以,即使赘婿真的拥有了真实的岳父的遗嘱,他能否据此获得财产继承权仍然是不肯定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因此而发生的争议:
御史中丞张咏为工部侍郎,知杭州……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才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咏览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傥遽以家财十之七与子,则子死于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给其子,馀三给婿,皆服咏明断,拜泣而去。[4](P941)
此案中,赘婿确实持有真实的岳父之遗嘱,但是,法官显然认为这种遗嘱是不合情理的,它使得法定的继承人——亲子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侵害,因此,法官以主观的推测否定了遗嘱的字面意思,而以另外的方式处理了遗产。虽然,此案中的赘婿最终仍然继承了十分之三的遗产,但是,法官这种改变遗嘱内容的行为本身足以说明赘婿在这种非户绝情形下依赖遗嘱继承家产的不稳定性。
当然,这种不稳定除了归因于非户绝情形下的遗嘱缺乏法律根据外,还与宋代遗嘱的一般效力相关。因为在提倡同居共财的儒家社会里,家产在家庭内稳定地世代相传是人们的理想,法定的继承方式给了家产流向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方向,而遗嘱继承是家产在世代间流动的一个变数,人们因此对遗嘱继承总是怀着谨慎的态度。对有效遗嘱的要求从“证验分明”到“听自陈,官给公凭”,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化。即使是在正常的遗嘱人得行遗嘱的场合,法官在断案过程中也不一定按照遗嘱的处分方式裁判财产的归属,往往做一些调和,力求双方的和睦和利益的均衡。而在很多最后依遗嘱而判的案件中,法官也通常会给出大段的情理道德的说教,极力为这样的处分行为找到道德的根据,法官不是从法律上确定,而是从情理上确定这种处分行为的有效性。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遗嘱在处分财产时的局限。
所以,在一个有子招赘的家庭,继承发生时,在法律上赘婿被排除在外,习惯上对亡人遗嘱的尊重是赘婿在这样的家庭获得财产的唯一希望,但这显然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宋代遗嘱效力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得立遗嘱人在未立遗嘱而亡的情况,赘婿借助遗嘱来取得部分财产是不确定的,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出现任何一种差错,这种可能性就会立即消失。
2.赘婿与养子并存
无子的家庭以招赘婿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而以收养养子的方式来解决宗祧继承问题,赘婿与养子并存的家庭是较为常见的。他们对家庭财产的权利划分不同于赘婿与亲生子那样绝对,养子虽然承担着延续宗之血脉的职责,但他本身也是家庭中的特殊成员,与亲子比较是与赘婿一样处于弱势的人,他与赘婿之间的权利存在一种相抗衡的可能。尤其在父亲死后立嗣的场合,赘婿可能获得岳父的遗嘱,并以此方式对财产提出要求,而养子此时对家产又有法定的继承权,两者矛盾不可避免。法律为解决这样的矛盾不断作出调整,因此有了“赘婿与养子均分”的法律出台: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四月十九日,知涪州赵不倚言,契堪人户陈诉,户绝继养,遗嘱所得财产,虽各有定制,而所在理断,间或偏于一端,是致词讼繁剧。且如甲之妻,有所出一女,别无儿男。甲妻既亡,甲再娶后妻,抚养甲之女长成,招进舍赘婿。后来甲患危为无子,隧将应有财产遗嘱与赘婿。甲既亡,甲妻却取甲之嫡侄为养子,致甲之赘婿执甲遗嘱与手疏,与所养子争论甲之财产。其理断官司,或有断令所养子承全财产者,或有断令赘婿依遗嘱管系财产者。给事中黄祖舜等看祥,欲下有司审订申明行下,庶几州县有似此公事,理断归一,亦少息词讼之一端也。
诏:祖舜看祥,法所不载,均(今)【 分】给施行。[1](P5906)
需要注意的是,赘婿与养子均分的权利只在一千贯家产以内有效,超过一千贯的需要按另外的比例分割: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权知沅州李发言:近降指挥遗嘱财产养子与赘婿均给不行误。若财产满一千五百贯其得遗嘱之人依现行成法止合三分给一,难与养子均给,若养子赘婿各给七百五十贯即有碍遗嘱财产条法。乞下有司更赐参订。
户部看详:诸路州县如有似此陈诉之人,若当来遗嘱田产过于成法之数,除依条给付得遗嘱人外,其余数目尽给养子,如财产数目不满遗嘱条法之数,合依近降指挥均给。从之。谓如遗嘱财产不满一千贯若后来有养子合行均给,若一千贯以上,给五百贯,一千五百贯以上,给三分之一,至三千贯止,余数尽给养子。[1](P5906)
如此一来,赘婿与养子的继产矛盾就得以解决了,虽然限制了赘婿的继产份额,但毕竟将这种均分的方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赘婿持遗嘱而继承财产就有了一份法律的保障了。但此时赘婿的继承权仍然属于遗嘱继承的范畴,赘婿与养子均分家产只发生在赘婿持有亡人遗嘱的场合,这无疑又使赘婿的继承权回到了上面关于遗嘱效力的怪圈中。值得庆幸的是,或许是法律没有执着于这一点,在以后的发展中作出了改变,也或许是法官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没有严格要求遗嘱的存在,赘婿没有遗嘱而继承了家产的案件在南宋法官的判词中出现:
蔡氏两房无子,杨梦登、李必胜,赵必怈分别为这两房赘婿,后因为立嗣之事发生争议,法官判决蔡氏以拈阄的方式解决立嗣纠纷,随后对其财产分割方式作出了这样的处理:
合以一半与所立之子,以一半与所赘之婿,女乃其所亲出,婿又赘居年深,稽之条令,皆合均分。[2](P205-206)
此时法官并没有要求赘婿持有有效的遗嘱,事实上也并不存在这样的遗嘱,而法官仍然采用了均分的处理方式,这至少可以说明,赘婿与养子均分家产已经不需要有遗嘱的支持了,他已经从遗嘱继承人的身份变为法定继承人了,其财产继承权更为稳定。
另外一个赘婿没有遗嘱而可与子分割家产的情形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即赘婿为保甲之时:
义子孙、舍居婿、随母子孙、接脚夫等,现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亲属给半。[4](P8009)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既不要求有遗嘱,也不论其面对的是亲子还是养子,赘婿都有分得与其相比一半家产的权利。这可以看作是赘婿的一种特殊的法定继承权。
三、赘婿异居后权利的变化
赘婿之所以可以继承一部分的妻家财产,是基于他居于妻家,在妻家劳动,对妻家作出了贡献的事实,这种继承权实际是对他的劳动的一种报酬。一旦他离开了妻家归宗或者出外居住,他的这种基于同居而发生的继承权就会丧失。宋代的一份判词对此表现得非常充分:
刘传卿有一男一女,女曰季五,男曰季六,季六取阿曹为妇,季五娘赘梁万三为婿。传卿死,季六死,季五娘又死,其家产业合听阿曹主管,今阿曹不得为主,而梁万三者乃欲奄而有之,天下岂有此理哉!使季五娘尚存,梁万三赘居,犹不当典卖据有刘氏产业。季五娘已死,梁万三久已出外居止,岂可典卖占据其产业乎?[2](P236-237)
这里,赘婿梁万三出外居住已久,他对家产非但没有继承的权利,典卖处分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其家产应由寡妇阿曹来管理。法官的这种处理很明显地体现了赘婿可以继承妻家财产的根据,即他的同居劳动的事实和对抚养赡养义务的履行。梁万三出外久居就没能够尽到对妻家的义务,因此无权对财产提出要求。虽然寡妇与赘婿都是家庭中处于弱势的人,但是,因为守志的寡妇代表着丈夫的人格,又有“夫亡妻为主”的法律支持,寡妇此时的财产权利就优于异居的赘婿了。
当然,如上所述,在赘婿为保甲的特殊场合,赘婿在与妻家异居之日可以分得一部分的财产,这可以看做是国家对于保甲赘婿为国家服务的一种补偿吧。
四、结语
综合来看,宋初法律对赘婿财产权利的漠视状况经过不断地发展得到了改善,到南宋时其继承权已经较为合理了。但由于儒家“孝道”伦理和家族观念的影响,抛弃本生父母,以异姓人身份居于另外一个家族的赘婿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仍然是当受鄙夷的一类人,因此,赘婿对妻家财产的继承权利表现出明显的受制约性和不稳定性。
1.受制约性。家族主义、义务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精神所在,维护家族伦理秩序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是法律的宗旨,一切权利和自由只有在不超越家族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承认和保护。无论是户绝还是非户绝情形下,赘婿想要获得对妻家财产的继承权首要条件就是对妻家有所贡献,要“居于妻家”、“对妻家之尊长供输不阙,尽了赡养义务”,一旦赘婿离开妻家出外居住,就丧失了对妻家财产的继承权。其财产继承权利明显受到家族利益的制约。
2.不稳定性。这主要表现在赘婿依遗嘱继承财产的情形下。对于同居共财的封建大家族来说,遗嘱继承的方式最有可能使得家族财产“外流”,因此,在强调家族利益的中国古代,对于遗嘱继承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赘婿能否依遗嘱取得财产除了受到法律关于可否遗嘱处分财产以及遗嘱处分财产限额的约束之外,还要受到非法律的情理道德的约束,其所持遗嘱的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效果可能会因为法官主观的情理道德的说教而大打折扣。
到了元代,赘婿的法律地位有了较大地提高,主要是法律关注的增多和相关制度的规范,相比宋代对赘婿财产继承权利大多以临时性的部门法规或者法官的解释来贯彻,元代在最重要的法典中对赘婿的权利作出了明确。这种做法到明清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赘婿在法律上的地位稳定了下来。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不注撰者.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