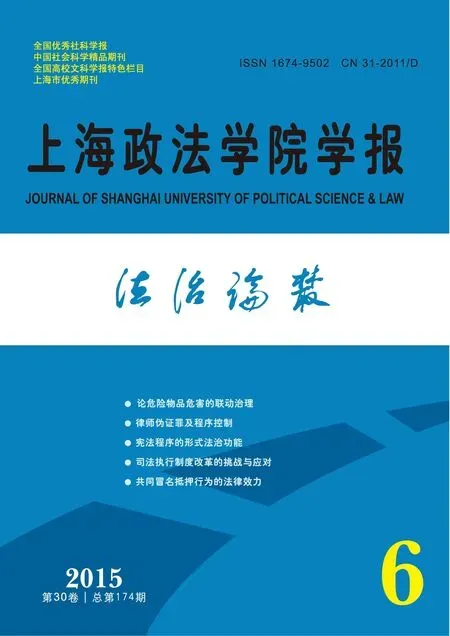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追加执行的困境与突破
张 欢 洪 宁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追加执行的困境与突破
张 欢 洪 宁
一、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追加执行的现实困境
股东追加执行,系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变更的一种,其理论渊源在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裁决既具有既判力,又具有执行力,且二者具有一定主观范围扩张性。①所谓主观范围的扩张,指判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所涉及的人的效力范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扩张。参见张卫平:《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予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第81~85页。在司法实务中,当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且作为公司投资者的公司股东,存在对公司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则可以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由该股东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但随着2013年《公司法》的修订,在执行程序中对股东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缺少了必要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股东追加执行制度面临较严重的实践困境。
(一)股东出资不实作为追加条件存在虚化风险
在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中,对于股东出资不实的认定,一般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首次缴纳出资未达到法定标准,二是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出资,三是股东货币出资未达到法定最低限。凡股东存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一者,可认定股东存在出资不实的行为,继而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但随着《公司法》的修订,作为判断标准的上述三方面均受到了严重影响,使股东出资不实这一情节难以认定。
1.首次缴纳出资限额取消造成注册资本不实缺乏认定依据
投入注册资本不实是股东出资不实的重要形式。在《公司法》修订前,股东出资要满足首次出资额高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和注册资本2 0%双重条件。若股东出资未能达到上述标准则一般可以认定为股东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存在出资不实的行为。但新《公司法》取消了一般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的限制,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关法律、法规对最低注册资本有特别规定的,仍从特别规定。但实际上,随着有关管制的放开,此类有特别限制的公司类型已屈指可数。也将股东最低首次出资额的法定限制彻底取消,①均交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再强行干预。②随着这两项限制的取消,以形式审查为主的执行程序缺少了直接认定股东投入注册资本不实的依据,极大限制了股东追加执行的有效适用。
2.缴纳出资期限由股东约定造成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难以认定
除首次出资不实外,股东追加执行制度还将股东未按约定或法定期限缴纳认缴出资作为股东出资不实的认定标准之一。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将股东认缴股份后的出资期限完全交由股东约定。如果公司设立时股东由于某种原因未对出资期限做出具体约定的,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应如何判断,已成为司法实践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③甘培忠、吴韬:《论长期坚守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核心价值》,《法律适用》2014年第6期,第92页。作为司法实践的一环,股东追加执行也面临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认定的困局,在没有进一步规定的情况下,股东出资期限的放宽严重影响了执行程序中队股东出资不实情节的认定。
3.出资形式放宽造成出资不实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收窄
根据2005年《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货币出资应当不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3 0%,这是从非货币出资难以估价,不利于保护公司交易相对方或债权人的角度进行的限制。执行程序秉承这一理念,将股东货币出资不足也作为出资不实的情况之一。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将货币出资最低额的限制予以排除,随着出资形式限制的取消,股东追加执行显得更为困难。
(二)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增添障碍
实践中股东追加执行制度对于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主要着眼于形式审查,以必要的登记材料和公司设立前置程序为依据。伴随《公司法》修订而来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认定抽逃出资行为依据的形式证明证据也随之“消亡”,为基于抽逃出资行为认定而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增加了障碍。
1.营业执照不再记载实收资本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困惑
营业执照记载的公司基本信息具有极强的对外公示效力,是对公司情况和自身实力的彰显,也是股东对其履行了相应义务的对外承诺。因此,当公司将其从股东获得的实收资本登记于营业执照上时,即相当于股东承诺已将相应资本投入公司。若此后公司资本低于实收资本,则可以认定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可以对股东追加执行。营业执照上实收资本的登记实际上起到了证明股东抽逃出资与否的作用。但随着工商登记制度的改变,实收资本不再作为营业执照的记载事项。对于法院而言,丧失了判断股东抽逃出资的最简单明了的标准。要如何在申请人、法院执行机构间平衡证明责任的分配,成为横亘在执行实务面前的难题。
2.验资程序的取消造成抽逃出资缺乏必要对照
《公司法》修订后,不但营业执照不再记载实收资本,公司设立及增资时的验资程序也将随认缴制的实施而取消。但在新《公司法》框架下抽逃出资的概念仍然存在,验资制度的取消并不必然杜绝现实中抽逃出资的现象,④林晓镍、韩天岚、何伟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下股东出资义务的司法认定》,《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68~69页。反而对执行程序中认定股东抽逃出资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认定股东存在抽逃注册资本过程中,验资程序往往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价值。在程序上,其成为股东财产与公司资本界分的标准,经历验资程序后股东从公司抽取财产的行为一般就认定为抽逃出资;在实体上,验资程序确定的公司实收资本数额成为确定股东抽逃数额的依据,继而确定是否应对股东予以追加。但随着验资程序的取消,上述程序与实体依据均消失,既有的实务操作标准失去了存在基础,必然造成实践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据不清、标准不明。
二、理论与实践冲突下股东追加执行困境的根源分析
(一)股东追加执行中效率与规范价值平衡的摇摆
1.股东追加执行制度源起于效率追求下对法律渊源的突破
在法律渊源方面,股东追加执行一般适用《执行规定》第8 0条的规定。但该规定实际是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的规定,而非对公司股东追加的直接规定。但在实践中,对《执行规定》第8 0条进行扩张适用,将公司股东视同开办单位,继而将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扩张为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作为追加执行公司股东的条件,已成为普遍的选择。①如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追加出资不实股东为被执行人已体现在相关案例中,参见孟德楷、李福恒:《公司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过程中追加出资不实的信托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法律问题——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案评析》,《中国法律》2013年第6期,第49页;金星、高中营:《执行程序中对增资不实股东的追加》,《人民司法》2012年第24期,第54页;而有关地方司法文件也对基于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而将股东追加执行作了相应规定,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北京市高、中级法院执行局(庭)长座谈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关于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这是在当前公司制度高度发展,公司纠纷普遍存在的背景下,民事执行程序追求债权实现最大化、高效化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②沈志先:《强制执行》,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也充分体现了执行程序适应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惩处规避执行行为的需要。③金星、高中营:《执行程序中对增资不实股东的追加》,《人民司法》2012年第24期,第53页。但必须承认,《执行规定》第80条中的开办单位与当前公司制度意义下的股东并不完全等同,“单位”这一概念未能包含自然人股东;④朱伟:《关于‘执行规定’第80条的理解、适用及修改建议》,http://www.shezfy.com/view.html?id=6517,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网,2015年2月12日访问。“开办”这一行为与设立或投资公司也未必能够等同。基于效率原则下的股东追加执行,存在类推适用法律渊源之嫌。
2.规范制约下对股东追加执行的自我限制
正由于股东追加执行制度的产生,是对原有法律渊源的扩张适用,是在实践中对已有规范的突破适用,若对该制度恣意使用,将存在滥用的可能,违背执行程序优先实现申请执行人权利,兼顾保护被执行人合法权利的目标。⑤杨海超、李欣:《执行程序中的裁量权及其规制》,《人民司法》2014年第19期,第78页。因此,基于规制执行权行使的需要,在股东追加执行制度的实际适用过程中,对于股东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行为的审查,司法机关采取了自我设限的态度。即对上述情节的认定,一般局限于形式审查,以能够直接体现股东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证据,如营业执照登记;及法定的必要出资标准,如最低出资额、出资期限和货币出资底限等为基础,一般不能运用审计、鉴定等司法手段查明事实,也不通过组织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追加股东质证后进行事实认定来审查,实际上自我摈弃了司法审查在股东追加执行过程中的主动查明权能。
正是在这种法律渊源突破与自我权能限定的平衡和摇摆中,伴随着《公司法》修订对一系列赖以依据的法定审查标准的取消,既有的股东追加执行制度显然难以适应法律基础和客观实际的巨大变化,自然陷入适用困境。
(二)鼓励创新价值冲击与司法谦抑性的双重影响
《公司法》修订降低公司设立门槛、进一步放宽市场、鼓励投资创业,开拓投资资源,推动公司设立与发展目的极为鲜明。①蒋安杰:《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解读与思考》,《法制资讯》2014年第3期,第28~29页。虽然从长远角度而言,有助于倒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速。②张伯晋:《新公司法倒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速》,《检察日报》2014年3月8日。但是,司法实务需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在相应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背景下,为了最大限度兑现胜诉方的合法权益,执行程序需要的是加大制裁和打击拒执行为力度,与目前《公司法》鼓励创业、强化股东自治的修法理念必然冲突。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体现了加快政府职能改变,激发市场活力的需要,也已通过修法后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体现出其积极意义。③成慧:《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专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人民日报》2014年8月24日。司法裁判无法脱离于社会环境。在市场主体制度已经跟随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尊重社会、经济环境现状,限制适用股东追加执行,是司法机关的主观判断受到价值理念冲击后的主观必然。
此外,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基于各种原因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谦让与自我克制,是司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④陈道英:《浅议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原则——兼论与司法谦抑(judicial passivism)的关系》,《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47~148页。面对因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而来的股东追加执行基础的动摇,认可具有更高层级的《公司法》的效力,对司法解释进行限制适用,对股东追加执行予以限制使用乃至搁置,是司法谦抑性原则下,司法机关面对公司法律制度变革的客观必然。
三、股东追加执行与公司资本制度价值契合下的制度完善路径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追加执行之所以出现适用上的困局,原因一是在于其承载的高效保障公司债权人价值在面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鼓励商业创新理念面前,司法机关尚未充分平衡二者的冲突与矛盾,造成制度功能的暂时搁置;二是《公司法》修订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一系列变更,使股东追加执行审查中的事实认定丧失了部分标准,造成了实践中的困难。因此,需要对股东追加执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契合点,继而完善和改进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使之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债权人保护与交易安全保障的价值契合
在公司制度中,除了公司、股东外,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债权人也是这一制度的主体。因此,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除了要保障公司自由开展业务,鼓励股东充分投资,也要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在这一点上,股东追加执行对债权人的保护显然公司制度关于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契合。
1.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不免除股东确保出资真实和资本维持的义务
从公司资本制度的原则看,《公司法》的修订只是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而非对法定资本制的颠覆,①蒋安杰:《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解读与思考》,《法制资讯》2014年第3期,第28~29页。包括出资真实和确保公司资本维持在内的各项股东出资义务并未被取消。②张伯晋:《新公司法倒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速》,《检察日报》2014年3月8日。即使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的门槛未作规定,现实中也仅出现了所谓“一元公司”,而没有注册资本为零的公司“诞生”,这意味着法律仍然为净资产设立了维持底限,净资产必须要秉持刚性的资本维持理念。③杜军:《公司资本制度的原理、演进与司法新课题》,《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第7页。可见,在修订后的《公司法》框架内,股东出资义务即是一种约定义务,更是一种法定义务,且股东的出资义务不仅指向已届履行期的出资,也覆盖未到履行期和根本没有履行期的所有出资。④赵旭东:《资本制度变更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20~22页。一旦股东未按约定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或在履行了出资义务后对出资予以抽逃,仍是对公司制度下法定资本制的侵害,更伤及基于公司法定资本而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理应对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无论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与否,基于股东出资责任产生的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仍有存续的基础。
2.给予债权人足够救济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
没有交易安全,债权人必然缺乏安全感,寻求债权的担保与保全手段,交易成本自然上升,商事流转必然窒息,投资机会必然锐减。反之,若交易安全获得法律保障,则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活络,投资者、企业与消费者皆大欢喜。⑤刘俊海:《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认识误区及辨析》,《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第25页。而要实现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给予债权人必要的安全感,就需要给予债权人必要的救济途径。可以说,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永远是公司法律制度的“主旋律”之一,放弃或动摇对债权人保护的目标,即是在撼动公司大厦之基础。⑥朱慈蕴:《公司资本理念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31~134页。巩固和完善股东追加执行,正是强化债权人救济诸多途径中的一种,通过优化股东追加执行,能够及时兑现公司债权人的胜诉权益,保障《公司法》维护交易安全理念的落地生根。
3、强化股东责任是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超前理念与社会诚信现状差距的必然选择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转“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的改革模式,更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因而最为核心的莫过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⑦陈静骅:《自贸区背景下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知识经济》2014年第5期,第31页。完善社会诚信机制,特别是公司信用体系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及相应修法对公司及其股东的监管模式革新,虽凝结着立法者的超前理念和远见卓识,但与当前的社会诚信现状仍有不小的差距。通过发挥股东追加执行的作用,强化股东责任,充分利用包括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全国联网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等社会信用体系公示平台,对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行为的股东进行相应的信用惩戒,将有助于帮助其他市场主体了解上述股东及公司的真实信用水平,保障公司法律制度有序运行。
(二)股东追加执行的制度完善进路
在解决了股东追加执行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带来的理念冲突后,正视股东追加执行在实践中的不足之处,顺应修法带来的实践挑战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要从规范适用条件、明确股东追加审查方式和完善作为追加依据的事实认定标准等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规范股东追加执行的适用条件
首先,应当严格依照《执行规定》第8 0条的规定,以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作为股东追加执行的前提。否则,就可能出现无视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设计的情况,“从而否定现有的民事交易秩序与安全”。①沈志先:《强制执行》,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对于该条件的证明,由于股东的追加执行应当以被执行人人无财产清偿债务为前置条件,因此进入审查是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程序首先应当掌握被执行人人无财产清偿债务的证据。但此类证据的获取具有较强的职权性,其条件是否成就也直接关系到追加程序的合法性,因此法院应当承担必要的审查责任。此外,由于股东的追加执行实际上是债权人享有代位行使公司对股东追责的权利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②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12页。申请人显然应当对其行使权利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也应当由申请执行人提供必要的证明依据,作为法院审查结论的旁证。
其次,应当严格遵循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的适用前提。执行当事人的追加属于执行裁判事项,具有准审判权的特性,因此,在追加被执行人的过程中,执行机构应当保持被动,只有当事人提出申请才进行裁断,减少依职权主动追加被执行人的适用。③谭秋桂:《论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程序构建》,《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31~132页。特别是股东的追加执行,由于存在对公司有限责任原则的突破,更需要严格适用。这既是尊重当事人私权、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也是维护《公司法》修订制度创新取向,寻求公平保护与制度创新平衡的要求。
2.明确追加执行公司股东申请的审查方式
对追加执行股东申请,法院应当采取有限度的实体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申请,应当按照执行异议审查的方式进行。作为执行裁决权的体现,执行异议审查显然能够,也应当涉及一定的实体审查事项。且如果执行裁决部门完全采取形式审查标准对追加执行公司股东申请进行审查,则将法院的审查范围等同于申请执行人能够通过信息公开获取的信息范围,这种审查将是无意义和重复的,法院的审查程序将失去其制度价值。
同时,有限度的实体审查意味着法院的审查范围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因为债权人作为申请执行人,除了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外,还可以基于代位权直接通过诉讼途径向公司股东主张权利,以实现自身债权。④杜军:《公司资本制度的原理 演进与司法新课题》,《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第11页。若允许对追加执行公司股东申请采取无限制的实体审查,将模糊执行程序审查与诉讼程序审理之间的界限,从而超越生效裁判既判力和执行力扩张的范围。
为了充分确保对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申请的有限度实体审查,就应当做好执行程序审查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股东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行为或不能形成充分确信的,不宜直接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以告知申请执行人另行诉讼确认权利为宜。对于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情况复杂的,如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股东均存在上述行为或被执行人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往往涉及比较复杂的事实判断,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可能造成较大影响,也应当采取诉讼确权前置的模式,裁定终结审查程序,中止执行,告知申请人另行提起诉讼。
3.完善作为追加依据的事实认定标准。
完善认定公司股东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标准,就是要根据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形式依据不足的现状,合理分配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追加的公司股东之间的举证责任,充分完善审查制度。
一是应当采取适当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于股东出资形式、出资内容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司内部经营事项,他人很难得知。如果简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对申请追加人而言过于严苛,可以在申请执行人提供合理证据的前提下,由被申请追加股东承担 证明出资到位或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①金星、高中营:《执行程序中对增资不实股东的追加》,《人民司法》2012年第24期,第54页。申请执行人提供合理证据的认定,一方面是已提供了证明被执行人无财产或剩余财产不足以偿还剩余债务的证据,另一方面是就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提供了初步证据和线索。
二是对于未届缴纳期限的股东认缴出资,随着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缺乏可供执行财产,自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起,缴纳期限当然届满。因为《公司法》第3条既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公司债务,又要求股东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已实缴的出资和认而未缴的出资均属于公司责任财产范围,债权人可要求该股东向公司提前缴付来保障自身债权。②李志刚:《公司资本制度的三维视角及其法律意义》,《法律适用》2014年第7期,第95页。因此,当法院经审查确认公司股东尚未缴纳出资,且经催缴后仍未缴纳的,可以认定股东存在出资不实的情节,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三是对于股东首次出资是否到位的认定,应当由法院依职权,查阅被执行人公司章程或设立协议后确定。由于股东对公司出资义务一般均由公司章程或设立协议约定,因此,首先查阅被执行人公司章程或设立协议,是明确股东究竟对公司承担何种出资义务的基础。对于上述文件明确了股东应缴纳出资额而股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相应出资义务的,应当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认缴出自范围内承担责任。
四是对抽逃出资行为应认定为股东出资后再对公司财产进行处分行为。随着股东向公司出资,其个人财产已转化为公司财产,股东个人不得对公司财产进行处分。因此,应当对《执行规定》第8 0条的“注册资金”进行扩大解释,既包括股东出资资本,也包括全部注册资本在内的其他公司资产。除非其能够证明已获得公司授权,只要股东存在对公司财产进行处分,就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行为,予以追加。
总之,《公司法》修订带来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追加执行股东的限制,为加大执行力度、破解“执行难”带来了一定障碍。但是,根据立法本意,对执行中相关规定进行合理解释,合理完善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从而寻求债权人利益公平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平衡,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需要根据执行工作实际加以实践和进一步思考。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