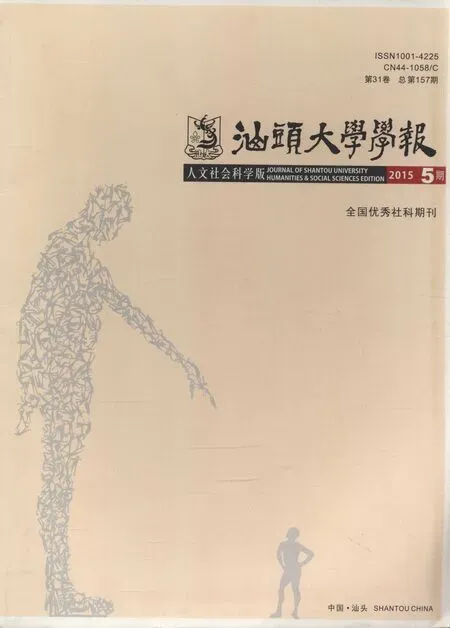关于“意义”的四种叙事——王安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再解释
王军
(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9)
关于“意义”的四种叙事——王安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再解释
王军
(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9)
新时期小说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非常丰富和个性化,而王安忆的“意义”自觉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新时期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通过对现实生活和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王安忆的小说建构出了四种关于“意义”的叙事:审视未来,反思传统,追问性爱,探求纯粹精神。从时间的视角来说,这四种“意义”叙事隐含了新时期小说的基本意义脉络。
王安忆;新时期;意义叙事;时间意识
人类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究历史由来已久,这一历史在现代社会的推动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意义”不是一元的、绝对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而且更具有现代意味的是,充满困惑、迷失和自我否定的意义寻找过程,代替了寻找到某种意义这个结果,成为意义发现的典型符号。从这个角度说,新时期文学无疑很精彩地诠释了这一现代特征,程文超曾经用“意义的诱惑”来总结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意义情结[1]。实际上,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我们都看到了众多作家在意义的诱惑下进行着多样化的文学叙事,而王安忆的小说把个体的独特性和时代的普遍性融合在了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发现新时期小说“意义”道路的范式样本。
新时期的王安忆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其“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2]但是,王安忆对自己的“多变”却另有一种表述:“评论家们说我是在求新求变。其实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老老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循序渐进。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地变化”。[3]局外人看到“求新求变”,自己却只是“老老实实”,要对这个矛盾做出合理化的解释,有必要追溯到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和意识——在丰富的意义大世界中不断寻找独特的道路。正是因为这种意识的自觉存在,王安忆在新时期初、中、后三个阶段,通过对现实生活和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和执着探求,通过四种颇具代表性的“意义”叙事,完成了个体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一、“向前看”及其自我审视
王安忆以“雯雯”系列小说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坛获得声誉。与社会转型状态相呼应,新时期初期的文艺各领域都弥漫着一种“温柔的感伤、忧郁和迷茫”情绪,并在文艺作品中“呈现为一条美丽的女性画廊”,李泽厚把这一现象描述为“敏感主义”。[4]“雯雯”无疑也属于这个女性家族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之一。《雨,沙沙沙》是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在一个雨夜,纺织厂女工雯雯接受了一位男青年的帮助,他的温暖治愈了雯雯在文革中经受的生活和爱情创伤,重新带给了她生活的热情,怀着对这个不再露面的男青年的期待,她放弃了和一个大学生组成家庭的可能。故事结尾写的是雯雯在又一个雨夜中独自前行:
她隐隐地但却始终地相信,梦会实现。就像前面那橙黄色的灯。看上去,朦朦胧胧,不可捉摸,就好像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幻影。然而它确实存在着,闪着亮,发着光,把黑沉沉的夜,照成美丽的橙黄色,等人走过去,就投下长长的影子。假如没有它,世界会成什么样?假如没有那些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梦想,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生活又会成什么样?①本文引用的小说作品,不单独做注,都出自: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五卷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小说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幻想,王安忆让雯雯抒发情感时把“对事业的追求”、“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堆积在一起,无疑有些溢出了小说的主题。但正是这些具有统一性的生活内容以及价值判断构成了王安忆第一个小说阶段的意义叙事:现实的烦恼没有顺理成章地带来焦虑、痛苦或者沉重,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时间去解决,关键在于有“梦”,有了“梦”,人生就有了意义。
如果认同了“雯雯”对于意义的此种表达,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陈信”和“欧阳端丽”理解成“雯雯”在不同境遇下的化身。《本次列车终点》中的返乡上海的男知青陈信,在爱情问题之外,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住房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后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实质上已经超过了爱情,所有的矛盾最后集中爆发了,故事也以陈信逃避式的出走而告终,但有意思的是,在此困境中陈信的精神却突然出现了超越,他决心通过个人的思考来超脱这些眼前的烦恼,他乐观地相信并等待一定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流逝》的主人公欧阳端丽在身份上和雯雯、陈信完全不同,她是解放以前的大学生,嫁给了大资本家的大少爷,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她和雯雯、陈信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生活挫折和磨难,并在磨难中逐渐成长为一家人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撑。十年浩劫结束,公公落实了政策,房子回来了,钱多得用不完,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对于欧阳端丽来说,重新回来的生活总是让人觉得缺少一些什么东西。缺少什么呢?小说结束时,欧阳端丽决定保留自己在街道工厂的位置,伴随这个决定的是文光的感慨:“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这一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酸甜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看出王安忆探索个人生存“意义”的自觉和执着,其“意义”叙事也是统一的,这几篇小说都是写经历文革磨难并面对新生活时,人如何选择并确定自己的价值。最值得注意的共同性是,小说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让主人公沉浸在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中,并选择了一种朦胧的理想作为精神上的支撑。这种基于理想和信仰的意义阐释,相当直接地呈现了新时期初期主流化的时间意识,在建国之后相当长时间里,“进化-革命”的观念一直渗透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社会向前发展,历史不断进步,挫折和困境只是螺旋式上升中的一支插曲”成为普遍性的潜意识,人们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这一切,并相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对文革的否定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5]。在新意识形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召唤下,“进化论”的历史思维方式继续延续下来,引导了新时期初期文学,也包括王安忆小说的意义选择。
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和“梦”,历史性地构成了王安忆和新时期初期小说共同的意义基石,但是,这种意义叙事模式却隐含着一种巨大的逻辑裂缝:在被否定的过去和苍白的现实之后,如何能够跨越性地到达一个完美的未来?在以往的革命小说中,这种逻辑链条是完整的,从过去(痛苦)到现在(斗争和胜利)再到未来(美好)。而此时,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创伤、爱情、婚姻和人生的各种困境,构成了灰色的“现在”和“感伤、忧郁和迷茫”的敏感主义情绪,它们撕开和扩大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缝隙。要从这个环节起步到达“美好的未来”,不能依据逻辑,而只能依赖一种超自然的精神跨越,于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意义叙事的三个结果:首先,“未来”扮演的是现实替代物的角色,而不是现实的合理发展;其次,进化论历史意识的延续也并非一种主体性的选择,而更像是一种惯性,因为惯性,人们再一次把命运交给了未来,交给那个“梦”,这种刚从噩梦中出来又不得不走入一个新梦的历史循环,使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梦”意象失去了其在革命叙事中原有的强烈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带有苦涩和虚幻的意味;最后,这个无法解决的逻辑裂缝也必然导致对“未来”的重新解释。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关于未来的逻辑矛盾得到了细致的呈现,相对于《雨,沙沙沙》中雯雯对于“梦”的单纯信奉,《本次列车终点》的陈信已经知道在“相信未来”时还“真该好好想一想”,《流逝》中的欧阳端丽也意识到了个人精神和未来选择之间的矛盾,她决定继续去街道工厂,然而“心里却有点发虚”。阿格尼丝·赫勒曾经描述过“借助于未来而对现代性进行的合法化已经破产了”的过程[6],当陈信和欧阳端丽心中那种理想的坚定性正在悄悄溃散,那种可信赖、可托付的未来正在失去光芒时,我们也意识到了,未来所能承载的人生意义是脆弱的。王安忆在以“梦想”或“未来”设定意义道路的同时,也发现了这条道路的迷失和中断,从“雯雯”到“欧阳端丽”,展现出王安忆对于信仰、理想、未来的思考开始复杂化,这意味着王安忆“意义”叙事第一阶段的结束,也是她重新寻找新意义的起点。
二、“仁义”反讽和“传统”失效
这个新起点来得很快,它就是写于1984年的《小鲍庄》。评论家赞扬这篇小说突破了《流逝》之前的情感表达方式,显示出了“在人生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复杂化趋向”和“一种全面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7]小说也因为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探讨,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力作。“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为重大的一次文学思潮。它不仅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团结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创作力量,而且“体现了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经验与美学境界”。[8]对于寻根文学核心特征的讨论一直以来都非常激烈和丰富,而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寻根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相对而言,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寻根作家虽然写作风格迥异,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态度和理解,他们在“纯洁祖国民族语言、恢复汉文化的意象思维,以及对完善传统文学审美形式的追求上”[8]是同一的。
寻根文学对“意义”的叙事方式,带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把这种意识变成一种集体形态的强烈情感。不过,它和“进化-革命”叙事不同的地方是,它选择的意义支点不是时间链条上“未来”那端,而是“过去”。这种反向的时间选择呈现出与新时期初期大相径庭的意义取向,让人感觉到,“未来”所具有的寄托性意义在遭受怀疑的时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过去和传统”就通过“意义倒逼”变成另一种精神源泉,线性时间在面对现实时使用了它自己的独特逻辑。传统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心中展现出来的力量,既是现实的推动、呼唤,也是知识者的有意为之,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和阿城的《文化制约人类》这两篇“寻根文学”的宣言都把文学乃至人类生存意义的指向明确在传统或者民族文化上,但是无论是想通过“寻根”来摆脱当时的政治简单化,还是试图从西方获得灵感,无论是仅仅要表达一种感情,还是设想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最终这些意图都落在“传统”这一文化范畴上,使“传统”这一文化范畴成为集体认同的“意义”焦点。
王安忆在“寻根文学”的高峰期写出了《小鲍庄》,这篇小说的主题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仁义”这一核心思想,正与寻根作家所呼吁的文学应该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相呼应,这也让王安忆和《小鲍庄》极其自然地被纳入到寻根文学的洪流中来。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认定王安忆和《小鲍庄》与寻根文学的同一化,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王安忆的独特性。在王安忆的情感记忆中,知青生活、农村生活并不温暖,而是带有一种冰冷的个人感受,她在一封信件里写道,文革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不能认同其他知青作家对插队生活的怀念:“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9]至于原因,王安忆信里提到自己1983年在美国停留的几个月时间:
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9]
后来王安忆多次提到1983年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以及在美国游历的经历,但是她却一直没有清晰地阐释出这段经历给予她的巨大影响。那么,美国之行让她看懂了什么?在将近20年后与张新颖的一次对谈中,我们看到王安忆高频度地使用一个词来试图说出自己那一个时期的文学思索,这个词就是“意义”。那一年的王安忆似乎陷入了一个精神困境,她不停地问自己:写作有什么意义,怎么让自己写的东西有意义?[10]有理由相信:意义问题,正是此时王安忆自觉地思考并看懂的中心问题之一。机缘巧合,寻根文学的出现填上了王安忆前期创作结束时的“意义空白”,把王安忆“意义”之路和“文化”一下子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个意义的取向不是像大部分知青作家一样把感情寄托在对那个“青春期”的怀念,也不是像很多寻根作家那样重新用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来建立自己的精神认同,而是在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对比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缺失。
所以,王安忆在《小鲍庄》里试图展现的不是“传统”的魅力,而是通过对“仁义”模型及其死亡的描述,揭示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文化的虚伪性。王安忆说,“捞渣是一个为大家赎罪的形象,或者说,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最后崩溃!许多人从捞渣的死获得了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11]。因此,《小鲍庄》虽然设计了一个“仁义榜样”捞渣,但是捞渣周围的一系列人物,包括鲍仁文、拾来、小翠、鲍秉德媳妇等的故事,却建构起一个与“仁义小鲍庄”相对立的文化语境,这些包围了主叙事的小叙事,不是在衬托和呈现主叙事的庄严,而是在消解主叙事的“仁义”道貌,其批判性撕裂了很多寻根小说追求的“古典歌谣式”的美学想象。王安忆倾注于《小鲍庄》中的意义取向,与被误读的《小鲍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鲍庄》被误读的原因各种各样,很多人看到了“仁义捞渣”,而没有看到“反仁义的小鲍庄”,看到了“仁义”的文字性表现,而没有看到王安忆的“反讽”意图,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认同乃至迷恋传统的时候,忘记了“传统”是一个复杂的宏大叙事,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心理转型来说,它也许难以承受其重。
《小鲍庄》代表了王安忆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基本立场,也展现出她对于寻根文学历史观和时间观的另一种认知: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是否具有支持现代精神新生的能力?王安忆表现出了怀疑。在这一点上,王安忆和当时的很多寻根作家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她既没有像阿城一样对传统拯救精神抱有幻想,也没有像李杭育、贾平凹一样对传统的没落唱出一曲挽歌,当寻根作家返身向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寻求生存意义的时候,王安忆却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这种意义选择。与第一阶段不同,王安忆新时期中期的“意义”叙事集中于“传统作为意义”的可能,而与第一阶段相似的是,王安忆再次通过自己的独特思考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二、“性”和“纯粹精神”:上下的两难
时间作为一种线性的维度,其结构一般被分类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这种带有自然客观状态的时间意识在面对复杂的人类历史社会和心灵世界时,显现出了一定的苍白性和扁平性,人类繁复的情感和意识创造出了简单线性时间无法全面包容和有效描述的时间感。易水寒曾经总结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困境进行“突围”的历史,提出人类大致经过了宗教、理性、本能、传统这四种途径寻求意义,它们分别代表了向上、向前、向下、向后的时间方式。[9]这些时间意识的细致区分,丰富着时间的层次性,让人类的感受得到更加精细的呈现。新时期文学以及王安忆的意义叙事,正是通过意义选择的不懈探索,展现出了同样丰富的时间意识。从这样一个视阈,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王安忆从简单线性时间中超越出来,她以非常熟悉和擅长的“爱情”主题自觉性走出了另一条意义道路,从而扩展了意义的可能性。她在一篇带有回顾性的文章中写出了她的思索:
我尝试将爱情分成精神和物质两部分:写情书、打电话、言语都是精神方面的,而物质部分就是指性了。大概说来,我一九八九年写的《神圣祭坛》《弟兄们》《岗上的世纪》就是想分别走精神或物质的路。《弟兄们》和《神圣祭坛》尝试光凭精神会支撑多远;《岗上的世纪》可以和《小城之恋》一块看,它显示了性力量的强大:可以将精神扑灭掉,光剩下性也能维持男女之爱。[11]
《小城之恋》写得最早,也是王安忆较为满意的一篇作品。王安忆对于爱情两个部分的探讨,可以从《小城之恋》算起。这部小说写的是两个无名的青年男女“她”和“他”的性爱故事。“这是两个人的故事。我就想设计一个纯两人化的行为,那就是性了。”[10]小说的故事设计可以看成是王安忆所追求的“故事的逻辑性”的体现,在一连串的描述中,“她”和“他”逐渐成为两个被排斥在整个群体之外的“异类”,他们因为练功方法错误而练坏了的体形,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割裂状态,都在把他们推向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的封闭世界。剧团排演《艰苦岁月》最终拒绝了“他”,斩断了他们进入正常世界的最后一条途径,也使他们曾经朦胧的感情得到了一个契机结合并确定下来,他们只能就此进入这个被“性”所主宰的世界。然而,与其说他们被“性”所控制,不如说他们被一种“性的意义”所控制,他们有着与其身份不太适应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使“性”成为他们的灵魂巨大动荡的场所。他们相互体验着“性”带来的幸福和崇高,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又恐惧地感觉到了“性”的疲乏和肮脏,为自己不再纯洁而悲哀和悔恨。他们之间的亲近和搏斗,其实是他们心里无法认定“性的意义”所带来的灵魂亲近和搏斗。
小说不厌其繁地铺叙了主人公游魂飘荡、居无定所的状态,也展现了作家心灵的深度介入,这一过程不仅属于主人公,更属于王安忆,那是一种把问题逼到绝路式的追问:对于个体而言,“性”的意义何在?“性”真的“可以将精神扑灭掉,光剩下性也能维持男女之爱”吗?《小城之恋》似乎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小说的结尾描写“她”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毅然断绝了与他的关系,并且最后在“母爱”的肃穆与庄严中走向了纯净。《小城之恋》的“性”被母爱所否定,“性”曾经“近乎疯狂地宣泄和放纵”,曾经容纳了幸福和崇高,但此时却构成了对性意义的自我消解,作为存在和意义支撑的力量也就此宣告失败。王安忆对于“性”的探索,更加接近于一种“正名”,她否定了视“性”为羞耻的意义扭曲,也否定了以“性”获取存在意义的可能。
如果说作为物质性因素的“性”代表了形而下生活的一种方向,那么,和性相分离的异性或同性之爱,则是王安忆设想的形而上精神最具现实意义的表现。在这相反的两端,王安忆都走出了探索性的道路。但是,在把这两种生活方向和意义追寻相联结的过程中,和“性”这一本能因素相比较,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既显示出了极端的纯洁性,同时也显示出由这种纯洁性带来的极端脆弱性。《弟兄们》写了三个住在学生寝室里的女人,在许多彻夜不眠的夜晚,互相敞开心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建立了一个精神同一体,对于她们来说,这种极端自由的状态无疑属于精神上的巅峰体验,她们互相“唤醒”,这是“一生中最好的她们,最自由和最觉悟的她们”,她们也因此抛掉了一切性别负担,转换成了“三兄弟”。但是,对这个精神同一体不断进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让它解体、消融的力量也如影随形。老三首先在这个精神同一体上割开了巨大的裂缝,她回到了苏北老家,回到了家庭,最重要的是她在精神上背弃了“三兄弟”的同一体,她对于男女关系的最后认识竟然是“自我”的不置可否状态:“如果男女之间有爱情,那么自我被吞没也是快乐和有价值的,而如果自我无法给人快乐,还会带来破坏,那么要它有什么意义?”毕业之后,老二和老大分别在南京和上海生活,过了几年她们才又一次相见,这是又一次精神结合的过程,她们又一次敞开心扉,共同推动她们之间纯洁而高尚的友谊走向高潮,“这不像男女之间有情欲的推动,这全靠了理性。这是一个理性的、智慧的关系,这是人性的很高境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她们的关系达到了极点的时候,老大的孩子从童车里摔了出来,眼角血流如注,老大的情谊绵绵刹那间却转化成对老二的仇恨,因为老二使她们陶醉在自己的友谊里而忽略了孩子,并造成了孩子的受伤,她下意识地对着老二喝道“别碰我的孩子”,这句极具伤害的话,结束了她们之间的精神结合。绝望的老二最终给我们提供了纯粹精神的真谛:“有些东西,非常美好,可是非常脆弱,一旦破坏了,就再不能复原了。”
和《弟兄们》稍有差异,《神圣祭坛》讨论的是异性之间的纯粹精神,女教师战卡佳找到了她在人世间唯一的对手,天才诗人项五一,他们俩在人间存在似乎就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是了解,一个是被了解,当他们耗尽了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在一个夜晚将了解和被了解的关系推向了顶峰之后,他们之间的故事就此结束。这两篇小说对传统的“知音”关系是一种深度解构,因为它们讨论的主题不是生活的日常状态,而是精神的极端可能,是摆脱物质因素影响的纯粹精神如何在人的世界存活的终极性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明朗,在这种纯粹精神中,人注定了无法获得意义的完满,而只能接受精神的煎熬。
纯物质的“性”和纯精神的“爱”,从时间形态上来说游离于线性结构之外,然而,从性质上来说,它们都呈现出强烈的“时间性”特征。倭铿指出,人在神、理性、自然等外在性意义变得不可靠的时候,“为了保全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仅剩唯一一条路可走:人转向其自身。”[12]人建立起了属于自身的内在意义生活,也建构起了内在心理时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时间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延伸,而是以强度的方式决定其存在的短暂或永恒。《小城之恋》中的“性”,是带有强烈的物质消耗式的“瞬间性”时间,而《弟兄们》、《神圣祭坛》中的纯粹精神则类似于宗教里的“永恒时间”,但与宗教中的“神的时间”相比,它是“人的时间”,它不是彼世的,而是现世的。在新时期后期,王安忆通过物质和精神这两种“意义”叙事摆脱了未来和过去的意义模式,通过内在心理时间的开拓使线性时间转化成三维的立体时间,和前两个阶段一样,王安忆仍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意义”的答案,但是这种“意义”拓展的探索,却呈现出了一种和新时期精神非常契合的意义自觉和开放。
意义,是人对于现世的解释和承诺,而意义后面的时间意识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结构。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多样化的意义方向和时间意识,虽然有很多的表达并不完满和深刻,但是那种极具创造力的青春激情和亢奋,却为当时的历史做出了生动的记录,也给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新时期文学十余年的时间里,许多优秀作家都以个人化的方式参与到寻找意义的道路探索中,王安忆从新时期初期的审视未来,中期的反思传统,再到后期探索纯粹性爱和纯粹精神的可能性等四种“意义”叙事,编织出了未来、过去、瞬间、永恒等四种不同时间方向的网络。“意义对既定现状的超越性张力与意义的意象希望或憧憬未来情调内在相关。意义往往是有待于实现的前景。因此,可能性是意义本质性特征”[13],王安忆不仅自觉地走上了意义探索之路,而且把握住了“意义可能性”对于意义本身的本质性特征,虽然每一种意义方向在王安忆的小说中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栖居地,没有带来人的精神自足和最终支撑,但是这个寻找意义的故事,以及执着于“意义”寻找本身,不正揭示出一种属于现代性特征的意义状态吗?
[1]程文超.意义的诱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60.
[3]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6.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56-261.
[5]巴金.怀念曹禺[C]//吴福辉,朱珩青.百年文坛忆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
[7]何志云.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N].光明日报,1985-08-15.
[8]陈思和.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J].文学评论,1986(6).
[9]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N].光明日报,1985-08-15.
[10]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2-143.
[11]王安忆.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J].当代作家评论,1991(6).
[12]倭铿.人生的意义与价值[M].周新建,周洁,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2013:22.
[13]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84-85.
(责任编辑:李金龙)
I206.7
A
1001-4225(2015)05-0026-06
2014-12-08
王军(1971-),男,江西宁都人,文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叙事”(2012SJD7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