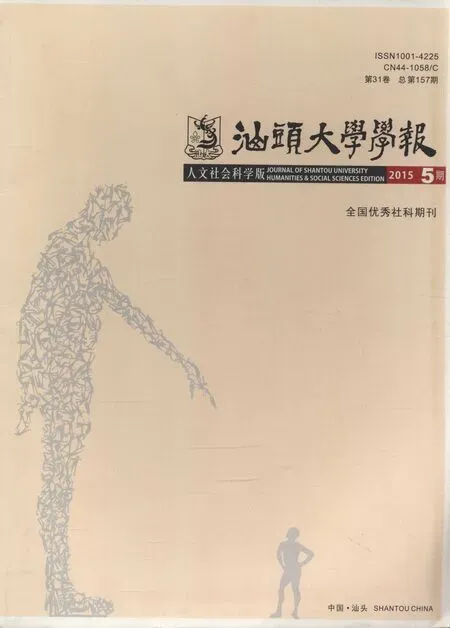“西方主义”为什么源自西方——对伊恩·伯鲁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核心理念的解读
朱望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西方主义”为什么源自西方——对伊恩·伯鲁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核心理念的解读
朱望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西方主义既源自西方,也来自东方。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社会犯有四重罪:西方现代城市化、西方商业化、西方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西方开放社会无宗教信仰与性道德混乱。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批判,辨析根植西方的西方主义者如何被伯鲁马视为“敌视”自己的国家,厘清源自西方的西方主义者与反西方主义者的双方辩驳,为误读西方主义这一当代社会思潮的中国读者提供看待东西方社会的不同视角,有益于国人在传统向现代性转型期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摒弃非黑即白的僵化思维模式。
西方主义;城市化;商业化消费;英雄主义的失落;唯科学主义
据伊恩·伯鲁马(Ian Buruma)和阿·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观察,与西方人妖魔化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正好相反,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是仇恨西方和攻击西方的思想倾向和“带有漫画化”的丑化西方的意识形态表达。西方主义多为妖魔化西方人,刻板化解读西方社会,扭曲现代西方文明的政治和文化偏见:“西方世界被它的敌人所描绘的去人性化图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主义。”[1]7“西方主义”是指东方人反对西方和一部分西方人批判西方的当代社会思潮,其中正误交织,是非难辨。
西方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十分复杂,包括本土文化传统与全球现代化运动的博弈、争取民族独立的非西方国家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斗争、东方传统政治威权和东西方极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间的冲突、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对欧美盟军国家的仇恨、现当代东西方国家的政治较量和经济竞争、东西社会的文化差异,尤其是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峙。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潮包涵了“所有历史上的联系与重叠,从欧洲的反宗教改革到反启蒙运动,从东方和西方的许多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变种,从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最后从今天在许多地方肆虐的宗教极端主义”。[1]10西方主义者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群体,而是所有出于各种原因在某时某地反对欧美国家的人士。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甚至对立的政治阵营,包括东方人和部分西方人——以国家神道为首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主的传统宗教人士、德国纳粹分子、批判现代性的欧美和俄国文人、传统社会中抵制现代化运动的本土知识分子、冷战中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所有西方主义者的无意识联盟基于反西方的共识,东西方的西方主义者都不愿看到全球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他们指控西方社会犯有多重罪:(1)西方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腐败的都市生活;(2)西方以商业化为导向的物质享受取代了崇高的英雄主义;(3)“空虚的”西方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破坏了传统人文主义;(4)西方放荡生活毁坏了东方宗教道德的“深邃”精神,惹起了“上帝的愤怒”。西方主义者把西方的一切观念和实践批判为“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尤其把美国视为“西方魔鬼的化身”。
西方主义者的来源复杂:(1)源自西方的西方主义——为何西方主义在西方?(2)来自东方的西方主义——为何西方主义在西方之外?本文篇幅有限,只谈第一个问题。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西方人批判资本主义、抵制西方现代化运动,他们大多是人文知识分子(文学家和文化哲学家),他们被伯鲁马称为西方的西方主义者,甚至是西方主义的始作俑者:“西方主义……全部诞生于欧洲,然后才流传到世界的其他地区。”[1]6这就是伯鲁马关于“西方主义源于西方”的命题。笔者将从上述西方主义者的四个指控来分析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批判,辨析根植西方的西方主义如何被伯鲁马视为“敌视”自己的国家。
一、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第一宗罪:城市化导致腐败堕落
西方主义者认定西方第一宗罪是城市化。城市是“罪恶的象征”:西方“狂妄自大、帝国建筑、世俗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与人居于有罪之城息息相关”[1]17。厌恶都市的西方主义者认为,现代化意味着都市化和世俗化,必定产生以商业化和享乐主义为主导的庸俗腐败堕落;城市人坑蒙拐骗、溜须拍马、巧取豪夺、男盗女娼,他们只有金钱交易、声色犬马的物质感官享受,没有宗教的高洁精神和诗意典雅。城市罪恶还包括“黑暗撒旦般”的现代工厂,引诱朴实农民涌入“拥挤的平民窟”,堕入“工业区的陷阱、犯罪团伙、或妓院之中。”“都市巨兽”“以惊人胃口吞噬了整个乡村人群”,城市变成无灵魂的交易市场:“西方主义者把城市看作非人道的、一群为贪欲所控制的堕落动物寄居的动物园。从西方主义的角度出发,城市居民实实在在地丧失了灵魂。”[1]22
在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始终对资本主义社会保持警醒和质疑的态度,尤其担忧城市化这一现代化运动的后果。本雅明称:“害怕、厌恶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2]151恩格斯如此批判伦敦大都市:“像伦敦这样的城市,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也遇不到表明接近开阔田野的些许症像……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上几天,费力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察觉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特点……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类本性的东西。”[3]58近现代西方文学家持续批判西方现代性,包括18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的现代主义,如D.H.劳伦斯、T.S.艾略特、A.赫胥黎和D.莱辛等。艾略特和波德莱尔是伯鲁马指认的源自西方的西方主义者,其诗歌主题就是批判现代都市生活。艾略特厌恶地描述城市化导致的社会恶性演变:“屋宇建起又倒坍、倾圮又重新扩建,/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旧石筑新楼,古木升新火,/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而黄土如今已化为肉,毛,粪。”[4]79在他眼中,城市是行尸走肉的现代人的精神荒原:“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我没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他悲怆地预言:“伦敦桥倒坍了,倒坍了,倒坍了”。[4]17波德莱尔在1851年就观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这个病容满面的群体吞噬正工厂的烟尘,呼吸着棉花的花絮,让铅白、水银以及生产人间杰作所需要的种种毒药都渗透进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个衰弱憔悴的群体,但地球上的奇迹应归功于他们”。[5]161他关注“巴黎的忧郁”,用“充溢死亡的田园诗”诅咒这“可怕的城市!”把现代城市的污染、颓废和堕落形容成“恶之花”。西方人文知识分子显现了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疏离。在伯鲁马眼中,这类批判现代都市化的西方文人就是西方的西方主义者,这是作者称“西方主义源自西方”的第一证据。
伯鲁马和马格里特对西方主义者的“西方都市罪恶论”有两个反驳。其一,城市非现代西方独有:“城市这种象征什么时候成了西方世界独有的,什么时候西方的城市成了西方主义者憎恨的焦点?”他们辩解道,东方同样有古老和现代城市—古代中东的巴格达和君士但丁堡,19世纪日本的都城江户,从13世纪富饶的北京城到现代时尚的北京上海。其二,都市化意味着社会进步,现代城市生活是科技文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多元种族和社会群体、大众教育、大众传媒、民众参政议政的集合体,“提倡个人主义、民主意识和多种族的共存社会。在商业化都市中,一个植根于血缘和土壤的单一文化被打破,一个都市文明从世界主义多元化中被锻造出来。”[1]29他们称道现代城市人的自由民主意识、科学探索精神、社会法制体系、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工商经济发展、看似淡漠的人际关系中更为宽容自由的私人生活空间。伯鲁马反西方主义者的结论是,正是现代都市繁荣发展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促进了开放社会价值观、政治观念和文化风尚。他们认为,人们纵有一万个理由不喜欢城市,但西方主义者贬斥都市化过于偏狭。
二、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第二宗罪:商人战胜英雄
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社会犯下第二宗罪:商人战胜英雄,平庸销蚀崇高,商业化替代英雄主义。在他们眼中,西方人的“平庸”有三个肇因。(1)商人金钱意识引导西方人只追求物质享受,因而没有崇高情怀;(2)欧美自由主义注重个人权益,导致西方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不愿为国牺牲。西方主义者对西方人“产生轻蔑之感,只因为他们不将慷慨赴死当做人生的最高愿望”;(3)西方人的“反乌托邦特性”导致人们无远大理想,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注私人日常生活,“这个普遍的社会冷漠”致使“西方生活无意义。”西方主义者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最坏样板,因为西方商业化和个人主义毁坏了政治和道德理想主义:“民主西方所欠缺的是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民主社会的政治家缺乏‘追求宏伟壮观的意志。’”这是“最令人鄙视的”平庸。[1]49
西方的西方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表达。一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普遍批判。本雅明指出:“商品本身提供这种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5]22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中哀叹全民经商的腐败:“啊黑暗黑暗黑暗。他们都走进了黑暗,/空虚的星际之间的空间,空虚进入空虚,/上校们,银行家们,知名的文学家们,/慷慨大度的艺术赞助人,政治家和统治,/显要的官员们,形形色色的委员会主席们,/工业巨子和卑微的承包商们都走进了黑暗,/太阳和月亮也暗淡无光了”。[4]86A·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痛惜人们丢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伦理学和哲学”,嘲讽浪费奢侈的现代消费观:“我爱新衣服,我爱新衣服,我爱……”。[6]50波德莱尔痛斥金钱意识:“你最喜欢金子?我憎恨它,就像您憎恨上帝。”[7]5波德莱尔看透西方社会缺乏“丰富的精神繁荣”而走向颓废:“‘乏味,平庸,我很少见这样乏味的沙龙。’……在任何时代都是平庸占上风;确实又令人痛心的是,它从未像现在这样支配一切,变得绝对地得意和讨厌。”[8]345西方文人看清了现代社会趋向“平庸”:商人战胜英雄,金钱胜过信仰,吃喝玩乐替代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对西方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便成了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然而,在伯鲁马的眼中,这些务虚不务实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几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能量,他们一味地批判西方商业社会的黑暗面,把自己变成西方社会的“敌人”。这是伯鲁马等西方学者称“西方主义源自西方”的第二个证据。
其二,伯鲁马认为德国纳粹极权者也仇恨西方,鼓吹西方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个概念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们所说的西方世界是腐朽衰落的、贪婪积财的、自私浅薄的”,“只有在钢铁风暴中的牺牲才能将自己从西方世界的陈腐中挽救出来。”因此,“把西方描绘成懦弱、沉迷于舒适和缺乏牺牲精神。因为紧紧攥住生命不放手,西方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不能算作真正的人类。这样的指责正是战前德国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分子攻击西方世界时所用的言辞。”[1]50在希特勒、纳粹党和德国人民结成的三位一体的法西斯极权国家,在精神魅力型领袖希特勒的准宗教宣传蛊惑之下,每个青年都认为纳粹“极其粗暴的民族主义在伦理上是正确的”。[9]他们饱含对领袖的忠诚而献身于法西斯国家主义,狂热呼应自我牺牲的誓言:“血与荣耀”,“只要元首下命令,我们就遵守!我们全都只说‘是’!”仅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希特勒青年军的数量已经跃升至360万,1939年战争来临时,其数量已经达到890万——这还不包括由于年龄增长而退出希特勒青年军进入德国主要军事力量的几百万人。希特勒青年军的毕业生们从未停止过为希特勒德国而斗争”[10]108,最终成为第三帝国的殉道者。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狂热情绪和刚烈意志就是伯鲁马眼中的西方主义者的“死亡崇拜”情结(death cult)和西方主义式的“牺牲崇拜模式”,这是作者称“西方主义源自西方”的另一佐证。
反之,西方自由主义者不赞同西方主义式的英雄主义崇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从不曾假装是一种英雄的信仰。……重要性已被赋予给‘日常生活,而不是卓越不凡的生活’。”开放的社会给“每个人以自由去成为一个平庸的人”[1]59,《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1]西方人有理由拒绝国家对公民牺牲个人的要求,原因之一,西方社会注重公民权利,个人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原因之二,西方社会尊重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力保公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原因之三,西方社会主张有限政府,反对国家以高调宣传或铁腕强制手段干预或指挥个人行为。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主义所赞赏的民众英雄主义情结为官方专制政治文化所塑造:“政治化的宗教运动往往以同样的原因吸引着人们。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献身,为一个理想的世界而献身,为荡涤人类的贪婪和不公正而献身,这是普通人感受英雄主义的一种方式。宁可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光荣死去,也不愿苟活在舒适惰性中。选择以暴烈死亡的方式献身,变成了人类意志的一种英雄行为;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它可能是个人能够自由选择的唯一行为。”[1]60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西方社会告别崇高,除却宏观叙事的官方思维模式,“承诺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具有物质享受、个人自由和平常生活的尊严,这种生活打掉了所有乌托邦的白日梦。”[1]60西方人拒斥极端的自我牺牲崇拜,他们赞赏以协商和妥协的方式保全公民的个体生命,他们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善意态度”和“良好心愿”,因而出现了美国大兵携带官方“投降书”上战场的事例。①美国士兵上战场(朝战和越战)时都携带一份求救书,实则投降书(13种文字写成,包括中文):“我是美军某某部队某某分队的某某兵,现在不能完成作战使命,被贵军所制,愿意投降,以保障自身性命,达成双方和解。”http://lt.cjdby. net/thread-955662-1-1.html。在西方主义者眼中,这类西方价值观和行为是平庸和可鄙的。因此,反英雄主义和反乌托邦的西方社会便成为“宗教极端分子、神权统治者、纯洁和英雄般救赎的集体寻找者的最大敌人。”国家主义对峙个人主义的不同价值观导致了西方主义者与反西方主义者的对立:“在含笑赴死的神圣勇士和沉迷于舒适惰性的人之间的一场战斗。”[1]59-61
三、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第三宗罪:理性主义导致唯科学主义
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社会犯下第三宗罪:理性实证哲学所支持的唯科学主义。他们称这是比军事帝国主义杀伤力更大的“思想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通过散播西方的相信科学主义和信仰科学作为唯一求知途径,强力地在全球扩张着”[1]76,从而取代了人文主义传统。伯鲁马赞赏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指出西方主义者妖魔化实证科学思维:“西方的头脑往往被西方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高级弱智。配备了西方头脑的人就像一个白痴专家,一个心智缺陷者却拥有做数学运算的特殊天才。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头脑,有着像计算机般的高效率,但是绝无希望做出具有人性的任何重要事情。西方的头脑肯定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以及发明和推广先进技术,但它不能掌握生活中更高层次的东西,因为它缺乏精神性和对人类苦难的理解。”[1]65西方主义者十分蔑视西方人自从启蒙主义以来发展的理性主义,指斥为“高度愚蠢”的工具理性:“西方的头脑在西方主义者的眼中是一个被截断的头脑,它擅长于寻找最佳方法来完成既定目标,但是,在寻找正确目标方面,它却是彻彻底底地束手无策。……西方人是一个患有多动症的瞎忙者,永远地找着正确的方式来完成错误的目标。”[1]66
伯鲁马认为,俄罗斯西方主义者就有反科学主义的情绪。其一,俄国西方主义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德国自然哲学家弗·谢林把宇宙描绘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反对英国科学家牛顿关于自然受力于物理机制的科学理性思维,谢林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其二,俄国本土知识分子有更为突出的西方主义倾向。19世纪的斯拉夫派是一群捍卫传统,抵制西方思潮的俄国文化哲学家,他们对西方工具理性的批判深刻而易懂:人类的头脑被“描绘成一所大学,其中分成了许多院系,理性在里面只能算一个院系。感情、记忆、认知和语言等等这些院系,都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西方的头脑……就像一所只有一个院系的大学,即只有理性这个院系。”这群人文知识分子指出了西方工具理性价值中唯科学主义的极端错误:“傲慢的西方背负理性主义原罪,有罪于傲慢无比地认为理性这个院系能让人类洞知一切该知道的东西。”[1]79俄国文学家更有明显的西方主义倾向,他们尤其关注民族命运,因而产生了融宗教道德和人文关怀为一体的苦难救赎文学,包括“俄国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文学家关注人文,维护传统,抵制现代化对俄国人文主义传统的危害。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钥匙”这一现代主题;屠格涅夫害怕虚无主义者“输入西方有害思想”,破坏“不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美学、传统道德、宗教或者一切形式的权威—教会的,家庭的,或政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贬斥象征西方现代科技成就的1851年伦敦世博会水晶宫:“西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水晶宫,只被干瘪的理性主义驱动着”,“西方世界致力于科学主义,并相信社会能像水晶宫般被设计规划。……输入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构成危险的蛊惑性意识形态”。[1]80-81俄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对毁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多有诟病,他们被现代改革派视为浪漫无知而又幽怨怀旧的“反启蒙运动”人士。虽然他们无意发起西方主义,但在批判现代西方机器文明方面与东方的西方主义者达成一致。因此,作者再称西方主义的源头在西方。
同俄国传统文人一样,所有欧美人文知识分子都对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深度批判。英国传统文化的主将马修·阿诺德早在19世纪就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他尖锐地揭穿以工具理性和GDP论英雄的虚幻大国梦:“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我们常常相信机械能做好事,既便如此,这种信仰同它作为工具的功效也是极不相称的。……什么是宏基伟业?这是文化要我们问的问题。……我们的思想习惯有多么不健康,竟动辄将煤啊铁啊之类当成英国的国脉所系”。[12]12-13法兰克福学派的H·马尔库塞分析了实证哲学、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予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负面影响,指出后现代西方社会已沦为“单向度的社会”,现代人已变成“单向度的人”。他称实证科学思维是“单向度的哲学”,现代科技是“新的控制形式”,已为现代人所接受和享受:“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虽然现代科技解除了体力劳动的痛苦,但导致新问题:在舒适的“不自由”中,现代人只追求“虚假的需求”,失去“大拒绝”的反抗精神,致使“政治领域的封闭”;技术和商业意识控制了语言,令“高雅文化世俗化”,导致“言论领域的封闭”。[13]145哈贝马斯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14]62为此,哈贝马斯十分推崇马尔库塞,认为他是提出“科学和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家:“只有马尔库塞才把‘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当作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理论出发点。”[14]41务实的经济学家哈耶克(1974年与Gunnar Myrdal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质疑科技的负面意义,指控“科学的反革命”和“理性之滥用”。哈耶克谴责孔德实证哲学所指向的唯科学主义日趋独断:“在孔德的科学等级表和许多类似的论证中,都包含这样的观点: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自然科学为‘基础’,只有当自然科学大有进展,足以使我们能够用物理概念、‘物理语言’来研究社会现象时,社会科学才有望取得成功。这种观点可谓荒唐透顶。”[15]45哈耶克着力批判“有严重迷幻作用”的唯科学主义和技术统计论以机械的实证研究干预有机的人类精神世界,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还原为简单划一的规律性,以工具理性消除自然演进的人文传统。他将“现代科学大奏凯歌”的“这种盛极一时的普遍精神”称之为“唯科学主义傲慢的根源”。哈耶克甚至批判了西方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人物—培根、圣西门、笛卡尔、牛顿,因为他们“赶走哲学家、道德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最高牛顿委员会将领导他们的工作。”[15]8哈耶克悲观地预言,科技的过度使用将使人类社会堕入“危险处境”:“当人们沿着一条给它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时,他们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谬误。”[15]113-117
代表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西方主义者)和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科技知识分子(反西方主义者)各执一端,由此产生深刻的隔阂:“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16]4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现代化运动从西方扩展到全球,势不可挡,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则以批判性思维对此保持冷峻的警醒。因此,伯鲁马把他们归为西方的西方主义者,认为西方主义仍是源自西方。
四、西方主义者眼中的西方第四宗罪:反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
西方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的第四宗罪是反宗教,已引起“上帝的愤怒”。东西方宗教的纷争包涵种族、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性别问题。其一,宗教西方主义者反对西方拜物教:“西方世界在西方主义者的眼中是崇拜物质的:它的宗教是物质主义。另一方面,东方世界如果能存留自己的东西,免受‘西方毒化’,那么它是具有深邃精神性的王国。东西方的斗争是爱世俗世界的拜偶像者与真正崇拜神性者之间的斗争。”[1]90其二,西方开放社会的男女平权理念与东方传统社会的男权意识有严重分歧:“妇女问题不是边缘问题,它是伊斯兰西方主义者最为关心的问题。”[1]104宗教西方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掀起了道德败坏之风:“男女之间的明显差异在西方世界被故意抹煞,使妇女能够更容易地为资本主义服务。”[1]108在宗教西方主义者眼中,整个西方生活就是放荡的闹剧——非法性关系和同性恋,女人抛头露面与男人同行。穆斯林世界把西方女性贬为“妓女”:“西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妓院”,“西方女性是为西方物质主义服务的神庙妓女。西方世界的性道德,或者说是缺乏性道德,使西方生活看上去堕落异常,简直与动物无异。”[1]107在西方生活过的中东人尤其反感西方生活方式,因而成为彻底的西方主义者,他们最终要以宗教形式清除西方影响。
西方人对宗教问题有两种相反的反应:一是批评东方宗教制度下的男权宗族社会,主张公民自由权利的西方人认为,东方宗教中隐含男权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充满男权隐喻,这是应清除的“世界观的残余”。经历过女权主义运动的西方人认为,中东宗教西方主义在男权制度庇护下产生严重的性别麻烦:家庭暴力的“残酷行径”、一夫多妻制、隔绝妇女于公共生活的深闺制度和面纱服饰:“面纱成为一种抵抗西方世界的象征。”[1]96西方人欲强行解放中东妇女,缓慢而坚定地掀开其束缚人性的面纱,宗教西方主义者称之为干涉内政的威胁。宗教西方主义与西方世界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大战,中东世界的宗教西方主义者就是抵抗西方世界的文化圣斗士,西方人士则清一色地反对含有男权意识的宗教西方主义。二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同传统东方人一样,期待重建宗教信仰,纯化现代世界。在伯鲁马眼中,艾略特就是来自西方的宗教西方主义者。艾略特是一个宗教道德理想家,欲以贤良敦厚之心守望精神家园,以高远恬淡之道立社会和谐与繁荣。在他的宗教观体系中,核心是建立“基督教社会”,以抵抗商业社会的世俗主义。特别令艾略特不安的是现代工业文化是对宗教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这种无限制的工业化趋向则造成了各个阶级的男男女女脱离传统,疏远宗教,并变得容易受群众煽动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成了群氓。”[17]15艾略特在《岩石的合唱》中诉说道:“二十个世纪天国的循环往复/使我们疏远了上帝,/接近了尘土。”“那里人们告诉我:我们有太多的教堂,/太少的小吃馆。/那里的人们告诉我;让牧师们退休。/在城市中,我们不需要教堂钟声。”[18]“上帝死了”,礼拜日成为吃喝玩乐的世俗狂欢节。传统宗教落花流水,这是艾略特之大悲,因此他义无返顾皈依宗教,期望重建宗教理想主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本致因在于信仰体系的崩溃:“这些意义存在于宗教、文化和工作中。这些领域内意义的丧失造成一系列理解的缺乏,这种缺乏让人们无法忍受,迫使他们尽快去寻求新的意义,以免只剩下虚无感或空虚感。”他珍视宗教信仰的两个功能——抑恶扬善和文化传承:“在西方社会,宗教曾有两个功能。一是它看守着魔鬼的大门。……第二个功能是提供跟过去的延续性。”[19]他继而指出后工业化时代的复兴旨在重建宗教信仰。上述西方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的倚重与东方宗教文化有相通之处,他们无疑被伯鲁马列为源自西方的西方主义者。
在考量西方主义这一当代思潮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从不同视角看待西方社会的重要参考,不应简单化地认定其对错。况且,这只是西方主义思潮的一半,另一半尚待研究(来自东方的西方主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主义的研究有益于国人在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期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摒弃非黑即白的僵化思维模式。
[1]伊恩·伯鲁马,阿·马格里特.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M].张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151.
[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8.
[4]T·S·艾略特.情歌·荒原·四重奏[M].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A·赫胥黎.美丽新世界[M].李黎,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
[7]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散文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
[8]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M].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5.
[9]梅尼克.德国的浩劫[M].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90.
[10]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下“帝国梦”[M].熊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11]Jefferson,Thomas.Thomas Jefferson o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M/OL]//Digital Archive of Thomas Jefferson. Virginian University,[2015-05-12].http://etext.lib.virginia. edu/jefferson,119
[1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弗·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6]C·P·斯诺.两种文化[M].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7]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8]托·艾略特.四个四重奏[M].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172.
[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5-156.
(责任编辑:李金龙)
I06
A
1001-4225(2015)05-0005-07
2015-04-10
朱望(1956-),女,山西永济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