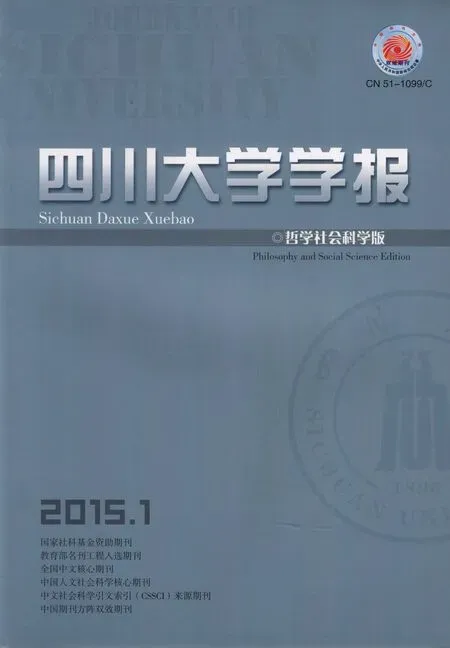刑法规范中的行政处罚
施锐利
引 言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行政不法行为的制裁,不法行为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分,近些年来学界较多关注对民事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比较研究,对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比较研究则相对较少。不同的不法行为的责任方式也有不同,民事不法行为的责任方式与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的责任方式迥异,而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由于侵害的客体均为公法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责任方式的处罚都体现了国家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因此何种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何种行为当处以刑事制裁至今是“令人绝望”的问题。①1845年德国法学者K.Koestlin把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这个争论多端而未能获得满意结论的问题,称为“导致法学者绝望的问题”,见K.Koestlin:Neue Revision der Grundbegriffe des Crimianl rechts,1848,S.28.转引自林山田:《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第108页。学界对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分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从两个向度进行,一个是从实体规范上进行界分,即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调整对象具体有哪些不同,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德国学者提出的质量区分说,我国学者也沿着这一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②如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著《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版);陈兴良教授的《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但这一学说存在质的不易把握、量的具体衡量困难和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另一个则是从程序衔接上进行研究,探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程序上如何衔接问题。在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分别由不同的执法主体依据不同的实体法规范,遵行不同的程序进行。我国立法由行政义务的违反到构成犯罪的模式是一种平行交叉模式,即对行政违法行为既可以用行政处罚模式,也可以用刑事处罚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台湾地区的“违法-行政处罚-违反行政处罚-犯罪”的递进式的处罚模式。如台湾空气污染防制法第49条第1项规定,公私场所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递进式处罚模式的优点是程序衔接好,不存在交叉问题,而平行交叉模式下,突出的问题是一行为两罚是否合理,两种处罚方式在衔接时如何既保证程序公正,又无害实体权利。对这些问题,仍旧有探讨的必要。
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分已然存在以上所述的实体与程序上的困难,而我国刑法更具特殊性的是,刑法中有许多规范直接规定了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要素,这更强化了界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二者实体上界分的难度和程序衔接上的困惑。我国学者提出“罪量”是犯罪构成的要素,包括数额、情节,①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而基于刑法对行政犯罪作出规定时将行政处罚纳入到刑事规范中,除了“罪量”是犯罪构成的要素外,行政处罚也因此成了某些行为犯罪构成和影响量刑的要素。这种以行政处罚为定罪量刑要素的规定下,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必然对刑事案件产生程序上的影响。本文归纳梳理刑事法律规范中的行政处罚规定,对作为定罪量刑要素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加以界定。在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研究成果时,程序的衔接研究上也立足于我们立法的现实,关注到我国立法的这种特殊性。
一、行政处罚在刑法规范中的体现
刑法关于行政犯罪的法律规范中有大量涉及行政处罚的内容。这些行政处罚不仅关系犯罪的成立与否,也关系到量刑问题,由此可见,对某些行政政犯而言,行政处罚对定罪量刑具有规范意义。具体体现为:
第一,行政处罚影响犯罪成立与否。这种影响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肯定性的规定,由刑法规范直接规定受过行政处罚的再次实施同性质行为时构成犯罪。二是否定性的规定,即接受行政处罚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承担。肯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153条所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一年内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走私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行为表现之一,受过行政处罚成为走私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前提条件。行政处罚也可以成为犯罪的定罪情节,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9日联合发布的法释 (2013)21号《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且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②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达到了诽谤罪的定罪标准的“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犯罪。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数额较大”的,按照盗窃罪规定标准的50%确定。这一规定将行为因受过行政处罚而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数额标准减半,行政处罚间接对犯罪成立产生影响。在我国对于行政处罚的单纯不履行行为,一般是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其履行,不法行为主体拒绝履行行政处罚的,并不直接构成犯罪,除非其行为方式因采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才构成妨害公务罪,从而进入刑事评价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一般是附属刑法模式,在行政法中先规定行政不法行为,并应当予以行政处罚,如对行政处罚不从的,则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如台湾的《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第1项规定:事业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因为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而将该行为直接交由刑法来评价,但是不法行为主体受过行政处罚对于其再次行为是否受到刑法的评价以及评价的起点却有影响。否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所谓“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不应以犯罪论处,即逃税行为经过行政处罚从而阻却刑事处罚。这种规定给予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行为人履行了行政义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作用。刑罚适用的补充性不仅应体现在逃税数额、比例的“量”上,而且应体现在违法行为本身的“质”上。①邹日强:《逃税行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研究》,《犯罪研究》2010年第4期。逃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在该类行为中,将经过行政处罚的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不动用刑法但已经起到了保护国家税收的作用,这符合刑法谦抑性、补充性的要求。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如果有许多措施可用时,宜先用轻罚,只有轻罚不能有效阻止行为目的时,才有必要动用重罚。刑罚作为国家对于不法行为的最后而且最重的手段性,为避免过于严苛,对于单纯的违反义务的行为,如果行政处罚手段足以达到管理的目的时,没必要动用刑罚。
第二,行政处罚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故意”。罪过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不可少的要件,刑法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故意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对于以违反行政法规范而构成的故意犯罪来说,构成犯罪必须行为人具备明知。而明知是主观方面的要素,必须以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行政犯是一种法定犯,与自然犯不同,伦理可责性低,违法与否的界限模糊,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行为人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自我辩解,那么这时受过行政处罚可以作为其主观明知的一种证明。如走私罪是故意犯罪,对于如何认定故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第5条规定的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明知”。
第三,行为未被行政处罚的,其未被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从而影响其后行为的刑事评价。刑法中有多个条文规定“对多次实施前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如刑法第201条逃税罪“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第153条“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12条第2款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以上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体现了不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作为影响下次行为的定罪数额或者量刑数额。如果计入累计的数额达不到定罪数额,当然不构成犯罪;如果累计数额足够定罪,将成为影响适用法定刑幅度的数额。
第四,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影响量刑。曾经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不法行为的,说明行政制裁对行为人的无效性,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再次行为构成犯罪时量刑的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自不待言。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刑法规范中也有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醉酒驾驶机动车,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重处罚。行政处罚也可以作为情节轻重的评价标准而决定行为适用法定刑的幅度。刑法中在对法定刑幅度进行规定时,考量的要素包括数额、情节等,刑法根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情节的一个评价因素从而影响法定刑档次的适用。司法解释中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中很多包含受过行政处罚的内容,如《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受过行政处罚除直接影响量刑外,还影响量刑制度的适用。刑法规定了缓刑制度及缓刑适用的条件,在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操作上受过行政处罚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考察因素。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在缓刑适用条件里规定,受过行政处罚三次以上的不得适用缓刑;在具体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时,受过行政处罚的不得适用缓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规定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二、作为定罪量刑要素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分析
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使用时,行政处罚所处理的行为应当与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同一性质,并且在法定时效期内。首先,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只有同一性质的行为才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政处罚无效时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当然同一性质的行为未必同一罪名,刑法中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为犯罪对象的不同规定了若干罪名,这里不要求前后的行为罪名同一,只要行为属于同性质即可。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可见一斑,如2014年9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以及其他货物、物品;“又走私”行为仅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其次,只有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涉及到行政处罚的刑法规范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些明确规定了必须是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对定罪量刑造成影响,而有些则没有予以规定。规定了只有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进入刑事视野予以刑事评价的,一定的期限有的规定是一年有的规定是二年,超过此期间的不进行刑事评价。如刑法规定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中的“一年内”,以因走私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走私”行为实施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即是指在这一年内的行政处罚对于定罪量刑有影响,超过一年的不能成为刑法的评价事实。但也有些只规定了受过行政处罚而没有规定所受行政处罚的时间界限的,如1999年10月9日《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曾因邪教活动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又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7条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应予立案追诉的根据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这些规定里都没有指出行政处罚对于刑事处罚的影响时间,是否意味着只要曾经受过行政处罚,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可以影响定罪量刑?申言之,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处罚适用的前提事实,是否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从条文规定本身看应当理解为对行政处罚可以追溯的时间上没有限制,但基于刑法规定了追诉期限,作为构成犯罪的事实行为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那么同样地作为犯罪事实的行政处罚应当也有追究期限的限制才符合同一性。
刑法中除了明文规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因素外,还存在一些隐含性的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要素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窃罪的行为之一是多次盗窃,根据司法解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那么构成多次盗窃的行为是否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是仅指没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某被告人在两年期间共盗窃三次,数额分别为:第一次600元、第二次400元、第三次500元,三次行为中的前两次行为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在认定“多次盗窃”的次数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不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的次数计算在内,那么其第三次行为仍旧是行政不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多次盗窃包括已经受到的行政处罚,那么其盗窃500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从立法目的看,应当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计算在内。如果将行政处罚排除在“多次盗窃”之外,对盗窃惯犯而言,接受行政处罚反而可能成为规避刑事责任的方法,这显然不合常理,违背制裁的目的。这种处理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定罪并予以刑罚处罚,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已受的行政处罚次数在刑事评价时作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依据而存在。
在刑法规范中多处规定的实施某种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数额累计计算”关系到罪与非罪,关系到刑罚的轻重。首先,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如赵某先后为A、B两公司的工作人员,两公司都涉嫌单位走私,赵某是其中直接负责的人员,那么对其行为的追究只能是分别累计在A、B两公司的未经处罚的数额,而不能将两个犯罪中的数额累计。①冯先美:《在不同公司实施单位走私可否累计数额追究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2007年第11期。其次,累计的行为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从每次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多次实施某一行为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的组合:第一,多次行为中每次行为均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犯罪行为。第二,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第三,多次行为中部分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犯罪行为;部分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违法行为。就第一种组合形式而言,因为其所涉及的是同种数罪和连续犯,数额累计计算没有疑问,也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在此不赘述。第二、三种情形则涉及到如何对待违法行为的问题,对这些违法行为是否均应累计,如何累计。针对第二种组合方式,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的,对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而理解为未经行政处罚的一并累计为犯罪,是一种将行政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跨越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与分权原则不符,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越权行为。如果允许如此解释,那么所有的未经处罚的行为均可因为未及时受到行政处罚而构成犯罪,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当然,在此应将多次违法行为与“一罪”的行为加以区别,有些行为每次单独看都因为数额不够犯罪的界限而只成立违法行为,但这些行为有可能是刑法所指的“一罪”的行为表现,如“蚂蚁搬家式”走私行为,利用邮寄方式逃税,每次所寄的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达不到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但这种行为是一种营业犯,即“通常以营利为目的,意图以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②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对营业犯,应当累计计算数额。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累计计算的类型应当说就是指的这种营业犯。第三种组合方式,其中一次或者几次行为构成犯罪,其他行为达不到犯罪程度的,应当累计。第三种组合方式中具体又存在如下三种可能的情形:犯罪成立在先,行政违法在后;最后一次为犯罪行为,之前为行政违法;犯罪行为在中间,前后均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2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已经废止,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再对盗窃数额累计计算加以规定,但是关于盗窃数额如何累计的问题仍旧存在。从一般法理层面分析,对于行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意,连续实施数个相同的危害行为,尽管刑法学上对其罪数形态存在连续犯、集合犯等不同归类上的争议,但对于其法律后果是不存异议的,共同主张认定为一个犯罪行为,仅作一罪处罚。③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4-700页。因此,对连续实施的行为,累计各次数额就成为“作一罪处罚”的必然选择,而无论各次行为中构成犯罪的行为居于违法行为前后。综上,刑法中所指的累计计算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如果其多次实施的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以避免将本应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累计成为犯罪。再次,对于累计的时限,即应当累计计算多长时间内的未经处罚的数额,现行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累计的时限,有些则规定了累计的时限。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抢夺公私财物,未经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笼统规定了未经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追诉的累计计算数额。这里应当追诉是指应当受刑事追诉还是指未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概追究,不得而知。对累计计算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多次行为中,对于构成犯罪的单次行为,应当以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为准,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单次违法行为,则应当以处罚的追诉时效为准”④叶良方:《刑法中数额的性质及其计算》,《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笔者同意这种区分时效的观点,按照此观点,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如逃税的追究期限为五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期限为六个月等以外,多数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应为两年,超过两年发现的,不得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连续犯或者继续犯的责任追究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只应当累计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内的数额,超出有效追究期限的不应当累计。
三、行政处罚对刑事案件审理的影响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是并行的两种责任,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行政法和刑法规范,因而构成违法与犯罪的竞合时,究竟应当如何处罚。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选择适用,即只能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选择其一进行处罚。理由是“一事不再理”;二是附条件并科,即在竞合时,任何一个“罚”被执行后,另外一个罚没有必要执行时就可免除;三是并行适用,即主张既要适用刑事罚又要适用行政罚。①李晓明著:《行政刑法学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从分权的角度,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互相不能代替,正如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一样,在追究刑事责任时不妨碍民事责任的承担,法律不因为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应当采用并行适用处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从《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可以看出业经行政处罚过的行为仍可予以刑事追究,②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罚金。对同一个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评价并不矛盾。但是从实体上说,行政犯罪应受双重处罚与实际上是否受到双重处罚不可混同。由于程序的复杂性和处理上的公正性,有时会出现不能并行适用的情况。程序上看,绝大多数的案件是由行政机关先行调查处理,先行做出行政处罚。对行政机关的先行处理,于审理同一行为的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而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程序上如何对待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二是实体上审理刑事案件并作出刑事处罚时,如何处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关系。
从程序上说,一个行为同时构成行政违法与犯罪时,在处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上,应当采取“刑事优先”原则,③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但行政处罚程序有时会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先,④周佑勇、刘艳红:《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适用衔接》,《法律科学》1997年第2期。这可能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一是不当考虑了某些因素而先行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明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而有意作为行政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谓之“以罚代刑”。“以罚代刑”是替代主义衔接模式带来的现实困惑之一,也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行政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以罚款了之,该立案的不立案,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不移送,在涉及到经济犯罪时尤为突出。⑤张书琴:《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研究》,载戴玉忠、刘明祥主编:《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及惩罚机制的协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二是基于行政处理的客观需要,紧急情况下对行为人所作的行政处罚。三是行政机关将犯罪行为当作行政违法而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定性错误是业务能力造成,而有些则是行政处罚后发现了构成犯罪的新证据。行政处罚程序先于刑事处罚程序时,应注意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好案件移送与刑事立案时的衔接关系。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由于是行政机关缺乏正当理由故意以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理,应当责令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或者由司法机关根据法律程序自行决定立案审理,必要时要追究相关行政机关责任人员的行政与法律责任。对于第二种情况,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但行政机关发现该行为已构成犯罪时,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立案处理。对于第三种情况中由于业务能力所限将刑事降格处理为行政的,司法机关主动发现比较困难,但一旦发现也应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移送或自行决定立案处理。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后发现了新证据而认为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从实体上,同一不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在先给予行政处罚后,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如何对待这一行政处罚?首先要明确行政处罚对于刑事处罚有无当然效力。由《行政处罚法》第28条允许罚款、拘留和罚金、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折抵的规定,可以推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并不以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为前提条件。①章剑生:《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基于〈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之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但这一结论并非意味着刑事处罚应当然折抵行政处罚。原因一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不能全部折抵。原因二是当行政权越权时,司法权排斥行政越权的决定。
前文提到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时,应当按照“并行适用”的规则处理,但在具体适用时要考虑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由于具体制裁方式不同,有些制裁方式可以折抵,而有些则不能折抵。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都体现为国家对不法行为人的一种制裁,二者的制裁在具体方式上有重合之处,这不同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行适用。民事责任是一种补偿性质的责任,刑事责任是一种制裁性质的责任,二者同时适用不存在冲突,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制裁方式的重合有可能导致一行为两罚的处理结果。我国行政法学界一般根据行政处罚方式所作用的领域不同,将行政处罚分为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和申诫罚。人身罚也称为自由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者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包括拘留、驱逐出境。财产罚是强迫违法者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一定数量的物品,或者限制、剥夺其某种财产权的处罚。包括罚款、没收。行为罚是一种剥夺或限制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如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申诫罚,也称精神罚,是一种影响名誉的行政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包括警告、通报批评。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272-275页。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种分为主刑与附加刑两类,共9种。在刑法理论上,根据刑罚所剥夺犯罪人权利的性质,将刑罚分为生命刑 (死刑)、自由刑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财产刑 (罚金、没收财产)和资格刑 (剥夺政治权利)。由此可见,从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看,两者的区别明显但又有制裁方式的重合。对于性质相同的制裁,司法机关在处理犯罪行为并予以刑事处罚时应当将行政处罚中内容相同的制裁予以扣减,这样才符合一事不两罚原则。而对于行政处罚特有的制裁方式,并不属审查起诉需要审查的范围,也不涉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处罚,司法不需处理,行政责任的承担与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并行适用”。
行政权越权时,行政处罚能否在刑事处罚时予以折抵?行政处罚之所以可以折抵是基于处罚的公平性,即一行为不两罚,但前提是行政权的规范合法行使。如果行政权侵越了刑罚权,作为行政权行使结果的行政处罚并不当然对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机构有拘束力。如2006年5月张某因无证运输卷烟,案值26000元左右,被某市烟草部门以无证运输卷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查明张某于2003年3月、7月曾因无证运输卷烟,被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两次案值分别都在13000元左右。某市检察机关根据《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关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而生产、批发、零售烟草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3、曾因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的,非法经营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认为张某2006年5月的无证运输卷烟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第225条,应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并根据《关于办理违反烟草专卖管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的“多次”实施违反烟草专卖管理行为,未经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货值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计算,要求烟草专卖机关撤销2006年5月对张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追究其刑事责任。③史林炯:《涉烟行政与刑事处罚衔接》,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focus/focus/200610/2006101217931_23116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18日)。又如《刑事审判参考》中的第378号案件:郭金元、肖东梅非法经营案——被行政处罚过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否计入犯罪数额?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8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在该案件中,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金元于2001年5月11日将其非法经营的172件卷烟,从富平运回渭南时在临渭区大什村被西安市阎良区烟草专卖局查扣,总价值15.432万元的事实,经查,此事实已被西安市阎良区烟草专卖局经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审批,依法作出行政处理,且合法、正确。在累计计算郭金元非法经营烟草价值数额时,不能将该笔数额再累计计算予以刑事处罚,故此笔不应计入被告人郭金元非法经营数额之内”。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法院对郭金元于2001年5月11日非法经营卷烟172件 (价值15.432万元)的事实,以已被西安市阎良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作案数额不能累计计算再作刑事处罚为由不予认定,有违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8日公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七十条和1996年10月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于法无据,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对已经行政处罚过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所以对已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再予刑事处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2)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的追诉标准,非法经营5万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2001年7月9日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发现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作了具体规定,但阎良区烟草局仍依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对郭金元作出行政处罚,显属违法,没有法律效力,故对该笔已经行政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当计入犯罪数额。从以上两个案件中可以看出,已经行政处罚过的违法行为,由于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范围“以罚代刑”,并不具有当然的效力,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时不受其拘束,其所处的罚款不予折抵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