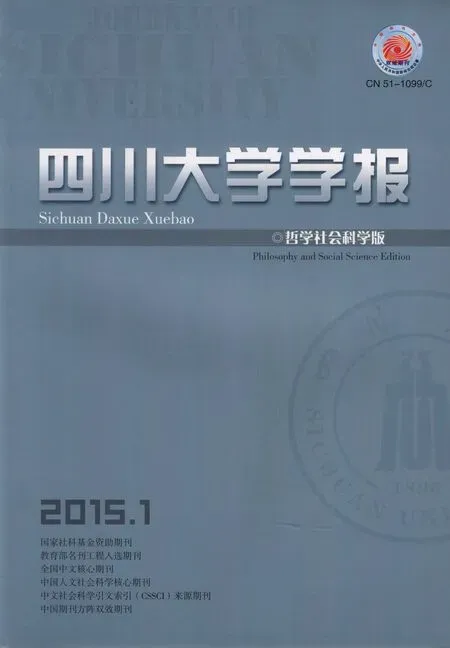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 “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 “乡愁”书写
杨 慧
199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黑婴①黑婴,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1915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祖籍广东省梅县,客家人,七岁时回故乡读书,十三岁又回棉兰,读英文学校,同时在一家华侨报馆《新中华报》半工半读;1932年只身到上海求学,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并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帝国的女儿》,1933年出版散文集《异邦与故国》。抗战爆发后自上海重返棉兰,任《新中华报》总编辑。1950年回到中国,进入《光明日报》工作,曾主编《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东风》,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1985年离休,1992年10月逝世。参见千仞:《黑婴生平简介》,见《生活报的回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96页。命名为“新感觉派后续作家”,②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9页。根据该书“后记”介绍,包括“海派小说”等内容的第十四章由吴福辉撰写。而这样的评定及相关叙述均脱胎于这本著作的作者之一吴福辉先生的另外一部更早一些的海派文学研究专著,但稍有不同的是,在该书中,黑婴被称作是“新感觉派的后起之秀”。③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0页。从“后起之秀”到“后续作家”,这大概是吴先生为适应文学史公允严正的特有文风而做的修辞调整,但其共同而关键的意指都在于:黑婴是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最为优秀的模仿者和继承人。这一看法基本上也是当下学界的共识,不过早在黑婴成名之初,就有评论者指出他自有区别于穆时英的文学独特性。④锦枫:《记黑婴》,《十日谈》1934年第46期。而在吴福辉看来,“黑婴是南洋华侨学生,创作一直带着这个南洋背景”,因而他那与众不同的“新感觉性”正来源于“海外游子”的“流离感”。⑤参见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80-81页。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黑婴的小说里凸显了种族和国籍的问题,都市流离感中揉进了异国飘零的游子情怀”。⑥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笔者认同上述学者对于黑婴文本“乡愁”的发现,而本文的主旨则在于给予其更加深入的历史化、语境化和个体化解释。进而言之,作为唯一一位被193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坛接受的南洋华侨作家,⑦韩侍桁认为1933年前后文坛上涌现出六位“可以当作新起的作家而无愧色”,即臧克家、徐转蓬、沙汀、艾芜、金丁和黑婴。参见侍桁:《文坛上的新人》,《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此外,1933年12月《矛盾月刊》第2卷第4期曾编发题为“一九三三年文坛新人”的一组照片,分别为徐转蓬、黑婴和万国安。黑婴的海外游子身份绝不仅仅是可以被一笔带过的作家背景介绍或文本主题描述,恰恰相反,华侨身份理应成为追问黑婴文学独特性的起点。或许我们需要接续思考的是,黑婴的华侨身份与南洋经历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他的文学叙事?他的那些始终扭结在文本中的乡愁书写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脉络和个体亲在的生命印记?它们带给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哪些新鲜的变化?通过上述追问,我们或许可以再次突破海派文学研究的“临界点”,在“‘现代’的追认和‘摩登’的礼赞”之外,①解志熙:《序》,张勇:《摩登主义》,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2页。探寻黑婴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经纬。
一、“民国时态”的南洋书写
1932年黑婴在棉兰第一次读到了穆时英的小说《公墓》,马上就被“那抒情的,带着淡淡哀愁的情调”所吸引,并由此喜欢上刊发这篇小说的《现代》杂志。就在这一年黑婴回到祖国,成为暨南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一名侨生,并登门拜访了穆时英,从这个“声名日噪”的作家那里获得了“最初的友好”。②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在这次“一个作家同一个爱读他的作品的读者的会面”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穆时英对黑婴的南洋华侨身份很高兴,对南洋情况也很感兴趣。或许正是穆时英对南洋和华侨的关注促成了他和黑婴“最初的友好”。无独有偶,1933年夏,正在筹划出版《无名文艺月刊》的叶紫和陈企霞如约来到黑婴在暨南大学的宿舍。在这初次见面的交谈中,叶、陈二人同样被黑婴的南洋华侨身份和殖民地成长经历深深打动。③黑婴:《叶紫与无名文艺》,《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重温黑婴的这两次文坛交往,我们不难读出隐喻的味道:在穆时英那里,黑婴靠近了“新感觉派”的文学技术和都市态度;从叶紫那里,黑婴体会了左翼的文学担当和革命关切,而这些秉承着不同文学气质的作家却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黑婴的南洋华侨 (南侨)身份。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聚焦于此?这一聚焦行为又隐藏着国人怎样的南洋认知与南洋想象?
正如时人所论,“南洋这个南字,在欧洲人的载籍中,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识,都是没有的”。④佐新:《南洋华侨的分析》,《南华评论》1932年第3卷第9期。进而言之,区别于“远东”、“中东”等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 (西方)地理命名,“南洋”是中国特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理名词。根据李长傅先生的考证,所谓“南洋”,“南者指方向,洋者指海外,与东洋、西洋成对立之情势”。⑤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6月1日。追溯起来,“南洋”始见于清人的《海国见闻录》等文献,清末通行于官牍报章,但因晚清有南北洋大臣之官职,故该词义尚在杂糅之中。直到民国成立,国内南北洋之称渐不惯用,作为南洋群岛之简称的“南洋”“遂成地理学上惯用之名词”。李长傅认为,厘定南洋的地理范围有三个“中国”标准,并且据此对“南洋”做了地理区划。⑥这三个“中国”标准是:1.地理上与中国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2.历史上或为中国属邦,或在中国势力范围;3.现为华侨集聚之地,经济上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南洋的具体地理范围如下:1.南洋半岛,又称印度支那半岛,包括法属印度支那 (今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暹罗王国 (今泰国)、英属马来半岛 (今马来西亚、新加坡);2.南洋群岛,简称南岛,又称马来半岛或东印度半岛,包括英属北婆罗洲 (今文莱)、荷属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葡属帝汶岛东部 (今东帝汶)、美属菲律宾群岛 (今菲律宾)。参见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李长傅编:《南洋地理志略》,《南洋研究》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1日;李长傅编:《南洋地理志略》(续),《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1日。按,纽几尼亚/巴布亚岛 (今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虽在地理上不属南洋,但因政治上与南洋殖民地主要宗主国荷兰和英国关系密切,故亦属于南洋范围。参见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南洋研究》第3卷第6期,1931年6月1日。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地区的官方称谓变成了“东南亚”,“南洋”遂成历史陈迹。
综上所述,“南洋”这一地理专名负载着“民国时态”重要的思想意涵:1.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2.华侨的中国认同与民族意识;3.国家的孱弱与护侨的无力;4.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华侨的苦难。而在此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语境之中,“南洋这个名词,大概在国内知识分子的脑海里都有这个印象的存在”。⑦许道龄:《南洋华侨没落的原因》,《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8、9期合刊,1937年1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内地作家都有过“下南洋”的经历,他们或逃亡,如洪灵菲;或游历,如老舍;或工作,如汪馥泉。特别是通过时任棉兰《南洋日报》编辑的汪馥泉与国内文友的通信,我们发现陈子展、叶鼎洛、钟敬文等人都曾有过具体的南洋工作打算。⑧参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10、156、215页。正是缘于诸如此类的南洋经历或南洋想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南洋叙事。⑨比如许地山的《辍网劳蛛》、《商人妇》,洪灵菲的《在木伐上》、《大海》,许杰的《椰子与榴莲》,老舍的《小坡的生日》等。参见王瑶:《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东南亚》,《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由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联华公司摄制的《母性之光》在上海上映,并轰动一时。多年以后,田汉对这部南洋题材的电影的回忆或许能够让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上海的“南洋氛围”:“我虽至今没有到过南洋,却因种种缘故,对南洋兴趣很高,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我研究过各地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我非常愤慨于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压迫和对我国侨民的屠杀。”[10]田汉:《影事追怀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也正是在1930年代初上海浓郁的“南洋氛围”之中,读者注意到了擅写“椰子林”、“水手”、“黑妮子”等南洋风情的黑婴,[11]郑康伯:《“帝国的女儿”》,《现代出版界》1934年第26、27、28期合刊。更有评论者猜度,“黑婴”之名缘自这位“生长于‘赤道线’上”的作家特有的黝黑肤色。[12]参见前辙:《1933年文坛的新人》,《十日谈》1934年第17期。不过,黑婴的文学志向远不止于此。出于南侨独特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黑婴的文学写作很快突破了那些在外界看来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符号,镌刻出充满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华侨青年以真诚之笔饱蘸情感”,[13]素明:《理解父亲》(代序),蓝素兰主编:《黑婴文选》,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页。黑婴在上海书写了其文学生涯的光辉岁月,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留下了南侨作家的叙述。
二、认同与疏离:祖国的“怀抱”与侨生的“寂寞”
1932年12月,黑婴以其真名“张又君”发表了近乎归国感言的散文《归国的途中》,文中借由叙述人之口,黑婴颇为动情地讲述了自己寻找“祖国”的艰难历程:童年时不知祖国为何物,长大后明白自己是“中国人”,决心“回到祖国去受一回洗礼”,如今终于“生活在大上海的怀抱中”。[14]张又君:《归国的途中》,《新时代》第4卷第2期,1933年3月。
通过那些带有自传色彩的文本寻绎黑婴的归国之旅,可见其中所饱含的经年期待。在小说《爸爸上园口去》中,年仅13岁的主人公渴望回到中国读书,并坚信自己的“上海”之梦一定会实现。①黑婴:《爸爸上园口去》,《中学生》第38期,1933年10月。在千万南侨青年的心中,“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点”,代表着“祖国的怀抱”,而回到上海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和人生道路的抉择。“回国之旅”让黑婴散文中的叙述人第一次走出棉兰,观察更为广阔的南洋。在新加坡街头,他看到马来半岛像波浪一样涌进来的经济恐慌;感受到了中国政府侨务委员们难以想象的华侨痛苦:他们受到殖民统治者的经济剥削与精神威迫,丝毫没有思想自由;②黑婴:《归国杂记》,《十日谈》1933年第14期。而面对槟城“一个中国字也不认识”的土生华侨—— “峇峇” (男孩)和“娘惹” (女孩),他越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到上海接受现代的中文教育。③黑婴:《过槟城》,《社会月报》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
在小说《我的祖国》中,主人公怀着一颗“波涛那么急激地跳”的心,来到上海这“伟大的都会”,感受到“祖国的怀抱比母亲的更温柔”。在家信中他幸福地写道:这所大学“有不少生长在异国的人,而大家相逢了。我们是多么热烈地握手啦!……放心吧,祖国会好好保护这十七岁的少年的”。然而,在祖国的怀抱中“醉了”那般的生活很快被“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沪战的国难所改变,他开始带着“一颗大了一年,有点异样的心”重审上海,并决心将“悲哀的眼泪,创痛的灵魂,和这没有死去的身子”献给受难的祖国。④黑婴:《我的祖国》,《中国文学》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1日。遗憾的是,救国热忱尚未消退,他的上海生活却开始被“寂寞”包围。在第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中,黑婴也曾将自己创作的直接动因解释为寂寞。⑤黑婴:《自序》,《帝国的女儿》,上海:开华书局,1934年,第3页。然而,如其所言,受教于心仪的大学,与众多年龄相仿、经历相近的同学朝夕相处,又怎么会如此寂寞?
对此,我们需要对黑婴在暨南大学的侨生生活进行考察。暨南大学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江总督端方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其后经过停办、复校和迁校上海等诸多变迁,1927年由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⑥参见郑洪年:《国立暨南大学创立及沿革记》,《暨南校刊》1933年第85期。该校“筑基于南洋华侨的全体,是华侨的最高学府,也是华侨的领导机关”,⑦南洋文化事业部:《为南洋问题敬告本校全体教职员与全体同学》,《暨南校刊》第3期,1929年9月16日。以培养华侨海外发展能力为特质,⑧陈刚父:《暨南大学的特质》,《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学生以“沟通中南文化,发展海外事业”为使命。⑨江应梁:《暨大学生的双重使命》,《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不过虽说是侨校,但内地学生还是占了大多数,侨生与内地学生数量之比大约是1:3。[10]193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学院侨生80人,内地生205人,而整个学校侨生149人,内地生435人。参见《国立暨南大学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暨南校刊》1936年第182期。而两者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精神气质,自然使他们彼此倍感陌生。《我的祖国》中的叙述人在入校之初,就感受到了“祖国的青年”的“淡漠”。而在小说《初秋的风》中,相比于“粗头发,赤色皮肤的强健的”洪姓侨生,其章姓内地室友则显得优柔寡断、气量狭小,章的女友荷同学对于南洋的印象更是仅限于“咖啡”与“马来半岛的风光”。[11]黑婴:《初秋的风》,《新时代》1933年第5卷第3期。不仅如此,对于南洋侨生,上海当地人也觉得很是新鲜:“暨南大学在沪西真如镇的北首,……一群异国情调的青年,异样的面相,异样的服装,异样的狂歌和跳舞,把乡村的农民怔住了。……那乌黑的脸,粗肥的腿,哄然的哗笑,以及古怪的马来语,使我们可以想见南国的风物。”[12]曹聚仁:《暨南大学》,《涛声》1933年第2卷第24期。曾在暨南大学任教九年的曹聚仁为南洋侨生总结出一种“天真,热情,不计利害得失”的“暨南精神”。[13]曹聚仁:《暨南前页》,《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56页。对此区别与隔阂,校方亦深有体认:“生长异邦的华侨子弟,其秉性习尚,都不免和国内青年有多少的不同,他们的优点,在于英勇果敢,豪迈爽直,但他们的缺点也就在此种性质的过度发达而流于粗莽暴戾。同时来自国内各省的学生,便又不免有些‘软绵绵的’畏葸怯弱,夸诞浮华。合这些千差万别的学生于一校,……实在是不容易的事。”①叶绍纯:《暨大今后之训育》,《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
1934年7月,黑婴在仰慕已久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小伙伴》。在这篇“流浪汉”小说中,黑婴在一些看似粗野蒙昧的小游民身上,发掘出常人所缺乏的纯朴、坚强与勇敢。②黑婴:《小伙伴》,《现代》第5卷第3期,1934年7月1日。而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不仅体现了黑婴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更折射出他作为南洋侨生的“强劲的性格”。③黑婴曾写道:“生长在南洋的孩子,总是活波可爱的,好动的,强劲的性格教他们每天都打一次架。”参见黑婴:《南洋之街》(一),《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30日。
老陈居然不知道于魁智是谁。他痴迷京剧,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于魁智的《四郎探母》。《四郎探母》之后,是马连良的《借东风》。
如果说南侨学生因独特的南洋文化习俗而与内地同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那么生硬刻板的学校教育则加深了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失望。南侨子弟“对于富有革命性的热心教员,非常尊敬。腐化、消极,及头脑顽固者,非常讨厌。思想趋向新奇,陈旧学说极难引起同情”。④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1933年第3期。在黑婴的小说《文凭》中,主人公姜仲海对那些“留声机似地”讲课的“死板板的教授”很是反感,更为关键的是,他的质疑并非仅限于暨南大学一隅,而是深入到中国大学教育本身。因此,在入学三个月后,姜仲海就选择了退学,“像扔掉一块什么废物那样扔弃了对于一张大学文凭的希望”。⑤黑婴:《文凭》(续),《通俗文化》1935年第2卷第10期。
现实中的黑婴似乎就是自己小说主人公的模版。在《文凭》发表前一年,即1934年秋,已在沪上文坛小有名气的南侨学生黑婴做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辍学。目前学界有关黑婴生平的考述均确认其1932年进入暨南大学外文系,但均未提供毕业信息。⑥参见巫小黎:《黑婴传略及创作年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四分册“黑婴”词条,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61页。1932年秋的一份《侨生资格审查委员会通告》中有“张又君”这个名字,⑦按照暨大规章,凡新生入学后需查验各项资格证明文件。张又君在检验无误通知领回证件学生之列。参见《侨生资格审查委员会通告》,《暨南校刊》1932年第35期。可证前述入学信息无误。然而,在1934年秋暨南大学第一学期学生注册名单中却再没有出现“张又君”或“张炳文” (原名)的名字。⑧“第一学期”的起止时间为1934年9月2日至1935年1月31日。参见《国立暨南大学二十三年度校历》,《暨南校刊》1934年第105期。按照暨南大学学则,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均为四学年,分八学期修完。⑨参见《国立暨南大学学则》,《暨南校刊》1936年第160期。因而,黑婴应于1936年毕业,至迟也不超过1937年,而在1936年和1937年度的暨南大学毕业生名单中均没有他的名字。[10]参见《历届毕业生名录》、《本届毕业生名录》,《暨南校刊》1937年第213期。由此推断,黑婴很可能在1934年就辍学了。[11]黑婴的自述也支持这一论断:“自幼就念书,一直念到去年,出了学校靠着写作去换饭吃。”刊发此文的《青年界》杂志是月刊,考虑到截稿时限,黑婴写作并提交此文的时间该在1935年,那么文中的“去年”应为1934年。参见黑婴:《我还没有职业》,《青年界》第9卷第1期,1936年1月。此说还有一个旁证,1934年10月19日一位自称认识黑婴的评论者指出:“他以前在暨南念书,这学期却不继续了。”参见锦枫:《记黑婴》,《十日谈》1934年第46期。
黑婴或许从未想到,自己曾经满怀期待、踌躇满志的归国求学之路竟以如此方式戛然而止。虽然黑婴自此成为职业作家,但是我们不难想见,这一告别昔日梦想的过程一定伴随着深深的疏离与彷徨。而这一如影随形的寂寞感不仅激发了黑婴的写作,而且左右了他书写的情绪。于是,黑婴小说中的主人公由于寂寞逐渐患上了“怀乡病”。在小说《怀乡病》中,主人公在“做了一场乡梦以后”,心底生发出蚀骨般的乡愁。[12]参见黑婴:《怀乡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8日。小说《黄昏》的主人公每到春天——在这与南洋温暖气候相若的季节——都会成为“怀乡病者。”[13]黑婴:《黄昏》,《矛盾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3月。而在散文《过年》中,黑婴更是深情抒发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离愁。[14]黑婴:《过年》,《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19日事实上,正是这疏离于上海的乡愁,使得黑婴初期作品呈显出其热烈的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的“南岛怀恋”。[15]黑婴:《南岛怀恋曲》,《帝国的女儿》,第34页。小说《没有爸爸》就做了这样的表达:温暖的南岛和美如桃花源,那些外来的闯入者是邪恶的破坏者。①黑婴:《没有爸爸》,《帝国的女儿》,第176页。
1934年秋天的辍学彻底改写了黑婴的人生轨迹:他从此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深入到“魔都”上海万花筒般的缭乱生活。②“魔都”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用来形容上海的“造语”,出自其1924年取材自上海之旅的小说《魔都》。参见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增补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109页。不过,黑婴虽然离开了暨南侨校,但缠绕在他身上的南洋关切与家国期待不曾褪去,而此后“魔都”生活的历练,更重塑了他观照南洋和寻求自我的文学视野。
三、“咖啡座的忧郁”:别有意蕴的乡愁表达
1930年代的上海,星罗棋布的咖啡馆可谓是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一道亮丽风景,并因此成为“新感觉派”乃至海派作家反复书写的都市空间与文学主题。在海派作家张若谷看来,这些咖啡馆不仅是文人雅集的绝佳去处,而且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③参见张若谷:《饮食男女战争》,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第145页。咖啡馆代表着追慕西洋——特别是法国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上海城隍庙的茶馆与法租界咖啡店的差距几乎就是从蒙昧到文明的距离。④参见《文艺茶话》,《文艺茶话》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15日。然而,对于同样徜徉于十里洋场的南侨作家黑婴而言,咖啡馆却有着别样的意蕴。
黑婴生长的荷属印度是咖啡的重要产地之一,而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之下隐藏着南洋殖民地人民痛苦的历史记忆。1696年荷兰殖民者将咖啡由阿拉伯半岛引入爪哇试种,1711年取得成功。1830年荷印殖民政府总督范·登·波士在爪哇颁行“强制栽培制度”,咖啡由此成为“强制栽培”作物。该制度规定,土著种植者必须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政府指定作物,收获物则交给政府抵偿税收。然而实际征用土地的比率远超五分之一,大部分地区是三分之一,有些地区甚至高达二分之一,由此关乎当地民生的基本粮食种植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引发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当地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是当时荷印殖民政府引入华侨“契约工人”的主要原因之一。⑤参见朱杰勤:《十九世纪中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契约工人》,《东南亚研究资料》1961年第2期。经过两百余年的种植推广,咖啡在整个荷印都有栽培,黑婴的家乡苏门答腊东海岸正是咖啡种植面积最多的地区之一。1929年整个荷印的咖啡产量高达80702吨,占世界咖啡总产量的5.9%,仅次于南美、中美,位居世界第三位。⑥参见周汇潇:《东印度之物产》(续),《南洋研究》第5卷第5期,1935年12月1日。
正因为海量的出产与长久种植的历史,咖啡成为南洋重要又普通的日常饮品,咖啡店亦是遍布街头巷尾。在那些有着“常年不夜城”之称的南洋都市,人们大都“中午匿处室中,以避炎日,入夜则三五成群,以滨海大马道咖啡馆为群众娱乐场”。⑦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151页。1928至1929年间,左翼作家许杰为躲避国民党追捕逃往吉隆坡,担任华侨日报《益群报》总编辑,他在晚年曾忆起南洋亲切而自然的咖啡文化。⑧参见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八),《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黑婴的故乡棉兰是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州的首府,“规模宏伟,气象堂皇”,堪称“东方新都市”。⑨参见郑健庐:《南洋三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77页。据1934年1月的统计,棉兰当时共有1064家华侨商店,其中“咖啡茶室及旅馆”就有127家。[10]这一数字仅次于“粮米粮食杂货商”的207家,在各类商铺中排名第二。参见驻棉兰领事馆:《棉兰华侨工商业统计》,《外交部公报》1934年第7卷第8期。黑婴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亦写到,故乡的“南洋之街”,每夜最迟关上店门的总是一家有着海南小伙计的咖啡店。[11]黑婴:《南洋之街》(二),《申报·自由谈》,1935年5月20日。
比之于“个性”极强,外人难以入口的榴莲,[12]许杰认为榴莲是整个南洋社会的象征,“要做老南洋的人,是非学会吃榴莲不可”,而这种以臭为香的“学会”,正是华侨丧失人格的表现。参见许杰:《榴莲》,《椰子与榴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第54-55页。移植而来的咖啡可谓南洋社会文化杂交状况最为突出的表征。具体到华侨而言,尽管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重重宰制,但是凭借勤俭耐劳、坚忍奋斗的精神,他们与当地文化深度融合,开始学会品味咖啡苦中之美,在遥远的异国形成根深叶茂之势。[13]曾有论者指出,华侨在南洋取得成功有三大原因:与土人妇女通婚,与土人友好,勤俭耐劳。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第159页。因而,咖啡和咖啡店不仅是南洋标志性的特产风物,更体现了华侨独特的生存样态。故此,当生长于南洋的黑婴在遥远的上海与咖啡相遇,咖啡自然而然地成为家乡的印记。另外,上海咖啡馆往往兼具舞厅功能,而在南洋“跳舞是白种人家庭常见的娱乐,侨生受其影响,故跳舞的经验极为丰富”。①参见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1933年第3期。因而,常到咖啡馆坐坐,喝杯咖啡品味家乡味道,这既是黑婴南侨生活习惯的自然延伸,也是其慰藉乡愁的一种方式。然而睹物思乡,黑婴小说中得了“怀乡病”的主人公在寂寞时刻甚至不敢喝咖啡——这“家乡的出产”;②黑婴:《圣女》,《好文章》第8期,1937年5月。不过,在快乐时分,那来自故乡的咖啡颜色则最适合表达心中洋溢的幸福。③在小说《Trail》中,美丽的少女李韵就“穿着咖啡色的春装,戴了一个咖啡色的小塌帽儿”走到了主人公的心里。参见黑婴:《Trail》,《西北风》1937年第7期。
与黑婴家乡那些朴素的咖啡馆不同的是,上海的咖啡店更时尚,浸染着舶自日本的“咖啡侍女”文化。1927年10月,张若谷就撰文指出,“咖啡侍女”带来的“异性方面的情感满足”正是咖啡馆的三种“乐趣和好处”之一。④参见张若谷:《现代都会生活象征》,《珈琲座谈》,上海:真善美书店,1929年,第4-9页。而到了1930年代初,“咖啡侍女”之风已流布沪上,以至于“真正咖啡座,营业较有轻佻女招待者远逊,咖啡店老板为投客所好,不能不转变其作风矣”。⑤郭兰馨:《蜃海楼随笔》,《珊瑚》1933年第3卷第9期。1933年7月,黑婴在茅盾主持的《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五月的支那》,其主要的“时空体”正是一家有着白俄侍女的咖啡馆。然而,茅盾在本期杂志的“社谈”中对这篇小说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黑婴此篇在内容上非常贫弱。作者也许要借一个外国水兵的荒淫娱乐来表示‘五月的支那’现在是怎样的‘平静’罢?但是衬托得没有力量了。”⑥茅盾:《新作家与“处女作”》,《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该文首发于《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1930年代初的中国,因为关涉“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九”国耻日以及“五卅”纪念日,原本平常的“五月”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涵。而在这篇小说中,黑婴不仅以曾参与制造“五卅”惨案的英国水兵佐治为主人公,而且使用了第一人称相对封闭的叙事视角,因而没能深入批判这位英国水兵饱含殖民气息的“上海故事”。这些应该就是茅盾所言“衬托得没有力量”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我们将考察重点从英国水兵佐治转到白俄咖啡侍女柏拉芙娜身上,将会发现黑婴独特的问题意识。
小说中,自称“地球流浪者”的英国水手佐治来到上海——他猎艳之旅的又一站,却在白俄咖啡侍女柏拉芙娜那里遭到了“毁灭性”狙击。这位白俄姑娘出人意料地以“今晚必须回家看母亲”为由拒绝了他的“俄国大餐”邀约,对于沉迷于欲望游牧的佐治,“母亲”这一久违的字眼激发了他无边的乡愁,让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失去母亲的流浪者”和“怀乡病”人。在黑婴看来,乡愁是迷乱都市生活中最为安全的心灵锚地,并且有着疗救人性的力量,可以说,此时的白俄侍女柏拉芙娜既是乡愁的激发者又是人性的疗救者。
黑婴1933年发表的小说《蓝色的家乡》,同样是以白俄咖啡馆侍女为主要人物,只是主人公由英国水兵佐治换成了南洋华侨“我”。小说中,白俄侍女娃丽娜那双蓝色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大海的颜色,引发辽远的乡愁。不仅如此,这位“可怜的俄罗斯女儿”的悲惨的流亡命运更让“我”庆幸自己是个有家的“幸福的孩子”。⑦黑婴:《蓝色的家乡》,《妇人画报》第17期,1934年4月。
《五月的支那》与《蓝色的家乡》可被视作姊妹篇。这两篇思想内涵略显单薄的小说开启了黑婴“风尘女子”题材小说的“乡愁”主题,并且确立了她们作为“乡愁激发者”和“人性疗救者”的叙事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白俄舞女也曾出现在黑婴的“新感觉派”前辈穆时英的笔下。如小说《夜总会中的五个人》一开篇,就是一场“斯拉夫公主们”末日狂欢般的疯狂艳舞;⑧穆时英:《夜总会中的五个人》,《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G No.Ⅷ》中,有着白俄舞女身份的多重间谍康妮丽冷漠而悒郁,漂泊而又疏离于奢华而迷乱的都市生活。①穆时英:《G No.Ⅷ》,《文艺月刊》第8卷第5期,1936年8月。比较而言,在穆时英笔下,“白俄舞女”是一个“颓废”的符码,而在黑婴那里,她们则是充满乡愁的流亡者。
在1935年发表的小说《咖啡座的忧郁》中,黑婴描写了一间兼有舞厅功能的咖啡座,充分展现了上海的国际化:日本侍女、白俄侍女、白俄流浪者以及南洋侨青年,来自不同国家的各色人等汇聚于此,在醇酒和舞步中消磨苦涩时光。②黑婴:《咖啡座的忧郁》,《文艺月刊》第7卷第4期,1935年4月1日。这种洋溢于上海咖啡馆的异国情调,曾让很多海派作家惊喜不已。张若谷的文友—— “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家黄震遐就认为,那些镶嵌在法租界的白俄咖啡馆突出体现了上海的“世界主义”气质,只有能够拥有并畅享这一气质者“才是上海真正的市民”。③参见黄震遐:《我们底上海》,《申报·艺术界》1928年12月30日。不过,对于黑婴这样一位生长在有着“人种博览会之称”的南洋,④参见陈枚安编著:《南洋生活》,第149页。从小穿行在不同肤色、语言和文化的族群之间的华侨而言,⑤参见坚峰:《南洋华侨教育之现状》,《侨务月报》第3期,1933年12月。那令许多国人骇怪与惊喜的异国情调,不过是让他倍感亲切与熟悉的文化符码而已。小说中,“我”与日本侍女千代子颇为亲近,她不仅抚慰了“我”的苦闷与疯狂,更是劝“我”远离这种“流浪在舞场里,咖啡座上”的迷醉生活。在此意义上,千代子更像是“我”的姐姐,用无私的爱心和苦难的经验引领着一个迷惘少年成长。如若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此类“姐姐”形象在黑婴的风尘题材小说中经常出现,如《帝国的女儿》中的日本妓女勉子、⑥黑婴:《帝国的女儿》,《申报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春光曲》中的舞女茵子,而后者更是此类人物的代表。旁人眼中的卖笑舞女茵子,其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十六岁时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后来成为国民革命中的女战士,但随着革命落潮而不得不在上海的“黑夜中讨生活”。对照茵子的苦难经历,“在黑夜里摧残着生命”的主人公小希羞愧难当,最终在茵子的规劝下回到南洋家乡休养生息。⑦黑婴:《春光曲》,《狂流》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而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诗作中,黑婴也对咖啡侍女和舞女的乡愁表达了强烈的共鸣。⑧黑婴:《珈琲女》,《诗歌月报》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1日;黑婴:《舞女》,《诗歌月报》第1卷第1期,1934年4月1日。由此可见,黑婴对他笔下的风尘女子不仅怀揣深刻的同情,更抱有严肃的尊重,她们绝非情感消费乃至侮辱淫虐的对象,而是乡愁的激发者、人性的疗救者以及青春的领路人。
在黑婴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野兽般调戏咖啡侍女的外国水兵身影。《咖啡色的忧郁》开篇就出现两个调戏侍女的外国水兵,“蓝色的眼球要吞人似的放着光”。⑨黑婴:《咖啡色的忧郁》,《青青电影》第2期,1934年5月。而在《雪》中,走投无路的青年方吉秋在一家咖啡店中看见两个外国水兵肆意玩弄日本咖啡侍女,他突然想起负情的女友,竟然猛地“抓了女招待复仇似的揶揄着”。然而,这种取法帝国主义者压迫弱者的举动不过是饮鸩止渴的自我异化而已,只能让他继续像“幽灵”般游荡在青春的废墟中。[10]黑婴:《牢狱外》,《帝国的女儿》,第18页。1935年该小说改题为《雪》,连载于《春色》杂志。同时,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黑婴笔下也有颇具民族主义气质的“咖啡馆客人”。在小说《一〇〇〇尺卡通》中,“我”痛恨那些“凶狠得狼一样”的外国水兵,他们是“磨灭”咖啡侍女美美的“魔鬼”,面对美美的“厄难”,“我”想去“保卫”她,然而“摸摸自己的手膊:我低下了头”。[11]黑婴:《一〇〇〇尺卡通》,《新时代》第5卷第6期,1933年12月。总之,在上海普通的咖啡馆,从别人看似平常的调笑玩弄之中,黑婴不仅深深体会到了那些同为“漂泊者”的咖啡侍女们的乡愁,更敏锐地感受到了隐藏在那些“外国客人”身上的殖民主义气息,进而刻画了弱国子民饱含屈辱、愤怒、无奈乃至自我异化的复杂心绪。而追溯起来,黑婴的这种敏感无疑离不开南洋华侨殖民地生活的独特体验。[12]
结 语
1936年黑婴发表了短篇小说《南岛之春》,主人公南洋富家小姐“蕙小姐”曾在上海过了“两年的放情生活”,如今却从那些“视祖国于无有,看人生如空虚,因之尽情享乐的”南洋“高等华人”身上发现了行尸走肉般的恐怖。①黑婴:《南岛之春》,《内外杂志》第1卷第1期,1936年8月。这个文本并非黑婴的代表作,但却有着对于南侨青年命运不乏自传色彩的深入思考:一个经历“魔都”历练的南洋青年失去了很多单纯的美好,生发出更多的人生迷惘,但却由此获得了省察南洋的“中国视野”,从而让自己的乡愁有了稳固的祖国锚地。进而言之,在1930年代初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机加剧的历史语境中,黑婴难以通过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与国家关系建构自己的国家认同,但他却在一种笔者称之为“亡国的恐惧”的防御性意识中获得了坚定的认信——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祖国。而正因为有了祖国的锚地,黑婴的乡愁紧紧咬住了中国古典诗学根脉,即“因思念故乡而引起的愁绪”,②参见《重编国语辞典》第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61页。并没有进入“nostalgia”的层面,③“nostalgia”一词中文译作“乡愁”或“怀旧”,“这一英文词汇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参见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页。更没有演变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意义上的生命飘泊。
不可否认的是,年甫弱冠的黑婴缺少生活历练,文学素养也尚显单薄,商业化的文学生产方式更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些因素都拉低了黑婴的文学水准。尽管如此,黑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民国时态”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书写了带有自己生命印记的文化乡愁,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因而,“黑婴”笔名的真正意旨不仅在于南侨青年特有的肤色之“黑”,更在于“婴”——这是新一代南侨青年用“孩子的心去体验人生”,④黑婴:《自序》,《帝国的女儿》,第3页。去创作“成长小说”。就此而言,那些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