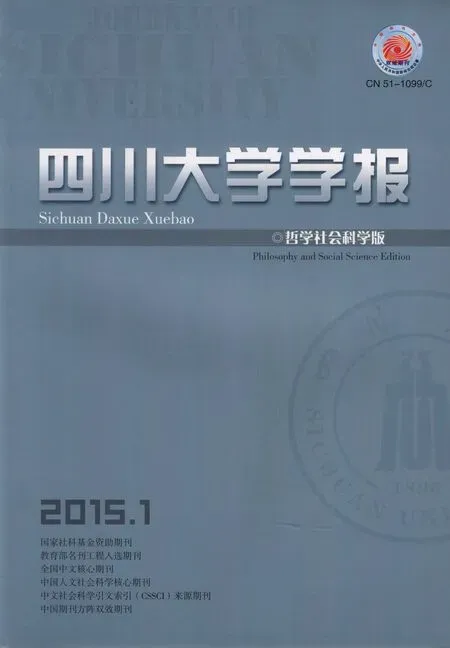原始宗教阶段的超自然观念的产生及其特点
刘长东
一、引 言
超自然观念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其在信仰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在宗教的四个基本要素①关于宗教的四个基本要素,中外学界持说略异,如吕大吉说四要素是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感情或体验”、“行为或活动”、“组织和制度”(《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76页);美国戴维·波普诺说是“圣物或圣地、仪式、信仰体系,以及信徒组织”(《社会学》,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0页)。中的地位,因宗教发展的阶段和宗教信徒所秉神学观之异而有所不同。如人为宗教阶段持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某些信徒,就怀疑甚至否定超自然观念的部分要素。但是,就更多的信徒而言,超自然观念的诸要素对其信仰起着必要条件性质的先决作用,而在宗教的四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尤其在更早的原始宗教阶段益是如此。因此,对超自然观念的探讨,无疑将有助于加深对宗教诸相关问题的认识。在学界关于宗教的本质和起源、信仰客体的性质、神学观的发展等理论问题以及宗教史和具体宗教现象的研究中,超自然性虽常见述及,然多是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质的推论基础,而较少见其本身被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在对它所作的为数不多的专门讨论中,论者大抵亦只说明其内涵,而罕论其在宗教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生、特点等问题。故笔者不自揣谫庸,尝就此类问题,分原始宗教和中、西方的人为宗教阶段之三部分,而试作浅探。②刘长东:《中国古代灵验故事在宗教学理论上的意义 (一)》,“东亚文献与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韩国交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成都,2014年7月。限于篇幅,兹先呈对原始宗教阶段的讨论,以就教于读者。
在进入讨论之前,试先说超自然观念的具体内涵、基本要素等问题。超自然观念最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于所谓宗教奇迹或曰神迹中,奇迹的灵验传闻与记载全都蕴涵有超自然观念;故对超自然观念的研究,莫善于以前人对宗教奇迹的论述和灵验记载为出发点或载体,结合对灵验奇迹的讨论以展开之。关于超自然性的具体含义,西方哲学家已有所论,如荷兰斯宾诺莎说:“奇迹就是一件不能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不能确指其与何种自然界的运行有关的事。”③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2页。法国霍尔巴赫说:“奇迹是超自然的现象,也就是与不变之神加给自然界的英明规律相矛盾的现象。”④保尔·霍尔巴赫:《袖珍神学》,单志澄、周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0页。德国康德言奇迹“是尘世中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原因,我们绝对不知道并且必然始终不知道其起作用的规律”。⑤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卷,第87页。德国费尔巴哈说宗教信仰就是确信“跟自然之规律与理性之规律相对抗的主观的东西”“具有现实性”,而“信仰所特有的客体,就是奇迹”,“奇迹不仅超出而且违反自然秩序和自然本性”。①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荣震华译,刘磊、荣震华译校,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下卷,第159、748页。诸说皆以为宗教奇迹之超自然性质的含义,乃指奇迹是与自然的本性、秩序、规律相矛盾而不能以自然的原因解释者。其说甚是。关于超自然观念的基本要素,可借中国古代关于灵验奇迹的故事以分析之。在此类故事中,奇迹的超自然性质主要表现于与人之利益无直接关系和密切相关的两方面。前者只是为了显现神灵的“临在”(presence),如佛骨舍利、佛菩萨像的无故放光等 (a类)。后者则是为了显示神灵对信与不信神的存在及信从和违背神谕者的赏罚,如佛菩萨为信众疗病、解刀杖之难、预示吉凶、降雨以纾旱灾,或佛菩萨对不信佛法、污辱神像者降以灾病死亡等 (b类),这些都是在现世利益上,神对其信徒与不信及轻慢者的劝奖、惩罚。而神灵使入冥者得以复活或超拔,使死者直接往生净土等奇迹 (c类),②凡此奇迹均极常见,考论者亦多,兹据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 (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2、59、64、74-76、79-80、84-88、77-78、96-100、127-128页)和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164、269-272页)所录材料而胪列。则是神灵对信徒的终极利益的关怀。此外,在道教经典中还有神的创世界、生万物之奇迹 (d类),③黄勇:《道教笔记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217页。周西波:《道教灵验记考探——经法验证与宣扬》,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第88-89页。不过因其与人之现世利益无直接关系,故罕见于奇迹证明的灵验故事。此等奇迹皆属与自然的本性、秩序、规律相矛盾者。若对上述奇迹再作抽绎,其超自然性又可化约为四个基本要素:1.就信仰的主体言之,信徒是灵魂不灭的 (如c类);2.作为信仰的客体,神灵是存在的 (如a类);3.就神灵的神性而言,神灵是意志自由的 (如b类)。4.在神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上,前者为创造主、立法者,后者是被造物 (如d类)。以上对超自然性质的内涵与要素的界定和抽绎,将是下文的论题探讨之基础。
在大多数宗教的观念中,既然神是世界万物的创造主,是自然的本性、秩序、规律的立法者,而如古希腊泰勒斯所云“万物皆充塞着神性”,④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0页。亚里士多德引“昔贤”之语亦云:“万物 (众生)莫不充塞乎神,凡我们眼所可见,耳所可闻,所有其它官能所可感知的一切事物,无不有‘神’在。”⑤亚里士多德:《宇宙论》,《天象论 宇宙论》,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7-298页。那么,灵验事迹的性质为何不可以被规定为非超自然性的自然事物或自然奇迹,而必须是超自然性的奇迹呢?对此疑问,借吕大吉先生之说似可移解,吕说之核心观点为神迹的超自然性是由神的基本神性所致。其推论过程大致可分为三:(甲)神作为“主宰自然和世界”者,其基本神性表现于神具有自由的意志和全知全能的能力。(乙)神能用其“不为自然律所限”的“超乎自然力之上的能力”,以实现其“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丙)因此,“神必须拥有废除自然法则,至少是在必要时暂时中断自然法则的效力,才能证明他是真正的神。惟有证明他废法,才能证明他是自然的立法者。奇迹便是神可以废法或中断自然法则的证据”。⑥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册,第234-235页。吕先生之说虽精辟,然犹未达一间。一是其说只关涉上述超自然性中的第3、4要素,而未及第1、2要素。二是吕先生对第3、4要素的讨论,因其论证方式之故,而显得论证的有效性不足。其论证方式,若从康德对两种判断的阐述来看,是近于分析判断式而非综合判断式的:⑦康德说“在含有主宾关系之一切判断中”,“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共有二种方法。或乙宾词属于甲主词而为包含于甲概念中之某某事物,或乙与甲虽相联结而乙则在甲概念之外。前一类我名之为分析判断,后一类则名之为综合判断”。而“所谓综合,就其最普泛之意义而言,即联结种种不同表象而将其中所有杂多包括于一知识活动中之作用”。“分析判断 (肯定的)其中宾主连结,视为相同之事物;凡其连结,不以宾主二者为相同之事物者,则应名为综合判断。前一类,因宾词对于主词之概念一无所增益,惟将主词之概念分剖成‘所含在其中构成此一概念之若干概念’(虽属混淆),故亦可名之为说明的判断”。“后一类则对于主词之概念加以一‘其所绝未含有,且即分析亦不能自其中抽绎’之宾词;故又名之为扩大的判断”。“吾人之知识由分析的判断绝不能扩大,仅我所已有之概念提示于前,而使我易于理解耳”;而“在综合的判断中,如欲知一实辞不包含于此概念中而又隶属之者,则必须于主词概念之外,别有为悟性所依据之某某事物”(《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5、87、37页)。上之所谓“宾词”、“悟性”,邓晓芒以今通用术语而译作“谓词”、“知性”(《纯粹理性批判》之《导言》,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注①),故正文从邓译。即吕先生论证中的 (甲)之自由意志和全知全能的神性,相当于主词;其 (乙)的“为所欲为”、“不为自然律所限”、“超乎自然力之上的能力”,以及其 (丙)的“废除”和“暂时中断自然法则”等,相当于谓词。其谓词 (乙)包含于主词 (甲)之中而未在 (甲)之外,谓词 (乙)对主词 (甲)的概念无所增益,而仅是对主词 (甲)的分剖性的说明,对主词 (甲)的原因的知识并未扩增。主词(甲)与谓词 (乙)之间只具有同一性关系。而 (丙)作为结论,它只是将主词和谓词的语序颠倒为先谓词 (乙)、后主词 (甲)的重组性之叙说而已。因此,吕先生对超自然性的第3、4要素的论证是近于分析判断式的,仅对超自然性作了同义异词的说明或复述,并未触及神迹具有超自然性的原因问题。此外,由于神迹的超自然性问题,与吕先生著作的论题序列中之神的存在、灵魂观问题密切相关,故在对后二问题的讨论中,吕先生亦论及超自然性的四要素中的第1、2、4要素,①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册,第141-151、189-206页。其中虽不乏精当之论,然同样不免有鞭辟而未入里者。
灵验故事的创作和传播显然主要以宗教“起信”为目的,对灵验奇迹的超自然性之原因的探讨则不妨从创作、传播者与灵验宣传的对象入手。灵验宣传的对象就其与灵验的创作传播者之关系而言,可分为三类:(1)同教之同宗与异宗者,(2)异教者,(3)无神论者 (包含部分经验论者、怀疑论或曰不可知论者)。灵验奇迹“起信”的效果实取决于三类对象接受奇迹的可能性之大小,而由于三类对象实含整个人类,因此对于三类对象接受奇迹的可能性问题,应结合人类心灵、精神活动以考察之。在此意义上,奇迹接受的可能性问题实质上同时亦是超自然观念的产生问题。在人类心灵、精神极复杂的活动中,有三种活动在其表现、功能上的区别甚为显著,它们即法国孔狄亚克所分的“本能、疯狂和理性”。②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洪洁求、洪丕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1-72页。而其中与奇迹接受的可能性或超自然观念的产生密切相关者,当为人的个体本能、社会本能、理性三者相结合而产生的需要之程度。兹先讨论原始宗教阶段超自然观念在人类理性活动与需要中的产生及其特点问题。所以先言理性者,乃因人纵然由其本能需要的驱动,而对超自然性有欲望,然在现实上,其奇迹接受的可能性之大小,实首先取决于其理性中是否本有超自然观念的安身之所,以及安身空间的广狭如何。至于本能的需要方面,以及上文所言二问题,即人为宗教阶段何以某些信徒怀疑或否定超自然观念的部分要素、神迹何以具有超自然性,则需在讨论中、西方人为宗教阶段的论题之后方可解决,故俟他文论之。
二、超自然观念在原始宗教阶段的人类理性中的产生
所谓理性,即推理之能力,如黑格尔说“我们一般时常和多次听见人说起理性,并诉诸理性,却少有人说明理性是什么,理性的规定性是什么,尤其少有人想到理性和推论的关系”。其实,“任何理性的东西也都是一个推论”,“理性的东西便只有是推论”。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5-356页。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下卷,第341-342页。推理有直接推理与间接推理之分,而更准确地说,理性就是作间接判断的推理之能力,如康德说:“理性实为推理之能力,即间接判断(由于包摄可能的判断之条件于所与判断之条件下)之能力。”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第265页。在宗教信仰的发生期,各阶段的原始宗教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说其中已尽含超自然观念的四要素,而它们正是原始人运用间接判断的推理之产物。
在超自然性的第1、2要素即灵魂不灭和神灵的存在问题上,中外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此二要素多与梦等现象相关。英国泰勒说,原始人从己之梦、幻觉而生己之肉体、生命、灵魂可分离的意识。推己及人而料想他人亦然,遂将其梦见的活人视为此人灵魂对己之造访。又“把出现在梦中和幻觉中的死人的形象看作是死人留在活人中间的灵魂”,从而“相信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其后推人及物,而以为动植物和武器、工具、食物、衣饰“及其他物品中有特别的灵魂”。在“我们看来没有生命的物象”,“蒙昧人却认为是活生生的有理智的生物”,“跟它们谈话,崇拜它们,甚至由于它们所作的恶而惩罚它们”。最后又由人类社会的结构等而推论,自万物有灵观中产生多神教之至上神的观念。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1、362、410、389-390、599-600页。法国列维-布留尔持论与泰勒亦相近,说万物有灵观包含两个连续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原始人在梦中看见了死人和离别的人”,“他相信这些表象的客观实在性。因而,对他来说,正如那些在他梦中出现的死人和离别的人的存在一样,他自己的存在也是双重性的”;即“他既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个人而实际存在着,又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可以离开身体而以‘幻象’的形式出现的单独的灵魂而存在着”。在第二阶段,“他们想要解释那些使他们惊摄的自然现象”,就“把他们对自己的梦和幻觉的解释加以推广。他们在一切生物身上,在一切自然现象中,如同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同伴身上,在动物身上一样,统统看见到了‘灵魂’、‘精灵’、‘意向’”。②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11页。在此方面,中国古文献和少数民族田野调查材料,亦有可证泰勒、布留尔之说者。③汉王充《论衡·纪妖》云“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梦见帝,是魂之上天也”(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918页)。《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梦书》云“梦者像也,……魂魄离身;……魂出游,身独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835页)。此二者皆可证魂由梦生之说。中国少数民族亦多有此观念,如景颇、傈僳、壮、珞巴、基诺、鄂温克、达斡尔、瑶、黎等族,或认为人做梦或生病时,暂离身体者为灵魂,或以为人死亡后,永离身体者为鬼魂;鬼魂凶恶而四处游荡,生人灵魂若遇之,会被鬼魂勾去而使人蒙横祸或死亡等(吕大吉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之《景颇族卷》第377-378页、《傈僳族卷》第716页、《壮族卷》第485页、《珞巴族卷》第696页、《基诺族卷》第934页、《鄂温克族卷》第173页、《达斡尔族卷》第298页、《瑶族卷》第239页、《黎族卷》第6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8、1999、2000年)。至于在万物有灵观、多神教之至上神观念产生的原因方面,中国少数民族亦多有印证泰勒、布留尔之说的田野调查材料,恕不赘举。据上可见,超自然性的第1、2要素即在这两个阶段,生自原始人之间接判断的推理。
超自然性的第3、4要素即神灵意志的自由和神造万物,原始人亦由推论而得之。如英国弗雷泽说人类的巫术时代之结束,是因“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他们是无力随意左右某些自然力的,而迄今为止他们曾相信这些自然力是完全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中”;遂用对于“比任何他所能支配的都更为强大”的力量之屈从,亦即“对神灵意志的屈从”,“替换了他不愿放弃的统治自然之权力”;从而自巫术时代进入宗教时代。④詹·乔·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7-89页。法国莫斯对弗雷泽之说的撮述,比后者本人之言更精劲简切,故不妨略引之:巫术是“人类思维进化的第一个阶段,宗教则是从巫术的失败和错误当中脱胎而来”。最初原始人以为“可以从思维当中创造他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他幻想着他是外部世界的主宰”,但“最终他发现世界并不允许他这么做。很快,他就把曾经认为自己拥有的神秘力量赋予了他的世界。以前人就是神,现在他知道这个世界为神所占据。这些神不再向他的意志屈服,而他却要去向他们献祭和祷告,带着崇拜依附于他们”。⑤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奥地利佛洛伊德亦说,人类最先以为自己是“思想全能”的,“可以经由一种简易的方法来控制世界和获取无法达到的目标”。其全能甚至到认为人本无死的程度,即“原始民族把生命的无限延长——不朽——认为是一件当然的事情。死亡的观念只有在稍后才被带着怀疑的接受”。⑥佛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98-99、112-113、115页。原始民族的死亡起源之神话传说、宗教经典所言人本有不死的可能性或人本长寿之观念,甚至中国的长寿或不死仙人的信仰、观念等,皆可说是原始人关于人本不死之信仰的反映或变型,乃原始人思想万能观念之孑遗。①人本不死或原有不死之可能性,从原始民族的死亡起源神话传说、宗教经典等可证之。如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采集有孟加拉湾安达曼岛人的死亡起源之传说,言某家有一母二子,一子因无意之自伤而死,此子之魂回家看望其兄弟,后者正忙于他事而于前者有所疏忽怠慢,遂被前者杀死。其母即“对人们说:‘发生的这一切你们都看到了;唉,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去,就像他们两个那样。’”岛民们自言“在此之前,人间并没有死亡这回事”(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0-161页)。此可证岛民以为在死亡起源之前,人乃不死者。又如《圣经·旧约》言上帝允许亚当、夏娃吃伊甸园中包括生命树在内的诸树之果,而禁止其吃分别善恶树之果,否则“必定死”。二人犯禁后,上帝恐其“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遂将其从园中逐出,“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世纪》2:16-17,3:22-24)。是见人若不犯禁,且吃生命树之果,本有不死之可能性。世界各民族亦有人本长寿之观念,如古印度婆罗门教之合教律、法律为一的《摩奴法典》,将历史分为四个时代,说“在第一个时代,人免于疾病,得遂其一切愿望,可享寿四百年;在第二及其以下时代,生命渐次失去其存在时间的四分之一”(法国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20页)。到原始佛教时期,人寿被夸大到本为八万岁,如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一《大本经》载释迦牟尼佛云过去“毘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尸弃佛时,人寿七万岁;毘舍婆佛时,人寿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3年,第1册,第2页)。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一五《转轮王经》则言在转轮王们御宇时期,人以其德行之退堕与增进,其寿命在八万岁到十岁之间递减和递增(《大正藏》,第1册,第522-524页)。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言人类历史分为渐次退化的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种族之五期。其中,黄金种族虽有死亡,然“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白银“种族的孩子在其善良的母亲身旁一百年长大”;黑铁种族“如果初生婴儿鬓发花白,宙斯也将毁灭这一种族的人类”(《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6页)。又,希腊神话言宙斯使潘多拉给人类带来诸种灾祸,于是“死神,过去原是那么迟缓地趑趄着步履来到人间,现在却以如飞的步履前进了”(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册,第6页)。是见古希腊神话中亦有人寿随世而短促的观念。中国亦有长寿如彭祖者之传说,关于彭祖的较早记载,见《国语·郑语》:“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韦昭注“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7页)。其寿数见《世本·氏姓篇下》“彭祖,姓篯,名铿,在商为守藏吏 (史),在周为柱下吏 (史),年八百岁”(《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秦嘉谟辑补本,第293页)。彭祖为个体之例,作为整体之长寿者,则有《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载黄帝“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能形与神俱,而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郭蔼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上册,第2-4页)。又《论衡·气寿》云:“儒者说曰:‘太平之时,人民侗长,百岁左右,气和之所生也。’”其《齐世》亦云:“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黄晖:《论衡校释》,第1册,第31页;第3册,第803页)。古印度、古希腊等的长寿观念与中国上古及其后道教的长寿或不死仙人之观念及信仰,均为人本不死信仰的反映或变型,当是原始的思想万能观念之遗存。然而正如佛洛伊德所说,当人们在发现“绝无可避免地必须接受死亡”之后,遂不得已将其思想全能“归诸于上帝”。②佛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12-113页。思想的重要工具是语言,故在原始人的巫术时代,不仅有思想全能观,且由之而生语言万能观。如莫斯发现,在巫术活动中,“没有语言的仪式并不存在,外表的沉默并不等于巫师没有在念表达其意志的无声的咒语”。“形体仪式只不过是不发声的咒语的一种转译: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语言”。即使巫师“不做任何一个正规的身体动作,巫师也可以在他的声音或呼吸的帮助下,或者仅仅是依靠他的意志去创造、毁灭、指引、搜寻,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③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第71页。英国马凌诺斯基的田野调查亦可证巫术语言之强大功能: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巫术的诸要素中,唯有咒语是不可或缺者。 “咒语是巫术中最隐秘”和复杂的部分,“巫术的主要法力来源是咒语”,即“巫术的价值、力量和灵验在于它们的咒语中”。仪式则无秘密性且简单,仅“是把咒语传递到或转移到目的物上”。而“念咒者的声音是传达法力的媒介”,法力是通过不断的声音“重复来糅入对象物里的”。岛民对声音的重视和强调,甚至影响其“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使其用咽喉指称头脑、智力,将哑巴“等同于智力残障”者。④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48-352页。美国伊利亚德亦说,盖于旧石器时代,“语言被赋予了巫术—宗教的价值”,“语音的发明则肯定更是一个巫术—宗教力量的无穷源泉。甚至在清晰的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声音就不仅能传达信息、命令或意愿,而且也已能通过高音和声音的变化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语言越是完善,它所具有的巫术—宗教的能力也就越强大”,“语言能够达到几乎与仪式行为同样的效果”。如古埃及“在第一王朝法老们的都城孟斐斯,围绕着卜塔神构造了一个最系统的神学”;“卜塔是以其思想 (他的‘心’)和语言 (他的‘舌’)来创造世界的”,“众神的起源以及宇宙的创造都是一个神的思想和语言创造的结果”。①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28、78-79页。按,卜塔是古埃及的太阳神名之一。卜塔的创世方式类似《圣经》所载,在《旧约》中上帝亦以言说的方式创造万物;《新约》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②《圣经·旧约·创世纪》1:1-31。《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1-3。此“道”与其通常所见的英译Word,均是“兼‘理’ (ratio)与‘言’ (oratio)两义”③钱钟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册,第408页。的古希腊文logos之意译;其汉语音译多作“逻各斯”。伊利亚德引威尔逊所说“在埃及历史的开端,我们发现了一条类似于基督教神学中逻各斯的教义”,④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79页。殆就上引《圣经》所载而言。最高神之以思想语言创世,应是人类从巫术进入宗教的时代后,将己之思想语言全能观推论为最高神的神性所致。灵验奇迹的超自然观念里亦有与原始人的思想语言全能观近似者。如佛教中习见的六神通说与神通灵验奇迹等,⑤《长阿含经》卷十《增一经》曰“云何六证法?谓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证,二者天耳通证,三者知他心通证,四者宿命通证,五者天眼通证,六者漏尽通证”(《大正藏》,第1册,第58页上)。颇近乎全知全能的观念。又,佛经的陀罗尼咒语亦或与语音的巫术力量有关。陀罗尼咒语在六朝即多不意译之,⑥如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对《长阿含经》卷一二《大会经》集中出现的诸种咒语,即唯音译之(《大正藏》,第1册,第80-81页)。唐玄奘对不意译它的解释是因其“祕密”之故。⑦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一,《大正藏》,第54册,第1057页下。所谓“祕密”或出于两种可能,一是虽知其义而不译之,二是其中有昧其义而不能译者。前者显然与上述语音本身之巫术力量有关。后者则与法国斯特劳斯所揭示者相关。斯特劳斯说,在有的原始民族中,因畏惧鬼魂而被讳的死者之名及其同音嫌名所“污染”的普通词汇,会被排除于日常用语的词汇系统之外,而进入巫术仪式的专有圣语系统。此类普通词汇因有新造词汇替换之,故其词义日久失落而为后人所昧。⑧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0、239-240页。按,为使行文简洁,正文以“嫌名”替换李先生所译“与这些名字相似的语音”、“在发音上是类似的”词等意的表达法。“嫌名”语出《礼记·曲礼上》“礼,不讳嫌名”,汉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上册,第114页)。讳名甚至讳嫌名,是因灵魂系于名字,名字系于语音,故发其音则无异于招鬼来害己。在此俗中,语音显然亦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咒语特点和我国黎族的讳名风俗,亦有近似于斯特劳斯所说者。⑨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言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咒语中,有很多词不属于日常用语,都是些古字、神话名称或根据少见的语言规则组合的生僻词”。“有些愚钝的老人虽然可以熟练地背出一段咒语,但却从不关心或遗忘了它的意义”(第376页)。其咒语特点与斯特劳斯所言近似。另外,在我国海南保亭县黎族聚居的毛道乡,“人死了就禁止再说他的名字”,对祖先“只笼统说祖先鬼,但不说祖先鬼的具体名字”,“说祖先的鬼名是最大的禁忌”。祖先鬼名只由主持祖先祭祀的鬼公“牢记着,以便代代相传”。“鬼公是以血缘近亲相传授”,只“在自己血缘集团范围内主持做鬼仪式”;“祖先鬼为他的主要献祭对象”,“念鬼名为其仪式的主要内容”。在乐东县黎族聚居的番阳乡,若有说他人祖先鬼名者,将被罚;为婴幼孩取名亦询老者,以避与祖先鬼重名 (孔季丰、潘雄整理:《毛道乡调查》,易谋远整理:《番阳乡调查》,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62-65、154、160页)。黎族死者名被永远避讳,只由世袭鬼公牢记而唯用于祭仪语言系统中,此与斯特劳斯所言亦近似。而在某些兼音义二译的陀罗尼咒语中,其归命者除有佛法僧外,亦有其他神灵等对象,[10]刘宋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祕要法》卷下云“世尊而说咒曰: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摩诃梨师毘阇罗阇……”(《大正藏》,第15册,第340页中)。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言为召请大吉祥天女,“即说咒曰:南谟室唎莫诃天女……”(《大正藏》,第16册,第439页下)。其中或有死而升格为神者之名。而且印度阿萨姆邦的库基人、泽米人、卡查那加人,南部的托达人等,在近代犹有讳名之礼,[11]詹·乔·弗雷泽:《金枝》,第370、375页。按,阿萨姆邦诸族群虽为讳生者之名,然实与托达人讳死者之名出于相同观念,即灵魂系于名字,生者隐匿己名是为免鬼魂循名害己,讳死者名则是惧称其名而招其魂来害己。显为古俗所遗。是见陀罗尼咒语所以“祕密”,盖与古印度讳名礼俗有关。陀罗尼咒语之不义译,无论出于上述的何种可能性,均是语音全能观在两方面之体现。至于民间巫术与道经中的咒诀以及儒经、子书等所载祝辞,殆与原始人在巫术时代的思想语言全能观亦不无关系,或为原始信仰之遗存。①《礼记·郊特牲》载蜡祭之祝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正义》,中册,第1073页)。《吕氏春秋·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王利器: 《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034页。按,王利器引蒋维乔曰“离、罹古通”。)儒经、子书之此二辞皆属咒语性质。至于民间巫术与道经中的咒诀则其例极多,恕不举之。据上所述,可见超自然性的第3要素即神灵意志的自由,与前述思想语言全能观极近似,而前者显然是产生于原始人由己及神的推论。超自然性的第4要素即神造万物观,亦不例外。法国孔德说,人类的所有思辨都先后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之三阶段。“一切思辨的第一次飞跃必然是神学性的”,在神学阶段,人类拿“自己所制造的现象与所有任何现象比拟,从而将人类的模式到处移置。这样一来”,人类“凭借着对各种现象的即时直觉,便开始以为对这些现象有了相当的认识”。②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是则神造万物的观念,即是原始人在思索万物的本源、诸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方式时,将自己制造物品等的现象和模式,比拟、移置亦即推论于神身者。
以上所述表明,超自然观念的四个基本要素在原始宗教阶段已主要由间接推理而全部具备。而人类理性之需要,则是此阶段的超自然观念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如孔德所说,在神学阶段,人类“全部思辨都本能地对那些最不可解决的问题,对那些最无法进行任何根本性探索的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偏爱。由于反差作用,人类智慧就在那连最简单的科学问题尚未能解决的时代,便贪婪地、近乎偏执地去探求万物的本源,探索引起其注意的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 (始因与终因)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一句话,就是探求绝对的知识”。“这种原始需要,就其可能得到满足的范围内,自然得到了满足”。③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第2页。而前文所述者则正是原始人满足其理性需要的方式与过程。
上文曾说灵验宣传的对象主要分三类:(1)同教之同宗与异宗者、(2)异教者、(3)无神论者。在已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前二类对象中,就其所信超自然性要素而言,应有部分要素得自近同于原始宗教阶段的推理方式,亦有部分要素得自于人为宗教阶段的其他推理方式。就灵验宣传对象而言,前二类中的不同对象对两个宗教阶段之推理方式或各有去取;或某一对象在其理性发展之人生的不同时期,对二阶段的推理方式亦有所去取。至于其去取的原因,当与二阶段的推理结论之可靠性与必然性的程度及有无相关。而此可靠性与必然性的情况,又由二阶段的推理的特点所致。
三、原始宗教阶段的关于超自然观念的推理之特点
原始宗教阶段对超自然性要素的推理过程或曰逻辑结构,从前述西方学者据田野调查而述的实有者与推测者,加上我们揆度其可能有者来看,约有11个 (在下文中依其出现次序,分别标以 (1)、(2)……等)。古典的普通逻辑学之推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演绎、归纳、类比。原始宗教阶段的推论对此三种方式皆有采用,然其推理形式有效而且推理正确者,唯见于一个环节。它蕴涵于超自然性的第1要素 (灵魂不灭)的推理中,即人皆有灵魂存在的环节。在最初,此环节只可能采用类比的推理方式,据前述泰勒所言原始人的推己及人之说,可补其推理过程为 (1):“我有做梦现象,此现象说明我有灵魂之存在;他人说他们也做梦,则其梦说明他们亦有其灵魂。”从逻辑学和今天的科学常识去看,此类比不仅推理形式有效,而且推理正确,④类比推理的特点之一是其格式有四词项,而不同于只能有三词项的演绎推理中的三段论之格式。类比的四项即其内涵表述中的“若A、C皆有中项B,则A有D,C亦有D”之四字母。由于D在客观上是否处于中项B之内,是未知而待定的,则D是否在C之内,并不确定,故其结论亦不确定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373-376页)。在正文所言推理中,“我”是A,“做梦”是中项B,“他人”是C,“灵魂”是D,其词项符合类比的格式;且其推理过程亦符合类比的内涵表述中之过程,故其推理形式是有效的。又,在此推理环节中,“灵魂”D尚只单指非意志所控制之梦中意识,并不涉及它是否可与肉体分离而于人死后犹不灭的问题,而从人为宗教阶段的常识去看,“灵魂”D确定地是在“做梦”的中项B之内,故其推理是正确的。故其结论不仅可靠度高,甚至已具必然性。原始宗教阶段的其他推理则皆不然,如同样以类比推理言之,在超自然性的第2要素 (神灵存在)中的至上神观念上,泰勒所言的原始人之类比,亦被古希腊之先民采用,亚里士多德说:“古先的人既一般地受治于君王而且现在有些民族仍是这样,有些人就推想群神也得由一个君王 (大神)来管理。人们原来用人的模样塑造着神的形象,那么凭人类生活来设想群神的社会组织也就极为自然了。”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据此可知其逻辑结构为 (2):“人类有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中有至上者;群神也有社会结构,群神亦即有至上者。”其推理形式虽然有效,然在其四词项即A“人类”、B“社会结构”、C“群神”、D“至上者”之中,由于词项C“群神”的存在问题即使仅在逻辑上亦不具有必然性,故其结论是不确定的。词项C“群神”之所以不具逻辑必然性,又是因产生此观念的推论环节之推理问题所致。据前述泰勒、布留尔说,原始人相信梦中表象是客观实在的,可见词项C“群神”当是以之为大前提的二个演绎推理环节的结论。在基于前述类比推理所推出的人皆有灵魂存在的观念基础上,其第一个演绎推理环节为 (3):“凡梦中出现的灵魂皆是客观实在的,死者的灵魂出现于我梦中,故死者的灵魂是客观实在的。”即灵魂是不灭的。其第二个演绎推理环节为 (4):“凡梦中出现者皆是其客观实在的不灭之灵魂,万物出现于我梦中,故万物有其客观实在的不灭之灵魂。”此有灵之万物亦即群神。此二演绎的推理形式虽皆有效,然据人为宗教阶段的常识和理性,其大前提皆是虚假判断或真实性待定的判断,故其结论并不具备演绎本应有的必然性。在至上神存在的类比中,词项C“群神”的存在既然是其前推理环节的非必然性的结论,故此类比虽推理形式有效,然其结论是不可靠的。在原始宗教阶段对超自然性第3要素 (神灵意志自由)的推论中,亦存在类似问题。如在人的思想语言全能之环节,其逻辑结构可能为 (5):“他人和动物是有灵魂者,有灵魂者对我的思想语言有反应;他人和动物以外的万物皆是有灵魂者,故万物对我的思想语言皆有反应。”此类比的词项B“灵魂”,据人为宗教阶段的常识和理性,是否是A“他人和动物”与C“他人和动物以外的万物”相交叉的中项,亦是不确定的,故其推理形式无效,结论不可靠。此环节的另一可能的逻辑结构为(6):“他人对我的思想语言有反应,动物对我的思想语言有反应;他人和动物都是万物的诸部分,故万物对我的思想语言有反应。”此属不完全归纳中的全称归纳,其推理显然犯“以偏概全”之错。在人本不死的环节,其推理过程可能为 (7):“我欲且能杀毁者会死灭,我自己不是我所欲杀毁者,我自己不会死灭。”在此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中,其大项“死灭”作为肯定判断的大前提中之谓项,是不周延的,然其作为否定判断的结论中之谓项,却是周延的。据三段论的“在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不得周延”之规则,故此推理犯“大项不当周延”之错。②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5-156页。在神灵意志自由的环节,基于其前的推理的结论,其可能的推理过程为 (8):“思想语言的全能是人性或是神性,此全能既然非人性,故此全能是神性。”在此演绎的相容选言推理中,推理形式虽符合其否定肯定式而有效,然如前所述,“神”之存在是不具必然性的结论,故其词项“神性”的真假待定,因而此选言推理的结论亦不可靠。在超自然性的第4要素 (神造万物)的推论中,据孔德所述,其逻辑结构为 (9):“我有造物之思与模式,由此思与模式产生我造之物;神亦有造物之思与模式,由神的造物之思与模式产生万物。”此类比的问题同于前所分析的推理 (2)的问题。对第4要素的推理,原始人亦可能会采用另一推理方式,其过程含二连续的环节。前一环节是 (10):“此物被我造,彼物被我造;此物、彼物等皆是万物,故万物皆被造。”此归纳的性质与问题同于前所分析的推理 (6)的问题。后一环节是(11):“万物是被我造或是被神造,非我所造之万物不是被我造,故非我所造之万物是被神造。”此环节的问题同于前所分析的推理 (8)的问题。
在以上实际有与可能有的11个推理中,演绎有5个,类比有4个,不完全归纳的全称归纳有2个;有效式有7个,非有效式有4个;前提判断或前提词项虚假或真假不确定者,有10个,真实者有1个。从中可见四点:第一,从推理的性质去看,演绎是必然性推理,不完全归纳和类比为或然性推理,故原始宗教阶段对超自然性要素的推理中,或然性推理超过必然性推理。第二,推理形式的非有效式较多,超过总数的1/3。第三,前提判断或前提词项虚假或真假不确定者,分布于推理 (1)之外的所有推理。第四,推理结论在逻辑上的可靠性程度低,或无逻辑上的必然性。当然,在原始宗教阶段,亦可能还有前述11个之外的其他推理,然其对我们关于此阶段推理之可靠性与必然性的四点总体判断,当不会有大的影响。而此四特点,是与原始人的理性发展程度相应的。正如孔德所说,神学阶段的人类满足其理性需要的方式,“其实是与当时我们智力的最初的真实状况完全相符的”。①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第2页。布留尔亦说,原始人所采用的推理方式,虽只“是朴素的逻辑运算,但它是不随意的,是‘原始’人的智慧所难于避免的。正如那个在这种运算之先并作为它的基础的心理幻觉一样是必不可免的”。②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1页。总之,超自然观念是原始人的理性之需要以及与其理性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理方式之产物。
四、余 论
从上节对原始宗教阶段相关推理的特点之分析与归纳中,可知造成此阶段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低和不具必然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前提判断或前提词项虚假或真假之不确定。而其虚假或不确定者主要有三:(A)梦中表象的客观实在性,(B)万物有灵,(C)神与神性。此三者具有递为因果的关系,可见前提的虚假或不确定的根源性始因在于 (A)。而在人为宗教阶段,与原始人“把梦看成是”“与清醒时的知觉一样”“确实可靠”的“一种实在的知觉”之观念相异,人们认为“被感知的现象或存在物在同样的条件下被一切人同样的感知着”,“是了解知觉客观有效性的基本标志”;“感知着的主体之间的一致”,是区分判断“实在的现象与想象的现象”的前提条件。因此对梦中表象,“作梦的人在醒来以后,由于缺乏为证实它们的客观实在性所必须的条件,是不会有丝毫相信的”。③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48、53页。按,《庄子·齐物论》有梦觉不分的长梧子的吊诡之言、庄周梦蝶的物化之论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册,第104-105、112页),虽似以梦为真,然其实皆是为倡齐生死之旨,所取人生如梦之譬而已。在人为宗教阶段,人们虽仍以梦为“神来往”以“预见过失”、“吉凶”的神秘现象,④《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梦书》,第2册,第1835页上。又参亚里士多德《自然诸短篇:梦占》所言世人对梦由神启的信念(《灵魂论及其他》,第288页)。然要求“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之事,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1卷,第315页注①。当不至于或极少发生,而多已从真幻不分,进步到从梦前觉醒时的现实与生理因素出发,去思考做梦的原因、本质等。⑥《周礼·春官·占梦》有六梦之说:“一曰正梦 (郑玄注“无所感动,平安自梦”),二曰噩梦 (郑注引杜子春云“谓惊愕而梦”),三曰思梦 (郑注“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四曰寤梦 (郑注“觉时道之而梦”。清孙诒让注云寤梦“盖觉时有所见而道其事”所致梦,与“思梦为无所见而冯虚想象之梦异”),五曰喜梦 (郑注“喜说而梦”),六曰惧梦 (郑注“恐惧而梦”)。”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册,第1972-1974页)惧梦与噩梦之别,盖在惧梦为梦见觉时所畏惧者;噩梦谓梦见觉时未想及而无所谓惧与否之事物,然梦中见之而生怖畏。六梦之说多以觉时的现实因素以分。汉王符《潜夫论·梦列》有十梦之说:“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5页)其精、想、感、时、病五梦,皆被认为以觉时之现实与生理状况等而致梦。又,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 “卫玠……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 (徐震堮: 《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9-110页)晋乐广所言“因”当指觉醒时的感觉印象,盖相当于《周礼》噩、寤、喜、惧之四梦。凡此皆以梦中表象为觉时之现实与生理状况所致心理现象,均非真实。亚里士多德《自然诸短篇:说梦》则将思想所致幻觉排除于梦之外,而异于中国古说。亚氏认为灵魂有司思想和感觉的二部分。虽然“一个梦境未必全是睡眠中所显示的心理现象 (幻觉),却也凑合着我们思念所及”,然而“如果其人自知其正在睡眠,自知其所见的现象出于寐中的感觉,于是在他的内中”“常有灵魂的某个部分,向他报说,他所见闻的色声,只是梦境中的如影如响”。故“那些于睡时出现的相关于心理印象而实际上是属于思想 (心识)的情事,也不得[称之为梦]。只有人在睡眠中,在绝未脱出睡眠的境界以内,从他的感觉机能的活动 (运动)之中,兴起的心理印象 (幻觉)这才是‘一个梦’”。做梦属于灵魂中的“感觉机能的活动”,梦中所见是觉醒时“引发印象 (视象)的外来客体,业已离脱于感官之后,其印象……遗留于感官之内”的幻觉。在生理上,做梦是睡时“由于热量倒流,由外表而内注,渐以上升及于诸感觉作始的位置”等因素所致(《灵魂论及其他》,第274-287页)。梦境的客观实在性,作为原始宗教阶段的超自然性四要素推论之逻辑起点,虽在人为宗教阶段被否定;自此起点开始的推演之结论,虽亦因其可靠性程度低或不具必然性,而未必为人所尽信;然超自然观念作为前一阶段所留的精神遗产,却未被后一阶段的人放弃对它的继承。不过,后一阶段的人类理性不再止步于或然性、非确定性,而超自然观念在人类向理性之本性所要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①莱布尼兹:《单子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88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623页。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3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上卷,第155、157页。的进发中,亦将既是以超自然观念自身为目的之理性活动的对象,又是为其他目的而进行的理性活动之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