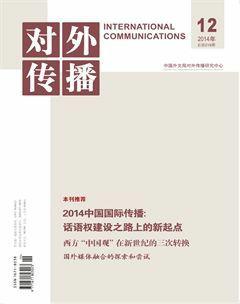国宴外交:元首外交的重要维度
钟新+陆佳怡
2014年3月22日至4月1日,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彭丽媛访问欧洲四国并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在此期间,荷兰国王和王后3月23日招待习近平夫妇的王宫国宴受到参加国宴的荷兰各界人士、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笔者就公共外交、元首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问题,通过电子邮件专访了亲临王宫国宴的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高级研究员、安特卫普大学扬·梅理森(Jan Melissen)教授。梅理森教授致力于公共外交研究多年,其2005年出版的《新公共外交:国际关系领域的软实力》(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较早地对“新公共外交”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梅理森教授在5月21日回复的邮件中,生动地再现了亲历王宫国宴的情景以及体验观察,并深入点评了习近平夫妇欧洲四国行的公共外交意义。
一、近距离接触效应:亲历王宫国宴的体验与观察
问:请与我们分享王宫国宴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梅理森: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时刻。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习主席夫妇与所有嘉宾一一握手,这令所有嘉宾都深感荣幸,印象格外深刻。这个意义不仅仅在于亲自握手,不仅仅在于与中国最高政治领袖和他的配偶近距离接触,而是意识到中国元首不远万里来到欧洲,在他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四国短暂访问期间与几千人握手。第二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国宴进行中,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或手机拍照,完全不顾不可拍照的外交规定。现场工作人员也没有制止这些热情的摄影者。在移动媒体技术和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与国家元首见面、共享国宴无疑是一个值得分享的时刻,这一时刻在与地处阿姆斯特丹王宫之外的人们分享过程中获得成倍放大效应。这个自发的拍照环节意味着开放和分享人生经历,是难以被规则约束的。有趣的是,中国与荷兰政府在此之前已经决定强化“开放与务实”的双边关系。
问:您用什么词汇来描述亲眼见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感觉呢?
梅理森:亲眼见到习主席夫妇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你眼前的是真实的人。这两个人带着使命,履行职责,他们与公众见面博得尊敬,但某种程度也证明了,高高在上权威感的动态性和在最高权力机关工作的临时性,使习近平更具有对普通人的亲和力。
问:国宴嘉宾的构成体现了组织方希望沟通和影响的范围。那么,什么人被邀请参加王宫国宴呢?
梅理森:大约200人参加了这次国宴,分别大致有80个中国嘉宾和120个荷兰嘉宾。
这个群体来源广泛,充分地代表了不同领域,真的令人鼓舞。嘉宾们尽管来自荷兰不同的领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各自领域与中国深度互动,这些领域包括文化、教育、政府、政治、商业、体育、外交关系、媒体等。各行业都有代表。有些嘉宾是全国性知名人士,另一些人则默默地促进荷中合作,或者刻意避开聚光灯。一些嘉宾与政府联系密切,其他人则代表社会各种自治主体的真正声音,或者促成荷中合作的一些普通人。把这个多样性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因素是他们共同致力于最广泛的“双边关系”。这个群体的构成表明,中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与经济关系。参与代表的广泛性体现荷中关系的务实性、真实性并且令人振奋。王宫国宴证明,峰会不仅仅只有讲话人的“大特写”。实际上,高层会议创造了最大范围沟通的机会,为荷兰嘉宾与中国嘉宾提供了见面机会,也为未曾谋面但有很多可分享经验的荷兰嘉宾创造了见面机会。参加国宴的每一位嘉宾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简言之,国宴情形充分证明,把如此丰富多样的中荷关系仅仅定位为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是不准确的。中国与荷兰远不止互动的经济体,荷兰人与中国人也不只是“经济动物”。
问:习主席和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的国宴演讲传递出什么讯息?
梅理森:荷兰是习主席欧洲四国行的第一站,而王宫国宴为习整个欧洲之旅奠定温暖基调。这显然是华丽的第一乐章,正如最后一站东道国德国认为他们上演的是华丽终曲。在这气氛和谐的隆重国事活动上的演讲当然令双方都“感觉良好”。很多来参加核安全峰会的国家元首也像习主席一样是第一次访问荷兰,但只有中国元首得到国事访问的礼遇。
问:您如何评价这次王宫国宴和峰会的公共外交功能?
梅理森:荷兰媒体以极大兴趣详细报道了国宴,对人物、礼仪的关注度超过对政策、外交的关注度。活动的人情味属性增强了公共外交效果,而图片、影像、面对面接触等非语言传播在欧洲峰会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因为受众更容易接收到眼见的信息而更难集中注意力倾听讲话内容或者报道文字。社交媒体对增强公共外交效应也起了很大作用。很多荷兰人通过社交媒体私下谈论国宴和习主席的其他活动。国家元首与外国公众直接接触,以个人的超凡魅力与公众建立真实的联系。个人形象对捉摸不定的政治现实有很大帮助。例如,很多人对奥巴马个人魅力的关注度超过对他对欧洲强硬语言的关注度。当奥巴马到达海牙参加核安全峰会时,这位美国总统立即成为欧洲社交媒体上的主要明星。
习主席此行的公共外交效应还体现在,荷兰公众赞赏习主席对加强与荷兰的良好关系做出的个人贡献。国家元首出访他国时与当地人的近距离接触和发表精彩演讲都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外国公众意见往往难以预测,并且不总是友善,但也可以是宽容的。近来,欧洲媒体报道了中国的污染、食品安全、政府管理模式等问题,但是,习主席此行所产生的公共外交效应有效抵消了这些报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荷兰的最佳中国时间。
二、传递对话意愿:习主席欧洲四国行印象与观察
问:习主席访欧期间,以不同形式发表了演讲或观点。您认为这些讲话或观点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对于欧洲公众来讲,是否具有感染力?
梅理森:尽管国家元首通常少有发表观点性文章,但是,习主席发表在欧洲媒体上的文章仍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的演讲都根据演讲场合和听众构成进行了精心设计,其中一些演讲还设置了问答环节,让在场听众感受到习主席希望对话的良好意愿。总体而言,习主席访欧期间发表的报刊文章和演讲可被视为中国魅力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十分有效。习主席欧洲行程中,艰难的贸易谈判是硬币的一面,而习主席与欧洲各种形式的对话是硬币的另一面。endprint
习主席此次在欧洲学院的演讲传递出了主要内容。他希望欧洲尊重在历史、文化、政治方面与欧洲不同的中国。他提到,中国和欧洲有责任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并且祝贺两大古老文明之间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关系。很多欧洲学者对习主席强调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表示赞赏,因为中欧之间在多样性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评论员也注意到了习主席重申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据此拒绝谴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欧洲媒体引述了习主席的演讲内容。
习主席的汉语演讲通过同声传译与现场的欧洲听众建立实时的直接联系,但有时候缺少这种联系。例如,在海牙的国宴上,组织方向嘉宾们提供了演讲翻译稿,没有同声传译,这样,不懂汉语的嘉宾们很难专注听演讲,一些人凝视远处,还有些人在研究皇家菜谱上的阿根廷牛排。
尽管尖锐的新闻评论依然存在,但总的来看,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比以前减弱了很多。从这个角度看,习主席这次展开的元首外交是非常有效的。
问:会见或演讲场所的选择如何为系列峰会增色?
梅理森:尽管有时候由于外交礼仪的限制,可供选择的空间有限,但是,活动场所在外交中和公共外交中都很重要。例如,习主席在布鲁日的演讲场所就很有效,体现了更开阔的图景,而不仅仅是对政治关系的评价。在荷兰,美国总统选择在位于首都的国家博物馆里著名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世界名画《守夜》(Night Watch) 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令人印象深刻。
问:您认为,此次习主席欧洲之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加深对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了解?
梅理森:欧洲向来对中国存有很大的兴趣,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关于中国的报道都不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习主席此次访问带来的积极成果是展现了公共外交的潜力,证明同一现实(reality)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版本,公开对话有利于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而双方实质性合作与交换则更有意义。但是,人们不能过高评价一次访问的价值。公共外交不是应急措施。正如早期修建寺庙或教堂一样,改善关系和提高声誉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工程。我希望欧洲公众听到了习主席呼吁欧洲人民不要轻易下判断、对中国持更开放态度的声音。
三、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创新变革:建言中国公共外交
问:关于进一步做好面向欧洲的元首外交,您有何建议?
梅理森:中国对欧洲的公共外交具有很大潜力,因为双方存在很多接触点。其中,一个重要接触点就是元首外交。关系需要培育和延续,并且需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因此,要提升元首外交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可以再次甚至多次到访欧洲,例如与普京更经常见面交流。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可以更加放松一些,在希望欧洲更了解自己的同时,努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体现“中国想要更了解欧洲”。
国家元首国事访问的内容当以“最大化传播时刻”(moments of maximum communication)为目标进行策划设计,最充分地利用这样的独特机会,并以此为杠杆撬动整个中欧关系。峰会本身终归不是目标,而是推动更大、更广、更重要的进程。
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第一夫人外交”?
梅理森:第一夫人在场会使公众眼里的元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更加人性化,更加平易近人,而不仅仅是政治领袖。第一夫人外交可以弱化一些社会问题的政治性。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访欧前接待了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及其母亲和女儿一行。在她访问荷兰期间,她为谐音“国泰”(Cathy)的郁金香施洗礼。这些都展示了第一夫人外交的柔性一面。正如其他公共外交形式一样,第一夫人外交还需“边做边学”,在将来会有更大的空间。彭丽媛曾经是职业歌唱家,非常习惯走在聚光灯下,这为她创造了很大优势。
问:中国在设计高层公共外交方面是否比以前更富技巧性、更专业?
梅理森:相较以前,中国的确更富技巧和专业性。但是,中国对欧洲的公共外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致力于提升软实力方面,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投入的公共资源都多。在显然必要的巨大投入之下,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的确有所改观。中国公共外交可以更充分利用社会本身作为公共外交资源。例如,在借助数字媒体影响欧洲年轻一代方面,中国公共外交官还少有涉足。
问:您最后想对中国公共外交说什么?
梅理森: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客观、公正、冷静地评价他们与欧洲公众接触中的成功与失败之处,那就意味着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即有效沟通。公共外交不是新瓶装老酒并希望老酒能变成新酒。公共外交应该是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以新公共外交适应今天的环境。
(本成果受到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1JJD8600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