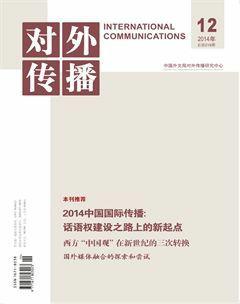浅说孔子学院的现在与未来
安然
任何一个个体、群体乃至国家,当它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时,它一定会考虑自身对周边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层面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对于一个群体和国家,这种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影响自然而然就反映在它与周边的交流,它的语言文化习俗被周边认识接受并采纳。比如19世纪的英国,曾有过日不落的辉煌;20世纪的美国,绝对的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是英语盛行并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通用语。向往并追随西方文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奋斗目标。自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以来,世界格局及其发展的态势显示,西方化或美国化只是全球化表现形式的一种,本土化并要求区域独立的思潮和现象已越来越彰显并被认同。中国,一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贫穷大国,在21世纪崛起了。崛起的中国,在其经济迅速发展、体量不断增大的情形下,也自然而然想到了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去影响这个世界。于是借鉴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的想法很简单,做法也基本上是在模仿和追随,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按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将孔子学院总部冠以政府行政级别,强调政府的掌控和关注,且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理论上来讲,孔子学院的发展应该不会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指责和质疑。
海外学者关注孔子学院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一方面,孔子学院迅速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400多所孔子学院相继诞生;而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始终在遭到质疑和指责。犹如孔子学院总部在《孔子学院10年发展回顾》中提到的,“从国际上看,有的国家和民众对我汉语国际推广存有戒心、疑虑和偏见,对孔子学院警惕防范”。搜索EBSCO数据库(截止到2014年4月),得到与海外孔子学院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献25篇,内容涉及孔子学院与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与软实力、孔子学院与学术自由、孔子学院建立的区位因素、孔子学院与经济贸易关系等。海外学者最早研究孔子学院的文章发表于2006年①,后续的许多研究关注孔子学院对西方学术自由可能造成的影响。美国马里兰大学派克分校的彼特·施密特(Peter Schmidt)提到,政府在合作大学邀请涉及台湾敏感问题的演讲嘉宾一事中对其施加压力②。而这些看法多缘于孔子学院拨款来自汉办的缘故,因而西方学者认为,孔子学院在资金和管理上都受制于中国政府。刚刚发生的芝加哥大学停办孔子学院事件,也认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其学术性与政治性模糊不清,汉语教材、教师也是由孔子学院统一挑选和“控制”,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师招聘上也存在歧视等。事实上,2010年就发生过芝加哥大学签名信事件③。
在西方的理念中,“政府是必要的恶”。由此出发,孔子学院也受到了牵连,同时,这些结论也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痕迹。海外学者有关孔子学院影响力的研究多集中于意识形态层面,认为孔子学院不仅仅是推广汉语的语言机构,其背后可能还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中国外交的“野心”,甚至认为孔子学院通过课堂搜集华裔信息等④。以西方意识形态来看待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研究中主观加入“政治隐喻”,较少客观、系统关注孔子学院本身,“研究”的含金量会大大降低。
当然,对孔子学院的理解并非一边倒,伊丽莎白·雷登(Elizabeth Redden)认为,美国国内的资金捐赠能让美国大学走向一流,孔子学院的捐赠也不例外⑤。此外,澳大利亚佛林德斯大学的杰弗里·吉尔在《亚洲社会科学》撰文指出,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树立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帕拉代斯(James F. Paradise)则在《中国与国家间关系和谐:孔子学院在北京提升软实力过程中的作用》(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孔子学院的建立作为一种软实力“很是时候”⑦。而且,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福尔克·哈蒂格(Falk Hartig)认为,孔子学院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一道,能够平衡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⑧。
数据显示,海外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孔子学院对其所在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上,而对孔子学院自身情况缺乏考察。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于2014年第6期刊登了孔子学院总部特稿和一系列“孔子学院与公共外交”专题文章。孔子学院总部的特稿提到,要“进一步创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渠道途径,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个提法是很到位的,但要做到需要几代人的尝试和努力。
问题与出路
孔子学院“走出去”这一举措意味着,一大批中国人(作为中方院长的中国管理者、大量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要走向跨文化沟通与交流平台;中国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要走向跨文化教育与教学平台;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要走向跨文化认知和理解平台。这一切,中国都准备好了吗?答案并非全部肯定。
被派往孔子学院人员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使他们的奉献精神因人而异。中国式教育方式和教材的本土化问题是孔子学院教学的瓶颈。而中华文化的内涵能否在这些派出者身上展示,通过他们的举手投足、言行举止来反映,让交流者和学生们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来学习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对中方派出人员的又一挑战。
中方人员的准备不充分,外方的戒备和质疑,一些媒体对个案的渲染和炒作,不免让一些本来就对自己国家、自身文化不自信的人担忧起来,“孔子学院出问题了?”,“孔子学院办不下去了?”等等。孔子学院的一些传闻也让国内一些网友认为孔子学院项目浪费纳税人的钱、不如用来发展国内教育等,这些评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孔子学院缺乏对内传播,没有让国内民众对设立孔子学院的目的和意义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endprint
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有助于大众客观看待孔子学院及其发展,也有助于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1.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孔子学院的发展
跨文化交流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双方觉得有益有利就开展合作,双方觉得暂时有困难、有差异就停止合作,这都很正常,无须大惊小怪。孔子学院遍布全世界,一定有非常成功的典范,也一定有不成功的案例。落户的国家不同,接纳的程度各异。在布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四百多所孔子学院这个大舞台上,希望所有事情所有的孔子学院都一帆风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不是真正的跨文化交流使者的想法和心态,而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学停办孔子学院,就产生恐慌,从而不敢再往前走。我们要以正常的、平和的心态看待“成”与“不成”。现在不合作不代表将来不合作,同样,现在的热闹不意味将来不出现冷清的局面。另外,孔子学院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体现民间性和交流性,没有必要将政府官方外交的基准应用到孔子学院的发展上来。
2.以跨文化冲突来促使孔子学院的反思与调整
作为一个在这么短时间内走向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其跨文化前进之艰难是国人无法想象的,那么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冲突在所难免。“跨文化冲突”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将事态直线向负面转化乃至失败,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博弈的零点使双方重新协商调整到一个新的平衡。没有冲突不成其为交流与碰撞。如何应对冲突和有效的冲突管理,是孔子学院时刻应该意识到并有能力处理的。以芝加哥大学停办孔子学院事件来看,或许能促使孔子学院总部反思并调整下一步的运作部署和策略。过分渲染官方色彩、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特色运作模式或许在西方会遇到阻碍,多一点民间的、少一点官方的、淡化意识形态的、不参与具体事务管理的模式或许值得借鉴,只要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间传播与交流,其运作、管理、合作等的方式方法应不受局限。在对方喜欢并接受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前提下,多元的世界可以有多元运作和管理的方式和方法。
3.以多元文化的认知和融通作为孔子学院的努力方向
孔子学院是一个新生事物,它需要一批有热情、敢尝试的人们去认识体悟其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去探索孔子学院在异国特定环境下的发展模式并能把握其发展方向。这种开拓并需要耕耘的工作,没有一种探索精神支撑是不行的。而这种精神支柱不仅仅建立在单向奉献的基础上。王晓朝在《西方经典翻译与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文中提到,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传教士与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儒生们,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理解非常透彻,“两种不同的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理解。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⑨。这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自己的认知空间,在自己认知拓展的同时,也丰富了整个社会知识,给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若能在发展和丰富自身及人类认知能力的精神支撑下融通两种文化,其办学模式的动力和发展前景将不可估量。那样他们会更加关注如何充实自身的文化内涵,使孔子学院回归文化本位。
另外,语言只是载体,是一种形式和表象,它背后的文化因素影响着孔子学院中外双重管理而导致的冲突思维模式。从入乡随俗到全球视野的升华,中方对所在国文化教育模式不应该仅仅是接受,而是要能揉合融通,使之成为孔子学院独特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绝不是全盘西化就可得来的,也不是仅靠懂某种语言就能解决的。孔子学院应该通过学习探索发展出一套融合的、优于单向教育模式的发展模式。这需要孔子学院总部更多地从宏观来把握世界范围的几百所孔子学院,并在具体事务上放权,多元的、多层级的、包容的、协商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崇。有时,必要的妥协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策略和对策,是对多元文化中的不同认知的理解和包容的体现。如果让孔子学院真正成为各大学的一部分,按照各大学的章程来管理发展,以各自特色来彰显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的百花齐放,多元文化理念才能在各孔子学院得到真正体现,而孔子学院或许也能更加被认同。
跨文化/跨教育的融通能力决定了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融通能力是建立在多元文化认知之上又超越认知、驾驭认知、游走于两者之间并能整合的一种能力。如果孔子学院的发展能够挖掘自身文化中可以走向国际的优势,同时也能驾驭文化间的互动特点,在当今多元文化此消彼长的浪潮中,就可以推波助澜,将本土文化推向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状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达到庄子所描述的状态“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到那时,质疑声自然就不复存在,对孔子学院的偏见也会消失,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地位完全确立。
总之,孔子学院携自身的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相交集,二者关系犹如中国太极理念的阴阳互补共生,相辅相成。它需要人们去思考并开拓一个让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华裔传播学者陈国明认为,全球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拓宽视野,以避免对不同文化有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或偏见。展现自我要求人们不停地教育、解放和净化自身以培养健全的自我身份,从而同心协力为人类社会创建圆满的未来。另外,孔子学院要创文化软实力之“特色”,需要一批有志有识之士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并具备参与多元文化、促使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互通共荣的能力。
「注释」
①Ding, S., & Saunders, R. A.(2006). Talki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hinas Rising Cultural Power and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ast Asia, 23(2), 3-33.
②Schmidt, P.(2010). At U.S. Colleges, Chinese-Financed Centers Prompt Worries About Academic Freedom. Retrieved 2013-12-27, from http:// chronicle.com/article/At-US-Colleges/124975/?key=Smx.
③Redden, E.(2012). Confucius say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newscenter.nmsu.edu. Retrieved 2013-12-25.
④同②
⑤同③
⑥Gil, J.(2008).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Chinas Soft Power. Asian Social Science, 4(10), 116-122.
⑦Paradise, J.(200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49(4), 647-669.
⑧Hartig, F.(2011).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1, 53-76.
⑨王晓朝:《西方经典翻译与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新华文摘》,2007年5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