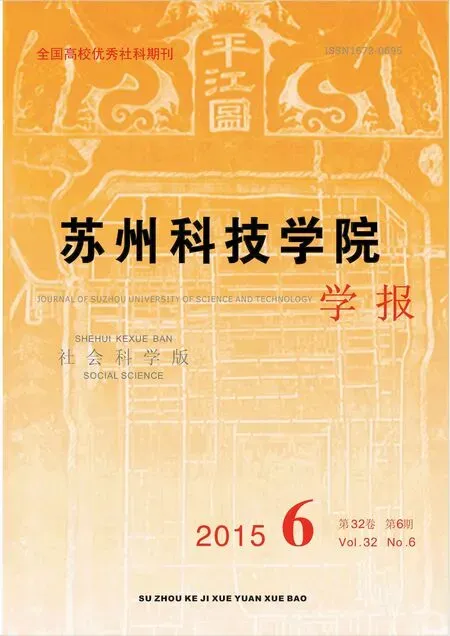尊严与权利关联的两种进路分析
陈慧珍
(苏州科技学院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
尊严与权利关联的两种进路分析
陈慧珍
(苏州科技学院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
尊严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含糊的概念。学界对尊严的含义理解仍存在争议。人的尊严经常与权利同时出现,从尊严与权利的关联中定义是界定尊严概念的一个方向。围绕着尊严与权利的关系,对人的尊严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及其主要论证均存在问题:通过契约论论证作为权利的尊严,无法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通过能力进路论证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无法解决人的尊严与能力之间的必然关联问题。
尊严;权利;契约主义;能力进路
尊严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含糊的概念。对尊严的含义理解依然是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一些世界性文件,如《世界人权宣言》中,人的尊严经常与权利(或人权)同时出现,以至于尊严和人权被形象地比喻为“连体婴儿”。因此,从尊严与权利的关联中来定义不失为学者尝试界定尊严概念的一个方向。围绕着尊严与权利的关系,对人的尊严概念主要有两种理解:作为权利的尊严和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笔者试图分析这两种理解及其主要论证中的问题,最后主张应通过其他进路论证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
一、作为权利的尊严与契约论论证
虽然在尊严是一项还是几项权利,抑或是权利的总和,以及作为尊严的权利与人权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一些学者主张把尊严看作权利*权利分为道德权利(moral rights)与法律权利(legal rights)。道德权利在逻辑上先于并独立于被各国认可和通过的法律权利,是法律权利确立和评判的依据。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权利均指道德权利。。权利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对待。在费因伯格(J.Feinberge)看来,如果B有权要求A为B做(或不做)X,那么B可向A主张做X。同时B拥有豁免A履行做X的义务之道德力量[1]。
(一)对作为权利的尊严之理解
在将尊严视为人应该受到何种对待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肯定人的尊严就是人的道德权利。纽曼(U.Neumann)认为,人的尊严是“合乎为人之尊的对待上的权利”[2]。第二种观点主张人的尊严是一项道德权利。沙伯尔(P. Schaber)指出,“人的尊严是一项权利,即不被侮辱”[2]。甘绍平研究员则进一步把侮辱分为侮辱性的行为与侮辱性的状态两种,其基本特征是受害人在强制力量下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侮辱性的行为,指摧毁受害者的自我或个体性,使其处于一种既无自卫能力,又无外援之指望的绝对任人摆布的恐怖境地的行为;侮辱性的状态,就是由绝对贫困、家庭悲剧、病痛折磨以及精神崩溃所引发的自我完全失控的状态。[2]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的尊严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德国多特蒙德大学(University of Dortmund)伯恩巴克(D.Brinbacher)教授认为,尊严既是伦理概念也是法律概念:依据载体是否具有主体性,可将尊严分为核心概念和扩展性概念。*核心意义上的尊严主要应用于人类个体,即基本权利的享有者,具有强规范作用。扩展性意义上的尊严概念则应用于个体之外的人类形式,包括其他各种人类生命形式、尸体、人类物种等,他们作为尊严的载体是抽象的,具有弱规范作用:可让位于其他价值和权利。参见Dieter Brinbacher, “Ambiguities in the Concept of Menschewurde”, in Kurt Bayertz:Sanctity of Life and Human Dignity,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p.101-121.核心意义上的尊严,作为法律和伦理概念都指不可转让和不可剥夺的个体权利的集合。作为道德权利的尊严涵盖了个体享有的、禁止被用于同其他善和权利进行交换或换算的优先性的四项基本善的权利:其一,生存性必要手段的供给;其二,免受强烈的、持续的痛苦;其三,最低限度的自由;其四,最低程度的自尊。作为法律权利的尊严,是个体享有的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最基本权利,是以最基本的四项权利为核心、涵盖众多其他权利的权利总和。作为法律规范的尊严,在内容上比《德国宪法》的第1—19条规定的权利总和要多,但由于尊严规定的是最低数量权利,因而与《德国宪法》中的人权目录的内容又有所不同;在权利的优先性上,尊严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如禁止羞辱性对待和迫害。[3]
关于作为权利的尊严的理解,一个关键性问题是,道德权利的主张是否蕴涵了这一前提:法律权利的保障。在笔者看来,上述不被侮辱的权利实际上蕴含了人权体系中的各种法律权利:第一,关于避免陷入或解除侮辱状态的条件,尊严意味着获得最低限度的身体营养供给等法律权利;第二,关于避免遭受或消除侮辱行为的条件,尊严意味着最低程度的自由、获得司法救济和公正对待等法律权利。故笔者认为,相对而言,伯恩巴克关于尊严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的观点更为合理。由于道德权利是法律权利确立的依据,笔者拟着重分析伯恩巴克关于尊严作为道德权利的论证。
(二) 对作为权利的尊严之契约论论证
1.作为权利的尊严之契约论论证
伯恩巴克认为,尊严作为上述四种基本善或基本权利的说明,可以借助格特(B. Gert)的道德规则理论中的第一组规则来证明。格特提出的道德规则,不仅指出哪种行动方式产生最少恶,而且还为可能遭受以有利名义侵犯的个体提供有力保护,因而是普世的、不变的底线伦理。在格特看来,权利是对道德规则的阐释。他提出了二组(共十条)道德规则,其中最为基本的是第一组*即不被杀害、不造成痛苦、勿使人残疾、勿剥夺自由、勿剥夺快乐。。格特主张道德是所有理性人都提倡和遵守的、制约所有理性人行为的公共系统,主要通过制定和遵守公共道德规则来指导和约束所有理性人的道德行为。格特关于道德规则的制定和论证,是基于理性人的基本自我需求的弱假定:理性人具有基本理性欲望,即生命、不遭受痛苦、能力、快乐和自由*在格特那里,理性欲望是与非理性欲望相对的。一个欲望是非理性的,仅是为了直接满足它而依它行动,即我们日常理解的未经反思而受之支配的直接欲望,如我只是为了看看我被砍断的胳膊后是什么样子,我就拿刀把自己的胳膊砍断了。理性的欲望包括理性要求的欲望(我们所说的绝大多数人赞同的欲望)和理性允许的欲望(如施虐者和受虐者是有一个享受快乐的理由而愿施加或接受痛苦)。。避免痛苦及生命遭到杀害,获得更多快乐、能力和自由,是合乎自我利益的。格特认为,理性要求的个人信念与基本理性欲望相对应,包括“我是会死的”,“我能遭受痛苦”,“我能被致残”,“我能被剥夺自由”,“我能被剥夺快乐”*格特把信念分为两类,具体为三种:非理性信念(理性禁止的信念)和理性信念(理性允许的信念和理性要求的信念),其中理性要求的信念是每个人都会理性地相信的信念。。理性的行动是理性要求和理性允许的行动,是自我利益优先、但允许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的行动。理性的行动禁止在缺乏理由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自我利益。
格特认为在制定道德规则时,只能以所有理性人都理解和接受的公共理性所要求的个人信念为前提。所有理性人最初都会基于自我利益和亲人、朋友等“近我”的利益,只要求他人服从,而希望自己逃避遵守这些规则,即不引起死亡、痛苦、能力、自由和快乐的丧失。所有理性人对规则都可能持一种“自我中心”态度,即“我希望:所有其他人都遵守我为了自己关心的人(包括我自己)而制定的规则,除非当我有(或如果我知道事实,我会有)关于遵守这些规则的理性欲望”[4]105。然而,如果规则要成为道德规则,就必须要获得其他理性人的接受、认可和服从,这是由格特对道德的定义决定的。但是,对于其他理性人来说,接受这种单向规则并非是理性的,因为他自身的基本自我利益并没有被纳入考虑中且获得保护。因此,就必须以恰当的道德态度取代对规则的自我中心态度。格特认为,对规则的自我中心态度有两种限制方式:假定理性人是不偏不倚的,或者采纳所有理性人都接受的态度。但这两种限制在效果上并无多大区别[4]109。在笔者看来*我认为,即便在取得对规则用恰当的道德态度取代自我中心态度方面具有相同效果,但两种进路论证的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进路是客观理性之必然,即必须设定理性人是不偏不倚的。广义上的不偏不倚,在格特那里,是独立于道德的,理性行动者中立于各方的,不包括在任何群体之中,“行动者A是在R方面对于群体G是不偏不倚的,当且仅当A关于R方面的行动不被群体G中的成员的利益所影响或被这些行动所伤害”(参见Bernard Gert, Mor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95.)。道德不偏不倚,是指在遵守道德规则方面存在两组群体:以我、亲朋好友为一组的群体;所有现在存在的其他理性人和曾经是理性人的另一组群体。任一群体中的任一成员决不能因为偏袒其所在群体以及成员的利益而允许破坏道德规则,除非破坏道德规则是可以公开并得到允许的。道德不偏不倚是以理性为前提的:第一,理性行动者追求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任何理性的行动者将自我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在缺乏足够的理由下允许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或增加受到伤害的机会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第二,自我利益保护的合理性。任一个行动者要想保护自我利益,即让其他理性行动者遵守规则,必定要承认其他理性行动者利益的平等性,在将自我利益纳入规则保护的同时也必定要使规则同等地保护其他理性行动者的利益,使规则对所有理性人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任何理性人的自我利益想要得到规则的保护,就必然同等地遵守保护他人利益的规则。,第二种进路是通过使所有理性人都从对规则的自我中心立场出发,最终达成所有理性人都将采纳的恰当道德态度,这种进路实质上属于契约论论证:所有理性人在一个共同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每个理性人接受规则是对自我利益的保护的同时,接受同样的规则也应当保护其他理性人同等的自我利益——即出于保护自我利益的目的,而去遵守保护每个理性人同等的自我利益的道德规则。具体论证如下:第一,以理性要求的个人信念作为演绎的前提,表明理性行动者追求的自我利益具有合理性——理性行动者优先考虑自我利益,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允许自我利益受到伤害或增加受伤害机会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第二,承认所有理性行动者合理的自我利益,即理性要求的个人信念禁止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使自我利益受到侵犯和自我损害。第三,理性行动者诉诸规则保护合理的自我利益。任何行动者基于自我利益制定规则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其他理性行动者同等的自我利益,因为双方都拥有基本自我需求,具有自主意志,处于平等地位的理性人。只有单个行动者在接纳其他理性行动者依靠规则保护同等的自我利益之需求后,其他理性行动者才能接受这个行动者对规则的自我中心态度,即这个行动者想通过规则保护自我利益是以其他行动者的利益考量为前提,才能使其他理性者遵守规则。行动者在承诺保护其他行动者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就承诺了遵守规则——放弃了自我中心态度,代之以所有理性行动者平等地遵守规则的道德态度。
尽管在沙伯尔那里,尊严仅被看作一项不被侮辱的权利,但关于尊严的论证很可能遵循着契约主义道德理论的路线。甘绍平在关于尊严作为一项不被侮辱的权利的论证时,就认为权利(人权)来自于人们的相互赠予或认可,道德义务来源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权利、义务就是通过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契约确立的。自尊是人类的核心需求之一,与自尊相关的人的尊严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人的尊严来自于一种对人际间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人的尊严的需求是存在于每一个具有自尊能力的人身上的事实。人之所以有人的尊严的需求,在于人的独特性:人除了独特的人类身体之外,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自我。自我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独一无二和独立自主。同时,自我又是以易受伤害性和脆弱性为前提,即易受他人侮辱。正是基于此,人产生了一种根植于人的自我或个体性的最基本的需求——不被侮辱的需求:作为尊严的权利[2]。
2.契约主义论证的特点及缺陷
从上述关于尊严的两种不同版本的契约论论证,可以发现契约主义的特点是,契约的达成是以平等的自主意志为前提,以满足人的利益或需求为目的,契约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对等的地位,即便在事实上有强弱之分。
作为权利之尊严的契约主义解释和论证具有以下理论优点:它说明作为权利的尊严不是来自某种神秘的本源,也不是来源于人的纯粹理性意志命令,亦不是来自独断的人类物种的内在优越性或作为人类物种的某种生理属性,而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的相互约定和赠与,尊严是为人的契约和人为的契约。作为权利的尊严论证是以现代契约论为基础,克服了古典契约论的内在缺陷:在进入契约的前政治时代,古典契约论抽象出来的契约者,是将个体从其融嵌的生活环境、其融入的社会关系、其个性形成的文化传统以及个人的独特品格中剥离出来。现代契约论承认订立契约者是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各种欲求、允许自己偏爱和关心对自身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并允许他们以这种独特的身份出场,商议和订立契约。正如在关于尊严作为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的论证过程中所描绘的契约者——自我是“承载着其家庭教育、生活环境、社会联系、文化熏陶、宗教信仰的印记,呈现着当事人的特征与品格”[2]。在格特那里,每个理性人不仅有生命、自由、快乐、能力、避免痛苦的需求和信念,而且个人还有保护其亲近的人之偏爱性的需求。现代契约论是对尊严作为保护基本需求的个体权利的强证成。作为个体权利的尊严具有不可侵犯性、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性,具有“类-绝对”(quasi-absolute)的规范力量*当然,不排除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存在为了更高的价值和其他权利作出牺牲的可能。。因而,当涉及权利主体的尊严与其他人类存在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权利的尊严就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契约主义理论本身及其应用于尊严的论证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1)契约主义是以契约者拥有自主意志为前提。这意味着缺乏自主意志的个体将被排除在契约签订者范围之外。虽然所有契约者可能会通过商议决定赋予非契约签订者同等权利,但被赋予的权利因其意志不在场而缺乏绝对同等的保障,很可能大打折扣。(2)契约主义以当代人为商谈主体,忽略对未来后代的需求和利益的顾及。未来后代是非个体性主体,非具体个体将来是否存在,对于当代人说是未知的,对他们的利益与需求的感受是远距离的、模糊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未来后代很难与个体契约者发生直接的强联系,从而进入个体契约者的需求而获得契约的保护。(3)契约的地域性限制问题。契约的效力仅存在于订立契约的群体中,其保护的利益仅是该群体中的个体需求,与契约之外的群体利益无涉。在现代民族国家依然存在,地区利益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地域主义无疑对契约主义构成一大挑战。如何使契约主义顾及乃至契合全球主体的利益是现代契约主义需要回应的。
其次,契约主义理论在应用于尊严的论证时存在的问题。(1)关于尊严的主体问题及其尊严的差异性。甘绍平没有明确指出尊严的主体,但可以管窥的是:尊严的主体同人权的主体范围无异,即从婴儿到死亡前的人类生命存在者。胚胎或胎儿这样的人类生命形式以及遗体在文中被明确排除在外。显然他采纳了单一、同质的尊严概念,“统一、同质的尊严概念的大部分吸引力似乎正在于这个事实:它不需要任何谁有资格成为强的意义上的尊严*笔者注:核心意义上的尊严。承担者的标准”[3]101-121。实际上,甘绍平对一项不被侮辱的权利隐含着一个尊严主体资格标准:与尊严相关的自尊感来源于具有自我意识能力和自我支配能力。这些能力是自我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意识到自我与他人区别的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自我支配的能力。按此标准,即便在活着的人类存在者中,仍有部分群体不够“格”:精神病患者、植物人、智障者等因不具备自我支配能力将都不能享有尊严;早期婴儿则并不具备将自我与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能力。同样,在缺乏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对同样不享有尊严的胚胎、胎儿的人类生命形式与人类尸体、未来人的地位和态度,给予相同的尊重。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伯恩巴克采用双重判断标准,使尊严概念具有两重维度:核心意义和扩展意义上的尊严。核心意义上的尊严即个体基本权利,即个体和具体的尊严,主体在权利与义务上是对称的,是以意识能力或主体性*subjectivity,根据该作者后面的说明,指的是感受或最起码的欲望的能力(the capability to experience anything or to have even minimal preference)。参见Dieter Brinbacher,“Ambiguities in the Concept of Menschewurde”, in Kurt Bayertz: Sanctity of Life and Human Dignity,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119.为标准的。扩展意义上的尊严是只享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抽象性权利,是一般的和抽象的尊严,为各阶段人类生命、人类、未来人,和不能合理地被算作真正“主体”的实体。在规范地位上,前者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性,后者地位更低和更不确定。后者的证成主要依赖于旁观者的情感,更多地随各文化的价值观念而变化,呈现出相对性。[2]虽然伯恩巴克意识到的核心意义上的、作为个体权利的尊严有所不足并提出了补救措施,通过扩展性尊严满足权利主体对人类生命存在者的同情,但不清楚的是,扩展性尊严的具体含义:虽然意味着对抽象的尊严主体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规范概念,缺乏具体的约束力。(2)无论是古典契约主义,还是现代契约主义(斯坎伦的契约理论除外),预设了契约方是以互利互惠为目的、契约签订者在能力和力量上基本平等。这隐含着契约主体(即契约签订者)和契约对象(契约的目的对象)的动机相同:契约者为了保证和增进自我利益而签订契约的。契约主义假定了所有契约者均拥有人类共同的“正常”能力,以不损害或牺牲自我利益为前提。这无疑将正常能力范围外的残疾人以及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依赖者(或借用另一个词来形象地表达“社会的包袱”) 排除在契约对象之外;即使不被排除,至多被认为是派生的契约对象。派生的契约对象,在权利的分配特别是在可利用资源的分配方面,与原初的契约对象不具有同等性,居于次要地位。以上表明:契约主义并不能保证尊严使所有人(拥有不同能力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拥有的能力)享有同等的权利(包括能力的行使机会),尤其不能保障他们获得可利用的分配资源以便发展自身的能力。
为了给平等的公民权利寻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纽斯堡姆(M. Nussbaum)提出了以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制定了以所有人的能力平等发展为目标来分配基本的社会资源,对尊严进行论证。
二、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与能力进路
纽斯堡姆提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价值,即尊严,因为人能通过行使人类独特的功能而过上一种人类特有的生活。因此,具有人的底线能力被认为是人拥有尊严的必要条件。尊严作为权利基础的能力进路(capability approach),把发展底线能力和提供行使底线能力的条件当作公民权利的道德基础。
(一)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及能力进路的论证
纽斯堡姆遵循着亚里士多德路线,主张人的价值根据在于人通过行使独特功能,过一种人类特有的生活:“第一,特定功能的表现,通常被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标志,在人类生活中处于特别中心地位;第二,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存在着以真正属于人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动物方式行使这些功能。”[5]71-72如果个体要参与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实现人类追求,必须具有一些可行使的底线能力*即纽斯堡姆所说的最低程度的内在能力。纽斯堡姆将能力分为三种: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y)、内在能力(internal capability)以及结合能力(combined capability)。基本能力指未经训练的能力,有时指待运用的能力如听力和视力,更多的指初级的和未能立即转化为运用的能力;内在能力指已经训练过的能力;结合能力指内在能力与适于它们行使的环境的结合。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84-85.。但是,这些能力是由人的基本能力发展形成并需要通过外部条件的支持来实现,即转化为结合的能力,它们是依赖于世界的、而不是自足的。关于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这种理解,可以通过能力发展进路作如下论证:
第一,人的尊严在于人因为能过一种真正的人类生活而具有独特价值。真正的人类生活(兴旺发达的生活)存在于人的多样目的性选择和行动中,但这些选择和活动是人在必要条件下通过行使某些底线能力实现的。
第二,缺乏底线能力以及不能行使底线能力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第三,人不应当不得不过那种不值得人过的生活。
(1)如果政府适当地尊重人的价值,那么不得不过缺乏底线能力的或缺乏行使底线能力之必要条件的生活将是一种恶,政府必须消除这种恶。
(2)政府必须适当地尊重人的价值。
(3)一个人不得不过他缺乏底线能力以及缺乏行使底线能力之生活是一种恶,是政府必须消除的恶。
结论:人有权发展底线能力和拥有行使底线能力的必要条件,并且这种权利是政府必须尊重的。*本文的论证,参考了魏斯曼提供的论证,补充了一个条件,并对之略作修改。原因在于:根据纽斯堡姆的结合能力说,该文作者仅强调了内在能力的发展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底线能力的运用需要必要的外部条件的提供,虽然具有这些底线能力的人可以选择不参与这些人类活动。Paul Weithman, “Two Arguments from Human Dignity”,in Edmund Pellgrino, Adam Schulman, and Thomas Merrill: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9.
人能够以一种独特方式生活、展现人类的卓越性是人的尊严之价值基础,具有一些底线能力则是人拥有尊严生活的必要前提。纽斯堡姆在《妇女和人类发展》一书中列出了人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十种核心能力: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性、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交往(affiliation)、关爱其他物种并与之相处、玩耍、控制自身的环境。这些能力不仅仅是人实现各种追求的工具,而且本身就具有价值:使人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
(二 )能力进路论证的特点
尊严的能力进路论证表明尊严是权利的基础,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其前提本身是“重叠的共识”——作为人之尊严的基础,人的价值,是不同宗教、各种世俗观念都接受和认同的观念,是超越了各种文化的共识。人的价值来源于人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我们把人看作是有活动、目标和谋划(projects)的——看作是毫无缘由地令人敬畏地超越于自然的天然行使,且人的多种核心计划是需要支持的。”[5]73它表明,尊严是众多宗教与世俗观念汇通的共同桥梁。其次,联接人的内在能力及其实现的自由主义方式,能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化生活观念相兼容,这体现了尊严的普世性。人的尊严,在于人能有计划地追求自身的目的,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自己独特的善生活。内在能力的拥有是追求和实现善生活的必要前提。纽斯堡姆主张的能力与行使分离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兴旺发达生活的、统一的善生活观念,能够为拥有不同善生活观念的人接受。它不是用统一的善生活观念要求底线能力的统一行使,而是将焦点聚集在发展底线能力所需的制度性保障,能力的行使完全由个人决定:根据各自的善生活观念,是否愿意利用制度安排或提供的机会行使这些能力。
能力进路及其产生的结果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尊严的能力进路论证克服了契约主义倚重程序而忽视了顾及内容或结果之缺陷。能力进路将拥有底线能力作为人拥有尊严的前提,为契约主义注入了内容:发展底线能力和提供行使能力的条件构成了权利的基本内容。
第二,尊严的能力进路独立地以人的底线能力发展为前提,而不预设契约的签订以各方具有平等的效益生产能力或具有产生预期互惠的能力为前提。“我们无需通过生产能力赢得尊重。我有支持人类自身的尊严需要的权利。”[6]159-160因而,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尊严为基础的权利是人的一种先验权利。
第三,尊严的能力进路蕴含着丰富、全面的人的概念。康德将人性与人的动物性对立,纽斯堡姆则把人的理性和动物性看作统一的,理性能力只是人类动物的功能之一。人的尊严不仅根植于理性之中,也根源于人的需要以及追求需要的多种形式之中。与只截取人的特定发展阶段(发展到理性能力的出现这一阶段)不同,纽斯堡姆把人类动物描述为具有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人的理性及其他能力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需要获得外部的支持,得到训练发展和获得运用的机会,有其脆弱性。斯多亚派把人的道德能力和理性本性看作充分的,将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性、财富、友谊等外在善排除在外;纽斯堡姆把理性能力及其他能力看作是动态的,是脆弱的、易受到外界环境和运气的影响,是需要发展与维护,使底线能力的发展成为拥有尊严的必要前提。
第四,人的核心能力的多样性标准使尊严具有更大的平等性,涵盖了更大范围的人类成员。一方面,拥有核心能力保证了所有人平等的尊严,而不是将人类存在者分成不同等级。另一方面,纽斯堡姆将理性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看作是组织和架构所有十种核心能力的主要能力,只要具备其中一种主要能力就可赋予尊严,因而扩展了尊严的主体范围。因为如果仅把理性能力看作尊严的基础,那么严重精神病患者等将被排除在尊严主体的范围之外。即便转向某种其他能力,如社会交往或关爱的能力,许多人类存在者仍会被排除。如果儿童的任何一种核心能力受损、但能被修复和发展时,他们仍可被赋予完全和平等的尊严。严重精神患者和幼儿等都可被纳入尊严享有者和权利的主体中,其中某些人能够爱和关护、但不能阅读和理解,有些人能阅读和理解、但在社会交往领域有严重缺陷或障碍。[7]
尊严作为权利基础的能力进路,把人的底线能力看作是人拥有尊严的前提,发展底线能力和提供行使底线能力的条件成为公民权利的道德基础。人的尊严不是先于并独立于人的能力而被定义的,人的能力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有尊严的生活本身就是部分地由人的一些核心能力构成。正是由于能力(如作为支柱能力的理性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使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体现出了人类生活的独特方式,与人拥有最低程度的尊严生活相符。有尊严的生活在于人拥有最起码的核心能力以及具备这些能力行使的条件,享有各种底线能力的发展和行使的条件就成为基本的道德权利的来源。
尊严的能力进路论证,一方面在弥补部分契约主义的缺陷上作出了贡献:纠正了契约主义对契约主体权力和能力的对称性、以互惠为合作动机的启动机制的倚重,揭示了契约主体的“独立”特征的内在限度,为契约主义造成的可能结果予以合理限制。例如,在斯坎伦的契约理论中,从接受和互惠两个基本的“薄”伦理概念中就不能推导基本善的理论。另一方面,能力进路与罗尔斯的契约理论不同在于,它不是仅把能力当作人的有尊严生活的一个手段,认为基本善的理论工具性地依赖于理性力量,而是将这些底线能力本身看作是有尊严的生活的必要部分,各种能力是不可替换的:“在一个领域中的能力*此处“能力”为笔者加。缺乏,并不能通过发展另一种更大的能力来弥补。这限制了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应用。所有公民,基于公正,有权提升所有能力到一个适当的底线水平”[6]166-167。
从根本上说,纽斯堡姆的能力进路论证虽对契约主义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和改造,但仍然是一种契约主义,只不过是对契约的内容和目标在其达成上有所设定,不至于使契约主义完全成为毫无方向甚至空洞无物的程序主义。因为在选择哪些能力能够成为人的尊严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和组成部分时,在评价哪些能力能构成基本道德权利的合法来源时,她认为她所列举的十种中心能力(尽管是尝试地列出并使其保持开放性以便被适时修改)的权利是“重叠的共识”,即它们是被持有不同的善生活概念的人都共同接受的、作为好生活的一个部分的善。在这里,“重叠的共识”与斯坎伦的契约理论不谋而合:一个观念或价值的证成主要是通过被所有人合理地接受。“接受性,因为稳定性——一个概念能恒久稳定地为所有人接受——和尊重的原因,与证成相关。……要求接受性作为证成的条件固化了这个观念:善的理论不是独立于人的同意的,而是能被论证为仅与这种同意的可能性相关的善的正当政治概念。”[6]163她认为,这个共识能跨越传统和宗教,可被国际广泛接受和普遍应用,即拥有这些中心能力——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个有尊严的人类生活来说是必要的,能够成为普遍性权利。
在确定拥有哪些能力是属于基本善、决定哪些能力构成一个有尊严的人类生活的最低条件、成为重要的基本权利时,纽斯堡姆通过采纳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来达到一种融贯的“重叠的共识”:关于能力是否构成有尊严的生活来说必要的评价任务并不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在思考能力和思考兴旺发达的生活之间来回移动,同时需要敏锐想象和在理论中反复确认,正如当我们到达某些基于我们的直觉观念的政治原则然后回过头来看它们怎么样。(我在这里追随罗尔斯,我主张一种整体的论证。在其中直觉和政治原则以及两者的其他论述,是受到我们反思的判断的支持和省察,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反思的平衡,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7]。纽斯堡姆并没有在人的尊严的生活(即存在于多种形式的目的性的行动和选择的兴旺发达生活)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客观理性的特征,然后依据这个客观特征必然地得到支持哪种权利。因此,在契约主义理论下达成的“重叠的共识”中,即核心能力之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是必要的,构成了基本道德∕政治权利,虽然大致解决了人的能力使人的尊严构成权利的根基问题,但人的能力与人的尊严之间的联结方式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因而其作为普遍和相对稳定的接受性就很难赢得保证。
结语
从尊严与权利的关联中界定尊严概念的尝试,主要有尊严作为权利和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两种理解。笔者考察了这两种理解及其代表性论证。从契约论出发论证作为权利的尊严,能够说明权利是来自于人为了自身利益与需求的相互赠与和保障而达成的约定,但契约论无法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从纽斯堡姆的能力进路论证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具有底线能力被认为是人拥有尊严的必要条件,因而发展底线能力和提供行使底线能力的条件成为了公民权利的道德基础。在确定哪些能力构成基本道德权利的合法来源问题上,纽斯堡姆的能力进路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契约主义,无法解决人的尊严与人的能力之间的必然关联问题。笔者主张,作为权利基础的尊严需通过其他进路来进行论证,以克服能力进路论证中面临的问题。
[1]Joel Feingerg. In Defence of Moral Rights[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2,12(2):149-169.
[2]甘绍平.作为一项权利的人的尊严[J].哲学研究,2008(6):85-92.
[3]Dieter Brinbacher. Ambiguities in the Concept of Menschewurde[M]∥Kurt Bayertz. Sanctity of Life and Human Dignity.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4]Bernard Gert. Morality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M]. Cambridge: Belkan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al Press, 2007.
[7] Martha C. Nussbaum. Human Dignity and Political Entitlement[M]∥Edmund Pellgrino,Adam Schulman, and Thomas Merrill.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9.
(责任编辑:张 燕)
2015-09-25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欧洲生命伦理原则研究”(11ZXB00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洲生命伦理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15ZXC020)
陈慧珍,女,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
B82-0
A
1672-0695(2015)06-0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