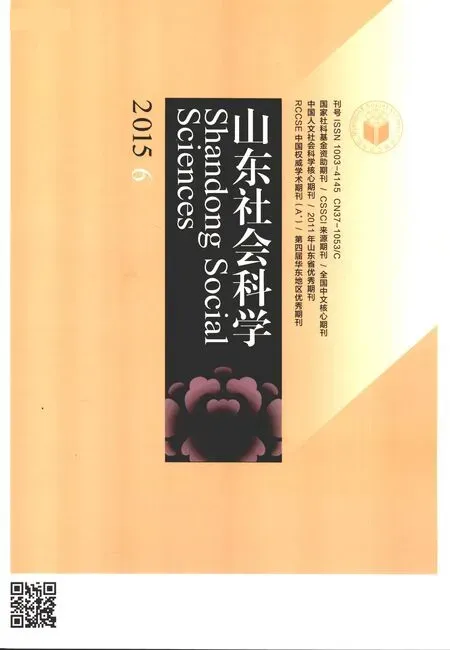论现代主体总体性的失落及其救赎策略
——走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
马廷新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哲学研究·
论现代主体总体性的失落及其救赎策略
——走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
马廷新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工具理性批判使现代性批判理论陷入困境,并造成了主体的严重异化,使现代主体的总体性陷入失落的境地,因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用来批判的规范基础总是那种已被现代意识超越的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实体理性观,这种理性观是对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反思,既不能展示启蒙现代性理想的规范内容,也不能揭示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特殊限制,更不能明确提出现代性合理潜能实现的途径。因此必须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由主体性哲学的工具理性基础转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基础。只有建立在生态存在论“实践”基础上的交往行为理论,才能既可以超越先验理性和超验理性的证明模式,又可以摆脱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困境,从而能够为现代性理想的兑现提供合理的理性基础。只有根据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将其建立在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从意识哲学转向存在论语言哲学,才能超越现代人们长期墨守着的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才能使现代批判理论走出困境,才能使现代主体的总体性得到真正的救赎而摆脱失落的境地。
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生态存在论;实践;总体性;主体间性
自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笼罩着传统社会宗教伦理的神圣光环被打破,社会被还原为功利的世界。人们开始按照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想来重建社会理论,开始由追求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和善的生活转向社会关系的合理调节。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理性高于一切的理想最终导致了人在技术上操控一切,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最终也导致了对人的技术统治。启蒙工具理性思维与传统生活理想的冲突和碰撞,产生了现代性的张力。工具理性批判的矛头总是指向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其用以批判的规范基础,却是已被现代意识超越的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实体理性。启蒙工具理性使现代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异化,现代主体的总体性不断陷入失落的境地。工具理性批判理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仍墨守着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没有根据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新批判理论基础;建立在主体哲学基础上的现代性反思,不能展示启蒙现代性理想的规范内容,不能揭示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特殊限制,不能明确提出现代性合理潜能实现的途径。因此,人类要消除现代主体间关系的异化,救赎失落的主体总体性,就必须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走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
一
现代二元论及工具理性使现代人坚信,自己就是经验着的、有目的的存在者,所以认为自己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他人用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于是,他们有理由相信,应当推己及人,把他人也看作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一个主体不把与之交往的另一个主体视作主体,而是视作手段、客体、物,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就降格为主体与客体的交往。人们都把交往的对方视作手段、客体与物,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就降格为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或金钱关系,其结果是物的关系吞食与取代了人与人的关系,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异化就是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物化、客体化;人们将自己看作目的,而将他人作为自己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私利欲望,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只为目的,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毫无友谊、感情可言,即使有时满嘴友谊,那也只是达到目的的幌子。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了。
人与人的物化关系表现为功能化、表面化的关系。功能化关系,是指交往双方均把对方当作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和欲求的手段或工具,也就是忽略对方的情感、品质、尊严等而将对方视作客体、物、抽象的实体。联结人与人的感情和友好的伴侣关系,变为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活机器之间的物物关系,在与他人交往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对方有什么价值与功能,如何从对方身上获得现实利益。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可转换的功能交往。人们同他的同伴之间没有密切的亲人关系的意识,不再能够爱他们,而只是利用他们。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心灵的碰撞与沟通。“个人被仅仅当作是一种被实现了的功能,它在无限空洞的形式中丧失了自己的本真性。人们开始害怕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害怕自己的愿望和情感。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其他一切均不再留存。而且,当技术问题被处理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默无言,但这并不是一种意义深刻的沉默,而只是空虚的表现。人似乎但愿能放弃他自己,但愿投入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投入欲望之海中去一样,但愿不再是自由的,而只是‘自然’的,仿佛‘自然’即等于某种被技术把握住了的东西。”①[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交往关系的表面化,表现为主体间的交往仅停留在礼节性的应酬上,其交往的动力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这种交往的方式体现为个体对大众观念统治的服从与认可。
物化意识还导致了人和自身相分离。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人已不把自己当作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②[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3页。。对他来说,学习和工作,都是一种投资,他的品质、人格、技术、知识、情感都溶化于商品中,其目标是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格,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市场上交换价值的实现。如果不能顺利地推销出自己,他就将被社会所遗弃,失去存在价值。因此,人只是尽力地适应外界的需要,按社会需要的模式塑造自己,成为没有自我的物品。
二
在现代“实利主义”或者“经济主义”的影响下,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首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成为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至上,金钱第一。人们对物的崇拜与占有已经达到了极端,对物质财富占有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与身份的象征,这种获取财富与物质的能力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用来评价人的那些标准:如诚实、善良、高尚、纯洁等,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做人标准统统被物欲的洪流冲垮。因而,弗洛姆把这样的社会称为“集体性的疯狂”时代,他说,“正如有过两个人的疯狂一样,也有过‘数百人的疯狂’,大家具有相同的恶行,并不能使这些恶行变成美德;大家犯有相同的错误,并不能使这些错误变成真理;大家患有相同的精神病,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健全的人。”③[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3页。在这个时代,人不再是“目的”,当个体功利主义地处理物时,存有本身表现为手段、目的、工具、需要和操持(procuring)的世界,人成为人的工具,这时“伪具体的世界”(科西克语)生成。人把自己的生活意义投射到对“物”的占有与追求上。经济观代替了道德观,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随着物化的加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者货币化的关系。人们坚信“人是经济的动物”这一信条,将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金钱成为衡量个人存在价值的唯一尺度,同时金钱也成为确定和他人的关系及其保障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最有力的手段。万事“钱”为首,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权利”和“前途”,权利,有“权”就得“利”,“前途”,有“钱”就“图”。万般皆下品,唯有“金钱”高。在商品社会中,“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征”①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153页。。金钱可以使爱变成恨,使恨成为爱,使平庸成为伟大,使不尊敬变为尊敬,金钱具有统摄人类灵魂的力量,一个人是什么与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其个性来决定的,而是由金钱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了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具有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②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153页。有一首打油诗是对现代拜金主义的最好的反映:现代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称意,没了它寸步也难,瘸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一分钱能难倒英雄好汉,孔明没钱也说不过潼关……。可以说,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货币是把我同他人、自然、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它是交往的基础与动力来源。金钱欲望已经成为他们存在的最重要、事实上是决定一切的特征。人们还坚信“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一信条。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一大众观点使我们坚信,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错误地认为金钱越多就越幸福,金钱万能论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于是,人们见钱眼开,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他们为了金钱,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丧失人性。人性异化程度之甚史无前例。弗洛姆精辟地描述了上述种种异化现象,他说:“是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人变成了商品,其生命变成了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存市场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已经异化为自动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③[美]弗洛姆:《爱的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其结果是现代人成为失落个性的机器人、待价而沽的商品人、贪婪占有的消费人。
三
交往关系的功能化、表面化、货币化必将导致的结果就是彼此心灵之间的日益陌生、疏远与冷漠。这种交往关系的冷漠化,一方面表现为:在大城市中,每个人和每个家庭,与左邻右舍的人几乎无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大家都充满戒备、彼此孤立地生活。并且主体间的这种冷漠感已经漫延到夫妇、父子、兄弟姐妹之间。从根本上说,这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化”所导致的彻底利己主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淡化还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这种难以沟通是指“我”在“人群”之中的寂寞。“我”在言说着、交往着,然而却依旧感到寂寞。这是因为“我”的言说与交往并不是发自于“我”的内心,来源于“我”的思想,而是在说“众人之所说”。陀斯妥耶夫在《地下室手记》中,以文学的手法描述了个体的孤独与苦闷。卡夫卡在《变形记》一文中更以敏锐而极端的形式表述了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心灵障碍。对此,海德格尔也写道:“互相关心、互不反对,互不关照、望望然去之,互不关涉,都是烦神的可能的方式。而上述最后几种残缺而淡漠的样式恰恰表明日常的相互共在的特点。”④[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9页。
在现代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最终陷入了两难状态,即为了生存与避免孤独,个体必须与他人交往,融入社会生活中,但是这却将导致主体被社会的同化与消解,最终使人的自由与个性丧失。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描述了人的这种两难状态,他说,人渴望自由,却又缺乏承担自由的能力,因为自由带来的空虚是无法逃匿的。对于人来说,积极性的自由存在于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中,一种创造性活动中,它的先决条件是精神的完整。然而现代人却失去了这个要素。自由带给他的只是无可归依的空虚,正是对自我存在无根的漂泊感的恐惧,使当代个人根本上依赖于大众意识形态,依赖于秩序,试图藉此摆脱个体存在的危机与孤独。韦伯也为现代人的形象勾勒出一幅悲观的前景:“每当想到世界有一天将会充满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着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像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我们只需要‘秩序’,此外别无他求;倘若一旦秩序发生动摇,我们就会感到六神无主,畏葸不前;倘若完全脱离秩序,就会感到孤立无援。”⑤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实质上,依靠大众确认自我,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虽然与大众合流可以摆脱孤独,但是,同时大众意识又使个体更深地消解自身。这种大众意识对于真正人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个人日渐迷失在大众之中,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意义。他已不再是孤立的自我,因为某种一致的普遍的大众意识具有的一般特性占据并同化了他的身心。它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成为千篇一律“单面人”。这样,在真正的自我消失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停留于表面,越来越功能化、单一化、公式化了。
四
物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格的完美性的消失、人的世界的片面化发展。当人们把对物的追求、占有与消费当作人的全部目标时,人自身的完整性就失去了,因为他失落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精神世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向善、向美的动力,完全沉溺于外在的、表面的、物化的存在状态中。在现代社会中,面对局部工作的丰富成果,我们都处于一种可悲境地,无法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对待,物化意识已经渗透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它对于真正人的总体的存在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个人日渐迷失在物质之中,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意义。他已不再是他自己的孤立的自我,因为某种一致的、普遍实用的模式化的社会的一般特性占据并同化了他的身心。这种物化意识竭尽全力地使我们有目的的生活变得无效。它悄然地损害着人的个体自我。甚至人处于其中,但却依然不晓。“这种生活秩序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①[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精神的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个人被融入了功能之中,生命被客观化了。他的存在的目标在于增进物质生产的效率。
在这种状态下,实用化、功能化日益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普遍的社会尺度,雅斯贝尔斯指出:“一旦普遍的秩序所起的作用是将这个整体肢解成诸种局部功能,而这些功能的执行者可以无差别地替换,那么,在工作中的这种快乐就被毁掉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关于总体的理想便消退了。以往曾经要求将整体的存在寄托于连续的构成性成就之上的活动,现在则被贬低为一种仅仅是副业的活动。”②[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精神的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这个世界是以疯狂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目的。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均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它试图转移人应具有的价值与尊严,从而成为它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如果说人们现在仍然恪守着常规,那只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或惧怕法律的惩罚,而非源于任何道德和良知,不是源于真心。因而,“当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为生活利益的目的性时,关于整体的实质内容的意识便消失了”③[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精神的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人的总体性失落主要指的是超验世界——信仰、意义、价值、理想等神圣性的丧失。从宏观上看,这种失落将导致我们失去向善、向美的动力。而对于人类个体来说,总体性的失落意味着人自身人格的完整性的丧失,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远遁。人沉浸在物化的状态中,成为纯粹的个体感官经验主义者。在这种状态中,人的一切活动、一切行为均以对物质的追逐与占有为目标与尺度,其结果是人自身降格为商品。随之而来的是人的世界全方面的物化、功利化,全都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受价值规律所左右,而演化为物质世界的附庸。总之,总体性失落之后的人自身及人的世界处于失去精神之维的黑暗状态之中。
现代为幸福而立法的理性之梦结出了苦果。最恶劣的反人性的罪行以理性的统治、更佳的秩序和更大幸福的名义得以施行,思想麻木的破坏却原来是哲学必然性与职权的骄傲自信相结合的结果。现代的普遍理性与完美的浪漫向往已被证实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事务;秩序的伟大工厂继续带来更多的混乱,反矛盾态度的圣战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因此,它们也被证实是失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异化问题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复杂困境,不断地骚扰着人们的神经。于是,人类的心理宇宙倾斜了。
五
俗话说:“治病要治根”。人类要消除现代主体之间关系的异化,救赎失落的主体总体性,就必须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规范基础。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重建,必须为现代性理想的兑现提供理性的基础,既超越先验理性和超验理性的证明模式,又摆脱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困境。首先,必须满足后形而上学时代理性重建的可能性,因为现代意识已经超越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其次,这种理性必须能够满足现代性理想的规范要求,即现代科学、道德和审美经验的内在有效性要求;第三,必须能够为人类再生产和社会合理化提供普遍合理的条件,文化合理性必须成为社会全面合理化的力量;第四,必须能够历史地经验地说明合理性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系统制度化的具体形式。总之,现代性规范重建的任务,就是要澄清文化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的理想,为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提供一盏规范、准确的“指路灯”。
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进行哲学基础和范式的转换,因为现代性危机实际上是理性的危机,理性的危机就是传统哲学范式的危机,对启蒙的批判也是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主体意识哲学的批判。如果我们仍然从主体哲学的认知和目的行为关系出发,以建立在主体意识哲学基础上的理性批判理论来批判现代性,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由意识哲学转向生态哲学,才能使批判理论走出困境;人类才能消除现代主体之间关系的异化,救赎失落的主体总体性。如果人类从相互理解、相互平等的生态关系出发,就能从另一方面看待人类再生产和社会合理化。“如果我们假定,人类是通过它的成员社会协调行为维持的,而这种协调又是通过交往建立的——即在核心领域通过达到一致意见的交往——那么类的再生产也就获得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的令人满意的条件。”①[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l卷),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84年版(英文版),第399页。这种交往理性,并不是自我维持的主体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同客体发生认知和行为关系,而是建立在生活世界共同的意义背景基础上,通过社会成员相互理解达到共识。主体的自由和人类关系的和解的力量包含在生态关系的相互理解机制中。社会理论必须告别主体意识哲学的工具理性,转向以生态关系的理解机制为核心的交往理性。只有在新的理论语境中,才会既能保留批判理论的积极因素,又不堕入理性的怀疑主义和人与自然无中介交往的非理性或超理性的乌托邦。
六
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行为理论背景出发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即通过形式语用学阐明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的基本特征,重新把握理性概念,其目的是要超越形而上学和工具理性概念;二是从社会理论背景出发提出的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结构理论,即通过对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化的不同方式的研究揭示社会合理化的基本要求,其目的是要超越社会总体性的社会观,把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批判发展为社会功能主义批判。
交往理性不是以认识论为基础,而是要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以语言理解式的话语实践为核心。交往理性不能建立在传统本体论的存在或宗教上帝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基础上,而要建立生态存在论语言之上。因为理性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要求一种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媒体,这一媒体只能是生态存在论语言。哈贝马斯早在1965年就明确指出:“使我们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东西:语言。通过它,自律和责任就被置于我们前面。我们最初的语词毫无疑问地表达了那种普遍的非强制的共识意向,而自律和责任一起构成我们先天(在传统哲学意义上)所拥有的观念。”②[德]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类利益》,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71年版(英文版),第314页。他还认为,理性的基础不可能消亡,因为人类还有语言,“今天语言问题代替了传统的意识问题;语言的先验批判超越了对意识的先验批判。”③[德]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法兰克福出版社1971年版(德文版),第220页。当人类用语言相互沟通时,理性已经蕴含其中了。因此,交往行为理论是既包括理性的规范重建,又包括现代社会经验研究的系统理论。生态存在论语言转向意味着批判理论从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转向对知识和行为合理性基础的积极重建。
对批判理论的重建,既不能通过传统哲学的先验演绎,也不能通过现代经验科学的经验归纳来实现。对此,哈贝马斯在现代的重建式科学的范式当中为我们找到了理性证明的新模式。他认为,重建式科学是一种区别于具体经验知识的特殊理论,它从具体行为和经验知识出发,揭示一类行为和知识合理性的普遍形式和结构。在我们看来,无论从语言学转向来说,还是从社会学转向来说,交往理论都离不开“实践”这一最根本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物质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及其活动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交往活动是人的个体活动加入和转化的社会活动总体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活动总体的各要素在不同个体或集团中分配的基本形式。交往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正是在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而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扩大,也发展和扩大着人们对交往本身的需要,并提供交往发展和扩大的前提。而交往的发展和扩大又反作用于物质生产,通过产生新需要、发展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另外,用来交往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形式,而且要强调交往实践的话语,必须是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
七
生态存在论认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的关系。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践是交往关系产生的基础,它总是展开与生成着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主体对客体的重塑与创造。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等。这双重关系,在生态存在论看来,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再从交往与实践的产生来看,二者是同时的、互为前提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决定着交往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受强制的、被迫的。对此,马克思有一种形象的比喻:当强制性限制一解除,人就将像逃避鼠疫一样逃避劳动。这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异化的,一少部分人以大多数人作为手段、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其体现为对人的潜能的开发,人“按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在劳动中,人感受到美,自由、创造的喜悦等。马克思认为,“在理想的交往主体身上将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真正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对手段而是对目的的需要,换言之,交往本身就是目的。”①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这样,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交流自身的感受,人不仅可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反观到自身,而且可以丰富自身,使自我得到确证。这时,社会就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每一个人存在的同时也都是为他人的存在,而以往迫于生存需要而进行的交往,变成了人对自身生命本质的自由的全面占有,交往成为人的内在需要。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由被迫的生存性活动转变为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交往也不再是以往形态的简单延续,而相应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唯有如此,人类才能从过去已有的条件出发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才能得以解决,这样个体既克服了封闭感、孤独感,又不会被社会同化,社会为个体提供了表达其潜能的机会,整个社会成为富有个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个体重又获得了丰富性与全面性。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方能独立的动物。”②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交往问题的真正解决,离不开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尽管现代有些哲学家也意识到“交往”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他们大多将其视为观念的东西,而忽视了“交往”产生的根源和现实基础,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主体总体性失落的困境。唯有回到实践中来,认识到交往与人的最本质的存在方式——实践是息息相关的,认识到现存的交往的异化状态是目前人类实践活动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摒弃主体性哲学的启蒙工具理性,走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才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改变,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目前“交往”中所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才能使现代主体的总体性得到救赎而走出失落的困境,才能实现一个和谐的、以理解为目的主体间性关系,才会使人具有全面性、丰富性,即“完美人格”的实现。
综上所述,工具理性批判使现代性批判理论陷入困境,造成了主体的严重异化,使现代主体的总体性陷入失落的境地,因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用来批判的规范基础总是那种已被现代意识超越的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实体理性观,这种理性观是对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反思,既不能展示启蒙现代性理想的规范内容,也不能揭示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特殊限制,更不能明确提出现代性合理潜能实现的途径。因此,必须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由主体性哲学的工具理性基础转向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基础,因为建立在生态存在论“实践”基础上的交往行为理论,既可以超越先验理性和超验理性的证明模式,又可以摆脱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困境,从而能够为现代性理想的兑现提供合理的理性基础。可见,只有根据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重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将其建立在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实践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性哲学,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从意识哲学转向存在论语言哲学,才能超越现代人们长期墨守着的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才能使现代批判理论走出困境,才能使现代主体的总体性得到真正的救赎而摆脱失落的境地。
(责任编辑:陆晓芳)
B83
A
1003-4145[2015]06-0142-06
2015-05-08
马廷新,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