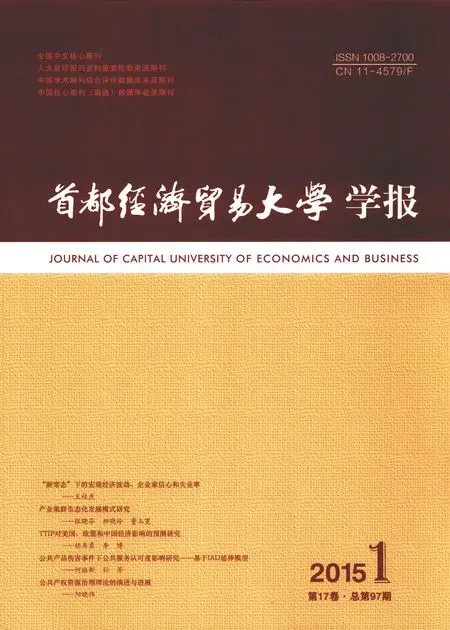公共产权资源治理理论的演进与进展
阳晓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公共产权资源治理理论的演进与进展
阳晓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1954年,戈登(Gordon)最先抓住了CPR问题的本质,并对其属性进行了模型化论证,成为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哈丁“公地悲剧”的发表则激起了学界研究CPR问题的热潮。早期学界主张要么通过“利维坦”,要么私有化来治理CPR。由于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努力,社区自治作为事实上的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日益得到认可。拉赫曼(Rahman)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在特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公地不仅不会导致悲剧,而且具有私地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希尔(Hill)对美国野牛的研究发现,即使是经济学家公认的公地悲剧也未必真的就是悲剧。
公共产权资源;公地悲剧;私有化;利维坦;社区自治
引言
公共产权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下文简称为CPR)问题不仅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且关系到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由于CPR的特殊属性——非排他性和使用上的竞争性,往往会导致CPR的过度拥挤,经济租金耗散,甚至使人类连同CPR一起走向毁灭。长期以来,CPR治理理论是主流经济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CPR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相对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言,CPR可能导致的问题往往还要更加严重和迫切。国内对于公共物品问题的理论已经有学者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研究,但是全面总结和介绍CPR治理理论发展脉络和最新进展的文献却非常匮乏。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学界对CPR治理理论的认识,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国外对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文献。
一、戈登(Gordon)的开创性贡献
戈登(1954)发表了其开创性论文《渔业:公共产权资源的经济理论》[1]。他指出导致过度捕鱼的症结就在于缺乏任何“有意义”的产权安排。通常而言,既定水域能够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成本生产若干种鱼类,当人们对某种类型的鱼的需求超过水域生产力的临界值时,渔获的边际成本将会上升。换言之,随着鱼类资源储量的下降,近海捕捞的每一单位捕鱼付出(fishing effort)所能得到鱼的数量将会下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人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将捕鱼的范围推向离海岸更远的地区。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推进,一方面将会导致某些鱼类的枯竭,另一方面会导致渔业资源经济租金的消失。政府规定限渔期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租金消失问题,甚至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恶性竞争,造成资源的更大浪费。戈登认为所有产权共有,但是其使用(或开发)却是基于个体竞争的自然资源都会面临经济租金枯竭的问题;海鱼仅仅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
虽然克拉奇菲尔德(Crutchfield,1956)[2]指出,戈登的模型过于简单化,限制捕鱼量并不能保证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跨期产出等于、小于或大于没有这种限制的情形。但是这并不影响《渔业:公共产权资源的经济理论》作为公共产权资源理论真正发端之作的历史地位。理由如下:
最先关注某些海鱼繁衍困境的是生物学家,但他们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大致持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海鱼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第二,赫胥黎(Huxley,1881)[3]和麦金托什(MacIntosh,1899)[4]等认为,即使海鱼数量在特定时期明显减少,主要也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类商业性捕捞行为无关紧要。而戈登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出海捕鱼数量减少,海鱼存量明显增多”的事实对此加以反驳。在戈登之前,也有学者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某些海鱼的繁殖难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产权的非排他性和使用的竞争性,而是借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来展开论述。他们的理论逻辑是:人类得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但是鱼类等其他生物却不能像人类那样“改变环境”,因此难免走向灭绝。因此,在戈登的文章发表之前,无论是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没有抓住某些海洋鱼类(CPR)不断消失问题的本质。
自戈登以后,从产权安排的角度来研究公共资源(又叫“公地”)就变成了主流范式。很大程度上讲,公共资源(the commons或common resources)问题就转变成了公共产权资源问题(即CPR:common-property resources)。不过《渔业:公共产权资源的经济理论》也存在着某些不足。比如,他认为公共产权是“无意义”的产权,相当于无产权,这未免过于武断,因而受到了后来学者们的批评。
二、以“利维坦”或私有化为唯一治理手段的时期
自1954年公共产权资源理论开创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界对于公共产权资源的治理对策,从本质上来讲要么是以“利维坦”*利维坦(Leviathan),最初的意思是《圣经》中描述的海怪,在经过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演绎之后,一般代指国家,或者国家政权机器。,要么以产权私有化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当我们把研究的问题变为“没有外部强制力量的公共产权资源条件下,如何使人们同意遵守某种有计划的使用资源的规则”时,公共资源问题就变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一个特殊的子问题——集体行动理论问题。
(一)三种最有影响力的集体行动模型
1.囚徒困境博弈
它是指两个被警察分别监押的囚犯,警察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两个囚犯之间不能做任何信息沟通的情形。其规则如下:首先,警方已经掌握了两个囚犯部分犯罪事实,根据这些证据只能将两个囚犯关押较短时间,比如两年。如果甲供出其团伙乙的其他犯罪事实,且乙保持沉默,则甲将仅被关押一年,而乙则将被关押五年;对乙而言,该规则同样适用。如果两个囚犯都保持沉默,则双方都将被关押两年;如果两人都选择坦白,则都将被关押四年。
囚犯出于个体最优的考虑,最终都会选择其占优策略“坦白”,从而都将被关押四年。然而对于两个囚犯而言,其集体最优策略是都选择沉默,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将仅被关押两年。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但是,囚徒困境博弈是建立在极强的假设条件之下的:它要求两个囚犯之间不能有任何信息上的沟通,而且博弈次数仅为一次,两个囚犯之间不存在信任。
2.哈丁的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缘起于哈丁(Har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地悲剧》[5]。尽管哈丁并没有直接使用囚徒困境这一术语,但是他得出的结论与囚徒困境博弈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哈丁一开始就让读者设想一个“向所有人自由开放”的公共牧地。每个牧民都是理性与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因出售放牧的牛羊而获得正效用,因公地的过度放牧而承受负效用。当全体牧民总放牧量达到牧场的最大承载能力时,对于全体牧民这一整体而言,放牧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从而达到最优的放牧量。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放牧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单个牧民的私人边际收益;而另一方面,放牧的私人边际成本则远远小于社会边际成本*因为每一位牧民只承担他自身过度放牧的部分成本。。因此,当总的放牧数量超过牧场的最大承载能力时,还会有足够的激励促使理性和自利的牧民选择继续扩大放牧数量。最终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促使他无任何限制地扩大其放牧量的系统”,但是该系统本身的资源是有限的。哈丁认为对于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有人而言,“毁灭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地”。
污染问题作为一种公地悲剧,是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而显现出来的。哈丁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将“公地”作为粪池并不会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公共领域”;而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繁华的闹市区则变得难以忍受了。在人口稀少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一种“自动调节”的能力。可是当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污染速度就会超过大自然“自动调节”的能力,污染问题就会日渐凸显。这时,重新界定产权就变成了一种必要。
哈丁认为道德并不能够承担起有效解决公地悲剧的任务。因为对于一个处在公共资源环境当中的人而言,他的意识或者潜意识早晚都会传达给他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号:(1)如果不像公众所要求和期待的那样做(减少自己的占用量),我会受到公开的谴责;(2)假如果真像公众所期待的那样去做,暗地里我又会被当成“冤大头”来嘲笑,而其他的所有人则尽情地攫取着公共资源。现实当中,第二种信号会占据大多数人的内心,带着某种“内疚感”尽量多占,进而有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贝特森等(Bateson et al,1956)[6]指出“内疚感”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导致精神分裂症。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公地的“悲剧”色彩。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地”事实上变成了“私地”。这一过程的肇始领域是食物。越来越多的耕地被篱笆围起来变成私有财产,继而牧场、渔场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就连生活垃圾的处理也不再是“公地”性质的了。一方面,私有化是有效解决公地悲剧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也会限制人们的某些自由。黑格尔(Hegel)语“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知”(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而教育则有助于使人们对必然性的认知,从而有利于使人们获得自由。哈丁认为:要想做到既解决公地悲剧,又避免因私有化而失去某些自由,就必须剥夺人们的生育自由权,从而降低人口密度。但是,控制人口数量与世界人权宣言是相违背的*1967年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社会最基础构成单位的家庭拥有决定家庭规模大小的权利”。。
哈丁认为要解决人口过度繁衍带来的公地悲剧问题,最终出路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妥协”的外部强制性手段。他认为政府当局理当成为实施这种强制性手段的机构——即通过“利维坦”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
3.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囚徒困境博弈具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他的核心观点是“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7]。因此,要想让理性和自利的个人为集体利益而行动,就必须要么借助强制性力量,要么提供“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是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为克服“搭便车”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它大致可以被定义为:赋予对个体成员偏好的价值超过其承担集体物品成本的份额时的动力机制。。当这两种机制都不存在的时候,理性个体都会采取“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设某一集体能够有效采取集体行动的程度为函数f,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和笔者的总结,f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变量:集体规模、集体利益大小、集体成员从集体行动获利的异质性程度和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创设。
f=f(集体规模*集体规模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它是指在某一集团中成员行动对集体其他成员影响的显著性程度,主要但不仅仅受集团人数的影响。,集体利益大小,集体成员从集体行动获利的异质性程度;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创设)
其中前三个变量为集体行动模型的内生变量,指在没有人为制度设计条件下模型本身将会自发产生的集体行动规模或程度,从主观经验上判断,集体行动的程度与集体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与集体利益大小和集体成员从集体行动获利的异质性程度则呈正相关关系,且它们三者的权重依次递减。集体行动程度负相关于集体规模,正相关于集体利益大小是不言自明的。对于集体行动程度正相关于集体成员从集体行动获利的异质性程度,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理解:当集体成员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异质性程度较大时,该集体的行动将更加有可能从囚徒困境转变为“斗鸡博弈”或“智猪博弈”,从而走出囚徒困境。相对于前三个变量而言,最后一个变量是外生的。
对于前三个变量,奥尔森本人强调最多的是集体规模,其次是集体成员异质性程度。韦德(Wade,1987)[8]认为奥尔森对于集体利益的大小虽有论及但强调较少。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创设则是奥尔森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提出的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条件下,奥尔森对人数非常多的大集体行动持悲观态度,对人数较多的中等规模集体的集体行动持开放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还不能下定论的问题,而对小规模集体的集体行动则并不悲观。当考虑到外生制度创设——选择性激励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并没有像世界银行的韦德(Wade)等人所认为的那么悲观。对于这一点,奥斯特罗姆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该书的英文原版是:Ostrom E.(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8页)。
总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虽然与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悲观色彩,但是这种程度远远没有前两种理论那么强烈。而且当我们以一种综合与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时,这种悲观色彩就变得更加弱化了。加上奥尔森在理论上为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提供了其解决方案——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创设。因此,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中所论述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成败从理论上来讲,正是受制于选择性激励制度创设成功与否的影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基于“田野式调查”,其论述更具有现实基础,是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公共产权资源自主组织和治理方面的应用和细致化。
(二)以“利维坦”或私有化为“唯一”治理手段的阶段
奥斯特罗姆(2012)认为基于以上三种集体行动模型,或者类似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得出除非借助外界力量(即政府机器“利维坦”),或者对CPR实行私有化,否则CPR问题就无法解决的结论。本文认为前两种模型确实如此,但奥尔森的理论是否真正带有这种倾向则是有待商榷的。借助利维坦或者私有化来解决CPR问题的传统由来已久,很难确定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始于何时,自从奥斯特罗姆等人在理论上,尤其是大量的经验事实上,证明了社区确实能够通过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CPR问题以前,应对CPR问题的备选方案除了借助于利维坦,或干脆对CPR实行私有化以外别无他途。而且这种观点长期占据着CPR治理问题的“主流”地位,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末。
1.“利维坦”解决方案
主张以利维坦为解决CPR问题唯一方式的学者主要有哈丁、奥菲尔斯(Ophuls)和海尔布罗纳(Heilbroner)等人。比如,奥菲尔斯(Ophuls,1973)[9]认为,公地悲剧是必然存在的,这样环境问题就无法通过合作加以解决,因此具有较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就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据此,他得出结论:“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它也只有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的手段时才能够做到”。哈丁则在他的经典论文《公地悲剧》发表十年之后,继续发表意见称,人们对于政治制度的真正性质以及每个人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10]。带着“公地的替代物太过棘手以致无法做深入探索”的成见,哈丁认为:“无论何种力量能够用来制止变迁”,就必须将变迁制度化。哈丁指出“在一个混乱的世界,若要避免毁灭,人们就必须对存在于他们心灵之外的某种强制性力量表示臣服,这种力量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利维坦’”[10]。
海尔布罗纳(Heilbroner,1974)[11]则更是鼓吹,“铁的政府”,甚至是军事政府,对于实现生态平衡是绝对必要的!埃伦费尔德(Ehrenfeld,1972)[12]的观点则相对缓和一些,他认为个人对于维护公地是不会产生兴趣的,要想解决公地悲剧就必须借助公共机构、政府或者国际权威实行外部管制。借助“利维坦”来解决CPR问题,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大。
2.“私有化”解决方案
以德姆塞茨(Demsets)和张五常(Cheung)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认为,唯有实行产权的私有化才能对CPR进行有效的治理。比如德姆塞茨(1967)[13]、张五常(1970)[14]和约翰逊(Johnson,1972)[15]等认为,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都必须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史密斯(Smith,1981)[16]指出:“无论是哈丁论述的公地悲剧还是对公共产权资源进行的经济学分析”,都表明“在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问题上,要想避免公地悲剧唯一的方法就是,创建私有产权来取代公共产权制度”。更有甚者,韦尔奇(Welch,1983)[17]声称:“为避免过度放牧造成的低效率,将产权完全私有化是必要的”。他认为公地的私有化对于所有公共池塘资源而言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他关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实行私有化,而是如何强制推行私有化!私有化解决方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非常大。
三、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社区自主组织与治理”方案异军突起
奥斯特罗姆是CPR社区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倡导者,也是CPR治理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由于在CPR治理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她荣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成为史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女性。
(一)逻辑实证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第五类”博弈模型,从理论上论证公共产权资源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方案的可能性。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收益参数e,它表示执行协定的费用。在这一博弈中,牧人必须事先就放牧牲畜的数量进行谈判,以决定各自如何分享牧地的承载能力和分担执行协定所需的费用。假设牧人之间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合约就不能得到执行。在谈判中,任何牧人提出平等分配执行费用但是不平等地分享牧地承载能力的提议,均会被另一位牧人所否定。从而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可行和唯一的协定——两位牧人平等地分享牧地的资源,并且在每个牧人支出的执行成本低于10的情况下,平等地承担协议的执行费用,见图1。
在本博弈中,博弈人总是可以保证最糟糕的选择就是(不合作,不合作),而并不取决于政府官员获得关于他们策略信息的准确与否。因为如果当一位牧人提出的建议是基于不完备或者有偏差的信息时,另一位牧人就会反对,这样合约就是局中人一致同意的结果,要求执行者执行的只不过是他们自身业已同意的方案。若执行者索取的服务费用过高(大于或等于Pi(C,C)-Pi(D,D),此处i=1,2),则博弈双方都会反对。
(二)经验实证
在公共产权资源(尤其是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经验实证方面,奥斯特罗姆不仅本人做了长期、大量的实地考察,对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案例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与总结。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她详细地介绍了瑞士的托拜尔(Torble)公共牧场,日本山村(平野村、中生庄和良木家庄)公地[18],西班牙巴伦西亚木尔西亚(Murcia)、奥瑞辉拉(Orihuela)的公共灌溉系统[19]、雷蒙德西部和中部流域[20],菲律宾的巴卡拉一文塔,西班牙的阿里坎,土耳其的阿兰亚,斯里兰卡的加勒亚,加拿大的莱蒙隆港,土耳其的伊兹米尔湾和勃德拉姆,斯里兰卡的马维尔和科林迪奥亚,莫哈韦的地下水流域,雷蒙德的西部和中部流域(早期)等地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治理的组织设计原则及其制度绩效的情况
至少对于满足她总结的八项原则的几种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行没有私有化和外界干预条件下的公共池塘资源直接利益方,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公共资源难题。比如瑞士的托拜尔(Torble)公共牧场,日本山村(平野村、中生庄和良木家庄)公地,西班牙巴伦西亚木尔西亚(Murcia)、奥瑞辉拉(Orihuela)的公共灌溉系统、雷蒙德西部和中部流域,菲律宾的巴卡拉一文塔等公共资源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这就进一步从经验事实上证明了“利维坦”或者“私有化”确实不是解决公共资源问题的唯一方案。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治理的制度设计原则与绩效
奥斯特罗姆将促使公共池塘资源保持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治理原则总结为以下八个方面:(1)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际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积极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成本低廉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7)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8)嵌套式企业(nested enterprises),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在一个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
奥斯特罗姆列举了14种制度安排是否满足其八项原则的情况,和各自对应的制度绩效,详见表1。
注:①NR=不相关。②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从1937年至1840年,从1930年至1950年。③资料遗失。
通过表1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当一个地区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治理的制度设计,完全或者较好地满足奥斯特罗姆归纳的八项原则时,其对应的制度绩效是成功的。否则,对应的制度绩效就是脆弱甚至失败的。但是奥斯特罗姆对她自己提出的八项原则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她认为在得到足够多的理论与经验事实的验证之前,尚不能下定论,认为这些原则就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必要条件。
四、最近几年的代表性文献概述
1990年奥斯特罗姆的专著“Governing the Commons”出版以后,对西方经济学界关于CPR问题的研究范式和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范式上,大都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以带有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案例分析为主;在思想上,大部分学者接受了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并沿着她的思路展开研究。
自奥斯特罗姆以后直到今天,关于CPR治理问题基本上没有重大理论突破*如果说有例外的话,Hill(2014)的文章至少应当算得上是其中之一。它是自奥斯特罗姆之后为数不多的在理论上有一定贡献和新意的作品,因此放在后文作为独立的一小节重点介绍。,无非是将已有的三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案进行组合式的运用,并被冠之以新的名称,比较常见的有“协同管理(co-management)、分散化管理(decentralize management)或者网络式管理”等。然而,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章,如果不能吸收和反映最新的文献未免是一种缺憾。因此,本文选择了最近几年有代表性的文献予以简要介绍。
哈勒(Haller,2009)[21]研究了赞比亚的泛滥平原“喀辅埃低地(Kafue Flats)”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的历史变迁。在殖民统治以前,喀辅埃低地居民将当地的牧场、野生动植物以及渔业资源等置于公共产权的管理模式之下,并且较好地维持了这些自然资源的长期存续。然而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公共产权模式下的社区自主治理制度被强行打破了,并被代之以政府管理。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外来移民势力的干扰,以及政府管理的信息难题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的政令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最终的结果是,当地的自然资源要么落入势力强大的帮派之手,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要么变成了开放式(open-access)的CPR。最终导致了资源枯竭的“公地悲剧”。
哈丁非常肯定地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公共产权资源会逐渐变成私有产权;否则将会导致共同毁灭的悲剧[5]。有趣的是,拉赫曼(Rahman,2009)[22]找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他研究了巴基斯坦北部美而浦(Mehlp)山谷地区越冬饲料资源(栓翅芹)利用模式的历史变迁。在几十年前,在当地人烟稀少时,饲料资源的产权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产权的个人私有制反而自然地(automatically)过渡成了家族共同所有制;而且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当地人很好地解决了饲料资源的CPR问题,并没有像哈丁所设想的那样走向毁灭。
孟加拉采用国家配额的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比如孟加拉国对公共渔场资源实行配额制,最终导致渔业资源向有政治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聚集,而广大没有政治影响力的穷人则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孟加拉国于1995年实行了政府与地方社区“协同管理(Co-management)”的模式。卡恩等(Khan et al,2012)[23]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孟加拉国实行协同管理政策对渔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expenditure)造成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允许穷人参与的协同管理模式对当地渔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存在着显著和积极的影响。
普拉丹与帕特拉(Pradhan & Patra,2013)[24]研究了公共池塘资源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异质性与CPR治理制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大、社会等级(caste status)越悬殊,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越差,与社会地位相比,经济地位的这种影响更加突出。
巴兰德与蒲拉图(Baland & Platteau,2014)[25]指出,在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不应该坚持将政府和社区对立起来的“二分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介入和社区自主治理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当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组织不够稳固,或者其内部存在严重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当面临外部利益集团的非法侵占时,借助政府的力量,实行某种政府与社区“协同管理”的模式,也许不失为解决地区性CPR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政府官员应当重视培育社区机构的组织和自治能力。
五、总结性评论
(一)交易费用最小化应当成为方案选择的重要标准
在解决CPR问题时,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从一开始的“利维坦”或“私有化”作为唯一方案,到逐渐接受自主组织与治理作为替代性解决方案,目前理论界形成了以上三种方案并存的格局。在具体实践中,这三种方案,尤其是自主组织与治理,分别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具体实践中究竟应当选择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以及选择某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具体形式,应当根据CPR问题的具体形式和条件才能确定。此外,具体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是以某一种形式为主,辅之以其他形式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比如上文提到的协同管理(Co-management)模式。
由科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决定究竟选择何种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交易费用最小化。新制度经济学派内部对于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认为交易费用即为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成本。但是该标准的适用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不同解决方案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的收益相等,或者至少差别足够小。
(二)“公共产权资源”问题远未得到完全解决
时至今日,CPR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离较为满意地解决因产权的公共性带来的环境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由过度排放二氧化硫导致的酸雨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史蒂文斯(Stavins,2011)[26]认为,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乃是终极“公地悲剧”。
造成许多CPR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理论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对于“利维坦”方案而言,如何解决政府自身的缺陷,比如独裁、腐败、寻租和特殊利益集团等,带来“政府失灵”的“二阶困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哈丁(1968)认为,实行宪政就能解决政府失灵的二阶困境,但是事实表明他的观点也许太过乐观了。。对于私有化方案而言,当市场手段运用于CPR问题时,很多情况下又难以避免“市场失灵”问题,况且某些CPR本身具有整体性,很难被分割,若强行分割,代价过于高昂,且容易导致其原有价值发生退变,造成“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27]问题。对于前两种方案的替代性方案——“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其对应的也仅限于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而不是全部的CPR问题。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具体是指“其位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50到15000人之间,这些人的经济收益极大地依赖着公共池塘资源”的特定情形。退一步讲,即使仅考虑小型公共池塘资源问题,自主组织与治理方案也可能是脆弱,甚至是失败的。
其次是现实的异常复杂性。由CPR导致的问题可以少到仅涉及几个人,多则可以涉及世界所有居民(如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而且,由于人口、生物资源、污染物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贫富悬殊等现实因素,都进一步加大了解决大范围CPR问题的难度。因此,CPR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实践的继续推进和理论的继续探索。
(三)“无为”甚至“不治”未必就不可取
许多CPR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有些则不然。对于部分悬而未决的CPR问题,它们之所以没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是因为即使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解决问题本身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其高昂的代价。对于这类CPR问题,人们宁可选择“无所作为”,而不是像哈丁所认为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毫无作为”[5]。
对于解决成本过高,其潜在收益小于解决成本的CPR问题,人们选择“无为”,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行为。当然,解决CPR问题的收益和成本也是随时间和具体的条件而改变的,当技术足够进步,或者这种CPR问题变得足够严重时,选择“有所作为”主动出击,就逐渐变成了理性行为。
(四)“悲剧”未必可悲——机会成本不容忽视
在整理CPR理论的最新文献时,我们发现以往的经济学家在提及CPR问题时往往存在过度悲观的倾向。甚至每当提及CPR时,就先入为主地将其视为“悲剧”。然而实际上,即便传统上许多经济学家“公认”的“悲剧”也并不一定就是悲剧。
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荣誉经济学教授希尔(Hill,2014)[28]撰文指出,就像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样,被经济学教材作为公地悲剧经典案例的美国野牛(bison)数量锐减问题,并不是真正的悲剧。在我们讨论资源的过度利用时,绝对不应该忽视机会成本。特定资源的迅速耗散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地悲剧”,而是要根据这种资源的其他替代性用途而定。
他认为,野牛的主要用途在于为人类提供牛肉和牛皮等。而牲畜(cattle)在这一作用方面具备比野牛显著的竞争优势。虽然19世纪,美国西部地区草原上的野牛数量锐减,但是草原的利用本身是有机会成本的。此外,野牛自身具有很强的组织性,但是极难被驯服。即使从小牛犊(calf)的时期开始饲养,其野性也难以消除,有许多野牛驯养师甚至被其杀死。这就使得大规模饲养野牛的成本极其高昂,而且必须当场宰杀,否则其肉味的新鲜度会大大降低,即使有了冷柜技术,但这种物流成本也是很高的。希尔指出,在19世纪,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被狩猎者带回家的野牛仅占被杀死野牛总数的0.7%~1.7%,绝大部分野牛在被杀死剥皮之后被弃尸荒野任其腐烂。
即使考虑到野牛物种本身以及供人类观赏及研究的价值,大量野牛的消失也不是一种悲剧。因为随着野牛数量的锐减,单只野牛的边际价值大大上升,虽然饲养野牛的成本很高,但是圈出一片草场,建成特色养殖场或者自然公园仍然变得有利可图了。希尔认为即使没有政府的参与,市场的自发作用也能很好地解决野牛物种的延续和野牛于人类的观赏及研究问题。
因此,人们在考察CPR问题时,不能忽视机会成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赞同公地悲剧。
[1] GORDON H 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62 (2): 124-142.
[2] CRUTCHFIELD J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and factor allocation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canadienned’ Economique et de Science politique, 1956, 22 (3): 292-300.
[3] HUXLEY T H. The herring [M]. London: Nature, 1881.
[4] MACLNTOSH W C. Resources of the Sea [M]. 1899.
[5]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1968(162): 1243-1248.
[6] BATESON G, et al. Weakland [J]. Behavioral Science, 1956(1): 251.
[7]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M].陈郁,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8] WADE R. The management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collective ac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privatizatio n or state regulation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7(11): 95-106.
[9] OPHULS W. “Leviathan or Oblivion”,in Toward a steady state economy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3.
[10] HARDIN G. Poli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eserving our common heritage In wildlife and America [M].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78.
[11] HEILBRONER R L.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M]. New York: Norton, 1974.
[12] EHRENFIELD D W. Conserving life on ear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 DEMSETZ H.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2 (2): 347-379.
[14] CHEUNG S N.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13): 49-70.
[15] JOHNSON O E. Economic analysis,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land tenure system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2(15): 259-276.
[16] SMITH R. Resolv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crea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wildlife[J]. CATO Journal, 1981(1): 439-468.
[17] WELCH W P.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full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s: the cases of pollution and fisheries [J]. Political Sciences, 1983(16): 165-80.
[18] MCKEAN M A.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ommon lands(Iriaichi)in Japan [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19] MASS A, Anderson R L. The Desert Shall Rejoice: conflict,growth and justice in Arid Environments. Malabar [M]. Cambridge: MIT Press,1978.
[20] BLOMQUIST W. Getting out of the commons trap: variables, process, and results in Four Groundwater Basins [Z].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21] CHABWELA H T, Managing common pool resources in the Kafue Flats, Zambia: from common property to open access and privatization [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09, 26 (4): 555-567.
[22] RAHMAN F. The use of communal fodder resources in Mehlp Valley, North Pakistan [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09(6): 380-393.
[23] KHAN M A, et al. The impact of co-management on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mmon property fishery resource management in Bangladesh[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2(65): 67-78.
[24] PRADHAN A K, Patra R. Heterogeneity, collective action and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in common property forest resources: case study from the Indian state Odisha [J]. Environ Dev Sustain, 2013(15): 979-997.
[25] BALAND J M, Platteau J P. Co-management as a new approach to regulation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 STAVINS R N.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 still unsettled after 100 year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101 (1): 81-108.
[27] HELLER M A.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J]. Harvard Law Review, 1998, 111 (3): 621-688.
[28] HILL P J. Are all commons tragedies? the case of Bi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 The Independent Review, 2014, 18 (4): 485-502.
(责任编辑:魏小奋)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PR-Governance-Theory and Its Latest Achievements
YANG Xiaowei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In 1954, Gordon first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CPR, and made a clear demonstration by modelling, which served as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in this field. Hardin’s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 of academic study on the issue of CPR. In the earlier times people advocated either by “leviathan”, or privatization to solve problems caused by CPR. Due to the great work of Ostrom et al., community autonomy, as a factual alternative solution method, has been recognized. Rahman et al., suggested that in certa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commons will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ragedy, and common lands have some advantages that private lands cannot match. Hill’s study of “American buffalo” found that even economists acknowledge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s not necessarily a real one.
CPR; tragedy of the commons; privatization; leviathan; community autonomy
2014-10-18
阳晓伟(198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公共资源、制度与经济发展。
F062.6
A
1008-2700(2015)01-0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