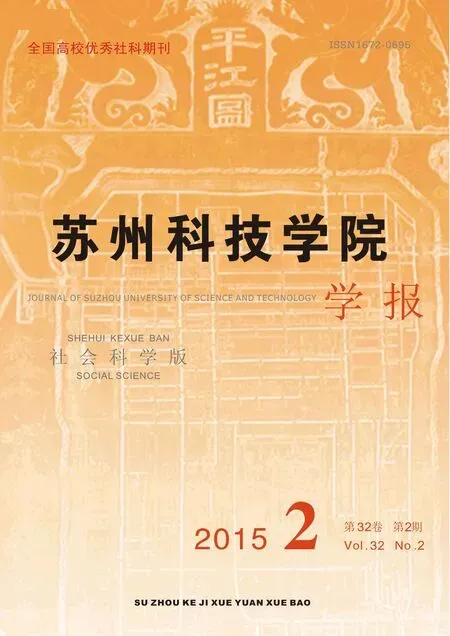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沈 潜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沈 潜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翁同龢;江南社会;传统士绅;文化交往
近代著名政治家、文化艺术家翁同龢(1830—1904)的一生,与江南区域社会有过前后三个不同时段的因缘,包括早年故乡常熟求学、继以中年省亲守墓以及晚年开缺回籍。其间,1862—1872年的十年,翁同龢遭遇了父亲翁心存、三兄翁同书*翁同书,翁咸封第三孙,翁心存长子(行伯又行三),故称三兄。翁同爵,咸封第五孙,翁心存三子(行季又行五),故称五兄。和母亲相继离世的一系列家庭变故。父亲、三兄去世后,由于当时南方太平军战事没有结束,灵柩不能护送回乡。妻子汤松1858年去世后,同样因战乱一直未能归葬入土。1868年,随着南方太平军和北方捻军战火的熄灭,京杭大运河恢复开通。当年9月,翁同龢就回籍葬亲事宜奏请,旨令准假三个月。1872年2月母亲许氏病逝,时任同治帝师的翁同龢经奏准,于当年5月与五兄翁同爵等家眷沿运河扶柩南下,再度踏上故土,将父母合葬,此后在籍丁忧。至1874年8月丁忧服阕,启程回京。
应该说,翁同龢藉以先后几次扶柩南归,就此贴近了长年寄寓京城的他与乡音乡情的距离。除了1868年、1877年来去匆迫的二次回籍,难有余暇赋闲。撷取1872年丁忧服丧的乡居生活,翁同龢有了从容回旋的余地,得以重温江南风情、开拓文化视野。长期以来,学界有关翁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视野大多被纳入政治史的论域,以日常生活史为视角的考量则较少。笔者基于《翁同龢日记》的文本梳理,以翁同龢在籍丁忧的1872—1874年为视界,力求再现当时生动的文化交往场景,进而窥探翁同龢与江南区域社会的文化互动。
一
据1872—1874年翁氏日记可知,在籍丁忧期间,翁同龢除了相度墓地、依墓设奠、为慈亲服丧尽孝、诵经念佛并抄经缅怀、读书校诗外,大体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一是整治家族形象。
宋明以来,祠堂、义田和族谱一直是传统世家望族“敬宗收族”的普遍模式。作为常熟著名的文化世家,翁氏家族始终把建祠堂、设义田、修族谱视作家族生活自治保障的基本要务。翁氏祠堂建于1607年,至1860年兵乱后焚毁。1872年归里后不久,翁同龢与五兄将“榛荆塞路,颓垣尚在”的石梅翁氏祠堂加以重建。接着,在虞山鹁鸽峰前建翁氏丙舍,作为祭拜先人墓庐之所。为了赈济族内贫困,两年后又与五兄在常熟阜成门外开设翁氏义庄,置田1 000多亩,还在先祖遗产中拨出200亩作祭田之用。1874年4月19日记:“五兄定议遵先公遗命,于遗产中拨二百亩列为石梅祠、顶山、鸽峰祭田,余田悉归先兄文勤一房管业,深合小子夙昔之志矣。”*参见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二卷,北京:中西书局2012年版。以下凡注明日记具体年、月、日之处,不再一一标识。南行前夕,翁同龢续撰完成了三兄翁同书的《巽斋自订年谱》,又将三兄西行期间与自己的往来家书合编一卷。归里后,他为先父编校了遗集,还写了《先母事略》、《先母行述》、《兄子曾文述》、《适俞氏姊墓志》、《亡妻汤夫人墓志铭》、《清故优贡生诏举孝廉方正俞君墓表》等篇章。为进一步纂补《海虞翁氏族谱》,他又先后走访了先世曾经生活过的翁家湾、黄泥桥、卫家浜、洞泾桥等村落,寻访族中后裔,重绘家谱支系图。现存《海虞翁氏族谱》一册,系翁心存编订,1874年翁同龢重修完成,主要介绍了世系族员姓名、行第、字号、生卒、科名、仕宦、姻娅等情况。
从编订先父文集到缕述族中眷属事略,从建丙舍、置祠堂到设义田、修族谱,翁同龢此次南归的忙碌,无疑对翁氏家族文献、家族形象作了一次系统整治。如他在1874年4月所写《族谱后序》中说:
先公事君则忠,事亲则孝,身居宰辅,刻苦甚于儒生。尝曰:“一世显宦,必至三世僚幕,盖世家子弟,往往不能安贫,不安贫则亟营微禄以自效,甚则走四方谋衣食以客游为事,当此之时,即欲求为农夫布衣之士而不可得,乌在其能自立乎?夫富贵不足保,而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故谨著先训以示子孙,以告我族之人,俾世世永以为式。[1]
以编族谱、立族约、建义庄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体现了翁氏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的家教,重视对子孙后代德行善举的教育和培养,以期在慎终追远中加强家族认同与情感皈依,告诫子姓后代保持并弘扬世代诗书富贵之家的家族文化之延续。这些活动,不仅提高并扩大了家族的地方影响力,确保了家族的自治保障,也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出游踏访山水。
乡居期间,翁同龢经常凭吊石梅翁氏祠堂或兴福、顶山祖坟(翁颖封、翁咸封等墓地),至于园林幽情、湖光山色、烟雨楼台、摩崖石刻、幽洞飞瀑的虞山胜景,更有就近驻足的处处身影。除了饱览虞山尚湖风景之外,日记载录了他不时的出行远游。
1873年2月下旬,翁同龢因年前去世的岳父汤修灵柩安葬事宜,有浙江萧山之行。2月24日晚泊苏州阊门,饮茶市楼,随后移舟山塘街,入龙寿山房看寿圣寺僧善继刺指血书《华严经》;过胥门至木渎天平山下,祭拜范仲淹祠堂;又循穹窿山西行,至司徒庙观赏“清、奇、古、怪”的千年古柏。3月3日抵达萧山,瞻拜了岳祖父汤金钊墓。之后与舅子汤伯述坐乌篷船前往绍兴,参观了兰亭旧址(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故居)及禹王庙。到杭州后泛舟西湖,又移舟嘉兴南湖,夜访烟雨楼。三月中旬过松江,初到上海,拜晤上海道台沈仲复,“听谈外国事”[2]955,1001。留住数日,不仅游览了黄浦江畔风帆如织、洋楼如云的“夷场”景观,还租马车闲游了徐家汇法国花园。翁氏3月16日日记载:“登岸,遍游黄浦江马头,殊形怛制,书不胜书。此吾君亲之仇,小人乃肆然过之,以为戏耳。临流痛愤,至于失声!”3月17日,“夷场起大东门,历小东门、新北门、旧北门止,夷楼如云,光怪夺目”。18日,“由马路西行,十八里至徐家围法国花园闲游,有四面厅,卖辣水,每瓶一元。结树为亭,中设座,云可避暑。疾驰归,其行如风”。19日,“晨诣黄浦江边,风帆如织,始见轮船出入,有小者才一叶,中有一轮,其行亦驶。饮茶市楼,颇旷心目”。虽说此行走马观花,且不无内心郁愤,但翁同龢对开埠通商30多年的上海有了初步的感观。1874年早春,翁同龢又偕五兄、庞钟璐、赵宗建等作苏州邓尉探梅之行,一路足登木渎天平、灵岩山,凭吊了范仲淹、韩世忠墓;过光福镇香雪海赏梅,又至司徒庙观赏古柏;临近太湖之滨,登石壁寺万峰台,“坐揽湖中诸山,若凫鹥著水”;由光福移舟,“雨中看山,濛濛如画”[2]1058。归途中,顺道经过三十年前一度避难的蒋氏丙舍,满眼石桥半圮、枝髠树秃的旧园,顿生物是人非的兴叹。
翁同龢重返故里,或登临吟咏,或寻古探幽,或拜亲访友。所到之处,均在视域上、心灵里、情感中温润着对江南社会的风情记忆和文化品味。
三是文物古籍鉴藏。
翁同龢爱古籍、爱书画、爱碑帖,在书画审美的精神境界中摆脱世俗烦恼,秉持文化品位,成为他一生的坚守与追求。1872年的乡居生活,为他的文物收藏提供了不少机会。稍有空暇,他就和好友步访古玩、逛书肆;更有随时与友人观赏与鉴别各自藏品的活动。
以寻访书肆为例。1872年8月31日,“偕儒钦、湘渔步入书肆,无所见”。9月10日,“与儒钦步衢术中,入书肆,无可观”。1873年7月28日,“至书肆闲看,无所有也”。9月11日,“至北市心骨董家,无所见”。9月29日舟泊苏州,在玄妙观前世经堂书肆见得朱竹垞旧藏《长安志》等抄本数种;在绿润堂书肆见有宋本《新唐书》、《通鉴》等佳品。10月1日,过玄妙观,闻绿润堂有宋本《白孔六帖》,书肆不肯见示。11月20日,“访儒卿,步至学福堂书坊,检出吾邑人著作数种,内抄本冯已苍《怀旧集》一册甚好”。11月28日,访李升兰,借得《海虞文苑》、《苏许公集》。以书画、金石鉴赏为例。1872年8月31日,随五兄、吴鸿伦前往姚福堃家观赏书画,“柯九思墨竹、王麓台仿子久、王尊古、王耕烟各轴皆佳” 。9月19日,购得旧拓《校官碑》手装之,又得百年前拓本《史晨奏铭》。1873年1月10日,见王蓉州所藏褚《圣教序碑》,为之惆怅,盖所收藏零落尽矣。又从曾伯伟处借得从未见过的家抄《虞邑杂记》。3月17日,在上海醉六堂书坊见有明拓本《皇甫碑》、《道因碑》,议价未成。次日再观《皇甫碑》,议价仍未成。4月24日,应李升兰之邀往旧山楼赴宴,见吴江沈叔平所携恽南田山水册等书画佳品。8月16日,应庞昆圃之请品赏王石谷摩古十二开画册;又见临钱谦益评选《归震川集》本。8月18日,赵宗建以吴江人费宝康《秋灯课读图》、《笠泽渔隐图》两图属题。1874年3月14日,拜访李升兰,得《景君铭》旧本。4月7日,题庞昆圃所藏石谷《七树图》卷。
此间,翁同龢先后觅得《校官碑》、《史晨奏铭》、古玉玦、玉印、玉鱼等藏品。离乡返京途中又购得汉铎、北监板《陈书》4册、旧玉碎件3件、明拓《怀仁集圣教序》。这一执着的文化情怀,丰富了自己的收藏阅历。
四是文化雅集交流。
在此期间,翁同龢更多的是与家乡在籍官绅友人之间充满文化内涵的雅集交流。这些人中,既有少小好友赵宗德(价人)、赵宗建(次侯)、吴鸿纶(儒卿)、杨泗孙(咏春)、庞钟璐(宝生)、姚福奎、张瑛(仁卿)、宗廷辅(月锄),还有庞钟琳(昆圃)、俞钟銮(金门)、俞钟燮(调卿)、李芝绶(升兰)、曾观文(伯伟)、季念诒(君梅)、曾之撰(君表)、曾金章(印若)、徐藻(月槎)、庞钟瑚(云槎)、钱禄泰(绥卿)、钱福棠(仲谦)、吴子儁(冠英),以及堂兄翁同祜、药龛和尚等等。
其间,有看画、访书之约。1873年10月12日,“晨偕兄泛舟出南门至范家市,赴钱仲谦看画之约,至则君梅、升兰、价人先至,同看王廉州画屏十二,虽精刻,疑有掺杂。并唐某荷花。恽寿平、王烟客、廉州题,为石谷作”。当年9月18日,翁同龢应庞钟璐约请赴常熟古里(时称罟里)瞿氏敦裕堂(铁琴铜剑楼)观书,次日同舟前往,拜访了楼主瞿秉渊(镜之)、秉清(濬之)兄弟,见到所藏宋椠诸本,“如游群玉,目不给览矣”。还与瞿氏兄弟戏言:“假我二十年日力,当老于君家书库中矣。”[3]294次年早春又独自造访了瞿氏兄弟,见藏宋刻本《老子》、《传灯录》及汉碑50余种。敦裕堂由瞿绍基建于乾隆末年,与聊城杨氏海源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并称清末四大私家藏书楼。传至第三代秉渊、秉清兄弟,承继世业,旁搜博采,所藏多宋元刻本精品。1860—1863年间,为避免家藏古籍遭战乱毁损,兄弟俩不得不将藏书四处分藏,前后播迁七次之多。1873年12月29日有《题瞿濬之〈虹月归来图〉记》写道:“私窃叹羡君家兄弟好古而不骛名,大异于世俗浮之习,又自伤薄祜,违父兄之训,中年废学,头发尽白,虽欲强自振厉而末由也。”[3]294题记表达了对瞿氏苦辛藏书的崇敬之情。此外有游园赏菊、看梅之招。1872年8月30日,“从五兄泛舟访晤姚湘渔、王赞钦、庞云槎、钱仲谦,入其园林,归时午初”。1873年11月5日,“从兄偕宝生、君梅、叔文同往湖巢姚筱冈家看菊,即去年所到者也,至则万花绚烂,长者七八尺,多至千余种,二万棵。洵壮观矣。主人饷客甚丰,适次侯、魏葆卿并徐月槎、宗香谷、钱玉方、俞绶卿等十余人杂坐花中,壶觞大举”。11月6日,“夜赴陆叔文招看菊,君梅、价人、君表、申兰及余兄弟”。1874年3月14日,“偕申兰、君梅、吴冠英、张雨生同舟赴次侯饯梅之约,兄与伯伟亦往”。还有冬至消寒之会,1874年2月21日,“午集庞昆圃处,消寒局也”。2月23日,“逆风篙行,午后达报慈桥,是日次侯消寒之约,梅花已放六七,而探梅之约尚迟迟也”。2月26日,“赴季君梅消寒之集”。3月13日,“夜赴伯伟消寒之集”。
较之一般人的附庸风雅之举,这些充满文化情趣的文人雅集方式,无不折射了相互吸纳提升的底蕴。翁同龢后来之所以能形成不拘一格、碑帖兼融的书学思想和书法艺术,成为晚清书坛的著名书法家,恰与这些旨在文化切磋的聚会密不可分。
二
在翁同龢丁忧乡居的两年间,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绅友好,处处洋溢了文化的情趣,兼有相知相勉的至亲温馨。当时,城中的彩衣堂、城北的旧山楼,以及虞山北麓的三峰寺,堪称常熟一地文化吐纳、聚合、交流的重要空间,就此形成了一个以翁氏为中心的文化交往圈。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赵宗建的旧山楼。
旧山楼位于虞山北门报慈桥畔。乾隆年间,赵氏曾祖赵同仁购得明代吴讷别业“思庵郊居”和魏浣初“乐宾堂”的两处遗址建宅;祖父赵元恺经义典籍,名噪一时,购有明代瞿式耜的“东皋草堂”;父亲赵奎昌(曼华)于道光年间在宅东辟地建“半亩园”。重风仪、善诗文,“三世皆以义侠闻”[4],门庭相传,名闻乡里,邑称报慈里赵家。赵宗建,字次侯,号次公,又号非昔居士,咸丰时官至太常寺博士,因无心仕途,罢归不出。时值江南战事纷乱,书画典籍散佚严重,他广购博收,所藏日益繁富。同治年间,赵宗建和兄长赵宗德将旧宅重加修茸,又新建楼台堂屋,总名称宝慈新居。位于园北最高处建有三楹“旧山楼”,藏有各种书籍、书画、碑帖数万卷。楼前白松红豆,楼后小山窈窕,园内有总宜山房、古椿书屋、拜诗龛、过酒台、非昔轩等景观,并植梅数百株,暗香疏影,池台竹石,极具园林幽胜。邑人张瑛有文记载:“赵君次侯,旧居北山之麓,因其旧而新之,名其楼曰旧山楼。赵氏自前明文毅公直谏以气节世其家,次侯食旧德,诵清芬,诗酒自放,徜徉山水,岿然一楼,与名贤遗迹并传。”[5]
翁同龢和赵氏兄弟的关系,前有父亲翁心存赵家坐馆课读的先世交情,继为游文书院学习的年少同窗,后有在京时经常切磋鉴藏、出入琉璃厂搜寻古本秘籍的同道志趣。如今居忧还乡,自有更加密切的过从厚谊。在他看来,宗德工于画,宗建精鉴赏,两兄弟不仅好客善饮,更有家富珍藏,通经博闻,又轻财好施,志节可感,风仪可重,因而相知最深,被他视为“吾邑魁奇磊落之士,亦余东阡北陌往来朋从之故人也”[4]。个中情谊,如他当时撰文所言:“故登赵氏之堂,盎然有古趣,虽偏僻如余者,每旬日辄思过二赵语也”。
梳理1872—1873年的翁氏日记,以旧山楼赵氏兄弟为切入点,处处留下了彼此往来的踪影。1872年8月21日,“谢客,晤赵价人、次侯兄弟,即在彼饭,季君梅亦至,观其字画,杂花满庭,布置曲折”。11月3日,“晨从五兄泛舟南门,拜城外诸客,遂至报慈桥,晤赵次侯,即留饭”。翁同龢每次往访旧山楼,其中不乏顺道小坐或便饭小叙,更少不了与赵宗建品鉴书画的记录。据翁氏日记记载,以旧山楼为中心,其中有几次颇具声色的游园聚会:
1873年4月4日,诣赵价人昆弟,桃花正开,风景秀丽,饮于旧山楼,李升兰、季君梅、庞昆圃、夏范卿价人亲家。皆在座。日落时徘徊花下,抵家曛黑矣。见次侯所收钱罄台手抄《吴郡文苑续》七本,不全,共四十一卷。明人书《杜东原集》,琼,诗不足观。董文敏画扇。
1873年4月24日,赴李升兰招于报慈桥赵氏,坐有吴江沈叔平、其兄己亥孝廉,能古文。屈达泉、曾伯伟。观沈君所携画册,恽山水册,佳。
1873年10月14日,晨从兄泛舟报慈桥,应赵价人昆仲之招,庞昆圃、宝生、季君梅、曾伯文皆在。看石谷画帖十二幅、廉州《虞山十景》册。饮半乘兴坐竹兜游三峰,坐良久,复诣赵氏晚饭,同散,抵家曛黑。
1874年4月29日,晨从兄泛舟北郭。是日宝生尚书移樽赵氏为别,昆圃、君梅、赵氏昆弟,主客七人,盆兰正盛,牡丹亦开,饭罢久坐。
同道知己携壶到访,待楼主焚一炷檀香,烹一盏新茗,宾主毕凑,闲庭有香雪成海,楼外有山色清远,眼前有金石图书展卷共赏,席间茶去酒来,留饮放谈,觥筹交错,俯仰畅怀,好一派恍如隔世的场景。直至十余年后假归省墓,惊悉杨泗孙已离世几天,翁同龢回想当年,不免吟诗咏叹:“呜呼我与君,交情同漆黐。我气盛如云,君虑密于丝。持此两相济,亦用相箴规。君为文章伯,出入凤凰池。至今禁扁字,照耀三殿楣”[4]152。与赵氏兄弟夜宿共话,还有“旧山楼下萧萧雨,七十年前古桂香。相与披图溯遗迹,更无人识乐宾堂”[4]153的喟叹。
丁忧期间,翁同龢既赴他人之请,也不乏在彩衣堂做东之约。彩衣堂原名“森桂堂”,为明代成化、弘治间常熟桑家所建,后数易其主。1833年翁心存从仲氏兄弟手里买下后扩建修缮,将堂名改为“彩衣堂”,作为孝养母亲的场所。父亲乡居期间,彩衣堂东侧辟有“知止斋”的藏书楼,楼上藏书,楼下会见宾朋,吟诗赏画,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生活。1872年7月27日记:“仲氏比邻之屋今归余家,五兄积廉俸所购也,本意奉亲,今乃挈余同居。五兄住柏古轩,余住新厅。”9月3日记:“是日巳刻挈安孙移居新茸后院之屋,明窗净几,上栋下宇,俨然华屋矣,是皆兄爱弟之诚,一一措置,然已太康矣。”可见,1872年丁忧还乡,翁同龢就入住于彩衣堂。因此,当时的彩衣堂显然成了宾朋数集、宴游忘返的主要场所。1874年3月22日,“邀吴冠英儁来写真,……价人、君梅先后来。夜招杨咏春、书成、庞氏昆仲、吴儒卿及冠英饮,冠英亦讲金石,而咏春深于籀古,剧谈甚快”。4月23日,“晚招咏春、书城、昆圃、宝生、申兰、君梅、次侯饮,为咏春洗尘也”。
此外,虞山北麓的三峰寺,也是当时翁同龢多所参访的场所。翁同龢与三峰寺的结缘,缘于三峰主持药龛和尚。药龛(1825—1909),常熟人,少小投三峰清凉寺披剃,为三峰名僧硕揆禅师九代法嗣,精研大乘,旁及子史百家,工诗善画,尤喜收藏,戒行著称于江南。药龛早年曾从翁同龢姐夫俞荔峰习诗,与邑中名士过从密切。追溯两人交往,初识于翁同龢请假南归的1868年,当时他以杜诗意书赠“世尊尘埃,龙象无力;斯人空谷,黄绮同游”联语一幅。翁同龢乡居日记里,不时有偕友人往访三峰,留饭僧寺、书画共赏的记录。
1872年9月5日,晨出北门,呼肩舆入三峰寺,寻药龛上人不遇,归过兴福寺,摩挲唐石。访次侯,坐良久,饭后步归,坐三峰松滨堂,东望苍莽,与谛上人语。
1872年9月17日,从五兄挈安、寿两出北郭,乘兜子入三峰寺,访药龛和尚,即食于彼,风帆沙鸟,一扩傫然者之心目。过兴福,归途过赵价人兄弟。
1873年4月30日,薄暮五兄归,余与次侯、药公同步至中峰寺,与病僧谈,西寻龙殿,摩挲宋记,遂宿三峰,人定后,钟鼓声涤人烦襟。是日看药公所藏书画。
1873年9月27日,兄约庞氏昆季,宝生有事不来。曾伯伟同行,出北门,孙祠堂小坐候齐,同至赵宅,并次侯兄弟,先至兴福茶话片时,次至三峰,丈室落成矣。
旧山楼、彩衣堂、三峰寺依偎古城常熟,虞山历史地形成了“十里青山半入城”的格局,三者之间相距路途不远。居住空间的邻近,便于一天之内相互走动,通过喝茶、聚饮、游园、逛书肆等形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样的交往更有日常化的意义。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不同形式的文化场域,无不成为翁同龢舒展浓郁文化情怀的重要空间。
三
由上述可见,自翁同龢丁母忧回籍后,在他的身边集聚了一个由乡邦文人绅士形成的人际网络,于游园聚会中谈艺论道、赏碑品帖,彼此联结成一个同气相求的交往圈。据翁氏丁忧日记所涉交往名录,过从最为密切的依次为赵宗建、吴鸿伦(儒卿)、赵宗德、曾观文、季念诒、俞钟燮、庞钟璐、庞钟琳、俞钟銮、李芝绶、俞外甥、钱禄泰、吴雅庭、曾之撰、曾金章、钱玉舫、徐藻、钱福棠、杨书城、杨鹤峰、俞寿卿、王赞钦、张瑛、庞钟瑚、庞伯深、吴子儁等人。
论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士绅,活动的空间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他们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此之外,有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其共同体的交往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6]3循此分析后不难发现,身处江南古城的翁同龢正是在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的基础之上,聚合并构建着自身的知识与人际网络。
在传统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宗族血缘关系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系和精神寄托,成为维持家族稳定的基础,也是家族发展壮大的前提。从血缘角度考量,翁氏家族分支众多,族员之间自成错杂交织的利益网络,这为翁同龢贯穿一生的人际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丁忧返乡期间,翁同龢与至亲族人之间多有日常交往,除朝夕相处的五兄翁同爵外,还有翁曾源(仲渊)、翁曾荣(鹿卿)、翁曾纯(吉卿)、翁曾禧(士吉)、翁曾绍(士复)、翁曾焕(士章)等侄辈,以及翁斌孙(寿孙)、翁安孙、翁奎孙等侄孙辈。由耕读起家的翁氏,经年累月中不以追求权势、财富为目的,而以读书力学、著书立说为职志,因此家族在整体上凸显了鲜明的文化型特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链,族员之间的频频交往,因此充满文化气息和志趣所向。由血缘关系自然联结的空间网络,使翁同龢的乡居守孝生活始终有着稳定的文化交往对象。
还要看到,明清二代,常熟出现了众多家学渊源深厚、文化系统承续,并为地方所认同的世家大族。民间谚语所云“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望族。他们或以诗书传家,或以藏书为业,或以绘事著称,甚至多重复合,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凸显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堪称瞩目的区域文化风尚。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文化品位、志向爱好,更易使这些世家族人集聚一起,开展相对契合的日常文化活动。留意翁同龢在此期间的交往行迹,多半与这些文化家族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究其缘由,其中还不乏文化世家之间缔结的姻亲之助力。姻缘是亲缘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族成员与另一家族成员结成配偶关系,由姻亲引出的裙带关系,让亲家之间联系更为紧密,家族的各自交往空间因此扩大。作为当时古城首屈一指的家族,翁氏族人与曾氏、杨氏、庞氏、俞氏等族人多有姻缘之亲。以翁同龢与俞钟銮交往为例。俞钟銮好诗文,通医学,清末书画家。翁、俞二人年龄相差20多岁,因一桩婚姻结成舅、甥关系。俞钟銮之父俞大文娶翁同龢大姐寿珠为妻,此后翁、俞两家关系亲密。俞钟銮虽非寿珠亲生,但在辈分上仍是翁同龢外甥。应该说,翁氏与其他著姓世家的姻缘关系,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翁同龢的文化交往圈,助成其文化交往空间的拓展与延伸。
与血缘相伴随的地缘,也是影响社会关系的内在要素。游子归里,乡谊绵绵,同乡间的交往有着相互吸引的亲切感与认同感。居乡士绅相近的志趣爱好,以及对地方事业的热心,更易促成文化交往圈的形成。
乡绅是传统社会的地方精英,他们以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公益精神服务桑梓,兼济与独善中获得地方社会的尊重,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明清以来,常熟人文荟萃,才人辈出,生活着一批充满社会公益精神、富有文化责任担当意识,且工诗善文、以金石书画怡情养性的乡绅。翁同龢之文化交谊空间,当与古城里巷众多乡绅的志趣追求不无关系。志书记载,李芝绶,道光举人。一再赴礼部试,同游多海内名士,居乡又与古里瞿氏友善,精于鉴别古籍,所藏富汇,编为《静补斋书目》,掌教邑中游文书院,成材甚众。徐藻,例授詹事府主簿,有才干。少时协助从父建凝善堂,收容饥寒流浪者。“邑中有筑城、浚河之举,捐赀为倡。水灾办振,殚心筹划,公正无私。”[7]1086钱福棠,国子生,例授同知。少小失怙,后弃书经商,性格伉爽,见义勇为。“邑中有荒灾振恤之事,每佐当事擘划。余如开浚白茆、福山塘、亦与其事。”[7]1162太平军攻占常熟时,随督办江南团练的庞钟璐集资募勇。战后悉心筹建文庙及常平仓,又捐资并劝绅商建清节堂,“一时苦节不能自存者,咸得所焉”[7]1162。暇则辟园亭,购书画,工山水。李芝绶、徐藻、钱福棠等,都是与翁同龢多有交往的乡绅,在关乎乡学、赈灾、水利等公共事务上多有不同程度的热心参与。
除了血缘、地缘之亲之外,学缘关系同样是联结私谊网络、确认身份归属的重要纽带。翁同龢从五岁到二十岁前的人生段,是在尚文崇教的江南成长,故乡滋养并见证了他从孺子幼童到青年才俊的学步履痕。始于家族乡里,经少小读书应试、父辈提携,通过私塾、书院的求学生涯,已然逐步构成并拓展了一个关乎学缘的师友交际网络。就此间结交的友人中,赵宗建、赵宗德、吴鸿伦、杨泗孙都是翁同龢当年游文书院的同学、同年;张瑛、姚福奎、宗廷辅等皆为少小交好。吴鸿纶家住西门内致道观附近,温和孝友,弱冠有文名,有藏书楼名“壶隐园”。杨泗孙从小遍览群书,秉性笃诚,咸丰殿试一甲二名(榜眼),授编修,入值南书房,先后主持湖南、福建、山东等省乡试,又两充会试考官,官至太常寺少卿。乃兄杨沂孙,道光举人,擅书法,尤好篆籀之学,中举后官至凤阳知府。庞钟璐是当年游文书院学师庞大堃之子,道光朝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及第,先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江南团练大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张瑛,诸生,候选训导,从事江苏书局,预修《苏州府志》。历署阳湖诸县学篆。平生好援《易》为谈助,有《知退斋集》、《韩文补注》。姚福奎,咸丰举人,选授娄县教谕,迁常州府教授。归里后掌教游文书院,著《三湘书屋诗》、《潇湘渔词》、《虞山画志补编》。[7]1083,1085
依托于血缘(同宗)、地缘(同乡)、学缘(同学同道)基础上形成的私谊网络,无疑构建了翁同龢乡居生活的基本人际交往空间。借助这一私谊网络,不仅丰富了他诗文唱和、艺事切磋的日常交流,并且因彼此投合的知识谱系、道德观念、文化品味、生活志趣,互动交往也更具内在的稳固性、持久性。1898年起回籍终老,翁同龢与这些乡间友好依旧接续前缘,更添了相知相勉、嘘寒问暖的近乎亲情的关系。其中与赵宗建、吴鸿纶、药龛等更是维系了毕生的友谊。
综上所述,血缘、地缘与学缘构成了中年翁同龢文化交往空间形成的根基。笔者聚焦于1872—1874年间翁同龢在籍丁忧的文化交往,旨在说明,其以宗法血缘与地缘学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人际网络,是一个大体承袭、固守了传统的乡村士绅精英网络,这与19世纪末置身于都市语境下的士人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等多元化的公共空间建构的关系网络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借以翁同龢在这一场域的交往惯习,不难看出他内在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思想底色之特征。循此路径追寻翁同龢接陈启新的思想性格及其步幅,后人当能见出个中的一些历史端绪。
[1]翁心存.海虞翁氏族谱[O].翁同龢,翁同爵,重修.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常熟图书馆藏.
[2]翁同龢日记:第三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仲伟行,吴雍安,曾康.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翁同龢.瓶庐丛稿:卷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张瑛.知退斋稿·旧山楼记[M]//赵宗建.旧山楼书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6]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修常昭合志(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周继红)
2014-09-01
沈 潜,男,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
K25
A
1672-0695(2015)02-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