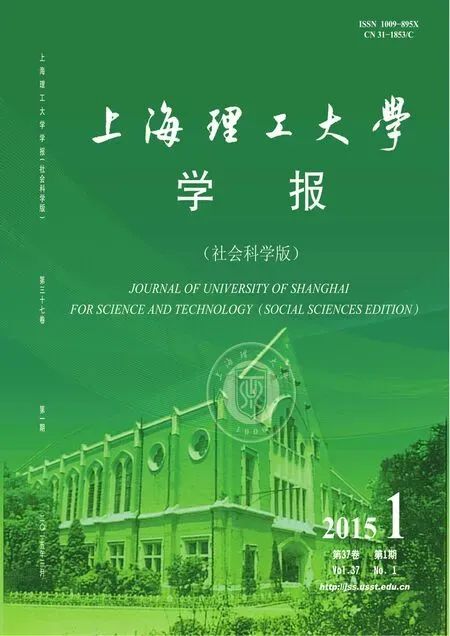浅论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体
浅论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体
周立人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围绕小说叙述视角、叙述体和它们之间的切换等展开论述。指出:许多被视为“叙述不可靠”的作品,由于读者视角的参与而弥合了其“不可靠性”;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不一定要让叙述者扮演一个诗性化的全能的角色,也可以把叙述角度严格地限制在“我”之所见所闻。这样做往往会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关键词:叙述视角;叙述体;叙述学
收稿日期:2014-04-05
作者简介:周立人(1956-),男,副教授。研究方向: 文学与文化研究。E-mail:zhoulirenpr@163.com
中图分类号:I 0文献标志码: A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1.011
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Style in NarratologyZhou Liren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style in narratlogy.Assume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reader’s perspective in many works may well be purged of “unreliable narration”and while adopting first-person narrative style can limit the narrator’s realm of sight.The limit in some cases can possibly evoke reader’s imagination and reflection.
Keywords:narrative perspective;narrative style;narratology
叙述视角,指叙述者(一般被认为是作者的代言人)在叙述故事时所确立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叙述者总是借助一定的视角来向读者展示一部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背景和事件等。小说中的“视角”问题向来是作家和批评家所关心的。自从18世纪以来,形成了许多关于“视角”的见解,散见于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如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珀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沃尔夫冈·凯瑟的《谁是小说叙事人》、瓦纳·布兹的《距离与视角:类别研究》等。
与视角相关的是所谓的“叙述体”。传统文学理论对叙述体的分类比较简单和实用,因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分类方法把叙述类型大体上分为第三人称叙述体和第一人称叙述体。当然,这两种最基本的叙述体又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它们是叙事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一、第三人称叙述体
在第三人称叙述体中,叙述者通常不卷入自己所叙述的事件之中,而是仿佛置身于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以超然物外的姿态讲述故事。这种不参与情节的叙述者,也被称作“隐含的作者”(即作家的“次我”),“他是舞台监督,是操纵傀儡之手;或者如乔伊斯所说,是位不声不响地在修剪指甲的无动于衷的上帝。……他往往比任何实在的人都更为精细,更为聪睿和敏于感受,具备更强的洞察力”[1]。
譬如,在菲尔丁的长篇小说《汤姆·琼斯》中,代表第三人称叙述体的叙述者在第一篇的第二章的开头说道:
在这个王国西部的一块通常被人称为萨默塞特郡的地方,从前居住过,或许现在仍然居住着一个名叫奥尔沃西的先生。他完全有理由被称作自然与命运的宠儿,因为自然与命运都争着要比试一番,看看谁能给他带来最多的祝福与财富。
(笔者译)
第三人称叙述体又可以分为两种叙述视角。
第一种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者像上帝一样君临一切,无所不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时间和空间中移动,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事件转向另一个事件。在叙述故事时有意渲染或隐去一些内容;在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的同时,他还拥有介入人物内心世界的特权。这个神通广大、能自由进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叙述者,还可以对他所描写的人物作一番分析与评论,而且,他的分析与评论通常被看成具有权威性,主导着读者的各种判断。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如菲尔丁、狄更斯、哈代、托尔斯泰等都喜欢采用此种叙述角度。在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介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叙述者甚至在故事中插入大量的议论,对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等极尽点评之能事。当然,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也可以是局外的、客观的。例如,《包法利夫人》的叙述者喜欢客观地描述戏剧性场景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而不作任何评判,也不介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彼得·凯里的《玫瑰》、亨利·劳森的《他母亲的伙伴》也是如此。这种客观的态度也是契诃夫所提倡的,他说:“可以为自己的小说哭泣、呻吟,可以跟自己的主人公一块儿痛苦,可是我认为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才对。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有力。”[2]
第二种是有限的视角。叙述者虽然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但只是使自己局限于故事中一个或几个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如亨利·詹姆斯喜欢将自己选定的人物看作叙述的“焦点”,让事件围绕人物的“意识中心”展开,通过它的过滤再传递给读者。后来的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弗吉妮亚、福克纳等)把这种技巧发展为意识流记叙体——这种叙述体将外部的观察同情感和思想的流变融为一体。
二、第一人称叙述体
第一人称叙述体的特点是: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即“我”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叙述者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又被自己有限的认识范围和视野所局限。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用的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叙述体:
假如你真想听这个故事,那么你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或许就是我在哪里出生,我那糟糕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的父母在生我之前都干了些什么以及所有那些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但我不想讲述这些,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笔者译)
第一人称叙述体中的“我”还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我”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如笛福的《摩尔·弗兰特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第二种“我”是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或表面上的参与者,如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中的伊斯梅尔,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第三种“我”只是以一个“偶然的目击者”的身份参与到故事的叙述中来,如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中的马洛。
另有两种常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也值得我们留意。一是“自我意识”叙述者的手法。“自我意识”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不仅自己意识到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让读者知道他在讲述着一个虚构的故事,他要读者了解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和他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这种叙述可以是严肃的,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滑稽的效果,如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香迪》。二是“不可靠”叙述者的手法。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经常使用这种独特的叙述手法。他们让叙述者表现出天真、无知或在心理上、道德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以致读者有时候无法确定作者心目中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例如,在亨利·詹姆斯的《使节》里,兰伯特·斯特雷奇对各类事件所作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这一点只有当事件临近尾声才能辨别出来。
批评家韦恩·布斯认为,个性、智力或环境上的问题都可以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就用了文盲流浪者哈克充当故事的叙述者。哈克同情黑奴吉姆的遭遇并竭尽全力帮助他寻求自由,但“良心”却“正告”他说,窝藏黑奴或帮助黑奴出逃不仅触犯美国当时的法律,而且用道德的规则来衡量是一种堕落,是要下地狱的。显然,哈克由于年龄、经历和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识破美国法律与道德虚伪且不公正的一面,但读者视角的参与往往能弥补这一缺陷,使一个智力低下的叙述者仍然成为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否则硬要将一个有头脑、有思想且对社会抱有批判态度的成年人的视角塞给哈克,反而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性。正如瓦纳·布兹所说的,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叙事者自称万恶不赦,而作者却在背后暗暗称道他的品德”[1]。
三、叙述体之间的切换
小说家在叙述故事时,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叙述体之间切换。换句话说,他们不必始终如一地使用某种叙述体。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德国著名作家郭特夫里特·凯勒,在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问世后,曾决定重写他的这部作品。他请出版商协助他收回第一版还未售出的书,然后自己亲自将它们付之一炬。他认为25年前的创作是失败的,因为里边隐藏着一个令他不安的瑕疵。他说:“你们给予我的书的荣誉是不合适的。原因在于,自传体是一种极乏诗意的形式,它排除了真正的诗的语言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而必须采用这种形式本身,恰好证明我的作品中存在一个根本的缺点。”[3]凯勒所说的“真正的诗的语言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纯洁性和客观性”即是指第三人称叙述体,而与之相反的“极乏诗意的形式”即是指第一人称叙述体(自传体)。而那个“根本的缺点”,即是他在写作品的时候没有让同一个叙述体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始终。具体地说,《绿衣亨利》(第一版)的开头和结尾所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叙述体,但中间相当大的篇幅却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体(即让亨利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由此产生了叙述者(叙述角度)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全知与客观的叙述视角,另一方面是局限于个人经验和回忆的狭隘的叙述视角。于是,在第二版中,凯勒把整个故事改成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他又怀疑自己做出的选择,担心在出于第一人称叙述的需要而放弃“讲故事的最高权力”的同时,是否同时也放弃了“诗人的最高权力”。然而,更有趣的是:当文学批评家将两个版本进行比对时,并没有发现凯勒所说的“问题”[1]。
沃尔夫冈·凯瑟指出,凯勒的困惑其实是多余的,“一位英国小说史专家指出:‘粗略地回顾一下从菲尔丁至今英国小说所走过的道路,令人瞩目的是作者的消失。’好像价值的层次被颠倒了,现代的小说家似乎认为客观的叙事人已经过时,是虚假的、反美学的程式,他们当中不止一人确实这样讲过。与此相反,叙事角度的变换,第一人称的叙述或某一人物角度的叙述却是正确的、符合美学要求的。我们知道,这个变化始于19世纪,亨利·詹姆斯首先提出要变换叙事角度,而后德国的小说史家又提出,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布伦塔诺,早就多次进行过变换叙事角度的尝试。奥林匹斯神式的叙事角度的一致性,这在过去也只是一部分作家追求的目标,在今天则几乎被完全放弃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及昆特·哈姆森的作品所采用的叙事形式是多么奇特!托马斯·曼在他晚年的几部作品中又是怎样得心应手地把众多特殊的叙事人推到了叙事的前台;如《当选人》中阿雷玛尼的修道士或者是那个讲述自己青年时代遭遇的老克鲁尔。同样,加缪的《鼠疫》和《堕落》的叙事形式也是很奇特的。马克斯·费里施的小说《沉默》第一部的叙事人是小说的主人公,第二部的叙事人则是主人公的朋友,两章中就有一章我们抓不到他的影子,因为他在转述其他人物的叙述,也就是说,他采用的既不是听叙事的角度,也不是叙事人的角度,他成了一个难以捕捉的隐蔽的观察者。”
沃尔夫冈·凯瑟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麦尔维尔的《白鲸》的第一句话是“叫我伊斯梅尔”。那么,小说的叙述者会不会就是这个被叙述的对象伊斯梅尔?细心的读者产生了疑问。其实,小说的主人公伊斯梅尔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一个未开化的人,而小说叙述者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懂得数学和历史,读过拉伯雷、洛克和康德的著作,还经常引用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中的话。他讲述的要比他经历的多。最后,读者发现,他已经讲了很多他根本一无所知的东西,然后他又重新混入船员中,似乎他不再是那个百科全书式的人,也不比其他船员知道得更多。不久,他又重新开始叙述,转述老船长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的内心独白和思想。沃尔夫冈·凯瑟指出,如果把小说中叙述视角的变化看成是技巧上的失败,或者把它解释成小说的几个不同的提纲的更迭和分期写作的结果,那就彻底的错了。在这部小说里,第一人称叙述者绝不是被叙述人物的直接外延,而是一个复杂的感性的面具。而叙述者身份的变化不过是一种游戏。
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既不是作者也不是作品里的人物,而是“叙事的精灵”。这个精灵通过其自身形成叙述,建构并展现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托马斯·曼的小说《当选人》是以罗马上空响起的一阵奇妙的钟声开始的。但作者在小说的第三页突然打断了对钟声的描写而转向对敲钟人(即所谓“叙事的精灵”)的探究:“是谁敲响了这些钟?敲钟人?不,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涌到街上听这悦耳的钟声。请相信,钟楼里空无一人,钟绳松悠悠地垂在那里,可是,钟却荡了起来,钟锤击发出阵阵鸣响。那么是没人敲钟了?不,只有语法知识贫乏并对逻辑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这么认为。钟在响,这就意味着有人使它们鸣响,尽管钟楼里空无一人。那么,是谁使罗马的钟轰鸣?是叙事的精灵——它可以无所不在,它可以出现在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出现在一百个不同的地方——对,确实如此,它完全能够这样。它像空气,轻盈飘逸、无所不在,它并不因地点不同而有所区别,正是它在说:‘所有的钟都在响。’所以,正是它把它们弄响了。这个精灵如此空灵、如此抽象,以致语法上只能用第三人称谈它,只能说:‘是它。’然而,它却可以使自己浓缩,甚至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小说的第一个出场人物,并用第一人称叙事。他说:‘是我。我是叙事的精灵。现在,我就在阿雷玛尼的圣·戛兰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坐在诺特克·勒白戈曾经坐过的地方,给你们讲故事。为了让你们享受到快乐并得到最庄严的启示,我从故事幸运的结局开始讲起,并敲响了罗马所有的钟。’”对此,奥托·路德维格指出:“他(小说叙述者)是时间和空间的绝对主宰,他具有与思想等同的威力,他再现的东西丝毫不受现实的困扰,他尽情地调动人物,安排情节,丝毫不受体力的限制。他拥有自然和精神的全部力量。与他的音乐相比,任何音乐都是笨拙和臃赘的,如同肉体相对于灵魂……”[4]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保尔·贝尼舒在一次与托多洛夫的交谈时所阐述的一个论点:“作品中某些明显的矛盾之处,不一定要被看成一种不完美,而应被看成一种符号、一种充满意义的符号。在纯粹不合逻辑(或表现如此)与意味无穷的歧义之间,出现任何情况都是可能的。”[5]
四、结束语
叙述视角与叙述体作为叙事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备受文学界的关注。对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体的划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但如何看待叙述的可靠性,如何看待第一人称的诗性化的延伸,则存有一定的争议。事实上,许多被批评界视为“叙述不可靠”的作品,由于读者视角的参与而变得极为可靠;而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也不一定要像《白鲸》和《当选人》那样,让叙述者变成一个“叙事的精灵”。也可以把叙述角度严格地限制在“我”所经历的事件的范围内,即叙述者对超出“我”视野之外的事物不作任何“全知”式的描述。这并不会损坏作品的可读性,相反,有时候反而会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英]瓦纳·布兹.距离与视角:类别研究[M]∥王泰来,编译.叙事美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30-131,140.
[2][俄]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09.
[3][德]沃尔夫冈·凯瑟.谁是小说叙事人[M]∥王泰来,编译.叙事美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0-103.
[4][德]托马斯·曼.当选人[M]∥王泰来,编译.叙事美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22.
[5][法]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M].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65.
(编辑: 巩红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