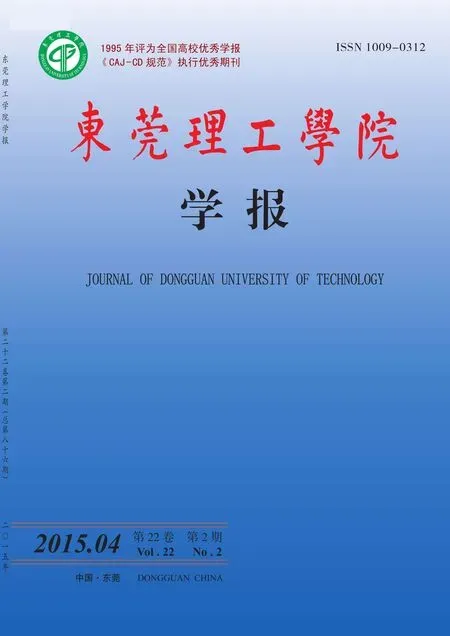韩礼德的翻译对等类型观初探
李忠华
(东莞理工学院 外语系,广东东莞 523808)
翻译对等问题不仅是西方过去两千多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现代翻译研究的重要论题。Holmes曾指出,翻译对等是几乎所有现代翻译理论著述的中心术语,同时也几乎是广大译者苦心追求的目标[1]。这既反映了翻译对等问题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反映了译界研究者在翻译对等问题上存在矛盾与争议。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翻译对等关涉翻译的本质、译本质量评价以及翻译的实践原则等根本问题;另一则由于长期以来语言学界过于关注语言形式而忽视了对意义的研究,因而无法为翻译对等研究提供系统、统一的语言学理论框架。
翻译对等的相对性要求将其纳入一致性理论框架进而建立明确的翻译对等类型,为研究翻译对等价值提供统一的语言学理论根据。韩礼德的翻译对等观源自其语言观,与其语言观相一致。文章首先讨论了韩礼德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定位,然后探讨了其翻译对等的意义首要性和语境决定性,最后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级阶观、层次观和纯理功能观等三个维度对其翻译对等类型观进行了阐释。
一、韩礼德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定位
从前系统功能语言学时期其关于机器翻译方面的研究直到21世纪初其对适用语言学的探索,韩礼德一直认为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语言问题,并将翻译问题定位为语言学问题。
在1962年发表的Linguistic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一文中,韩礼德明确指出,机器翻译是语言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因为机器翻译需要对不同语言进行系统的描写与对比,而普通语言学中的描写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能够提供系统的描写与对比所需的语言学理论支持。韩礼德认为,对语言系统的描写应领先于翻译,且描写的内容应既包括词汇、语法,也包括语境;语言描写必须以可靠而科学的理论为基础,而且其描写方法应该源于该理论,并且响应该理论[2]3;描写语言学的任务就是阐明语言这一独特的有规律的人类社会活动并彰显其运行方式,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尤其专注于意义研究,这是语言描写根本的不可或缺的部分[2]21-22。
由此可见,韩礼德对翻译研究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基于以意义为根本的对比描写语言学,这为其日后对翻译研究更加具体的定位奠定了语言学基调。
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韩礼德一直在探索这一可靠而科学的理论,以便能够对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和语境提供系统描写与比较。在其于1992年发表的Languag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一文中,韩礼德在对翻译进行界定的同时明确了其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定位。他指出,翻译这一有导向的意义创造活动决定了语言学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能够指导翻译这一意义创造活动的不可能是规约性的传统语法,而必须是功能语法,因为功能语法是“对意义潜势进行阐释”的语法。韩礼德认为,与翻译相关的语言理论必须是“选择就是意义”的理论,即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3]。
由此可见,韩礼德对翻译的语言学定位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晰,从最初的对比描写语言学越来越明晰地发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与一致性。韩礼德的翻译思想是其语言学思想的应用与发展,与其“适用语言学”思想发展是一致的。韩礼德在阐释“适用语言学”这一概念时曾明确指出,“实际上,我研究语言学就是为了寻找某种理论以思考我所面对的某些非常具体的任务:……其一便是我在1950年代晚期参加了剑桥大学早期的机器翻译研究项目。它对我集中思考整个语言系统的实际运行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14
二、韩礼德的翻译对等类型观
翻译对等是翻译评价的核心组织概念。可是,翻译对等类型各异,而且各对等类型的具体要求往往相互冲突,那么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翻译对等问题呢?这是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引发翻译对等研究领域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阐述韩礼德的翻译对等类型观之前,有必要了解其关于翻译对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一)基于意义的翻译对等观
韩礼德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定位体现了其基于功能意义的翻译研究思想,这种思想也渗透于其翻译对等观之中,主要表现为意义对等的首要性和语境决定性。
第一,意义对等的首要性。韩礼德指出,系统功能语法是语义驱动的、自然的语法;其中的每个范畴都以意义为基础,既有语义,也有形式;词汇语法与语义之间相互作用[5]3-4。很明显,人类语言漫长的进化发展使得它不同于早期的人类语言,语法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也因而极其间接和复杂。尽管如此,系统功能语言学仍然坚信能够清楚地追溯语言的功能源头,即语法结构与语言意义之间存在的自然性,甚至象似性(iconicity)关系。因而在讨论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义学定位时,韩礼德着重指出,服务于翻译的语言学必须与功能语义相关并不意味着其对形式模式 (包括句法模式与语音模式)不感兴趣,而是在强调意义对等的首要性,因为唯有通过功能语义才能把形式模式与翻译关联起来。韩礼德强调,只有当语义关系得到了合适的考虑,才能考虑语言形式,从本质上说这是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的价值问题。韩礼德认为,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形式对等被赋予极高的价值,然而,无论形式对等多么重要,它总是囿于功能语义关系所设定的范围,受到功能语义对等的约束[3]16。
第二,意义对等的语境决定性。韩礼德认为,不同语言之间、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之间的意义对等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部分的,须视相关语言项目在语境中的功能而定。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意义是语境下的功能,因而意义对等就是语境下的功能对等。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在就建立功能对等的语境进行判断和决策,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语境对意义对等的决定作用。韩礼德认为,语境决定着不同翻译对等选择之间的差异。他进而指出:语言学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翻译对等的理论,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一般性理论;但是语言学能够提供一套关于语境的理论,通过该理论译者能够根据语篇分析的结果建构意义对等的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乃至文化语境,从而建构翻译这一意义创造过程的导向——语境[3]16。
(二)韩礼德的翻译对等类型观
韩礼德认为,评价译作为什么好,甚至是否好都非常困难,因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复杂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即使是很可能作为译作评价核心组织概念—— “对等”,也缺少参考视角[6]15。这主要是由于在译界研究中,目前除了直译和意译这两个高度概括的标识外,几乎没有一个清晰的基于某一统一理论框架的翻译对等类型观[7]。
翻译对等的相对性要求将其纳入一致性的理论框架,进而建立明确的翻译对等类型,从而为研究翻译对等的价值提供统一的语言学理论根据。因此,韩礼德指出,有必要建立一定的翻译对等类型观,以赋予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翻译中的不同对等类型相应的价值。根据语言自身的参数,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韩礼德认为与翻译对等最有可能相关的是层次化、纯理功能和级阶等三个向量,因为它们是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比的关键维度,因而是界定翻译对等的参数[6]15。层次化是指语言的有序组织层次,包括语音、音位、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言之外的语境层次;纯理功能是语言内容层次 (包括词汇语法和语义层次)的功能成分组织,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级阶是语言的形式层次 (包括音位和词汇语法)的组成等级关系组织,包括小句复合体、小句、短语、词组、单词和语素等[6]15。下文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级阶观、层次观和纯理功能观等三个不同的视角来阐释韩礼德的翻译对等类型观。
1.级阶观。
“级阶”这一概念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韩礼德提出。他将传统语法中的句、小句、词组/短语、词、语素等5个范畴作为语言单位的基本级阶[8]。胡壮麟等人认为,“‘级’相当于等级体系的概念,其意义为‘包括’,指一个项目系统沿着一个单一的方面有联系,它必须包括某些形式上、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即由最高层次的单位向最低层次的单位移动,这离不开类的标准”[9]33-34。简言之,级阶是基于组构的不同等级单位,即某一等级的单位由仅次于其一级的等级单位构成。级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描写小句的基本方法。根据该方法,小句成分关系的描写便可参照级阶系统,自上而下按照不同的级阶依次推进。例如,英语中语法级阶依次为小句-词组/短语-单词-词素等,小句的功能由词组或短语来体现,而词组或短语的功能则由单词来体现,依此类推[10]170。
韩礼德关于翻译对等的级阶观最早见于其于1962年发表的Linguistic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一文。在该文中,韩礼德在探讨机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时,结合汉英翻译和俄英翻译实例,研究了词汇语法层次 (lexicogrammar)中级阶概念范畴下的翻译对等问题。即:首先将一组级阶最低的对等成分——语素对等成分,按照其或然率高低进行排列;然后将级阶提高一级到单词 (并将单词作为语境)来修正语素对等成分的选择,即每次都将所需翻译条目置于相对高一级的单位中进行考察——首先是单词,然后是词组,依此类推:语素对等的考察语境为单词,单词对等的考察语境为词组,词组对等的考察语境为小句,并根据语境对每一级阶的多个具有不同或然率的翻译对等成分进行选择,以确定对等价值最高的翻译对等成分,从而获得词汇语法层面中最符合(上下文)语境条件的理想对等语[2]。
韩礼德在1992 年[3]以及 2001 年[6]的翻译研究中都对翻译对等的级阶观进行了界定和阐释。韩礼德认为处于不同级阶的翻译对等具有不同的价值:翻译对等的价值随着级阶的升高而增长;小句复合体 (句子)级的翻译对等的价值高于小句级的翻译对等,小句级的翻译对等价值高于短语级的翻译对等价值,以此类推。但是,韩礼德也指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处于较低级阶的翻译对等会获得相对较高的价值[6]16。
2.层次观。
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其各层次之间具有不同的等级关系,主要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语言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关系,每个下一级层次都是对上一级层次的体现,即语义层 (对意义的选择)体现于语法层 (对语法的选择),后者则体现于音系层 (对语音的选择)。通常语言层次可以分为表达层次(包括语音层次和音系层次)和内容层次 (包括词汇语法层次和语义层次),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翻译处在表达平面和内容片面的交界处。“相同内容,不同表达”正是基本翻译策略衍生的原型。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思想,语义层是语言系统对语境的体现,即语言连接更高层面的意义接面层,因而层次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语言的外部——语境层,体现行为层或社会意义层[11]18。
在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Catford根据语言的不同层次对翻译对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12]。Catford认为人们所理解的最典型意义上的翻译对等应为语义层次上的对等;他同时认为,在语言的所有其他层次上也存在对等,包括内容层次和表达层次,虽然表达层次上的对等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6]15。韩礼德认为,不同语言层次上的翻译对等具有不同的价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对等价值随语言层次的上升而增长——语义层次对等的价值高于词汇语法层次对等的价值,语境层次对等所具有的价值或许在所有语言层次中是最高的;但是,不同语言层次上的翻译对等价值总是变化的,因而要根据任务对任何具体的翻译对不同层次的对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6]15。
3.纯理功能观。
所谓纯理功能,是指所有人类语言演绎发展所依据的基本组织概念功能,是意义组织的基础[6]15。韩礼德认为,任何语篇所固有的意义潜势都是三股意义或功能的复合体,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为意义的描写侧面,是指人们对存在于客观和主观世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的反映,即人们使用语言识解经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经验,描述发生其中的事件、状态以及各种存在等。人际功能则为意义的活跃成分,是指人们使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建立和保持关系,影响他人行为,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观点或态度,并激发或改变他人的思想,包括我们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方式、引介我们判断和想法的方式以及我们自身观察的情景视角等。语篇功能则是为意义的语篇侧面,即语篇发展的意义组织方式,如语篇中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的平衡、语篇自身构成成分之间以及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联系等[11]18。
韩礼德指出,尽管语言系统的三种纯理功能三位一体,不存在孰先孰后之分,然而就翻译对等价值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三种纯理功能中,概念功能对等价值通常是最高的,这是因为通常人们对“翻译对等”的界定是概念的,若译文在概念方面与原文不一致就不能视为翻译。正是因为如此,在翻译中最常见的批评是——尽管译文和原文在概念功能方面对等,然而在人际功能或(和)语篇功能方面却不尽然。用语境术语而言,即源语的语场在目的语中得到充分的识解,而语旨与语式却没有。韩礼德认为:纯理功能对等价值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尺度;非概念功能对等的价值有着很大的变化性。在有些语境下,翻译会高度重视译文与原文中所设定的权势与距离关系以及评价模式 (即人际功能)保持一致,甚至到无视准确的概念功能对等需求的程度。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当语境对等被赋予最高价值因而语义层次对等需求无效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因为该情形要求译文与原文在情景语境方面功能对等[6]16。
翻译对等的级阶观、层次观和纯理功能观构成了韩礼德的多维翻译对等类型观。韩礼德认为,在任何具体的译例中,对等价值可以赋予不同的级阶、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纯理功能。从级阶维度看,通常具有较高的词汇语法单位被赋予较高的对等价值,而对相对较低的词汇语法单位则容忍其变化。倘使视小句为对等的常量,则短语和词组不一定需要如此。从层次维度看,同样如此:语言内部的最高层次——语义层次通常被赋予最高的对等价值;最高对等价值也可以赋予语境层次,尤其当相对较低层次的对等有问题的时候。翻译对等的级阶观和层次观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使得我们能以一种变化的视角来观察翻译,即以更高级别常量为背景的变译,它是译者一直采用的翻译策略之一。尽管纯理功能之间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然而在翻译中概念功能对等往往价值最高,而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对等价值则存在较大的变化性。通常只有当概念功能对等得到了满足才会考虑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对等价值[6]17。
三、结语
翻译对等是韩礼德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其早期关于机器翻译研究的尝试,还是其后来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的讨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便是翻译对等问题。综观韩礼德历年来的翻译研究文献,其翻译对等的思想经历了早期的级阶观,这主要缘于其早期对于机器翻译研究方面的兴趣,因而其关注的焦点在词汇语法层面;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其翻译对等的思想从最初的级阶观扩展到层次观和功能观,并探讨了不同维度下的翻译对等价值,从而建构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对等类型观,体现了其翻译多维对等的思想。
[1]Holmes J.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Amsterdam:Rodopi B V,1988.
[2]Halliday M A K.Computational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C].London:Continuum,2005.
[3]Halliday M A K.Languag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J].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technica della traduzione,1992(0):15 -25.
[4]Halliday M A K.Pinpointing the choice:meaning and the search for equivalents in a translated text[M]//Ahmar M,Knight N K.Appliable Linguistics.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10.
[5]Halliday M A K,Matthiessen C M I M.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London:Cassel,1999.
[6]Halliday M A K.Towards a theory of good translation[M]//Steiner E,Yallop C.Exploring Translation and Multilingual Text Production:Be-yond Content.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1.
[7]Koller W.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and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J].Target,1995,7(2):191 -222.
[8]Halliday M A K.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J].Word,1961(17):241 -292.
[9]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Matthiessen C M I M.Teruya K,Lam M.Key Term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M].London:Continuum,2010.
[11]Halliday M A K.The Gloosy Ganoderm: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J].中国翻译,2009(1):17-26.
[12]Catford J 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