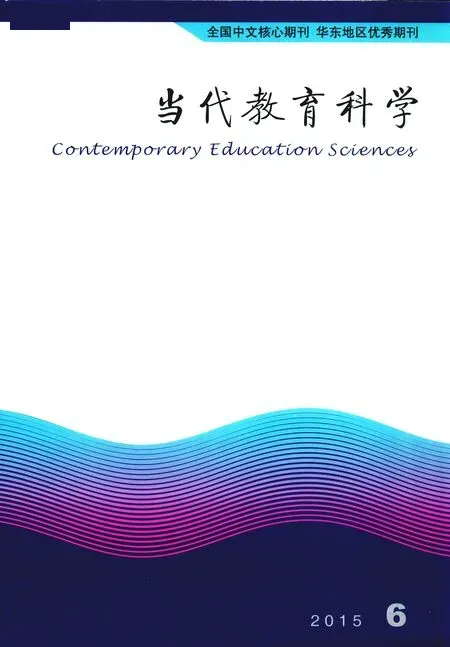教师实践智慧本质探析*
●赵正新
教师实践智慧本质探析*
●赵正新
揭示教师实践智慧的本质,是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前提。也为相关研究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实践智慧由“实践”和“智慧”两个核心概念构成,这也注定了实践智慧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哲学概念。在实践智慧中,“实践”和“智慧”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教师实践智慧表现为审“时”度“势”、“法”“理”合一以及“中庸”之道。
实践、智慧、教师实践智慧
自20世纪50年代以“专家取向”为特征的美国“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后,教师在教育改革与实践中的作用逐渐引起关注。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教师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教师实践智慧得到空前的重视。在我国,由于深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及相对滞后的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制约,教师教学自由度不大。同时,由于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基础教育主要受技术理性控制,对教师创造性要求也不高。无论是职前职后的教师教育和培训,还是现实的教育实践,都主要表现为对教师理论智慧或技术的偏爱。因而,实践智慧一直是哲学研究的“自留地”,与教育无关。本世纪初,伴随教师专业化浪潮以及新一轮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实践智慧才开始逐渐成为“显学”,并迅速成为教育领域的时髦话语,至今方兴未艾。然而,现有许多相关研究由于缺乏对教师实践智慧的准确把握或有不同的理解而自说自话,以致各种观点五花八门。如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知识说”、“能力说”、“机智说”、“素养说”等等,都是从不同方面描述教师实践智慧的某一特征,无法揭示其全貌和本质。
分析教师实践智慧的本质,是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基础,也是逻辑起点。教师实践智慧的本质不清楚,相关研究都将缺乏根基,势必将成为“无根之萍”,研究者之间也就失去了对话的平台。
一、“实践”和“智慧”内涵之辨
教师实践智慧是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概念。说其复杂,因其包含了两个重要而具有多元语义的哲学和生活用语:“实践”和“智慧”。这两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话语下的意义都不完全相同。所以,分析教师实践智慧,有必要首先厘清这里所指“实践”和“智慧”的应有之义。
“实践”隶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概观哲学关于“实践”的理解,“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实践主要来自于实践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对实践概念进行分析和反思的哲学家。他把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三个方面。其中实践活动主要指政治和伦理领域的活动,是旨在努力达到并维护一种道德上善的生活形式的行动;创制活动则主要指技艺、技能等生产制作活动,是一种工匠和手艺人的活动。创制和实践的根本区别在于创制的目的是为他物,即“成物”。实践的目的则是在其自身,也就是人本身,即“成人”(包括成人和成己)。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问题着眼于既定目标(价值和准则)的情况下手段的目的理性的组织,以及在不同的手段之间的理性选择。相反,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按其结构,用来解释实践问题的那些理论,是以深入探讨交往行动为目标的。在这些理论框架中获得的各种解释,当然不是直接作为行为定向起作用。”[1]实践,不是“工具行为和从技术上占有对象化的自然”。后来的康德和伽达默尔关于实践的理解都基本沿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领域探讨实践。
近代西方思想由于受到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影响,渐趋抹平实践与其他人类行动的区别,似乎一切行动都可以叫“实践”,结果是“行动”、“行为”甚至“经验”都成了实践的代名词。这种对实践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技艺”、“创制”或“生产”。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培根提出了“技术实践(practice)”,他认为这是一种能够产生功用的实践,也是能够用结果来衡量的实践。自培根和笛卡尔始,实践理性逐渐演变成技术理性。这种基于技术理性对实践的理解,声称人类一切行动都可称之为实践,看似扩大了实践的范围,其实质仅仅把实践局限于科学和技术应用的范畴。因此,其本质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并带来了诸多问题。正是这样的理解,才产生了所谓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种转换意味着一种文化危机:“这种观点意味着没有严格意义的实践科学,或者说实践与理论科学的区别必将被理论与应用科学的区别所取代。”[2]
广义的实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理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实践”概念,不仅包括人在政治、伦理领域的活动,还把生产劳动——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属于制作的部分——纳入到实践的范畴,而且认为这种生产劳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甚至是思想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实践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是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4]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明确把生活活动也纳入到实践的范畴,从而实现了“成人”与“成物”的统一。
教师的活动尽管也有技术的成分,如怎样备课、如何有效使用多媒体、板书的美化、语音语调的变化及节奏的把握等等。但教师的这些技术性活动,其目的不在“成物”,即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根本在于为“成人”和“成己”服务。因此,在教师实践智慧研究中,实践之内涵主要依赖于传统实践哲学的理解,强调实践与一般生产活动的区别,突出实践的“自由”与“道德”的品性。
智慧是日常用语中使用较为频繁的词语,其内涵也十分丰富。
在英语中,“智慧”通常用“wisdom”表示,“指人的最高思维能力。其原义与希腊语sophia(实践的技艺)相连。后逐渐改变其意义。”[5]柯林斯高阶英汉词典对“wisdom”的释义有:智慧、才智;知识、学问;明智;常识;好的判断力等等。
在汉语中,在不同语境下,“智慧”也有不同的内涵。《新华词典》[6]对“智慧”的注释有两条:①从实践中得来的聪明才干;②同“智力”。《辞海》对“智慧”的解释是:“①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如智慧过人;②犹才智、智谋。‘虽有智慧,不如乘势’;③见般若。”[7]“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语出《孟子·公孙丑》,其意为“与其有智慧,不如借助时势”,这里的“智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广义的认识能力。时势及时机,这种智慧显然与“时机”无关。因此,第①②两种解释基本把智慧与能力、智力、聪明、知识等同,这也是众多的汉语辞书中的主流观点。有些辞书在解释“智力”时,也直接将其与智慧同义。
可见,无论中西,把智慧与能力、知识、智力、聪明等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解释。但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智慧相去甚远,我们平常所说的智慧,虽与能力、知识、智力、聪明有关,但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关于智力和智慧的区别,我国学者孟宪鹏就做过很好的比较。[8]他认为:智力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它带有很大程度的先天因素。智慧则是指有一定智力的人,经过后天努力,运用智力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同机智、巧妙、灵感、发明、创造、谋略、方法等联系在一起的。智慧是先天素质和后天努力的合金,并以后天努力为主。智力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带有情感色彩。智慧则是一个褒义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人们把智慧给那些智力高、知识渊博、有修养并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智力仅仅是一种能力,犹如体力,不包含知识。智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包含知识、方法、修养等。总之,智力是智慧的子系统,是智慧的要素。用数学语言说,智慧是智力函数。
把智慧等同于能力或知识,也忽略了智慧灵动的品性,因为智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审时度势,然后择机行事”。另外,平常所说的智慧不仅仅是聪明,更是一种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田慧生认为,“智慧是个体生命活力的象征,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在知识、经验习得的基础上,在知性、理性、情感、实践等多个层面上生发,在教育过程中和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甚至也不只是心理学概念中的智商,它是每个安身立命、直面生活的一种品质、状态和境界。”[9]
由此,智慧的另一种释义——“般若”——值得我们关注。根据《伦理学大辞典》[10]的解释:“般若”(梵文prajna)是佛教用语。亦音译为“钵罗若”“波若”等。意译为“智慧”、“智”、“慧”、“明”等。全称“般若婆罗密多”或“般若波罗密”,意译“智度”、“明度”等。般若就是智慧,不过并非世人所说的聪明智慧,因为汉语里面没有恰好与其相同含义的词汇,所以就没有被翻译成智慧,而是直接用梵文的音译。“般若”是大乘六度之一,谓通过智慧达到涅槃之彼岸。佛教经典《大智度论》卷一百:“般若婆罗密是诸神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是般若婆罗密。”认为此智慧非世俗人所都有,是成佛所需求的特殊认识。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认为,般若这种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这个智慧。这不是普通的聪明,这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就是超越一般聪明与普通的智慧,而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这不是用思想得到的,而是身心两方面整个投入求证到的智慧。这个智慧才是般若。般若所揭示的智慧是一种综合素养,涉及身心两个方面;它不是一般的聪明,而是基于知识、聪明、才智,但又高于知识、聪明、才智;它没有定性,只有在实践中生成,也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它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需要要潜心修炼。佛教关于智慧的意蕴略显高深和玄奥,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智慧的本质无疑有很大的启发。
概括以上关于智慧的分析,就本研究的视角而言,讨论智慧的本质应明确这样几点:首先,智慧在实践中体现。历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将智慧分为思辨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前者要求有直观的理性和第一因的严格知识,体现于思辨科学中;后者有时也译为“谨慎”,表示过度的小心与鲁莽之间的中庸之道,与生活实践行为有关。因此,在实践智慧中,智慧与实践紧密勾连,智慧以实践为依托,而实践以智慧来彰显品性。其次,创造是智慧的精髓,没有创造就没有智慧。由于实践常常面临不同的情境,在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境下,总是需要实践者基于已有经验和知识,采取恰当的方式加以应对。每一次合理的应对都是一种创造性的体现,因为在教育实践中,已有经验和知识只能参照却无法复制。第三,智慧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智慧是对个体既有能力、技术或知识的合理支配,它是一种非编码的文化系统,无法复制、无法模仿、不可传授。“智慧与理解的境界处于一切生灵的眼睛不能看见之处。”[11]智慧的这种特性,暗合了佛教对智慧的理解。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智慧也常常给人以“神秘”之感,故只能“以道观之”,而所谓“道”又更显“玄虚”。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庄子也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2]儒家的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13]因此,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智慧“既非直觉,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推理过程。它是一种状态,能使我们预测、预先准备和更改我们取得经验的进程。”[14]第四,“生命是智慧的灵魂”。教育实践中的智慧是教师绚烂生命的自然流露,它由着生命,也是为了生命,没有任何的修饰和矫情,教育实践过程中每一次智慧的生成都是师生生命活力的精彩演绎。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体验到的是快乐和幸福。第五,德为智慧立法。智慧总是以高尚的动机、善的目的为指向。格兰特(Grant)认为,智慧离开了德性,就只是聪明,并很容易蜕变为狡猾。“灵魂这只眼睛,离开了德性就不可能获得明智的品质。”[15]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即使有才,有很强的辨析能力、发明创造能力,但如果没有德,不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
二、教师实践智慧的本质
鉴于对“实践”和“智慧”理解的多样性,“实践智慧”的复杂性就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实践智慧概念史就是一部实践哲学的发展史。笔者无意也无力去梳理实践智慧的发展脉络。美国学者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夏普(Kenneth Sharpe)曾把实践智慧概括为“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the right way to do the right thing)”。笔者认为这一描述相当精辟而恰当。这里借用大师的智慧,我们可以认为,教师实践智慧就是在教育实践中能够帮助教师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的一种品质。道尔顿(Jon C.Dalton)认为实践智慧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良好的知识;二是好的判断。也就是说,教师实践智慧不仅包括教师在特定情境下“怎么想”、“怎么做”的方法论问题,更有“为什么这么想”和“为什么这么做”的价值追问。教师实践智慧由教师实践伦理、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思维三部分构成。
教师实践伦理包括公正、正直、良心等等,它是教师实践智慧的价值导向系统。只有合乎伦理的才是智慧的,换言之,违背伦理的就一定不是智慧的。合乎伦理是实践智慧存在的前提,也是理解教师实践智慧的基本信条。
实践性知识是“怎么做”的知识,它不同于技术性知识,因为技术性知识只说明“做什么”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但无法解决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或使用到什么程度。技术性知识或理论知识具有普遍性或抽象性,可以独立于客体而存在,它们可“教”可“学”。而实践性知识是一种情境性知识,是应对复杂环境的一种“即兴性”知识,它源于经验,但又不是经验的简单复制或移植。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实践性知识只存在于实践中,它不可教不可学。因此,个体要靠“临床的方法”对他所必须处理的人或事作出判断。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实践智慧的核心,它们构成教师实践智慧的智力支持系统。
实践性思维与理论思维相对。理论思维是抽象的、舍弃客体的具体性,强调推演,追求因果,具有可重复性。理论思维着重于认识世界,认为改造世界不过是“真理的逻辑展开”。因此,理论思维偏爱“计划”,并认为过程和结果都是可预计、可预演的。而实践思维则是一种具体思维、关系思维、动态思维。它尊重具体性、差别性,能自觉地把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及相互动态关系作为思维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它强调实践过程的不可重复性和实践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实践思维并不迷恋真理。在实践思维那里,真理也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它为实践提供一种参照,并与实践共生长。教学过程不是一种预设的自动展开,而是一个不断反思、决策、重构的过程。实践思维在教学实践中表现为对“设计”的重视,设计的方案永远都不是呆板、一层不变的,它具有可解释性,实践主体能随着实践进程的变化而对方案作出主动调整。实践思维是实践智慧的思维保障系统。
三、教师实践智慧的策略选择
教师实践伦理、实践知识和实践思维三者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教师实践智慧的整体。在此意义上,教师实践智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审“时”度“势”。所谓“时”就是时机,是教育过程中的最佳“点”。及时有效抓住和利用这个“点”将事半功倍,反之,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或事倍功半。唐太宗李世民倡导“遇物而诲,择机而教”,就是强调在教育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时机。鉴于教育要素的复杂性,教育时机的把握并不意味着总是一定要迅速地解决问题。它既可表现为“即时性”,即教师迅速采取适当的措施,及时解决问题;也可表现为“延时性”,即先搁置问题,在适当时间后再予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冷处理”。无论是即时处理还是延时处理,都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察、分析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善于把握时机,及时进行教育”似乎已成为有效教育默认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只有具有一定实践智慧的人才能很好的把握。
所谓“势”可以理解为教师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综合背景条件,也可以理解为“行动的境域”。任何教育活动都是在具体、特定的“场域”中发生的,实践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把一般的原则同具体的现实背景相融合,消解它们之间的张力。“势”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使教师实践智慧成为可能和必要。富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充分把握和利用这种“势”,因势利导,为教育实践服务。杨国荣教授认为“势”既涉及时间,也关乎空间。“与行动相关的时间以历史条件为其实质内容,行动的空间形态则体现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场域”。[16]因此,“时”和“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王夫之也认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审“时”度“势”就是“时”和“势”的有机结合。
教师实践智慧要求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仅能“乘势”施教、“顺势”而为,而且还能“造势”。所谓“造势”,就是形成有利于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背景和条件,改变、消除或避免不利的实践境域。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境域常常都是偶然的、自发的,也是性质各异的,并不总是有利于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作为一个智慧型的教师,不仅应该具备对不良背景或条件加以识别和控制的能力,而且还能对不良的背景和条件加以积极的改造,使之有利于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例如,我国新课程改革打破了人们对课程资源的一般的、狭隘的理解,并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此理念下,教育过程中的“失误”有时也可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其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利用智慧,把一些教育的“事故”转化为教育的“故事”。
第二,“法”“理”合一。“法”指法则、规则、规律;“理”指伦理、价值、目的。教师实践智慧是一般教育原理和法则与具体情境结合中所体现的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性绝不是一种“天马行空”的随心所欲,而是基于理性,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一种形上理解,体现为对规律、规则、标准的把握和尊重。但这些法则、规则、标准甚至是行动指南又不能被当作僵硬的教条,因为实践智慧总是面临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对象,它不仅关注“是什么”,更强调对“应当成为什么”“应当做什么”的一种价值关切。正是源于这种对价值的追问,使得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实现了“成人”与“成已”的统一。教育实践中,教育目的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教育目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通常也规定了手段选择的方向。具有正当性的、积极价值的目的总是要求实现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正当的、消极价值的目的往往为“不择手段”提供“温床”。在教育实践中,教师面临的并不总是积极的教育目的,更多时候需要在多种价值之间做出选择和协调。这种选择和判断既依赖于教师的专业素养,更以其专业伦理为导向。正如科林·马什(Colin Marsh)所言:“教师每天都在作出道德层面的决定。教师不停地在各种要求之间作出权衡,但常常受到自身道德价值观的引导。”[17]这是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因为实践智慧都是追求善的目的,一个缺乏伦理道德的人,不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不具备高尚道德的人,无论有多么高深和完备的知识,都不能称之为有智慧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必定存在某种品质,一个人出于这种品质而做出的行为都是好的,就是说,好像是出于选择的和因为那个行为自身之故的。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的是德性。而使得我们去作为实现一特定目的而适合于去做的那些事情却不是德性,而是另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聪明,它是“做能很快实现一个预定目标的能力。”[18]因此,伦理和价值成为实践智慧的内在规定性。
概言之,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是育人,它既是一种科学活动,又是一种艺术活动,更是一种伦理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的这个特点,决定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是合法则性和合伦理性的统一、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教师实践智慧就是“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统一。
第三,“中庸”之道。“中庸”可谓是孔儒哲学的重要思想,孔子视之为最高的“德”。朱熹对中庸的注解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19]对“中庸”的一般理解就是,为人做事应当恰如其分,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分”。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中庸”之道,他在论述道德德性时,认为所有道德活动都有三种状态,即适度、过度与不及,相应有三种品质:两种恶(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和一种作为它们中间的适度的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就是适度,德性就是中道,是对中间的命中。所谓“命中中道”是指“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情况,对应该的对象,为应该的目的,按应该的方式……”。可见,实现德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每一件事物中找到中间,这是种需要技巧与熟练的功夫。”据此,教师实践智慧中的“中庸”之道,就是一种“分寸”感,其本质就是教师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度”的适宜性。事物的不同存在形式都是某种“度”的表现,事物的性质随着“度”的变化而变化。“适度”是事物的理想状态,是实践活动应该追求的,而“过度”或“不及”都是一种消极状态,都是应该力求避免的。教师能否把握合适的“度”是教师实践智慧的一个重要表征,它体现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例如知识的学习、作业的布置、奖励和惩罚手段的运用等等,其背后都有理性的考量,价值的追问和“度”的把握。“中庸”之道也是教师工作艺术性的重要体现。
教师实践智慧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教育实践活动是一项“择宜”的艺术,也是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主体性人格的体现。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专业化的内在需求。
[1]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2]列奥·斯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40.
[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4]毛泽东.实践论[G]//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83.
[5][10]宋希仁等主编.伦理学大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256,388.
[6]新华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86.
[7]辞海·第六版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8]孟宪鹏主编.智慧方法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2.
[9]田慧生.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及智慧型教师[J].教育研究,2005(2).
[11]库萨的尼古萨.论有学术的无知[M].伊大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
[12]庄子.知北游.
[13]王阳明.见斋说.
[14]刁培萼,吴也显等.智慧型教师素质探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5:37.
[15][1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8.
[16]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43.
[17]科林·马什.初任教师手册[M].吴刚平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365.
[19]朱熹.中庸集注.
(责任编辑:曾庆伟)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师实践智慧的生长逻辑探析”(项目编号:BAA130009)的研究成果。
赵正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