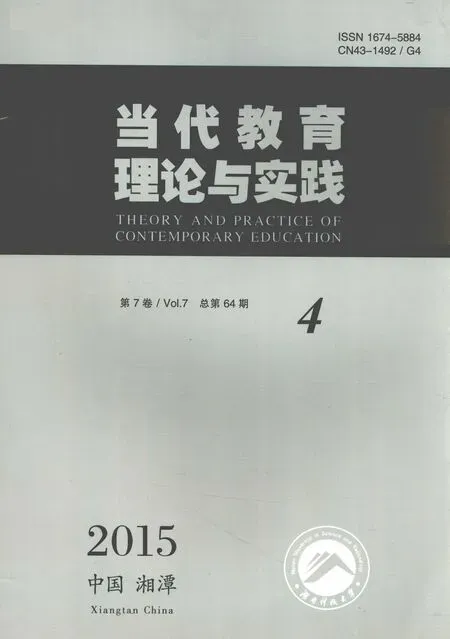徐渭《南词叙录》中“情”的思想体现
黄亚琴,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在中国丰富的戏曲理论长河中,徐渭的《南词叙录》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记录着一段南戏历史生命,同时,该书亦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即体现出徐渭对“情”的重视。“情”是徐渭的重要戏曲审美标准之一。在《选古今南北剧》一书中,他曾强调戏曲“情”的色彩:“人生坠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眥裂,哀而鼻酸,恍如与其人即席挥塵,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1]在《南词叙录》中,徐渭同样强调了“情”对唤起观众共鸣的作用。
1 创作主体有情
徐渭对明初南戏创作的弊端深恶痛绝,指出“以时文为南曲,荧末、围初末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2]他认为以“时文为南曲”的戏曲创作是当时的弊端,并且严厉批判了邵粲《香囊记》“最为害事”,实则以之为例来说明戏曲创作主体“情”的重要性。“《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非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2]徐渭的这些批评是“立足于以主体心灵和主体情感审视戏曲艺术真实,强调戏曲作品是审美主体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情动于中,有感而发”[3]。
戏曲创作者具有真挚动人的思想感情是戏曲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戏曲是写意的,戏曲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汇于笔下在戏曲中生成,观众通过戏曲中相应的情感交织从而感知创作主体的“情”。所以这种戏曲创作主体的感情抒发,是戏曲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前提,也就是戏曲创作中的“情在笔先”。因“情”所生产的戏曲,反映创作主体的思想状态,更表现个人的情感体验。
戏曲演出的本质是创作主体之“情”的具象化过程。创作者情动于心而形于笔成于戏,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将其倾注于戏曲剧本中。戏曲创作主体将情融入创作,戏随情运,情随戏走,戏感于情,情激于戏。通过《南词叙录》所举《香囊记》的例子分析,可以看出徐渭认为“情”对创作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作主体有情,是戏曲创作的重要基础。《香囊记》的作者邵粲“习《诗经》,专学杜诗”,“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非故事”。此剧写宋代张九成与妻子贞娘之间的悲欢离合,作品的典雅化、骈俪化、八股化倾向,大大背离了戏曲艺术发展的本质特性。剧中宣称“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光辉”[4],这表明《香囊记》是封建礼教之集大成之作。由于作者没有真实情感融入只是一味地堆砌华丽文辞,是不可能赢得观众情感共鸣的。再加之剧作带着浓烈的伦理教化色彩和对统治集团朱程理学的服务意味,因而使创作主体在戏曲中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即使有所传达也只能是“伪情”“矫情”。
创作主体的情感是戏曲创作的出发点、内驱力,直接影响到戏曲创作活动的方向、过程和结果。戏曲创作是对人的“情”的深化提炼,创作主体有情,戏曲才会有味。
2 艺术形象有情
只有艺术形象有情才能最直接激起观众的情感波澜,对于没有情的艺术形象而言,再美的形象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艺术形象的有情与观众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相互的存在,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艺术形象有情,才能激起观众与之相对应的情感召唤。
徐渭批评《香囊记》“最为害事”,但却较为推崇《琵琶记》。在《南词叙录》中,他说:“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於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2]徐渭对其中一些情感强烈的场景更是大加赞赏:“惟《食糠》、《当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2]高明《琵琶记》的贡献不仅在于“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更在于他以有情的形象传无穷的情感。
戏曲是以人的情感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感,也表现观众的情感。但这些情感并非抽象的表现,而是用情去塑造有情的形象来表现人的“情”。在《南词叙录》中多次提及《琵琶记》,其中的《食糠》《当药》《筑坟》《写真》等出是“从人心流出”的,故颇得徐渭赞赏。剧中人物赵五娘以其对公婆的“情”而深入人心。赵五娘的形象在《琵琶记》中是实在的,是有情感基础的。赵五娘是剧中最为有情的人物形象,正因如此,赵五娘的形象才让人感到是从作者“人心流出”。《食糠》一出中,赵五娘“孝顺歌”的有情之言,淋漓尽致地道出了社会伦理加在这个普通妇女内心深处的艰难和痛苦。“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这糠啊,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5]通过戏曲中“遭垄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些构思把赵五娘的怨情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通过有情的语言、有情的行动和有情的思想所塑造的“有贞有烈”赵五娘,使观众为之动心动情。观众对赵五娘因不幸和苦难造成的内心隐痛情感是真真切切的体味,乃是《琵琶记》动人情之根本。要创作出动人的戏曲,戏曲艺术形象要有情,一旦离开了这种“情”,便失去了构成戏曲动人的一个关键性过程。高明自言传奇创作“乐人易,动人难”,惟有“情”才能动人。艺术形象有情是戏曲“动人”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其大放光彩之处。
3 戏曲内涵有情
创作主体和艺术形象的有情还不是“情”的终点,创作主体和艺术形象的“情”最终都是要在戏曲的整体内涵中表现出来,最终形成戏曲与观众的情感相融:“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2]“感发人心”的戏曲艺术审美功能,表明徐渭在戏曲探索中,肯定戏曲中“情”的存在,戏曲的创作是不能脱离人的审美接受而存在的。这个要求就决定了戏曲必须是面向人的情感而存在。把戏曲的视线与创作主体的“情”相连,把戏曲的思想与戏曲形象相接,把戏曲的情感与观众相融,在戏曲创作活动中重视“情”的地位。戏曲内涵是根植于戏曲的情感,使观众在戏曲的一段故事、一个人物中直面现实生活的那些悲欢离合。如《南词叙录》中点评:“《琵琶》尚矣,其次则《玩江楼》、《江流儿》、《营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2]可以说《琵琶记》的成功正是在于戏曲自然真实的情感内驱力,引得徐渭不吝其辞地大加赞赏。
戏曲内涵有情是建立在戏曲以其整体与观众相互关联的基础上的,它要表现出戏曲“情”的本质使观众获得戏曲的情,这正是戏曲内涵的情感价值所在。徐渭的批评表明戏曲只有表达人的情才能融入艺术生命力,才能实现人与戏曲的同在。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是为了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戏曲创作当然也不例外:结缘于情,有情是戏曲以代言体的形式展现人生活画面最真实的前提,因此真挚的情感沟通了戏曲与观众在思想感情上的界限,达到“乐人”与“动人”。戏曲因情生戏,以情动人,只有通过情,戏曲才不是“空心”的艺术而是“实心”的生命体验。戏曲内涵有情会“使戏曲舞台成为现实中的人们情感稀释的场所”[6]。戏曲中故事的壮烈缠绵与人物的悲欢离合尽其能事,都带着创作主体与观众的情绪与感悟,表达着戏曲的内在情感,即在戏曲创作、表演过程中表现人生或生命的情感价值体验。
总之,徐渭以创作主体—艺术形象—戏曲内涵的“情”为核心的审美标准,深刻地把握了戏曲的本质特性,促进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研究的发展。《南词叙录》中的“情”既属于创作者又属于观众,它既是写意的又是具象的,它既是潜在地又是直感地存在于创作主体、戏曲艺术形象和戏曲内涵三位一体中,不可分割。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李复波,熊澄宇.南词叙录注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3]刘奇玉.古代戏曲创作主体思维特征论[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30(10):18-19.
[4]章培恒.四库家藏《六十种曲》(1)[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毛晋.六十种曲(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
[6]陈友峰.心灵之诉求与外物之超越——简论元典文化思维方式对戏曲审美形态之影响[J].戏曲艺术,2005,26(2):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