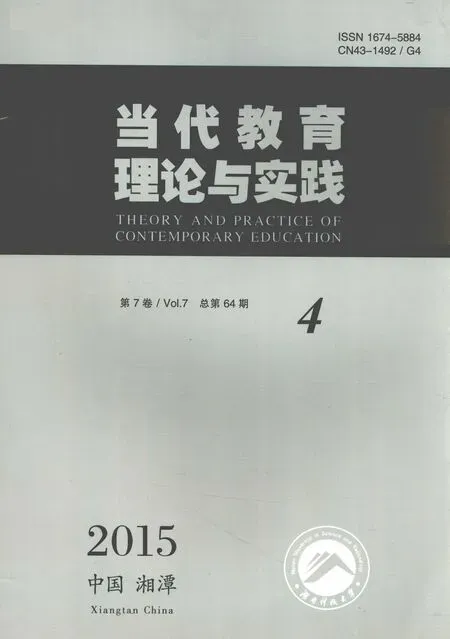从唐·德里罗“9·11”小说看美国女性形象
罗姣惠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01年的“9·11 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继“珍珠港事件”之后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自此之后,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以“9·11 事件”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在亚马逊网络书店中有一个“9·11”小说书单,该书单的创立者克雷格·范格拉斯提克将“9·11”小说定义为“所有涉及‘9·11’袭击及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和社会等议题的小说”[1]。依此定义,可以肯定地说当代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显然是一位“9·11”作家”[1]。本文结合文本细读法,研究德里罗《人体艺术家》和《坠落的人》中典型女性人物的女性气质,旨在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劳伦和丽昂的创伤生活经历来表达她们在男性受到严重创伤的情况下,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走出创伤,重建自我,承担各方面的责任,追求生命的蜕变。
1 从人体艺术表演中走出创伤,实现救赎的劳伦
《人体艺术家》描述了一个平静的早晨,人体艺术家劳伦和她的丈夫雷在厨房里烤着面包,心不在焉地交谈着。早餐准备好后,两人坐下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聊着。两人之间的对话简短、零碎。可第二天,劳伦就接到了雷突如其来的死讯,他在第一任妻子的曼哈顿公寓里开枪自杀。雷的自杀给劳伦带来了沉重打击,在参加完葬礼后,劳伦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在他们原来租住的破旧小屋里。然而,一个来历不明、幻影般的无名人物与她相伴。他甚至能像录音机一样惟妙惟肖地模仿劳伦和雷生前的所有谈话,劳伦给他取名为塔特尔先生。劳伦把他留了下来,希望可以从他身上找回与雷共处时光的记忆。塔特尔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模仿激发了劳伦对过去的回忆,让她沉浸在雷的自杀带来的伤痛之中。但与此同时,塔特尔先生的重复模仿,使得劳伦慢慢理解创伤事件,并获得顿悟。
丈夫的突然自杀给劳伦带来痛苦、失落和困惑。她打电话给雷的第一任妻子伊莎贝拉,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有关自己未了解到的雷的情况。雷的性格有着双重性,让人感觉到很恐惧,“他一直都有自佩手枪。不管在哪儿他都带着枪。”[2]在和伊莎贝拉通话之后,劳伦了解到了雷不为人知的一面。当雷的律师打来电话告诉劳伦说雷欠了许多债时,这个消息没有让她很惊讶。雷和劳伦一样,都身为艺术家,但雷却没能像劳伦那样从现实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最终,艺术没有成为他的避难所。在与塔特尔的交流中,劳伦重拾创伤记忆,在呈现、剥离、审视的过程中,她逐步加深对丈夫的理解,生活的真实面目——残酷、脆弱和破碎,慢慢地被展现出来。她意识到丈夫的死已是事实。她准备摆脱过去,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她的那段表演“人体时间”反响热烈,获得了大量好评。她的这次表演通过叙述创伤来引起观众的共鸣。首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古代日本女人,她出现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按日本能剧的表演程式做着动作”[2]。接着是一个盛装出行的妇人,“她拎着一个手提箱,看了一下腕上的表,挥手招呼出租车。”[2]最后是一个裸体的失语男人,“在表演持续了七十五分钟之后……羸弱不堪又不能言语,却拼命想告诉我们什么。”[2]当得知雷突然自杀的死讯,劳伦感到伤心,备受折磨。但是后来她选择坦然面对雷的死亡、雷的过去,接受残酷现实带来的挑战,让生活充满意义。最终,劳伦通过艺术获得救赎,重建自我,勇敢地面对生活,实现了对真实自我的寻找和精神的回归。
2 走出创伤,服务他人的丽昂
《坠落的人》中的女主人公丽昂没有因为丈夫的堕落而堕落,她不仅担当起自己家庭成员的责任,而且还负责对“9·11”受害者的无偿心理疏导工作,勇敢地面对过去、走出创伤。
作为女儿,她秉承孝义,对母亲百般照顾。父亲的自杀对母亲妮娜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因担心母亲的生活问题,丽昂把母亲接到纽约来一起居住,尽可能地满足母亲的一些愿望。作为妻子,她贤惠聪敏,全心全意。当“9·11”发生后,基思却毫不犹豫地带着满身的创伤,“一个满身尘土、满身碎片的男子”[3],回到已分居妻子的家中。母亲妮娜强烈反对丽昂接受基思,但丽昂没有丝毫犹豫,帮助他疗伤、照顾他,并尝试了解基思的思绪,试图帮他恢复以前的形象。后来丽昂试图谈论起他们复婚的事,基思一口否认,“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丽昂并没有因为基思说出的这些刺耳的话语而放弃复婚的打算。尽管她知道,把丈夫和男人放在一起完全是另外一个词。在最后,丽昂也表明她的态度,为了家庭,他们两个能够避免摩擦,过着幸福的生活。作为监护人,丽昂同时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一方面,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她必须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儿子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能够健康成长,她时刻关注儿子的思想动态,尽管有时会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而劳累至极,但她从未放弃过。她会时常带儿子去书店,享受凉爽和清净,“他们浏览了科学、自然、国外旅行和文学图书。”[3]也会时常关心儿子的学习状态,“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自从双子塔倒塌后,儿子和他的小伙伴时常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是否会有恐怖活动发生。为了尽可能减轻儿子的焦虑,丽昂及时了解儿童眼中的“比尔洛顿”,试图引导儿子少说单音节词语,和儿子调侃、开玩笑。“这可不是你在学校里学的哦。是我告诉你的哦。”[3]看似这样的调侃并带有一点戏谑的意味,实际上包含着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在丽昂和基思的引导下,贾斯廷较少运用单音词词语,说话也变得顺畅、流利。作为一名社会人,丽昂在关注自己家庭成员的同时,更是毫无怨言地做起社区义工工作。在面对一群阿尔茨海默病人的时候,丽昂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倾听和讲述现在是挽救他们的办法”[3]。她经常组织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讲述个人经历,并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通常,她和组员们讨论,谈一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他们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分发印有格子的便签纸和圆珠笔,让他们写作文。”[3]她尊重这些老人,与他们建立联系并互相理解。在一次次的倾诉中,老人的焦虑得以释放,精神获得解脱。在倾听时,那些老人同样要求丽昂将她自己的经历说出来。通过这些倾诉,丽昂也得到了释放。
3 结语
在男性不负责任,甚至缺席的情况下,女性勇敢承担起对个人、家庭、社会的责任。劳伦在经历丈夫自杀的严重家庭创伤后,出现过创伤症候——孤独自闭、幻听。但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通过人体艺术的表演获得救赎,重建自我,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丽昂在丈夫逃避家庭后,勇敢地担当起家庭顶梁柱,对儿子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她充当老年痴呆症人群的倾听者,帮助他们走出创伤。总之,在这两部小说中,德里罗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理想人格气质。女主人公面对巨大的家庭创伤,敢于面对现实,实现自我救赎,追求生命的蜕变。
[1]张加生.从德里罗“9·11”小说看美国社会心理创伤[J].当代外国文学,2012(3):77-85.
[2]唐·德里罗.人体艺术家[M].文敏,译.南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3]唐·德里罗.坠落的人[M].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