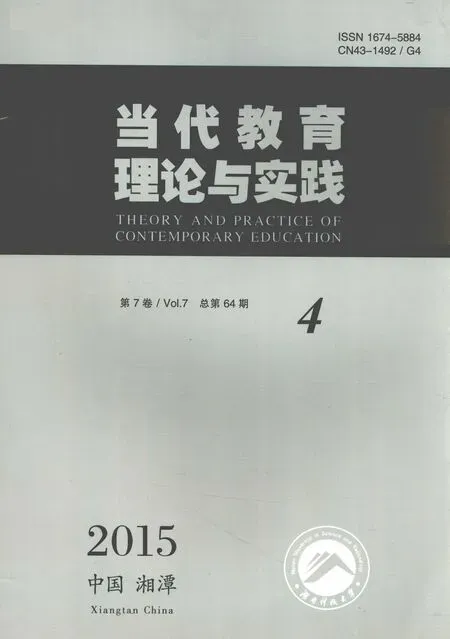语内偏误成因探析
陈凡凡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从偏误生成原因分,二语偏误有语际偏误、语内偏误和认知偏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人们主要研究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并认为母语干扰是导致二语习得困难和偏误产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1]。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内偏误才是二语的主要偏误[2]。但相比而言,语内偏误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其生成原因也总是被简单地归结为目的语过度泛化而不再细分。从二语偏误语料看,被归为过度泛化的偏误其实彼此间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对语内偏误进行剖析,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造成语内偏误的深层原因作分类论述。
1 语内偏误成因类别
1.1 错误类推
学习者简单认为目的语中形式与语言点P相似的另一语言点Q与P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因而将P的用法类推到Q上来,从而导致偏误。如动词重叠的错误类推:
(1)我们每天晚上喜欢到珠江旁边散步散步。(英语)①本文例句除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山大学中介语语料库。例句后括号中“英语”指该例句由英语母语者输出。下同。
(2)每个星期,我给妈妈打电话,谈话谈话。(俄语)
学习者学过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ABAB,碰到表面形式相似的双音节动宾离合词,以为都是双音节,都为动词,重叠形式也必定一样,于是便输出了“散步散步”“谈话谈话”这样的偏误。
错误类推是导致语内偏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学习者,尤其是成人学习者,经常通过比较已有目的语知识来类推获取新知识。这是探索新知识的有效手段,但是,语言的复杂度往往超越了学习者所能类推的认知范围,大量偏误因此产生。
1.2 错误理解
学习者学习了某个语言规则,但由于对句子结构理解分析错误,造成该语言点运用错误。如:
(3)在我们国家也我们吃米饭。
(4)这些中国节日活动也我参加过。
上面2 例实际上是学习者知道副词“也”应置于主语之后,但却错误分析了句子结构,把句首状语、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等当成“也”的主语,把“也”置于其后,导致偏误。这体现了学习者的一种输入处理原则:一般习惯把句子中的第一个名词当成动作执行者[3]。换句话说,“错误理解”实际是对目的语输入的解码失误,与语言点本身规则掌握程度关系不大。因此,由此产生的偏误随着学习者目的语知识的不断完善、目的语分析能力的逐步增强会逐渐减少。
1.3 忽视同现限制
“同现限制”指“有些句法分析的模式中,对句子成分作了限制,从而这些成分只能与某些而不能与其他成分同时出现”[4]。同现限制涉及的依存关系可以是单向的(有A 必有B,有B 不一定有A)、双向的(有A 必有B,有B 也必有A)、互相排斥的(A、B 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结构中)[5]。如果忽略这些同现限制,就会产生偏误。主要表现在音律搭配、词义搭配和语义句法搭配问题上。
1.3.1 忽视音律搭配限制(双向)
汉语重音律和谐①周小兵指出,在汉语4 音节组合中,2/2组合最常见,1/3组合很少,3/1组合几乎没有。,有时为了音律上的和谐,可以忽略语义的组合。如汉语说“三分/半钟”而不说“三分钟/半”就是为了音律上达到2/2的和谐组合,硬将“分钟”拆开[6]。音节搭配是一种双向选择限制,忽视这种音律限制,也会出现偏误,如:
(5)我洗碗用了三分钟半。
(6)我来广州两个月半。
有时,韵律和谐才是词语搭配的深层决定因素,语法规则只是某些表层因素[6]。学习者通常从词义、语法等方面考虑搭配问题,而忽略了隐藏其后的韵律因素。要想让他们注意到音律搭配的和谐问题,就必须在学习中逐渐培养汉语语感。语感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忽视韵律搭配限制导致的偏误到高级阶段还时有发现。
1.3.2 忽视词义搭配限制(单向或双向)
受词义限制,有些词只能与固定的某些词语搭配使用。忽视这种固定搭配,就会产生偏误,如:
(7)我从来没看过他做过很大的过失。(日语)
(8)随着年龄的成长,我和他说话越来越少。(印尼语)
词义搭配有时是单向限制。如例(7),与“过失”搭配的动词只能是“犯”或“出现”,而不能是“做”。有时是双向限制,如例(8),选择了“年龄”就只能用“增长”来与其同现,选择了“成长”就只能用“人”“我”“玛丽”等指人的词而不能是别的词。
选择词语搭配时,学习者往往只考虑该词符不符合句意,而忽略了与其它词语词义上的搭配限制,由此导致的偏误也是常见的语内偏误,是一种系统偏误,随着目的语水平的提高会逐渐减少。
1.3.3 忽视语义句法结构同现限制(互相排斥)
受词或短语本身语义句法功能限制,某个词或短语只能充当某些句法成分或与某些句法成分搭配,而不能与另外一些句法成分搭配。如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的语义句法功能就不同。
“更(加)”“还(要)”“稍(微)”等相对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组合后需要有比较对象②这个比较对象可以是在句中出现的,也可以是隐含于上下文的。的同现,语义才能自足。“很”“挺”“非常”“十分”等绝对程度副词与形容词组合后语义是自足的,不需比较对象。同样,如果句中存在比较对象,也不允许绝对程度副词与其同现,它们之间的选择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忽视上述限制导致的偏误,如:
(9)昨天比今天很冷。(韩语)
(10)广州的朋友比我们国家的十分忙。(越南语)
忽视语义句法结构同现限制造成的偏误持续时间各异,主要与同现限制的规则化程度有关,程度高,持续时间短;程度不高,持续时间长。
1.4 不完全规则运用
学习者因对某一语言规则掌握不够,导致运用中产生偏误。“在+处所词”在句中的位置和表达的语义相关。若强调动作发生的处所,就应置于动词前;若强调通过动作使人或事物处于某处,就应置于动词后。学习者知道“在+处所词”可于动词前或后,但没有完全习得作状语和补语时位置与语义的对应关系,有时就会产生偏误,如:
(11)蜡烛在帐子上倒了。(韩语)
(12)小时候,我经常和朋友跑在院子里,玩police和thief。(日语)
例(11)“帐子上”是动作达到的处所,应置于动词后作补语“倒在帐子上”。例(12)“院子里”是“跑”这个动作发生的处所,应置于动词前作状语“在院子里跑”。光掌握了作状语和补语时位置与语义的关系也还会出现偏误,因为动词的类别也会影响介词短语的位置。如:
(13)如果我们想要和好的时候,谁觉得错就写在一封信写几个词“对不起或者很抱歉”。(印尼语)
“一封信”可以是动作“写”到达的处所,因此可以说“写在一封信上”。但学习者不知道,“写”是一个二价动词,当他既需要介词短语当补语,又同时想引进宾语“几个词”时,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应该如何处理,于是出现上面偏误。
1.5 近似替换
当学习者所要表达的内容超过他的表达能力,或因各种原因忘了如何表达时,说话者会在知识系统内选择或生成一些与目的语意义相近的中介语,以补偿他们在语法知识或词汇上的不足。经常用来替换的有近义概念、上位词、否定概念或新造词。
1.5.1 近义替换
当表达某一概念发生障碍时,用意思相近的词替换,但因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视为偏误,如:
(14)中国打架戏很有名。(土耳其语)
(15)我在我国家的好朋友是唱歌学院的学生。(英语)
“以武打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电影、电视片”汉语叫“武打片”。例(14)中说话者不知道这个名词,便使用有“争吵打斗”意思的“打架”顶替,意思虽近但不准确。例(15)中说话者可能以前接触过“音乐学院”一词,但一时忘了,只记得是学唱歌的,因此杜撰出一个“唱歌学院”来。
1.5.2 上位词替换
用要表达事物的上位词来代替该事物,往往使表达不够准确,容易产生偏误,如:
(16)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教我们汉语。(日语)
例(16)中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但一时不知如何表达,于是选择比较熟悉的上位词“男人”“女人”。如果说例(16)中上位词的使用只能算是语用偏误的话,那么例(17)中上位词的使用明显已经导致了语法偏误:
(17)印尼人很喜欢打(拿出一个羽毛球来)运动。(印尼语)
例(17)要表达的显然是“打羽毛球”这项运动,但“羽毛球”一词对学习者来讲是一个较为陌生的词语。在说了动词“打”后发现后续词语的表达有困难,这时除了借助工具外,学习者立刻搜索出一个上位概念词“运动”来替代。
1.5.3 否定替换
借助相反概念和否定词来补偿表达缺陷也是“聪明”的学习者使用的一种办法。有时这种“小聪明”可以帮上一忙,如将“这是错的”换成“这是不对的”。但有时却会帮倒忙,如:
(18)——你去四川,那里天气怎么样?
——嗯……不好,不……太阳,嗯……raining。(德语)
显然,否定词“不”是不能直接加在名词前的。例(18)的否定替换尽管传递了一定的信息,但却导致了语法偏误。否定替换还可能导致语义偏误,如:
(19)上海的天气,不干燥,所以我不习惯,衣服很多水。(韩语)
“干燥”是形容词,可受“不”修饰,语法上没错。但从后半句可看出,说话者想表达的是“干燥”的对立面“潮湿”。可是,“不干燥”并不等于“潮湿”。这种偏误光看单个句子,语法没有问题,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发现偏误所在,因此此类偏误常常被忽略。
1.5.4 造新词语
说话者在找不到近义词、上位词替换,又没法用否定词和反义词连用时,便会根据一些已学知识自己创造出一个新词,如:
(20)妈妈每天每天干活,我想这是她的好点。(越南语)
(21)她是个我的非常好的母亲,而又是个我的知己人。(日语)
例(20)中说话者可能听过“优点”“缺点”,但记忆不牢固,用时便自创了一个“好点”。例(21)中说话者接触过“知己”一词,以为表人通常还得带个“人”字,像“好人”“工人”,于是自作聪明造出个“知己人”。
1.6 迂回表达
所谓“迂回表达”是指学习者用一些累赘的、不甚确切的词语迂回曲折地表达汉语一个词可以概括的意思,如:
(22)我们坐水里开的车去玩。(越南语)
(23)我们送奶奶去养老人的地方。(印尼语)
“水里的交通工具”汉语用“船”表达。例(23)中说话者想表达的意思可概括为一个词“养老院”。
2 结语
上述六类是语内偏误的主要成因。由前四类引起的偏误大致属于Carl James[7]的学习策略偏误,规律性较强,大部分是一种系统性偏误,教师可根据偏误形成的原因对学习者的偏误进行有针对性的纠正和解释,如果讲解恰当,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由后两类产生的偏误大致属于Carl James的交际策略偏误,任意性较大,主要是一种系统前偏误,教师可根据学习者的习得水平和偏误产生原因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或及时指出,抑或纠正并解释,不同层级的学习者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效果较好。
不过,有时这些偏误成因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有的偏误也可能由多个原因导致,本文的分析旨在帮助人们对二语习得的各种语内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1]Ellis R.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周小兵,李海鸥.对外汉语教学入门[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3]Van Patten B.Input Processing and Grammar Instru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6.
[4]Richards C J.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M].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周小兵.学习难度的测定和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2004(1):47.
[7]James C.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Exploring Error Analysis(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中的错误:错误分析探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