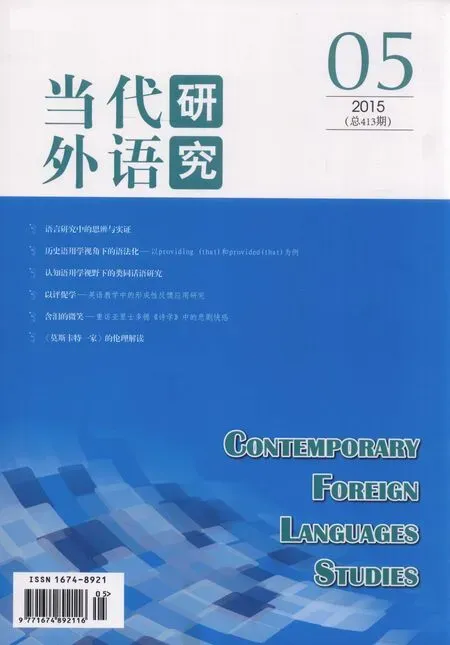含泪的微笑
——重访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快感
何伟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含泪的微笑
——重访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快感
何伟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其他古代的文本一样,因年代的久远和文本的残缺,令今人阅读理解起来感觉困难重重,甚或出现严重误读的情况。历来各种学说为“悲剧快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与其相连的“怜悯”和“恐惧”这两个词一直成为学术的竞技场,各类解释“累层”起来可以构成一部“悲剧快感”的演变史。本研究尝试不受“悲剧快感”演变史的束缚,从古希腊时期对“痛苦的欢笑”的共识及亚里士多德有关快乐的理论出发,结合他本人在《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修辞学》中的相关思想,来分析《诗学》中的悲剧快感,探寻悲剧“特有的快感”的深意。
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快感,怜悯和恐惧,疏导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快感”,诚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时的孔子》中所说的研究对象“孔子”:“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就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顾颉刚1982:131)。从如雷贯耳的大哲学家,到名不经传的文学批评家,无不对悲剧快感做出或富有哲思或离奇古怪的分析。从心理距离说、恶意说到同情说,各种学说不一而足;“悲剧快感”真的是“跟着他们变个不歇”。与“悲剧快感”相连的短短的两个词“怜悯”和“恐惧”,诚如朱光潜(2008:78)所言,“一直成为学术的竞技场,许许多多著名学者都要在这里来试一试自己的技巧和本领,然而却历来只是一片混乱”。借用顾颉刚先生的“累层说”概念,他们的解释“累层”起来可以构成一部“悲剧快感”的演变史。
毋庸讳言,对于“悲剧快感”,论者莫衷一是,各派争论不休。一部文学作品问世之后,就如同飞出笼子的小鸟收不回来了,或者说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Horace 1998:76),T.S.艾略特(1958:57-58)甚至认为:“同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是不同的,所有的理解或许都不同于作者本意,读者的解释可以不同于作者的,而同样有效,且每或胜于作者本意”。这正如钱钟书(1993:615)指出的,“‘诗无通故达诂’,已成今日西方文论常识”。诗歌一经发表,便不再受作者的控制,批评家和阅读者可以对它有不同的阐释,这里的多重含义(ambiguities)是因诗歌语言比普通语言含义更为丰富的缘故(Eliot 1958:58)。《诗学》虽说是一部论述诗歌的经典著作,但作为一部哲学家写就的理论著作,其中的概念不仅与诗歌中所用的词语迥然有别,而且往往有着严密而又精深的含义,这种含义还与同一作者的其他著作互证,尽管亚氏的著作如罗素(1988:143)指出的那样,不乏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诗学》和其他古代文本一样,因年代的久远和文本的残缺,今人阅读理解起来会困难重重,甚或会出现严重误读的情况。对于像“悲剧快感”这样的关键词,如果我们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它从文本中割裂出来,忽视它产生的环境和条件,那么它“即便不是毫无意义,也很可能使人产生误解”(Atkins 1934:3)。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就指出,人们对古希腊文本的理解出现了很多误读。本文尝试不受“悲剧快感”演变史的束缚,从亚里士多德有关快乐的一般性理论以及古希腊时期对“痛苦的欢笑”的共识出发,结合他本人在《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和《修辞学》中的相关思想,来分析《诗学》中的悲剧快感,着重探寻悲剧“特有的快感”的深意。
1.
亚氏关于快乐的一般性理论主要出现在《伦理学》的第七卷和第十卷当中。在第七卷的讨论中,他的理论核心是把快乐视为一种活动。他在“纯粹的”快乐与“偶性的”快乐之间做出区分,因而也在本身就是纯粹快乐的实现活动与那些只在偶性上令人愉悦的活动之间作出了区分。纯粹的快乐是指那些属于我们的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它是“不包含痛苦或欲望的快乐(如沉思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处于正常的状态而不存在任何匮乏情况下的快乐”(亚里士多德2003:219)。除了沉思的快乐之外,这类快乐还包括感知的快乐、推理的快乐,等等。偶性的快乐是由摆脱痛苦、纠正错误或与此类似的事情引发的。向正常品质的回复则是使匮乏得到充实的过程:“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以总体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而在向正常品质回复过程中,我们甚至从相反的事物,例如苦涩的东西中感受到快乐……快乐既是实现活动,也是目的。快乐不是产生于我们已经成为的状态,而产生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运用。快乐也不是都有外在的目的的,只有使我们的正常品质完善的那些快乐才有这样的目的”(同上)。也就是说,快乐是由活动导致的,引起快乐的活动以快乐结束。快乐使整个事情完满。
在第十卷的讨论中,亚氏的理论核心则在于快乐是完善活动。他在第四节“快乐与实现活动”中指出:“对每种感觉来说,最好的实现活动是处于最好状态的感觉者指向最好的感觉对象时的活动。这种实现活动最完善,又最愉悦。因为,每种感觉都有其快乐。思想与沉思也是如此。最完善的实现活动也就最令人愉悦。而最完善的实现活动是良好状态的感觉者指向最好的感觉对象时的活动”(同上:298)。由于实现活动不同,它们的快乐也就不同。每种实现活动都有其特殊的快乐,一种活动特有的快乐必定与另一种活动的不同,即快乐因实现活动的不同而迥异。比如,“视觉在纯净上超过触觉,听觉与嗅觉超过味觉,它们各自的快乐之间也是这样”(同上:301)。实现活动为它自身的快乐所完善,而为异己的快乐所破坏。“当一种实现活动伴随着快乐时,我们就判断得更好、更清楚”(同上:300)。例如,如果喜欢几何,我们就会把几何题做得更好,就对每个题目有更深的体会。有些实现活动会被其他的快乐所妨碍。比如爱听长笛的人听到长笛的演奏就无心继续谈话,因为他们更喜欢听长笛演奏而不是谈话,所以听长笛的快乐妨碍谈话的活动。
就以悲剧或史诗为主要代表的诗歌而言,虽说“人情乐极生悲,自属寻常,悲极生乐,斯境罕证”(钱钟书1999:884),但其中呈现出来的苦难能够给观众或读者带来快乐,即一种“含泪的微笑”,这在古希腊时期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哲学家和诗人的共识。关于这种情感体验的描写早就出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如第二十四卷中的“然而当阿基里斯享尽痛苦的欢乐时”(Homer 2003:525)。柏拉图毫无争议地把荷马描述的这种混合快乐接受过来,并且至少用在他的两个对话中。他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指出:“当我们听荷马或某一悲剧诗人摹仿某一英雄受苦,长时间地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你知道,这时即使是我们中的最优秀人物也会喜欢它,同情地热切地听着,听入了迷。我们会赞成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柏拉图1996:405)。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悲剧或史诗呈现出来的是苦难,而观众从中得到的是快乐;其二是诗人所采用的手段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柏拉图随后指出:
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理由是:它在看别人的苦难,而赞美和怜悯别人——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而又表现出极端痛苦的人——是没有什么可耻的。此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全然是好事,它是一定不会同意因反对全部的诗歌而让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在那些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同上:405-06)
柏拉图认为观众能够从别人的苦难,以及从赞美和怜悯别人中得到快乐。他认识到这种从摹仿中得到的快乐,不仅是来自令人愉快的情境,而且也来自引人哀怜的情境,尽管他不赞同甚至鄙视这类快感,因为在他来看,诗歌通过挑动情感,制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通往这类情感的危险途经,进而毒害人的灵魂,应当被控制。他在《斐莱布篇》中谈到这种快乐和痛苦的结合,比如愤怒、恐惧、悲哀、爱情、妒忌、羡慕等等,都是在痛苦中又结合有快乐的。人在观看喜剧时往往是在快乐中又感到痛苦,“还有,你记得人们在看悲剧的时候既欣喜又流泪吗?”(柏拉图2003:234)。对旁人的痛苦感到乐趣,对别人的无知——他不能“认识自己”,或是对自己的智慧、财富、美貌等想得过分,就相当滑稽可笑。“无知本是一种痛苦,但嘲笑它时却得到快乐”(汪子嵩等2004:1006)。柏拉图所言的观看悲剧时那种“含泪的微笑”的情感体验是欣赏悲剧时的核心体验。
亚氏的《诗学》是对柏拉图攻击诗歌的最初回应。他拒绝全盘接受柏拉图关于情感的思想,但两人在有关诗歌的不少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立场,其中之一就是尽管他们对待快乐的态度迥异,但两人都认为诗歌无论是作为一种摹仿,还是通过摹仿手段挑起情感,均会给人带来快感。亚氏承认悲剧能够给人带来快感,他在《诗学》中至少十次以上用不同的词语提及悲剧给人带来的“快感”,不过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这其中有的是悲剧特有的快感,有的只是一般性的快感,后者同样可以由史诗和喜剧引发。
2.
在亚氏《诗学》中有关悲剧快感的论述中,既包含着悲剧定义中提及的一般性快感,也包含与亚氏快乐理论及当时的悲剧实践相关的其他一般性快感,而这些都不是他所指的悲剧特有的快感。在第6章中关于悲剧的定义中,至少有三种是一般性快感: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导。所谓“经过装饰的语言”,指包含节奏和音调[即唱段]的语言,所谓“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不同的部分”,指剧的某些部分仅用格律文,而另一些部分则以唱段的形成组成。(亚里士多德1996:63)
这个关于“悲剧”的定义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悲剧快感。亚氏首先指出悲剧是一种摹仿,与此相应的是认知快感和由摹仿技巧引发的快感。他在第4章中指出,“在生活中讨厌看到的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同上:47)。亚氏强调摹仿带来的快感是某种从学习中得来的快感,这是一种认知快感。他认为“求知不仅对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同上)。这是因为理解摹仿要涉及到运用人的认知能力,这是人的一种本能。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并可就每个具体形象进行推理,“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同上)。亚氏进一步指出一种由摹仿技巧引发的快感:“如果观赏者从未见过作品的原型,他就不会从作为摹仿品的形象中获得快感。在这种情况下,引发快感的便是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同上)。这里的摹仿技巧也就是前文中所引柏拉图所谓的“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采用的手段。上述快感是悲剧快感,来自艺术家的摹仿,但它们却不是悲剧特有的快感,因为同样存在于喜剧中。伴随认知快感和由摹仿技巧引发的快感的,是某些中性情绪,而不是怜悯和恐惧。
除了摹仿之外,亚氏在悲剧的定义中格外强调悲剧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即指能够给观赏者带来快感的“包含节奏和音调的语言”(同上:63)。在同一章中的最后一段里,亚氏说:“唱段是最重要的‘装饰’”(同上:65)。也就是说,它是快感来源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经过“装饰”的语言在悲剧中同样会引发快感。这是一种文本快感。亚氏在第4章中有言道:“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格律文显然是节奏的部分)”(同上:47)。因此,它们和摹仿一样,对一般人来说同样是一件快乐的事。在第26章中,亚氏在对悲剧和史诗进行比较时还指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快感来源:“悲剧有一个分量不轻的成分,即音乐[和戏景],通过它悲剧能以极生动的方式提供快感”(同上:191)。不过,亚氏对戏景的评价不高,认为它虽然能吸引人,却“最少艺术性,和诗艺的关系也最疏远”(同上:65)。无论是音乐感和节奏感,还是经过“装饰”的语言、唱段,或者音乐和戏景,这些文本快感的确是悲剧快感,但同样不是悲剧特有的快感。它们不是由怜悯和恐惧情绪引发的,同样存在于喜剧当中,而且它们也不是由摹仿引发的,即不是由悲剧情节带来的。
除上述悲剧定义中由认知、模仿技巧和文本引发的快感之外,还有两种一般性快感。其一是亚氏快乐理论中提及的一种快感。在他看来,沉思高贵的对象同样会引发快感。悲剧摹仿的,正是高贵的对象和行动,如亚氏在《诗学》第2章指出的,“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同上:39)。他在第6章提到:“就以格律文的形式摹仿严肃的人物而言,史诗‘跟随’悲剧”(同上:65)。不过,只有在人物没有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的情况下,沉思这类高贵的人物才会引发快感。因此,这种快感不是取决于怜悯和恐惧。其二是在当时悲剧实践中常见的悲剧复线情节给观众带来的快感。这类复线情节往往有奖善惩恶的大结局,这与观众的心理诉求一致,因而受到欢迎。在《诗学》第13章结尾论及第二等的情节时,亚氏指出《奥德赛》中有两条情节发展线索,到头来好人和坏人分别受到赏罚,观众喜欢这样的情节,但这类情节给观众带来的却不是悲剧特有的快感。这是诗人“被观众的喜恶所左右,为迎合后者的意愿而写作。但是,这不是悲剧提供的快感——此种快感更像是喜剧式的”(同上:98)。对这类情节,柏拉图在《法律篇》第二卷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反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氏的《诗学》中,诸如认知快感、由摹仿的技巧引发的快感、文本快感、沉思高贵的对象引发的快感、复线情节带来的快感,等等,虽然都可以包含在悲剧快感这个含义较为宽泛的概念之下,但它们不是由怜悯和恐惧情绪引发的,均是一般性快感,而不是悲剧特有的快感。显然,在亚氏的诗学思想中,除了一般性快感之外,悲剧应给人带来一种由它才能引发的快感。亚氏还强调史诗也与悲剧一样,应给人一种由它才能引发的快感,如他在第23章指出史诗“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同上:161)。他只在第24章指出悲剧和史诗“提供的不应是出于偶然的,而应是上文提及的那种快感”(同上:191)。他没有明说适合史诗的那种特有的快感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快感。
3.
亚氏《诗学》中悲剧特有的快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明显不同于其他艺术带来的快感。其独特之处在于悲剧摹仿的对象是在实际生活中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情感和情境,而快感正来源于对此的摹仿。悲剧诗人既非通过消除其中令人痛苦的元素,也非通过在他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痛苦,来达致给人带来快感的效果。他运用自己的艺术技巧,通过他使人的思维进入同情之境的力量,将思考、情感和视听等感官作用于原本只会引起痛苦的主题上,进而引发纯粹的快感。亚氏多次指出,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能够引发快感,有的诗人错误地运用其才思,使一些让人痛苦的主题依然如故,给人带来的情绪毫无快感可言。在某种程度上,悲剧快感类似于朗基努斯论及的崇高语言和思想在一部作品中所产生的效果:“崇高的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一个崇高的思想,如果出现在恰到好处的场合,就会如黑夜中的闪电照亮一切,在刹那之间显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Longinus 1998:81)。因而,悲剧中有无这种快感是衡量一部悲剧之高下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悲剧快感是指悲剧特有的快感。
《诗学》对悲剧特有的快感的最直接阐述出现在第14章:“我们应通过悲剧寻求那种应该由它引发的,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快感。既然诗人应通过摹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那么,很明显,他必须使情节包蕴产生此种效果的动因”(亚里士多德1996:105)。这一段阐述表明悲剧特有的快感不只是来自观众或读者被挑起的怜悯和恐惧情绪,或者是来自摹仿,而是同时来自这两者,正如豪斯指出的,“很可能是说只有通过摹仿的手段,怜悯和恐惧才有可能成为快感的来源”(House 1956:116)。仅仅通过摹仿的手段所得到的快感,如前文所述,当属于一般性的快感,而从体验怜悯和恐惧中得到快感,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在《诗学》中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的这两种情感本身往往是与痛苦相关的。
亚氏在《修辞学》中把恐惧定义为“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并进而指出:“人们并不畏惧一切祸害,而仅仅畏惧足以导致很大痛苦或毁灭的祸害,只要这种祸害不是隔得很远,而是近在身边,迫在眉睫,因为人们并不畏惧非常遥远的祸害”(亚里士多德2006:88)。怜悯的定义与恐惧密切相关:怜悯是“一种由于落在不应当受害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或引起痛苦的、想来很快就会落到自己身上或亲友身上的祸害所引起的痛苦情绪。因为,很明显,一个可能发生怜悯之情的人,必然认为自己或亲友会遭受某种祸害,如定义中提起的这种祸害或与此相似的或几乎相同的祸害”(同上:97)。我们恐惧的一切事情,“如果落到别人身上,就都能引起怜悯之情”(同上:98)。毫无疑问,怜悯和恐惧会引发痛苦,如果我们假设怜悯和恐惧能够引发快感,那么这种快感必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快感。亚氏关于悲剧的定义为我们提示了这两种情绪与悲剧特有的快感之间的关系。
亚氏在悲剧的定义中指出,悲剧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导(katharsis)”①。弥尔顿在对其进行解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拥有引起怜悯和恐惧或者恐怖的力量,疏导思想中的那些情绪,以及类似的情绪。也就是说,以某种快乐来调节和改变由阅读或观看那些被惟妙惟肖地摹仿的情绪,使之达到适当的程度”(Milton 1999:619)。不过,弥尔顿在这里把“快乐”更多地与精湛的摹仿技艺,而不是与疏导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上一节的讨论中知道,悲剧中通过摹仿的手段得来的快感属于一般性快感,不是悲剧特有的快感,因为史诗或者喜剧同样可以通过摹仿引发这种快感。毋庸置疑,悲剧定义中那个含义扑朔迷离的“疏导”成了理解悲剧特有的快感的关键词。
亚氏关于“疏导”理论的说明与医学、宗教和诗歌均相关(Hardison 1968:133)。在医学中关涉的是人的身体状态,在宗教和诗歌中是人的情感状态,具体到悲剧中则是怜悯和恐惧的悲剧状态。亚氏曾在《政治学》中提到:“我们姑且先引用‘疏导’这一名词,等到我们讲授《诗学》的时候再行详解”(亚里士多德2012:437)。然而,在《诗学》中仅有的一次提及这个词就是在悲剧的定义中。因此,我们可以用他在医学和宗教上使用的“疏导”来帮助理解在诗歌中使用的“疏导”及其与悲剧特有的快感之间的关系。
就医学而言,“疏导”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用药物来排空某物,含有“净化”(purification)之意;其二是身体上发生的某种变化,回复到某种平衡状态,如热冷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以达到一种健康状态。在亚氏创办的学园里,有人稍晚于《诗学》写了一本名为《问题》的书,里面有关于冷热问题的论述,指出人体内黑色胆汁的冷和热直接与人的情感相关,据说黑色胆汁冷总是伴随着“绝望和恐惧”的情绪,而回复到正常的温度则能够矫正这种状态(House 1956:106)。亚氏在《诗学》中使用的“疏导”常被认为有与医学上的“疏导”相关的两种隐喻:其一是就像医学上那样用排泄药来排空某物,如F.L.卢卡斯在《悲剧》中不容置疑地强调这个词“绝对是一个医学隐喻——一种排泄药的隐喻”,并且用他那句令人难忘的隽语道出了他对该理论的深深厌恶:“剧院不是医院”(Lucas 1957:24)。不过,亚氏在《诗学》中从未在任何地方暗示过,指望去剧院疏导怜悯和恐怖的情绪是观众去看悲剧的原因(House 1956:113)。其二就是观看悲剧能够让观众的情绪回复到某种平衡状态。在意识和潜意识中存在着与黑色胆汁冷热类似的情况,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称的“反转”(anantiodromia)之说,即“意识中有偏向,则潜意识中能生相剋之反向”(参见钱钟书1993:612)。在情感和观念中,情况也不例外:“所谓情感中只有辩证,较观念中之辩证愈为纯粹著明”(钱钟书1999:1058)。这正如《老子》第40章中的“反为道之动”。
就宗教而言,亚氏最著名的论述出现在《政治学》卷八中论及音乐的用处时,他指出音乐可以疏导狂热的宗教情感。有些人的心灵对怜悯、恐惧、激动这类情感有着特别敏锐的感应,一般人也会有同感,只是或强或弱,程度不等而已。某些人尤其易于激起宗教灵感,而音乐则对他们狂热的宗教情感有疏导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己,几而苏醒,回复安静,好似服了一贴药剂,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亚里士多德2012:437)。同样,音乐也可以在另一些特别容易感受恐惧、怜悯、或其他任何情绪的人们那里引致同样的效果;对于其余的人,依各人感应程度的强弱,实际上也一定发生相符的影响。于是,“所有的人们全都由音乐激发情感,各各在某种程度上疏导了沉郁而继以普遍的怡悦。所以这些意在消除积悃的祭颂音节实际上给予我们大家以纯真无邪的快乐”(同上:437-38)。
就与此相关的悲剧的功能和目的而言,“疏导”是根本性的,它不是仅仅作用于观众中为数不多的情绪特别敏感者,而是作用于全体观众。“疏导”对情绪特别敏感者有治疗作用,能帮助缓解他们不适当地感受到怜悯和恐惧的压力,让他们回复安静,也可以对其余的人产生相应的影响。“疏导”之所以能“继以普遍的怡悦”,是因为回复到自然或健康的状态是令人怡悦的,正如前文中亚氏有关快乐的一般性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在对情感的疏导中存在着快乐,那么它必定是一种“偶性的”快乐,而不是“纯粹的”快乐。不过,通过这种方式,人感受“纯粹的”快乐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同时,亚氏在《伦理学》中还指出:“那些激起正常本性的活动的事物,则是本性上令人愉悦的”(亚里士多德2003:225)。我们由此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亚氏的诗学理论中,情感的疏导是引起悲剧特有的快感的唯一原因。有学者借用弥尔顿的《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中的最后一行诗,指出读者或者观众在看完一部悲剧之后终于获得“心绪宁静,所有激情燃尽”之快感,悲剧正是以这种快感吸引人的(House 1956:113)。然而,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原意相悖,也与人之常情不符。观众看完悲剧的感受既非暴风雨过后的宁静,亦非所有情绪宣泄完了之后的畅快。
4.
在亚氏看来,“疏导”并不是把某种情感或情绪清除出去,我们应当适当地感受到怜悯和恐惧的情绪。悲剧中适当的快感既为观众中那些情绪特别敏感者,也为其中最正常者而存在,因为在“疏导”的作用下,悲剧的情感体验不是增加而是削减了敏感者的极端情绪,使之达到适当的程度。而这个“适当”与他更具普遍意义的“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相一致,也与悲剧特有的快感中另一层深意相关。悲剧中特有的快感除了上述因疏导而能“继以普遍的怡悦”之外,还有怜悯和恐怖情绪因疏导而达到一种中庸状态,这种状态由于符合道德德性而给观众带来一种纯真无邪的快乐。
亚氏对这一思想的最清晰表述出现在《伦理学》卷二中。他首先指出每一个匠师都避免过度与不及,而寻求和选择一个适度:“这个不是事物自身的而是对我们而言的中间。如果每一种科学都要寻求适度,并以这种适度为尺度来衡量其产品才完成得好(所以对于一件好作品的一种普遍评论说,增一份则太长,减一份则太短。这意思是,过度与不及都破坏完美,唯有适度才保存完美)”(亚里士多德2003:46)。亚氏继而指出,道德德性也同自然一样,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原因在于“道德德性同情感与实践相关,而情感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同上:47)。亚氏以人们感受到的恐惧、勇敢、欲望、怒气和怜悯等情感为例,说明这类情感给人带来的快乐与痛苦都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都不是德性的品质。具体就“勇敢”而言,勇敢的人是处于过度恐惧和过度鲁莽之间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该经受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同上:80)。在亚氏看来,只有“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品质”(同上:46-47)。他在《政治学》中将这种思想扩大及万事万物:“我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当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2012:439)。
就欣赏悲剧而言,观众感受到怜悯和恐惧的情绪,这种行为不仅因“疏导”而给他们带来“怡悦”,还因符合德性而给他们带来纯真无邪的快乐,这里在亚氏的假设中观众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德性者。他在《伦理学》中指出:“快乐是灵魂的习惯。当一个人喜欢某事物时,那事物就会给予他快乐……公正的行为给予爱公正者快乐,合德性的行为给予爱德性者快乐。许多人的快乐相互冲突,因为那些快乐不是本性上令人愉悦的。而爱高尚的人以本性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活动既令爱高尚的人们愉悦,又自身就令人愉悦”(亚里士多德2003:23)。
人们喜欢做自然的事情或在过去的经验中自然形成的东西,因此爱高尚的人喜欢做合德性的活动。怜悯和恐惧是对悲剧中令人怜悯和恐惧的事件的适当反应,所以对悲剧做出怜悯和恐惧的反应,对于爱高尚的人而言,就是进行合于德性的活动。作为一种合于德性的活动,这种反应对于爱高尚者就是令人愉悦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怜悯和恐惧是在悲惨的情境中被适当感受到的情绪,而这类情境与愉悦的情绪发生冲突,这种情况正如亚氏在《伦理学》中论及勇敢与快乐和痛苦的关系时指出的,勇敢的行为原则上对于勇敢者来说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周围令人不愉悦的环境“掩盖”了这种愉悦:“在引起恐惧的事物面前不受纷扰、处之平静,比在激发信心的场合这样做更是真正的勇敢……人们有时就把承受痛苦的人称作勇敢的人。所以勇敢就包含着痛苦,它受到称赞也是公正的,因为承受痛苦比躲避快乐更加困难。不过勇敢的目的却似乎是令人愉悦的,只是这种愉悦被周围的环境掩盖着”(同上:87)。然而,由于悲剧是一种摹仿,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剧中悲惨的情境令观众深深地感受到怜悯和恐惧的情绪,这种反应是合德性的活动,观众从中获得的愉悦,而剧中悲惨的情境又不与这种愉悦发生冲突。
亚氏的疏导理论既是他对柏拉图对诗歌的攻击的反驳,也是他为诗歌所作辩护的基本元素之一。对于诗歌挑起人的情感,亚氏非但不反感,而且认为情感不应当被抑制,抑制只会适得其反,使情感变得更为强烈。当然,情感也不应当不加控制,任其自由发展或许会导致混乱或狂热。人应当把握好一个度,用恰当的方式调节好情感,使其被适当地感受到。对于狂热的宗教情感,人们可以通过宗教仪式或音乐来加以疏导,继而使之回归到一种正常的平衡状态。悲剧通过“疏导”使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情绪达致适度的状态,进而“继以普遍的怡悦”。根据亚氏的描述,这是一种“顺势疗法”,类似于“以暴易暴”的方法。简言之,悲剧带来的这种适当的快感依赖于摹仿,经由怜悯和恐怖的情感体验而来,同时又为爱高尚的观众所能够获取。悲剧“特有的快感”的深意也正在于此。
附注
①希腊语中的“katharsis”一词,因译者所持观点不同,而在英文译本中出现了“purgation”、“purification”和“clarification”等不同的译法,在中文中也有“疏导”、“净化”和“祓除”等译法。笔者倾向于认同“疏导”的译法,但“疏导”难以完全涵盖“katharsis”一词的含义,特别是在医学和宗教方面。
Atkins,J.W.H.1934.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A Sketch of Its Develop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iot,T.S.1958.The music of poetry[A].In J.Hayward(ed.).T.S.Eliot:Selected Prose[C].Victoria:Penguin/Faber &Faber.56-67.
Hardison,O.B.Jr.1968.Aristotle’s Poetics[M].New Jersey:Prentice-Hall.
Homer.2003.The Iliad[M].London:CRW/The Collector’s Library.
Horace.1998.The art of poetry[A].In D.H.Richter(ed.).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C].Boston:Bedford Books.68-78.
House.H.1956.Aristotle’s Poetics[M].London:Rupert Hart-Davis.
Longinus.1998.On the sublime[A].In D.H.Richter(ed.).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C].Boston:Bedford Books.81-107.
Lucas.F.L.1957.Tragedy:Serious Drama in Relation to Aristotle’s“Poetics”[M].London:Hogarth Press.
Milton.J.1999.The Annotated Milton Complete English Poems(B.Raffel ed.)[M].London:Bantam.
柏拉图.1996.理想国(郭斌和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柏拉图.2003.斐莱布篇(《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
顾颉刚.1982.古史辨(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
罗素.1988.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钟书.1993.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
钱钟书.1999.管锥编(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
汪子嵩等.2004.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1996.诗学(陈中梅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2003.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2006.修辞学(罗念生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2012.政治学(吴寿彭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光潜.2008.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玄 琰)
I109.2
A
1674-8921-(2015)05-0056-06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5.011
何伟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论和当代英国小说。电子邮箱:weiwen_he@sjtu.edu.cn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BWW05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1YJA 752004)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2011BWY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