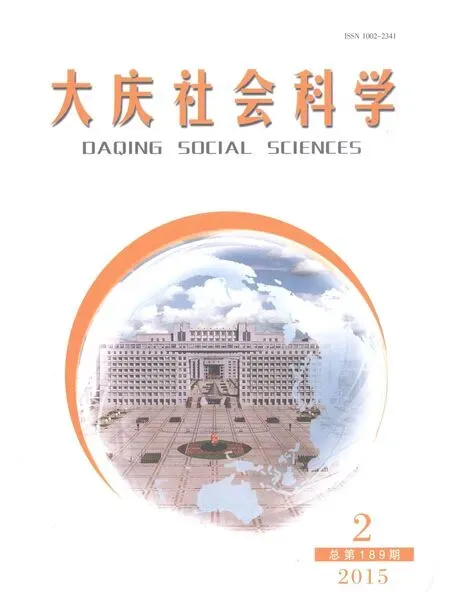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社会信仰的重塑
匡瑾璘,孙 爽,祁靖贻
(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社会信仰的重塑
匡瑾璘,孙 爽,祁靖贻
(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现代性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工具理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拥有主导性地位的理性,为了使人们的理性精神不断发扬,必然会导致对宗教的祛魅。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诉求,他们从对某一信仰的追求中脱身,继而又去追寻新的信仰来克服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信仰危机。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解读引发信仰危机的原因,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合理利用的同时将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以调制解救现代人类面临的信仰危机。
现代性;理性;信仰
不断发展着的现代社会不但给人们带来了进步与发展,同时又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不断涌现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理性是其核心。随着现代性的演变发展,由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的变革,引发了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信仰问题的出现。现代性是一种逐渐祛魅的过程,世俗化趋向与信仰超脱化的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抗衡,多元权威的要求与信仰追求终极权威的矛盾,都逐渐加深了信仰的现代性危机。
一、现代性中信仰缺失的原因
“现代性”一词出现于19世纪。学界普遍认为,法国的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是最早提出“现代性”这一词语概念的人。他认为,“现代性”一词主要是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或品质,它所强调的是现代性的感性特征。但是在哲学领域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最初就与理性相关。黑格尔主张现代主体性的自由;韦伯把现代性划分为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哈贝马斯把现代性从工具理性、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这几个方面理解;福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或一种“精神气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
在现代性不断发展演变过程里,为了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启蒙理性认为需要经过抽象的分析,把分析过的对象归纳总结为“量”,把人们所研究的现代世界看作可以量化的世界,并以此来征服世界。即笛卡尔认为的,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对于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规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1]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2]在不断探索科学知识的过程之中,启蒙理性逐渐演变成了工具理性,这里所涵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意义都有着消失的危险;然而,伴随产业革命中社会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令这些消失的危险不断增大继而演变成现实;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理性也由解放劳动者的方式逐渐演变成为压榨劳动者的方式,启蒙理性进而发展成为了技术理性,变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
在工具理性占据主导的现代社会,为了使人们的理性精神不断发扬,必然会导致对宗教的祛魅。韦伯认为,理性的出现同现代性不断发展有一定关系。并把发扬理性精神解释为“合理的”,在西方社会中这种现代性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引发宗教信仰的崩塌,进而衍生出世俗文化。由此能够看出,理性化推动了世界的祛魅,世界的祛魅化则证明了宗教神学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解脱,人类对于信仰有了自主抉择的权利。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
人类开始“用技术和理性的支配方式”来阐释和构建现代社会,不断促进宗教向世俗化转变。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原本覆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发展领域中的“神圣帷幕”被赤裸裸地揭开。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信仰的追求在经受了物欲横流的社会的腐蚀下逐步消散。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诉求,他们从对某一信仰的追求中脱身,继而又去追寻新的信仰来克服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所以,在现代性背景下,宗教的世俗化引发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信仰与个体自主性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传统宗教的制度权威日益受损于个体自主性,然而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又产生出更强烈的需求去构建新的信仰。[4]
二、现代性视域下信仰危机的表现
无论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都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信仰活动,即“了解人真正相信什么,看他们的行为比听他们所说的话更加可靠”[5]。所以,信仰是信仰个体与其信仰的对象相联系的结果,表现出信仰者对于信仰对象的追求,以求对物质世界的僭越。因为发生了相互联系,所以肯定存在运行的方法,也就是说信仰者怎样突出其对于信仰对象的追求,反之信仰对象又以怎样的方式来吸引信仰者。由此可以看出,信仰有三个基本构成点:信仰者、信仰对象、信仰方法。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现代社会信仰的基本状态,同时也影响了信仰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信仰危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相对而言更关注信仰对象,认为信仰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信仰对象权威性的丧失,为解决信仰问题,更换信仰对象似乎成为更多数人的选择。但要看到的是,并非所有信仰危机都是由信仰对象引起的,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中,引发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仅仅把原因归咎于信仰对象,只是从对象的变更来考虑,反而不能真正舒缓和解决危机。
一方面,现代性崇尚主体性的自由,主张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过度的个体化、独立化,导致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锐减,使个人脱离群体生存,容易使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发展,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最高目标,衍生出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群体生活与社会活动是个人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极端个人主义主导下,这二者被个体忽略,甚至排斥,最终导致个人的孤立无援,对生活丧失信心,对信仰产生动摇。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过分推崇工具理性,认为自身能够控制通过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物质生产资料,甚至仰仗工具理性来处理人们自身的信仰问题。正是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依赖,使人们放松警惕,不去考虑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最早察觉出理性在不断畸形发展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他认为人们把理性运用在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理性也同时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范畴,主宰了人们的欲望。最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失去了主体性、创造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由主体转变为客体,人们变为异己的运转着的机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处于一个异化和物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导致信仰放弃了自身的超越性,不断走向低俗的境地,商品拜物教成为信仰危机的表现之一,异化和物化以及拜物教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超越性一去不复返,信仰也失去了原有的终极关怀和指向性。按照韦伯所说,这个超越性的追求被资本替代了。最终引发了现代社会中信仰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
由此可见,“信仰危机”的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个体的自身信仰的缺失,其中,信仰缺失的具体表现为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匮乏者,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占据主导思想者,对生活充满失望、认为自身前途渺茫的对信仰动摇主义者,封建愚昧迷信甚至加入邪教者,等等。
然而,信仰危机并不一定被认为是信仰者完全丧失信仰,而是对于原来自身所主张的信仰,由于一些因素引起了自身的困惑与迷失,从而不再坚定自己的信仰。这也正是说明,人类对于自己过往的一切行为活动和信仰信念,甚至是固有的思维方式,都进行了一种重新的反省,以期追求自身认为的更适合自己的信仰。因此,人类自身的信仰在不断地升华。
三、现代性视域下信仰重塑的途径
劳伦斯·E·卡洪认为,信仰危机是能够被克服的。“需要重新注入活力。这并不意味着要回转到17—18世纪时现代性的各种信念。”他提出要用新的理念来补救,即“发现一个新的综合,一套新的观念,这些观念能够保存现代性的功绩而又不阻隔它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并且能为现代性提供一个新语境。”[6]对现代性中各种弊病与缺陷的攻克,既不能依赖于离不开资本主义文化沃土和西方文明优越感的后现代主义,也不能认为启蒙理性将神的地位取代,人类就主宰了一切,而单纯依赖技术理性为现代人创造的物欲社会而丧失了信仰,人们只是对信仰产生了动摇和迷失。要想解决现代人的困惑与迷茫,为现代人的信仰寻求出路,就需要我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价值重构以及从文化根源中寻求修补信仰缺失之方法,在对现代人信仰祛魅的同时,重塑现代人的信仰,以期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合乎人类理性的状态。
在重塑现代人信仰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为技术理性为人类带来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同时所产生的弊端与危机而完全地批判其作用,也不能由于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畏惧而拒斥现代性的发展将自身完全回归于传统文化之中。而是在对理性的合理利用的同时将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以调制解救现代人信仰迷失的良方。这首先需要对技术理性的重塑,这一方式也是对人类理性的重塑和发展。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些弊病来源于启蒙的缺陷,他提出要修补启蒙的缺陷。主张寻求主体间的共性,以防止主体对于自身的过于注重,进而使个体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充实。此外,胡塞尔提出以“主体间性”理论取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过分发展,用以防止任意的主体。他认为主体性即个性,主体间性即群体性,主体间性包含着主体性,又被译为“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是主体性之间的互识,主体间只有能够互识,达到共识。这就说明,杜绝信仰危机从根本上需要经过理性交流,并在此基础上,从中找出主体间认识的共同点以达到对人类共同信仰的重塑和完善。最终,激发主体确立一种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得以完全把握以及认识自身。雅斯贝尔斯认为,信仰是需要自由的,需要个体在生存中自身是自由的条件下,对于个体进行自我超越,他认为信仰需要通过交往使未来的自由共同体成为可能,个体只有超越自身的狭隘思想,融入群体之中,与人进行交往、交流,人类才能够求同存异,使得主体间性中的个体得以充分发展。马克思认为,要重塑现代人的信仰,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上的改变,从共产主义理想出发重塑信仰。
为了克服信仰危机,需要我们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价值重构以及从文化根源中寻求修补信仰缺失的方法。对现代性信仰的重塑也使得现代人的理性在消解与重构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升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性视阈下,为了实现信仰的重塑,不但需要从文化根源寻求解救之法,还需借助人类理性重新恢复对神圣的认知,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76、79.
[2]MaxHorkheimer,TheodorAdorno.DialecticofEnlightenment[M].NewYork:TheContinuumPublishingCorporation,1972:6、23.
[3]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4]汲喆.迈向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宗教社会学[R].社会学研究,2005,(1).
[5][英]约翰·希克.第五维度[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5、62.
[6][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敬晶〕
D64
A
1002-2341(2015)02-0095-03
2015-01-10
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风险社会语境下大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SGB2014011
匡瑾璘(1966-),女,黑龙江克山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