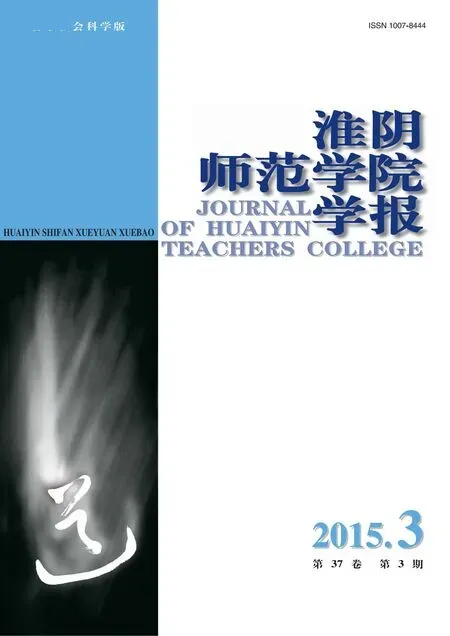建国前进化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易显飞, 章雁超
(1.中国社科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2.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一百年里,西方进化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与碰撞,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了中国的进化主义思想。鸦片战争后,国人致力于寻求救亡图存、求强求富之路。尽管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均总体上以失败告终,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并未因此而停下。幡然醒悟的有识之士认为,强国之路必由引进西学为始。在进化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对西学的传播经历了三种不同层面上的选择,即从物器层面到制度层面、最后再到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层层递进;而进化主义思想,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精神文化层面引进的第一种成体系的“西学”。
一、进化主义思想传播的时代背景与动力
自17世纪以来,与西方国家蒸蒸日上的发展进程相比,中国的发展进程显得江河日下,可谓天壤之别。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结束后,西方世界经历了“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封建社会开始土崩瓦解,掀起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潮流。政治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等各国相继在本国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与科学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经济上,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世界实现两次大跨越:从农业手工业时代迈入蒸汽时代,进而跨入电气时代,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进而开始了海外殖民扩张。文化上,西方学术,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热情与躁动,走向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产生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主义,奠定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与之相对的是,遥远而古老的中国,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崇皇帝乾纲独断,使封建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政府,在康乾时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形成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这种表面的盛世却掩盖不了日趋衰败的局面。政治上,军机处的设立以及“跪受笔录”,标志着封建皇权达到鼎盛,使得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形成的微弱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氛围烟消云散,正好与西方世界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潮流截然相反,实可谓“逆流而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更是将农民牢牢地钉死在土地上,自耕农的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扼杀了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文化上,“八股取士”和考经证史的考据学的兴起,几乎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使学术往无聊的“考古”方向发展;“文字狱”的兴盛,更使得明末清初活跃的启蒙文化氛围烟消云散,学术思想凋敝成为“盛世”之下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也因此被迫加入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尽管此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原有的社会进程被打断,走向了一条畸形而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艰苦卓绝地向西方探求真理、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被重新启动。进化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播到中国来的。强大的传播动力使它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它对中国的影响无所不至,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些传播动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自强求富和亡国灭种的矛盾,是进化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动力。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清王朝的绝大部分士子们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地大物博”的美梦中。他们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博大精深,是“夷人”所无法超越的,因此他们对于当时在西方影响力如日中天的进化主义思想视而不见,并导致进化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内因始终不充分。这里所说的内因不充分,是指中国对西学的内在需求因素和动力机制的缺失。自诩“天朝上国”的满清政府认为,无论从物器层面上还是制度层面上抑或精神层面上说,中国依然处于强盛时期并领先世界。盛世繁华之下,人们并没有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实经验有什么明显地不适。再加上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惊天巨变一无所知,因而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一致认为,中国断无必要从国外引进新的技术和文化。此外,西方先进思想向中国的传播,仅仅依靠少数传教士等外因作用,实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直到“甲午海战”乃至“庚子赔款”之时,面对现实的羞辱,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幡然醒悟,此时引进西学才有了充足的内在动因。这一内因扼要地概括起来就是:自强求富和救亡图存的需要。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时间分割点,战前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战后中国出现了时代的大转变,由独立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最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急欲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大转变必然会同时孕育挑战和机遇。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并给中华民族带来奴役、灾难和耻辱的同时,也给中国人送来了摆脱奴役、灾难和耻辱的思想武器,猛然醒悟的中国人纷纷加入“开眼看世界”的行列。此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精神文明的心态也显著转变,由不屑与唾弃转变为接受,进而趋之若鹜。至此,进化主义向中国的传播,已然形成了充分的内因和强劲的内在动力。
其次,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要求中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观念或文化。西方世界自18世纪起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变革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包括其殖民体系的形成。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对华资本输出,大肆在华倾销其工业产品,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外国商人在华投资建厂,洋务派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吸引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建厂,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华的侵略和压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华商品倾销量有所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办企业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大增,为中国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造就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的春天”。虽然出于多重因素,中国最终没有正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在中国存在并发展着,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必然要求相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或意识在中国出现。当进化主义思想在欧美大行其道并逐渐形成影响世界的进化主义思潮时,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自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再次,“甲午海战”对“体用之争”的现实回答,使中国人由“中体西用”的观念逐渐转变为“西体西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在对西学的认识和选择的实践上,经历了一个从物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从制度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洋务运动着重于对物器层面的选择,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民族工业。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使得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继而展开的是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此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着眼于制度层面的选择,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为榜样,掀起一场资产阶级的自我改良运动,结果依然以失败告终,从而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也使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认识到“体”和“用”的辩证关系。对此,严复曾做过形象的比喻和精辟的描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1]接着他又指出:“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同种人之面目然,不可谓之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西方物器层面与制度层面之所以先进,是根植于其精神文化层面的先进或发达。正如梁启超说到的:“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2]基于上述体悟,在西方学术界当红的“进化主义思想”,便首先作为精神层面的“西学”传播到中国。
二、西方进化主义思想传播的历程概况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使得源远流长的进化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严复认为,自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在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反响,不仅在欧美几乎家家有其书,而且西方学术政教也为之斐变[3]90。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揭示了生物体与外界环境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斗争过程,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科学规律,因而被誉为19世纪人类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此后,生物进化论,不仅被迅速扩展应用到自然科学领域,还影响并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发展与变革,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理论复合体。正如梁启超所言:“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4]30史壮柏格则更加强烈地提出:“演化的观点几乎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里,渗透于我们现在的思想……它已变成研究现象的正常程序……对演化的兴趣已走出学术圈,而进入到商业与工业领域。”[5]进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普遍思潮的时代,恰逢近代东、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逆转”而形成鲜明对照。当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时,引领世界潮流的进化主义思潮便被有识之士引入到国内。
(一)进化主义初传中国。
通常人们提到进化主义,首先想到的是严复的《天演论》,事实上,早在严复之前,进化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有了零星的传播。在进化主义思想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充当着重要的媒介角色和启蒙作用。
早在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al Jermore Macgown)口译、我国著名学者华衡芳做笔录而合作译介了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学浅释》(即《地质学原理》)一书,由江南制造局铸刻出版。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本介绍西方进化主义思想的著作,这本著作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进化均变”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华衡芳在《地学浅释》的序言中谈到翻译这部著作的艰难之处时说道:“惟余于西国文字未能通晓,玛君于中土之学又不慎周知,而书中名目之繁、头绪之多,其所记之事迹每离奇恍惚,迥出于寻常意计之外,而文理辞句又颠倒重复而不易明,往往观其面色、视其手势、而欲以笔墨达之,岂不难哉!”[6]35《地学浅释》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前,就已经涉及生物进化论的部分内容,可以说,赖尔的《地学浅释》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先声,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广泛传播和其掀起的进化主义浪潮起到了“预热”的作用。《地学浅释》作为一本关于地质学的自然科学专著的问世和在中国传播,在当时来讲,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这位进化论巨匠在中国的传播,还塑造了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并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此外,傅兰雅和丁韪良分别在《格致汇编》和《西学考略》中介绍了生物界“由简到繁、人猿共祖”和“动、植各物均出一脉”的理论。1877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格致汇编》,其中的“混沌说”一文介绍了动物经历了从简单到繁杂漫长的演化过程,即:初有者为虫类,后渐有鱼与鸟兽,兽中最灵者为大猿,猿渐化为人,盖从贱而贵、从简而繁也[7]。由于西方进化论的问世对教会义理的挑战毕竟太过直接,极少有教会人士愿意承认进化论的合法性。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首次谈及人类和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一对他们而言最敏感和难以接受的话题。188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同文馆作报告,后经整理为《西学考略》出版。书中,丁韪良首先介绍了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在《动物哲学》一书中的进化论观点:“法国有赖摩者(今译拉马克),又创新说……谓动植各物均出一脉,并非亘古不易。”[7]书中也谈到如下思想:在创世之初,水中最先出现一种或数种虫类,后经漫长变形,生足则陆生,生翼而升空,再经千万代,兽中直立者渐通灵性,化而为人。丁韪良在书中接着介绍道:“四十年前,有英国医士达尔温……乃举赖氏之说而重申之。伊云:各类之所以变形者,其故有三。一在地势……一在择配各物之形……一在强弱以决存亡。”[7]
上述可见,传教士来华对进化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他们所译介的著作如《地学浅释》,则成为进化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路先锋,对晚清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等这些实实在在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人,都受到过这些著作的影响。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对《地学浅释》大加肯定地说道:“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急读。”[6]37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传播到中国来的大多还属于生物进化主义,此时的生物学或地质学层面的进化主义,还没有被广泛地、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和发挥到哲学或社会学层面上来。
(二)严复:进化主义思想传播的推进。
如上所述,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始于严复,在他之前,早有来华布道的传教士对西方进化主义思想做过一些简明扼要的介绍。不过,这一时期的进化主义思想,还只是以碎片化的介绍形式被传入的,进化主义的传播范围和影响还非常有限。但是,当1898年严复出版了他那本半是翻译、半是理论创作的《天演论》时,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普遍地接受进化主义[8]。如果说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地学浅释》以及傅兰雅和丁韪良等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介绍仅仅只是进化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由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天演论》中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更把进化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推至巅峰。《天演论》以“物竞”“优胜劣败”等进化的理念,取代“国本不可动摇”这一抱残守旧思想,并使之成为普通国民的世界观。
严复翻译《天演论》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后来的职业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79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在普茨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严复留学英国的这一时期,正值实证主义哲学在英国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实证主义认为,除了观察到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再也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都是关于现象的相对的知识,而非现象背后的实体的绝对的知识。实证主义研究的是真实、有用、肯定和精确的知识,也就是完全可以由经验加以证实的现象的知识。如此一来,哲学就是实证,哲学知识就是实证知识,也即科学知识。在实证主义思想家看来,经验的社会现象和经验的自然现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应该且必须把行之有效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研究社会科学中来。由于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对其思想的冲击,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兴趣从航海驾驶专业转移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等学科上来。他除了在学校学习航海驾驶的专业知识外,把注意力和精力则更多地放在了当时进化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上,广泛地涉猎了达尔文、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人的理论。早年的求学经历对晚年严复的学术成就来说,就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外,为后来包括《天演论》在内的“严译八大名著”的问世,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毕业归国后,由于缺乏政治实力,严复的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恃才立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成为严复“译著立言”这一学术转向的直接动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标志着以引进西方物器文明为主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派把“强国梦”的希望寄托在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等火器和建造现代工厂上,他们苦心经营的自强之路最终在甲午海战中毁于一旦。严复指出,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乃是“盗西法之嘘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西学内容则是“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在他看来,引进西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使国人摆脱“华夷之辨”等高傲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进而认识到当前的国际新秩序乃是建立在各民族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又是民力、民智和民德之间的竞争。早在英国留学时,严复就注意到,以英吉利民族为代表的西方人对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重视在对国民教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反观中国,出于千百年来实用主义心态,国人对科技文化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简单运用的层面上。他从价值层面上提出,当下中国亟须引进并消化吸收的是西方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而非仅仅是具体实用的科学技术。为此,严复欲以其著名的“严译八大名著”,开拓国人的眼界,启蒙国人的思想。
由于严复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深受实证主义这种“科学主义”哲学的影响,加上他身处中国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此,严复在考虑译介西方哲学的内容时,并没有把法国启蒙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重点考虑。因为在他看来,真正能够挽救中国于水火的,并不是这些思辨性强的大陆理性哲学,而是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可以为这些科学予以方法论指导的英国式的实证主义哲学[9]。所以,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严复首先重点译介的内容就是充满实证主义精神的进化论哲学。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结合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进化主义思想,才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哲学,才能起到新民德、树新风的作用。严复在《天演论》中所译介的进化主义思想,总是伴随着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理论观点。表面上看,严复的进化主义似乎是对他们的进化论的简单糅合或翻版,实际上,《天演论》中所译介的进化思想贯彻着严复自身对进化主义的独特理解。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是一切进化论学说的基础,但严复没有首先选择翻译这本著作,因为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物种起源》作为一本纯粹的自然科学和生物学著作,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帮助并不大。在斯宾塞的著作中,他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延伸并应用到人类社会。从个人感情上来讲,严复更认可斯宾塞版的“进化”理念,但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与严复当时的救亡图存的思想亦存在冲突。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与达尔文所言之生物界的进化过程并无二致,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自然过程”,遵循自然规律,无需人为干涉。基于此,他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更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著作中的理论,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更能满足严复以实用为目的而传播西学的需要。因此,严复以《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原本译介了《天演论》。但严复却不同意赫胥黎通过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来限制“天演”这一残酷的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通用企图。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宾塞的观点保持着高度一致,认为天演法则对人类社会同样有着普遍有效性。严复通过赫胥黎著作中所描述的自然界中各种残酷竞争和生存淘汰现象,鲜明而生动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一些基本观念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以此印证变法的需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中国要想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进化”,要“进化”就必须变法。此之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在《天演论》中,严复第一次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并把进化论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他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也正是满足他突出进化世界观的愿望[6]71。他解释“天演”中的“天”字是指物质“自然而然的因果内在必然性”。在这样的解释下,严复所谓的“天演”,不仅可以与达尔文所言“自然选择”的观念相通,并且上升到了世界观的层面上,使之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样,他就成功地把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纳入到“天演”的范围内;而“天演”的理念作为严复所创造的独特“范式”,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演进。严复坚信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基于作为“天道”的普遍进化原理。
在对“天演”的理念进行界定之后,严复继而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他通过“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这两个基本点,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阐释。所谓“物竞天择”,即:“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10]15“物竞”即生存竞争,天择即“自然选择”。“物竞”在一开始是不同的“种”之间的竞争,然后是同一“种”内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导致的结果便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只有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强者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生物界进化发展普遍的规律学说。
严复通过缜密的逻辑,将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他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天演”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普遍进化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应该且必须被纳入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的关系,而且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亦有着生存竞争的关系。由此,严复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生存哲学,其核心观点就是“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10]5。为了进一步说明他所谓之具有普遍意义的“天演”是如何在人类社会发生作用的,严复借助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辅证其观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世间万物繁衍不息,总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飞速增长,如若灭亡之物种的数量远低于生存下来的物种,那么地球上很快就会出现生存空间不足的状况,加之其他区域的竞争者对当地资源的抢占,更加剧了生存竞争的程度。他举例说:墨、澳二洲的土著人的生存状况今不如昔,皆因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并与他们争夺资源,欧洲殖民者凭借强大装备武器,毫不费力地击溃原始的本地土著人,导致他们几近灭亡[3]11-12。据此,严复指出:“物竞天择之用,未尝一息亡于人间。”[10]101
三、进化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
冯契先生曾指出,“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真正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两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1]。冯先生的这一精辟概括,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它不仅赋予了进化主义哲学在西学东渐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还阐明了进化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启蒙先导作用。
首先,由传教士和严复所译介的进化主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长期以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观念的形成,除了受到“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即“盖天说”[4]21。这种学说认为,天地是上下对立的两部分,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不塌地不陷,天圆地方,永恒不变。从这种宇宙观出发,最后必然推导出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尊卑贵贱”的政治思维,以及支撑这种政治思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思想。而19世纪末的中国,正值社会动荡不安,大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明白中国亟须变革。可是,由于“道不变”这种发展了数千年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在人们思维中根深蒂固,如何打破这道束缚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则成了最棘手的问题。恰逢进化主义这种充满“变数”的学说适时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得国内众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同久旱逢甘露般,把在书中汲取了的进化主义思想,用以冲击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如谭嗣同认为,“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日不变也”,康有为也提出“盖变者,天道也”,梁启超更是喊出了“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的口号。这些,不仅为进化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还为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武器来对抗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主张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先声。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其与反封建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锐利武器”及其维新变法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其次,进化主义作为“近代西方科学的象征”,在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征服了中国社会的第二时期(1895—1927)”,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主流[12]。胡适曾经说过:“读《天演论》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和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胡适之)也是这种风旨底下的幻念品。”[13]由此可见,西方进化论的传入,不仅在唤醒国人“开眼看世界”方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还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发奋图强、救亡图存的斗志,还改变了士林风气,使中国出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群。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把“进化主义”看成是“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近代文明三大特征之一。《天演论》的传播,更是促成了近代中国“进化”的时代风潮,使得知识分子群中以不言“进化”“物竞”“争自存”等为耻就意味着“自甘堕落”、就好似在“革命时代”不谈革命就意味着落伍一般。
其三,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凡已经接受进化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多都不会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从进化主义跨入唯物史观并没有明显的逻辑障碍。因为进化主义本身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冲突。唯物史观就其内容而言,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进化的思想,其“阶级斗争”的内容更是与进化主义中的“生存斗争”学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前者强调的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竞争关系,而后者则是谈论整个自然界中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李大钊是第一个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曾是进化主义的忠实信徒;甚至直到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并没有抛弃进化主义的观念,可以说,进化主义观念已深深地浸透到他的意识中。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如果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他们(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笔者注)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并渗透到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14]由上可见,进化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续传入,提供了思想上强有力的支撑。
[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M]//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412.
[2]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叙论[M]//梁启超哲学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7.
[3] 严复.天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丁祖豪,郭庆堂,等.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0.
[5] 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491-492.
[6]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J].世界宗教研究,2001:61-73.
[8] 尹继左,高瑞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9] 胡伟希.中国本土视野下的西方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6.
[10] 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
[11] 冯契.冯契文集:第七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
[12] 姜义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81.
[13] 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27.
[14] 李波.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早起在中国传播的影响[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