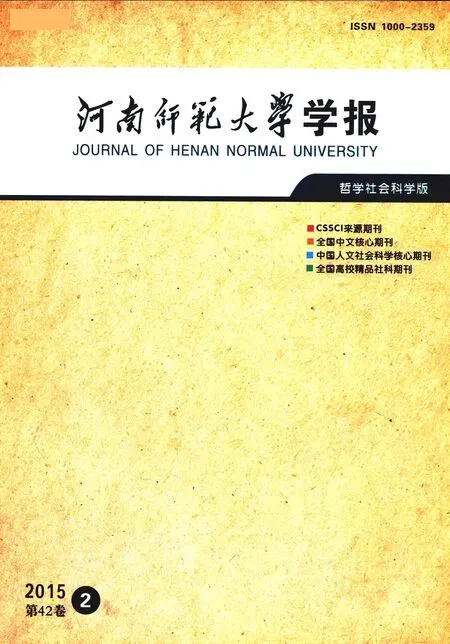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形成的根源探析
丁 一 平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形成的根源探析
丁 一 平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耻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搞清耻感文化的形成,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了解耻感文化的功能与机制。探讨耻感文化的形成,应当从中华文明形成早期的生产方式入手。耻感文化产生于集体主义的农耕文明之中,它发端于古老的祖先崇拜,由祖先崇拜形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使耻感政治化、社会化、伦理化,而儒家的推崇、传承、传播,最终形成了耻感文化,并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符号,广泛影响到周边各国。
耻感文化;产生形成;根源
正如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概念的创立者,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说,区别以耻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为基调的文化是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耻感”与“罪感”是我们分析与比较东西方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重要工具与研究视角。基于西方学者这一背景,鲁思·本尼迪克特对于耻感文化的形成没有深入涉足。近些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作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代表性的观点如,“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思想之中”,“中国的耻感文化是儒家耻感文明数千年来积淀的结果”[1];“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在先秦时期”,“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2]。还有学者上溯至夏商时期,认为《尚书》中的伊尹放太甲、《周礼》中的“耻诸嘉石,役诸司空”、《诗经》中对统治者的讽刺,“说明殷周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使人知耻的心理因素对于控制人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上述解释有启发性。笔者认同儒家是耻感文化的巨大推动者和主要倡导者、耻感文化在先秦时期确立这些观点,但笔者认为,儒家仅是耻感文化的二传手,是耻感文化的促成与倡导者,耻感文化另有其根源。探讨耻感文化的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耻感文化发生作用的机制。在此,笔者试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在对耻感文化的根源作进一步探讨时,我们需要厘清,耻感文化与羞耻感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将荣辱作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和社会控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发展出来的泛人类的文化感受。耻感并不必然导致耻感文化的形成。实际上只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才发展为耻感文化,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圈则发展或被定义为罪感文化,它的基本特征将“赎罪”(同样是导人向善)作为人生最终目的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耻感文化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一、集体、家族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耻感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
罪感文化产生于由个体组成的社会,而耻感文化产生于由家庭或家族组成的社会。罪感文化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耻感文化则是集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罪感文化的社会中,个体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每个个体都在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每个个体仅对个体自身的行为负责,独自承担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导人向善,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需要由内向外,故产生内向或内化的罪感文化。而在耻感文化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社会中的自我是大自我,集体的自我。个人的行为与其所处的集体(家庭或家族)有关,个体的行为是集体行为的组成部分,要对集体负责,受集体的监督和评价(嘲笑和赞许)。个体的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在于在集体中获得赞许并使其所处的群体(家庭家族)感到荣耀,而不是受到嘲笑、蒙受耻辱。因此,罪感“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感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反映是由内向外,无需要外人在场,而反应则是对外部刺激的回应,因此,反映是个体的,而反应是群体的。“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3]154。因此耻感文化只能产生于集体组成的社会。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影响与决定思维方式。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形成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西方文明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的自然环境不适合农耕,但良好的港湾、优越的区位,使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适应中选择了商业贸易作为生存方式,形成商业贸易的社会。贸易交换需要明晰产权,重视交换主体的平等,否则,交换无法进行。明晰产权导致强调个体。商业交换强调个体的社会化使得原始的血缘氏族关系被打破,由此产生了西方社会思维和文化的特点。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是最小经济单位,从个体出发,强调个体,重视个人价值。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在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初期进入了农耕社会,农耕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生产活动,需要集体合作,尤其是水利的利用,更离不开集体。这样早期的血缘氏族分化而成的家族就成为基本生产生活单位。血缘氏族关系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这种家族式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导致每个人都是所属群体的派生物,人的自我意识集中在家族,而不是个人,“其人格自我不是小自我,而是大自我”[4]。个人的价值在于群体之中,家族的命运就是个人的命运,个人必须服从群体。故“中国人对人的重视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不是肯定个人的价值,而是肯定人对其它人的意义。强调人的历史使命,强调人对社会,对别人的关系,人要对社会,对别人做贡献”[5],甚至“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
这种集体的生产方式和家族的生活方式是耻感文化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耻感文化只能产生于集体的社会意识中,而罪感文化则产生于重视个体的文化背景中。罪与罪感是个人的,无社会联系,只有个人承担。耻感则既是个体的更是个体所依存的那个群体的,而且主要是群体的。既然群体中个体的某种行为与相关群体中的他人产生某种关联,自我是大自我的家族,个人的价值在于个人对他人的意义,个人生命的意义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个体的耻辱也成为群体的耻辱、家族的耻辱。个体因为其所处的群体的耻辱并受到群体的指责而觉得丢脸。诚如孩子犯法,最感耻辱是他的父母而非本人,本人则因为父母的耻辱而加重罪恶和耻辱感,因为“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映”,耻辱感需要“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的旁观者”[3]154。这种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耻感文化产生社会基础。
二、祖先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制度与宗法意识是耻感文化产生的文化背景
罪感文化的理论或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人灵魂与文化深处的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原本生活在伊甸园,因蛇的教唆,偷食禁果,产生了后代,犯下“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是人类的原罪及一切其他罪恶的开端,人的出生是罪恶的结果,“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基督教圣经《诗篇》)[3]133。人类祖先的这种原罪一代一代地传给后代,只要有新人的诞生,就会产生新的“原罪”,连绵不断。因此,罪性就成为人的本性,人类世代不能逃离罪恶之网,要得到解脱,就必须忏悔、祈祷,通过行善来赎罪,以便有朝一日进天堂而不下地狱。由个体组成的现实社会,强调个体的商业贸易的社会,容易使个体很产生贪婪的、无限的、获取更大财富的占有欲。要遏制这种欲望,西方人通过宗教将贪婪、欲望视为原罪。而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限制欲望和行善来赎罪,这是个体不可替代的人生任务,也因此成为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所在。
既然罪感文化来源于灵魂与文化的深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耻感文化也应当是灵魂深处具有宗教信仰控制力的产物,否则它不可能成为根文化观念,左右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的人生目的或人生价值。因此,耻感文化的形成与古老的祖先崇拜有关。
与西方人生来就带有原罪不同,中国人一旦出生,就欠有“原债”。所谓“原债”,即新生儿一来到世上即欠了一笔恩情债。婴儿的诞生是祖先恩泽、父母的辛苦换来的。父母为了新生命的成长,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传承、积累了或多或少的财富。因此,每一个新生的人类能来到世上,首先欠了父母祖先的恩情债,而他或她成人首先和必须要做的就是报恩。报恩就要孝顺父母、祭祀祖先,它的高级境界是光宗耀祖,它的最低要求则在于即使不能光宗耀祖,也要避免让父母受辱、使祖先蒙羞。因此,获得荣耀、远离耻辱成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
这就是作为耻感文化根基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观念,因此成为耻感文化的源头。祖先崇拜的产生有至少有四个基础,一是祖先或家长生前的权威,二是家庭私有制的形成与家族财产的传承,三是感恩的情绪,四是当时的人类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被误读。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生产是家长率领的家庭或家族式的集体生产,农业生产尤其是水利建设形成大规模的集体劳动,需要有人负责,而年长、有经验的家长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便产生了血缘家庭的家长制,维护家长的地位,增强家长的权威成为必要,这是祖先崇拜的社会基础。家庭私有制的产生,使后代总是从父辈或者祖辈的手里继承土地、财产、工具、财富等。如此循环,造成后辈生命中的一切,地位、财富、荣誉都是从祖先的手里传承下来的,感念先祖、崇拜祖先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是祖先崇拜的经济基础。父母为了养育后代,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应当报恩,这是血缘亲情的基础。有权威的家长去世后,时常会进入晚辈的梦中,古人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而微生物侵袭入土后的尸体所产生的“巨人观”更使他们惊讶不已。他们以为祖先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处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祖先可以庇护自己的后人,而要使这种庇护能力存在,就必须祭祀自己的祖先。于是便有了崇拜祖先的各种仪式,强化祖先权威的观念也随之形成。而崇拜祖先最基本的要求是后人的所作所为不能让祖先蒙受羞耻,要对得起祖先。因此,原始的祖先崇拜成为耻感文化形成的信仰或思想基础。
在耻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法制度根植于祖先崇拜,正是宗法意识与宗法制度使得祖先崇拜制度化、社会化,上升为天理,所谓“奉天法祖”,代代相传,成为文化基因。宗法意识的制度化、社会化正是耻感文化的社会化、制度化。宗法意识存在于夏商时期,但宗法制度的确立却是在西周。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解决权力与财产的继承与分配问题,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由嫡长子继承所发展出的大宗小宗的家族结构体制,以确立远近亲疏、尊卑贵贱,建设一个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格局。虽然这个结构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瓦解,但是它的思想体系与文化观念却已经深深植入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人的许多根意识和一些看似很难说清的思想问题,往往都能从中找到答案。因此,祖先崇拜和其派生出的宗法意识成为了解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文化传统的一把钥匙,也因此成为我们解秘耻感文化的一把钥匙。
宗法制度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后果,一是在制度上和意识上进一步确立以家族为单位、以血缘定亲疏的社会生活方式。天子以血缘定尊卑,普通人则以血缘定亲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推崇共同的祖先,规定继承的秩序及成员自身的身份和权利义务。在这个制度设计中,家是社会的核心,血缘是社会纽带,形成“家—族—宗—国”这样亲疏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圈子,家由父、己、子三代构成,由父亲往上推至祖父,由儿子向下推至孙子,亲属关系就由原来的三代延伸为祖、父、己、子、孙五代,形成大家。族是由祖、父、己、子、孙五代分别再向上、向下推两代,延伸为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九代。“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礼记·丧服小记》)。宗则为祭祀同一祖先的族人。“九族”“五服”制,用血缘亲属的网络结构把个体凝聚成为组织严密的家族共同体。“家—族—宗—国”构成整个宗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圈子。这样,个人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其个人的行为必然影响到整体,因此也必须对整体负责。处在层层圈子之中的个人必须服从与接受圈子的监督管理,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因整体而存在,为家族而生存。“个人生存的目的,就是承继祖宗的余绪,维系家族的延续”[6],进而光宗耀祖而不能使家族蒙受耻辱,愧对祖先。这是耻感文化形成的社会氛围。宗法意识加强了家族观念、整体观念,从而强化了耻感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与社会联系。
宗法制度的第二个结果是尊祖敬宗。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的确立强化了人的权力、财产、土地、生命都来自祖先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应当尊祖敬宗,感念祖先的伟业,继承他们的家业。要祭祀祖先,孝顺父母,由此发展出了中国人“孝”的核心价值理念。不孝有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十三经注疏》)。因此,即使不能光宗耀祖,但至少不能愧对祖先。这是人生的基本要求,由此,尊祖敬宗、光宗耀祖的荣辱观发展起来,并赋予耻感文化核心内容、社会责任与核心价值。而这种荣辱观的社会化,便成为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
宗法制度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最为典型的形态是西周的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一等级结构,既是政治分层,也是家族的内部结构,形成宗统与君统的统一。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家庭的结构就是国家的结构。虽然这一结构被秦建立起来的郡县制瓦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植入中华文明之中,它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伦理上升为国家政治伦理,家族观念上升为国家政治观念,于是“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7]由于家国同构和家族伦理的政治化,家族价值的核心之一的耻感也随之政治化、伦理化、社会化,成为传统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念中的重要内容。
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推崇使耻感文化最终确立,并传承传播、发扬光大
诚如前述学者所言,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管仲曾说:“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虽然管仲等一些法家也重视耻感的意义与作用,但是真正把这一观念条理化、规范化、理论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的却是儒家的先哲。在耻感文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儒家思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儒教文化将祖先当作神灵一样崇拜。在儒家的伦理和理论中,“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礼、义、廉、耻”作为四德,是作为人处世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成为“以德治国”的理念依据。以德治国离不开知耻,耻是导人向善,进行有效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礼记·哀公问》)。“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到了汉代,经过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宗法思想国家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与政治思想,耻感文化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再发展,到了宋明时期,耻感文化更加深入,“必有耻,则可教”[8]。人只有“耻于不善”,才有可能“至于善”[9]。“五刑不如一耻,百战不如一礼,万劝不如一悔”[10]。这些先哲进一步强调耻感文化的导人向善和社会控制功能,甚至将宗法思想神圣化,将尽忠、尽孝、尽节、尽义纳入耻感的内容,脱耻成为个人的人生目的、意义与价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成功,便成仁”。正是通过儒家的传承与推广,耻感真正成为覆盖东方社会的文化观念。
总之,耻感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的集体主义之中,发端于中华文明古老的祖先崇拜,由祖先崇拜发展出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意识加强了耻感文化的社会基础,赋予耻感文化以核心内容,使耻感政治化、社会化、伦理化。儒家的推崇、传承、传播,最终形成了耻感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符号,并广泛影响到周边各国。
[1]许兰.耻感文化溯源[N].北京日报,2006-04-03(17).
[2]胡凡.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M].光明日报,2009-09-08(12).
[3]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威尔海姆,沙莲香.中国民族性[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5.
[5]戴逸.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C]//沙莲香.中国民族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序.
[6]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J],社会科学战线,1982(2)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C]//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8]周敦颐.通书[M].徐洪兴,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
[9]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549.
[10]吕坤.呻吟语·治道[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62.
2014-11-07
B82-052
A
1000-2359(2015)02-0094-04
丁一平(1961-),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