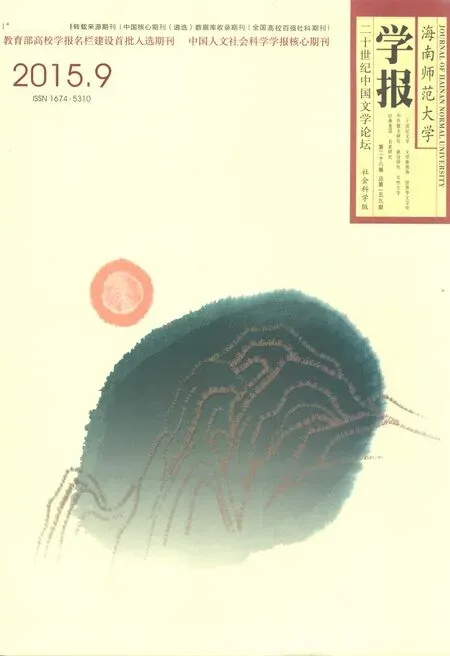误读·还原·参照·融合·对话——论结构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路径
潘吉英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一、文本轩轾的误读
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在80 年代的方法论热中,结构主义是其中的生力军之一。由此,文本成为文学领域,特别是叙事学的新生词,作品却日益边缘化。但中西文本的内涵并非完全对等,在某些场合甚至相异,这一轩轾有其思想背景。简言之,在西方,文本是结构主义者以语言学为介质的科学研究对象,大致等同于“结构”的内涵,其作用是取代作品——以作家为主体的人文价值研究的对象;在中国,文本是当代文论者引介西方结构主义理论时,为翻译英文text 而造的词,但在实践层面上,作品并未取代文本,只是延宕文本转化为作品的过程。
“许多学者对于结构主义思潮中文本与作品的对立关系不甚了了,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文本成为作品的替代词,表现为一种时髦。”[1]有的书在对西方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本主义文论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后,总结出“文本为文学作品之本”这一立足点,并藉此阐述汉字文本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古代辨体分类、小说理论、诗歌理论中的文本观念。这一对文本的“误读”固然展现“洞见”——赋予中国文论全新视角,却使中西方结构主义文论间的对话,犹如庄子《齐物论》中影子与罔两(影子的影子)的对话,中西文化的异质区隔在无意间被抹平。由此,对文本的“误读”进行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建构,有可借镜的价值存在。下面,简略还原这一误读的思想背景。
二、思想背景的还原
(一)结构主义在西方:“语言学”的科学内转
“结构主义”这一词是从西方译介的,不具中国原生性,不仅有特定的内涵,也是动态发展的,随历史进程呈现多义现象。就当代西方文论而言,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结构主义指酝酿于上世纪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峰,以具有普遍性的结构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思潮,“包括美学的(新小说)、政治的(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2]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对结构主义特征的阐述,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他概括出“结构”的三个特性: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转换功能”的规律性、“自我调节功能”的封闭独立性。列维- 斯特劳斯在他的基础上,写作《结构人类学》一书,进一步细化“结构”的特质。此外,应再补充两点:结构主义者着重在可直接观察的表层结构中,通过认知模式探知深层结构;常运用“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3]的思维方式,以二元对立的科学配对的“对子”形式探知结构,但这一“对子”也成为结构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最后被德里达所解构。
狭义的结构主义指上世纪60 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领域中的一种运用,以反叛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姿态出现,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密切相关,是科学文论转向以内部语言学符号为研究介质的一环。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倡导与传统语言学一贯重历时性相异的共时性观念,以语言/言语、能指/所指、共时性/历时性、横组合/纵组合、二元对立比较原则等4 个对子与1 个基本原则的结构建构,带来语言学的革命性范式转换。俄国形式主义为反抗实证论而接受、借鉴索绪尔的方法,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如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布拉格学派的代表雅克布森,以隐喻/转喻的典型模式,分析诗的语言,探索诗性功能所赖以生存的诗的内在结构。英美新批评采用文本细读法,研究单部文学作品的肌质,如语言文字技巧、修辞手法。法国结构主义重在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语言结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构主义的重新阐释、格雷马斯三对对立的行动者的“矩阵”符号学理论。
(二)结构主义在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外转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思想背景下,结构主义是“和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处于错综复杂的共时性理论网络中。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结构主义批评的魅力,阻碍了它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这造成了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接受语境”[4]。与西方文本内部结构的科学研究相异,中国结构主义偏重于叙事作品的外部的文化价值研究。
第一,诗歌研究。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对波德莱尔的诗作《猫》所进行的分析,是结构主义批评实践的经典之作,在细致入微的科学分析后,“所辨认出的某些结构甚至就是最警觉的读者也无法察觉”。[5]但周宪认为,这一方法犹如奥姆斯剃刀理论,在“揭示了一般读者常常看不到的语言学规则”时,对“优劣在何处则语焉不详,它对于作品的文化价值更是漠不关心”。[6]在诗歌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如旅美学者高有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意在“把‘传统’这一概念引入结构主义的理论”,[7]以作为对“传统”进行扬长避短地加以改造的最好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因未有效化合以背景意图为基点的语意分析与以科学结构为中心的文本分析间的“逻辑”自足性,于是,“背景渗入文本之后的分析者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背景证明文本,文本证明背景,结论产生于根据,根据却来源于结论”[8]。中国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诗歌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叙事学研究的成果。
第二,叙事学研究。在西方,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英语转译俄文“反常化”)概念,[9]意在使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东西重新变得新奇、陌生,进而重新唤起人对周围世界感受的方法,并且延续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在叙事文学中重情节,人物则退居其次。普罗普从一百多种俄罗斯童话中,归纳出7种角色、31 种叙事功能,并制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叙事结构。托多洛夫不考虑叙事的媒介,如文字、图像、声音等,旨在总结叙事的本质与分析的原则;而热奈特有感于当代大众传媒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秉性,将叙事学缩小为叙事文学的研究,不涉及影视等部门。二人对叙事学的定义成为西方学界的权威。
在中国,借镜西方结构主义而建构的中国叙事学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为分析小说叙事和文学史提供值得借鉴的范例。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他在对中国叙事作品而非文本的分析中,条分缕析出:叙事结构功能有“笼罩全文”的统摄之道与“疏通文理”的具象之技的区别;双构思维方式——“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结构形态是“有气脉神韵贯注于其间,形成一个统一的生命体”;结构意义的动词性——“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的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而且还指向叙事文学史上已有的结构”。[10]41-47在充分挖掘中国叙事结构独特性的基础上,他的最终指向是建立可与西方进行充实、深度对话的具有中国特色并充分现代化的叙事体系。
总之,无论是周宪对西方诗歌文本的结构分析方法的优劣评断,抑或是《唐诗的魅力》未有效融合异质文化而现的怪圈,还是中国结构主义文论比较成功地将西方“语言学”的内部科学研究,转化为“叙事学”的外部文化价值研究,深层之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结构主义的文化轩轾——处于不同的历史域境,及其随携的“结构”、“解构”思维的异质性。
三、历史域境的参照
(一)中西解构主义:“五月风暴”与“五四运动”
在西方,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形成一股否定理性、怀疑真理、颠覆秩序的强大思潮。此思潮孕育出1968 年“五月风暴”学潮,虽未能颠覆现存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结构,却在讥笑结构主义者“从不上街参加战斗”这一冰冷的中立态度中,进而质疑、否定、解构其语言中心的结构思维、方法、体系。事实上,结构主义过分强调封闭自存的结构的普遍性,而这又建立在抽象假设之上,不承认独立于结构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有意无意地切断文学与社会、作者的联系之“根”。解构主义即檗蘖萌生于此“根”基,进而从内部颠覆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欲破译关于文学的神话,但看来它只是营造又一个关于文学的神话。
在中国,时间往前推移近50 年的“五四运动”,与“五月风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是二律背反性:由学潮到社会精神向度的转向,看似偶然性的事件,有自身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二是尼采式的标语口号:“重估一切价值”、“作者死了”、“消解中心”等。三是解构主义的表征:前者是由内部引发的对国家政治体制、大学管理制度的反叛,到内心深处的激情、迷惑、狂暴的精力宣泄,成为解构主义产生的导火索;后者是由外交事件引发的激烈的反传统,在试图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在无形中创设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实现现代转型的契机。
“五四运动”受西方进化史观的影响,形成单一、线性前进的“优胜劣汰”式时间观,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刺激时,激烈地反传统,“全盘西化”。打倒文言“古文”导致三个遮蔽: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忽视学术文化的本土化追求;“纯文学”观念代替“杂文学”观念,无法真正把握民族特点,满足文学史主体性的追求;批判“旧派”的文章批评专家、专书,隔断古代文章学的根脉。[11]此外,否定汉字,尤其是形意完美结合的繁体字被简体化后,也丧失诸多传统文化内涵。
“五四运动”在批判传统、现代二元绝对的时间对立时,无形中也空前强化中国、西方二元绝对的空间对立,忽视真正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化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是中西异质文化融合的转化性。但是,没有“五四”,何来现代中国?反传统在表层层面上似乎是冲击、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具有消极性;在深层层面上,它既是传统的常态,正如朱自清《诗言志辨》中的“以变求正”,也是传统文化结构现代转型,抑或是具备现代性的途径之一,具有积极性。由此,哲学家汤一介的“中国文化的内在转化”,历史学家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思想家李泽厚的“中国传统的转化性创造”,尽管三人语言表述略有差异,但均以五四“解构”两极性的思想资源为反思之基,致力于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中西解构思维:福柯与鲁迅
在中西解构主义产生的不同历史域境中,以福柯与鲁迅为个案更能明晰中西解构思维的异质性。二人皆深受尼采影响,均经历沉寂、模糊、犹豫、明晰、爆发等不同的人生阶段,但自身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在二人的个体“自我”中却有不同映射,如在古希腊神庙所镌刻的铭文——“认识你自己”的烛照下,二人对主体“自我”的消解路径迥然不同。
第一,福柯对真实个体自我的执念与毁灭的崇高。福柯一直不认可别人将他归入解构主义抑或结构主义,因为他在权力与知识结构背后,更关注的是主体性问题的认知——更内在的人(自我)是什么?刚开始,福柯只希望“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给我们以自由”,[12]但因摇摆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进而幻变出一种显具地下人足迹的飘摇无根状态。“五月风暴”后,他坚信政治同于艺术与性,也是“极限体验”,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先知。他异于马克思式“新人”,通过改变经济、社会进而改变世界,竭力成为尼采式“超人”,通过改变自我身体、灵魂认知,诉诸实体与人心双重“监狱”的开放,释放被压抑的人性,从而改变世界。然而在现实中,权力惩戒的缺失,孳生的是恐怖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至此,他从未有过地对那条仅供他一人走的路,也流露出怀疑情绪,只能借“死”寻求慰藉——“既无片刻的停顿也无预先的决定,将照亮你的全部生命”。[13]405
福柯以解构思维重读历史,想通过站在萨特存在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对立面,确立自己的学术权威与政治地位,进而跳出西方文明潜隐的权力/知识结构的控制。由此,他在尼采“权力意志”中抽绎出“不服管的艺术”,固然在哲学层面上与康德“自由”、海德格尔“纯粹的超越性”具有同质性,但与二者有别的是,他在现实层面上并未超越尼采始以激情澎湃、终以发疯的伟大探求,成为尼采式的“超人”。他为反抗主体自我的规训,追求独立真实自我的路径,是通过积极的政治革命的外部体验,发现此路径并不可行之后,只能转向消极的同性恋施虐、受虐,在内部生与死临界的“极限体验”中落幕。在反抗社会把人的存在驱逐到内心的同时,自我也被迫走向悲剧性的毁灭。因为只有死,他才是其毕生所追求的最真实的自我;因为只有此刻,他才能真正脱离社会,不再承载文化记忆,也才最自由。虽极力逃避,但终究无法逃逸,仅此而已。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悖论,犹如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尼采曾说:“对真实的爱是可怕而非凡的,”[13]530这正是福柯活出“自我”的一生,及其随携的西方文化精神的逼真写照。
第二,鲁迅对自我文化传统的解构与建构的虚妄。今天,“当我们重新来阅读‘五四’时期的那些有关‘人的发现’的文章时,仍感到一种含混和模糊”。[14]这除了因“五四”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审视中/西、古/今、传统/现代的文化,未有效融合二者间的异质性,并未确立中国文化的自我主体性,更深层的原因是“五四”并未逃逸传统思维模式——重由感悟兴发的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这一框限,缺失西方如康德等区分人的认识能力中科学分析的知性。由此,即便高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内涵更多的也是一种抽象、玄学的内涵。因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不仅证言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进而反思“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15]的文化传统,更透过“五四”反传统的层层迷雾,揭破其伪装,最终,在“国民性三问”的思索中,试图解构儒家文化主体结构。
严家炎曾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走向成熟。”[16]这不仅因为鲁迅在小说中使用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以及白描笔墨、断面式的情节安排,已具现代性,更因为他在小说中“开始了中国神采与现代世界人类精神相融合的历史进程”。[10]33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肥皂,竟诡异地成为四铭这类笼罩着封建意识的绅士阶级发泄淫念的象征,鲁迅“在这戏谑化了的艺术构思中,严肃地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怵目惊心的事实:缺乏接受现代文明的心理基础比缺乏接受现代文明的设备更为可怕”。[17]阿Q 革命首先想到的是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这刻画了人活着就是为现世享受的心态。四铭、阿Q 正是鲁迅刻露、批判、解构儒家文化主体结构的典型。因为正是作为中国文化起源的氏族群体的巫术礼仪→周公制度化→孔子心灵化→儒家的“内圣”之“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之“礼”(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文化主体结构→天人合一的演变历程,导致社会统治、精神信仰体制混同合一,个体自我也更为集中关注现实世界和日常经验的生活、行为、情感、心境。[18]
(三)“结构”“解构”的两极共构思维
但丁《神曲》中通向天堂的地狱大门上写着:“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深受这一西方历史文化精神浸润的福柯,试图解构权力/知识结构的普遍性,最终也只能如缔造文学神话的结构主义被解构一样,绝望地捐弃个体的自我生命,这一“自我”的解构路径并不具备足供借鉴的普遍性,但他为追求独立自由、真实的人的存在中,所呈露出个体性、特殊性的执念却在毁灭中倍显崇高的伟大。
别样于福柯自我毁灭中崇高的伟大,鲁迅则是责任担当中崇高的悲凉。鲁迅自日本回国后曾有近10 年的“彷徨”,在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民族危机意识的触发下,“呐喊”解构儒家主体文化;在众声喧哗的“五四”退潮后呈现的一片“虚无”中,用庄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填补、消弭这种空虚。因为他仍背着自我承载的文化记忆这一“因袭的重担”,肩住“内圣外王”的闸门,致力于以反抗的“热风”来“立人”,建构“尊个性而张精神”且“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的现代文化结构。虽然他深刻感受到个体存在的虚无——人是社会群体动物,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记忆,而这正如弗洛伊德的“集体无意识”,是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的,但他却有“从血泊里寻出闲适”的时间性的珍惜,犹如“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野草”,在绝望中仍隐隐有一丝丝若无还有的希望,在如“野草”般坚韧地推动自我的人生充满意义的同时,也推动文化转型的历史。
正如恩格斯所言:“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19]我们一经研究,就会发现,“五月风暴”/“五四运动”、福柯/鲁迅,在中西不同时空的历史域境的参照下具有极端的相似,进而在无形中确证“结构”、“解构”并非西方独有而是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中西解构主义所形成的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隐藏的也许是一种由思维方式两极性的转换、延续而凝聚成的巨大创造力。
四、中西文化融合与文论对话
(一)微观:译介中学术话语的择定
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是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他在此书中流露出对汉字的景慕,并大量引用西方学者夸赞汉字的论述,其中有热奈特的一段话:“文字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对语言的一种语音分析,从来就不是对言语的一种忠实的或不那么忠实的转达。这就是为什么书写的符号,某种同样是这般独特的现实的象征,一直保持了它的居先地位。没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言语不具有同文字相仿的功能,很可能它的力量是部分地为文字所遮蔽了。”[20]
虽然热奈特真实指出汉字的独异性,却有以西方观念绑架东方文化的嫌疑。因为自符号出现之日始,现实也同时为符号染指,不复有纯而又纯的状态,所以古代中国在汉字发明之前,言语并未拥有如今日西方学者在理论意义上的本原地位。在对中国汉字历史的溯源中,可以发现汉字并非来源于言语,也不具有言语的普遍性,而是与原始巫术象征密切相关,具有“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权威性、神圣性、神秘性。闻一多、李泽厚等学者的著述中已充分论证此点。由此,汉字的形音二合(重义不重音)、词的明暗二义(成语尤其显著),句子的“兴”、词曲小说等作品的隐喻复调等等,均体现出两极共构思维的表征。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以汉字的独异性作为解构西方文论,进而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阿基米德支点呢?中国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文化交汇时期,译介中学术话语的择定,即在微观上折射出这种可能性——中西文化融合与文论对话。
第一次融合与对话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支娄迦谶再传弟子支谦译《般若波罗蜜经》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若’译为‘大明’,当取自《老子》‘知常曰明’的意思,‘波罗蜜’译为‘度无极’即是说达到与‘道’(‘复归于无极’)合一的境界。这一译经名称已见他使佛教迎合‘玄理’”[21]。通过“援佛入儒”的转化性创造,将来自印度的异质的“佛”,本土化为带有明显儒学色彩的“禅”:在担柴挑水的平凡生活中参禅悟道。
第二次融合与对话是“五四”时期。鲁迅以《文心雕龙》中的“神思”,汉译佛典《摩诃波罗多》中的“摩罗”,来标示西方两个文学和文化流派。“既以中国词语的特殊意义,强化了对西方流派‘争天抗俗’之恶魔性的阐释力度,又以西方流派的异样作为,丰富了中国词语张扬个性的内涵。”[22]
第三次融合与对话在当代的现实可能性。“结构”一词在中西异质文化域境中有动名之别,在西方是名词性意义,指带有普遍整体性的客体——文本;在中国是动词性意义,不管是段玉裁《说文解字》中的字义解释——“结,缔也”,“构,盖也”,还是杨义《中国叙事学》中条分缕析的结构内涵,都侧重人文精神价值诉求的终极关怀的作品建构。这已在微观探异上摸索与尝试着解构西方叙事学,重构中国叙事学体系。
(二)宏观:当代“十字街口”的转型
当代,在西方处于环环相扣的历时演变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现代、后现代文论几乎是同时涌入中国,形成多种主义共时并存的局面。在纷繁扰人、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方文论中有两种主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的是社会历史整体性、经济决定论的必然律,一是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史观,强调的是零散化、碎片化、平面化及对意义、中心、主体的消解。然而,“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反对中心、本质、必然等观念,貌似向东方直悟性感受这一悠久传统的自然回归(当然不可怀疑这一传统所起的有形无形的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对西方逻各斯中心的一种抗拒,或者说是对目前西方逻各斯中心消解运动的一种迎合”[2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在相似的“十字街口”,我们正可借鉴前文所述中西“结构”、“解构”两极共构的思维转换所凝聚的创造力,融合异质文化,建构可与西方文论“对话”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其具体路径有两种:
一是借鉴“结构”科学的语言分析,解构传统思维方式,增知性一维。古代“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庄子》)等玄思,现代“五四”人的抽象内涵等,常是我们最熟悉,并“深以为然”的,但因惯性思维,我们从未质疑其“应然”、探本溯源而知“其所以然”。犹如封建时期的忠君可谓是“五四”时期的爱国的本真存在。
爱国二字虽随时代变迁,蒙上意识形态(当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遮蔽、歪曲、片面化的“尘埃”,但我们极少思考爱国之“所以然”。儒学大师钱穆曾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24]我们在思考“天地君亲师”中,常常指责“忠君”思想的不是,但我们却极少思考“忠→君”二者间的联结所在。这不仅是因为儒家主体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规范制衡着我们的公私生活;更因为感性→理性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架。若转换成公式将更为明晰,即A→B(联结AB间的“→”为C),C(儒家主体文化所凝聚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常量,AB 则为变量。故在辛亥革命后,“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国亲师”,“忠→君”很容易就被替换为“爱→国”,以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然而其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由此,我们应借鉴“结构”科学的分析方法,解构由感性直接上升到理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增加西方康德区分的人的认识能力中,知性的科学认知这一维度,重新建构感性→知性→理性的思维模式,以减少知性缺失的盲点。
二是借鉴“解构”在消解中心中对真实自我的执念,解构传统人文心态,在两极共构中理性思考,明确自我文化意识。“当一个古老的民族摇摆在迷信和砸烂传统之间时,解构思维或可使人们清醒地走出困境。在情感上既要克服恋旧的情绪所带来的逃避,也要走出力图摧毁过去的狂热。”[25]如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在无锡演讲,台下一位因听不入耳而一直摇头的国文教师,听到他引用荷马史诗时,立刻被震住,不敢再摇头。小说中的这一幕并非纯属虚构。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经过前后40 年的思索、比较中国弹词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的文体无异后写就的《论再生缘》,仍言其“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26]。可见,“人文心态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可谓不深。今天追逐西方新思潮的风气不过是旧样翻新而已”[27]。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以“解构”思维为前提,越过这一层心理障碍,从单纯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阴影中脱身,超越退避性的“自卫”抑或是保守性的“自尊”,方能理性地思考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建构。
[1]钱翰.回顾结构主义与中国文论的相遇[J].法国研究,2010(2):20.
[2]〔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0.
[3]〔英〕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
[4]陈太胜.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J].社会科学研究,1999(4):124.
[5]〔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3.
[6]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J].文艺研究,2008(11):10.
[7]高有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M].李世耀,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81.
[8]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45.
[9]方珊.形式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59.
[10]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王水照,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J].文学评论,2010(4):18-23.
[12]〔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19.
[13]〔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M].上海:三联书店,2002:99.
[1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 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440.
[16]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J].文学评论,1981(5):21.
[1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52-53.
[1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6:56-58.
[19]〔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9.
[20]〔法〕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1.
[21]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
[22]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7:437.
[23]曾艳兵.解构主义与中国的“解构”意识[J].中国比较文学,1997(3):30.
[24]钱穆.晚学盲言:上册[M].台北:台大图书公司,1987:377.
[25]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J].文学评论,1997(2):59.
[26]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72.
[27]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