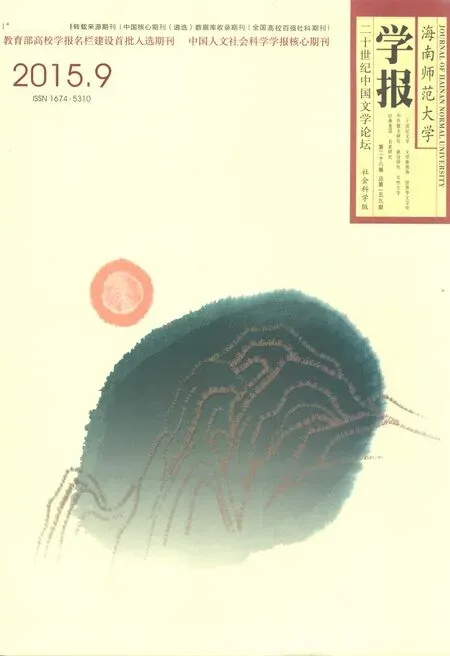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
晏 亮,陈 炽
(1.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430052;2.湖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430052)
“五四”前后作为中国诗歌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重要转型时期,当时的中国诗坛,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并行存在,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其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巨大而又开放的互文性网络。《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①《新诗集(第一编)》,由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社出版部于1920 年1 月出版。《分类白话诗选》,由许德邻编选,上海崇文书局于1920 年8 月出版。后参照原诗发表刊物作了校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8 年7 月出版。本文所引译诗参考后者。作为20世纪前期最早出现的新诗选集之一,集中体现了早期特别是从1917 年到1920 年前后中国诗歌翻译与创作的概况和成就。鉴于此,论文以《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这两个早期新诗选本为考察对象,全面审视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
“五四”前后,“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为后劲”[1],中国文坛中的许多文学社团和组织,其成员大都既从事文学创作,又进行文学翻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既是文学创作家,又是翻译家,同时还是理论家、思想家乃至社会活动家。中国诗坛主要诗人的诗歌翻译与创作基本上也是同步开始和同步发展的,进行诗歌翻译的作家,几乎首先都是一个诗人,比如其翻译作品和创作作品同时被《新诗集》收入的王统照,其上述两类作品同时被《分类白话诗选》收入的刘半农、黄仲苏、田汉和胡适,还有其上述两类作品同时被《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都收入的郭沫若。翻译是一种输入,同时也是一种输出。在译介外国诗歌作品的同时,上述诗人也在不知不觉塑造着自己的创作品性。虽然从晚清开始,中国诗歌就开始了发展新道路的尝试,但“五四”前后数十年间与林纾所代表的晚清年代相比而言,模仿之风更加盛行。不仅仅是诗歌,当时文坛盛行的多种文体,比如小说和戏剧等都有很多人模仿,最终这些颇有天分的模仿者便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翻译诗歌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新诗创作的训练过程。在翻译诗歌这种创造性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早期新诗自身在创作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对推动中国新诗创作具有相同的功用和价值。这些译者在本国语境中赋予原作生命的翻译行为,可以等同于这些诗人赋予其作品生命的创作行为。随着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传入,中国早期新诗创作无论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还是在创作技巧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爱情题材的译诗大量出现。胡适翻译了大量的爱情诗,被《分类白话诗选》收入的就有两首:《老洛伯》和《关不住了》。《老洛伯》中女主人公锦妮陷入了爱情和道义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深爱着她且“并不曾待差了我”的老洛伯,一边是自己深爱着并且也深爱着自己的吉梅。女主人公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煎熬和挣扎正是胡适自己当时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诗人心中,锦妮、老洛伯和吉梅分明就是自己、江冬秀和韦莲司的化身。胡适用一生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与江冬秀的传统婚姻,其中有多少真正爱情的成分我们无法判断,而他与另一位美国女士韦莲司相爱多年却始终没有步入婚姻殿堂,多少应该算得上是胡适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另外一首《关不住了》,明显反映出胡适希望冲破压抑人性的传统爱情理念,当然,他始终未能在行动上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翻译这些爱情题材的诗作,是为了弥补他无法付诸行动的感情的缺憾,借译诗来抒发自己被压抑了的真实的情感。与《老洛伯》同期发表在《新青年》第4 卷第4 号上的《新婚杂诗》,我们从中很容易体会出诗人对新婚妻子的深深情意。《分类白话诗选》中归类在卷三写情类的大部分胡适的诗歌,基本上都是表现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情诗。虽然胡适的这些译诗和其创作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充满着矛盾,但是诗人无疑是根据自己情感表达的需要去选择诗歌翻译文本,而这些译诗又激发了诗人创作同类题材作品的兴趣。同样被《分类白话诗选》收入的,由黄仲苏翻译的两组《太戈尔》,总共22 首诗均选自泰戈尔《园丁集》。《园丁集》是泰戈尔重要代表作之一,是一部“生命之歌”,它更多地融入了诗人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地描述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可以视为一部青春恋歌。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成员,有关黄仲苏的资料留传至今的非常少,我们虽然无法探寻诗人当时的情感轨迹,但是黄仲苏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翻译这些诗歌应该是有感情寄托的。紧跟在后一组《太戈尔》之后的,是由黄仲苏创作的两首诗《有希望么》和《有希望咧!》,这两首诗在内容、情感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后一首紧承前一首。但是就两首诗整体内容而言,都是表现男女之间感情的爱情诗。考虑到上面两位诗人译作与创作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以及在诗集中编排上的邻近关系,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说译诗在题材内容上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其次,“五四”译诗使中国早期新诗语言染上了浓厚的外化色彩,促进了其语言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更新。正如朱自清所言,“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他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2]372—373“五四”时期,通过翻译从西方引入新的词汇是解决中国现代汉语词汇匮乏的有效途径。早期诗歌引进的外来新词汇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在字形和字义上完全采用原语形式。如《新诗集》中周作人所作《路上所见》的最后一句:“宛然一幅Raphael画的天使与圣徒的古画”。二是对原语采取音译的形式,这当中采用比较多的是一些专有名词。如《分类白话诗选》中田汉所作《漂泊的舞蹈家》中“你们经过了西伯利亚”,“你们从彼德格勒来的?”等。三是对原语采用意译的形式。这些词汇通常表示的是中国没有的事物或者是对中国已有称谓的改称。如《分类白话诗选》郭沫若所作《日出》中“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此外,由于翻译表达的需要和原语构词的特点,翻译诗歌也使中国早期新诗语言的构词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仅以代名词为例。我国古代诗歌大多没有人称代词“你”、“我”、“他(她)”以及“你们”、“我们”等,而且这些代名词的缺席并没有影响古代诗歌中情感的表达。但中国早期新诗却大量使用代名词,很明显,这是受到了翻译诗句的影响。以《分类白话诗选》中胡适《一念》为例。全诗共使用了12 个代名词,这些代名词的使用,主要是增加了诗歌的叙事文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代名词都去掉,这首诗仍然是成立的,并且诗性似乎更强。最后,早期诗歌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句法变化。一是翻译诗歌句法中的时态引起中国早期诗歌句法的更新。比如很多诗人翻译时常把英语中的过去时态、完成时态译成相应的汉语动词并在后面加上“过”或“了”,将来时态加“将”,进行时态加“正”,等等。如《分类白话诗选》康白情所作《窗外》中“回头月也恼了,一抽身儿就没了。月倒没有;相思倒觉得舍不得了。”二是早期新诗的诗行在翻译诗歌句法的影响下变得复杂甚至冗长。这主要是由于在英语一些复杂从句的翻译过程中,很多诗人常常把这些从句翻译成修饰语,常常是以“当……时候”、“在……之后”、“……的原因”、“……的方式”等。这些翻译实践使英语诗歌中句子的复杂结构渗透进了早期新诗的句法,并使它们较古代诗歌更加复杂,有些甚至复杂得让人感到冗长。如《新诗集》周作人所作《小河》,其中有这几句:“我只怕这回出来的时候,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不可否认,西化文法对早期新诗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迫于新诗诞生之初的语境,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这些先驱者不得不汲取这些外来营养去滋润早期新诗的成长。
最后,诗人从翻译中掌握了外国文学中一些修辞手段和诗歌组织的技法,实现了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全面更新。首先,中西语言差异和文化翻译不可避免的缺失,译诗不可能完全照搬原诗的韵律形式,但是在诗形上大多仍参照原形,绝大多数还采用押韵方式。《关不住了》原诗是4 句1 诗节,偶句第一个单词后退一个词书写。胡适的译诗也是4句1 诗节,偶句退后一个词书写。这种分节书写方式成为后来新诗创作竞相效仿最流行的方式。此外,胡适在这首诗的第一、第二节都使用了重复的字,即第一节中的“生生”,第二节中的“阵阵”,造成了诗歌原来韵律的适度破坏。同时,胡适还改变了原诗的具体句式,在最后一节的最后两句前加上“他说”,使原诗的句式变成散文句式而更加通俗。被《分类白话诗选》收入的胡适创作的诗歌《江上》,这首诗总共4 句,第2、4 句第一个字均是后退一个字书写。另外一首《一颗星儿》,整首诗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节奏感和韵律可言,诗形组织上也没有一丝规律可循,整首诗与散文并无二异。不仅仅是胡适,郭沫若也是这样。在《新诗集》中,郭沫若翻译了惠特曼《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惠特曼的诗歌在形式上,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歌陈旧的格律束缚,开创了自由奔放的诗风。郭沫若曾经以诗性的语言谈到惠特曼给他带来的震撼:“当我接近惠特曼《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时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他们写在纸上。”[3]213在阅读了惠特曼的诗歌之后,郭沫若彻底被惠特曼雄浑、豪放的调子所激荡,他抛弃了中国传统诗歌外在的形式,依据诗人内在的情感节奏创造了全新自然的诗歌韵律。例如被《分类白话诗选》收入的《日出》,全诗采用回环、反复的手法,在每一节开头都重复“哦哦”,而且每一节的第一句都是感叹句式,造成了咏叹的效果。这是惠特曼诗歌风格直接影响的结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外国诗歌声援了中国早期新诗作为新生的独立文体地位的确立,并且进而对具体的诗歌形式产生了影响。
翻译诗歌与中国早期新诗创作之间也呈现出互动的关系。“五四”译诗在促进中国早期新诗创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从译诗和中国早期新诗的发展诉求来看,二者之间呈现出双向的互动关系。
首先,中国早期新诗形式或理论倡导限制了译诗形式的选择。在中国早期新诗的各种体式中,自由诗与中国古代传统诗歌在形式艺术上的审美差距是最大的,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诗词严谨的排列格式和韵律节奏,真正实现了诗歌在形式上的自由:自由诗没有固定的节数,每节没有固定的行数,每行没有固定的字数,在音韵上也实现了胡适提倡的“句末无韵也不要紧”[4]的简单韵式。因此,自由诗的产生是对传统诗歌形式最彻底的叛逆。在胡适等人大力倡导白话自由诗创作并且身体力行之后,自由诗成为早期诗歌各种体式中最为流行的诗歌体式。正如朱自清所言,“这时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白话译诗渐渐的多起来;译成的大部分是自由诗,跟初期新诗的作风响应。”[2]70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 世纪20 年代的译诗形式迎合了中国新诗的形式。《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中收入的三十多首译诗,几乎都是自由诗的形式。而胡适通过一首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布新诗成立的“新纪元”,更加证明“五四”时期,自由体形式的译诗和自由体形式的创作几乎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在中国新诗诗坛上出现的时间几乎也是同时的。
其次,创作对于翻译诗歌内容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五四”时期是追求民主、追求独立自由的时期,是开放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民主、进步、豪放而不是奴役、保守或者内敛含蓄。在“五四”运动之前,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深受泰戈尔的影响,这段时间他也创作了一些泰戈尔式的恬静小诗。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特征,让郭沫若感到诗歌创作必须与时代风潮相应和。惠特曼诗歌不受传统束缚、强烈表达炽热情感的叛逆风格深刻地撞击着中国一大批诗人的灵魂深处。因此惠特曼的诗歌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之音以及粗犷豪放的气魄正好迎合了郭沫若对民主自由的期盼。郭沫若曾经以这样一段已为广大研究者所熟知的文字,来强调惠特曼诗歌对其创作的意义:“我的短短的作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5]《分类白话诗选》中田汉的3 首译诗,都是选自他翻译的一篇文章《诗人与劳动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 卷第9 期。这篇文章也是田汉在其新诗创作的早期阶段发表的4 篇重要的诗学文章之一。同样出现在这一期《少年中国》上,还有田汉创作的一首诗歌《竹叶》。诗中提到的“劳动家”,其实是指日本的一名产业工人,在“人家都忙着过年的时候”,他“只唏唏嘘嘘的在那儿痛哭”。这首诗既体现了诗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同时诗人以饱蘸同情之心的笔触描写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他所倡导的平民主义精神。在稍后也就是1920 年田汉创作的另外一首诗《漂泊的舞蹈家》中,他直接喊出了“与其与艺术奉事贵族,何如以艺术救济平民!”艺术的“救济”,目的在于“慰藉”大众的种种“痛苦”,诗人希望艺术家们能够真正与平民大众统一阵营,与他们“一块歌”、“一块哭”。这两首诗体现了诗人彻底的平民诗人的姿态。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田汉会选择英国诗人戈斯璧《一个大工业中心地》《最后的请愿》和《骂教会》这3 首诗来翻译。在《诗人与劳动问题》这篇文章中,田汉既关注诗人与劳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诗人通过对社会黑暗毫不留情的揭露,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底层大众的同情。综上所述,郭沫若、田汉的早期新诗创作引导着诗人去选择那些与其创作的旨趣和所表达的情感相近的作品去翻译,而他们在译诗里也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中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
最后,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也直接决定了其诗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新诗理论的倡导和新诗创作的实践方面都扮演着拓荒者角色的刘半农,明确提出新诗创作应该写实求真,“可见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6]我们以他创作的第一首新诗作品《相隔一层纸》为例。这首诗纯用口语,以对比的手法真实地刻画出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在这首诗里,老爷和叫花子的生活,仅一层薄纸之隔,迥然两重天地。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使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得以真实再现。刘半农的诗歌大部分创作于新诗拓荒期,在诗歌艺术技巧上不够成熟,我们自然无法苛求他达到后来的徐志摩、卞之琳等人的高度。但是正如鲁迅曾针对指责刘半农诗歌思想浅薄的人所作的反驳一样,“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他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7]“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刘半农以其诗歌创作实践着这一精神。与他的创作观念一脉相承,刘半农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念:“我们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译。因是直译,所以我们不但要译出它的意思,还要尽力的把原文中的语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为直译并不就是字译,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自然。”[8]在《分类白话诗选》中,刘半农惟一的译诗《海滨》鲜明地体现了其直译的翻译理念。被称为“泰戈尔诗歌翻译第一人”的郑振铎,同样也翻译了这首诗。通过对两者的对比,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刘半农直译的特色。以第一段为例。刘半农译为:“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会集着。无边际的天,静悄悄的在头顶上;不休止的水,正是喧腾湍激。在这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呼噪,跳舞,会集起来。”而郑振铎的翻译是:“小孩子们会集在这无边际的世界的海边。无限的天穹静止地临于头上,不息的海水在足下汹涌着。小孩子们会集在这无边无际的世界的海边,叫着跳着。”郑振铎的翻译无疑更富文采,更接近中国人的语法习惯。而刘半农的翻译,从结构到内容,更忠实原文和作者本意,尽可能少地增加译者的感情和观点。《分类白话诗选》中郭沫若的两首译诗均出自田汉《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这篇文章,《暮色垂空》与《感情之万能》都是田汉请郭沫若代为翻译的。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郭沫若有一段附白:“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9]虽然在这一段附白里,诗人并没有对“风韵译”作进一步的言说,但是我们联系郭沫若当时的诗歌创作情况就可以推断出“风韵译”的真正内涵。1920 年1 月18 日,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首次从创作主体情感表现的角度发表了对诗歌的看法:“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诗歌),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3]237在同一封信中,他又通过诗人与哲学家的比较,称“诗人是感情的宠儿”[3]240。正如茅盾所说,郭沫若是“五四”诗坛的“霹雳手”。在那个地震式的大变革时代,郭沫若极为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精神,迅速发出激越的呼喊,以雄浑、豪放、宏朗的调子掀起了紧张、激动、奋发的情感风暴,猛烈地冲击封建罗网。《日出》就抒写了由这种乐观情调和革命精神带来的欢畅激情。因此,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观念也就决定了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不可能简单地直译或者意译,他的落脚点在于不违背作品原意的基础上译者自身的情感表现。到此,我们可以说,所谓“风韵译”,就是要在所翻译的诗歌中完成一种译者主体的情感呈现。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刘半农选择的“直译”,还是郭沫若选择的“风韵译”,都是由诗人前期诗歌创作实践直接决定的,他们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身创作观念在翻译领域的另外一种延续。
“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潜力、激情、变革的年代,从“五四”中成长起来的,或是受“五四”影响的中国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外国文学译作的惠泽。在《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这两部早期新诗选集所涉及的诗人当中,尤其是其创作和译诗均被收入的诗人,其翻译与创作这两条线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既并行发展,也互相渗透、互为补充。他们几乎全都是经过翻译实践之后又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着掺杂自己的翻译所获。他们在翻译外国诗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借鉴被翻译作品的主题风格、结构题材、情节构思、语言特点等。于是他们一边翻译,一边模仿,从被翻译的诗人以及作品那里提炼出自己所能接受或者自己所需要的艺术技巧,然后加以诠释、改造、利用,再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以及自己所寄予读者的期待视野,创作出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他们重新回到翻译活动中,又自觉不自觉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心得和才能渗透到翻译过程中。于是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彼此相对而行,由翻译到创作,再由创作到翻译,来来回回,相互促进。当然,我们以上所有的分析与研究必须基于以下事实,那就是中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轨迹,它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成长起来的,译诗引入的异域文化和新鲜营养仅仅对早期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促动作用,而不能成为根本原因。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8.
[2]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372-373.
[3]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C]∥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303.
[5]郭沫若.学生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8.
[6]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J].新青年,1917,3(5).
[7]鲁迅.忆刘半农君[J].青年界,1934,6(3).
[8]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3:27.
[9]郭沫若.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J].少年中国,1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