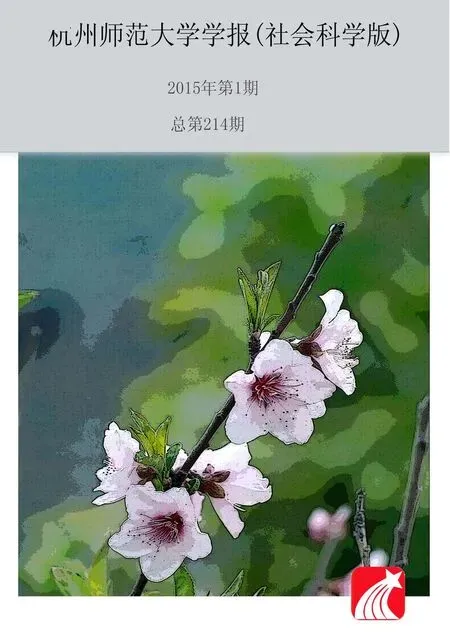论哈维的三种巴黎空间
陆 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一、1948:现代性的神话
大卫·哈维作为今天英语世界与曼纽尔·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三足鼎立的空间理论领军人物,其对城市和社会公正的描述一向引人关注。在他卷帙浩繁的相关著述中,巴黎的城市空间显然是一个焦点。梳理这一段因缘,我们可以发现,哈维大体是以历时态的叙述,给我们展示了巴黎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第一时尚都市的三个空间视野。假如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它们分别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奥斯曼的巴黎和列斐伏尔的巴黎。
我们可以从他2003年出版的《巴黎:现代性的都市》说起。该书开篇的话题是现代性。作者说,关于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就是判定它是过去的决裂。这决裂是如此绝情而又绝然,以至于世界仿佛白板一块,新世界可以在上面尽情书写,但凡有过去横亘中间,那也只管删除便是。这样来看,现代性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管它是温和民主的也好,创伤革命的也好,抑或独裁专制的也好。这类现代性之所以是神话,哈维说,据他观之是因为在重复大量并非如此的证明面前,它依然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和影响力。而另一种现代性理论发端于圣西门,马上就给马克思接手,它认定社会制度的任何变革,必先孕育于现存秩序之中。问题是,圣西门也好,马克思也好,这两位现代性的先贤一方面坚决否定决裂传统,一方面又在鼎力鼓吹革命。革命能够不破坏传统吗?你能够不打破蛋壳做出一份煎蛋来吗?事实是一切新世界的建立,必以打破旧世界为先决条件。这样来看,言说现代性,“创造性解构”当非无稽之谈。
哈维大量引用法国19世纪著名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的巴黎时态像,图文并茂,洋洋洒洒讲开了巴黎的故事。这段故事的起点是1848年:
在这之前,城市愿景充其量不过是浮光掠影,修修补补中世纪城市的基础建设;在这之后,有奥斯曼大开大合将巴黎拽进了现代性;在这之前,有古典主义者安格尔和大卫、色彩主义者德拉克罗瓦;在这之后,有库尔贝的写实主义和莫奈的印象主义。在这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及小说家,如拉马丁、雨果、缪塞和乔治·桑;在这之后,有洗练紧凑、精雕细琢的福楼拜的散文和波德莱尔的诗。在这之前,是一盘散沙的制造工业,由工匠行会分头组织;在这之后,它们大都给机器和现代工业取而代之。在这之前,小店铺沿着狭窄蜿蜒的街道,或在拱廊里面开张;在这之后,巨大的百货商店闪亮登场,张牙舞爪挤兑到了大街上面。在这之前,流行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之后,是精明务实的管理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PP.2-3)
在这一长列排比句里,作者的激情跃然纸上。一切的一切无不表明,1848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时刻,许许多多的新生事物从旧时代中破茧而出。这一年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848年的巴黎见证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英勇巷战。这是平民阶层和君主政府的对决,其结果是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国王逃往英国。巴黎成立诗人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昙花一现的第二共和国由此诞生,并且最后由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坐定总统位置。哈维重申这场革命就是典型的“创造性的破坏”。群众攻进国王的杜伊勒里寝宫,大肆劫掠,割烂了所有绘画,挨个儿坐到王位上过瘾。然后王座给拖到巴士底,付之一炬。哈维指出,巴尔扎克虽然急着去俄国幽会他心爱的韩斯卡夫人,但还是忍不住亲自赶到杜伊勒里一观究竟。福楼拜也到了巴黎,20年后的《情感教育》中,作者精准又详实地回溯了这一事件。波德莱尔则直接卷入了这场革命。后来成为巴黎空间大改造幕后推手的奥斯曼,当时则在布莱任副省长,事发两天后才得到消息,跟其他外省人一样,他感到惊诧不安,认为临时政府不合法统,罢官以示抗议。但最终是这位波拿巴主义的拥趸,破旧立新开启了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哈维发现,奥斯曼1853年受命政变称帝的拿破仑三世,主掌巴黎的现代化工程之后,是立志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来进行创造性的破坏。重建巴黎基础设施的计划七月王朝时期即已出台,如在凯旋门和西边的布洛涅森林之间新建大道,改造中央市场等。但奥斯曼总体上对现成的计划视而不见,甚至皇帝的指示也是虚与委蛇,一心创立一个与过去决裂的神话,而事实上这个神话也一直维持到了今天。这里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创造出建国的神话,这对于一切新政权都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二是让人相信独裁帝国施行仁政,它是唯一选择。哈维特别提到了著名建筑家维克多·巴尔塔(Victor Baltard)被人戏称为“市场堡垒”的中央市场(Les Halles)最初设计。它修到一半给拿破仑叫停,皇帝说是他宁可要一把“钢铁雨篷”。巴尔塔另起炉灶,果真就交出了这么一个钢铁支架的超级市场。奥斯曼觉得这个1855年完工的古典又现代的中央市场,正合心意。哈维却觉得遗憾,巴尔塔这一类空间巨大的新科技拱廊建筑,如何就没有给本雅明的法眼看中,收入他的《拱廊街计划》呢?
哈维对奥斯曼全面改造巴黎的计划表示赞许,认为这个计划虽然是个与过去全盘决裂的神话,故而值得质疑,但是它毕竟在新科技和新组织的启发和推动下,给巴黎带来剧变,使巴黎甚至包括它的市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1848年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分水岭,哈维强调,不光是奥斯曼的勃勃雄心,甚至福楼拜、马克思和波德莱尔,也都是1848年之后才锋芒毕露的。在福楼拜,只有在1848年根除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幻想之后,几近潦倒的他才抛弃对巴尔扎克的物质主义偏见,从1851年开始,历时5年埋头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在马克思,1848年他正流亡伦敦,但是他是年3月确实到过巴黎,假如没有1848年至1851年间巴黎发生的那些事件,马克思不可能摆脱早年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热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这当中的差异,只要比较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日后的《资本论》,便见端倪。在波德莱尔,哈维指出,这位现代性的使徒每天都生活在传统和反传统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一个愤世嫉俗的偷窥者;一方面又是一个热烈追求美好目标的人。1848年他参加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可是理性幻灭之后,又转向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造就了波德莱尔一力鼓吹的美学现代性的不尽魅力。
二、巴尔扎克的巴黎
那么,1848年之前的巴黎是什么模样?《巴黎:现代性的都市》的第一部分《表征:1830—1848年的巴黎》,是通过巴尔扎克的视野得以展示的。哈维指出,巴尔扎克是用散文来描绘老巴黎的日常生活,但是其中并非没有诗意。巴尔扎克的全部小说绝大部分以巴黎为中心,从1828年到1850年巴尔扎克51岁去世,《人间喜剧》约90部长短小说,差不多都是在这20余年间写成的。要从这些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中挖掘出现代性和巴黎的神话,自然殊非易事。言及空间,哈维指出,巴尔扎克小说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作者很明白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种生活方式,它揭示你是谁,你干什么,你来自哪里,你又在追求什么。故分隔不同阶级的物理距离,一样是展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道德距离。而社会阶层的分隔,不仅见于横向的空间生态,同样见于垂直的空间表现,诚如巴尔扎克所言,巴黎的脑袋在阁楼上,那里住着科学家和天才;二楼装着满满当当的胃;底楼店铺林立,那是腿脚,因为忙碌的商人就在这里进进出出。哈维特别引了巴尔扎克小说《十三人故事》中一大段巴黎社会中看门人的角色描写,认为它正可印证巴尔扎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空间理念:每一个历史时期,上层阶级与贵族的巴黎都有它自己的中心,一如无产阶级的巴黎亦有它自己的空间区域:
在巴黎这座张牙舞爪的巨大城市里,每一部分的面相都有其不同类型,而这些类型又天衣无缝地配合着城市的总体性格。所以看守,或者说看门人、门房,不论我们管巴黎这巨兽体内这个基础神经系统叫什么名字,他总是跟他工作的地区匹配无间,而且经常还是画龙点睛。圣日耳曼区的看门人每一条衣缝上都有穗带,是条悠闲的汉子,还研究政府股票;昂丹大道的门房过得舒坦惬意;证券交易所的看门人各自看报;蒙马特区的看门人兼做生意;红灯区里,门房本人就是退休的妓女;在玛莱区,她可敬可畏、特立独行,想入非非。[1](P.39)
《十三人故事》是巴尔扎克第一部巴黎场景小说集。哈维认为,巴尔扎克上文所展示的空间模式,意义远大于门房这个阶级的范围。只要有人跨出自己的空间,即在错误的时间进入错误的空间,他就得死。故小说人物倘若越位,就是搅乱生态和谐,玷污道德秩序,必须付出代价。如朱丽夫人出于对父亲费拉古的一片孝心,进入一个与她社会身份不相符合的地区,结果就身体疾病和精神摧残双管齐下,死于非命。
但哈维发现巴尔扎克的空间视界也有一个演进过程。即是说,早期作品如《十三人故事》中壁垒森严的空间等阶,到了后来有所松动。如晚期作品《邦斯舅舅》,天下好吃者无出其右的同名主人公,就是断送在他可恶的女门房手里。因为这个公寓女管理员不光掌管着邦斯舅舅的居住地,给他提供一日三餐,而且还利用看门人关系的“神经系统”,编织了一张阴谋大网,同网络遍布整个巴黎的歹徒结盟,轻而易举盗走了邦斯舅舅品位极高的绘画和古董收藏。这可见,即便是处在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如此这般来主掌和生产空间,由此来颠覆既定的空间模态。
本论文为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委托课题《伏牛山区农业生物质资源研究与分析》(课题编号:2017W015)阶段性成果
哈维特别注意到巴尔扎克对巴黎的大街小巷和公共景观倾注的满腔热情。认为它可以让我们从多重视野来了解巴黎。一方面有万花筒般旋转不休的迷宫;一方面又有若干稳定中枢,辗转承合城市意象,使之定型下来。如圣日耳曼区、右岸那些大道上的商业世界、证劵交易所、皇宫、圣奥诺雷街、索邦周围的学生区,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人阶级的影子。还有巴黎美轮美奂的标志性景观,歌剧院、各种剧院、林荫大道、咖啡馆、纪念碑、公园等等,它们星罗棋布点缀在城市的幕布上面,给城市生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络,使它不再晦暗不明。特别是巴黎的林荫道,那真是充满诗情,是城市的象征。
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小说的空间观念是雄心勃勃的,即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消灭时空,进而主宰世界的崇高欲望。这是笛卡尔和歌德的传统。动态与静态、流动与运动、内部与外部、空间与地方、城镇与乡村,这当中的辩证关系值得深究。哈维指出,巴尔扎克是有心占有巴黎的,可是他对这个城市太多敬重,太多热爱,将它当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道德实体,结果就很难对它颐指气使。所以他的占有欲并不是破坏欲。巴尔扎克需要巴黎来滋养他的形象、思想和情感,他不可能像以后的奥斯曼和福楼拜一样,把巴黎当做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巴黎不但有血肉之躯,而且有人格品格。所以,巴黎这个“最漂亮的怪物”,经常是被描绘为女人形象,用《十三人故事》中的话说,她既悲伤又快乐、既丑陋又美丽、活力十足又死气沉沉,每一个人,每一栋房子,都是这个伟大妓女的一片细胞组织。可是巴黎的大脑功能却是男性的,他是全球的思想中心,是引领文明的天才、不断创造的艺术家,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哈维指出,巴尔扎克的巴黎愿景就是流行于19世纪的巴黎形象。他这样比较了巴尔扎克和奥斯曼的巴黎情结:
奥斯曼装备了气球和三角测量台,开始来重建巴黎的时候,一样也是在想象世界里占有了巴黎。不过这里有个重大差异。在于巴尔扎克是一意孤行欲发号施令,穿透、分解,然后将与这个鲜活城市相关的一切吞下肚去,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于奥斯曼,则是将这一异想天开的冲动转化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计划,其中国家和金融家将来领导表征和行动的技术。[1](P.50)
国家和资本将替代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巴黎幻想。在哈维看来,这就是奥斯曼改造巴黎的实质所在。
三、奥斯曼的巴黎
奥斯曼受命拿破仑三世,主掌改造巴黎的命运,是在1853年6月,第二帝国成立后的第七个月。哈维认为延续了18年的第二帝国并非如梯也尔预言的那样“痴呆”,也未必就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滑稽”,反之它是个同时拥有警察力量和民意基础的独裁国家,是一场相当严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拿破仑及其幕僚有心将巴黎连带她的经济、文化、生活,从坚固的中世纪束缚中解放出来,应是势所必然。有些工程是迫在眉睫的,如改善通往中央市场的交通道路,清除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和通往市中心的交通等。在于奥斯曼,哈维觉得他具有浓重的马基雅维利情结,口头上全心全意贯彻皇帝的意志,实际上雄心勃勃,压根不把异议和民意放在眼里。不管怎么说,奥斯曼着实是在政界大放了一阵光彩。
但哈维发现奥斯曼有一点甚是吊诡,即他一方面对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经济体面临的种种危机了如指掌,一方面他的反应却总是集中在叫人非常头疼的细节问题上。比如他仔细监督街道设施的设计,包括煤气灯、报摊,甚至行人小便处的设计,而且他分明是给直线迷住了。如调整塞纳河上叙利大桥(Pont de Sully)的角度,以使先贤祠和巴士底的立柱成一直线,又大费周折将胜利纪念柱移到了新建的夏特莱广场。总而言之,到奥斯曼失势被解职的1870年,他启动的城市转化已经势不可挡,无人能够阻挡它的脚步。另一方面,哈维强调,巴黎外部空间关系的转化,也给内部空间的协调带来巨大压力。就此而言,奥斯曼的成就堪称现代主义都市规划最伟大的传奇之一。奥斯曼有皇帝的支持,又有大规模公共工程来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这都使他能够有条不紊地对巴黎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空间构架进行重组。故投资不仅涵盖了新的道路网络,而且波及下水道、公园、纪念碑和标志性空间、学校、教堂、行政建筑、民居、旅馆、商业用房等等,不一而足。总之:
奥斯曼展开的都市空间概念无疑是相当新颖的。他不是“东拼西凑将彼此少有联络的一条条公共大道计划集合起来”,而是追求一个“总体规划,其中细节不厌其详,足以将各地互不相同的地方环境完美协调起来”。空间被视为一个整体,其间城市的不同区块和不同功能相互牵掣,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整体,奥斯曼也是这样做的。[1](P.106)
但是哈维更看重的是资本在空间重组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奥斯曼虽然大权在手,而且经常是异想天开,可是也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其实是多有限制的,知道巴黎要转型,光是将物流和民众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他必须启动资本的流通,而且事实上到头来是资本主掌了奥斯曼本人。这也是第二帝国成立之初必须面对的现状。它要生存,就必须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而转化了巴黎内部空间的公共工程,也通过有的放矢重新布置原有环境的空间格局,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通。而资本一旦挣脱它的封建紧身衣,便根据自身独特的原则来重组巴黎的内部空间。哈维强调说,奥斯曼希望将巴黎建成一个对得起法国,倘若不说对得起整个西方文明的现代首都。可是到最后,他整个儿就是推波助澜,将巴黎打造成了一座资本流通成为真实至尊权力,掌控一切的城市。新的空间关系对巴黎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深远,给巴黎人造成的情感冲击,更是举足轻重。仿佛他们一头钻进了一个不断增速,空间关系给急遽压缩的眼花缭乱的世界。所以不奇怪,第二帝国在经历剧烈的时空压缩之后,反作用也纷纷冒将出来,特别是空间和地方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如新投资总是趋向于巴黎行政、金融、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化,这就将国家疆域内政治权利如何处理地理集中和地理分散的棘手老问题,重新推了出来。导致建构公民权利和政治认同过程中,社区扮演怎样的角色,也成为论争焦点。中央集权仿佛是天经地义。哈维引拿破仑的话:巴黎就是中央集权;又引奥斯曼的话:巴黎就是法国的大脑和心脏。君臣一唱一和,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可是这自豪在挑战地方共同体的生存和意义,甚至危及巴黎内部的地方共同体。政治利益的地理疆界愈益模糊,这又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地方空间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诉求?
哈维在他的多种著述中区分过三种空间。其一是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这是欧几里得、牛顿和笛卡尔的空间,通常表现为先天存在的和固定不变的坐标方格,亦即我们的物理空间,如国家领土、城市规划等。其二是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它涉及爱因斯坦的理论,比如根据交通方式的不同,可以绘制出完全不同的距离地图。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和拓扑关系来确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它当然也影响到现代人对世界的看法。其三是相关的空间(relational space)。这是莱布尼兹的理论,反对牛顿式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仿佛上帝都处在这样的绝对时空之内。相对的时空暗示时间和空间的内在关系,会把我们带到数学、诗和音乐的汇聚点上。假如有人问天安门广场和世贸大厦遗址意味着什么,那么回答只能是按照相关的状况来进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中提出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关键概念,哈维认为它们大体正可对话他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的空间:
一切属于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存在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领域中。个体劳动者、机器、商品、工厂、道路、房屋、实际劳动过程、能源消耗等等,全都可以在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框架内部被个性化、描述和理解。一切属于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存在于相对时空之中,因为交换需要有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和人员在实践和空间中运动……资本的循环和积累发生在相对时空之中。然而,价值是一个相关概念。因为它的所指是相关时空。马克思(有点令人惊讶地)宣称,价值是非实体性的,却是客观的。[2](P.147)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错综复杂的空间认知,以及它同权力和生产过程密不可分的联系,哈维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的名言,“在权力空间中,权力并非如其本然显示于人,它隐藏在空间的组织里。”[3](P.370)进而指出,奥斯曼很显然明白他手里这一形构空间的权力,一样也可以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比如,他很显然希望巴黎能摆脱它的工业基地和工人阶级,如此或者可以摆脱革命,成为支持资产阶级秩序的温和堡垒。这个愿景太为宏大,一代人难以完成。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最后几年里,奥斯曼当年的这个梦想,才最后成真。但是,奥斯曼不断施压巴黎的重工业和污染工业,甚至轻工业,以至于到1870年,巴黎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工业化。工人阶级也大都被迫迁出城市。市中心让位给了帝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以及行政、金融和商业区域,还有急剧增长的旅游服务业。这大体上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模样。
四、列斐伏尔的预言
今天的巴黎什么模样,哈维似乎并不乐观。他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是从列斐伏尔的预言出发,分析了今日都市的动乱动因。该书序言就起名为《列斐伏尔的愿景》,作者一开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有位生态主义者给了他一张招贴画,画面上是熙熙攘攘的旧巴黎邻里生活景象:阳台上鲜花盛开,广场上老老少少摩肩接踵,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咖啡馆铺天盖地,喷泉流淌,行人休憩河岸,还有星罗棋布的社区公园。当此良辰美景,真叫人情不自禁欲找三两好友一叙心扉,或者掏出烟斗抽上一把。哈维说,他非常喜欢这张宣传画,可是天长日久,破损严重,他给扔了。如今,他真希望有人把它重印出来。
那么今天的巴黎呢?也许我们永远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今天的巴黎在哈维看来,城市景观是令人沮丧的,与那个充满生机、极具亲和性的老巴黎适成对照。对此哈维的描述是,意大利广场周围幢幢高楼林立,虎视眈眈,仿佛欲同56层身高的蒙巴纳斯大楼联手,里应外合入侵老城。还有计划中左岸的快速路,13区和郊区那些毫无个性的公共廉租房,千篇一律的商业化街道。当年玛莱区生机勃勃的手工作坊、巴士底杂乱无章的房舍、孚日广场的曼妙建筑,今天都给毁于一旦。总而言之,从20世纪60年代起,巴黎就在历经生存危机,老的不能长久,新的又太不中看,空空洞洞没有灵魂。哈维认为法国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1967年的影片《我略知她一二》(Deuxou trios choses que je sais d’elle),是用审美的眼光,恰到好处捕捉到了这个敏感时机。电影讲述一个已婚母亲做兼职妓女,究其原因,固然是有生计的无奈,可是也有生活的无聊。电影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大举入侵巴黎,越南战争本来是法国的事情,如今给美国接手,巴黎郊区的扩张工程中,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没心没肺的消费主义全面登陆城市的街道和店铺。不过哈维对戈达尔以妓女之口来对建筑和城市发表无厘头感慨的先驱后现代作风,并不以为然。
哈维指出,同样是在1967年,列斐伏尔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城市的权利》。这权利既是一声呼喊,又是一个要求。所谓呼喊,是回应城市里日常生活日益凋敝的生存危机;所谓要求,是指清醒认识此一危机,以创造一种全新的都市生活。它将少一些异化,多一些意义和游戏。但是诚如列斐伏尔的一贯描述,它也总是布满冲突和辩证契机,永远开放通向未知的新世界。今天回过头来看列斐伏尔这一时期的写作,哈维发现时不时可以读出海德格尔、尼采和傅里叶的影子,或者对阿尔都塞、福柯的默默批评。当然,整个框架必然是马克思的遗产。但是,哈维呼吁学者关注实际上经常被当代学者忽略的社会空间维度。即是说,今日流行城市的各种情绪,都是从街头产生的,拆迁改造工程似乎是无所不在,有些区域像中央市场那样,给整片整片推倒重来。街头游行的悲欢喜怒,13区廉租房地带那些星罗棋布的越南餐馆,毫无个性的郊区中,给边缘化后的绝望,失业率上升导致年轻人无所事事,这一切最终都将是动乱的根源。
哈维认为列斐伏尔是清醒意识到城市的这一反叛态势的。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权利》是提供了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潜在动因,而这一部分的研究,恰恰是被日后的学界所忽视了。哈维强调说,1968年巴黎革命之后那段和解时期里,当城市生活经历文化转型,赤裸裸的资本披着商品拜物教、小众市场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外衣,扮演的角色远不是清白无辜的。一如当年萨特等人创办的《自由报》,就渐而转向个性十足的文化激进主义,政治上却不温不火。他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城市的权利这个问题有所复兴。街头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都不例外。可以达成共识的则是,城市权利的思考主要并不是发生于各式各样的学院幻想和流行时尚,而是来自街头底层阶级的绝望呼喊。而关于“工人阶级”的构成,哈维注意到列斐伏尔已经在暗示它并非清一色出自工厂的产业工人,反之成分比较分散凌乱,目标和需求也各各不同,经常处在流动不居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假如从革命而不是改良的角度来看城市权利这个问题,那么列斐伏尔的预言就绝不是明日黄花:
无论如何,列斐伏尔立场背后的逻辑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是更进一步强化了。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厂要么消失,要么缩减,导致产业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创造和维持都市生活的日益扩张的重要劳动,越来越靠那些毫无保障、经常是临时性质的劳工完成,他们没有组织,收入低下。所谓的“朝不保夕阶级”(precariat)替代了传统的“无产阶级”。倘若我们的时代会发生革命,至少在世界的我们这一部分(如另一边有正在工业化的中国),这个问题丛生,漫无组织的“朝不保夕阶级”,是必须认真以待的。[4](p.xiv)
哈维一向对列斐伏尔推崇备至。《空间的生产》1991年出英译本,后记即是哈维所撰。除了向英语世界全面介绍列斐伏尔,哈维指出,1968年之后,列斐伏尔开始特别关注都市化的性质和空间的生产。但是对都市问题的关注,很快又导致他否认城市在现代生活中具有任何意义实体地位,认为作为实体的城市必给都市化过程,或者广而言之,空间生产的过程取代。由此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都以完全不同的崭新方式连接起来。这样来看,列斐伏尔曾经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也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革命政治也好,最终将在一个恒新恒异的空间生产的背景中,得以重新阐释。
巴黎是引领天下浪漫时尚的现代性之都。雨中漫步在拉丁区的鹅卵石街道上,感觉优雅寂寥,恍惚而又迷离。从巴尔扎克笔下的曲折小巷,到奥斯曼督建的星形广场和金碧辉煌的巴洛克歌剧院,一切无不时时刻刻发散出迷人的古典现代性光泽。但是巴黎也有阴暗面。当年波德莱尔作为19世纪藏污纳垢都市里的“游荡者”,他所见证的巴黎,到今天也还是栩栩如生。特别是美丽城这样的“朝不保夕阶级”的城中之城,依然是女孩晚上怯于单身行走的罪恶滋生地。2005年发端于巴黎郊区的移民暴动,迄今让人记忆犹新。它亦足以显示,列斐伏尔的预言并没有过时。
由此我们看到哈维笔下的三种巴黎空间。它们分别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奥斯曼的巴黎和列斐伏尔的巴黎。从现代性的尺度来看,前者可谓自然的空间,以物理空间标界出社会等级。诚如巴尔扎克所示,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揭示出你的身份和欲求。其次是资本的空间,就像哈维所言,奥斯曼重造巴黎,必须启动资本的流通,可是到头来资本反客为主,主掌奥斯曼本人,成为了巴黎至高无上的第一主人。最后是反叛的空间,一如列斐伏尔的预言,今日都市的各种流行情绪,都是从街头产生,拆迁、移民、失业,这一切最终都将是动乱的根源。这三种巴黎空间叙述不光是历时性的描述,而且一样具有毋庸置疑共时性的意义,无论对于巴黎这个古典现代性的地标,还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中一切如火如荼抑或不动声色的都市再规划,它未必不是一个形象写真。故而,假如我们判断它们一定程度上都在呼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关键概念,应当不是夸张。即便经过奥斯曼的大规模改建,巴黎市区依然建筑密集,小巷曲曲弯弯一如迷宫,多首尾相衔泊于小街的汽车,在这个大都会中心的地位,显得相当尴尬。无论如何,当绵长雄厚的历史成为浮光掠影,当美和艺术的经典成为走马观花中的飘忽拟像,巴黎将会记住大卫·哈维煞费苦心,立足资本,为她量身打造的城市空间分析。
[1]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M].New York:Routledge,2003.
[2]大卫·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C]//外国美学:第22辑.阎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
[3]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M].Paris:Anthropos,1974.
[4]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M].London:Verso,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