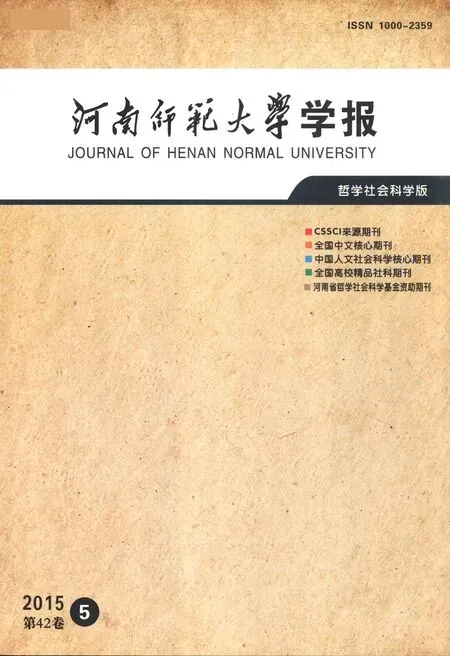文学与图像关系论析——从书画的同源异流关系出发
原小平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453007)
文学作为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其诸多特性必然会受制于语言文字这种媒介的形式和质料特点。而从语言文字的起源来看,图像性则是其突出特质:“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1]因此,若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就必须从探究语言文字的起源与性质开始,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指出的那样:研究文学的学者,“最好还是首先研究语言,然后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2]23-24中国传统的文字学——“小学”,历来也被认为是通经之根本(而中国传统经学也大都可看作文学作品),有“非先通小学无以通经”[3]之说,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文字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与西方学者并无实质差异。
一、书画同源对文学-图像关系的影响
人类语言文字起源和可视性图像密不可分。文字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人类早期的口语与手势。在原始人最初试图表情达意、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身体肌肉的收缩迫使空气从肺部穿过声带发出声音这一动作,与伴随的面部表情与姿态手势,都是同时发生的自然身体反应,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信号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最有效的人际沟通得以进行。比如,美国人类学家科林.M·特恩布尔在他的著作《森林人》中,对生活在刚果伊图利森林中俾格米人借助神情动作相互讲故事的交流过程的描述[4],就是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即使在现代生活中,手势、表情仍旧是口语有效交流的最重要条件——也许只要对比一下广播与电视、普通电话与视频电话的效果差异,就不难理解这种重要性。由于口语和表情手势都是人体对某一情境的进行表达的自然身体反应,这就决定了它们从本性上来讲是难以分离的——倘若分离,必然有所缺憾。并且如果我们考虑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些著名的著作里对视觉的大加赞美之词:“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对于诸神能够给予我们人类的东西而言,这是最大的福气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5]“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6]考虑到在西方长期存在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以及中国长期流传的“百闻不如一见”的论断[6],就不难推想,在人类语言尚不发达的远古时代,表情手势等可视信号很可能在当时的人类交往中还曾居于主导地位。出于对强大视觉的依赖性,当然还为了方便长期保持或远距离传递信息,人类的手势、语言逐渐衍化出了图画、文字等新的事物[8]。
因此,不仅使用表意象形文字的中国有“书画同源”的观念,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英语世界,西方主流语言学也认为:“文字是图画的产物。”[2]实际上,当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言的时候,一方面书面语言仍旧记录有声音可以诉诸听觉,另一方面它也就具有了可视符号的特质。然而,并非所有的语言表达或文字文本都具有文学性质,只是有意味的语言形式,才可能成为文学[9]。
从文学语言的根本意义上来讲,它作为人类语言的一个类别,与科学语言(乃至日常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别。科学语言主要诉诸人的理性思维,突出的是语言的抽象概括性、简洁准确性和逻辑推理性,典型代表是数学符号;文学语言主要诉诸人的感性思维,突出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含混性和感悟性,典型代表是诗歌语言。中外的文艺理论,都对此有过做过精彩论述。比如刘勰就认为文学构思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0]。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则指出语言有两种形式:“推论的形式”和“表现的形式”,文学艺术主要使用的是后者[11]。他们都强调了文学语言要倚重形象,尽管这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理形象,但无疑和包括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沟通——正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所认定的那样:各种艺术都在模仿事物,只不过使用的媒介不同而已[12]。
换言之,文学语言比之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是更具原生态、本初性的语言,这应与文学艺术指向人类内心世界,天然追求内在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感悟(不同于科学指向外在客观世界,追求理解与掌握客观世界的结构与运动规律)有密切关系——现代人类心灵的种种欲望与悸动,与原始人类不见得有多少本质性区别,那么,原始人类表达与交流思想情感的许多基本模式,也仍旧适用于现代社会,同样可以使现代人感动得潸然泪下或欢呼雀跃,尽管许多可以深刻撞击人类心灵的原始模式在现代社会被层层帷幕以“文明”的名义所遮蔽,但它们常常改头换面仍深藏在文学之中,也正因如此,文学语言在深层面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的原初状态,具有更多的绘画性。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绘画性、形象性(亦即图像性)常常成为了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例如苏轼称赞王维的诗歌是“诗中有画”),那是因为,某种恰当的典型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通用的心灵交流、生命表达模式。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神话原型批评的合理性,并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神话原型批评家们,在强调和盛赞文学原型(原始意象)那种能够突然且剧烈地拨动我们内心最深处琴弦的神秘力量的同时,还强调文学语言的绘画性,认为其在呈现模式上,是“近似图画的有寓意的符号体系”[13]。因为它们都是那种来自远古的人类精神纽结点的一体两面,具有天然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还认为原型本身就是心灵图画[14]。这实际上揭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原型)还是在语言(形象)上,都具有明显的绘画性或曰图像性。这种高级的艺术境界,中国的传统文论称之为“意境”:“意”偏重于文字,“境”偏重于图画,两者浑融无间,是意境高妙,如此,方为文学艺术的上品。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存在一个强大的文人画传统,那是因为:“绘画是文学的梦”[15]15。而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一方面将作家与梦幻者相提并论,认为文学作品本质上就是白日梦,另一方面又认为:“梦虽不是全部却也是以压倒优势的视觉意象进行思维的。”[16]46“梦的显意大部分是由图画似的情境组成的。”[16]648可见对图画与文学这种关系的认识,中外皆然。
由于文学原型的图画特征,所以我们看到文学作品常常会表现出一种返本(向绘画靠拢)的冲动,并且,如果文学作品越具有经典性,其中的文学原型感召力就越大,激起的返本冲动也就越强烈。这似乎可以解释这样一系列疑问:为什么文学作品常常配有插图?为什么经典的作品常常会吸引更多的艺术家为它们创制更多的插图(或会获得更多的影视改编机会)?为什么人们尤其是专业人士,会对某些文学作品的拙劣插图或疏离原著式影视改编表现出强烈不满?为什么人们又常常会对另一些文学插图或影视改编表现出赞赏态度?文学作品返本冲动的另一个表现是,经典作品,如果没有经典性的插图的话,那么具有艺术性的书法,尤其是作者的书法原迹或作品手稿,就比那些规范划一的印刷文本,更让人感觉韵味悠长,这是因为书法原迹或手稿,尤其中国的传统书法,显然更接近与绘画,也更具心灵图像性质与原型意味。于是,有些经典性文学作品的书法原迹,如苏东坡的书法《赤壁赋》、毛泽东的手迹《沁园春·雪》、鲁迅的手稿等,也常常被作为书籍插图,这都说明了文学、文字、图像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对此,西方学者也颇有认识,认为文学家的照片和手稿所引起的视觉反映,“对文学阅读和欣赏有直接帮助”[17]。
二、书画异流对文学-图像关系的影响
一方面,文字作为书面语言和图画具有同源关系;另一方面,文字和图画还有明显区别,那就是:文字还表示声音,还是人类口头语言的记录符号。而图画显然是纯视觉的艺术形式,并不直接诉诸听觉。原始图画要想成为文字,必要条件就是与人类的原始声音(口语)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我国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说:“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18]这就将图画与文字的渊源关系及本质区别描述的很清楚。在欧美的主流语言学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论述:“文字是图画的产物。一切民族的人民大概都会涂颜色,划线条,刻划,或雕琢,借以制成种种图象。……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就不妨称之为字。……在真正的文字里,有些个字具有双重价值,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了。”[2]357-359
然而欧美的语言学进一步认为,人类的最初有声语言,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区分于其他动物)的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或仅仅是一股空无内容的气流,它具有先验性,它根植于人类独有的悟性(理性、思考能力)。只有会思考的人类心灵才会发明语言和理解语言(即使他是一个哑巴),因为人类的语言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悟性:“就清晰明确性而言,听觉是适中的感官……触觉实在太含混不清了!它无力应付世界,不加区分地感知一切。依靠触觉很难确立一个区分特征,其感觉是难以言状的!视觉则太明亮,它所提供的大量区分特征叫人眼花缭乱;心灵因此为现象的丰富多样所窒息,或许只能勉强区分出一个特征,日后却难以再度识辨。处在视觉和触觉之间的仍是听觉:来自触觉的所有交织成一团的含混特征都被弃置一边!来自视觉的所有过于细微的特征也被剔除在外。但是,被触摸和注视的物体发出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集合起了触觉和视觉所感受到的特征——于是,这个声音就成了词语符号……而通过多样性的统一,通过区分特征的确立,语言便产生了。”[19]57由此不难看出,语言,诉诸听觉的声音,一开始就具有理性思维根本性的功能特征:分析推演(“区分特征”)和综合概括(“多样性的统一”),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初体现:“所有的感官共同发挥作用,而我们仿佛处在自然这所学校里,通过听觉学习抽象思维,同时也学习说话;视觉随理性一道完善起来,而理性的成长则与命名表达的能力相关。”[19]59-60由于语言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最直接的表现,那么,人的语言也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不断增强,也不断改变自己的状态,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少图画特征,整体表现出由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到字母文字,不断抽象化、简略化的演变过程:“所以,任何语言都是通过声音和感觉而形成的一种抽象。语言越原始,抽象的东西就越少,感性的东西则越多。”[19]68汉语的演变史显然也符合上面的分析[20]。这显然也强调了文字相对于图画在表达抽象意义方面的优势,并说明了理性思维在文字由图画演化为符号过程中的作用。
不过,文字表音的特点以及与理性思维的密切联系,虽然使其在历史演变中愈来愈远离图画本源,甚至在现代人类语言系统内出现了许多专业性很强、逻辑严密精确的科学语言,但人类语言的原初本性,毕竟不可能完全丧失,在人类精神为汲取向前力量而不断回顾遥望曾经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人类语言的原初含混性(即图画性),显然会不断彰显,并世代延续,形成“有意味的形式”——文学。然而,文学毕竟又不是纯粹的图画组织,其原型意味是通过具有流动性质的声音符号——文字来表达的,这就使得文学实际上成为了时间艺术,其优势在于:线性的叙事与明晰地表达可意识到的精神世界。相对而言,图像(尤其是图画),作为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常与人类内心深处的具有原型意义的事物相关(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认为: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具有恒定不变的性质,其优势在于:静态的状物与精妙地传达难以意识到的心灵隐秘。由于人类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都同时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流动性和相对静止性,那么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图像艺术,都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优势对表现对象进行完满表现,于是常常需要互补。这样,我们常会看到一幅画,常常需要特定的语言提示,意义才能明晰;或者一个画家常常会在一幅画完成之后感到意犹未尽,情不自禁的在画面上题写诗文。同样,我们也常会看到一段文字,常需要恰当插图的配合,情状才能明了;或者一个作家常常会在一篇文章中感叹:“假如我是画家,那么……”而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作家确实常情不自禁地为自己作品配插图或强烈希望他人能为自己的作品配上恰当的插图,如,冯骥才曾多次谈自己的此种文学创作感受:“我经常往返在文学与绘画之间,这是一种甜蜜的往返。”[15]30-31
文学艺术与图像艺术的这种互补现象,显然是由两者既相关又差异的艺术性质导致的,这就给希望游走在两者之间艺术家们提出了挑战,中国文人固有追求兼擅“琴棋书画”的传统,但无论中外,真正能同时以画家闻名于世的文学家,并不多见,清代郑板桥诗书画皆佳,号为三绝,世人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此类通才少见,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在更为重视分门别类的科学精神的西方社会,文学家兼擅美术的现象就更为罕见,文学与绘画的互补功能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常见的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会努力论证插图与文学作品的异质性与不相容性,西方的艺术理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达·芬奇的《绘画论》、莱辛的《拉奥孔》、再到黑格尔的《美学》、罗丹的《罗丹艺术论》,都强调文学与绘画的差异而将它们视为平行艺术[21]。这样就更增加了两者在西方作家创作中的艺术互补难度[22]17。即使如此,西方的文学理论也不得不承认,文学如果能通绘画结合,就能够更好的表现作者的精神世界,只不过他们坚持认为,由于艺术媒介的差异明显,文学家能否有效地跨越这种鸿沟,是非常可疑的:“无论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做的解释怎样不确定,在艺术家与诗人集于一身的极其罕见的例子中,可以对他们的创作意图进行再好不过的探索。例如,比较布莱克或者罗塞蒂(D.G.Rossetti)各自的诗歌和绘画,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绘画与诗歌的特征(不仅是技巧上的特征)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22]144-145
尽管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图像与文字有同一性,但历史演进所造成的差异又是如此明显:“词与其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字典必须不断修订,因为语言总是在不停地发展。”[23]59而图画在数千年里的变化与新陈代谢,显然缓慢得多。这样,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流动不居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相对恒定的作为视觉艺术的图像之间,关系可能更为复杂。这就更要求我们在对此进行探究时,应有审慎的态度与全面的考察。
三、文学与图像的辩证关系
不难看出,文字图画的同源异流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文学竭力在保持图画原型的特质,另一方面文字演进中逐渐发展的理性力量,又不断将文学牵引向失却诗意的现代荒原。于是,文学与图像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与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等心理学、哲学思潮紧密缠绕在一起,不分彼此;在作者们舞动的理性之刀下,人类精神世界已无法保持完整和谐的画面,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在中国,宋元以来长期存在的繁盛文人画传统,其后也衰微得成了空谷足音:文学与绘画兼长(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那样)在现代中国几不可见。大量的文学不再承担精神家园的责任,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理性地转变成了换取利益的码字工作;各种充斥着商业气息的逼真的影视图像与先锋性的离散的形象同时汹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目迷五色,而据说,这又和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关。当然,图像艺术和文学艺术的这种在现代社会的巨变,从现代生活汲取了许多东西,也并不见得总是破坏的象征,但古典主义的图像被分解[24],传统的文学诗意被挤压,显然加大了两者的沟通距离与沟通难度。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图像与文学的这种现代性巨变,一方面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总还有部分艺术家坚守着传统主义的信条(比如撰写《西方正典》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现代派艺术最为风行的时代坚守写实主义的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坚守中国水墨传统的一些中国画家,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中国作家路遥等),甚至现代艺术家们也有时会重回传统……这样,近代以来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多变而不易把握。
具体来看,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艺术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之间至少具有如下关系:一方面,图像对文学有三种作用。1.阐释作用:具体形象,有时候即使千言万语也难以说清,因此,图像常常用来具体展示语言所描述的对象,起到说明、阐释、印证、强调的作用,自然科学的书籍图像(如动植物外形、山川状貌、机械构造图等)大体都属此类性质。不过,文学类书籍图像,相当一部分也是用来图解文字文本的,但这种图解本身就包含着选择,因而具有强调意味。这类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历史传记类、新闻类记实性强的作品。对于人类来讲:“眼见为实”,只有看到的才是最可信的,而历史一旦过去,便不可能倒流,不可能让人们再次身临其境观察考证,这时阅读图像无疑就成了重返历史现场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正像英国著名批评家罗斯金所强调的那样,比语言文字记录更为真实可信[25]232。所以有不少传记性文学作品,图像比重很大,甚至直接以“画传”为名。在中国近现代,为了让人们了解世界、传播新知与奇闻趣事,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画报,这些画报上具有新闻性的绘画所配语言,往往类似散文小品,极富文学意味。在这类画报中,图画甚至以压倒文字,成为叙事的主体,其对于语言的阐释作用更为突出。中国“以图像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正式确立于晚清的《点石斋画报》[26],而鼎盛于民国,仅2007年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出版的《民国画报汇编》就汇集了民国画报近百种,其中大部分的图像,都属阐释性质。
还有一种与画报类似,但更具普及性文学性的图文书是“连环插图”或“连环画”,其许多内容属文学名著,而主要阅读对象是少年儿童,它们的图像最主要也是用来图解文字内容的。由于这类图文书中,图像实际上已占据主要地位,图像叙事的独立性很明显,绘图者在对原始著作进行图解的过程中,个人的阐释和理解也非常突出,因此这类图文书,尤其是“连环画”,就往往被视为运用另一种艺术行书对原著进行的“改编”,从而被赋予“二次创作”性质。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如:丰子恺1949年前所做的《祝福》《阿Q正传》等“绘画鲁迅小说”九篇;1961年,画家程十发为纪念鲁迅去世二十五周年,在《羊城晚报》发表的《阿Q正传》102幅连环画;1960年代,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从更广义上来讲,现当代的影视艺术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影视图像代替文字成为了叙事的主要手段,在这一方面,现当代影视与民国时期流行的画报、与新中国初期流行的连环画,艺术本质上并无不同。
2.延补作用。图像作为一种艺术存在,还有一种文字所不及的直接象征暗示作用,宜于表达更精微、不易察觉的可心悟而不可逻辑论证的某些精神意蕴。中国先哲们很早就意识到,有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可以通过“立象”的方法得以传达:《庄子·天道》中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周易·系辞上》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古人已认识到诉诸视觉的“手舞足蹈”,比诉诸听觉的语言或音乐具有表达更深层情意的能力,它现于舞台,是为舞蹈;载于书籍,即为图像。类似的意思外国学者也多次表达过:“话语终止处,音乐开始;音乐终止处,颜色开始。颜色是漩涡般难以言述事物的表达,是眩晕-陶醉情态的表达。”[27]“‘纯粹的’描绘(绘画性‘意义’也一样)拥有它自身的并不属于语言学的力量,拥有以孤立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方式进行交流的能力。日益模糊的平面、地平线、人物形象与背景的关系、绘画空间内(绘画空间的真正意思)可被视为客体的东西,以及对平衡或不平衡的节奏与图案的视觉想象,对这些的探索是能够被画出的全部东西,并且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对图画的指涉,或对素描、油画、速写的回想,才能够被语言学影射。”[28]233“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29]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常会情不自禁地自创插图、封面等图像。例如,1920年代,《朝花夕拾》中鲁迅的自绘的“活无常”插图,1940年代,张爱玲在《杂志》上为《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小说所绘的插图都属此类,这类与文本同时出现的图像,热奈特称之为:“原创性副文本”[30],在探求作者的深层创作心理方面,意义尤为重要。
3.修饰作用。文学书籍中还有一类图像,绘制者的本意仅仅是为了美化装饰书籍,和书的内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种书籍图像许多属于图案画,在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是不发达的,这可能和中国文人的重道轻技心态有关,因为和西方书籍装饰画类似的中国传统纹样,在中国民间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没有用于书籍装帧而已。纯装饰性插图在欧洲早期的《圣经》中很常见,据说:“拜占庭的手抄本最初都是装饰画,直到12世纪才出现插图,也多为宗教书籍。”[31]装饰性的书籍图像,直到近现代才通过叶灵风、闻一多等人,对中国书籍装帧产生影响(鲁迅则将中国传统纹样引入书籍装帧)。因此,书籍装饰画一般属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印刷文字的字体大小与类别,都可能蕴含着某些情感特征(比如宋体严肃、楷体就活泼些),所以那些看起来和书籍内容无关的装饰性插图,都包含特定时代的审美风格、社会心态。比如民国初年鸳蝴派杂志充满商业气息的“封面女郎”与《新青年》封面洋溢着思想革命精神“世界伟人头像”,都属此类。所以极端地讲,没有纯粹的装饰性插图,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在暗示或烘托文字文本的主题意蕴,我们把这种插图的作用称为修饰作用。
另一方面,文学对图像也有三种作用。1.提示作用。文字的抽象概括性规定了它不能穷尽一幅画的所有内容,但它确实可以直接简洁地引导我们对某一图像进行某一角度的理解。因此,图像的标题与解说,就成了对图像的一种意义规定或意义提示。由于图像接近事物的原生状态,观赏者可以从各个视角来理解它,因此在表达意义方面显然比文字具有更大的多义性含混性(这是图像的优势也是它的不足),只有图像与文字的配合,才方便人们具体地理解它的含义。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曾做过一个课堂实验,结果面对同一个浅灰色的贝壳,学生们有的认为象征“死亡”、“枯燥无味”和“空洞”,有的则认为象征“自然的”、“优雅的”和“美丽的”[23]31。而借助于语言的引导和指引,只要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无论是“空洞”还是加上“优雅”的标题,它就会让争论平息下来,而更趋于理解。但有些时候,仅仅标题的语言提示,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荷兰现代画家梵高曾于1885年画了一幅题为“鞋”的油画,围绕此画的意义,海德格尔、夏皮罗和德里达曾有过旷日持久(1935年-1978年)的学术辩论,而仍莫衷一是[25]241-255,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梵高绘画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如果缺乏足够语言提示,即使那些最具思辨能力的人类才俊,也难以准确把握一幅画的真实内涵。因此,“我们为了理解大多数图画,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其他的,通常使用一整套实质上要求语言学措辞的知识与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西斯廷天顶画(对狄更斯而言不过是插图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将一些(或许非常多的)神话故事与信念带入我们对它的解释,否则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求,对绘画性最严肃的运用在最广泛意义上是‘插图’”[28]233。因此,对于文学图像来讲,它能够被我们准确理解,那是因为有语言背景的存在。
2.分析作用。当然,有时候对于一幅画,我们可能找不到他的语言背景,那么,就只能靠后人对某一图像意义的猜测性阐释或强调,古代岩画,中国出土的一些古代帛画等。分析作用和提示作用都是来解说图画的意义的,只不过提示作用多是作者的说明,而分析作用指的是后人的猜测。
3.联结作用。文学作为时间艺术,具有突出的叙述功能,图画作为空间艺术,展示场景的能力突出。书中的插图以及连环画的图画,之所以能够在读者心中构成一个流畅连贯的故事,一方面是读者根据画面的合理联想,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伴随的文学语言——语言通过叙述功能将图画连接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儿童,即使他认识图画,还有必要请别人给他讲述,只有这样,儿童才能更完整地理解画面内容。
总之,文学与图像的理想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及其插图来讲,绝不是“诗中有画”或“画中有诗”那么简单。宗白华说:“诗中有画,而不全是画,画中有诗,而不全是诗。诗画各有表现的可能性范围。”[32]对于某一文学作品来讲,它的文字文本及其相关图像,是我们理解之旅赖以抵达作者心灵的两条铁轨,文学的文字文本优势在于历时性的叙事与逻辑性思考,作为副文本的文学图像优势在于空间性状物与象征性隐喻。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讲,所有的图像都存在于一定的语言背景之中(而这种和图像密切相关的语言最常见、最重要的类别就是文学语言),没有语言背景的图像是不存在的,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理解;而所有的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又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场景、形象——图像,来进行叙事或思考,所以文学语言尤其强调形象性与典型性。文学的文字文本与图像,实际上就是文学自身营造的第二自然的时空因素与情理内核,两者有重叠有渗透,还可以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替代,但绝不可以完全替代。仅从文学的文字文本或相关图像,我们很可能只主要触摸了作者心灵某一方面。而两者相互借重(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书画并重),则既创作者得以充分敞示自我心灵的方式,也是读者得以充分领略文学经典的正途。试观清朝郑燮的“衙斋听竹图”与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仅有墨竹图无题诗,作者关切民间疾苦的情怀得不到准确阐释,但仅有诗句无墨竹图,作者那种孤傲、那种虽纤弱但独立不移的精神底蕴,又无法尽情展示,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郑燮的立体且丰满的精神世界。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在最能体现其生活经历与真性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后记中,会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记忆中的各种旧画像来,并手绘出了自己心中的“活无常”图,因为在鲁迅看来,无论文字还是其他图画,都不足表现自己心中独有的那个“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33]的“活无常”图像:鲁迅所绘的“活无常”图,宽袍高冠,草鞋破扇,嬉笑跳跃,确实是“鬼气”少而人气多,充满童趣与生命的率真。同理,张爱玲在最具私密性与自传性的散文集《流言》(1944年五洲书报社初版)与《对照记》(1994年由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初版)中,也插入了大量自绘的图画或旧存的照片,显然在这两本集子中,张爱玲这位对文字极为敏感才女也意识到了文字已不足以表达自我的情怀,必须与图像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表现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张爱玲《流言》集中的插图之一《一九三几年》,图中那女性妖媚如蛇的眼神与华服下虚无的身影,无不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艳异繁华表象下生命的苍白与虚无,这的确是张爱玲对自己所亲历的民国沪港都市生活独特体悟。
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文字文本与相关图像都处于理想的和谐状态。由于对文学语言理解与驾驭能力的差异,由于对图像感悟与创作能力的差异,乃至由于特定时空对文本理解的历史性制约,同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存在不同的插图,而同一幅图像艺术品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字阐释,这在艺术史上本来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些不同的插图或文字阐释,自然也就会有优劣高下之别,它们造成的图文关系自然也会有和谐与悖离之分,和谐的图文关系相辅相成地共同构筑了作者的心灵世界,但那些即使相互悖离的图文,如果我们耐心探求的话,也很可能发现它们从破裂、矛盾的意义上,构成一种特殊的参差补益关系:有些艺术幼稚的涂鸦,儿童的稚拙绘图,出现在某些书籍中,有时候还可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原因也在于此。
四、余论
不难看出,在文字与文学萌芽之初,图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文字和文学,甚至还更受重视,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们的著作中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典籍《易经》《庄子》中,都可以发现对视觉与图像作为人的第一性认知手段的推崇;后来随着人类文明与理性思维的发展与文字不断抽象化,图像艺术与文学艺术沿着自身的艺术特性而各自不断发展。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图像受到文学挤压而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隙与矛盾,西方中世纪曾经有过长期的“圣像崇拜之争”[34],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曾耻于绘画(唐代阎立本曾自言:“以丹霄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35]),中外封建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曾长期缺少封面画与插图等图像因素,都说明了在人类古代文化史中曾长期存在文字、文学与图像不断疏离、相互睽违的现象。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文字与文学中理性因素的膨胀与对原始生命情怀的挤压,人们对承载着更为鲜活丰富个体生命经验的以绘画为代表的图像,也更加渴求。因此,恰恰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此期西方以培根、笛卡尔代表科学精神勃兴,两人都极力反对偶像崇拜[36]),在中国理学盛行的宋明时期,西欧与中国的绘画艺术出现了以注重表现人性情怀为特色的突破——西方是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为代表的油画的出现,中国是苏轼、米芾倡导的文人画的出现,文学与图像在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呼应的艺术趋向也不断增强。于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文学书籍中封面画、插图等图像因素越来越多,《莎士比亚戏剧集》与《十日谈》插图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插图在明代达到鼎盛,尤以《西厢记》《水浒传》等戏曲剧本与小说插图为代表[37]。
在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加强,中外文学史上先是启蒙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彰显人类理性的文学潮流盛行,后来文学与各种哲学思想紧密搅合在一起,文学哲思化趋向明显: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风起云涌,文学精神愈来愈显示出更强烈的理性主义,同时也导致文学诗性更为匮乏和文学荒漠化、粗鄙化的流行;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图像也借助愈来愈先进的科学技术(照相机、影视、电脑多媒体等),不断繁衍增殖,以缤纷斑斓、无孔不入的姿态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并呼应着我们内心的隐秘情愫,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与影视互动频繁、图文书的流行等,都是这种影响的标志。于是,就形成了当前我们的所谓的“图像时代”和文学创作的图像化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未来会被图像所吞噬,文学无疑还会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只是说,它作为一种原本与图像密切相关的文字媒介艺术,再也不可能保持其古典时代所流行的疏离图像的传统艺术姿态了。
[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2.
[2]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谢启昆.小学考声韵[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
[4]科林·M.特恩布尔.森林人[M].冉凡,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30-135.
[5]柏拉图.蒂迈欧篇[M].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
[7]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74.
[8]I.戈德伯格.语言的奥妙[M].张梦井,李万峰,李瑛,田志东,郭峥嵘,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390.
[9]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98.
[10]刘勰.文心雕龙[G]∥郭绍虞.历代文论选: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4.
[11]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28.
[12]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2.
[13]吴持哲.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8.
[14]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6.
[15]冯骥才.艺术丛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6]弗洛伊德.释梦[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18]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
[19]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0]詹鄞鑫.汉字说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31-32.
[21]汪流,陈培仲,余秋雨,等.艺术特征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1-102.
[2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3]阿瑟·阿萨·伯杰.眼见为实——视觉传播导论[M].张蕊,韩秀荣,李广才,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24]凯瑟琳·库赫.分解:现代艺术的核心[G]∥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1.
[25]丁宁.图像缤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6]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香港:三联书店,2008:8.
[27]瓦尔特·舒里安.作为经验的艺术[M].罗悌伦,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306.
[28]萨林·柯马尔,伊万·卡斯克尔.艺术史的语言[M].王春辰,李笑男,杨扬,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29]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
[30]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4).
[31]于凤高.插图的文化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3.
[32]宗白华.西洋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31.
[33]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1.
[34]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95-334.
[35]刘昫.旧唐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80.
[36]汤用彤.《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导言[G]∥汤一介,赵建永.会通中印西.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2:431.
[37]刘辉煌.中外插图艺术大观[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