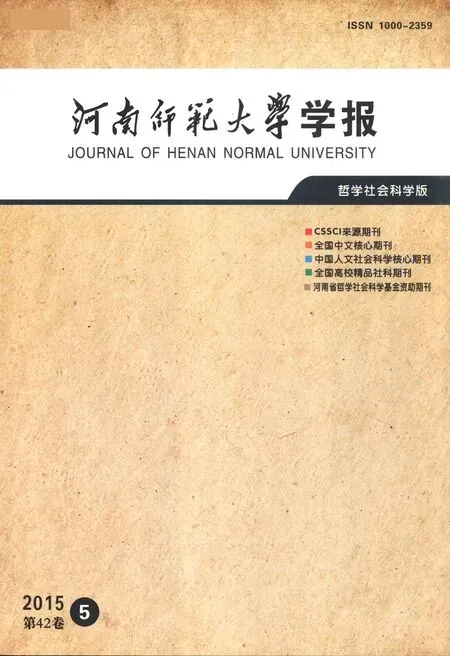李详《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义例探讨——兼论中古文学创作的“递相祖述”问题
雷恩海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一
从萧统的观点来看,《文选》所选文章堪称“美文”,乃精心结撰、锤炼文辞、声律等“辞采”“文华”之作,遍及诸体、兼顾古今,是后人研习欣赏的典范。《文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和“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两方面功用[1]1685,更为后人上窥前代文学精华、研习佳作开了方便之门。所谓“世间除诸经、《史记》、《汉书》之外,即以此书为重”[2],阮元《序》,扼要地说明了《文选》的价值。近代选学大师李详撰有《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揭橥其义例,有裨益于学者,尤为关键者乃在于抉示出中古文学的“递相祖述”现象,实用深入探讨之必要。
李详(1859-1931),字审言,中年又字愧生,江苏兴化人。私淑汪中,学问出入于阮元、钱大昕,名其斋曰“二研”,是清末民初扬州学派的代表。张舜徽《李审言文集序》说:
余生平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大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莫由畅抒所学。焦循《家训》有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扬州李审言先生,兴于清季,精于选学,能为沉博绝丽之文,早蜚声于士林,为长老所推重……深服其学与文并渊雅精醇,非时流所能逮。[3]1
且指出李详乃扬州学派大师阮元、汪中之后的殿军:“先生于阮氏之学,服膺无间;于汪氏之文,摩挲研绎,至数十年,渊源有自,不可掩也。故先生之学之文,博厚典重,卓然为晚近大师;世徒尊其为文之美,固未足以知先生也。”[3]2王利器先生亦称:“兴化李审言先生详,幼课《文选》,长而熟精《选》理,发为文章,以骈文知名当世,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牢笼百代,自铸伟词,一时有北王南李之称……其为学以乡邦扬州学派为靳向,游心于阮元、汪中之间,仰止前修,蔚为后劲。又尝与桐城城派诸古文家游,马其昶、姚永概,皆在相知之列,然率重其人而轻其文,盖病其刻意语助,自诩义法,置考据词章于不顾,殆未足以厌人望也。”[3]3
此类看法,正是学人的通识。陈训正《兴化李先生墓表》称:“先生读书,力锐思犀,靡坚不破,间有所获,辄立论断,眉评尾识,自然语隽。夙昔董理经史训诂而外,于昭明《文选》所诣尤精,曲会旁籀,撮其理要,蓄腹既多,振笔自异,并世萧学,罕比闳通。”[3]1451有《文选》学著作五种:《选学拾瀋》《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文选萃精说义》《李善文选注例》。当时学界泰斗沈曾植广为延誉,称曰:“此江淮选学大师李先生也。”“湘潭王湘绮,负材傲世,怒视曹辈,独于先生书问过从,殊其称署。”[3]1452名儒王先谦批其《选学拾瀋》,曰:“阅生所撰各条,并皆佳妙,无可訾议,只恨少耳。汉魏六朝为文,皆递相祖述,余《琐言》中所称举数事是也。唐人犹有之,宋以后竞出新意,此义荡焉无存,亦文场一大变局也。生所注兼能蒐讨古人文字从出之原,与鄙意符合,不专从征典用意,目光尤为远大。如能一意探求,俾成巨秩,允为不朽盛业。”[3]3王先谦目光如炬,拈出李详掘发汉魏六朝及唐代文学之递相祖述,实为卓见。
李详治选学,能够自出机杼,不但作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而且亦能统观全书,作宏观的总结、探求。钱泰吉(警石)《曝书杂记》卷下所收之“《李氏文选注》自明注例,散见各篇,录之以为注释古书之法”条,“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4]66,李详以为所录未备,乃广之而成《李善文选注例》。该文有云:“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注:‘《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3]154又,“‘朝廷无事’。注:‘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朝廷以言之。’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对此,李详加案语曰:“前已见举先以明后之例,此又举引后以明前之例,统观全注,此二例最多,实开 注 书 之 门 径。”[3]154又,“‘以 兴 废 继 绝 ’。 注:‘《论语》:子曰:兴废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3]154此注例意谓,词语虽有出典,而作者却在创作时赋予了新的意蕴,故李善解释此语意思曰:“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由此可见,李详总结李善注例,其会心处乃在于揭示著书之门径,“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3]154。另,曹大家《东征赋》注引陈思王《迁都赋》,“陈思之言盖出于此”,李详案曰:“此即(李)善引后明前之例。”[3]155谢惠连《雪赋》“愁云繁”,注:“班婕妤《捣素赋》‘对愁云之浮沉’,然颖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李详案曰:“(李)善于此不敢援举先明后之例,盖其慎也。”[3]155而“引后以明前”,其意则在于以后人的理解来阐释说明前代文人的思想与构思。
此外,李善尚有引同时代人之文章,以示文思之相类,如曹植《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注:“繁钦《定情诗》‘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有此言,未详其本。”李详案曰:“此引同时人以证之例,善未表出。”[3]157任昉《奏弹刘整》注:“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李详案:“此(李)善备引全文,俾与原弹一一附著。又为一例。”陆机《演连珠》李善注引《宋玉集》,李详说:“不引本选宋玉《对问》者,以此有‘绝节赴曲’,可证士衡祖述有自。此与《琴赋》引《对问》‘陵阳白雪’,各随所用引之。可见(李)善注兼蒐异本,不轻以未见、未详所出了事。书簏之称,信不虚也。”[3]157大概从此点认识出发,李详撰述《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以发明唐人熟读《文选》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故而《韩诗证选》自序称:“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夥,惟宋樊汝霖窥得此旨,于《秋怀诗》下云:‘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并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余据樊氏之言,推寻公诗,不仅如樊氏所举,因条而列之,名曰《韩诗证选》。宋人旧注,如诠‘贱嗜非贵献’及‘徒观凿斧痕,不瞩治水航’诸语,能以嵇康《绝交书》、郭景纯《江赋》证之。始知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此余之所不敢攘美。”[3]35
《杜诗证选》自序曰:
杜少陵《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又《简云安严明府诗》“续儿诵《文选》”,后世遂据此为杜陵精通《文选》之证。自宋以来,注家能举其辞者,已略得六七。然或遗其篇目,或易其字句,或多引繁文而与本旨无关,或芟薙首尾而于左证不悉,凡此皆病也。又少陵每句有兼使数事者,有暗用其语者,但举其偏与略而不及,皆有愧于杜陵“熟精”二字。如《客居诗》“壮士敛精魂”,既效谢客“幽人秘精魂”句法,又用江淹赋“拱木敛魂”,不仅古《蒿里歌》也。《玉华宫诗》“万籁真笙竽”,此用左思《吴都赋》“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语,故云“真笙竽”,盖引古自证也。如此之类,历来注家,尚未窥此秘。[3]71
揆之所述,李详所作《证选》,甚有深意,旨在抉发唐代文学创作递相祖述之旧习,故能深醇雅致,得为文之本,并非琐屑饤饾,仅仅注重文辞之出处、使事用典而已。如审言先生哲嗣李稚甫《二研堂全集叙录》所说:“二书取杜韩集中,单词片语,遍加钩稽,得其来历,使知文家如杜韩,隶事之醇雅,盖无一不出于《选》。”[3]1458事实上,精研六朝骈俪文,融其典雅遒亮于散体文之自然流畅,变化多姿,意味深长,此秘乃为扬州学派之大师汪中(字容甫)所抉示①《清史稿·儒林传·汪中》说:“生平于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王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袭欧、王、曾、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陈寿祺《清故拔贡生敕赠内阁撰文中书诰赠户部员外郎汪先生墓志铭》曰:“其治古文词,醇茂渊懿,陶冶汉晋,糠粃宋后作者。世所称颂者《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而其他篇雄丽,大率称是。下逮诗章书翰,无所不工,可谓绝特奇才矣。”。李详少喜汪中之文之学,浸淫其中,遂有《汪容甫文笺》之作,李稚甫说:“先君尝于乡先生汪容甫之文章,素所心折。尝谓容甫先生之文,熟于范蔚宗书,而陈承祚之《国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晋之文,华而不实,质而不俚,朴而实腴,淡而弥永。容甫得窥得此秘于单复奇偶间,音节遒亮,意味深长。又甚善沈休文、任彦升之树义遣词,不敢轻涉鲍明远江文通之藩篱,此其所以独高一代,而谭复堂先生推为绝学也。”[3]1459
受此影响,李审言沉浸于《文选》之精研,精熟文理,骈散文兼擅,力图融会唐宋古文之流畅与魏晋六朝骈文之醇雅为一体,以期致于自然高妙。李详《学制斋文钞》卷一《骈文学自序》论其为文之心得,曰:“古之文皆偶也。自六经以及诸子,何尝不具偶体。魏晋之后,稍事华腴之词,积而为骈四俪六,然犹或散或整,畅所欲言,情随境生,韵因文造。昭明所谓沉思翰藻,诚据自然之势,导源流之正,而文与笔划为二区,由是成焉。笔为驰驱纪事之言,文为奇偶相生之制。”[3]898
“或散或整,畅所欲言,情随境生,韵因文造”,诚然能揭示出文情兼美之妙。融会骈俪与散体为一,所谓“积材宜富,取法宜上,摄于训诂,而归之典则,防其泛滥而为隄障,使于奇耦交会之中,有往复流连之致”[3]蒋国榜序,754。文章之道,发乎自然,而勤学好古之士,有所本而为文,因华以见实,李详“少通群籍,涵濡宫商,好为闳丽之辞,善持文质之变”[3]《学制斋骈文序》谭献序,749。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李详博览群书,精熟《文选》,“熟精逾夫诗圣,贯穿过乎书簏”[3]缪荃荪序,751,晚近的文献学家缪荃荪以为李详对《文选》的精熟超过了诗圣杜甫和《文选》学大师李善。故而,李详“精理学积,发为文章,据江介以泝洛中,本裴、谢以济江、鲍。文清旨诣,秀擅当时,素练轻缣,质周世用。以言情者,语古思新;以述事者,文华理畅。”[3]沈曾植序,753皆能揭示出李详文章的学术渊源。
李详精研《文选》,且创作才能颇高,成绩斐然,“邺下雅材,揖逊嵇阮;广陵耆旧,抗希徐刘。并驱萧梁之先,不队李唐之下”[3]冯煦序,750,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文选》之体悟颇深切。故而,斟酌《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之义例,抑或可以明了李氏用意所在。总体而论,二书义例大约有如下几种:一、直接援用。二、翻用。三、用意,命名制篇,全用其意。四、櫽括其意,以成一新诗。五、虽词意俱用,却赋予新意。六、用成句。七、套用句式。
此类义例,大约近于黄山谷所说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则。李详证《选》,旨在揭示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杜少陵、韩昌黎之巨擘,尚且学习、模拟《文选》,借之以为进入文学创作坦途的门径。杜甫《戏为六绝句》说:“未及前贤更勿,递相祖述复先谁。勿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5]898正是揭橥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
二
杜甫所揭橥的这一现象,在唐代文学中多有呈现。最为明显的是有许多同题文章,如《明水赋》,《文苑英华》卷三二《鉴止水赋》,收有吕温、张仲素、王季友之作,卷五七则收有崔损、贾稜、欧阳詹、韩愈、陈羽之作,卷一四七《幽兰赋》,收有杨炯、乔彝、陈有章、韩伯庸、仲子陵、李公进之作,《青苔赋》收有王勃、杨炯之作。至于诗歌中的同题之作更多,而乐府诗之同题拟作,也很普遍,其间的传承借鉴,亦颇为重要。至于句法、句式,情节的敷演、叙事抒情的深化,俯拾即是。
其实,此乃六朝以来文学创作上的常态。面对一个有名或者感人的故事、题材、话题,诸多的作者共同创作,较长量短,一旦有成功的作品,产生巨大的影响,遂不径而走,成为人们学习、摹仿的对象。因而,六朝人往往以前人或同时代成功的作品为学习摹仿的对象,进行拟作。如汉代梁孝王筑兔园,方圆三百里,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二十余里;园中又有百灵山、落猿岩,栖龙岫,雁池;而雁池间有鹤洲、凫渚。一时文士游从,枚乘遂作《梁孝王兔园赋》,为人所称道。《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宴集文士,使各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而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韩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各五匹。这一故事,遂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遂假托其人以拟作之,以为一时之胜,而《西京杂记》所列各人之赋,也很可能并非原作,乃六朝人的拟作①这个故事,很有吸引力,至清代,毛奇龄假托而作《觯赋》,其小序曰:“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进抽词之士,饮以美酒,授以札牍。于是邹阳、枚乘、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之徒,各有所赋;独韩安国赋几不成,邹阳代为之,阳与安国扬觯并罚。于是羊胜进前,谓邹阳止罚乃得饮,中其所喜,不如勿饮,且为赋觯,成即受酒,不能即退。于是邹阳左手执觯,右手操管,口讽手追,而为之赋。”《西河集》卷一二五)。
此外,枚乘《七发》,波澜开阖,创意造端,丽旨腴辞,烂然可观,遂吸引后来者心摹力追,作者颇多,遂形成“七”体的文章体裁②曹植《七启》序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傅玄集》之《七谟序》:“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徙,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时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侈而托讽咏。扬晖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为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又,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闲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逹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问》,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颕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文心雕龙·杂文》说:“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辩》,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穷瓌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7]255-256
刘勰批评“七”体,指陈其创作之成就与不足。因为枚乘首创《七发》,摹拟者众,遂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优秀的作家在这一体裁上,既能因袭,亦各有新变。七体,总共有八段文字,其中开篇叙事交待文章撰述之缘由、背景为一段,而问对则七段,因而称“七”体,故而“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故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其中枚乘《七发》、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三篇,“辞旨闳丽,诚宜见采;其余递相模拟,了无新意,是以读未终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8]138。
诗歌的创作上也是如此,《文选》卷三十至三十一,有“杂拟”类,选录陆士衡、张孟阳、陶渊明、谢灵运、袁阳源、刘休玄、王僧达、鲍明远、范彦龙、江文通等之拟作。陆机拟《古诗十九首》,钟嵘称之为一字千金,《文选》录十二首,同时也选录了刘休玄的拟诗,如《拟行行重行行》:
陆机(字士衡):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沈。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沈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9]435
刘铄(字休玄):眇眇陵上道,遥遥行远之。回车背京里,挥手从此辞。堂上流尘生,庭中绿草滋。寒螀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华月,佳人无还期。日夕凉风起,对酒长相思。悲发江南调,忧委子衿诗。卧觉明灯晦,坐见轻纨缁。泪容不可饰,幽镜难复治。愿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时。[9]441
《拟明月何皎皎》:
陆机(字士衡):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9]436
刘铄(字休玄):落宿半遥城,浮云蔼层阙。玉宇来清风,罗帐延秋月。结思想伊人,沈忧怀明发。谁为客行久,屡见流芳歇。河广川无梁,山高路难越。[9]441
其命意、造境、抒情、叙事,皆摹仿《古诗十九首》,颇有亦步亦趋之态势,能得其仿佛。如,《拟行行重行行》陆机之作“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即《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即《十九首》之“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即《十九首》之“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9]409。又如,张孟阳《拟四愁诗一首》: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且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9]437
乃是拟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佐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9]414模拟离别忧愁之思,命题、造境、抒情,完全一致,所不同者,张孟阳增添“我之怀矣心伤忧”,将首三句化为整齐的四句,以增强抒情性和艺术的整饬。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小序曰:“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9]437
小序,谢灵运完全以曹丕的身份、情思来模拟、创作,以求切合人物情思,曲尽其妙;其次诗歌则拟曹丕太子身份,以及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徐幹“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应玚“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阮瑀“管书记之任,有优渥之言”,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摹写情状,以求神似,当然诗歌也寄托了谢灵运的某些情思以及身世之感。此外,袁淑《効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模拟曹植《白马篇》;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模拟《古别离》,李陵(从军)、班婕妤(咏扇)、曹丕(游宴)、曹植(赠友)、刘桢(感遇)、王粲(怀德)、嵇康(言志)、阮籍(咏怀)、张华(离情)、潘岳(悼亡)、陆机(羁宦)、左思(咏史)、张协(苦雨)、刘琨(伤乱)、卢谌(感交)、郭璞(游仙)、张绰(杂述)、许询(自序)、殷仲文(兴瞩)、谢混(游览)、陶渊明(田居)、谢灵运(游山)、颜延之(侍宴)、谢惠连(赠别)、王微(养疾)、袁淑(从驾)、谢庄(郊游)、鲍照(戎行)、惠休(别怨),所摹写者乃各人所擅长的题材,因而李善注引《杂体诗序》说:“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9]444李善说得很对,江淹摹拟,正是“学其文体”,“品藻渊流”。前人的作品,正是标准的范本,用心揣摹、拟写,以求得其神似,从而熟悉相应题材、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很快成熟起来,从而得窥写作的门径。这样的方式,正是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应该说,当时文学创作上的“拟”、“补”、“代”等,皆是学习、模拟的方法。
至唐代,递相祖述的现象依然很盛。大量的应制诗、宴集诗、咏物诗等,皆存在着递相祖述、甚至陈陈相因的现象。如梁简文帝有《咏风》诗:“飘飘散芳势,泛漾下蓬莱。传凉入镂槛,发气满瑶台。委木周邦偃,飞鶂宋都回。亟摇故叶落,屡荡新花开。暂舞惊鳬去,时送药香来。已拂巫山雨,何用卷寒灰。”[10]731而同题作者有沈约、刘孝绰、王台卿、庾肩吾、何逊、祖孙登、阮卓、李世民、虞世南、董思恭、王勃、李峤、张祜、韩琮等。其命意、造境、遣词,甚至名式结构皆颇为相似,如:“浸滛不可议,去来非有情。乍见珠帘卷,时觉洞房清。暂拂兰池上,潋淡玉波生。一辨雄雌异,还恶庶人轻。”(王台卿)“宋地鶂飞初,湘州燕起余。拂烟聊动竹,吹薤欲成书。苍梧桐尚在,合浦树应疎。阳鸟一转翅,千里定非虚。”(庾肩吾)“飖扬楚王宫,徘徊绕竹丛。带叶俱吟树,将花共舞空。飘香双袖里,乱曲五弦中。试上高台听,悲响定无穷。”(祖孙登)“萧条起闗塞,摇扬下蓬瀛。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披云罗影散,泛水织文生。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李世民)“萧萧度阊阖,习习下庭闱。花蝶自飖舞,兰蕙生光晖。相乌正举翼,退鶂已惊飞。方从列子御,更逐白云归。”(董思恭)“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王勃)“落日正沉沉,微风生北林。带花疑鳯舞,向竹似龙吟。月动临秋扇,松清入夜琴。若至兰台下,还拂楚王襟。”(李峤)“遥遥轻扇举,悄悄舞衣轻。引笛秋临塞,吹沙夜遶城。向峰回鴈影,出峡送猿声。何似琴中奏,依依别带情。(张祜)”[10]732-733
诸诗命意造境遣辞,极为相似,如出一手,很难看出作者的个性和才情以及生命体验。又如李世民有《春日望海》,杨师道、许敬宗有同题之作[10]821;李世民有《登骊山高顶寓目》,李峤、刘宪、赵彦昭、苏颋、崔湜、武平一、张说等奉和[10]822。又如,隋之薛道衡作《昔昔盐》,大为时人所称赏,尤其“空梁落燕泥,暗牖悬蛛网”,更是万口相传。诗人遂递相祖述,拟之者颇多,会昌二年登进士第、因“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句而得“赵倚楼”雅号之赵嘏,更是以《昔昔盐》每一句为题,作诗二十首,足见其影响之广泛,为人赏爱之深切①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七“昔昔盐”:“《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録》载籧篨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疎勒盐》《满座盐》《归国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今南岳庙献神乐曲有《黄帝盐》,而俗传以为‘皇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不考也。”。
在其他文体中,递相祖述的现象依然兴盛,如大诗人李白三前后三拟《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11]卷一二,今集中仍有《拟恨赋》。江淹《恨赋》曰:“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森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9]235而李白《拟恨赋》开篇亦曰:“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草宿坟毁。浮生可嗟,大运同此。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殁。”[12]14结构相同,而且造境抒情,颇为一致。此下,文通、太白皆罗列古往今来之恨事,不过,太白避忌与江淹所列恨事之重复,挥洒才情,别列恨事,以充盈之感情发抒不尽之意。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尾宕开一笔,以江山风物之永存,而人事之难久,兴发无限感慨。江淹说:“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李白说:“已矣哉!桂华满兮明月辉,扶桑晓兮白日飞。玉颜灭兮蝼蚁聚,碧台空兮歌舞稀。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而同归。”[12]15日月长存,玉颜难久,不过,太白以“与天道共尽”生命之自然过程,最终皆必然走向死亡,体现出道教徒的达观的生命观。既然生命乃一自然过程,自应努力而不致虚度,空使遗恨无穷。
对此,前人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有所论列。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列举其递相祖述,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文人递相祖述”条亦曰:
《容斋随笔》曰: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有未见者,辄录于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穷词》亦工。仆观《逐贫赋》,备载于《古文苑》《艺文类聚》中,洪氏何未之见乎?《送穷文》虽祖《逐贫赋》,然亦与王延寿《梦赋》相类,疑亦出此。仆谓古今文人递相祖述何限,人局于闻见,不暇远考耳。据耳目之所及,皆知韩、柳二作拟扬子云矣,又乌知子云之作无所自乎?《续笔》谓文公之后,王振又作《送穷词》矣,又乌知子厚之后,孙樵亦作《乞巧对》乎?樵又有《逐痁鬼文》甚工,其源正出于《逐贫赋》,类以推之,何可胜纪。[13]
又孙奕《示儿编》卷九“递相祖述”条有曰:
老杜戏为诗曰:“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所谓夫子自道也。尝观其《后出塞》曰“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纯《游仙诗》“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句法得之渊明《杂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复愁》云“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即李义府“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之体;《醉歌》云“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即灵运“日暎昆明水,春生洛阳殿”之体也。若夫退之“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句法,又使少陵《今夕行》云“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祭侄孙湘》文云“情一何长,命一何短”句法,又使少陵《石壕吏》云“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也。[14]
可见,递相祖述,一方面,这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以前人的诗文为标准为范本,用心揣摩,模仿,以求得神似,掌握基本体制和写作要求。乐府诗有“拟”“代”之类,即是。另一方面,题材、对象相同,写作上就存在着不得不相近、相似的问题,却往往陷于陈陈相因,难出新意,缺乏独创性。
三
自魏晋文学自觉之后,文学遂与人生密不可分,乃表现人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而自求不朽:“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9]《典论·论文》,720刘勰说“一朝综文,千载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7]702。当文学成为必要的社会交际工具之时,能否善作诗文,就成为衡量士人才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多读书,多积累,熟悉前代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和经验、优秀的作品、丰赡的辞藻,才有可能写好诗文。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尽快掌握诗文写作的相关素材、语汇辞藻、典故以及名章秀句、句式、结构篇章,遂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于是类书应运而生。
第一部类书,乃魏文帝曹丕于延康元年至黄初三年间,命群儒编选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5]88可见,曹丕命诸儒撰类书,其目的在于通知古今、网罗天下学问,便于著述。因此,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说:
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盖施之文为通儒,厝于事为达政,其为益亦甚巨已。[16]
类书的作用在于“包络古今,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文人读类书,可以为通儒,而为政者读类书,可以明达政事。就是说,类书以类相从,把此前的各种知识、学问胪列,一方面,便于临事而征引考信,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熟悉其时全部的文化知识,而这一切皆有益于文人的诗文撰述。齐梁时,士大夫诗文喜欢使事用典,且以为学问浅深之表征,因而,类书更为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按类检索,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了丰富的事例、繁富的辞藻,从而准备了创作的“素材”。因此,中古时代,类书颇受人们的重视,大规模地编纂延续数百年之久①《皇览》之后,梁武帝萧衍诏修类书,刘杳撰《寿光书苑》二百卷,刘峻编《类苑》,萧衍更令编纂《华林遍略》;北齐后主高纬诏撰《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隋代则有《长洲玉镜》、《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之编撰;唐初则大规模编纂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初学记》三十卷等。。高士廉受唐太宗之命,编纂《文思博要》,其序说:“义出六经,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则,极圣贤之训,天地之道备矣,人神之际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离离若星辰,错行于躔次。斯固坟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为国者尚其道德,为家者尚其变通,纬文者尚其溥。谅足以仰观千古,同羲文之爻彖;俯视百王,轶姬孔之礼乐。岂止刻石汉京,悬金秦市,比丘明之作传,侔子长之著书而已哉。”[10]卷六九九
高士廉说《文思博要》这样的类书,是学问的渊薮,足可与《左传》《史记》相媲美,亦可广闻见,备知识,所谓:“开卷而上下千数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骈四偶六,协律谐吕,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愚愿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祈至于文王孔子之用心处而后止,毋为猎取其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以治聋俗之耳目焉,乃善学者也。”[17]南宋刘本《初学记序》
事实上,作为文章渊薮的《文选》在当时有着与类书相似的功用,其流行有其必然性。唐高宗永隆二年(681),进士考试,“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18]卷七五《贡举上》,所谓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19]卷二70。大约“文律”乃指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的基本功用和格式,而“诗赋”重视声律对偶。《文选》选文重视“文之时义”,看重“随时变改”之文,在泛文学观念的指导下,既选录了许多诗赋类的纯文学作品,也选录了大量的应用文。从创作艺术而言,“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皆为美文。李善注本,完成于显庆年间(656-661),旁征博引,音、辞、事、义兼释,且颇注意知人论世和文意的贯通、理解,极大地丰富了《文选》的内容,并因此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础。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就指出萧统撰集《文选》之功:“搴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緜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9]3从作为学习、参考的资料这一角度而言,搜罗宏富的前代文章总集《文选》,和唐初所修撰的专供研习诗赋创作的《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具有同等的实用功能。于是,《文选》受到了唐人的宝重,李白有拟《文选》之作,杜甫、韩愈均精熟《文选》,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20]卷一四○,甚至诗歌形成了所谓“选体”,足见其影响之巨。可见,《文选》提供了“递相祖述”研习之范例。
四
当然,《文选》提供的是完整的篇章、精选的诗文,而类书以类相从,罗列的是一些知识的片断,甚至仅仅是辞藻的类编,并非系统的知识、严密的叙事或论述,对于作文,委实有其方便的一面,但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原,则流敝无穷。朱熹曾批评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此书流传,恐误后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21]卷三三《答吕伯恭书》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当作‘稗’)贩,实学颇荒。”[1]1141事实上,在中古时期标榜“沉思翰藻谓之文”的时代,文人为求速成、以广见闻,积累知识、储备创作“素材”,往往舍弃原书,而以类书为宝典,以为学问渊薮,检寻典故、辞藻,敷衍成篇。如此,诗文在某种意义上,乃变相的类书,只不过是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编撰方式,对相同的材料进行华样翻新的再编排而已。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将之称为“类书式的诗”,并且说:
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22]6
人的才能有很大的区别,“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7]719,在以诗文为交际的时代,类书为众人准备了创作诗文的“材料”,提供了作诗的方便,倘若心无所见,则便于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以类书为阅读、寻检对象,这样,大家的知识、学问来源皆一致,自然就易于造成中古文学之递相祖述的现象,诗文相似度很高,很难出彩,可以说是将天才与庸人拉平,难以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正所谓“术不素定,则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7]543。可以说,类书的出现,加剧了递相祖述的现象,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锻炼了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文学创作存在着陈陈相因,难以创新出奇的弊端,制约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职是之故,杜甫倡言“递相祖述复先谁”,重视别创生面、有创造力的作家;韩愈则批评之,“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主张“陈言之务去”,“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23]541。黄宗羲以为:“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乃谓之去陈言。”[24]卷三《论文管见》刘熙载以为:“所谓陈言者,非必勦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25]68显然,陈言即指递相祖述而无变化的命意、造境、遣辞等。因而,韩愈提出要有充实的内容:“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23]145以济其模拟沿袭之穷,以充实之内容而改变一时创作风气。
递相祖述,是中古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文学创作中学习、演进的重要方式,也易于作者之间的互相学习,积累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当然也刺激作者着力求新求变,以创新出奇;而杰出的作家,往往开创一种新的表现领域及表现形式,引起诸人的慕习,形成一时的创作潮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隆,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26]1778所谓“各相慕习”,正是递相祖述之意。司马相如辞赋之重在体物,形象逼肖;班固辞赋则以言志抒情说理为长;曹植、王粲则彰显作家独特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皆开创一时之风貌,各自引领而形成一时创作风潮。至唐代,递相祖述而引领一时文学风貌的现象依然存在,唐人正有这样的认识:“唐有天下几二百年,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华)、萧功曹(颖士)、贾常侍(至)、独孤常州(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10]卷七○三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而且,这一见解为欧阳修所继承,《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文三变之说,正是来源于此。
当然,递相祖述有其不足,往往限制才思,不能出古人之藩篱,实则把递相祖述的学习,变成了全然的摹仿,失去了积极的意义。而要在递相祖述的基础上,把握文学写作的纲要,熟练掌握,转益多师,广泛学习,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7]726,从而创作出有新意的作品来。因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人摹仿之病”条对此有所批评: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夫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27]1097
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27]P1098
而且,顾宁人指出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所论,“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畴之外”[27]1098。又《日知录》卷二一“诗体代降”条有曰:“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27]1194
千载而下,顾宁人的批评无疑是深刻的,要求“未尝不似而未尝似”——有传承有创新,更有自我。递相祖述,乃学习文学创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把握文学之纲要,事半而功倍;当然还应“转益多师”,融通各家各派、各体文学,而形成自己的创造,确立独特的文学风格。宋末的刘辰翁认识到递相祖述的意图,《须溪集》卷六“语罗履泰”条说:
杜诗“不及前人更勿疑,递相祖述竟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此杜示后人以学诗之法。前二句戒人之愈趋愈下,后二句勉后人之学乎其上也。盖谓后人不及前人者,以递相祖述,日趋日下也;必也,区别裁正浮伪之体,而上亲风雅,则诸公之上转益多师,而汝师端在是矣。[28]
事实上,面对递相祖述的困惑,唐代李德裕《文章论》则已经认识到文学创作,一方面必然要传承,另一方面也要求创新,有曰:“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载于此。曰: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澹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见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10]卷七四二
文学创作的魅力大约就在于,于永恒主题的描写中,表现出不同的才情,以不同的艺术美、思想力量而发生感染作用,吸引古往今来的读者。然而,李德裕的意见,并未能引起后世的重视,学习诗文,往往深溺于因袭、模拟,以求肖于古人之声气、辞藻。章学诚目睹唐宋派古文大家归有光以五色批点《史记》——“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29]286亦步亦趋,唯恐不肖于古人,所谓“归(有光)、唐(顺之)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此类因袭、模拟,正是递相祖述之不足处之影响所致。章学诚以为:“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29]287和韩愈“文必有诸其中”一脉相承,为文之要,在于“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言,则其道矣”,“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29]288。章氏意见,实乃见道之论。
递相祖述,乃中古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有利有弊,也有其兴盛之必然,同时也揭示了文学史上的通变传承、相互影响,且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仁智之见纷然杂呈。正确认识这一通变传承,关键在于把握作家、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非语源上的简单比附,抑或文学主张上的公然宣示。所谓通变传承,一种情况乃“显性”的,作家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甚至理论主张亦桴鼓相应,颇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类相从,甄别论述,容易形成一时之风气,为世人所关注、了解。另一种情况,则是“隐性”的,作家对自己所学习的前辈及其著作,并没有明确宣示,甚至没有片言只语的评介,然而深入考察其实际,无不受其人理论及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种隐性的文学现象,应该说是文学史上通变传承的常态,历来却鲜有关注。漠视这一隐性文学现象,就难以深入文学通变传承之实际,亦不能切入文学的内在精神意脉[30]。如若未能深入了解其内在精神意脉,故论其通变传承,论之愈多而隔膜愈深。李详证《选》,并非只是简单的《文选》注释,而是以扎实的功力,宏通的视野,探讨文学史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是有其深刻意义的。缘此,方可比较好地认识文学的发展衍变,把握其内在理路,避免傭耳赁目之弊。
[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梁章钜.文选旁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李详.李审言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钱泰吉.曝书杂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1]段成式.酉阳杂俎[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王楙.野客丛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孙奕.示儿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焦竑.明史经籍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王溥.唐会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黎靖德.朱子语类[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黄宗羲.南雷文集[M].四部丛编初编本.
[25]陈立人,陈文和.刘熙载集·艺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8]刘辰翁.须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0]雷恩海.一种隐性文学现象之考察[J].文学评论,2010(5).
——论唐代类书编纂的特点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