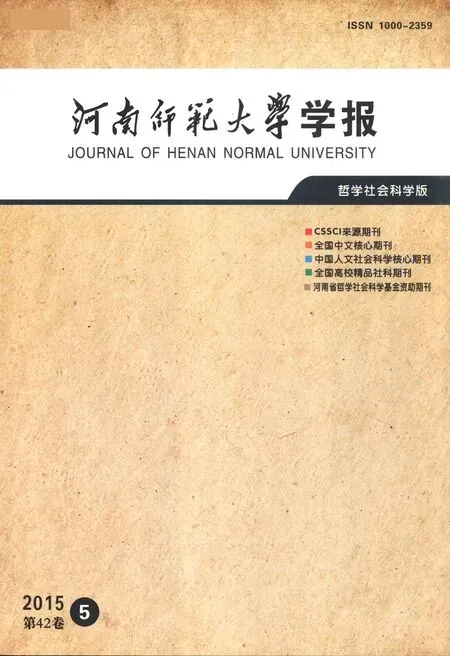休闲与幸福之关系辨正
韩 艳
(河南师范大学 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453007)
休闲(leisure)和幸福(happiness)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正确的措置。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等级差别,而且存在分工的不同,休闲被当成某些社会阶层进行纯粹思想创造的活动,休闲和劳作构成了一组对立的关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不仅消除了等级社会的阶级划分,而且对何谓幸福有了更为多元的理解,这些变化有助于我们在当代正确评估休闲和幸福的密切关系。
一、古代和现代思想中的休闲和幸福关系之比较
从古至今,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休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惟一本原”[1]269。然而这种不约而同的赞美并不意味着从古至今人们关于休闲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也不意味着在关于休闲的传统和现代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分歧。为了更好地评估休闲的幸福价值,我们将首先对古代和现代思想中的休闲和幸福的关系进行回顾和比较。
Annette Holba认为英语休闲(leisur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词skole和拉丁语词scola,这两个词也正是英语语词学校(school)的起点,而学校是一个接受教育和学习的场所,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这种语源学的考察表明,休闲对于古希腊人来讲并非娱乐或玩游戏,而是和学习相关的某种活动。Annette Holba进一步指出,休闲对应的罗马语词是otium,而otium 意味着“免于行动”,是指一种平静的生活,随着语言的发展,otium这个语词后来逐渐意味着使得一个人精神富有的活动。所以Holba得出结论说:“从古代世界作家的观点来看,休闲更像是对思想的反思活动,而不仅仅是一段不用来工作的时间。”[2]59Holba的这个判断表明休闲对于古希腊人的价值和当代人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他的这个判断也可以通过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休闲和幸福观的具体考察得到印证。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建立在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基础之上,奴隶只配进行辛勤的劳作,并无资格享受闲暇。虽然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1]269,但是,他的这一论断是针对城邦中的公民而言的。亚里士多德是在讨论如何对城邦中公民的子女进行教育以使得他们人格的发展能够合乎德性的要求过程中谈到闲暇或休闲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教育可以分为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四种,读写和绘画有实用性,体育可以培养人的勇敢。但是音乐有什么用呢?一般人认为音乐的目的仅在于娱乐,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城邦公民在闲暇时的一种休闲方式,“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2]271。所以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式的休闲概念表明了一种在artes liberals(自由的技艺)和artes serviles(奴役性的劳作)之间的区分”[2]71。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一切知识和选择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就是“四因”中的目的因,比如医术的善就是健康,战术的善就是胜利,建筑术的善就是房屋。在各种目的之中,有些目的的达成只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是工具和手段,比如钱财。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所追求的各种目的背后,有一个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说是一切善的顶点,“只有这个东西才有资格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3]12。那么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具体是指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3]12。最完满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哲学的思辨活动,因为“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乎智慧的活动……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满幸福”[3]228。所以最完满的幸福存在于有智慧的人的自由思辨活动之中。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作为最高的善只能以自身为目的,普通人所谓的快乐、财富和荣誉都不能以自身为目的,所以都不是所谓的幸福,只有“那最为平庸的人,则把幸福和快乐相等同”[3]8。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休闲和幸福的论述中,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基于其关于城邦政治制度的等级设计,将休闲看作某一社会阶层免于劳作之辛苦、增进情操和德性的活动,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幸福作德性论的客观主义理解,将客观的幸福和主观的快乐加以区分,这两方面结合的结果就是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无法对休闲和幸福的关系进行公允的评价。
在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功利主义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并且发展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和德性论相对立的伦理和经济学说,不再侧重于从抽象的、客观的德性出发来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而是将幸福和快乐密切结合起来,以实现快乐的最大化。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明确指出:“所有利益有关的人的最大幸福,是人类行动的正确适当的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适当并普遍期望的目的,是所有情况下人类行动、特别是行使政府权力的官员施政执法的唯一正确恰当的目的。”[4]11因此,功利原理被边沁称为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边沁认为幸福就是享有快乐,免受痛苦。“组成共同体的个人的幸福,或曰其快乐和安全,是立法者应当记住的目的”[4]34。边沁同时列举了若干种快乐的类型,包括感官之乐、财富之乐、技能之乐、名誉之乐等,并依据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临近或偏远等情况,把快乐之值和痛苦之相相加减,来估算快乐本身的值。
可以说,古代文化对休闲和幸福的肯定主要限于“纯粹的思想事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休闲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否定了中世纪禁欲主义对感性幸福的压抑,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对幸福和休闲的德性分析,幸福成了普通大众唾手可得的事情。也正是随着现代功利主义的兴起,休闲和劳作、休闲和幸福之间的对立才得以逐渐消解。然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虽然使得幸福与普通大众的快乐相联系,功利主义关于幸福的计算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正确评价休闲的价值。所以要想正确评价休闲的幸福价值,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代的休闲和幸福观,并超越现代功利主义的幸福观。
二、幸福的本质:自我实现
在当代社会,幸福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纯粹的思辨活动,也不是功利主义所理解的简单快乐,人们对幸福有了更加多元的理解。幸福不仅仅是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也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关注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幸福。也有学者认为幸福只是美好生活的一个方面,幸福是一个关乎个人的问题等等。美国独立宣言甚至声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幸福成为西方社会追求的基本人权之一。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如何衡量幸福,幸福是不是等于简单的快乐,在此我们需要加以厘清。
幸福常常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术语交叉使用。一般而言,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强调的是主观感受,但同时可以用一些客观标准来衡量。因此,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从客观上讲,幸福感受到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影响,从主观上讲幸福感则受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学者布鲁诺·S·弗雷指出,影响个人幸福感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有五个方面: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我应变能力、乐观、外向和内向;社会人口统计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因素,如个人的总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如特殊的雇佣和工作条件、在工作中的压力、同事之间的关系、亲戚和朋友、婚姻伴侣;制度因素,如政治分权的范围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等[5]10-11。国际社会根据这些主客观因素形成了衡量幸福感的指标——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是由不丹国王在1972年提出来的,并且成为国际社会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普通大众也常常根据这些指标来衡量自身的幸福,如把身体的健康程度、物质生活的满足和工作的顺利与否等方面当成幸福感的主要源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幸福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6]3。这种观点或许受到了边沁对幸福界定的影响,把幸福等同于一种感官层次的满足。但是,塞缪尔·S·富兰克林认为我们仅仅承认快乐是不够的[6]9。国内学者也意识到了幸福和快乐的区别,认为幸福以快乐为基础而又高于快乐,快乐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而幸福则直接指向整个人生[7]。快乐是一种完成某种行为之后的感觉,是短暂的,而幸福则应是长久的,幸福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快乐。学者所提及的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以及幸福是一种快乐的感觉的观点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幸福的来源,从而增加个人幸福感,但这些都没有真正揭示幸福的本质。
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来寻求幸福的真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他(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8]43马克思同时提到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46。从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个人而言,幸福是指个人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从事有意识的、创造性的活动。但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存在,个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性劳动,因此在劳动时间里根本体验不到幸福。“只有在自由时间内,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工人只有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8]45。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吃、喝、生殖等方面的自由活动并不是人的惟一终极目的。但是在异化劳动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工人所拥有的少量的自由时间以及大量的工作时间只是用来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要,从而为其他阶级享受自由提供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富兰克林认为幸福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潜能以及朝向更好人类生活的生活方式[6]12。富兰克林在分析各种幸福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一个结论:幸福不是一系列短暂的快乐,不是财富的积累,也不是宗教信仰的结果,而是一种促进人类潜能实现的生活方式。富兰克林认为人类被赋予了各种潜能,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可能性。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常常忽视那些天赋而把全部生命投入到所谓的“更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导致普通大众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富兰克林甚至认为只要我们在追求,向前进,发展,实现潜能,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类生活:幸福。追求的幸福(happiness of pursuit)没有真正的终点或终点线,这里只有旅行。旅行是幸福的,成长是幸福的,实现潜能是幸福的[6]15-16。
根据马克思以及富兰克林对幸福的诠释,我们认为幸福不同于短暂的快乐,幸福不是仅仅通过一些外在指标就能够简单衡量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理解,幸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能够从事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进而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那么,工作能带来幸福吗?弗雷指出在工作中比较成功的人比较幸福[5]13。他所提到的这些工作应该是能使个人充分实现自我的工作,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劳动者能充分地实现自己的潜能,因而是幸福的。然而,在当前,由于绝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存在着马克思所讲的异化现象,因此,从实现人类潜能、自我实现这一角度来看,工作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那么,除了工作以外,曾经作为工作对立面的休闲能够带来幸福吗?接下来,我们分析休闲对于幸福的重要价值。
三、对休闲幸福价值的当代评估
休闲和幸福一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当下生活最具活力的领域[9]。休闲是指“在自由时间内从事的非强迫性活动”[10]。亚里士多德虽然对休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3]227,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时又提到“我们为了闲暇而忙碌”[3]227,这种观点把工作和休闲置于对立的关系,休闲仅仅是工作的中断。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普通大众把休闲当成一种缓解工作压力、休养生息的手段,休闲等同于娱乐、休息、放松等词汇。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活动是有报酬的工作,唯有工作才能带来幸福,休闲只是工作的补偿,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注重个人成就,它的具体衡量标准是工作与创造,并且习惯从一个人的工作质量来判断他的品质”[11]。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作为增进人类情操和德性的活动的休闲已然成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当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以后,人类开始从追求生存转向追求自我实现,当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不能完全提供人类实现个性化、创造性和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时,休闲的价值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类面前,越来越多的休闲活动开始取代工作,成为推动人类实现自身潜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幸福的本质,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阐述也表达了休闲对于人类幸福的重要价值。一般认为,马克思的论著中以隐喻的方式用自由时间一词阐述了休闲理论,自由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12]282。“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12]281。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类在自由时间内所从事的活动既包括简单的娱乐休息活动,又包括复杂的、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较高级活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能够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85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休闲理论可以看出,人们只有在自由时间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幸福,幸福存在于休闲之中。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休闲和劳动的界限基本消失,每个人从事的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也正逐步向马克思的设想推进。休闲不仅仅是缓解工作压力、愉悦心情的重要方式,而是正逐渐成为取代工作、获得幸福的重要源泉。西方学者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发现,休闲在影响个体幸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3],作为幸福源泉的休闲比收入和健康更重要[14]。当代西方休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罗伯特·斯特宾斯根据西方社会的休闲习惯把休闲分成三大类,即随意休闲(casual leisure)、项目式休闲(project-based leisure)以 及 深 度 休 闲(serious leisure),其中深度休闲不同于看电视、散步等随意休闲方式,深度休闲是一种需要一定技能、知识和经验,并且具有一定复杂性和挑战性的活动。随意休闲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快乐,能够满足人们浅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但长期从事,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如个体容易形成酗酒、药物成瘾等不良嗜好,甚至引发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随意休闲带来的快乐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幸福。深度休闲则不同,深度休闲在给参与者带来快乐的同时,能够使参与者获得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并且形成强烈的社会归属感[15]。斯特宾斯认为积极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能在一定种类的工作和休闲中呈现[16]。一定种类的工作如斯特宾斯提到的职业奉献(occupational devotion),由于是劳动者发自内心喜爱的职业,所以能够使劳动者深刻地体验到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而休闲尤其是深度休闲是在自由时间内从事的活动,是人们根据内在需要并自愿选择参与的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活动。在休闲时间里,人们可以摆脱各种束缚和压力,自由地、有效地发挥个人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深度休闲体验是一种需要技巧、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人们通过这种富有创造性和价值的实践活动,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能,从而实现自我。我国学者马惠娣认为通过休闲促使人对生活(生命)进行思索,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成熟,使人真正地走向自由[17]。因此,当个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充分施展的时候,个体幸福感是最强烈的。这大概正是富兰克林所说的实现人类潜能的幸福。可以说,休闲是人们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那些拥有大量休闲资源的人最幸福[18]。
四、结语
古希腊的哲人把幸福作德性的理解,休闲只是有闲阶级增进信仰的的思想活动,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则把幸福当作简单的快乐来加以估算。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拥有的自由时间相当有限,而且有限的自由时间也只是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我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在当代社会,人们对休闲和幸福有了更为通俗实用的理解。金钱的富有、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愉悦等能带来一定的快乐,工作的成功被视为幸福的重要来源,相对比而言,休闲只是工作的“补偿”并且常常与娱乐、休息、放松等术语相提并论。当人类进入贝尔所讲的后工业社会,闲暇时间越来越充沛时,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生存的需要,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化的生活、自我的实现,感官层次的满足已然不能成为幸福的真正源泉。休闲作为一种自由的活动,不仅具有放松、娱乐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工作和休闲依然存在一定的区别,工作还带有一定强迫性的情况下,工作将获得越来越少的认可,而休闲则体现出更多的价值。人们会尽量选择与工作完全不同的休闲种类,而这种选择是依据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进行的,因此,休闲尤其是深度休闲能够让参与者充分地发挥个人创造性,实现个人的潜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正如斯特宾斯所说:“深度休闲和项目式休闲更有可能带来长久的幸福,尤其是当这两者与随意休闲结合时,将促成最为理想的休闲生活方式”[9]。只有当社会真正发展到工作和休闲的界限消失,工作就是休闲,休闲就是工作,人们所从事的活动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由选择时,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Annette Holba.Philosophical Leisure[M].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2007.
[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Bruno S.Frey.Alois Stutzer.Happiness and Ecomomics:how the Ecom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M].Pri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6]Samuel S.Franklin.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A Good Human Lif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7]江传月.现当代中西方幸福观研究综述[J].学术论坛,2009(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罗伯特·斯特宾斯.休闲与幸福:错综复杂的关系[J].刘慧梅,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10]Robert A.Stebbins.Leis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Bridging the Gap[J].Library Trends,2009,57(4).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1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Miao Wang.Mao Chiu Sunny Wong.Leisure and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evidence from survey date[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11(18).
[14]Luo Lu.Michael Argyle.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s a fun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J].Kaohsiung J Med Sci,1994(10).
[15]Robert A.Stebbins.Serious Leisure:A Conceptual Statement[J].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82,25(2).
[16]Robert A.Stebbins.Happies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Contexts,2010,9(2).
[17]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77.
[18]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等.休闲与生活满意度[M].杜永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