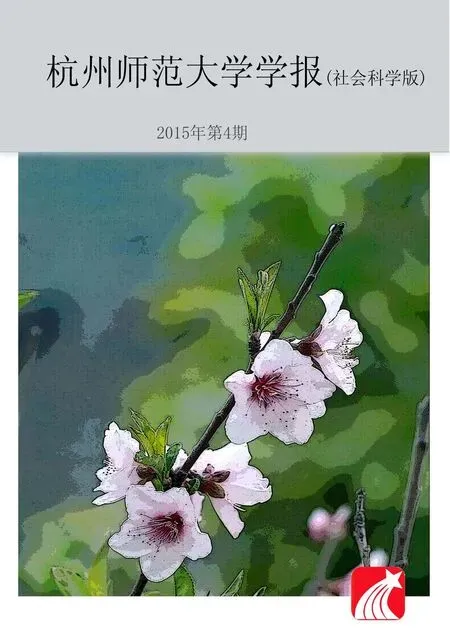陈独秀:有革命家气质的启蒙思想家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陈独秀:有革命家气质的启蒙思想家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五四精神的重要阐释者,陈独秀视伦理觉悟为国人最后之觉悟,形成了从思想文化入手根本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基本路向。他坚信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对儒家纲常名教进行猛烈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抹杀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他以“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强硬态度来推进文学革命,体现出一位具有革命家气质的思想家的魄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以启蒙为手段来达到政治救亡的目的,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政治救亡,更没有脱离当时的实际政治活动。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之放弃了西方的民主主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由于他接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论述,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待民主问题,将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并致力于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多数人的民主。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启蒙
陈独秀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五四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和重要阐释者,但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始终伴随着他的一生,甚至在他逝世后依然争论不休。在《新青年》创刊10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会发问:陈独秀为什么要创办《青年杂志》而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为什么视伦理觉悟为国人最后之觉悟?他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孔批儒?他这种激烈的反孔态度是否就是全盘反传统?他从政治运动转向了文化启蒙,但为什么后来又从思想启蒙再次走上了政治救亡之路?他为什么放弃了自由民主理念而主张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既是以往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也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拟以“问题”为中心,站在历史的高处和事后反思的立场上,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重新进行点评,力图对其作出自己的阐释。
一、陈独秀为什么要发起新文化运动
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本来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但因广大民众没有觉醒,民主制度缺乏社会根基,少数人的革命只是改换了政权的名号,民主制度之实杳不可得。用陈独秀的说法就是:“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1](P.2)当时中国的先觉分子认识到,徒有共和国的名号是没有用的。要使中国真正从专制、落后、腐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走上民主、富强之路,必须使中国国民之大多数,清除其头脑中的专制主义余毒,树立民主共和思想。陈独秀指出,中国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故“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2](P.2)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欲以思想启蒙的方式为政治变革创造条件和基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实际上是要走一条法国式的启蒙主义道路。这种思想启蒙的思路,在稍前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时期开始显露,并且以陈独秀在《甲寅》第4期上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为代表。陈氏在这篇政论文中批评了国人只有传统的“忠君爱国”的盲目“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揭露北洋政府“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残民的活动,得出了“其欲保存恶国家哉,实欲以保存恶政府”,而“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骇人论断。这些言论表明,陈独秀开始思索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近代西方人那样的“自觉心”问题。其思索后得到的答案是: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掀起一场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培植国人的现代思想,才能使民主共和国有可靠的思想基础。这个答案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初步提出,在随后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九一六》等文中给予明确阐释。他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P.4)
陈氏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三个时期所进行的描述,大体符合西方文明输入中国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西方文明从器物层次逐渐深化为精神层次的输入中国的进程,也表明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飞跃。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缺少文化思想上的革命:“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3](P.1)伦理的觉悟是比政治觉悟更深的层次,只有伦理的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提出的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的深刻内涵:中国政治的变革必须从思想文化的变革开始。从思想文化入手根本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是其“伦理觉悟”的基本路向。这个思路是新颖而深刻的。辛亥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儒家伦理思想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宣教儒家伦理的旧文学,灌输这个思想并教育青年只知个人升官发财的旧教育,和教人认天命、不抗争、迷信鬼神的佛老庄哲学,仍然禁锢着国人的精神。在传统旧伦理、旧教育、旧思想、旧文学充斥的国度里,是难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陈独秀已经认识到,只有进行思想启蒙,唤醒被禁锢在旧伦理思想中的广大民众,将其培养成有独立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权利的真正的人,才能建立起真正自由独立的现代国家。
二、陈独秀为什么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具有“自觉心”的国民应该具备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4](P.1)故这六条标准首先是新时代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其基本精神就是“科学”与“人权”。用陈氏的话说就是:“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P.6)在他看来,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中国者,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起科学与人权两面大旗,为新文化运动定下了基调,为创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确定了目标。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演进的历程后会发现,由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被迫进行的,并在较长时间内困扰于古今、新旧、中西等纠缠不清的文化纷争中,所以,国人在追求近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构成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准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陈独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形成了民主、科学、人权、理性及个性解放等新文化准则,将“民主与科学”确定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他公开宣布将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作为建构中国新文化的核心:“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5](P.2)陈独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并导致了中国文化结构核心价值的根本变化:由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转变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三、陈独秀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孔批儒
陈独秀先后发表《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文,严厉批驳康有为的国教运动及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在反孔批儒运动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陈独秀反孔批儒,首先是针对孔教会的尊孔活动而来的。其云:“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6](P.4)他从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均提倡儒学、鼓吹尊孔的事实中看到孔教与帝制的密切关联,认识到“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2](P.3)
但陈独秀的反孔批儒的根本原因,是坚信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树立起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价值观,必然对处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进行猛烈批判。他在《宪法与孔教》中分析了作为“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的孔教与根据“欧洲法制之精神”制订的宪法之间的矛盾,指出将“尊孔”条文载入宪法的荒谬。他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3](P.1)他认为,儒学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故为了倡导民主与科学,必须批判专制迷信及封建礼教:“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P.5)他公开申明:“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7](P.11)
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的激烈批判,并不意味着抹杀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也不是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全盘反传统”,更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陈独秀在与吴虞、常乃德、俞颂华等人的通信中,就反孔批儒的理由、意图展开过较详尽的说明。尽管陈独秀批孔时讲了一些“偏激”、“极端”的话,但是其本意是清楚的:为了建立一个欧化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就必须抛弃作为封建专制政体思想基础的孔子之道,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正因如此,陈独秀并不赞同钱玄同之偏激意见:“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5](P.2)
四、陈独秀为什么要以“不容他人之匡正”态度推进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具有深远影响并收效最显著者,当推文学革命。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变革,以及使用标点符号等,使中国在文字语言和文学以及书写与印刷格式上发生重大变革,取得了突出成绩。陈独秀以“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强硬态度来推进文学革命,体现出一位具有革命家气质的思想家的魄力,但也由此受到不少人非议和诋诟。
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后,约请留学美国的胡适撰稿。1916年8月21日,胡适致函给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这些主张在当时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震撼威力,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并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8](P.3)
胡适立即撰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阅后“快慰无似”,立即安排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陈独秀考虑到当时旧文化传统势力之巨大,“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而胡适的八条主张尚有不彻底之处,故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助威并弥补其不足,恢复其“文学革命”气势。他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宣告:“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9](P.4)
这样,陈独秀将胡适的“文学改良”上升到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1917年4月9日,胡适致函陈独秀:“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中国人士之讨论,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他表示:对于自己的“八事”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的讨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不赞同陈独秀那种“不容他人之匡正”之武断态度。但具有革命家气质的陈独秀态度毅然坚定。他立即致函胡适解释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0](P.4)
从陈独秀与胡适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两人在五四文学运动中的风格差异:“持重”与“激进”。胡适的风格是刚柔相济、稳扎稳打;而陈独秀则是猛冲猛打、一往无前。胡适主张新文学运动需要一个“讨论与尝试”时期,通过自由讨论取得进展;而陈独秀则主张以激烈的方式立即推行,决不容因无谓的讨论而延误。在陈独秀看来,改良中国文学是无须讨论的,讨论只会容许反对者的抗拒而无益于文学改良。故其解释说:“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10](P.6)这是陈独秀坚持“不容他人之匡正”态度之目的所在。而正是这种坚定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全国性的气势磅礴的文学革命运动勃然兴起,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显然与陈独秀这种决断的态度和革命家的气质密切相关。
五、陈独秀在思想启蒙时忘记政治救亡了吗
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伦理学说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因为在他看来,“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11](P.3)这实际上是把个人解放与国家振兴联系起来了,是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并重,将思想启蒙作为变革政治的手段。
正因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启蒙与救亡是并重的,故其批判旧文化是从当时中国的危亡形势出发,紧扣近代以来的政治救亡主题。如强调改造国民性重要时,他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弥乱源,为国家增实力。”[12](P.2)陈独秀是在民初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才独辟蹊径,企图从文化革命着手,寻找新的救亡之路,所以,他从事文化运动的目标仍是要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为此,他创办《新青年》之后,并没有停止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他在《新青年》上专门开辟了“国内大事记”等栏目,先后发表了《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对德外交》《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评议时政的文章,就是关注现实政治的明证。
1918年7月,陈独秀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为题,开宗明义纠正人们对《新青年》不谈政治方针的误解:“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3](P.1)由此可见,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以启蒙为手段来达到政治救亡的目的。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从来没有忘记过政治救亡,更没有脱离当时的实际政治活动。
欧战结束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使陈独秀对政治产生了更大兴趣。《新青年》作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大型文化月刊,难以适应及时评论现实政治问题的需要,陈独秀遂产生了创办新政治刊物的想法。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在自己的文科学长办公室里约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等人,决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12月22日,《每周评论》正式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陈独秀阐明该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提出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14]他随后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5]《每周评论》是介绍和评论国内外政情的政论性刊物,是陈独秀及其新文化阵营谈论政治的重要阵地。它将言论主题锁定在当时全国注目的焦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陈独秀不断发出鲜明而强烈的政见,支持学生爱国行动。5月11日,他列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中日军事协定到参战借款等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指向三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5月18日,他发表文章呼吁:“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更绝对的万万不能批评学生和政客的不是。”[16]他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随后告诫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文明。”[17]从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就成为五四青年的座右铭。6月9日,为了实践“出了研究室”不怕“入监狱”的诺言,陈独秀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亲自到闹市区向群众散发,不幸被暗探逮捕。可见,陈独秀在进行思想启蒙时并没有忘记政治救亡。他先是以《新青年》为阵地,唤醒了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觉悟,继而以《每周评论》为阵地,提出了推进政治活动的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
六、陈独秀为什么信仰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的陈独秀笃信18世纪法国民主主义启蒙思想。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为什么放弃了西方民主主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呢?
陈独秀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其思想转变与被捕后在狱中所作的深入思考有关。他在出狱后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中,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是耶稣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并称赞“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稣是穷人底朋友”。[18](P.22)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正是从基督教中发现了以“穷人”为主体的、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和阶级调和的平等博爱宽恕精神,故出狱后一度信仰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并放弃了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他在《新青年》上宣布《新青年》同人意见时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还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19](PP.1-2)正因如此,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支持王光祈等人组织互助团进行工读互助试验。但互助团试验的失败,促进了陈独秀从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
陈独秀之所以要接受“Bolsheviki”及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接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论述。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20](P.630)而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20](P.634)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阐述,引起了陈独秀的格外重视和共鸣。他认为,18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近代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20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新兴无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故资产阶级民主远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更符合自由平等和民意,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打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21](P.4)他还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22](P.8)他还针对有人用“德谟克拉西和自由”口头禅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公开责问:“(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23](P.9)这样,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毅然接受了列宁主义,以阶级分析方法看待民主问题,将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并致力于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多数人的民主,逐步从一个信仰“德谟克拉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1916,1(6).
[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J].新青年,1917,3(3).
[3]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1916,2(3).
[4]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
[5]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辨书[J].新青年,1919,6(1).
[6]陈独秀.复辟与尊孔[J].新青年,1917,3(6).
[7]陈独秀,佩剑青年.通信[J].新青年,1917,3(1).
[8]陈独秀,胡适.通信[J].新青年,1916,2(2).
[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2(6).
[10]陈独秀,胡适.通信[J].新青年,1917,3(3).
[11]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916,1(5).
[12]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J].新青年,1916,2(2).
[13]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1918,5(1).
[14]陈独秀.发刊词[N].每周评论,1918-12-22.
[15]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J].每周评论,1918-12-29.
[16]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J].每周评论,1919-05-18.
[17]只眼.研究室与监狱[J].每周评论,1919-05-25.
[18]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J].新青年,1920,7(3).
[19]陈独秀.本志宣言[J].新青年,1920,7(1).
[2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J].新青年,1920,8(4).
[22]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1920,8(1).
[23]陈独秀,柯庆施.通信[J].新青年,1920,8(3).
(责任编辑:吴芳)
文学研究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研究
主持人的话:优秀的文学家/批评家大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在18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中,这种冲动烙上了一种特殊的时代印记,即群起为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冲击而濒于瓦解的传统共同体寻求出路,并描绘出理想的共同体愿景,而在其背后,不乏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焦虑,为化解焦虑而谋求对策。
本栏目的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英国文学家/批评家们是如何发挥想象来构建共同体的。他们所在的时代,是“共同体观念”(the idea of community)空前生发的年代。由于快速“进步”给社会带来了迷茫,人们对共同体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作为对这一需求的回应,欧洲各国相继涌现了一批探索并宣扬共同体观念的仁人志士。正如凡宁斯卡娅所说,“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家集权化的欧洲,出现了一些最激烈地提倡共同体观念的人,如英国的卡莱尔和罗斯金、德国的滕尼斯和韦伯、法国的杜尔凯姆”。作为对凡宁斯卡娅的研究成果的补充,本栏目的论述聚焦于华兹华斯、切斯特顿、利维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共同体”。那个时代由于得益于后者的创作和著述,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语境,其影响日益深远。
上述作家/批评家想象共同体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有着相似的价值诉求。例如,他们都意识到共同体的建设首先要从破除对工具理性/机械主义的迷信入手。又如,在他们的共同体蓝图中,个人与社会、传统与进步、知识与价值、科学与信仰、情感与理智、道德伦理与审美趣味、锐意改革与文化守成、引领文化发展的少数人与受过教育的民众之间都呈现出辩证、和谐的关系。再如,在如何维系共同体这一问题上,他们也不乏共识:都把希望寄托于共同的信念、共通的思想范型、共有的习惯、文化记忆和情感结构,以及共享的知识、艺术、伦理和风俗等方面。
(殷企平)
Chen Duxiu: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 Full of Revolutionary Temperament
ZUO Yu-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As the promoter of New Culture and the interpreter of spirits of May Fourth Movement, Chen Duxiu treated moral awareness as national ultimate enlightenment, which developed his primary way to solve the political problem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Chen believed that the Confucianism was not adapted to the modern life, and criticized strongly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However, Chen Duxiu did not wipe ou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He took uncompromising attitudes to promote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showing his courage of being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full of revolutionary temperament, which got him a good result. His primary thinking of initiating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to achieve political salvation by the enlightenment means. Therefore, he never forgot political salvation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divorced himself from political activities. Chen Duxiu gave up democratism and believed in Marxism in the lat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ain reason of which was that he had accepted the exposition of Lenin on proletarian democracy. According to Lenin’s view, democracy could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class analysis and divided into bourgeois democracy and proletarian democracy, in which the true democracy and the wider democracy—the democracy for the proletarian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broad masses should be ultimately pursued.
Key words:Chen Duxiu; theNewYouth;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nlightenmen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的研究成果。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6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53-06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殷企平(1955-),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28 2015-05-19
主题研讨二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专辑